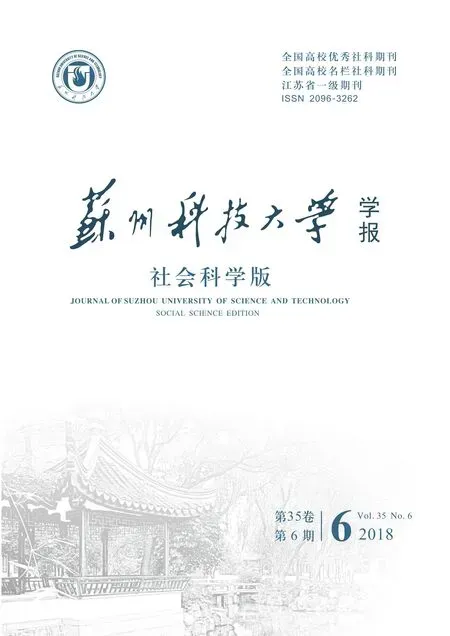萨摩亚的妇女、文化与政治参与*
潘尼罗培·司格埃菲尔 米亚赛娜·玛瑞迪夫 鲁塔·费迪-辛克莱,著 曲 升,译
(1.萨摩亚国立大学 萨摩亚研究中心,阿皮亚 WS1622;2.聊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山东 聊城 252000)
一、导 言
就其法律与习俗的杂糅性而言,萨摩亚的选举制度堪称独一无二。一院制国会每5年举行一次选举,而只有马塔伊(matai,拥有大家庭授予的头衔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1962年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马塔伊可以投票;直到1990年一场公投之后,普选制才得以实行,所有年龄到达21岁的公民不论性别均拥有了选举权。国会49个议席——47个选区席位,2个城市席位——均由选民直选产生。
从1962年萨摩亚获得独立起,在49名议员组成的国会中,女性议员席位从未超过5个,尽管捐助者资助有选前活动,鼓励并帮助妇女参选。正如K.贝克尔(K. Baker)所指出的:“就女性政治上未被充分代表的问题而言,不敢断言世界上还有哪个地区比太平洋岛屿地区更严重;该地区女性议员加起来仅有区区30名,仅占议员总数的6.1%。”[1]近来学界对于太平洋岛国此种普遍现象的学术分析和解释[注]P. Soaki, “Casting Her Vote: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olomon Islands”, in M. Macintyre and C. Spark(eds.),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in Melanesia,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95-114; B. Julien and K. Baker, Improving the Electoral Chances of Pacific Women through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A synthesi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Centr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State Society and Governance in Melanesia Program, AUU; K. Baker , “Great Expectations: Gender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16, pp.1-27; P. Chattier, “Women in the House (of Parliament) in Fiji: What’s Gender Got to Do with It?”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No. 104, pp. 177-188; A. Molotii, K. Baker, and J. Corbett, “Women’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Temporary Special Measures in Tuvalu”, ANU In Brief : 2014, No. 17, http:∥ssgm.bellschool.anu.edu.au/.,“文化”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因素。例如,麦克里奥德(MacLeod)在其关于太平洋妇女领导地位的泛区域研究中发现:“社会组织以及性别化的文化观念和习俗,构成了妇女在一切领域参与的巨大障碍。”[2]
本文以萨摩亚为个案,意在揭示社会组织、特定宗教教义以及性别化的文化观念和习俗如何限制了妇女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进程的机会。这些特别限制是萨摩亚所独有的。从区域层面对太平洋诸岛的相关情况进行概括,难免对一些显著的差异挂一漏万。比如,萨摩亚是一个单一文化社会,这与美拉尼西亚国家不同。它不存在生息于外岛的孤立的农村社群,这与其他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国不同。在萨摩亚中央控制的稳定政治体系中,为国家所承认的乡村政府具有一席之地[3-4],同时,在文化和经济上又深受邻国美属萨摩亚以及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庞大的萨摩亚移民社群影响。在性别问题上,太平洋岛屿的相同点在于,绝大多数太平洋岛国从宪法上对传统文化进行肯定,尽管相关规定可能模棱两可,但足以抵制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规范和价值观的框定。
如果基于教育和就业等指标来衡量性别平等状况,萨摩亚甚至可以与许多“发达”国家相媲美。萨摩亚女孩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水平要超过同龄男孩。[5]在专业岗位中,妇女的比率为50.6%,略高于男性;而在技术性岗位中,妇女的比率为45.2%,比男性略低一点儿。妇女占据了管理性工作36.3%的岗位[6]80,并构成了目前商业在岗人员的47.8%。[7]
萨摩亚政治领域内的性别不平等比较严重。以国会女性议员比率的全球分类标准衡量,萨摩亚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59位[8],比其他太平洋岛国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在这些国家,妇女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就业不匹配现象,要比萨摩亚更为明显。[2,9-10]1962年独立以来的58年间(新一届议会至2020年届满——译者注),总共仅有21位女性当选议员,其中又有3人的选举胜利被选举上诉所推翻,因此实际上只有18位女性真正坐到了国会议席上。如前所述,只有登记的马塔伊才有资格进入国会。不过,萨摩亚的马塔伊数量不在少数。据2011年人口普查,萨摩亚有16 787人拥有马塔伊头衔,其中女性仅占10.5%。2016年选举中,164名候选人中妇女为24名,最终仅有4名女性当选议员。这一结果未能超过此前的选举,只是根据最近修订的选举法,第5名女性被指定为议员,从而使议员的总量达到50名。下文对此将有所解释。
政治上的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萨摩亚乡村生活中性别社会角色分工,以及萨摩亚选举制度特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将从地方和国家层面对妇女政治参与的障碍加以分析,所用数据来自萨摩亚国立大学萨摩亚研究中心进行的两项研究。一项研究的主题是乡村政府中妇女的参与度[11],另一项则考察了24名参与2016年选举的妇女的经验[12]。
二、鼓励妇女政治参与的平权措施
1985年,萨摩亚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并从那时起,陆续提交了5份进展报告。根据2012年进展报告,联合国CEDAW委员会做出了这样的评论:“陈规陋习、传统糟粕以及关于女性和男性角色、责任和身份根深蒂固的成见,限制了国家和政党消除这些歧视行为的努力。”2016年,萨摩亚政府向CEDAW委员会报告说,关于性别角色的传统态度构成了萨摩亚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生活的主要障碍。[13]
萨摩亚政府对本国落实CEDAW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三(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方面存在的差距有着清醒认识。千年发展目标三的指标之一是妇女占据一定的议会席位。此外,2015年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五则宣布应“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并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策层的平等机会”。可问题在于,萨摩亚政府能否在不触动男性马塔伊主导政治根基的前提下,在解决妇女政治参与度低的难题上有所作为。另外一个顾虑源于1962年《萨摩亚独立国宪法》(TheConstitutionoftheIndependentStateofSamoa)有关条款。尽管宪法第13条明文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但第100条却又规定:“马塔伊头衔应根据萨摩亚的惯例予以保留,并依据与这些惯例相关的法律加以运用。”
2013年,政府决定对《选举法》进行适当改革,以表明正在采取平权措施以推动妇女参与国家政府。这一改革的目的在于确保国会中妇女议席不少于10%;为此所做的安排是,如果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不足5名,便增加国会席位,专门留给那些尽管未能赢得竞选但得票领先的女性候选人,直至国会中女性议员人数达到5位。但这一旨在实现选举公平的法律并未建议萨摩亚去依靠政党预选出同等数量的女性和男性候选人,因为政党不愿冒风险在每个选区仅选出一名候选人。2016年选举中,萨摩亚两大政党——人权保护党和为萨摩亚服务党(Tautua Sāmoa Party)均在普选中有自己的候选人,尽管许多候选人已正式宣布属于同一党派,却仍然为拉选票而竞争不已。
在2016年选举中,有4名妇女赢得席位,而根据选举法“10%条款”,应增加一位女性候选人去占据一个议席,也就是成为第5个女性议员。为此,国会议员数量从49人调升为50人。“10%条款”的主要动力并非源自公众情绪,而是CEDAW、千年发展目标三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五框架下,萨摩亚的国际人权承诺。一项关于2016年选举的研究报告[注]这项研究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萨摩亚国立大学、萨摩亚选举委员会办公室、萨摩亚领导者(Leadership Samoa)与萨摩亚非政府组织总会合作完成。显示:不论男性选民还是女性选民,均缺乏让更多妇女代表出现在国会的热情。[1]7-10该报告中有如下一些受访选民的言论:
从竞选广告和电视节目中不难发现,妇女候选人的表现良莠不齐,有的差强人意,另外一些则准备不足(21—29岁间女性选民)。
《圣经》并未告诉我们国会需要更多的妇女存在;国会中不应该有妇女存在,我们不应该有女性议员;她们会分裂国会(30—59岁间女性选民)。
只有拥有高级别头衔且出身政治世家的妇女才可以参加选举……政治是肮脏的,妇女不应该成为某某议员(姓名省略)所热衷的黄色玩笑的对象(60岁以上女性选民)。
三、争取妇女的竞选运动
鼓励妇女竞选国会议员的努力始于2005年,最早由萨摩亚妇女国家委员会在2006年选举前成立的“因纳伊拉乌妇女领袖网络”(the Inailau Women’s Leadership Network)[注]在萨摩亚语中,Inailua意为“屋顶”。该词源于一个萨摩亚故事,传说一帮男人无力建成一间由岩石堆砌屋顶的房子,而妇女则最终完成了这一艰难任务。可见,Inailua颇有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之意,这可能也是该组织以此命名的寓意所在。译者注。发起。[3]不过,这些努力并未换来女性议员数量的显著增长,22名女性候选人中,仅有5人当选议员。这一成绩并未超过1996年,当年选举中也有5名女性议员产生。
2016年选举前,一场经费充足的选举运动“提高萨摩亚妇女政治参与度”(Increas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Sāmoa,简称IPPWS)被发动起来,以鼓励更多妇女登记为候选人。该运动的主要赞助方是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作为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和联合国妇女署(为争取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而成立的机构)共同项目的一部分,并得到当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基于更多妇女懂得如何竞选造势,便会有更多妇女当选议员,妇女越能有效运用现代通信手段竞选,便越有可能赢得更多选票的假设,IPPWS将妇女参与选举的意识激发、教育和能力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并在选前为政党提供信息和培训。该运动的总体方案是多媒体造势,即通过利用电视、无线广播网,以及进入地方报纸和社交媒体平台等,向公众解释和宣传“10%条款”、登记投票的基本程序、当前为打击选举腐败行为(贿赂、操纵)而采取的政策和修改选举法等多方面情况。该运动还以印制宣传册的方式,为候选人提供某些帮助,但不提供竞选经费支持,并为所有当选议员提供与性别相关的预算和立法事务的选后辅导。
IPPWS的特色活动之一,是电台节目“谈选举”(Fa’asōa I Le Pālota),对每周选情进行回顾,重点是推动妇女的政治参与。节目由旨在培养妇女领袖和推动妇女从政的非政府组织“觉醒的萨摩亚”(Sāmoa Ala Mai)主持,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间,由两家电台同时播出。节目涵盖了宪法修正案、选民登记意识、提升妇女领导力、鼓励妇女竞选公职等话题,为女性候选人提供推动竞选活动的平台。24名女性候选人中,超过一半的人曾接受过该节目访谈。IPPWS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媒体报导,其中包括对萨摩亚国立大学新闻系学生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2015年8月组织的以“性别敏感的选举”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的报导。
萨摩亚非政府组织总会(the Samoa Umbrella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参与了一个研讨会,以引领社区进一步介入选民登记和投票、欣赏妇女的领导角色、理解宪法修正和近期选举法重大修改等重要事务。培训人员深入全国农村(乌波卢岛和萨瓦伊岛共有30个村庄)和城市社区,为全国选举做准备动员,包括领导力培训,邀请来自选举委员会、萨摩亚人权学会以及联合国发展署驻萨摩亚办事处等机构的嘉宾为培训助力。另一项行动是“政治中的妇女圆桌会”,就妇女为何应该参与萨摩亚政治生活展开研讨。作为社区拓展战略的一部分,IPPWS 与萨摩亚国立大学萨摩亚研究中心结成伙伴,以“政治中的妇女”为课题,共同推出了4期圆桌讨论。
四、妇女候选人2016年选举的经验
尽管有上述受到资助的竞选活动,但妇女参选的最终结果却令人失望,她们赢得的席位并未超过上届选举。2016年选举中,共有24位妇女候选人在4个选区竞选,4人正式当选,还有1人是根据《选举法》平权条款被指定为议员。这5人当中,有3人为在任议员,她们是菲亚美·娜奥米·马塔阿法(Fiame Naomi Mataafa)、伽陶鲁爱法安娜·阿玛汤阿·阿丽桑娜·盖德洛(Gatoloaifa’ana Amataga Alesana Gidlow)及法伊玛鲁托亚·吉卡·斯塔沃斯·阿卡乌(Faimalotoa Kika Stowers Ah Kau)。菲亚美和伽陶鲁爱法安娜都是连选连任,且均为前总理之女。法伊玛鲁托亚是因某在任议员逝世而在2014年补选中胜出。菲亚美身为部长,长期供职于内阁;伽陶鲁爱法安娜则在上届国会期间担任副部长,更早曾占据国会某一正部级职位。阿丽依玛雷玛努·阿鲁法·图乌阿乌(Ali’imalemanu Alofa Tuuau)为新当选议员,而法阿乌鲁萨乌·洛萨·塔菲-斯塔沃斯(Fa’aulusau Rosa Duffy-Stowers)则是根据《选举法》新修订的“10%条款”被指定为议员。通过正式选举赢得议席的4位女性,均精心策划竞选策略,并确立了良好票仓基础。3位在任议员不仅有授予她们马塔伊头衔的村庄(也是她们的选区所在)为大本营,在城区也有着良好经营。她们均曾深入自己村庄的教堂,其中二人还是教堂执事。此外,她们还与自己选区的前议员过从甚密。
与这些胜选者相似,未能胜选的19位候选人的条件也相当不错。她们几乎均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在商业部门或专业职位从业的背景。其中,几乎常年在其选区村庄居住的仅有6人;其他候选人则大部分居住在首都阿皮亚,尽管她们声称自己经常探视自己的村庄,并在那里有自己的家庭。仅有1位候选人来自一个有村庄不承认妇女拥有马塔伊头衔的选区。
选举结束后对角逐2016年选举的24位女性马塔伊的采访[12]显示,她们大都认为IPPWS对选举结果影响不大。尽管那些参加过IPPWS举办的研讨会的候选人承认这些研讨会的激励作用,但她们同时指出,妇女候选人数量的增加(相较于此前的多次选举)并未显著提高当选人的数量。她们大都认为,来自现代民主国家的范例和竞选策略不能有效运用于萨摩亚以传统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一些人还认为,把“妇女问题”过多地暴露于那些习惯于男性领导的选民,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妇女进入国会的意义所在。[1]7-10另一个为许多候选人所提及的共性话题是,她们认为女性选民并不支持妇女候选人,原因或在于女性选民“嫉妒”妇女候选人[1]20-21,或在于生活于丈夫家庭和村庄的妇女认为有义务根据其丈夫或丈夫家庭的选择投票。不过,所有候选人均表示她们相信,随着更多妇女进入国会表达妇女的观点和关切,萨摩亚将会从中受益。她们还普遍提及妇女所扮演的和平缔造者角色,以及妇女作为母亲的真知灼见。
约半数的未成功候选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照反贿选法律法规行事反而削弱了她们赢得议席的机会。绝大多数竞选失败者表示,成功的候选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未遵守反贿选法律法规,金钱和礼品要比任何其他竞选手段更能打动选民。她们评论说,选民希望候选人为他们提供往返选民登记处和投票点的交通,还希望在这些场合能被提供食物、付给金钱。还有几个人提到,资助的资金若能用到对选民的面对面教育上,而不是妇女候选人培训和意识激发上,则其效果会更好。在她们看来,选民教育确有必要,人民将因此而理解议会民主的意义所在。此外,政府相关培训计划的经费应来源于税收或援助,而不应来自政治党派或政治家的口袋。这些候选人几乎一致表示,若无相关教育,人民就不会充分理解国会的运作以及政府优先事项决策的程序。
绝大多数候选人表示,通过参加竞选她们已经体会到介入当地的重要性,如果不是真正生活在村庄,那么也要经常而长期地参与当地活动、村庄议事会和乡村教堂,并且在选区一个或多个村庄中拥有支持自己的大家庭。许多候选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很少有女性马塔伊进入村庄议事会(fono),而那些进入者则拥有了使自己成为社群知名决策者的良好机会。成功的候选人同意这样的说法:那些希望介入公共生活的妇女需要获得马塔伊地位和在乡村议事会发言权的激励。她们的这种观点总体上证实了萨摩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被排除在乡村一级决策圈之外,是妇女很少被选进国会的主要原因。[11]胜选的两位候选人认为,一个渴望成为国会议员的人,应该拥有马塔伊头衔而且是地位显贵、资历更老的马塔伊头衔——因为资历老、地位高意味着名望和更大影响力。一位败选的候选人也提到了资历的重要性。她说自己虽为马塔伊却不能参加乡村议事会,没有发言权,但一位资深马塔伊则有此特权。胜选的候选人还表示,除了良好地位资格和背景外,选举成功还有赖于长期规划。她们指出,一名候选人至少需要准备5年,也就是一个竞选周期,以自己的大度以及参与村庄、社区和教会事务的方式获得选区支持,塑造自己作为未来乡村和社区知名领导人的形象。
五、习俗障碍
在地方一级,萨摩亚的乡村治理是“习俗型的”(customary)。它发展于19世纪萨摩亚大规模转向基督教信仰之后。[14]这一新信仰扫除了古老酋长制度的最上层高级酋长阿里依(ali’i)——在这一古老制度里,高级酋长阿里依被奉为神的后裔——一种新型“马塔伊制度”(fa’amatai)出现了。19世纪期间,随着萨摩亚人皈依基督教,世俗政治的领导方式逐渐演变为现代马塔伊制度。在现代马塔伊制度里,旧的等级森严的世袭制对于领导能力的重要性大为削弱,而成就、财富和各种专门知识的重要性则日益凸显。[15]
萨摩亚有这样一条谚语 e sui faiga ae tumau fa’avae,其大意为“风俗易改,根性难移”。在许多人眼中,现代马塔伊制度就有着这种根性,它没有变化,也永远不会改变——尽管麦雷西亚和柴科佐夫(Tcherkezoff)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4-15]在萨摩亚,一旦提及两性平等问题,最司空见惯的回答是:萨摩亚并不存在此问题;对姐妹的尊重、兄妹姐弟生死相助约定、源远流长的贵族妇女的传说,都是妇女备受尊重的例证。轶事般的证据表明,大多数萨摩亚人不认为存在妇女拥有马塔伊头衔或进入国会的风俗障碍。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如果说拥有头衔的妇女少之又少,那也是因为妇女根本没有成为马塔伊的意愿,进而,立于国会或新选进国会的妇女数量之少实际上反映了妇女自身的选择。假若此说成立,那么追问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便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大量妇女已经显示出在公共服务部门和私营部门担任领导职责之愿望这一事实。
六、女性马塔伊
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萨摩亚常住人口中,16 787人拥有马塔伊头衔,其中妇女占10.5%。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农村马塔伊中仅有5.5%为妇女。[11]许多萨摩亚人相信,1962年萨摩亚独立前的年代里,即便有女性马塔伊,那么其数量也屈指可数。可能随着1960年代教育机会向萨摩亚人开放,女性拥有马塔伊头衔的数量才开始上升。1950年代后期,政府选定的中等学校刚刚建立起来,因此,此时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的萨摩亚人可谓凤毛麟角。此前,外国人的子女或混血城市人口子女是接受这一过渡阶段教育的主体人群。在国家新选定的中学设立高年级教育之前,那些课业优异的学生被送到新西兰的高级中学就读,之后又被送往师范院校、护士学校和大学就读。
在这些获准进入萨摩亚和新西兰中学的学生中,女孩子的数量并不算少;而且,从那时起,各级教育入学人群中的性别差距微乎其微。显然,一般家庭认为对女孩子的教育投资与对男孩子的教育投资一样有意义。就此而言,萨摩亚的风俗对女孩子可谓有利。耕种和捕鱼被认为是男人的工作,而大部分日常养家糊口的杂活,比如从家庭种植园采集食物、饲养家畜、生地锅、砍杂草等,也均由男孩子完成。女孩子则被希望承担起大部分家务以及少量户外劳作,如修剪花园、清扫落叶等。送女孩子入学并不会造成养家劳力的锐减,况且许多小学离村庄很近。因此,女孩子接受教育的障碍少之又少。教育机会成功打开了妇女在现代经济部门、公共服务部门、商业和专业岗位就业数量不断攀升的大门。
1978年接受采访的10位女性马塔伊说,她们属于第一批获得奖学金从而进入中学、大学或海外培训学院的萨摩亚人。其中,1人成为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萨摩亚第一人;2人获得硕士学位;5人从新西兰拿到了中等以上教育毕业证书。1人还是萨摩亚妇女国家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国会议员,后任萨摩亚驻新西兰高级专员。这批女性中的多位被其家庭授予马塔伊头衔,以表彰她们的成就。她们很可能是第一批登记为马塔伊的妇女,尽管这一点并不能从当时的头衔登记得到证实,因为头衔拥有者的性别信息并未记录在案。[16]
对于那些1962年以后拥有马塔伊头衔并参与国会选举的妇女而言,教育上的成就仍不失为她们的一个共同特征。2016年选举中的24位妇女候选人几乎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在商业或专业岗位从业的背景。对于男性而言,接受教育的程度仅是他们成为马塔伊的尺度之一,其他一些传统标准,如年龄、资历、领导技艺、公共演说能力等,与教育和收入具有同等重要性。相反,女性则很可能因其高等教育成就和就业收入能力而被授予马塔伊头衔。当然,授予妇女头衔以示表彰,并不必然伴随着她将成为乡村领导的期望。事实上,绝大多数妇女马塔伊头衔是荣誉性的。这意味着,她们可能在其大家庭中有权威,但对村庄施加权威的机会却通常极为有限。头衔伴随着成为领导人的期望的例子十分少见,菲亚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她是自己村庄的领导人,并代表其选区担任议员长达30余年。她是萨摩亚某一高级头衔的唯一拥有者,而且是萨摩亚四位最高头衔拥有者当中三位的直系后代。她的父亲马诺亚法·菲亚美·法乌穆伊娜·木里努乌二世(Mata’afa Fiame Faumuina Mulinuu II)是萨摩亚首任总理(1962—1967),其母亲拉乌鲁·费塔维马雷(La’ulu Fetauimale)则是最早的妇女议员之一。
除了上述成就卓越的女性之外,萨摩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传统价值构成了妇女参与地方政府的种种障碍。马塔伊领导被认为是萨摩亚传统的核心内容。马塔伊头衔包括两类,即酋长(ali’i,阿里依)和代表(tulāfale,图拉法雷)。每个大家庭(‘aiga)都由一个或数个阿里依和图拉法雷所代表。他们是经过一番仪式而被授予某个与其祖先相关的头衔的。传统的村庄(其中,240个被研究过,包括48个大村庄附属的小村庄)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敬语(fa’alupega),以列出历史身份、等级和角色信息的方式,界定马塔伊头衔的等级序列。[11]马塔伊头衔是大家庭的公共物品,需由其男性成员和年长女性成员一致决定,方能授予。颁授仪式通常需要乡村议事会认可,之后,头衔才能合法登记。从20世纪初开始,马塔伊头衔在两个或更多拥有人之间进行分割越发司空见惯。时至今日,颁授仪式通常是表彰多名家庭成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居住在萨摩亚本土的人,也有旅居海外者。并不是所有马塔伊都要履行当地领导角色,除非居住在村庄。许多居住在阿皮亚或海外的人被授予头衔,一是表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的认可;二是确保他们能为本地、海外、城区和乡村的家庭分支贡献财力。
在村落里,每个马塔伊的角色和身份均由相应的敬语加以界定,头衔拥有者会根据他们的等级在会议室落座。由数排立柱支撑房顶的会议室四面敞开,每个立柱代表一个马塔伊头衔,位次不同则等级有别;每个头衔都配有一个座次,以标示马塔伊的不同等级。在两个或更多人拥有相同马塔伊头衔的情况下,该座次则一般留给年长且生活在村落者。每个村落都有作为自己地方政府的议事会(fono)。乡村议事会的收入来源包括集体所有制产业、国家政府津贴,以及罚款和馈赠。议事会决定村落发展优先事项,以及一些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涉及乡村自治与权威、传统权力和法律权力的划分、地方政府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等。国家无权指派地方政府议事会,但却给村长发放津贴(sui o le nu’u)。村长由议事会选举产生,在乡村政府和国家政府之间充当联络人。
马塔伊头衔通常仅授予成年人。萨摩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在由传统规范管理的乡村,所有马塔伊中年龄超过40岁的占92.4%。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绝大多数年龄在40岁以上的乡村男子均为马塔伊。研究还发现,在萨摩亚,大部分乡村领导角色由年长者或中年男子担任。他们当中,55.4%接受过中等层次的教育(绝大多数达到高中教育水平),14.61%完成了中等以上教育,29.43%接受过初级教育。从业构成上,大部分马塔伊(35.61%)为农民,其次为无职业者(20.51%),即因年事已高而处于退休状态。[11]
据报道,有14个乡村议事会不承认由大家庭授予妇女的头衔。[注]最初统计的有此禁忌的村庄为19个,其中5个村庄是否承认妇女马塔伊头衔,调查者没有形成一致结论。[11]有34个村庄虽承认妇女马塔伊,却不允许她们参加乡村议事会会议。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情况,妇女被明确排除在领导角色之外的村庄接近了全国村庄的总数(53个)。其余大部分村庄尽管没有正式阻止女性马塔伊进入议事会,但非正式公约实际上并不鼓励女性马塔伊进入,并最终导致她们主动做出不参加议事会的选择。据说,女性马塔伊不参加议事会的一个人尽皆知的原因,是男性马塔伊常常开一些与性有关的玩笑,而这些玩笑不宜被妇女听到。源于萨摩亚文化的禁忌要求兄妹(姐弟)之间应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o le va tapuia),以示对女性的尊重。
上述研究发现证明,对于萨摩亚妇女而言,正式参与以乡村为基础的政治决策并非易事。在萨摩亚政治中,尽管存在普选制,但乡村马塔伊在选择和推举国会议员上扮演着中心角色。妇女在乡村政府中的低参与度,必然转化为国家政府中女性领导的低数字。因为妇女被总体性排除在领导层之外,所以,能够战胜偏见、发动选民为女性候选人投票的妇女领袖楷模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村庄都存在着一些以聚居区为基础的组织,如居住区计划小组、青年俱乐部或体育运动队;而且,绝大多数村庄中通常有一些小规模非农业行当,如出租车、海滩棚屋、公共交通、商店、缝纫、纺织品印染等。尽管妇女可能领导着一些非传统的社群组织,或拥有自营商业——这并不触犯乡村组织公约,但以妇女为领导的社群组织占不到社群组织总数的一半(38.2%);而妇女拥有的乡村商业比例则更低,仅为34.1%。尽管许多妇女操持着小规模家庭商业,但若该业务在其丈夫的地盘上,她则没有产权。萨摩亚研究中心的研究还发现,乡村和地区学校管委会的任命取决于由马塔伊组成的乡村议事会;80%的学校管委会领导人为男性,女性委员仅占9%。此外,在教育职业中,尽管男性比例明显要低,但38%的乡村小学校长为男性,男性副校长则为20.5%。[11]
妇女在乡村的权威领域
萨摩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许多萨摩亚人相信,在乡村决策中,妇女并未被边缘化,因为她们在女性事务领域(nu’u o tamai’ta’i)拥有权威。[11]在古代萨摩亚,每个与某一头衔相关的村庄都设有一个名为“乡村之女”(aualuma o tama’ita’i)的社团组织。但在基督教化的萨摩亚,这些社团丧失了维持婚姻终身制的传统作用;妇女作为姐妹的身份衰落,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日益受到重视和强化。[16]教会附属委员会通常由执事的妻子而非其姐妹领导,而执事又通常为乡村资深马塔伊。这些附属委员会的职责包括提供食物、筹集善款,以及清扫和装饰教堂等。
在新西兰行政管辖时期(1921—1962年),一种新型乡村妇女组织被引进来,乡村马塔伊的妻子被赋予的新权威是推动聚居区的卫生保健。妇女卫生保健委员会(Komiti Tumama)首先被引入阿皮亚的周边农村,至1930年代,则在萨摩亚农村遍地开花。这些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遵循了当时的风俗习惯,由三个相对分离的身份群体构成,即马塔伊的妻子、村中未婚女子和无头衔者的妻子。根据妇女拥有与其丈夫相应的地位的原则,酋长和代表们的妻子组成了委员会的行政部门;在大多数委员会,最高酋长的妻子任主席,最高代表的妻子任秘书。村庄未婚女子在委员会中拥有专属部门,但在大多数村庄,她们没有正式委员会角色。委员会的“服务”部门则由村庄无头衔男子的妻子组成。不过,至少在一个具有传统重要性的村庄里,这种三方组织结构遭到了未婚女子的抵制,她们拒绝允许任何嫁到村落的妇女加入她们的委员会。[16]
从1930年代起,除了妇女交往组织的传统角色外,现代委员会在乡村治理中也开始发挥多种作用,包括进行日常检查以确保消除蚊虫和其他病害繁殖源、确保每家每户拥有蚊帐和防蝇食物盒,从而保持卫生的生活条件。她们检查乡村游泳池和饮用水水源,在走访公共卫生护士的带领下为新生儿及母亲组织每周一次的例行诊疗,并在许多村庄为小病小患和伤员提供基本的救助服务。[16-18]委员会还要处理由乡村议事会委托处理的当地管理事务,如对违反乡规民约的妇女进行罚款,甚至把她们从委员会中开除。
进入1980年代,委员会的重要性开始衰落。随着交通和通讯的进步、医疗效果的提升和健康检查服务的拓展,再加上供水的现代管道化,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基础的陈旧社群体系开始衰落;相应地,委员会的作用也衰落了。随着海外移民的加速以及汇款回流,居住模式发生了变化。核心家庭开始出现在公路旁大院的现代房舍中。房舍间距离的拉大开始削弱社会中妇女之间的互动。在许多村庄,原来一个村庄共同的委员会分化成多个更小的、以当地为基础的群体。
2004年,政府首次指定乡村妇女代表(Sui Tama’ita’i)并为其发放津贴。她们的津贴是付给村长的一半,尽管她们与村长在记录乡村日志、便利政府与乡村联系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或重复的责任。萨摩亚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许多传统村落仍保留村一级的委员会;在调研进行的那段时间,仅有7个村庄没有活跃的妇女委员会。时至今日,委员会已不再拥有村务上的任何权威,除非有乡村议事会的授权;妇女可能是妇女领袖,但在乡村政府的直接发言权很小;而且,很少有乡村议事会允许妇女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11]
宗教方面的权威
基督教深深地嵌入到了萨摩亚文化当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宪法前言所申明的:“萨摩亚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之上。”最近的宪法修正案(2016年通过的修正案第2条)更加明确了基督教的国家信仰地位。新式夫权制权威源自19世纪主流教派公理会、天主会和卫理会的影响。每个乡村至少拥有一座教堂,通常有多所教堂;而教堂的牧师或传教员均为男性。男性马塔伊,即乡村议事会成员,在这些主流教派的执事或世俗决策者中占有绝对优势。尽管这些教会的成员在乡村政府中没有正式角色,却是乡村家庭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以及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主要代理人。乡村议事会通常每月开会一次,而教会会众却因礼拜祈祷、合唱练习、募集资金以及领导人会议等事项而每周多次集会。
天主教和摩门教不允许授予妇女牧师之圣职,萨摩亚的公理会和卫理会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母教会早已打破此种禁忌(比如,美国公理会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授予妇女圣职,联合卫理会则从1950年代起授予妇女圣职)。萨摩亚公理会和卫理会拒绝授予妇女圣职的理由,是授予妇女圣职违背了“传统”秩序。然而,吊诡的是,这一秩序恰恰是一个世纪前在妇女们的襄助下建立起来的。
1830—1850年间,随着萨摩亚人皈依公理会、卫理会和罗马天主会,基督徒夫妇的关系模式得以确立。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乡村牧师、传教员及他们的妻子始终是这一模式的典范。这一模式的效力和影响力持续至今,并进一步为天主教会所采纳。由于独身天主教神职人员与村庄离群索居,天主教会便效仿其新教同行,训练传教员及其妻子填补他们所在教区的职缺。
婚姻因素
妇女获得马塔伊头衔和担任领导角色的另一大障碍,是已婚妇女应该从其丈夫那里获得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期待。如果婚前分属不同教派,那么婚后,妇女则被要求加入其丈夫所在的教会。对于阿里依或神职人员的妻子以及任何已婚妇女而言,“后室”(faletua)都是一个礼貌而适用的称呼。这一称呼意味着专心于家务。“后室”是提供一日三餐的地方,此处的工作就是管理家庭生活,与“前堂”判然有别。大多数居住在农村的高级马塔伊的居所前都建有一处会客厅,以资会议或其他正式公共场合所需。
已婚妇女乡村生活的角色是确定的。传统价值观念鼓励男女婚嫁到别的村落,而妇女应与丈夫的家庭居住在一起。妻子被期望屈从于丈夫的家庭,服侍丈夫的父母以及生活于此的成年姐妹和兄弟。这其实就是要求妇女侧身“后室”,灶下执炊,操持家务。当一个妇女的丈夫成为马塔伊,且其头衔在当地较为显赫,她本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妇女委员会和教会妇女组织的领导人。女性马塔伊的丈夫则毫无地位可言;女性马塔伊与其没有头衔的丈夫地位上严重失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常现象,因此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妇女应屈从丈夫的社会预期是妇女成为领导的个人志愿的巨大障碍,尽管萨摩亚拥有大量妇女,其能力足以成为其丈夫政治和教会职业的强大后盾。
如果一个男人选择与其妻子的家庭(faiava)共同生活,则其社会地位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屈从性,他同样被要求服务于妻子的亲戚。作为这一类家庭和村庄的女儿,他的妻子的身份注定要高于她选择到男方家庭和村中居住而获得的身份。在此种情形下,对一个妇女而言,要求自己的家庭授予其丈夫一个头衔以缓解其不正常的屈从状态,并满足丈夫地位应高于妻子的公共期许,便不是什么离经叛道之举了。当妇女居住在自己的家庭和村庄,就像许多能力强、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在当地做教师和医护人员一样,她们很少拥有马塔伊头衔。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便有可能相信她们的兄弟拥有要求家庭授予马塔伊头衔的优先权,即便他们受教育程度没有自己高。
一旦丈夫和妻子同为马塔伊,在分配资源相关利益上发生冲突便在所难免。马塔伊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在葬礼或其他一些仪式上代表他或她的家庭答谢其大家庭人脉。马塔伊必须在这些仪式上组织大家庭收集钱财和精美铺席,然后再分配收到的礼品,以示礼尚往来。一旦丈夫和妻子同时承担针对不同大家庭的上述责任,他们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便陡然增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女性马塔伊更倾向于选择孀居、不嫁或嫁给萨摩亚文化体系之外的丈夫。这就是大多数当选议员的妇女或年过50,或未婚,或孀居,或嫁给非萨摩亚人的原因所在。萨摩亚首位女性议员,已故的塔乌拉巴巴·雷阿乌佩佩·法伊马阿拉(Taulapapa Le’aupepe Faima’ala)连任两届议员,但每届所代表的选区却并不相同。她在新西兰接受教育,是被任命为国立医院护士长的第一位萨摩亚人,嫁给了一个居住在城区的具有欧洲血统的商人。在1976年选举中,塔乌拉巴巴与已故的赛娜·安南戴尔(Sina Annandale)一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当选。已故的马塔图莫亚·马伊莫亚昂阿(Matatumua Maimoaga),一个新西兰培养出来的护士,分别在1982年和1991年两度当选国会议员。她嫁给了一个非萨摩亚人,其经历与伽陶鲁爱法安娜极为相似。伽陶鲁爱法安娜身为1982—1997年萨摩亚总理托费拉乌·艾提·阿雷萨那(Tofilau Eti Alesana)之女,2005—2010年任政府部长,2010—2015年任副部长,2016年再度当选议员。已故拉乌鲁·费塔维马雷马乌(La’ulu Fetauimalemau)在1976—1978年担任议员时孀居,她的丈夫则是萨摩亚首任总理马诺亚法·菲亚美·法乌穆伊娜·木里努乌二世。马伊阿瓦·维塞克塔(Maiava Visekota),一位杰出的律师和公民组织领导人,在1996年当选议员时也是孀居。已故伊英阿·苏亚弗雷(I’iga Suafole),一个在新西兰接受过教育的教师,1976年当选议员时为独身。[3]前已述及的菲亚美也是独身,她是首位女性内阁部长,1985年起连续在几届政府任部长。2016年的选举延续了上述历史模式,24位候选人当中已婚妇女仅有8人,孀居、离异和独身者占绝大多数,已婚者当中2人嫁给了非萨摩亚人。
七、结 论
在萨摩亚现代生活领域,许多妇女领导人活跃在商业和公共服务机构;教育和才能成为促进妇女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与此不同,在乡村政府和乡村教会的传统领域,妇女则被视为助手,而非领导人。已婚妇女被要求屈从于丈夫及其家庭、教会和村庄。领导地位被认为是男性的特权,尤其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男性的特权。男子要比妇女——尽管从各方面说,妇女都堪当其才——更可能赢得由男性主导的乡村的支持和地区性领导地位。弗拉恩科尔(Fraenkel)关于选举制度对太平洋诸岛国议会女性代表权之影响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悖论在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普遍性。他写道:
妇女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国家的高级公务员队伍中;在教育领域,她们的表现也往往使其男性同行相形见绌;在商界,她们也表现抢眼。然而,在政治领域,妇女代表人物则严重不足。历史地看,政治领导历来是男人的专属,而且一种强大的保守主义倾向于阻止妇女进入国会,阻止选民、酋长、“大人物”或地方议会给予妇女议员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妇女代表权的潜在意义不言而喻,但其实现则需要付诸实质性努力——或者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围绕此一目标扎实工作,或者制定一些平权法律条款保障落实。[9]
萨摩亚选举法中的“10%条款”就是这种平权意图和努力的体现,不过,至今为止,其产生的影响还较为有限。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萨摩亚存在的基于文化规范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和意识形态性障碍有待克服。乡村是政治权力所系,萨摩亚的选举是建立在乡村群落的基础之上。绝大部分城市人口必须在他们家庭所在的村庄进行选民登记,除非拥有永久产权的城区土地并生活于斯。很少有妇女拥有马塔伊头衔,也很少有乡村议事会允许其构成中有女性马塔伊存在。绝大多数乡村议事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对于选区候选人提名具有很大影响力。议事会还会将他们的选择通知选区内的所有马塔伊,而后者接着会向他们的家庭提出投票对象建议。我们通过对2016年选举中妇女候选人的采访所获得的证据表明,仅靠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为村庄、社区、教会提供服务显然不够;想要当选,妇女候选人必须在其他一些方面出类拔萃,比如拥有财富、显赫家庭关系、国家认可、传统身份等级和坚强毅力等。
1962年以来,政府对萨摩亚的习俗总体上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认为行为习惯将对新的社会态度做出反应并发生相应缓慢改变。尽管大规模移民已极大改变了萨摩亚的乡村生活,但对夫权的尊崇仍被等同于对萨摩亚文化的尊重。在城市,妇女在许多职业任领导职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乡村生活决策层,男人和妇女仍死抱着传统角色分工不放。在这种分工传统中,妇女是从属者,一如教会和当代萨摩亚文化所要求的那样。夫权制下的角色分工被认为得到上帝的认可,天经地义。鉴于此,在萨摩亚,很少有妇女会像瓦努阿图的格蕾丝·梅拉·莫丽萨(Grace Mera Molisa)那样以诗言志,大胆呐喊:习俗不过是“巧借弗兰肯斯坦之尸还魂,耍恐吓妇女之把戏”[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