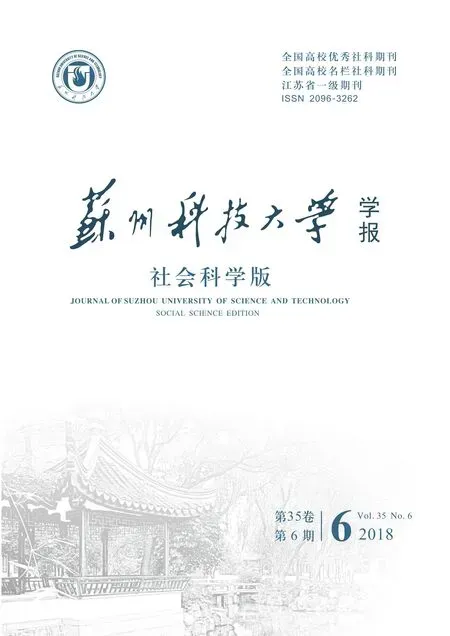国内外学界的夏威夷历史研究述评*
王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9)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世界史研究在领域拓新、选题更新和范式创新方面成绩斐然。然而,与众多热门领域的门庭熙攘不同,夏威夷史的研究难掩边缘而小众的尴尬。这固然与夏威夷地小偏僻、缺乏(更准确地说是“缺少发现”)足够的世界性影响密切有关,而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身份拘囿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定位困难,更使得它无法及时跟上历史研究范式的创新潮流,成为可及时承载显著“意义”的研究对象。夏威夷的历史身份困境主要是由它曾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太平洋岛国、后来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所造成的。作为一个偏处大洋深处的群岛,夏威夷在陆地中心和大国中心的研究范式下难以呈现显著的“意义”;作为美国的领土部分,它更无法跳脱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的束缚,通常只能以美国国内史(且是边缘历史)的身份出现,甚至因此而被淡化、抹杀了其曾经作为独立国家的发展历史。
然而,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一个经由研究者自觉发动的“发现”过程,一时一地的禁锢由研究者的视野局限造成,也必然经其视野的改变而打破。外在形势的变迁、学术风气的演替、研究范式的创新,最终必然影响到研究者的视野和选择,引发问题意识的改变。对新意义的追求进而导致了对新领域、新对象的发掘或对传统领域和对象的再发掘,边缘空间、间隙空间由此成为新意义的载体。西方学术界对夏威夷历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就呈现出了如此的逻辑发展,尽管不温不火,如丝如缕,却牵连不断,节节推进,映射出国际史学研究发展的大脉络。至于国内,夏威夷史研究在新世纪也逐渐开始汇入这股发展潮流,有了新的起步。
鉴于夏威夷历史研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更趋成熟,且演替脉络清晰,接下来的学术史梳理将把重点放在国外学术界,按照研究的时间顺序和阶段特性进行归类评述。大致而言,自19世纪30年代至当下,夏威夷史的学术研究可归纳为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了解“他者”:19世纪末之前的研究
夏威夷正式进入西方人的认识视野,是在1778年库克第三次远航“发现”夏威夷之后。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此后被称作“后接触时代”。随着西方文明的渗透,特别是19世纪20年代欧美在夏威夷殖民行动的开始,对夏威夷这个“他者”对象的初步了解和研究也就开始了。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末,主要由欧美传教士和受过西方教育的“有文化”的夏威夷人,对存在于口头流传中的夏威夷历史传统和他们亲身经历的社会发展进行追溯加描述式的书写和编纂。
19世纪20年代,新教传教士们帮助夏威夷人“创造”了字母文字,随之出现了首批关于夏威夷的历史叙述作品。依法连·埃弗莱斯(Eveleth Ephraim)的《夏威夷群岛史》、舍尔顿·迪布(Sheldon Dibble)的《桑威奇群岛史》、詹姆斯·雅夫斯(James Jarves)的《夏威夷群岛史》、T.德怀特·亨特(T. Dwight Hunt)的《桑威奇群岛的过去与现在》均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1-4]这些早期历史作品突出政治史,以见闻记录和口述史整理为主,资料性价值很强,历史分析性则相对较差。而且,由于基本是由欧美传教士书写,其西方化的思维和为帝国殖民扩张服务的目的性,导致这些作品虽然可相对客观地反映了传统夏威夷社会直到君主制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现状,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立场与观念的西化色彩,甚至在对夏威夷传统的解释上进行了改造和创造。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首批接受西式教育的本土作家的成长,少量由夏威夷学者写成的研究性作品开始出现,这为夏威夷历史叙事和研究增添了新的气息。历史学家塞缪尔·M.卡玛考(Samuel M. Kamakau)以夏威夷王国的历代国王为考察对象,写成系列历史文章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在他过世后,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书,以《夏威夷的执政酋长们》为题于1887年出版。该书以政治演变为线,叙述了自传说时代直到卡梅哈梅哈三世(Kamehameha Ⅲ)夏威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历史资料价值,尤其是在对夏威夷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上,较之欧美学者更深入和可靠。[5]另一位本土学者戴维·马洛(Davida Malo)系统整理出一部《夏威夷的古代风俗》,于1840年由J.F.波各牧师修订出版。这是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记录夏威夷传统风俗人情、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资料价值非常高。[6]
基督教传教史作品的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个典型特点。此类史著基本由新教传教士写成,其中尤以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和拉夫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的系列作品影响最大。威廉·埃利斯是早期赴夏威夷的美国传教士,他不仅投身于夏威夷传教事业,还热心于对夏威夷人的教育。从1827年起,他先后写成5部有关夏威夷传教的作品,其中1844年出版的《伦敦传教会史》和1866年的《美国的夏威夷传教》最具影响力。[7-8]拉夫斯·安德森在1864—1866年间先后出版了6部关于夏威夷历史和夏威夷传教史的著作,其中1864年出版的《夏威夷群岛在传教团劳工影响下的发展及形势》、1870年出版的《夏威夷传教史》和1872年出版的《ABCFM夏威夷传教史》成为了解和研究夏威夷新教传教史的代表性著作。[9-11]此外,1839年舍尔顿·迪布出版的《桑威奇群岛传教史概览》[12],以及1842年约瑟夫·特雷西(Joseph Tracy)出版的《ABCFM的历史》[13],也都是记载夏威夷早期基督教传教状况的重要史料。
进入19世纪80年代,随着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夏威夷史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深入化和专题化倾向,研究对象的层次趋于多样。W.D.亚历山大(W. D. Alexander)是19世纪末美国知名的夏威夷历史研究专家,对源自欧洲的史学科学化范式的熟练把握,使得他较之此前的夏威夷研究者更为严谨;学术的敏锐性和感悟力又让他摆脱了精英政治史的视野局限,将研究对象转向普通人和经济、贸易等多元化议题。亚历山大擅长于夏威夷土地问题研究,他在1882年出版了两本关于夏威夷土地权问题的专著,其中《夏威夷王国土地权简史》为该问题研究的代表论著。[14]1891年,他又出版《夏威夷人民简史》,一改政治史的精英叙事模式,其对夏威夷平民权利的关注体现出典型的美国式政治观念。[15]另外,他还先后在《波利尼西亚社会杂志》等刊物发表数篇关于夏威夷贸易、种族和外交等方面的文章。[16-18]相较于此前乃至以后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亚历山大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更具前瞻性和引领性,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火奴鲁鲁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早在1880年,劳拉·贾德(Laura Judd)就根据个人生活经历,写出了以火奴鲁鲁为中心,分析19世纪20—60年代夏威夷社会生活的专著《火奴鲁鲁生活概览:夏威夷群岛的社会、政治和宗教,1828—1861》。[19]
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夏威夷都是以一个独立存在的群岛国家存在并出现在研究者的笔下。但是,主要的历史撰述者的欧美人身份以及他们旨在向西方社会介绍这一僻远神秘的大洋“天堂”的意图本身,决定了此时期的夏威夷史著偏重于对文化“他者”的揭示和呈现,这不仅限制了研究的主题和深度,更导致其严重依附甚至从属于“帝国史学”模式的特征。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正式帝国”的追求在太平洋地区的展开,这一特点表现得更趋明显。学者们从大国殖民的立场出发,以“先进”的欧美文明发展(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为参照系,对夏威夷历史与社会的落后性以及它在欧美文明影响下的社会演进予以描述和阐释。夏威夷史的研究和撰述自觉地成为帝国扩张的文化同谋。
二、成为美国“内史”: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研究
19世纪90年代,海洋边疆观念在“新天定命运”的扩张思潮影响下甚嚣尘上,美国学界因此对夏威夷给予更多的关注。经历过1893年那场由美国白人种植园主主导的“政变”之后,美国国会最终在1898年7月正式通过吞并决议,将夏威夷纳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夏威夷群岛主体身份的变化,带来了对其历史研究的视野转变。此时期,民族国家史学范式渐趋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主流,它与帝国史学模式相结合,直接影响着夏威夷历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世纪末始,以美国学者为主体,史学界开始从美国国内史的角度,把夏威夷作为美国历史和文化的边缘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研究,对其既往传统与历史的否定和轻视极为明显。这一时期是夏威夷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大量极具代表性的整体史论著相继出现。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专题性研究呈现繁荣的局面。
1899年,埃德曼·J.卡本特(Edmund J. Carpenter)出版了《美国在夏威夷:一部美国对夏威夷群岛的影响的历史》。该著作详细回顾和梳理了18世纪末以来美国与夏威夷群岛的历史关系,以及美国对夏威夷历史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时值夏威夷新并入美国,该书的写作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对美国在夏威夷的影响的评述也是极尽夸赞之能事。[20]在他之后,威廉·布莱克曼(William Blackman)于1906年出版的《夏威夷的形成:社会演进研究》[21],阿尔伯特·泰勒(Albert Taylor)在1922年出版的《夏威夷天空下》[22],都呈现出为美国对夏威夷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和吞并合理性的张目倾向。哈罗德·布莱德利(Harold Bradley)的《夏威夷的美国边疆:1789—1843年间的拓殖先锋》是一部从美国角度重述夏威夷王国早期历史的专著,其最大的特点是所用资料丰富,缺点则是对美国在夏威夷王国发展中的作用评价过高,而对其他国家的作用有所忽略。[23]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学家拉尔夫·凯肯德尔(Ralph Kuykendall)专研夏威夷史,他的研究重视对史料的充分挖掘,以史带论、言之有据是其论著的突出特点。1926年和1928年,凯肯德尔与他人合作,先后出版了《夏威夷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夏威夷》,在该领域形成初步影响。[24]此后,他开始三卷本《夏威夷王国史》的写作,正是这部著作最终奠定了他在夏威夷史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夏威夷王国史》分别出版于1938年、1953年和1967年,是迄今为止最完整也最具学术价值的夏威夷王国编年体通史,其对夏威夷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且论述并重,观点相对客观,是研究夏威夷历史和社会问题无法绕过的经典名著。[25]除上述代表性著作外,其他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奥拉梅尔·古利克(Gulick Orramel)的《夏威夷的旅行者》、威廉·卡斯特尔(William R. Castle)的《夏威夷的过去与现在》、多罗西·哈扎马(Dorothy O. Hazama)的《古代夏威夷人》等。[26]
各类专题性研究论著的蓬勃涌现也是此时期夏威夷史研究兴盛的重要表现。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问题研究的兴盛,涉及夏威夷具体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或人物等议题的论文大量出现。几个重要的专业性期刊,如《夏威夷历史杂志》《波利尼西亚社会杂志》等,以及夏威夷历史协会成立后编辑和发布的《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夏威夷历史协会文件》,为各类专题研究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专业性的平台。集中于个案探究的学术论文和更具系统性的学术专著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这一阶段夏威夷专题史研究的繁荣。
在政治史领域,研究者不再简单停留于对夏威夷国王和酋长体系的研究,而是深入到对具体政治事件、人物等的细致挖掘和分析。不仅如宪政发展、法律制定等政治研究的重点领域受到普遍关注,政治人物研究和外交事件研究也成为热点。这一趋势在20世纪中叶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卡梅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 Ⅰ)、利霍利霍(Liholiho)、奇奥普奥拉尼( Keōpūolani)、卡拉尼莫库(Kalanimoku)、卡阿胡马努(Ka’ahumanu)、约翰·扬(John Young)、波基(Boki)等对王国历史发展带来重大影响的核心政治人物的历史和作用被多方发掘;拜伦勋爵来访,与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等签订条约等外交史问题也被放置在大国外交史的背景下反复讨论。在经济史方面,尤利西斯·帕克(Ulysses Parker)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夏威夷群岛经济史》,并付梓出版。这是最早的一部夏威夷简明经济史,叙事脉络清晰是其最主要的特点,但在原始资料的使用上还不够丰富,因此限制了它的学术影响力。[27]夏威夷土地和土地权变迁是一个热点经济论题,相关议题的论文数量众多,其中对1848年土地大分割及其影响的研究最为集中。专著方面也呈现同样的特点。托马斯·斯伯丁(Thomas Spaulding)于1923年出版了《夏威夷王室土地》,集中论述1848年土地大分割中出现的“王室土地”的历史发展情况。[28]琼·知念(Jon Chinen)1958年出版的《土地大分割:1848年的土地划分》一书,也以土地大分割为中心,专述夏威夷的土地权变革问题,对其背景、过程和影响有系统的分析呈现。[29]学者们对夏威夷王国社会史和文化史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中期以后,且以论文为主要的成果体现。诸如女性地位的变化、夏威夷文字的发展、教育的演进、音乐、舞蹈等,都成为历史学者的研究主题。劳伦斯·富克斯(Lawrence H. Fuchs)1961年出版的《夏威夷社会史》,是此时期少有的社会史研究专著。
截至20世纪60年代,夏威夷史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美国内史化倾向,单从大部分论著的标题就已经能够看出这一定位:除个别例外,此时期的整体史和专题史论著都极少使用“夏威夷群岛”“夏威夷王国”等称谓。作为美国的一处领地/州,夏威夷不再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对它的历史研究也就丧失了主体独立性,即便是对被吞并前的历史追溯,学者们也更多地强调美国对它的积极影响和改造作用。尽管这一时期恰逢民族国家史学兴盛的时代,但夏威夷作为一个失去了独立国家身份的地区,无法接受到这一光芒的照射,美国的民族国家意识超越和统摄了一切。在这一表现的背后,“帝国史学”的阴影若隐若现。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所谓的“民族国家史学”无非就是“帝国史学”的另一张面孔。
三、本位化的困惑:20世纪70至90年代的研究
进入20世纪70年代,受到“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后现代思潮兴起的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出现新的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兴盛,整体史和碎片化的新史学并行。在对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叙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历史学者们也开始从理论和方法的视角着手,考虑调整夏威夷问题研究的定位。然而,这次调整并不顺利。在七八十年代,夏威夷问题研究不盛反衰,进入了一个低谷期。夏威夷主体身份的尴尬,使得它成为被新兴的太平洋诸岛史研究基本排斥的对象,无法及时追踪上新的本位化史学研究步伐。此处所谓的“本位化史学研究”,特指20世纪60年代起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戴维森(James Davidson)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后发展成所谓的“堪培拉学派”)引领的太平洋诸岛历史研究新范式。该范式立足于使太平洋诸岛史摆脱“帝国史”模式,实现领域研究独立化。[30]为此,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新材料,特别是经由田野调查得来的本地材料,包括本地语材料、口述史料、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材料,并尝试从岛屿本位视角(即从太平洋诸岛内部来看视)叙事和论析,借此摆脱帝国史学模式的拘囿。戴维森提出,太平洋历史的研究应从双向性的视角、多元文化环境的视角,充分利用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以太平洋诸岛为中心对象,实现本土化的研究拓新。在政治史之外,更多关注经济和社会变迁,关注“人”(移民及社区),关注宗教、文化以及太平洋对欧洲思想和表达的反向影响。[31]正是在此新路径的影响下,至20世纪80年代,双向度和内视性的本位化历史研究主导了太平洋诸岛历史的研究。然而,在这场史学研究潮流中,当学者们面对夏威夷这一具体对象的时候,却因其现实身份的特殊性陷入了定位困窘:它作为一个群岛/文明的历史主体“本位性”是否还存在?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堪培拉学派”的学者们对夏威夷的历史选择了避而不谈。至于美国的历史学者们,则继续固守其传统的帝国史学/民族国家史学模式,查漏补缺,艰难维持。相较于上一个时期,这个阶段的夏威夷历史研究不仅数量剧减,总体质量也缺少突破。
当然,尽管出现量和质的总体滑坡,这一时期的夏威夷史研究也并非全然乏善可陈。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和推动,60—80年代的夏威夷历史研究虽然缺乏对整体性问题的关注,在纯历史研究的成果方面也缺少新意和突破,却在某些跨学科领域如社会史、宗教史、家庭史、劳工史等有所深入,呈现出一些新史学研究的特征。“禁忌”和“禁忌体系”是兼跨宗教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议题,它们成为这一时期夏威夷历史研究者较集中关注的新选题,如M.C.韦伯(M. C. Webb)的《夏威夷禁忌体制的废除》、S.西顿(S. Seaton)的《1819年夏威夷“禁忌”的废弃》、迈克尔·舍里斯(Michael Shirres)的《禁忌》、瓦列里奥·瓦列里(Valerio Valeri)的《王权与祭祀:古代夏威夷的仪式与社会》等。[32-35]劳工史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有了些新发展。爱德华·D.比彻特(Edward D. Beechert)的《在夏威夷劳作:一部劳工史》于1985年出版。该书对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夏威夷劳工输入、运行机制、生存状况以及对夏威夷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突出人力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同时,肯定了华裔、日裔等外来劳工在推动夏威夷近代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36]当然,除了能够适度体现出选题领域的拓展,这些作品在历史分析的创新性上还不明显,既没有多少新材料,跨学科借鉴也不突出。
值得称道的研究突破出现在80年代的历史人类学领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太平洋诸岛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通过田野考察,历史人类学家们认识到,所谓“落后的异文明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些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完备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体系,其文明有着内在的生命力。他们愈益重视异文化的完备性和体系性,开始尝试从异文化的角度对既往的历史现象做出新的解释。美国历史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通过深入的田野考察和广泛的材料搜集整理,对夏威夷以至波利尼西亚社会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发掘,对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此基础上,他以文化本土化/本位化为视角,写成《土著如何思考》《历史之岛》《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等论著,重新对夏威夷文化和某些具体事件进行解释,从而打破了夏威夷问题研究中帝国史学/民族国家史学单一范式的主导,为此后的夏威夷历史研究开拓新的可能性路径。[37-39]除他之外,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这一趋势。[40]
对夏威夷传统家庭和婚姻状况的研究也是这一阶段出现的一个新问题领域。早在5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学者E.S.C.汉迪(E. S. C. Handy)和玛丽·K.卜奎(Mary K. Pukui)在《波利尼西亚社会杂志》分两期发表了题为《夏威夷家庭体系》的文章,初步讨论了夏威夷的传统家庭体系和婚姻形态问题。之后,两人又在同刊连续发表6篇《波利尼西亚家庭体系:夏威夷卡乌地区》的长文,就夏威夷传统婚姻、亲属关系和家庭形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对摩尔根的古代婚姻形态论断提出了质疑。[41]在其影响下,1957年,夏威夷大学太平洋科学研究团队以毛伊岛东端的哈纳地区为考察点,开展了一项夏威夷文化渗入的专项性研究,其中重点涉及当时夏威夷的家庭组织形态和婚制。其研究成果在1960年的《波利尼西亚社会杂志》上发表。[42]美国学者对夏威夷婚姻和家庭制度的研究进展也得到了苏联学者的关注。C.A.托卡列夫(С.А.Токарев)等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时,就引用了美国学界的新发现。[注]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一次对“普那路亚”婚制和群婚制的讨论。蔡俊生的《摩尔根群婚概念的再认识》和刘式今的《为摩尔根古代“普那路亚”婚制辨正》,尽管对“普那路亚”婚和夏威夷的婚姻与社会形态提出了初步的质疑,但只限于粗线条描述,严重缺乏事实材料和论证说服力,也似乎并未引发国内学术界对摩尔根“普那路亚”婚的反思和修正。直至今日,对摩尔根“普那路亚”婚制和夏威夷传统婚姻状态的错误认识仍然普遍存在。1983年,简·L.西尔弗曼(Jane L. Silverman)发表了《再婚》一文,从法制史的视角,对19世纪夏威夷王国中后期基督教婚姻形态主导下逐步放开再婚限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43]
严格意义上讲,上述夏威夷问题研究的创新成就主要出现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算不上是纯粹的历史学研究。这一来自相邻学科的新发展能否被历史学者们吸纳和借鉴,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接下来夏威夷历史研究路径突破的实现。
四、寻求新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
如果说夏威夷历史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处在一种范式落伍、创新艰难的困窘状态,那么从90年代开始,这一研究终于从跨学科借鉴和全球史范式的外溢影响中找到了路径更新的可能。也正是在此形势下,夏威夷历史研究开始焕发新生机,涌现了一批具有明显新范式特征的作品。
受到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对历史学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的跨学科影响,跨域借鉴终于成为夏威夷历史研究者普遍接受的方法,他们开始在选题、理论、方法和材料等各方面寻求突破,贡献出一系列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问题意识和意义性明显的论作。朱利·米坎恩(Juri Mykkanen)是以新的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夏威夷王国政治问题的新生代学者。2003年,他的《发明政治:夏威夷王国的新政治人类学》出版,打破了夏威夷政治史书写的沉闷之氛。[44]2007年,鲍林·杜津斯佳(Dudzinska)写成题为《与男人共食的结果:夏威夷女性与文化转型的挑战》的博士论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夏威夷女性地位的变化进行分析,引领了夏威夷性别史研究的文化转向。[45]斯泰西·L.卡米西罗(Stacy L. Kamehiro)也致力于文化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研究,他2009年出版的《王权艺术:卡拉卡瓦时代的夏威夷艺术与民族文化》称得上是一部出色的个案研究作品。[46]应该说,上述这些作品在理论分析和方法借鉴上都有较大的学术参考意义。
全球史、跨国史的兴起也为夏威夷历史研究带来了视野的改变,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局限,转而从全球整体性、联系性的角度思考一地、一事、一专题,让夏威夷的个案史研究焕发新生机,疾病史、环境史、贸易史、移民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疾病史主题方面,O.A.布什尼尔(O. A. Bushnell)出版了《文明的礼物:夏威夷的病菌和种族灭绝》,集中论述病菌传入对夏威夷土著人口锐减的直接影响,从一个侧面抨击西方的殖民扩张。[47]凯里·A.英格里斯(Kerri A. Inglis)的《麻风病:19世纪夏威夷的疾病及其消除》则择取麻风病这一个案,从疾病史和环境史的双重角度,对外来传染病在夏威夷的传播、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治疗历史进行追溯和分析,其中受到克罗斯比等全球史学者研究思路和方法影响的痕迹明显。[48]格雷戈里·罗森塔尔(Gregory Rosenthal)和卡罗尔·麦克伦南(Carol MacLennan)将环境史问题跟蔗糖业、劳工等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发表了相关的论作。[49-50]劳伦斯·克斯勒(Lawrence Kessler)专事夏威夷甘蔗种植产业历史的研究,他最近的研究将之与环境史研究相结合,从生态保护的视角重新审视夏威夷蔗糖产业的发展。[51]劳工与移民史专题是体现研究的跨域特征更集中的一个领域。从80年代起,华裔、日裔、朝鲜裔劳工和移民就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1997年,罗伯特·戴(Robert Dye)出版《火奴鲁鲁的富商:阿芳和夏威夷的华人》,主要以夏威夷华侨领袖、华人商会会长和大清驻夏威夷首任领事陈芳为中心,论述了1849—1890年间华商华人在夏威夷的商业及族群发展情况。[52]艾伦·M.尤哈拉(Alan M. Uyehara)的博士论文则以比较的视野,对1782—1985年间夏威夷华人和英国华人的教育与社会同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53]埃莉诺·C.诺达克(Eleanor C. Nordyke)与人合作,分别就夏威夷华裔移民、日裔移民的历史和人口发展全貌发表了两篇概论性的长文。[54-55]韩裔学者崔永浩则就1903—1950年间朝鲜人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56]除此之外,其他族裔移民以及契约劳工(如南岛劳工、波兰劳工等)问题也相继有论著问世。[57-6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最早介入夏威夷历史研究也是从华人移民史开始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者先是以在夏威夷的华人华侨为研究重心,新世纪以后开始扩及对其国家移民的研究。叶显恩在1988年和1990年先后发表三篇关于夏威夷华人移民的文章。[62-64]黄英湖的《美国夏威夷州华人参政刍议》则聚焦1938年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夏威夷华人参政的情况。[65]安国楼的《早期夏威夷客家妇女的“黄金梦”》对加利福尼亚“黄金热”后移居夏威夷的客家妇女情况进行了概略性的述评。[66]近年来,祝曙光教授及其学生在美国的日裔移民研究领域发表了一些论文,对日本在夏威夷的移民历史均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其中,杨栋的硕士学位论文《夏威夷日本移民研究(1885—1945)》对从夏威夷王国至建州前约61年间日本移民夏威夷的历程及其生活状况进行了梳理、描述和分析,具有一定的填补性学术作用。
美国国内史视野下的夏威夷历史研究依然还在继续。2003年,汤姆·考夫曼(Tom Coffman)出版《美国的岛屿边界:夏威夷政治史》,对夏威夷政治发展特别是并入美国之后的政治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67]这是迄今为数不多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夏威夷政治史专著。而与此同时,在美国史学界“修正主义”思潮和“新帝国史”兴起的影响下,更多的夏威夷历史研究者开始反思殖民主义,试图归还夏威夷古代和近代历史的主体身份性。这成为此时期夏威夷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1993年,夏威夷裔学者豪纳尼-凯·特拉斯克(Haunani-Kay Trask)的《从一个土著女孩的视角:夏威夷的殖民主义和主权问题》出版,重提美国殖民吞并夏威夷的合法性问题,标志着这一反思和修正进程的开始。[68]接着,卡纳劳·G.T.扬(Kanalu G. T. Young)也出版了《对夏威夷土著历史的反思》。[69]此后,围绕该主题的论著不断涌现,与夏威夷原住民文化的觉醒和抗议运动结合在一起,向“美利坚帝国主义”发起挑战和冲击。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尼尔·B.杜卡斯(Neil B. Dukas)的《独立夏威夷国家军事史》、诺艾诺·K.席尔瓦(Noenoe K. Silva)的《阿洛哈背叛:夏威夷原住民对美国殖民主义的反抗》、肯尼斯·R.康克林(Kenneth R. Conklin)的《夏威夷种族隔离:阿洛哈州的种族分裂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J.克哈乌拉尼·卡乌阿努伊(J. Kēhaulani Kauanui)的《夏威夷血统:殖民主义与主权政治及原住民性》、罗伯特·J.霍蒙(Robert J. Hommon)的《古代夏威夷国家:一个政治社会的起源》等。[70-74]
与美国学界努力实现路径创新的发展态势不同,国内史学界的夏威夷研究从这一阶段刚刚起步,选题上总体呈现传统性特征,且基本是把它归入美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来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也比较有限。1992年,梁茂信教授在《世界历史》发表《美国对夏威夷的吞并与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这是国内较早涉及夏威夷的学术论文之一,其视角上的美国内史倾向显而易见。[75]1994年,《民俗研究》第1期发表了文华、厚芳和利项斯基的《夏威夷土著的奇风异俗》一文,其在研究内容和视野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新意。直到21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外夏威夷研究新路径的影响才部分显现出来。除上面已提到的移民史研究外,在其他一些专题领域也出现了部分体现新问题意识和全球史视野的论著,中国学者开始尝试从非西方的研究视野寻求学术对话。201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建军在借鉴美国修正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写成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夏威夷原住民民权运动与美国殖民政制的较量:阿卡卡法案本质及其影响分析》。王华则以“现代性”为视角,对跨文明冲突和影响下夏威夷王国的近代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并在2016年出版了专著《夏威夷近代社会转型研究,1778—1854》。[76-84]尽管如此,国内史学界在夏威夷历史研究方面还远不具规模,尚存在比较大的探索空间。
综上所述,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夏威夷历史研究在成果积累上不可谓不丰富,其研究视野和路径的不断更新更是推动了研究的多层次化和厚重感;在地域分布上,它却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国外特别是美国学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始终引领着发展的方向,国内史学界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尤其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相对于其他世界史热点研究领域而言,夏威夷历史研究的范式更新相对滞后,视角的单一化特征也更为明显,主体身份的认知束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夏威夷进入世界历史的关注范畴是伴随殖民扩张发生的,因而,对它的认知和研究也打上了浓重的西方中心的烙印,从认知定位到材料选择、理论依据都表现出强烈的西方单向性。夏威夷很少被看作独立和平等的文明实体,在西方话语描述下的原始落后成为西方殖民者单向的文明化解释的合理理由。而今,在全球史和海洋史范式的影响下,太平洋史的研究已经进入“太平洋世界”这一更具整体性意义的研究路径,即便是美国史的研究也已经深刻烙上了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印记。这些新的研究视野和范式是否也适用于夏威夷历史的研究,能否给接下来的夏威夷史研究带来新变化,尚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