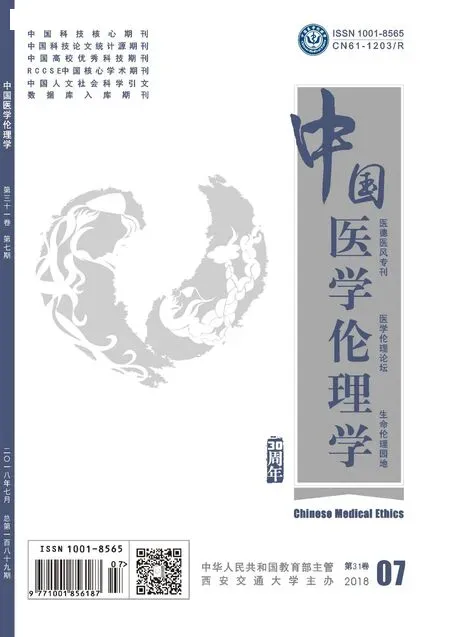线粒体置换技术的伦理学反思*
张 迪,刘 欢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730,zhangdi87@outlook.com)
2015年英国下议院批准了使用线粒体置换技术治疗/预防严重线粒体遗传疾病的法案,2016年世界首例通过该技术生育的婴儿降生,不少人将其称为“三亲试管婴儿”。2017年英国人类生殖与胚胎管理局首次授权纽卡斯尔生殖中心开展线粒体置换的临床应用[1]。一些学者从伦理学视角阐述了对该技术的担忧和反对,包括技术安全性、生殖系基因改造、亲子关系等。笔者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论述,明确线粒体置换技术的应用能够得到伦理学辩护。
1 线粒体遗传疾病与线粒体置换技术
1.1 线粒体遗传疾病
线粒体是人类机体内几乎所有细胞都含有的重要细胞器,为人类活动提供必要的能量。线粒体内的遗传物质(mitochondrial DNA,mtDNA)突变可引发多种遗传性疾病。线粒体遗传疾病属母系遗传疾病, 女性可通过卵子将突变mtDNA传递给后代。对能量重度依赖的器官和组织易受mtDNA突变的影响,如大脑、心脏、肾脏、肝脏、胰腺和肌肉等[2]。疾病的种类和严重程度受突变类型和突变mtDNA的百分比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十分广泛,如线粒体脑病、阿尔兹海默综合征、智力低下、心肌病、糖尿病和线粒体肌病等[3]。线粒体疾病可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并缩短其寿命。
mtDNA突变遗传引发后代发病的概率约为1/200至1/5000[4-7]。不同国家和地区线粒体疾病的发病率存在差异,如英国人群中1/3500患有线粒体疾病或潜在患病风险,芬兰人中mt-A3243G突变发病率为1/6000[8]。中国目前没有权威流行病学数据,由于人口基数大,发病率的确定有助于国家在科研与卫生资源分配上更具针对性地投入。
目前针对线粒体疾病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运动、饮食和对症治疗四大类,可改善部分患者线粒体功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但这些干预只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恶化,无法实现疾病的治愈。
另一些干预可在胎儿出生前实施。一是通过产前诊断及人工流产,避免患儿的出生,但该途径无法帮助夫妇实现生育健康后代的目的;二是通过胚胎移植前的产前诊断,选择将含有突变mtDNA较少的胚胎移植,以降低发病率或延缓发病时间。但这一方法只降低了发病的可能性,并未真正实现预防疾病发生的目的;三是通过第三方供卵的方式,使用线粒体健康的卵子与夫精结合形成受精卵并移植到母体子宫中。该途径虽可预防线粒体疾病,但后代并不含有该母体的遗传物质,对于一些夫妇而言,从心理、精神和社会层面上而言皆难以接受。
因此,对于为避免后代患严重线粒体疾病且希望生育具有夫妇双方遗传物质的人群而言,线粒体置换技术目前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1.2 线粒体置换
mtDNA为母系遗传,且只存在于细胞质内,因此可使用mtDNA健康的线粒体DNA替换突变mtDNA,即线粒体置换(Mitochondria Replacement MR)或线粒体捐献(Mitochondria Donation,MD)[9]。目前可通过两种方法实现:①中期纺锤体-染色体复合物移植(spindle-chromosometransfer,ST),将患者卵子或极体细胞核转移到捐献者健康的去核卵子胞质内;②原核移植(pronucleustransfer,PNT),将患者夫妇的受精卵原核转移到去除原核的健康受精卵胞质内[4]。
2 线粒体置换技术引发的伦理学争论
2.1 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于任何一项应用于人类身上的新技术而言,具备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伦理学所要求的。人们对线粒体置换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担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核不相容性、突变转移与遗传瓶颈、未知风险[10-12]。
首先是核不相容性。有学者指出,我们尚不清楚线粒体与细胞核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入第三方线粒体可能会引发线粒体与细胞核间的“不匹配”,从而对后代造成伤害[11]。一些研究发现,小鼠、果蝇通过线粒体置换获得的后代在认知功能、运动技能和生长发育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13]。但另一些针对猴类和小鼠研究显示,在线粒体与核基因“亲缘”较远的情况下,长期观察通过该技术生育的后代并未发现因“不匹配”导致患病或发育异常[14]。此外,遗传学家认为可以通过使用亲缘关系较近的线粒体可降低核不相容性出现的概率及其风险[15]。
其次为突变转移与遗传瓶颈。因能量需要,细胞核周围总会包裹大量线粒体,母体卵子中的缺陷mtDNA易与核DNA一同转移到新的胞质中,产生子代mtDNA混杂现象。一些学者指出,缺陷mtDNA可能通过“遗传瓶颈”,在子代某些组织或器官的细胞中复制和扩增,积累到一定阈值后将导致子代发病[2]。但有学者指出,在线粒体疾病患者体内,达到60%或更高的突变mtDNA阈值才会发病,因此认为低载量的mtDNA不太会导致子代患病[14-15]。
最后是对未知风险的担忧。由于线粒体遗传疾病存在阈值效应,即体内突变线粒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病,如在成年后发病,而在哺乳类动物身上开展的短期观察研究难以确保该技术不会引发长期未知伤害。此外,由于线粒体为母系遗传,未知风险可通过女性子代传递给其后代,进而引发对后代的伤害。但是,任何一种技术都存在未知风险,这也是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的目的之一,即在评估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时,探索技术可能引发的未知风险,仅因其存在未知风险而拒绝技术的应用难以成立。
英国政府2015年2月通过了线粒体捐赠技术用于临床的草案认可了其安全性与有效性,并于2017年3月首次授权允许纽卡斯尔生殖中心开展该技术的临床应用。2016年美国科学院发表专家声明,在满足特定条件下FDA应开放线粒体置换技术的临床试验[16]。从上述政府行为及专家意见来看,线粒体置换技术已具备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考虑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开展临床试验。与此同时,现有动物研究结果也提示我们该技术的应用仍存在已知和未知风险,但这并非禁止开展临床试验的充分必要条件。从伦理学视角出发,我们应当将这些风险与技术为患者及其后代带来的受益进行权衡。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线粒体遗传疾病的女性而言,通过自然生育或现有治疗手段难以确保后代的健康,而严重的线粒体疾病会使后代严重致残甚至早逝,这对于后代自身及其家庭而言伤害是巨大的。因此,在其他干预无效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生育含有夫妇双方遗传物质的健康后代这一愿望,线粒体置换技术的现有风险是可以被他们所接受的。此外,为了减少风险和伤害,该技术的应用可仅限于生育男性后代,并对其进行长期的随访和观察。
2.2 生殖系基因改变
生殖系基因疗法通常涉及对现有个体的卵子、精子,或对早期胚胎的核基因或线粒体基因,进行治疗目的的遗传改变,并通过生育传递给后代。线粒体置换技术可改变卵子、受精卵的线粒体基因,并可通过女性子代传递给其后代,因此该技术被普遍视为生殖系基因疗法的一部分。但一些学者并不将线粒体置换技术视为生殖系基因治疗,因为其非直接作用于核基因[17]。他们认为“生殖系基因治疗”仅用于描述对人类配子、合子或胚胎核基因的改变。核基因的复杂性,使得对其的改变风险较大,而通过线粒体置换治疗线粒体遗传病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这一解释虽然并不被大部分人所接受,但其揭示出线粒体置换与核基因改变这两类生殖系基因治疗的不同点。第一,线粒体置换的目的不是改变或影响核基因;第二,并不改变捐献者的线粒体,而仅仅是进行替换;第三,通过该技术获得的后代中,仅有女性会将线粒体基因的改变遗传给其后代。
首先,将线粒体置换技术作为生殖系基因疗法并反对其应用者认为,该技术会触碰生殖系基因改变的红线,引发道德滑坡,从允许线粒体置换滑向允许改变人类配子、合子或胚胎的核基因,从而打开“设计婴儿”的潘多拉魔盒,走向邪恶的“优生学”[11-12,18]。我们可从线粒体的功能、技术应用的目的和治理三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反驳。第一,线粒体作为机体的能量工厂,其功能在于为人类活动提供必要的能量供给,而线粒体置换技术是用正常线粒体替换携带致病突变的线粒体,并不改变细胞核基因。第二,线粒体置换技术应用的目的被严格限制在避免后代患严重线粒体疾病之上,包括中国、英国都禁止为治疗不孕不育或提高受孕率而使用此类技术[19]。健康对于个体生活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健康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基础。在确保线粒体置换技术具备一定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将其用于预防和治疗线粒体疾病,确保后代的健康成长是合理的干预目的。如反对这一目的,同样也要反对目前众多国家开展的各项围产期保健,如使用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其目的为确保夫妇生育健康后代,促进后代的健康福祉,而非歧视那些有神经管缺陷的患者,更不是“设计婴儿”。20世纪初期在欧美国家盛行的“优生学”其错误在于不公正的对待人群中的差异,与剥夺个体的自主性。但无论线粒体置换技术,还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的产前遗传诊断及胚胎移植前基因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均在尊重自主性的前提下实施,且并未有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技术本身对患有相应遗传疾病的群体造成歧视。这些所谓的歧视并非源于这些技术的应用,而源自社会对这些群体缺乏包容,缺乏合理的支持,故引发他们对于技术应用的担忧。但这一担忧并不能阻碍夫妇选择生育健康后代的自由。第三,政府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可通过严格控制适应证(如仅限于避免严重线粒体遗传疾病),并增加违法成本,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避免或减少技术滥用的产生。任何一项技术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但这并不是我们禁止使用该技术治病救人的理由。我们应当做的是不断提高医疗实践者的伦理意识、完善管理体制、完善法制建设,从而更有效的使用线粒体置换技术造福患者及其后代。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生殖系基因改造是非自然的,人类的遗传物质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非自然的干预将会对人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12]。因“非自然”而认为线粒体置换技术是错误的,这一论证可同样应用到所有医学或技术之上,如人工合成的化学药物(降压药、降糖药),或模拟人类器官工作机器(如透析仪、呼吸机、人工体外膜肺等)。这些药物或机器在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挽救患者生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皆是非自然的。此外,即使将“厌恶的智慧”(wisdom of repugnance或称为yuck factor)用于反对辅助生殖的Leon Kass教授也指出,有些进程是自然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天赋”,人们可以通过不断的使用和训练提升这些“天赋”;而另一些则像瘟疫一样需要通过克己或医学进行控制[20]。这意味自然的并非全是好的,或在伦理学上都应被无条件接受的,对于非自然的技术不应全然反对,而应通过理性思辨和伦理学分析,确定是否应当被允许,及如何使用。
最后,人们可能认为在没有征得后代有效同意的前提下改变后代的遗传物质不应被允许。但这一反驳缺乏力量,同样的理由可用于反对父母为未成年孩子寻求治疗、培养运动或艺术“天赋”等,因在孩子未成年之前我们并不认为任何针对他们的干预可以获得他们有效的同意。当然,反对者可能认为线粒体置换技术不同于后天的医疗干预和教育,因为前者会对后代产生长远的未知风险且可将这些风险遗传给孩子的下一代。但类似技术的应用并未显示出此类未知风险,例如单精子显微胞浆注射,将单个精子通过体外人工的方式注入卵子中以实现人工授精的目的,或PGD——为了确定胚胎是否携带致病突变而从早期胚胎发育的细胞中抽取一个甚至更多的细胞用于基因检测。这些辅助生殖技术也未获得后代有效的同意,此外其风险就目前的临床实践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在后代出生前的干预都无法获得孩子的有效同意,而这并不意味着干预不应被允许使用,或任由父母改变后代的遗传物质。尽管学界并未对这一权利的解释达成共识,但被普遍接受的一点是它应当包含确保后代的健康。线粒体遗传疾病无疑对这种权利构成侵蚀,而使用线粒体置换技术可提升后代的福祉,促进其“开放未来的权利”。
2.3 亲子关系
一些人指出线粒体置换技术会引发亲子关系的混乱,进而对后代及家庭造成伤害,故对该技术的应用表示担忧或持反对态度。部分媒体和学者将线粒体置换技术称为“三亲试管婴儿”技术,并称由于该技术使后代同时拥有两位女性的遗传物质,使得该胚胎/婴儿拥有两位母亲[11],并引发有关婴儿归属、抚养权、继承权等法律和社会问题,认为这无法从传统道德和伦理学视角解决[10]。此外,他们指出若后代知道自己的遗传物质来自于三位“父母”,可能会对其产生不良影响[21-22]。
但线粒体置换技术是否让孩子有了两个“母亲”?被称为“三亲婴儿”是否恰当?得知自己通过该技术出生,是否确实会对其造成不良影响?
首先,关于孩子是否有两位“母亲”,将从生物学、伦理和法律三个维度进行论述。
第一,生物学维度。自然生育和第三方供卵的情况下,遗传学母亲与卵子提供者一致,但线粒体置换技术使得卵子中线粒体基因的提供者与卵子核基因的提供者分离,那是否意味着后代有两个遗传学母亲?根据目前的生物学基础判断,线粒体仅与个体的能量代谢有关,而不同于第三方供卵还提供一半的核基因遗传物质,并影响后代的众多生物学特征。如果将孩子比作手机,线粒体则类似于手机电池,而核基因决定了除电池外的其他手机部件总和。如果电池出现故障,更换上功能正常电池以维持手机的正常运行,仍旧称为手机。此外,线粒体遗传物质约占所有遗传物质的0.1%[19],远远少于核基因所携带的遗传物质,且人群中不同线粒体单体型的差异微小[15]。因此,捐献卵子用于线粒体置换的女性并不能被称为遗传学母亲。
第二,从伦理学视角出发,该后代的出现源于某对夫妇的生育愿望,第三方供卵者出于协助这对夫妇实现该愿望而捐献自己的卵子,因此从动机出发,这对夫妇应当被视为孩子的社会学父母。如果我们将线粒体捐献与骨髓捐献或器官捐献类比,即使后两种捐献并不会遗传给后代,但这些的捐献行为与前者一样皆是为了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而非希望成为患者的一部分。此外,相比捐赠者而言,有生育后代动机的夫妇会更充分地为孩子的降生及其未来的发育和发展做准备,故从后代最佳利益出发,有生育动机的这对夫妇应当被视为孩子的社会学父母,捐献者不应被称为该后代的母亲。
第三,法律视角。中国现有法律规定,通过第三方供卵生育的后代,其母亲应为自然人母亲,即规定生母为孩子的合法母亲。在线粒体置换技术的应用中,在不使用代孕的前提下,卵子核基因提供者与生母为同一人,被法律认可为母亲,而线粒体捐献者在法律上不被称为“母亲”。如果我国开放利他主义的代孕,且夫妇不但使用线粒体置换技术,还使用代孕母亲生育后代的话,自然人母亲与卵子核基因提供者分离。此时,我们可以通过符合法律和立法精神的契约,或通过立法规定孩子的归属。因此,即使现在开放线粒体置换技术,关于父母的权利义务、孩子的赡养,及财产继承等问题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得到妥善解决。
其次,从以上论证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生物学、伦理学还是我国现有法律层面,线粒体置换技术并不会使孩子有两位“母亲”。将通过该技术生育的后代称为“三亲试管婴儿”是不恰当的。这种称呼不但容易让公众产生误解,不利于公众政策制定中公众的参与,更可能会加深对后代的歧视。
最后,一些针对通过第三方捐献配子出生后代的调查显示,当后代了解到自己的出生方式后,会对其造成心理、精神上的伤害,试图寻找自己的遗传学父母[21-22]。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其中一项研究样本量仅为16人[22],且在英国开展,难以作为充分的证据支持这种伤害会普遍发生。这种伤害可以被避免或降低其风险,如我国对第三方供精或供卵采取双盲政策,即捐献者和受者夫妇皆不知道对方可识别的身份信息。有研究显示,大部分被访者在接触配子捐献者后认为这对自己产生了积极作用[21]。这意味着在我国现有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后代与线粒体捐献者取得联系,通过正确的引导未必会产生坏的结果。最后,提供核基因的卵子捐赠与仅提供线粒体的卵子捐赠存在差异,前者使后代的出生成为可能,且影响后代诸多形状;而后者使后代免除线粒体遗传疾病的发生,并仅占后代所有遗传信息的0.1%。此外,这还与个体的同一性有关,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论述。
3 结论
线粒体置换技术作为生殖系基因治疗的一种方法,在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用于治疗/预防严重线粒体疾病时能够得到伦理学辩护。该技术并不会使现有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造成混乱,通过此技术生育的后代并没有两位母亲。将其称为“三亲婴儿”或“三亲试管婴儿”是不恰当的,建议媒体和公众讨论时慎用这类词语,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甚至加深对后代的歧视。
由于线粒体置换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存在争议,对于我国而言,在开放该技术前,应当召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就技术应用的风险和受益进行评估,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同时,完善我国线粒体遗传性疾病的发病率统计,确定相关领域研究和应用的紧迫度,促进医疗资源的公正分配。
〔参考文献〕
[1] HFEA statement on mitochondrial donation[EB/OL]. (2017-03-15)[2017-12-08]. https://www.hfea.gov.uk/about-us/news-and-press-releases/2017-news-and-press-releases/hfea-statement-on-mitochondrial-donation/.
[2] LIGHTOWLERS R N, TAYLOR R W, TURNBULL D M. Mutations causing mitochondrial disease: What is new and what challenges remain?[J]. Science, 2015, 349(6255): 1494-1499.
[3] PARK C B, LARSSON N G. Mitochondrial DNA mutations in disease and aging[J]. J Cell Biol, 2011, 193(5): 809-818.
[4] BROWN D T, HERBERT M, LAMB V K, et al. Transmiss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disorders: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J]. Lancet, 2006, 368(9529): 87-89.
[5] BITNER-GLINDZICZ M, PEMBREY M, DUNCAN A, et al. Prevalence of mitochondrial 1555A-->G mutation in European children[J]. N Engl J Med, 2009, 360(6): 640-642.
[6] ELLIOTT H R, SAMUELS D C, EDEN J A, et al. Pathogenic mitochondrial DNA mutations are commo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Am J Hum Genet, 2008, 83(2): 254-260.
[7] PARIKH S, GOLDSTEIN A, KARAA A, et al. Patient care standards for primary mitochondrial disease: a consensus statement from the Mitochondrial Medicine Society[J]. Genet Med, 2017, 59(5).
[8] MAJAMAA K, MOILANEN J S, UIMONEN S, et al. Epidemiology of A3243G, the mutation for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lactic acidosis, and strokelike episodes: prevalence of the mutation in an adult population[J]. Am J Hum Genet, 1998, 63(2): 447-454.
[9] HERBRAND C. 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Techniques: Who are the Potential Users and will they Benefit?[J]. Bioethics, 2017, 31(1): 46-54.
[10] 何美颉,蔡奥捷,司琪,等.“三亲试管婴儿”技术的伦理学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3):319-322.
[11] 王张生,唐增,周韵娇.“三亲”体外受精技术治疗线粒体疾病的反思[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28(5):679-682.
[12] 封欣蔚,杨小丽.对“三亲育子”技术的伦理审视[J].医学与哲学,2016,37(19A):25-28.
[13] REINHARDT K, DOWLING D K, MORROW E H. Medicine. 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evolution, and the clinic[J]. Science, 2013, 341(6152): 1345-1346.
[14] TACHIBANA M, AMATO P, SPARMAN M, et al. Towards germline gene therapy of inherited mitochondrial diseases[J]. Nature, 2013, 493(7434): 627-631.
[15] MITALIPOV S, WOLF D P. Clin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mitochondrial gene transfer[J]. Trends Endocrinol Metab, 2014, 25(1): 5-7.
[16] Medicine I O, Pvational Aeademies of Sciences E,Medicine, 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Techniques: Ethical, Soci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M].Washington DC:The V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6:200.
[17] BREDENOORD A L, DONDORP W, PENNINGS G, et al. Ethics of modifying the mitochondrial genome[J]. J Med Ethics, 2011, 37(2): 97-100.
[18] PALACIOS-GONZALEZ C. 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techniques: egg donation, genealogy and eugenics[J]. Monash Bioeth Rev, 2016, 34(1): 37-51.
[19] GEOFF WATTS, PETER BRAUDE E A. Novel techniqu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mitochondrial DNA disorders: an ethical review[R]. London :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12.
[20] LEWENS T. Human Nature: The Very Idea[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2, 25(4): 459-474.
[21] JADVA V, ET AL.Experiences of Offspring Searching for and Contacting Their Donor Siblings and Donor[J]. 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 2010, 20(4):523-532.
[22] TURNER A J, COYLE A.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donor offspring? The identity experiences of adults conceived by donor insemin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ling and therapy[J]. Human Reproduction, 2000, 15(9): 2041-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