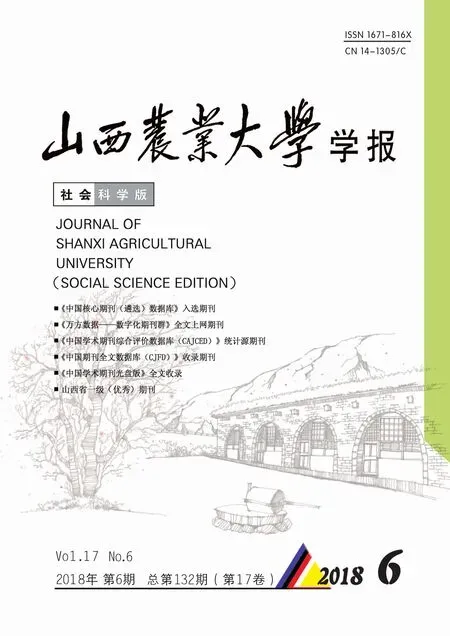“污名化”与“农民工”主体性的双重建构
李向振,李佳浩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过去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封闭的农耕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开放的多元化社会转变。正如王春光总结的那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城乡社会流动的频繁构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三大重要社会变化”[1]。作为城乡社会频繁流动的主体,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而这些从乡土社会来到大城市打工的人们,也逐渐被贴上了“农民工”的标签。从学术研究上看,对于进城务工农民群体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研究视角也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冲突与失范、社会网络、社会融入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到宏观问题分析,到日常表达与叙事、身份构建与认同等微观生活方面,不一而足。然而正如郭星华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著述在研究策略上大多是秉持一种“客位”立场,“大多是从外在的制度、社会或经济层面来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进行审视,忽视了农民工生活实践的主体性、能动性;看到的更多是农民工在结构下的被钳制,忽视了在被钳制状况下他们的生活智慧和生存策略”[2]。事实是,在国家与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农民工群体对于个体处境及社会角色定位另有一套话语体系。很多时候,正如田野资料显示的那样,进城务工农民自称“农民工”恰是对主流话语的反抗。当研究视角转向进城务工农民群体时,不难发现,“农民工”这个极具标签性质的词汇,实际上是多种话语体系的博弈。戈夫曼将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受损身份”概括为“污名”,并分析了蒙受污名者的自我感受以及他们与“常人”间微妙的互动[3]。这为本文继续关注“农民工”这一概念对进城务工农民身份形塑作用提供了理论方向。本文认为,对进城务工农民群体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对“农民工”概念及其内涵地生成过程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从主体立场理解和分析该群体的当下处境及日常行动策略。
一、从“盲流”到“民工”: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成历程
农民进城务工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而将进城务工农民贴上“农民工”标签却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事情。在传统社会,受“重农政策”影响,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并非常态,而且这些进城农民也极少以在城市生活为进城的目标,原因之一是古代城市主要经济形式是包括商业在内的服务业,这些行业门槛较高且所能提供职位有限,难以承受大规模进城务工农民的生活生存需要,同时城乡间经济和社会资源差异并非很明显,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因此,整体上,古代社会农民在城乡间流动,规模并不大,也未能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建立,城乡间差异日趋明显,尤其是在各种资源分配上,城市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到清末民初,随着传统城乡关系被打破,乡村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再加上其他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破产,这些破产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谋生。不过,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这批进城务工农民真正留在城市中人并非很多,大多数在农业经济稍有改善时,还是回到乡村继续从事农耕。总体而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多数时间是处于动荡之中,进城务工农民并未形成太大浪潮,也未能引起学界及社会知识精英的过分关注。
进城务工农民真正引起社会注意甚至成为社会问题是1949年之后。从时间上看,从1949年到现在,六十多年时间里,作为一个群体称谓的“农民工”的生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50年代初,为恢复战争期间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当时中央政府制定各种政策重点支持和鼓励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迅速建立工业体系,采取优先发展城市的策略。以此为背景,许多农民开始凭借技术或力气来到城市,从而变成早期的“城里人”*为了限制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无序流动,1953年开始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务工,这些盲目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当时被称为“盲流”。。不过此时尚没有形成“农民工”的说法,虽然部分城里人对农村来的人持有偏见,但总体性歧视和污名并未出现。50年代末,中国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城市粮食等社会资源供应不足,同时也为保证农村劳动力数量,维持粮食和农产品的稳定产出,国家开始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参见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之规定。,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同时也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自此,国家通过种种举措和措施,最终使得城市与农村,不仅从地域空间上出现分化,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和社会资源分配与政策配给方面,也呈现出极为明显地分化。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本质差别被精心的制造出来,并且关于这种本质差别的理念和物质不平等的形式之间的契合也变得越来越紧密[4]。不过,虽然政策和制度上,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出现分野,但由于长达二十多年的集体农业时代里,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直接交流并不多,对于大多数城里人来说,他们对于农村人的成见更多是来自想象和书本知识,再加上社会上对“劳动人民”的正面宣传,因此并没有形成厌恶的态度。
第二阶段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顺利开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生产出来。到80年代中期,受土地资源本身的限制,土地产出增长率放缓,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新长成的劳动力不得不去寻找农村之外的就业途径,而此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开展,城市社会资源及就业机会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求。为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因此不得不强化旨在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为维持农村社会秩序及改善农村生活水平,国家出台大量政策以助力扶持各式各样的乡镇企业。事实是,为发展乡村经济,国家在农村地区实行了许多改革,通过向乡镇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强化农村村办或地方政府集体举办企业优先,并要求城市工业可以向农村企业输入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市场也不断对乡镇企业开放。有赖于这些举措的实施,短短数年内,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农民流动被称之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些流动人口,从身份上看仍然是农村户籍,而且拥有土地经营权,属于农民行列,同时他们所从事的又大都是第二三产业,与其他产业工人无异,这样一种兼具农民和工人属性的群体诞生了。由于该群体采取的是离土不离乡的流动方式,大多数剩余劳动力被乡镇企业就地吸纳,也未形成大规模进城现象,所以在此阶段,流动农民群体也没有受到城里人歧视,相反,他们在亦工亦农中率先富裕起来,还成为许多城里人羡慕的对象*需要说明的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有许多新生劳动力突破种种藩篱,来到城市务工或做小生意,不过这些人被当时的政府称之为“盲流”,是受到打压或者抵制的对象。在政府主导的话语体系影响下,“城里人”对这些人也是充满了偏见的。。
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今。1984年前后,随着城市里国企改制进入实践阶段,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寻求生存的压力增大,再加上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国企开始和乡镇企业形成竞争关系。不过,由于国企改制时,乡镇企业已经形成规模,二者在市场竞争中国企处于不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乡镇企业过分发展,从而导致社会总供给失衡,国家农业部出台《关于乡镇企业情况和治理整顿意见的报告》,明确了城市发展取向,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乡镇企业改制或倒闭破产,随之而来的是原来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寻求他径以谋得生存需求。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开始调整户籍制度,对进城务工农民限制越来越松。由此,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并在80年代末期形成所谓的“民工潮”,“农民工”群体也就此走进城里人的日常话语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1992年后,为更好地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市场化改革,在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下,乡镇企业有了部分复兴,并在三四年时间里重新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改制日益深入,国企成为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不少乡镇企业逐渐衰落,到1995年后,随着私有制改革的实施,乡镇企业再次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大批私营企业兴起。到2000年前后,进城务工农民进入东南沿海地区私有企业的格局已经基本定型。虽然后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局部地区出现过进城务工农民的反向浪潮,但总体而言,迄今为止,进城务工农民流动格局尚未发生实质转变。
二、市场化机制的引入与当前进城务工农民潮
如前所述,80年代初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的大幅度调高,换得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在其他政策,比如市场逐步放开等因素的影响下,实现了自给自足并有结余的农民,将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并利用这些收入改善日常生活。比起集体农业时代,尤其是集体农业时代的后期来说,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各种市场也日渐丰富趋繁荣,尤其是农用物资市场,已广泛采用先进农具或进口肥料等农用物资的农民,越来越依赖市场。农用物资市场的繁荣,进一步拉近了农民与整个市场的联系。农民开始频繁参与市场交换,逐渐成为市场主体之一。到1985年前后,土地产出值达到极限。此时,在农业种植技术及农用物资未能实现大规模提升的前提下,依靠劳动力的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已经难以实现。换言之,农民在土地上的付出回报率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卷入市场体系的农民,所面临的生活风险迅速增加。
除此而外,虽然早在60年代初,国家层面已经提倡计划生育,到80年代更是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但在农村地区,仍有不少村民基于复杂因素多生超生。在已经失去集体时代“人多力量大”优势情况下,被解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未成年的潜在劳动力,相对于家庭收入而言,都成为纯消费者。这对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形成较大威胁。90年代后期,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措施的逐步实践,教育、医疗等费用成为农村村民重要开支。在收入来源有限,且开支增多的情况下,不少农村家庭陷入困境。甚至出现某种悖论,即国家经济越发展,市场越繁荣,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农民就变得越贫困。由于农民日常生活与市场联系更加紧密,而土地产出已经难以满足生活水平提升的需要,此时,农民必须提升自身劳动力价值,而最佳的途径就是变成所谓的“农民工”。无论如何,从事工业生产所得收入比单纯从事农耕高出很多。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城乡间也不平衡,因此边远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难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工作职位,于是,这些人不得不大规模背井离乡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工挣钱,而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家中,维持农耕生产,形成所谓的“跨地域家庭模式[5]。在这种模式下,年纪稍轻的老年人,还可以经营土地,获得部分农产品用以补给生活需要,或在生活之外,将农产品拿到地方市场进行交换,获取生活补贴。而年纪稍长或尚未成年的年幼子女,则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救济对象”。
对部分农村地区来说,市场化的到来,将依靠传统道德观念建立起来的村落社会彻底打散,其像一台收割机,所过之处,传统的基于道义形成的价值体系,几近崩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而又复杂,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原来温情脉脉的互助关系。村民在参与整个市场机制带来的社会转型时,不得不舍弃在传统社会被极为看重的东西,诸如传统道德、民俗规范等等。金钱的力量是巨大的,原来的共同体被肢解了,农村地区出现了更多的专业分工更为明确的“簿房”,这些村民在农忙时节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一些收入,以用来在更广泛的市场上,获取其他生存和生活所必须的产品。对于许多村民,聚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进城务工农民而言,与他们谋生手段多元化相呼应的是,其获取收入风险也大大增强。原来依靠种地能够维持温饱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在市场的强力渗透下,他们不得不在粮食生产之外,想方设法获得更多的收入,由于手工业被取代,简单的日常生活必须的物品,现在都变成了商品,都需要在市场上通过交易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对于生存安全的感受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种植业固然能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但要追求相对好一点的生活水平,则必须离开土地。因为土地的回报是实物产出,而实物变成金钱需要任由市场的波动来决定。换言之,对于许多村民来说,“种地”这一在传统社会中较为稳定的经济行为,现在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一些依靠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村地区,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为了获得持续性收入,许多村民不得不寻求更多的途径来增加收入来源,比如他们会尽可能的外出打工,或者在农忙时赶紧完成自家农活儿,而与他人一起组成出卖暂时劳动力的短工,成立半专业性质的短期“簿房”,可以看作是村民增强自我剥削的例证。年轻的村民则选择了外出务工,尤其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相对比较边远、闭塞的农村,大量的村民走到了远离家乡的大城市。
三、“城里人”、知识分子与成问题的“农民工”
80年代以来,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群体的日益壮大,城里人与农村人从地理意义上的分野变得越发模糊,“农村人”长期以来被知识分子和城市精英塑造的贫穷、落后、不讲卫生、愚昧等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标签,从后台走向了前台,由“不可见”走向了“可见”,并实实在在的进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6]。面对涌入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不少城里人认为农村人“侵占”和“掠夺”了更多原本属于他们的社会资源,因此从心理上他们更加疏远这些农村人,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农民工”这一略带贬义色彩的的词汇的出现。
与其说“农民工”是一种称谓,倒不如说是一种标签。这种象征身份的标签,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被知识精英与城市人认同为“落后”,或秩序破坏者的形象。直到现在,在很多人眼里,“农民工”仍然是“麻烦”的制造者或来源。在这种语境下,来到城市里的“农民工”彻底成了城市的客体和对象,他们要么成为被身在城市里生活的学者的同情对象,要么成为被鄙视和嘲笑的对象。总之,他们被构建成了沉默的对象而不是说话的主体[4]。
从学术研究来看,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被许多知识分子想象成为弱势群体的形象。作为知识精英,他们不愿意像其他城里人那样鄙视“农民工”,但不可否认,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中,“农民工”这一群体又的确是一种问题的存在,是需要被“拯救”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近几十年产生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北地区大搞“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李景汉等人,就是站在一种审视农村社会和农民行为的立场上,将农民的特征归结为“愚、穷、弱、私”,正如赵旭东所分析的,这些被称之为“病症”的特征,也许在某些村民身上有所显露,但绝不是在每个农民身上都会发生这类“疾患”。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带有明显污名化倾向的定论,却深深地影响着那些没有去过乡村、对乡村人并不了解的城里人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乡村及农民理所当然的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病态群体[7]。
80年代以来,媒体和出版物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呈现也对其大众形象有所影响[8]。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在进城务工人员日常生活中的断裂及在文化价值、理念方面的冲突,因为这些外来流动人口被视为夹在已然离开乡村世界和即将踏入城市生活空间。正如学者张鹂所说的,“不管是官方还是城市公众话语,都将流动人口刻画成为没有历史的、无差别的劳动力所进行的无定型(amorphous)流动。流动人口通常与自己有欲望、梦想、目的的活生生的个体无关,而仅仅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粗劣的劳动全体”[9]。
四、政府政策与“农民工”的制度性污名
进城务工农民被污名化,除社会知识精英和城里人歧视性态度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国家政策造成的制度性污名。如前所述,50年代末的户籍制度,“当代中国城市农民工的附属地位源自一直以来实施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规制与市场力量的释放之间独特的结合。”[4]城市里的雇主以更低的工资和待遇雇佣大量农民工,虽然并不是户籍制度本身所带来的问题,“户籍知道本身并没有创造这些实践,但是它已经成为这些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4]在此过程中,户籍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将籍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的文化分割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予以制度化,这就使得农民工一旦来到城里,他们便被剥夺了主体性,从而变成了客体。城市雇主们给予他们更低的待遇和报酬,实际上得到了包括农民工自身在内的许多人的普遍认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曾经严格限制人口区际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户籍制度逐渐失去了原有意义,意识到此问题的政府开始制定系列政策和法规。这些新政策法规,在户籍制度之外,重新确定了一套能够支配外来流动人口生活等方面的制度体系。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关注了像监狱以及精神病院这样的制度如何能够使得资产阶级的社会如何用更加弥散和隐秘的“规训权力”或者“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取代了建立在压抑与禁止基础之上的集权式的和等机型的控制形式,通过对于身体的规训而作用与个体之规训权力,创造了自己约束自己的对象。为解读“农民工”这一带有标签性质的群体,提供了理论视角。国家对于“农民工”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相对于集体时期以户籍制度进行严加限制农民流动而言,改革开放后对于农民工流动国家采取了更隐蔽的规训方法。正如经验所展示的那样,国家一方面鼓励农民工走向城镇走向城市,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政策或文件形式,将进城务工农民看作是“弱者”,是“既成事实”的当然的社会问题存在。这样,整个所谓的“农民工”群体就被隐蔽的打上了权力规训的烙印。换句话说,当提起农民工问题时,城里人的首先反应是,“这是一群有问题的人”。尽管城里人并未言明但也可以推测出,在城里人眼中,农民工是“次级”的或“低级的”存在。这也正符合了福柯所说的,规训的权力要求有一种有关对象群体的知识实体创造,当农民工这一群体被从农民群体里剥离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就变成了社会知识经营的一种客体,他们的主体性正是在学者们呼吁给予其主体性的过程中逐渐消失,最终他们真的沦落成社会的客体,他们的所有行动都被打上各种烙印,或者是基于同情,或者是基于厌恶,或者基于其他感觉方式,真正属于农民工自己的声音被社会噪音所吞噬了,直到农民工群体接受外界给予其形象和角色的定位,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时,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已经彻底消失,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已经是被社会所规训了的。农民工群体自己日益被召唤去填充那些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所创造出来的对于他们认同的建构,他们因此失去了对于他们共同认同或者界定自身的能力的控制。
五、“农民工”的自我隔离与主体性建构
与主流话语将农民工构建成城市客体不同,农民工群体对于自身主体性的构建则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特点。一方面,在叙述中他们认为自己是从偏远农村来到大城市,是从落后贫穷的地方来到了象征富裕与现代的城市,主体地位从边缘来到中心,而这也是牵引他们来到城市谋生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许多进城务工农民,尤其是年轻人,采取的往往是“去农民化”实践,即他们不愿意让城里人知道他们是农民,或者他们会宣称“早已经不会种地”等话语,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主流话语的逼迫下,承认自己的城市客体地位,采取自我隔离的生存策略,从内心深处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是“城里人”眼中的“他者”,而与此同时他们作为村子里走出来的人,本身又成为村落里的中心人物,这是构成他们时刻准备回归故乡,并对融入城市生活非但不认同,反而有所抵触的内在原因之一。此时,作为外在因素的户籍制度或其他社会政策,显然不足以解释进城务工农民的这种自我客体化的心态,“他们所具有的‘农民意识’更多是从祖辈、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是对‘乡土意识’、‘家族意识’的一种集体意识的继承”[2]。
这些进程务工的农民,在长期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后,逐渐生成一种自我隔离的倾向和生存策略。他们在将城市人对象化、本质化之后,开始在隔离中建立另一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建立在对城市的排斥与不认同,他们与城市和城里人的关系,仅仅是在物理空间上处于一体,在心理上则是高度疏离[10]。正如笔者在北京进行田野时,当地某拉面馆老板王永强所说的那样,“他们城里人就是牛气,可是牛气有什么用呢?我们不和你来往。现在什么事儿都是钱的事儿,钱办不了的,城里人也办不了,他们瞧不起我,我还看不上他们呢”*讲述人:王永强,刘晓芳的丈夫,厨师,生于1972年,90年代中期来北京务工,二人于2008年在姚村开办西北拉面馆至今。讲述时间:2014年3月28日,讲述地点:北京姚村西北拉面馆内。。像王永强一样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很早就离开了土地,来到城市谋生,并身怀一技之长,但他们仍然希望在年纪大点时,攒的钱足够多时,就在县城买个房,在家乡开办小餐馆。作为传统农耕文化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飞黄腾达”后荣归故里,成为许多外出进城闯荡的农民内心最实在的梦想,他们不是不喜欢城市生活,而是家乡自有一种他们割舍不掉的情感,或者说,家乡自有他们能够表达“成功”的场合。在乡亲们面前能够“抬起头来”成为这些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勤奋努力的农民们宣示自己价值的重要着力点。当笔者问起拉面馆老板娘刘晓芳是否感到受到歧视时,她告诉我:这有什么受歧视的,本来我们就不是北京人啊,为什么要户口,我们又不是黑户,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兰州的。也有些人想一辈子在这里住,想得到户口,大多数像我们一样的人,对这个没有太大的要求。我们都是年轻的时候,在这里挣钱,年纪大了就回去了*讲述人:刘晓芳,讲述时间:2014年3月28日;讲述地点:北京姚村西北拉面馆内。。
大概也正是基于此,进城务工农民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正如田野资料显示的那样,他们将不利的身份藩篱转化成了有利的劝导性因素,当他们受到城里人欺负时,他们群体之间或自我之间会相互安慰“谁让咱们是农民”,这种看起来对于农民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并非消极避让,而在笔者看来更多是他们在大城市夹缝中生存形成的一种生活智慧罢了。
六、结语
在主流话语、制度安排和自我隔离的多重夹板下,进城务工农民群体失去了主体性,他们成为以“农民工”为标签的被表达的对象,他们的生活自然也就缺失了自己。对于这些曾经心怀城市梦的进城务工农民来说,虽然身处城市空间,但城市生活距离他们又是那么遥远,当初离开故乡的决绝被城市生活的区隔击退,他们开始眷恋故乡,而这又使得他们更难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在诸多不利因素中,并非没有作为,而是艰难的建构着自己的主体性,尽管这种主体性看起来是微弱的,尤其是在面对各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时,他们的力量更是显得不堪一击,但他们仍然在夹缝中发挥自己所长,在这个既不认可他们,他们也不认可的生存空间里,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一种新的默会知识体系得以生成。这种知识既不同于农村生活中的传统经验,又与之难以完全分离。这些知识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处理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时所施为的社会行动的主要准则。
总之,作为研究者需要站在“主位”立场,秉持“主体—实践”的研究路径,以进城务工农民的日常生活及感受为基础,对他们的生活进行“深描”,分析该群体在进城务工时寄身特定的生活空间中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同、身体感受以及群体内部差异,进而分析这些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在处理群体内部、与村落原有村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所运用的生活智慧和采取的生计策略。沿着日常生活的路径,进入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世界,同时坚持“主位”研究立场,让这些人自己站出来说话,成为叙事、表达的实践主体,而研究者的任务应该是通过亲身体验,去理解他们的言行背后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1.
[2] 郭星华.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52,168.
[3] [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8,92.
[5] 熊辉.群体偏见、污名化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民族论坛,2008(3):41-43.
[6] 李向振.跨地域家庭模式:进城务工农民的生计选择[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5):63-71.
[7] 赵旭东.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3.
[8] 黄典林.从“盲流”到新工人阶级——近三十年《人民日报》新闻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J].现代传播,2013(9): 42-48.
[9] [美]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重构[M].袁长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34.
[10] 朱力.中国民工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