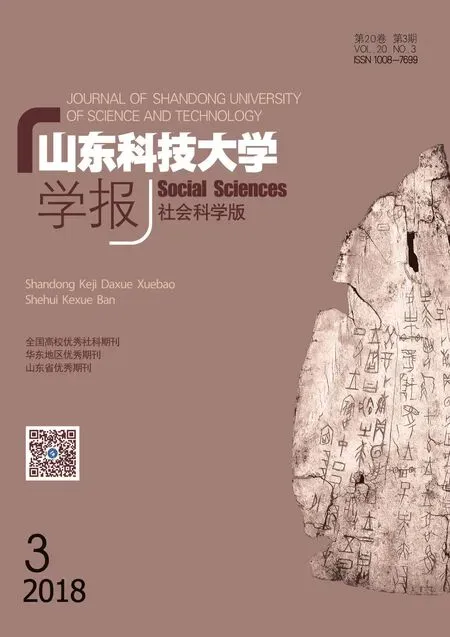海洋生态保护的法治要求:海环法修订视角下的实证解读
,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自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后,国家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一直大力推动法治海洋建设。而随着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纳入,“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给我国海洋生态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法治要求。换言之,就是要“强调自然—社会(人类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和生态价值”,[1]将海洋生态保护理念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立法的重要依托,实现海洋生态保护的法律化和制度化。这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加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法背景
1992年,《里约宣言》和联合国《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随后,我国1994年审议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确立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表现出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可。其中,《里约宣言》强调:“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将环境保护作为其积极追求实现的最基本的目的之一”。[2]与之相呼应,我国于1999年对1982年通过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环法》”)进行了首次修改,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为了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海洋环境保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中不难发现,我国早期就非常重视海洋开发利用中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但是,“由于早期的海洋环境问题主要是污染问题,因此法的重点主要是对各类污染源如何防治的规定,对保护海洋生态只做出了比较原则的规定”。[3]这就导致我国《海环法》从表面的制度设计上来看,其始终呈现着“重污染防治而轻生态保护”的特征。而在海洋环境保护立法方面,“生态保护法与环境污染防治法在指导思想上的最大区别是其贯彻生态本位观、综合生态系统观、生态基础制约或环境承载力有限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4]它要求充分地运用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方法。可见,《海环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许多变化,其本身的制度规定无法体现海洋生态保护的理念变化,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滞后性,无法满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我国《海环法》在2016年11月0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决定》和2017年11月04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决定》的基础上进行了2次修订,正式完成了我国《海环法》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的理念转变,确定了“海洋生态保护”理念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的制度亮点
海洋生态保护的理念转变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海洋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同时其又是我国整体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两次《海环法》修订,我国现行《海环法》对比修订前主要体现了三种较为典型的制度变迁。首先,在海洋生态的系统管理方面,我国首次在海洋领域确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并将其规定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其次,修订后《海环法》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存在了二十多年的“30万元”行政处罚上限的规定被取消;最后,在政府积极推进“放管服”*“放管服”:就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是促使我国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项国家政策。制度改革的大趋势下,《海环法》也提出了以“监督”代“许可”的新型管理模式,并以此为核心调整了相关制度设计。
(一)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确立
“红线”一词起初多见于建筑领域,一般是指各种用地的边界线。正如红灯在交通运行中所标志的“禁止”一样,“红线”的使用体现了这种边界线不可逾越和示警性的特征。“从运行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国土、水利、林业部门均提出过相应的‘管理’红线”,[5]此前在我国存在较多实践。而“生态保护红线”最早作为我国生态保护方面的一项创新性举措出现在国家政策性文件中,是2011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此后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件中,直到2014年我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时首次将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修订后《海环法》在第3条专门增设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国家在重点海洋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海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从而实现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确立。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主要指“依据海洋自然属性以及资源、环境特点,划定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并实施严格保护,旨在为区域海洋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优化区域开发与产业布局提供合理边界,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海洋管理制度”。[6]作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优势是可以通过系统划定重点海洋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海洋的不同生态状况实行严格的分类管控,实现有针对性地允许、限制和禁止开发,从而实现综合管理和分层管理的结合,即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从该制度发展脉络来看,其在国外还没有相关实践,是我国为应对现阶段下“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协调运行问题的一种创新性解决方式。[7]当然,也有学者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与“海洋保护区”制度相类比,认为其均有“生态环境与生物保护”的内涵,是中国过去“海洋保护区”制度的一种转型发展。[8]但总体而言,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设立对于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象征性和实用性的双层含义。前文已提及,我国此前《海环法》在制度设计上更倾向于“污染防治”,对“生态保护”重视不够,这种倾向性实质上是由于背后具体的海洋环境保护理念的不同:“环境强调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从环境污染造成的问题入手;而生态则阐述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侧重维护整体自然环境的安全和人类生存发展的权益”。[9]因此,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制度的设立是我国《海环法》转变立法理念的标志性成果。而在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层面,2015年,我国除了近岸海域污染形势仍较为严峻外,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有86%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10]但根据我国2017年最新发布的《2016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目前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的比例降到了76%。虽然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来源于多方面因素,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设立不可否认地为这些因素更好发挥作用打下良好基础。
(二)行政处罚上限的取消
《海环法》修订前后备受关注的一大制度变化就是对原《海环法》中“违法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相关责任内容的修改,其主要规定在我国《海环法》第九章“法律责任”部分。我国1999年《海环法》在第91条中规定了“违法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事故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按直接损失的30%确定罚款数额,同时规定了30万元的最高罚款限额。在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30万元代表了较大的惩罚力度。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30万元上限的行政处罚金额已不足以对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予以警示。该限制已经远落后于目前相关企业单位的承担水平,丧失了应有的惩罚性。而威慑力度的降低带来的是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疲软。更严重的是,这种限额规定会使我国海洋环境权益蒙受重大损失。
最为典型的就是2011年震惊全国的“康菲溢油事件”。*“康菲溢油事件”,即2011年6月渤海蓬莱19-3油田发生的溢油事故。经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农业部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定,该事故最终造成6200平方公里海域海水污染,其中有870平方公里海域海水受到重度污染。甚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童卫东看来,“康菲溢油事件”正是我国《海环法》2016年那次修改的直接动因。[11]该事故当时被国务院调查组定性为“中国迄今最严重的海洋生态事故和漏油事故”,然而除民事赔偿之外,其仅以行政处罚20万元而告终。反观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事故责任方,美国司法部依据美国《1990年油污法》针对海洋溢油污染对船东增设的无限制责任条款,宣布事故责任方需承担的最终罚款数额高达208亿美元,*中国新闻网:《英国石油因墨西哥湾漏油事故被罚208亿美元》,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10-06/7555903.shtml,2017年11月3日浏览。从而将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成功转化为污染者成本。[12]与之相比,我国海洋环境违法成本太低,不仅油污对我国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害难以得到及时补偿,同时也为我国沿岸船舶海上溢油相关问题的解决埋下隐患。“低污染成本、低处罚力度”的情势急需得到改变。基于此,大部分学者在提高我国海洋环境违法成本、增大处罚力度方面,都提出“加大行政处罚额度、提高行政处罚金额上限”等主张。而修订后《海环法》第90条除了按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严重程度细化了不同的罚款层级,即“‘一般或较大’者承担事故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二十,‘重大或特大’者承担事故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增加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之外,直接将“最高不得超过三十万元”的处罚上限内容删除。也就是说,我国《海环法》在修订过程中针对这一问题选择了“直接取消”罚款限额这一方案,建立了严格的责任承担制度。作为我国在总结并吸收实践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制度变革,行政处罚金额上限的取消大大提高了我国海洋环境违法行为的成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的油污事故大部分是沿海运输船舶溢油事故造成的,[13]这一改变不仅对相关企事业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相关问题的处理预留下空间,有助于更好地保障我国海洋环境权益。
(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既是配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而进行“一揽子”修改的一部分,[14]又是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中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在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我国《海环法》提出了以“监督”代“许可”的新型管理模式。其具体体现在三方面:(1)行政许可事项的取消。原《海环法》在第70条规定了6项行政许可,*原6项分别为:(1)船舶在港区水域内使用焚烧炉;(2)船舶在港区水域内进行洗舱、清舱、驱气、排放压载水、残油、含油污水接收、舷外拷铲及油漆等作业;(3)船舶、码头、设施使用化学消油剂;(4)船舶冲洗沾有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的甲板;(5)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过驳作业;(6)从事船舶水上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修订后《海环法》取消了原第七十条中有关船舶作业活动的5项许可,仅保留了有关“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物危害性货物过驳作业”的审批。(2)审批流程的优化。通过在2016年时对《海环法》第47条内容的修订,前置审批环节大大减少。*原47条规定:“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现47条规定:“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单位应当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编制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并在建设项目开工前,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首先,《海环法》修订后取消了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监督和备案权,现在只需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即可;其次,新修订《海环法》将海洋工程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时间从“可行性研究阶段”改为“建设项目开工前”,给予其更大的自我安排空间;此外,在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基础上,新《海环法》还加入了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选择,即针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可以仅选择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3)监管职能的强调。《海环法》2017年修订时,在入海排污口部分增加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海洋、海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发现入海排污口设置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互相通报机制,实现了双向监督。第70条也明确规定:“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的监督管理”,强调监督管理职责的实际履行。
“基于现代服务行政理念,政府不应当仅仅是利益的裁判者,还应当充当利益的协调者”。[15]因此,为实现行政资源的更为有效利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需要给企业更大的自主空间才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在这一层面上,此次《海环法》修订改变了我国从前政府部门在海洋生态保护治理中占绝对比重的情况,[16]加强了企事业单位在海洋生态保护上的参与度,符合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趋势。当然,针对“行政许可”事项的取消范围,也存在一定争议。例如,罗清泉委员提出,“对于第5项的保留是必要的,但是其他5项中危险化学品可能造成的污染,有可能更为严重,对于5项都取消持有保留意见。”[17]事实上,海洋行政许可本身有它的两面性。积极方面在于可以有效保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有效管理,但同时行政管理权限过大或者使用不当也容易降低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阻碍经济发展。2016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都在陆续减少行政许可数量的同时强调“加强监督”,即“行政许可”的形式取消了并不意味着降低对相应危险污染化学品的管理,因此从制度设计上还是可行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对我国海洋行政管理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海洋环境,尤其是近海环境,总体形势仍然比较严峻,针对相关污染源的管理许可取消给我国未来海洋环境保护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对比态势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正案)》配套制度的完善
《海环法》修订在制度内容的设计上做出了许多突破,设立“生态保护红线”、加大“海洋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以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三个不同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然而,虽然制度规定本身已包含进我国多年的海洋环境保护经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其相关规定仍具有原则性和框架性的特点。法律顺利出台后可形成的指导功能以及对相关理念的固定效果不言自明,其后引申出的问题是,由于缺乏具体的“行为规范”,制度构建后的具体操作成为实践中不可逃避的问题。因此,在《海环法》通过之后,有必要加紧出台相关制度的配套实施方案,明确实施细则,以解决实践中面临的可操作性低的问题。
(一)促使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落地”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从“经济中心”向“生态中心”转变的标志性制度设计,在相关配套制度的出台以及具体操作中均需以“生态保护”作为指导性原则。而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其重点必然离不开“红线的划定”,由于涉及技术性问题,又增加了其实践中的复杂性。因此,为实现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顺利“落地”,必须通过相关规定细化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具体内容,明确海洋生态红线的划定主体、划定标准、程序和方法等,建立起规范化的管理体制。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
1.中央层面,有必要从全局角度出台配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实施规划,以确保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配套制度的协调性。其既应成为各级出台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配套制度的基础,同时也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确定范围。主要应包含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应该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具体性原则。在“生态保护中心”的大概念下,应秉持科学划定、程序法定、统筹协调原则。第二,应明确划定主体。从全国到地方,针对海洋环境保护一直存在着部门管辖范围交叉、权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中央有必要在配套制度中具体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主体,以免增添实践中的复杂性因素。第三,应明确划定标准。不同海洋生态环境的特点以及受损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会产生多样性结果,但总体划定的评价机制需要统一。
2.地方层面,有必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符合当地海洋生态保护现状的具体实施细则。地方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配套制度的规定和出台情况是决定实施效果的直接因素。在符合生态规律和中央指导原则的框架下,地方的配套制度在具体规定上可各具特色,没有固定化的模式。通常需要考虑当地人口数量、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对长期发展进行一个科学性的预测,在此基础上,完善配套制度。
作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基本制度,目前我国围绕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出台的配套制度在中央层面主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范围——即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叠加部分。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和《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明确规定红线划定方案的报送时间、审查内容、标准和程序等。而在地方层面,沿海各省(区、市)主要采取的是制定相关规划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例如《山东省黄海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2016年~2020年)》和《江苏省海洋生态红线保护规划》,这二者均是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开展的相关规划编制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7月海南省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是采取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模式完善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配套制度,可以说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参见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2016年7月29日通过的《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从2017年10月18日海南省向外公开的数据显示,海南目前的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已达到97.7%,是全国生态环境最好的省份。[18]可见,下一步尚未出台具体配套制度以及已经出台但内容尚需完善的相应地方及部门有必要持续推进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工作。
(二)出台“按日连续处罚”的实施办法
“正是由于环境行政处罚权的行使,使得法从文本规定转化为人们实际行为规范”,[19]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环境处罚权的正确有效行使必须要以有明确的实在法为前提。《海环法》修订在加大海洋环境行政处罚力度的制度设计方面着墨较多,“取消三十万元的行政处罚金额上限”只是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点,就这一点而言其似乎并不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指引,只需在直接损害基础上确定罚款金额即可。然而,在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实践中,处罚规定的不断严格化与行政处罚力度的加强并不完全重合。背后存在着海洋行政管理职能交叉、处罚程序不明确、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强制性执行手段等多方面原因。而就《海环法》修订而言,其在取消行政处罚金额上限的同时,还规定了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增加海洋行政处罚手段等。这些规定本质上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实现海洋行政处罚的严格化,但是这些背后的问题尚无法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因此,可以先出台相关配套制度解决现实需要,再在必要时以相关配套制度为基础完善主要的制度内容。从实践来看,“按日连续处罚”作为“取消处罚金额上限”前提下的新型处罚模式,在规定上过于简洁。这样极易导致海洋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这种“自由裁量”在给执法部门造成适用上的障碍的同时,会使相关企事业单位、个人无法正确地衡量评价自己的行为,公民、社会也无法对这一制度的良好运行形成有效监督。从海洋环境保护部门公开的信息来看,已有公民咨询国际海洋局关于“按日连续处罚”的“具体适用程序”问题。*国家海洋局:《关于李杨咨询新〈海环法〉配套规定的回复》,http://www.soa.gov.cn/zmhd/hfhz/201709/t20170901_57655.html,2017年12月4日浏览。因此,为确保“按日计罚”有章可循,必须加紧出台配套的实施办法。
首先,应明确该实施办法同环保部曾就“按日连续处罚”适用问题出台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之间的关系。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本来就存在执法依据多样、混杂的问题,尤其应注意配套实施办法中针对海洋领域的特殊情况所设计的规定可能同其他法律规定矛盾或冲突的情况。其次,应确立“按日连续处罚”的处罚原则,作为统领海洋环境执法管理过程中的最高行为准则。一般而言,在处罚法定原则之外,应注意的是“处罚合比例性原则”的设计,即处罚内容应当与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及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再次,应明确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具体适用范围。《海环法》对此只做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规定,但是否一切超标、超总量向海洋非法排污、违法向海洋倾废而发生污染事故的情形均需适用“按日连续处罚”未加以阐述。因此有必要在配套办法中就具体适用划分一般和特殊情况,以有效地将 “按日连续处罚”的适用情形区分开来。最后,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起算日和终止日。针对连续性或继续性的环境违法行为而言,这二者的确定非常重要,它们不仅决定了整个处罚的周期,更决定了最终处罚金额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因此应当通过科学计算,做出系统规定。此外,“还可使用其他罚种作为按日连续计罚的补充,如停产停业、吊销执照等资格罚,从而避免‘按日处罚’机制在漫长而无谓的执法等待中丧失其可操作性”。[20]而在“按日连续计罚”的具体实施程序方面,应明确具体实施该处罚的主体以及有关部门适用罚款本身设置的不同数额标准的区别,对轻重程度、条件以及这样设计的目的均需加以解释,从而促进相关企业更加明确自己的行为走向,同时增加执法公开度和透明度,接受社会和公民监督。
(三)完成“行政审批改革”的制度接替
从2016年和2017年的两次修法结果来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都是《海环法》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修订过程中,除了减少前置性审批程序、将部分“审批性”事项转为“备案性”事项之外,其主要着力于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的数量。例如,原《海环法》第70条规定有关船舶作业活动的6项许可事项,在修订后删减至1项。前文已提及,制度设计时已经极力强调通过“加强监督”代替“行政许可”,行政许可事项的取消并不意味着“相关行为的完全自由”。但是,同时这也给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可事项的突然取消、相关企事业单位突然被“松绑”,极有可能出现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双方的“不适应”,从而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管理部门对相关事项的管理无所适从,部分企事业单位开始“过度行为”;二是直接修法形式化,对新法修改后的实践积极性差。而鉴于我国目前近海海洋环境污染总体情况仍然非常严峻,虽然有关“船舶在港区水域内进行排放压载水、残油、含油污水接收以及在船舶冲洗沾有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的甲板”等行政许可事项被取消,但是“有毒有害物质”本身种类和具体情况的复杂性决定其仍有可能会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有必要提前预防相关污染后果的出现。
为了使客观实践与制度设计的理想情形顺利接轨,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尽快完成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之后的制度接替工作,通过增加有关部门监督管理的具体内容,真正实现“监督”的“足额甚至超额”的替代性功能。首先,应对相关事项进行合理分类,明确相对应的监督主体。一方面整合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后的相关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另一方面重新明确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避免走向监督管理权限重叠的另一个极端,即各部门间由于权力内容模糊而引起的监督空白。其次,监督形式有必要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对于监督后的结果评价机制也需设计独立的方案。针对不同的结果,应及时收集数据以便于进行立法后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构思创新性管理办法。再次,应细化实施程序。例如,为减少前置审批环节,新《海环法》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核”改为“环保部门审批过程中内部征求意见”。对于具体的审核程序、审核内容等均应进行明确规定。防止有关部门在行使行政裁量权时具有过大的恣意性。最后,建立法律责任保障机制。应针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管理职责规定责任追究条款,针对其具体情形,可以设立责令改正、依法给与行政处分、罚款甚至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多种责任承担层次。通过这种责任机制的设立促使相关海洋行政管理人员增强履职责任感。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正案)》的监督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即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的有效实施,是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构建的最终目的。整体而言,在《海环法》以及我国其他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应有三方面的内容构成完整的“监督”体系: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管理、行政主体的内部监督以及公民和社会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外部监督。前文已论及,针对《海环法》修订中的重点制度在具体实施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出台相关配套制度予以解决,其本质上是完善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监督管理;在外部监督方面,《海环法》修订也增加了“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公开海洋环境相关信息和相关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公开排污信息”的规定,即通过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保障公民和社会监督权能的实现;但关于行政主体的内部监督情况,始终涉及较少。长期以来,在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落实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各涉海部门职能交叉等问题。这种问题对于法律实施效果的影响是破坏性的,更有学者明确指出:“由于一些沿海地方政府及海洋主管部门未能有力地贯彻执行相关政策部署和法律法规,造成海洋环境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严重退化等情况依然十分突出。”[21]因此,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完善的关键期,这种问题的解决是极其迫切的,通过完善行政主体的内部监督以加强对《海环法》等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监督实施显得尤为重要。为解决这一问题,应推进构建统一的海洋督察制度,形成独立运行的海洋督察体系。
“海洋督察”最早出见于国家海洋局2011年7月5日发布的《国家海洋局关于实施海洋督察制度的若干意见(国海发[2011]26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其中规定“海洋督察是指上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所属机构或委托的单位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权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活动”, 即通过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从而确定“海洋督察的本质是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参见国家海洋局2011年7月5日发布的《国家海洋局关于实施海洋督察制度的若干意见(国海发〔2011〕26号)》.而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海洋局2015年9月11日出台的作为生态文明领域改革顶层设计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其后出台的《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年~2020年)》中都明确提及“海洋督察”。目前,我国已有了一定数量的海洋督察实践。2016年12月30日,国家海洋局出台《海洋督察方案》,明确由国务院授权国家海洋局组织实施“海洋督察”。截至2017年9月24日,首批6个国家海洋专项督察组已完成辽宁、河北、江苏、福建、广西、海南6个省(自治区)的海洋督察进驻工作。[22]
由此可见,我国海洋主管部门正在进行“海洋督察”的有益尝试,也取得积极进展。但由于运行时间尚短,依据的也多是“方案”,因此,要建立“统一的海洋督察制度”和“独立的海洋督察运行体系”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制度设计。首先,确立海洋督察的基本原则。在《海洋督察方案》中,海洋督察实践依据来自于“指导思想”,而在具体法律制度构建时,海洋督察应明确“依法督察原则”、“合比例性督查原则”“督查程序正当”等基本法律原则。其次,明确海洋督查的主体。目前实践中的海洋督察主体主要是“海洋督察专项调查组”,尚未形成统一、专门的海洋督查部门。在法律制度构建中,有必要设立统一、专门的海洋督察部门,防止再出现部门管辖权限不明的情况,同时可以保持海洋督察主体的独立性,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第三,在督查方式上,可以采取多样性的监督方式,这也是海洋督察的优势。目前的海洋督察实践中有“定期与不定期、综合与专项、联合与独立、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可以根据实践中的督查情况,在制度设计中吸纳较为成功的经验。第四,强化法律责任。要根本解决国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中贯彻落实情况差以及因此造成的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在责任制度的设计上,要考虑海洋督察相关工作人员作为内部监督主体的特殊性。在惩罚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其作为内部监督主体身份的责任感,增强事前预警胜于事后处罚。“海洋督察”的法律制度构建是《海环法》得到顺利贯彻施行的必然需要。与此同时,海洋督察工作也在持续推进。在法律制度构建之后,关于国家海洋督察程序机制的完善、海洋督察干部队伍建设的加强等也是需要不断推进的工作。
五、结语
随着我国海洋生态保护法律的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在加快形成”。《海环法》的两次修订共达21处,其对确立“生态保护理念”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内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制度构建也吸收了我国多年来海洋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优秀成果。虽然,目前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情势仍较严峻,但就进一步问题解决的实施方案也在不断出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洋生态保护在我国将愈发受到重视,同时设立海洋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严格化和具体化也将是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未来持续的修法趋势。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和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3-4.
[2]吕忠梅.环境法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93-94.
[3]郭院.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4-17.
[4]杜群.生态保护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
[5]黄华梅,谢健,陈绵润,贾后磊,郑淑娴.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的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体系构建[J].生态经济,2017,(33):174-179.
[6]黄伟, 曾江宁,陈全震,杜萍,杨雁滨.海洋生态红线区划—以海南省为例[J].生态学报,2016,(1):269-276.
[7]人民网.生态保护红线 能更好地留住蓝天绿水吗[EB/OL].[2017-12-07].http://news.163.com/17/0208/08/CCO81SBE00018AOQ.html.
[8]曾江宁,陈全震,黄伟,杜萍,杨辉.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转型发展—从海洋保护区走向海洋生态红线区[J].生态学报,2016,(36):1-10.
[9]白佳玉,程静.论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理论起源与制度创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6,(6):19-24.
[10]国家海洋局.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EB/OL].[2017-10-23].http://www.soa.gov.cn/xw/hyyw_90/201604/t20160408_50782.html.
[11]人大新闻网.新海洋环境保护法取消处罚上限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EB/OL].[2017-12-6].http://npc.people.com.cn/n1/2016/1115/c14576-28861853.html.
[12]白佳玉.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初探——以油污治理为视角[J].西部法学评论,2009(5):6-12.
[13]白佳玉.我国海上船舶溢油事故损害赔偿法律问题研究[J].航海技术,2012(2):63-68.
[14]首都之窗.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拟一揽子修改,为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铺平法律道路[EB/OL].[2017-10-23].http://zhengwu.beijing.gov.cn/zcjd/gjzcjd/t1340836.htm.
[15]白贵秀.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36.
[16]杨振姣,吕远,范洪颖,董海楠.中国海洋生态安全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研究[J].太平洋学报,2014(3):91-97.
[17]新华网.提高处罚标准让违法者付出代价[EB/OL].[2018-04-27].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6-11/02/c_129346695.htm.
[18]人民网.十九大召开首日 海南代表团讨论向记者开放: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使命[EB/OL].[2017-10-23].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18/c414305-29595090.html.
[19]李铮.环境行政处罚权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35.
[20]程雨燕.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研究[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13.
[21]搜狐新闻.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EB/OL].[2017-11-13].http://www.sohu.com/a/124972286_114731.
[22]政府网.首批国家海洋督察组完成督察进驻工作[EB/OL].[2017-10-23].http://www.gov.cn/hudong/2017-10/02/content_52292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