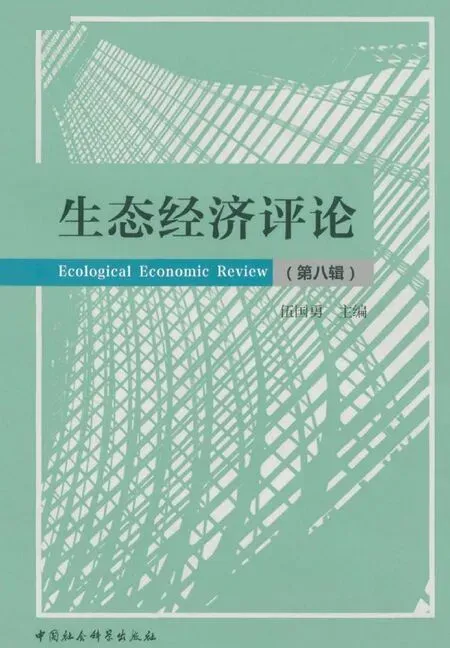从土地看南亚社会农村妇女的自我赋权
——兼论比娜·阿加瓦的“讨价还价”策略*
康 敏 张墨北
内容提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由于不断地抗争和自我赋权,南亚地区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近些年来有了显著提升。印度发展经济学家比娜·阿加瓦提出,讨价还价是妇女自我赋权的重要手段,土地则是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阿加瓦具体分析了影响妇女讨价还价能力的八个因素,并将在家庭内部的讨价还价与家庭外部的市场、社区和国家等三个公共领域的讨价还价联系起来。她强调需要区分家庭财产和妇女个人财产,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还呼吁妇女在各个层次上建立起集体合作组织,倡导跨种姓、跨阶级和跨族群的联合,以提升妇女个人的和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南亚地区①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八个国家。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为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极为低下,处境堪忧。然而,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随着南亚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最近这几十年来,南亚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例如出生时女性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1.44 岁延长到2014年的69.56 岁,男性的数据则分别为42.45 岁和66.75 岁; 中小学入学总人数的性别平等指数从1970年的0.553 上升到2014年的1.028; 15—19 岁少女中育有子女的人数占比从1993年的23.2%下降到2006年的16.06%; 能够接受孕期检查和照料的女性人数占比则从2000年的55.899%上升到2012年的72.985%。①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http:/ /data.worldbank.org/topic/gender? locations = 8S),2017年8月20日登录。这些数据的明显改善固然要归功于收入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妇女为争取自身权益所做的努力与抗争也不容忽视。
本文将围绕印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比娜·阿加瓦有关农村土地和“讨价还价”策略的理论,结合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例,分析土地在农村地区妇女自我赋权中的重要性,也探讨妇女自我赋权的可能途径。比娜·阿加瓦在其代表作《属于自己的土地——南亚的社会性别与土地权利》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缺少对财产(尤其是土地)的有效权利,是南亚地区妇女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处于屈从地位的最重要原因,“妇女为自己合法享有土地财产权利而斗争是为南亚妇女赋权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切入点”②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
比娜·阿加瓦出生于1951年,现任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主任,她长期关注印度及南亚地区的农村发展、妇女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2010年,全球发展与环境协会(GDAE)决定授予阿加瓦2010年度里昂惕夫奖(Leontief Prize),该协会联合主任古德温评论道:“比娜·阿加瓦的作品包含严格的理论、经验基础和政策导向型经济学,这正是里昂惕夫奖认可的。她对学问和对经济发展、环境、福利以及性别政策的贡献鼓舞了全球发展与环境协会许多年。”①Development and Well -Being in Times of Crisis (http:/ /www.ase.tufts.edu/gdae/about_us/leontief09.html).2017年8月20日登录。比娜·阿加瓦已经出版了9 本书以及70 余篇学术论文,她的作品被全世界的农业经济学家、女性主义者、环境保护专家广泛引用。在中国,尽管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她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引用,但总的来看,其作品至今没有被译为中文,也没有专门的文献介绍过她的学术观点,大家对她还比较陌生。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将围绕比娜·阿加瓦最重要的代表作来介绍她对农村妇女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的看法。
一 把“讨价还价”作为女性赋权的重要手段
既然在南亚农村地区,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是妇女提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那么,她们又该如何赋权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益呢?阿加瓦的回答是,她们必须提高自己在家庭内部与外部的讨价还价能力。她后来将《属于自己的土地》 中的一章加以充实,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家里家外的“讨价还价”与社会性别关系》②Agarwal,B.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1997,3 (1).的论文,详细阐释了这种“讨价还价方法”③Bargaining 一词是经济学博弈论中的专门术语,阿加瓦在农村妇女研究中应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关于该理论的经济学讨论可参见道格拉斯·盖尔的《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础:动态匹配与讨价还价博弈》 和阿伯西内·穆素的《讨价还价理论及其应用》。(Bargaining approach)。
阿加瓦指出,今天的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再将家庭视为一个未经分化的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基本单位,而是将家庭内部成员的互动视为合作与冲突并存,家庭决策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要取决于家庭成员相应的谈判能力。然而,多数经济学分析很少论及决定家庭成员谈判能力的诸种复杂因素,特别是质性因素,如:社会规范与自我认知在谈判中扮演什么角色? 追求自我利益时的社会性别差异(如果存在的话)可能对谈判结果有何影响? 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把家庭内部的动力学假设成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审视家庭所处的外部社会经济制度和司法制度,以及这些外部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改变。阿加瓦希望能借助于社会性别视角,拓展和完善经济学中的讨价还价方法。为此,她不仅详细分析了决定农村妇女谈判能力的八个主要因素,突破性地将有关性别关系的社会认知与社会规范作为新的质性维度,并且将“讨价还价”行为拓展到了家庭之外的市场、社区和国家等公共领域,揭示了这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影响讨价还价能力的八个因素
阿加瓦指出,分析家庭成员的讨价还价能力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讨价还价过程的复杂性,例如,有些影响因素不容易或不可能使用量化的指标;此次谈判的对象可能是彼次谈判的结果,即需要连续多次谈判; 长、短期来看,讨价还价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 讨价还价过程并不总是公开的、清晰可辨的,有时候仅凭存在讨价还价能力差异这一点就足以昭示其结果……影响讨价还价结果的因素也很多,但总的来说,人们在家庭中的讨价还价能力高低要取决于以下八个因素:1)拥有并控制财产的数量,在农村尤其是指田地; 2)就业机会和其他赚钱手段; 3)可获得的公共资源,如村里的公共土地和森林; 4)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保护人、亲属和种姓群体; 5)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 6)国家的支持; 7)对需求、贡献和其他应有回报的社会认知; 8)社会规范。①阿加瓦在其《属于自己的土地》 一书中只列出了五个因素,在后来的论文中她又增加了“社会认知”和“社会规范”这两个因素,并且把原先合并在一起的“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支持”拆分为两个因素。简而言之,一个人在家庭之外的生存能力越大,她/他在家庭内部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大,家庭成员之间在这些因素上的不平等会导致其在讨价还价地位上的不平等,而性别又是造成这类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这些因素会或独立或相互交错地影响一个人在家庭之外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其中前六个因素是通过影响家庭成员的生存机会和获得家庭外部资源的机会来影响其讨价还价能力,进而影响他们在家庭中的基本生活需要; 而后两个因素,即社会认知和社会规范,既可以间接地通过作用于另外六个因素来起作用,也可以直接地影响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因为在家庭内部,什么成员该配得到何种生活必需品是要受社会认知制约、由普遍的分享规范决定的。
举例来说,在那些传统上实践“父权制”价值观的地方,如印度的拉贾斯坦邦,由于普遍实行外婚制,女性在结婚后就要住到丈夫的村子里去,从而放弃对自己父母的财产的继承权。这些地方的妇女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行动也受限制,基本不认识丈夫家庭以外的人,所以很少有机会在新家建立起社交网络和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加上当地强势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关于一个年轻妇女的“得体行为”的社会规范往往已经被成功内化,这种“女性”行为规范会强化对妇女的身体限制和社会限制。阿加瓦指出,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实践相互交错,削弱了女性的能力和权利,因而也削弱了妻子从丈夫那里获得资源或寻找其他资源的能力。换言之,一个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会在社会认知、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中被明确化、具体化,从而不仅是在家庭空间,也在公共空间里影响人们的讨价还价能力。
阿加瓦进一步指出,上述因素决定讨价还价能力和结果的权重是有所不同的。在制定政策时,务必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分辨出哪些因素更加重要,哪些相对次要。就她本人最关心的南亚农村和农业经济来看,有效控制土地在前六个因素中占据着绝对重要性。
(二)讨价还价的四个场域
阿加瓦显然非常强调家庭所嵌入的外部社会环境和经济政治制度,并且强调讨价还价能力在家庭内部与在家庭外部的密切关系。她在论文中以土地为例加以说明。假设身为一个女儿,其父母并未立下遗嘱自愿授予其土地,那么,她成功获得其父母土地的能力就要取决于以下多种因素:现有的继承法; 社会对其主张的认可,也就是说,即使该主张在法律上无效,也被其社群认为是合法有效的; 她的受教育程度和法律知识; 接近土地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的可能性; 她在其竞争对手(如兄弟或亲属)所提供的支持系统以外获得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能力; 她前往司法机构的经济能力和身体条件。也就是说,妇女要分得家里的土地,就需要与家庭外的社群、国家等发生关系。因此,社会性别差异在家庭内部的讨价还价能力就与家庭外部的讨价还价能力联系了起来。这种情况在竞争土地所有权时尤为突出,因为控制田地有助于获得更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反过来,更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又有助于获得更多的田地。①Agarwal,B.,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1997,3 (1):14.
可见,家庭、市场、社群和国家这四个主要的竞争场域,每一个都会影响妇女的议价能力。同时,这四个场域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例如,相比于印度男性,印度妇女所分配到的公共资源份额或得到的社会自由(基于对改变社会规范的谈判)要比男性少得多,这一是因为妇女往往被排除在制定和修改管理社群规则的公共决策机构之外,或代表性严重不足; 二是因为妇女在家庭内部总是处于劣势的议价能力削弱了她在外部的议价能力,特别是在其丈夫和婆家反对其主张的情况下; 三是在那些实行从夫居和外婚制的地方,已婚妇女无法像男性那样得到来自亲属方面的支持。②Ibid.,31.
二 妇女需要属于自己的土地
比娜·阿加瓦始终关注南亚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发展,其创新之处在于将农村发展与女性主义视角紧密结合起来,并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农村妇女的财产状况进行分析,强烈呼吁农村妇女拥有独立的土地财产权和实际控制权,她认为土地是妇女自我赋权的必要前提。
(一)家庭财产与妇女个人财产需要分别看待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从事着生产、消费、投资等活动,家庭收入被集中起来,由户主根据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配。这种观点普遍假设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合作的,户主(往往是男性)获益等同于整个家庭获益。阿加瓦“挑战了这个将家庭看作未分化单元,其中各个成员有着共同偏好和利益的前提”③Agarwal,B.,Disinherited Peasants,Disadvantaged Workers:A Gender Perspective on Land and Livelihoo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98,33 (13):A2.,认为这种假设忽视了家庭内部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造成“性别盲点”(gender blindness),结果使妇女的利益受到损害。例如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项目中,除了那些家中没有成年男性的女户主(主要是寡妇)家庭之外,土地全都分配到男性名下。这样的性别偏见后来又在重新安置项目中出现,即使是在传统上实行双系继嗣制和母系继嗣制的斯里兰卡也如此。①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8 -9.
阿加瓦提出,如何看待妇女的阶级属性也是她强调区分家庭财产与妇女个人财产的原因之一。她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暗含了一个假设,即妇女的阶级属性是由她的丈夫或父亲决定的,来自有钱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妇女就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来自无产阶级家庭的妇女就属于无产阶级,即使她们本身可能就是工人。但这一假设是不牢靠的,一是因为相比于男性,妇女通过婚姻得到的阶级地位很容易被改变; 二是即使有钱人家的女性,如果没有自己的财产的话,也很难拥有相应的阶级地位。因此,当我们判断一个女性的阶级地位和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时,不能仅凭其家庭财产的多少,还要看女性所拥有的个人财产的多少。
(二)土地是农村中最重要的财产形式
家庭财产可以多种形式存在,如现金、珠宝、家畜,甚至家中的贵重物品(如嫁妆)等,但并非所有的财产形式在所有情境下都同等重要。阿加瓦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广大的南亚农村地区来说,耕地是所有财产中最最重要的。第一,耕地是一种生产性的、可以创造财富和维持生计的资产; 第二,耕地能为人们在当地社群中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第三,在人们心中,土地有着其他资产所不具备的恒久性。尽管其他形式的财产从理论上说都能转换成土地,但实际上农村的土地市场非常有限,可供出售的土地并不总有; 第四,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土地往往都有着购买来的土地所不具备的象征含义:在有些地方,祖先土地的连续性也代表了亲属关系和集体身份的连续性,在有些地方土地还具有仪式上的重要性。①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8.简而言之,土地决定着人们在村子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也决定着家户内外的关系结构。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阿加瓦以印度梅加拉亚邦的加洛人(Garos)、喀拉拉邦的纳亚尔人(Nayars)和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Sinhalese)社区为例,指出在这些实行母系或双系财产继承制的社会里,妇女地位要比那些(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孟加拉)实行父系继嗣制的社会的妇女高得多。
(三)名义上拥有不等于实际控制
从法律规定上看,大部分南亚国家的妇女已经争取到了平等的土地继承权和控制权,例如,2005年印度颁布的 《印度教继承法 (修正案)》 赋予所有印度教妇女,不论未婚还是已婚,与男性同等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尤其是在农业土地方面。②2005年修正案的进步之处还在于:规定了家庭中不论未婚还是已婚女儿都可以居住在娘家中; 规定已改嫁寡妇依旧可以继承亡夫财产。但阿加瓦认为该修正案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女儿的继承权有所增加,那么家庭中寡妇和母亲能继承到的财产份额就会相应减少。而且,法律并没有对遗嘱进行限制,如果父亲在遗嘱中指明将遗产交给儿子,这样的话女儿和遗孀还是无法继承财产。此外,2005年修正案虽解放了广大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妇女,但印度的穆斯林妇女、印度东北部父系继嗣部落中的妇女依旧没有土地继承权。然而,法律上的规定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与实际上的土地控制权仍有很大差距。
一方面,法律上规定的平等继承权未必能得到执行,在现实中能够依法继承土地的妇女很少。从国家机器的层面上看,法律、官僚机构总是制定有利于男性的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土地登记的官员甚至倾向将土地登记在家庭中的男性名下。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印度实现妇女权利的最大障碍是并无真正兴趣赋予妇女以权利的敌意的国家。在印度,其他不利于妇女权利的因素包括:国家的法律与秩序机器不能实施法律和在各级司法机构存在的性别偏见。”③[印度]科蒂·辛哈:《印度实现妇女权利的障碍》,黄列译,《外国法译评》 2000年第1 期。从家庭和社会层面上看,一些传统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认知会严重影响妇女合法继承土地。如很多妇女自己认为,远嫁到外邦的女儿无法照顾父母,所以父母也不可能将财产留给她们; 而且很多地区的家庭认为,既然给了女儿嫁妆,就不应再分给财产; 还有一些人认为把土地分给妇女会导致地块变小或家庭分裂,等等。一旦遇到土地纠纷,也极少有妇女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一是因为她们较少有社会行动自由和诉讼成本; 二是因为她们也害怕会由此被家庭和社会抛弃。
另一方面,就算是妇女继承了土地,拥有名下的土地,但也未必就能成为土地的实际掌控者。比如:深闺制度规定妇女无法和外界接触,从而迫使妇女将自己分得的土地交给家庭中的男性打理,以获得经济利益; 女性普遍认为如果在婆家受了欺负,娘家的兄弟是唯一可能给她提供救助的人,所以将自己娘家得到的土地财产交给兄弟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甚至女性被灌输“好姐妹会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家里其他人”的想法; 等等。此外,农村妇女参与社区决议的机会很有限,这更不利于她们维护自身的土地权利,也不利于她们对这些土地的实际控制。
(四)妇女需要有自己的土地
为什么妇女需要获得独立于男性的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 阿加瓦认为原因有六①在《属于自己的土地》 一书中她只提到前三个原因; 后来在论文里又补充了另三个。:第一,在南亚地区,尤其是半干旱地区,森林和乡村的公共土地正在迅速减少,这意味着补充性经济资源对穷人,特别是妇女的支持在迅速减少。第二,传统的庇护人、亲属和种姓等社会支持体系也在衰退,最受影响的是寡妇和老年妇女。第三,来自有偿就业和其他收入的回报往往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有数据表明,在南亚农村地区,相对于无地家庭,有地家庭中的妇女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非农业收入在其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更大,这是因为有地家庭可以为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开出更高的价格,从而提高平均工资水平。因此,有效的土地权利不仅可以直接抬高妇女谈判的筹码,还可以间接地通过增加其他收入的回报来提高妇女的讨价还价能力。第四,老年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要求得到子女们更好的赡养和支持。第五,在严峻的生存危机发生时,如干旱和饥荒,土地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首先会变卖首饰、家用器具和小型家畜等物品,而将生产性资源——土地保存到最后。在家庭层面上首先变现更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有性别意义的,因为那些东西通常都是妇女拥有的个人物品,而土地通常都在男人名下。结果,妇女就会被置于比男人更加不利的谈判地位,她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也会进一步被贬低。第六,从不同时期来看,土地权利都有助于妇女较少受社会规范的限制,并且得到丈夫更好的对待。①Agarwal,B.,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1997,3 (1):12 -13.
阿加瓦认为妇女拥有自己的土地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福利、效率、平等和赋权。
福利和效率是绝对意义上的,首先,从福利的角度说,妇女拥有独立的土地权可以减少家庭贫困的可能,因为相比于男性,妇女会把自己的收入主要花在家庭开销上; 再加上村里的男性多数到外地打工,因此最依赖土地的往往是妇女。第二,从效率的角度说,在拥有了土地权之后,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会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业产量会相应提高。过去人们往往以为将土地分给个人会导致地块面积变小,从而降低生产效率,减少农业产量。但阿加瓦指出,现存的证据表明,地块变小通常会提高农业产出而不是相反。
妇女获得独立的土地权绝对能产生福利和效率方面的积极影响,而平等和赋权方面的意义则是针对妇女在家中和整个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地位来提出的。一个社会只有达到性别平等,才能算是正义的社会。和土地权利有关的性别平等也有助于改善妇女在其他领域的平等和赋权。在阿加瓦看来,妇女拥有土地权利是她们改善与丈夫和社会的关系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这主要是指拥有土地的妇女能够提高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更好地维护自己权益。简言之,和土地权利有关的性别平等也有助于改善妇女在其他领域的平等和赋权。
三 为争取土地和社会性别平等而斗争
根据以上分析,阿加瓦得出观点说,当前为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而进行的变革必须在物质意义上和符号意义上同时发生,既要为获得财产权而斗争,也要为改变社会性别角色与行为的管理规范而斗争,还要为获得公共决策权而斗争。这意味着我们要挑战现有的家庭内外的社会性别等级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男性和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上的极不平等。在农村地区,土地的分配既是这类权力分配的初始结果,也会对这些权力维度产生决定性影响。阿加瓦认为,土地财产与农村权力之间的互动结果造成了一种难以打破的僵局。但与此同时,重重的阻碍也使得土地权利成为一个可以在多个层面上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关键性切入点。所以,“为土地而斗争很重要”,她说,“不仅是因为其最终结果,还在于这是实现结果的必要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也应当)使妇女在不同层面上的能力得到建设。”①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77.
为此,阿加瓦提出了几条具体建议,包括:(1)改革相关法律,包括继承法和相关的土地改革法案,既要去除现有法律中的性别不平等,还要确保法律得到执行。(2)处理好嫁妆与继承财产的关系。阿加瓦指出,虽然有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已经从法律上禁止了嫁妆,但嫁妆未必只会对女性产生负面结果。在某些地区,人们是把嫁妆看成提前分配给女儿的家庭财产份额,它多少可以提高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嫁妆无论如何都不是妇女谈判的最佳筹码,也不是增加谈判能力的最有效方法,它无法取代财产继承权。(3)建立事实上的土地继承权,必须在地契中明确妇女名下所分得的份额,而且妇女能够保留对那些份额的控制。(4)除继承以外,建设妇女可以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其他方式,为妇女主张土地权利提供更多渠道。(5)探索联合管理土地的模式,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同属一个社区的妇女可以共同拥有土地,她们各自耕种,却共同投资和使用大型设备,这样就使土地真正掌握在妇女手里。(6)建立社团,这至少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分别组建专业化的社团为农村妇女提供服务; 二是在本村的妇女当中组建社团。②Ibid.,pp.482 -490.
阿加瓦非常推崇妇女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她用大量的实例证明,“总的来说,如果妇女采取集体而非个人行动,她们在社区内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能得到加强。但在由多种姓和多阶级村庄里,即使低种姓的贫穷妇女形成一个集体,她们也不如高种姓的富裕妇女强势”①Agarwal,B.,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1997,3 (1):31.。因此,妇女中的跨种姓、跨阶级的联合是非常重要的。从地方层面来看,阿加瓦建议在基层和地方一级建立妇女支持互助小组(类似NGO 性质的小组),以帮助无地的妇女确立自己的土地权利,将土地权从以家庭为单位变为以个人为单位,从而实现妇女对土地的真正可控。此外,妇女还应当更多地参与到现有的决策性机构中去,改变“一户一名额”的代表制度,并在社区中形成集体认同,增加女性之间的合作与自信。从宏观层面上来看,阿加瓦认为应该提高妇女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权,认为只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打破阶级、种姓区分,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整个地区、国家乃至南亚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权利。
四 启示与评价
比娜·阿加瓦长期关注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农村妇女发展问题,她的代表作《属于自己的土地》 是第一部详细讨论南亚地区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问题的开创性作品,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也屡获殊荣②1996年,该书荣获阿难达·肯特·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图书奖、埃德加·格雷厄姆(Edgar Graham)图书奖以及K.H.Batheja 奖三项大奖。。埃德加·格雷厄姆图书奖的评委认为,“南亚妇女土地权利的改变会影响世界一大部分人口的社会和农业发展,而这些人恰恰是弱势群体。此书会成为通向这种改变的大道上经久不衰的里程碑。”③摘自埃德加·格雷厄姆图书奖的颁奖词。
在这部作品的基础上,阿加瓦继续聚焦农业、所有权和环境等问题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性别视角对传统经济假设提出质疑。④Agarwal,B. Gender Challe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她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粮食自足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之间的矛盾、大规模粮食生产与农民自主选择种植作物的权利之间的矛盾,以及通过创新性制度变革取得粮食主权等。①Agarwal,B,Food sovereignty,Food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Choice:Critical Contradictions,Difficult Conciliation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4,41 (6).在一些较近期的作品中,她延续了对集体抗争方法的重视,认为与传统的个人导向方法相比,由穷人团结起来,形成的小规模、自愿性、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积极参与决策的集体更有助于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②Agarwal,B,Rethink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llectivit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10,45 (9).
笔者认为,比娜·阿加瓦关于农村妇女发展的看法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强调土地(财产)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性,提出妇女获得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比就业更重要
如同阿加瓦批评的那样,虽然学术界一直研究妇女与收入、妇女与就业的关系问题,却长期忽略了妇女与土地财产权的研究; 很多由国家或非政府组织设计实施的妇女发展项目也往往把鼓励和提供就业放在首位。她认为这种错误认识的理论来源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全面理解有关。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认为,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两个相互交织的经济因素决定的:妇女所在家庭的财产状况; 妇女参与雇佣劳动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财产的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是等级化的,因为妇女不外出工作,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 而在无财产的无产阶级家庭,性别关系是平等的,因为妇女也外出就业。阿加瓦批评说,很多南亚左翼政党和妇女组织受到恩格斯的观点影响,强调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其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因此把妇女的就业问题置于中心,但恩格斯同时强调的伴随条件,即废除男性私有财产和使家务劳动与孩童照顾活动社会化的观点,却基本上被忽视了。所以说,根据妇女的就业状况来判断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性别关系是对恩格斯的误解。另外,阿加瓦指出,恩格斯也未能区分财产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其学说还需要加以补充修正。
从现实来看,已经成为常识的、衡量男性或家庭经济地位的指标是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但衡量妇女经济地位的首要指标却是就业。①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且不说这是一种双重标准,更重要的是,妇女并不能单靠就业维护自己的权利。例如,在印度,家庭暴力发生的比例是20%—50%,之前的研究总假设女性经济地位和就业有关,但有的研究结果是就业妇女受到家庭暴力比未就业妇女少,有的结果是两者没有太大差别,有的结果甚至是就业妇女受到的家庭暴力比未就业妇女还要多。②Agarwal,B.,&Panda,P.Toward Freedom from Domestic Violence:The Neglected Obvious.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2007,8 (3).
阿加瓦认为土地财产比就业重要的原因在于,土地财产相当于一个场所,可以安置离家出走的妇女,当然妇女并不是一定以离家出走作为唯一选择,但有了不动产,妇女就可以在某些方面震慑住丈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动产相对稳定,安全性也比较确定,而就业得到的收入则受市场影响大,不稳定。我们前面还提到过,有地家庭的妇女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筹码,可以抬高自己的劳动力价格,从而提高工资收入。也就是说,拥有和控制财产(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土地)对于加强妇女在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是很重要的。阿加瓦建议研究者和制定政策者应该将就业与不动产区别开来,并明确了维护妇女权利最根本的是取得土地权和对土地的实际控制。她说:“土地所有权能够提供的要比就业更多,它既能提供更强大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基础,还能在其他几个前沿领域向性别不平等宣战。”③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65.
尽管阿加瓦用的是南亚农村的证据,但依此类推,在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可耕地对农村妇女来说也有着相似的重要性; 在更加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城市里,不动产,尤其是房产对于妇女的重要性也一样; 更扩展一步来说,当更多妇女走向劳动力市场时,我们必须关注她们的劳动收入是否归自己支配,是否能够转化为其独立的财产。
(二)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提出帮助妇女获得土地(财产)比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更为根本
阿加瓦并没有明确说帮助妇女获得土地财产比教育她们认识到自己的屈从地位更重要,但从她对社会规范与社会认知这类影响讨价还价能力的质性因素的分析来看,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社会科学界对于穷人和被征服者如何对压迫做出反应,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比较传统的观点是认为受压迫者完全相信了压迫者的意识形态①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是一种“虚假意识”。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表达了统治阶级运用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等概念系统地掩饰了无产阶级被剥削、压迫和统治的事实。如果虚假意识不复存在,那么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很快推翻现有的统治。,错误地认识了自己真实的经济利益,从而无意识地固化了自己受压迫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观点以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为代表。②Sen,Amartya K.,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In:Tinker,Irene (e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Sen,Amartya K.,Rational fools: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Beyond self -interest,1990.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提高人们对自己所压迫事实的警觉,揭示其真实经济利益所在,就成了变革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对处于屈从和不平等地位的妇女进行教育,唤醒其阶级意识,帮助她们认识到自身的真正权益很重要。
另一种更为晚近的观点则是,被压迫者并不总是被动的受害者,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由统治者确立和传播的意识形态,相反,他们总是会以各种各样隐蔽的和细微的方式抵制压迫。这种观点以詹姆斯·斯科特(1985)为代表。③Scott,James C., 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如果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么受压迫者就被视为了有一定自觉意识的行动者,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能为自己筹划。这样一来,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阿加瓦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现有的经验证据更加支持斯科特的观点,她认为把社会性别不平等归咎于妇女对自我利益的错误认知是站不住脚的,(南亚地区的)农村妇女中并不存在虚假意识,即统治阶级并没有成功地利用虚假意识让妇女们毫无抵抗地沦为被压迫者。妇女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利用各种隐蔽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例如一些妇女会瞒着婆家人将自己的家畜养在邻居家,或者将自己的储蓄藏在洞里、竹筒里或天花板上,有些现在看来属于利他主义的决定(如把土地交给兄弟照管)其实只是为了自己更长远的私利(必要时得到兄弟的支持),等等。但是,斯科特的分析也有所欠缺,因为他没有家庭领域展开调查,仅仅关注日常抵抗的阶级本质,特别是贫农与地主之间的对立,没有探讨性别如何与阶级(或其他形式的社会等级)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决定抵抗的形式。阿加瓦认为,如果我们在审视不平等时只把阶级当作唯一基础,可能就看不出不同性别的抵抗所揭示出多种复杂性。①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422 -42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曾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 页。阿加瓦正确地坚持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破除虚假意识的关键是从变革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着手改变社会现实。她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引入这一原理,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三)国家和组织干预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阿加瓦并没有把家庭看成是封闭孤立的单位,她同样很重视妇女在市场、社群和国家等公共领域的讨价还价能力,并且高度赞扬集体性行动的力量。她的论述也细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首先,她把国家本身看成是充满合作与冲突的竞技场。国家可以通过提供相应政策,促进或阻碍妇女在家庭、市场和社群三个场域的赋权和讨价还价能力。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国家可以与进步的妇女社团/组织合作,制定有利于妇女的法律和政策,协助其开展项目; 可以增加妇女获得生产性资源、就业、信息、教育和健康的机会; 可以为妇女提供保护,使其免受性暴力侵害; 可以影响媒体和教育机构中有关社会性别关系的话语,从而改变落后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改变社会认知和社会规范等。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国家也同样有可能利用其资源和强制机构来加强现有的退步的性别偏见,在家庭和社群内造成冲突。①Agarwal,B.,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1997,3 (1):32.例如从19 世纪后半段以来,南亚地区国家政策的许多变化“使饱含着父权制道德的社会性别观念具体化并得到加强”②Agarwal,B., A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53.,由国家确立的管理规则使社会性别歧视合法化,从而掩盖和强化了当地的父权制实践。
其次,阿加瓦清醒地认识到国家与社团组织进行合作的难度。她认为,国家比较可能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项目类型是那些福利型项目,如医疗健康和教育,或者为穷人提供赚钱机会的项目。国家(尤其是非社会主义政权)比较不喜欢的项目是要求重新分配主要经济资源的项目,如土地,因为这类项目可能会对该国的主要政治选民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在妇女与国家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形成团体来行动尤为重要,社团组织的规模,他们将媒体、反对党和来自国家机器内部的个人/集体的支持汇聚起来的能力都会影响妇女讨价还价能力的高低。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国家理解为一个“天然的、统一的、超越历史的‘男权’ 国家”③Agarwal,B.,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1997,3 (1):33.,而是要看成一个竞争场所,一个内部分化的结构,在其间,不同的政党对于减少(或维持)社会性别宰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承诺,通过在不同层次上发生着的合作与冲突,通过一系列的竞争与讨价还价构成了现有的社会性别关系。“国家可以、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被挑战和改变的对象。”④Ibid.,34.
尽管中国是一个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一直把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视为重要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追求妇女进步的社团组织仍然需要与国家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要求对重要的经济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也并不容易。从近些年来因农村土地征用拆迁引发的多起冲突事件就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比娜·阿加瓦通过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农村地区进行的定量和定性调查,指出妇女独立占有并实际控制土地对提高农业产量、实现性别平等和自身赋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她的理论和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方向,同时也用社会性别视角和经济学博弈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于今天的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发展工作也多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