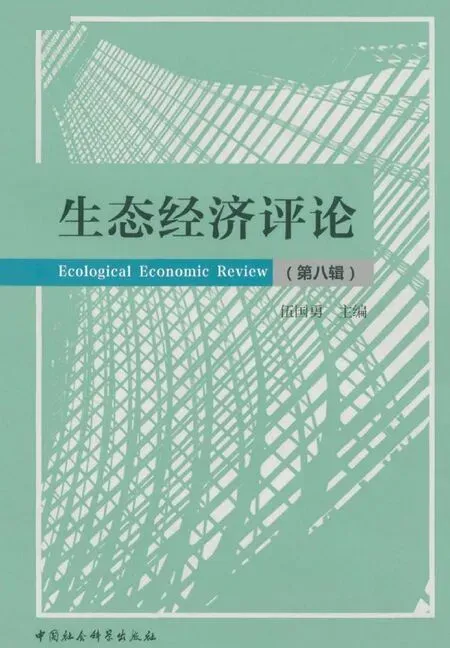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理解佤族剽牛活动*
李文钢
内容提要: 在20 世纪50年代开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中,人们对佤族宗教活动剽牛的认识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佤族的剽牛是一种严重的宗教浪费行为,阻碍了佤族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对佤族剽牛的认识有所深化,将佤族的剽牛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相类比,认为剽牛活动是佤族社会中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行为,其目的是缓解佤族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在本文中,作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把佤族的剽牛活动看成是一种与当地生态环境和佤族社会生产技术相互适应的宗教行为,并非一种物质财富的浪费。
一 问题的提出
据不完全统计,在20 世纪50年代前,佤族社会中剽牛活动有21 个种类,207 个套路。①冯强、卫林:《近代佤族剽牛仪式变迁的研究》,《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第3 期。在佤族传统社会中,最为常见的剽牛活动有猎头、拉木鼓、砍牛尾巴、盖大房子。1949年前剽牛活动的主要程序有:巫师祭天地、唱歌跳舞、拴牛、剽牛、巫师祭牛、勇士砍牛头牛尾、敬献牛头等。佤族全寨性的宗教活动都要剽牛祭鬼,这些费用一般不是由全寨人平均分担,而是由某一户人承担,承担的人便称为主祭人。担当主祭人的条件是要能够承受祭祀的花费,因为每次这样的宗教活动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酒米,以供众人食用; 要剽一条至数条牛作为祭品,杀一条黄牛取肝看卦。佤族学者赵富荣在《中国佤族文化》 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①赵富荣:《中国佤族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 页。:
马散寨1957年1—5月因“盖大房子”和宗教活动剽牛64 头,平均每月剽牛10 余头; 永广大“珠米”岩嘎1957年一次主祭剽牛32 头。佤族以剽牛为荣,许多“珠米”以剽牛显示自己的财富,树立威信。有的中等户和贫困户几代人都剽不起牛,门前没有一棵牛角叉,总是分食别人的牛肉而遭到嗤笑和歧视。于是终年辛苦,省吃俭用,存钱买牛,争取剽一次牛,争得一代人的荣誉,而把多年积累用于一次剽牛的主祭,将客人送出竹楼门后,家里便无米下锅,差钱欠债甚至卖儿为奴。1958年以后逐步革除了这一习俗。
在佤族的剽牛活动中,需要消耗如此多的费用,穷人自然是承担不起的,只能是富裕户承担,至少也得是中等户。因此,在20 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中,调查人员认为:“剽牛对佤族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其一,大量消费社会财富和破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其二,阻碍了牛耕技术的发展,相对地保持了刀耕火种的落后耕种方法。”②《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59 页。对于类似的看法,即使是在20 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改变。例如,学者马廷森认为,新中国成立前与佤族宗教信仰有关的种种仪式行为耗费了大量财富,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产,延缓了阶级分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剽牛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③马廷森:《论佤族的宗教仪式行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年第5 期。罗之基出版于1995年的《中国佤族历史与文化》 一书中也仍然认为:“这样大量的宗教牺牲和浪费,不仅残酷,严重破坏了佤族社会财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严重阻碍了佤族的社会分化和发展。”①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 页。
如果说剽牛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财富消耗行为,为什么佤族建寨最早的大马散寨,到解放时已有400 多年,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剽牛这种频繁的宗教活动? 我们是否可以站在客位的角度,轻易地判断佤族的剽牛对于佤族而言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在汉人社会中,在战争后恢复生产时期,屠杀耕牛会被当作是一种违法行为,而在传统佤族社会中却形成一种社会机制鼓励较为富裕的人家剽牛? 从吉登斯所论述的社会何以可能的角度来看,剽牛作为一种财富消耗行为,对于传统佤族社会的延续有何作用,这是需要人们思考和解释的地方。
关于为什么佤族社会中较为富有的人会心甘情愿把多年辛苦积累的财富在剽牛活动中消耗完,佤族社会也鼓励富裕户将自己的财富在宗教活动中与众人分享,众多的研究者围绕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目前,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把佤族剽牛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看成是同一种类型的人类活动。②王亚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从西盟岳宋佤族“夸富宴”看社会文化变迁》,《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8年。在笔者已有的研究中,指出佤族剽牛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把两者简单地等同看待不利于正确认识剽牛,佤族的剽牛活动客观上还是一种传统社会中风险均分的社会支持行为,有利于佤族社会的延续。③李文钢:《佤族传统社会支持的人类学研究》,《普洱学院学报》 2013年第1 期。除此之外,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早已指出,人类行为和所居住的生态环境是互相形塑的,只有把佤族剽牛这种行为放到佤族所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更加深入和完整地理解佤族的剽牛行为。
二 生态人类学的解释进路
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只不过是居于这个自然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顶端,和其他动物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社会和文化属性的人类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和技术等文化手段谋求实现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最大限度的控制和使用,而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反作用下,又不得不通过文化的手段尽可能地适应自然。①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 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类的任何食物生产和消耗行为或生计方式都不是简单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行为。
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对语言、“符号”“象征”等文化属性的研究,完全看不到生态人类学的经验主义。同时,在生态人类学领域,常常看到的是太多的生物学的还原主义。虽然为数不少的人类学者在过去的民族志撰写中已经注意到了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并提出了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来解释生态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仍然难以打通两者的隔阂。直到美国的生态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系统提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主张,并成为20 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文化生态学理论出现背后的意图是要解释不同地域的特定的文化特征的起源,主要注意在文化规定的方式下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那些特征。
文化生态学对待文化的重要态度是,文化本身并不是静止的,既能适应自然条件,又能改变自然环境; 而那些适应环境的文化因素构成了文化的核心,文化核心特征的集群也就形成了社会文化的地方类型。②吴振南:《海岸带资源开发与乡民社会变迁——以竹塔村为中心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 页。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然而后世的人类学研究在涉及生态环境和文化问题的讨论时,始终无法回避“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概念。正如内亭指出的,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的其他方法处理同一资料,显然能够看出文化生态学方法的长处。③[美]内亭:《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张雪慧译,《世界民族》 1985年第3 期。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认为人类和其所居住的生态环境,通过人类的活动而连接在一起,各种活动形成活动体系。这个人类活动体系中,由作为自然环境的生态的层面、人的生物学层面、社会的层面和宗教的层面构成。①[日]秋智道弥、市川光雄主编:《生态人类学》,尹绍亭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 页。
尽管《努尔人》 在学术界并没有被认为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民族志,但埃文斯·普理查德开篇即指出:“像努尔人这样物质文化如此简单的人群高度依赖于他们的环境。”②[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 页。东部非洲的环境系统制约着努尔人的日常生活,并影响了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努尔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态系统结合起来,游牧的价值偏好超过了定居农业,维持着努尔人对牧牛业的偏好。美国人类学家拉帕波特在《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生态中的仪式》 基于系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后指出,马林人为了解决猪的数量过快增长的问题,因此创建了一套复杂的循环式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就需要屠宰大量的猪。在仪式过后,就可以把猪以猪肉的形式分给朋友和献祭给祖先,达到快速削减猪数量的目的,以此达到生态平衡。拉帕波特认为,马林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家猪屠宰仪式有助于维护一个不退化的环境,调节人、家畜和土地的比例,以分猪肉的形式在整个地域中分配过量的猪肉。③[美]罗伊·拉帕波特:《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生态中的仪式》,商务印书馆2016年。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把礼仪性的屠杀猪的仪式这种文化实践,看成是基于人与当地生态环境的互动而对猪的数量进行控制的一种公共活动。
日本学者煎本孝以加拿大北部的亚北极地带的狩猎采集民琪卑人的生态和宗教的记载进行了分析,阐明了琪卑人所居住的生态环境和他们的宗教行为之间的联系。在煎本孝看来,对于琪卑人来说,要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是困难的,不确定因素始终是琪卑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因此,琪卑人创立了作为狩猎生活的行为战略观念,那就是他们的猎物驯鹿的灵魂有不死的特征,即可以再生的观念。琪卑人为被杀的驯鹿举行灵魂分离仪式,为了驯鹿能够再次回到猎人身边,让驯鹿的灵魂从肉体分离,并将其送还。煎本孝认为,琪卑人的狩猎与猎物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讲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互酬和某种媒介得以成立,也表明了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系。①[日]秋智道弥、市川光雄主编:《生态人类学》,范广融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9 页。
中国的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以云南基诺族的刀耕火种为例指出:“仅从刀耕火种的外在不良后果,即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和批评,而不是深入到这一山地民族生活方式的深层结构中,即不是从生态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和客观的评价。”②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 1988年第1 期。因而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和偏颇的认识。当我们探讨佤族传统社会中剽牛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时,不能仅从大量屠杀牛所造成的物质消耗来理解和评价,而是应该将佤族的剽牛活动与佤族所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进入佤族生活方式的深层结构中来理解。因此,本文将从生态人类学的是视角出发,理解和解释佤族历史上十分盛行的剽牛活动。
三 佤族剽牛活动的历史民族志记录
佤族是跨中国和缅甸两个国家而居的民族。佤族分布在中国云南省澜沧江南段以西和以其相对的缅甸萨尔温江以东之间,北至保山,南至勐海的地区。而佤族的主要人口又分布在阿佤山区,阿佤山区也因为佤族的居住而得名。阿佤山区的范围西至萨尔温江,北至耿马孟定南定河一线,东北至耿马四排山区,东至澜沧雪林、西盟中课,南至孟连,包括中国云南西盟、沧源两县及与其毗邻的耿马、双江、澜沧、孟连部分地区,也包括与其交界的缅甸佤邦附近。③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 页。中国的佤族普遍信仰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并且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在阿佤山核心地区的西盟和澜沧的雪林地区尤为盛行。
因为佤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所以佤族一年里的宗教祭祀活动就显得特别多,牛、猪、鸡、狗等家畜经常在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中被消耗。在阿佤山核心区域西盟和澜沧的雪林地区,每年全寨性较大的宗教活动有做水鬼、拉木鼓、砍牛尾巴和砍牛头祭谷等,遇到天灾人祸时,全寨也要做鬼消灾。佤族从一月起就开始大量剽牛和做“砍牛尾巴鬼”,直到当年的六月才停止。佤族砍牛尾巴时要先剽一头至数十头水牛和黄牛,后找一头“心好”的黄牛砍牛尾巴。每次在砍牛尾巴时,一些青壮年就持刀围在砍牛的牛桩周围,当魔巴砍掉牛尾巴时,便一拥而上,数分钟就把牛肉抢光了。“砍牛尾巴”是整个村寨的事情,哪户人家有牛,哪家愿意做“砍牛尾巴鬼”,就可以做。20 世纪50年代调查组人员记录了西盟县岳宋村最近几年因为宗教活动而剽牛的数量①《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7 页。:
“砍牛尾巴”是剽砍牛最多的宗教活动,加之做其他鬼的剽牛,佤族每年所剽砍的牛,数字十分惊人。根据岳宋三年来剽砍牛的不完全统计,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上半年,共剽砍300 头水牛、黄牛;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共剽砍300 头水牛、黄牛;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共剽砍274 头,三年总共砍了874头。岳宋共有407 户,平均每户合2 头多。剽牛和砍牛尾巴之家大部分是中等以上的户,主要是富裕户,贫困户是无力剽砍牛的。根据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剽牛户统计,岳宋剽砍牛的49 家,其中富裕户34 家,占剽砍牛户总数的70%; 中等户15 家,占30%。用于剽砍牛的耗费极大。如艾仿是大珠米,他的收入也靠自己劳动和高利贷与雇工。他家的生活不比一般人家好多少,吃的是烂饭,穿的也不好,却在1953年到1957年五年间,共剽砍牛22 头。艾状大珠米,他的收入也靠自己劳动和高利贷与雇工,生产水平比一般人高不了多少,从1955年至1957年却剽砍牛20 头。
除了“砍牛尾巴”活动中需要消耗大量的黄牛和水牛外,拉木鼓也同样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黄牛和水牛。在20 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大调查中,详细记录了西盟大马散一次拉木鼓活动中剽牛的数量②李仰松:《20 世纪50年代西盟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 页。:
1957年剽牛者有两家,即艾困和艾散。艾困剽水牛两条、黄牛一条,艾散剽水牛一条、黄牛一条。剽牛栽牛角叉,栽在房子的日出方向。牛角叉用木头砍成,高约2 米。牛角叉的数目与剽牛的数不一定相等。有的人家牛角叉有66 个。
佤族个人和家庭开展宗教活动的费用有个人和家庭承担,即便是全寨性的规模较大的宗教活动,也不是按照每户家庭来平均分摊宗教费用,而是由某户家庭出面做主祭,主祭的家庭承担一切花费。阿佤山核心区域的佤族每年都举行多次较大的全寨性的宗教活动,而每次宗教活动又需要剽牛和大量的花费,所以需要预先确定每次全寨性宗教活动的主祭者。那么,主祭者为什么愿意花去自己辛苦积累的物质财富,为全村村民祈福呢? 一个普遍的解释是,一方面可以给主祭者带来鬼神的特殊护佑,得到更多的好处,同时也被其他村民认为是一种美德,从而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应该鼓励主动担任主祭者。①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 页。如果经济条件能负担主祭的所有开销,却又不愿意担任主祭祀者,则往往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有时村寨里的头人还要强令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担任主祭。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富裕的家庭一般都会主动担任主祭。参加过20 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学者罗之基在《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 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②同上书,第357 页。:
有的富裕户主要祭一次砍牛尾巴,一般都剽牛数头,有的十几头,个别也有剽20 多头至30 多头者。马散窝努小寨富裕户艾戛,从他父亲到他,十五年内共剽牛100 多头。永广寨有一个富裕户,在一次主祭宗教活动中剽了约30 头,死牛躺了一片。岳宋寨富裕户艾仿1953年至1957年主祭三次,共剽牛22 头,其中1953年5 头,1955年6 头,1957年11 头; 富裕户艾壮,1955年至1957年主祭三次,共剽牛20 头,其中1955年8 头,1956年6 头,1957年6 头; 富裕户艾宋1954年至1957年主祭三次,共剽牛22 头,其中1954年5头,1955年6 头,1957年11 头。
通过上文的历史民族志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佤族的剽牛活动和人类学家所讨论过印第安人的“夸富宴”有很多相似之处。佤族剽牛与印第安人“夸富宴”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伴随着活动的进行,较为富有的人经过长久积累的财富在瞬间消耗完,并分配给贫穷者。通过这种夸张的形式,财富在社会中进行了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裂缝。当剽牛与“夸富宴”活动结束之后,穷人获得了物质上的实惠,富人获得了社会声望,并把财富转变成社会资本,富人与穷人共谋了皆大欢喜的盛大场面。基于此,一些研究者把佤族剽牛与人类学家博厄斯及其学生本尼迪克特等人描述研究过的北美洲西北岸夸库特尔印第安人的“夸富宴”等而视之,认为两者的目的和动机都十分相似。①王亚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从西盟岳宋佤族“夸富宴”看社会文化变迁》,《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8年,第466 页。
人类学家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如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社会现象,对这种现象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莫斯认为,“夸富宴”这种原始的生存方式是原始部落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建议保留“夸富宴”这种叫法来指称这一类型的人类行为。②[法]马歇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 页。这种看法加深了人们对剽牛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学术研究不仅要知其然,还应该知其所以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 一书中对“夸富宴”的产生背景做了详尽的解释,重点论述了印第安人生活其中的生态环境和日常生活方式。③[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锡章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 页。因此,我们要想正确理解剽牛之于佤族人的重要意义,首先应当把这种行为放到佤族所生活的自然生态与生产技术中做生态人类学的分析。
四 佤族的生态环境、生产技术与社会互助机制
生态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论述了“文化生态学”在开展研究时的三个基本程序:一是必须分析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二是必须分析用特殊的技术手段开发特殊地区中的行为模式; 三是必须弄清行为模式在开发环境中影响其他文化方面所具有的作用程度。①[美]J.H.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王庆仁译,《世界民族》 1983年第6 期。斯图尔德认为,这三个程序并不能孤立看待,而是应该将三者整合起来。因为孤立地考虑人口统计、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土地使用及其他关键性的文化因素的话,那就不能掌握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的关系。②同上。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具体切入研究对象的视角,为我们从自然环境、生产技术和社会文化交织之处探讨佤族的剽牛活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佤族居住的生态环境
佤族居住的区域大体上是在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这里山岭重叠,山脉纵横。佤族分布的沧源、西盟、孟连、澜沧以及双江、耿马的部分地区,因为在北回归线以内,处于亚热带地区,因而气候比较温暖。由于佤族居住地区普遍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也较为肥沃,很适合于农作物和林木的生长。
西盟县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立体气候明显,降水量丰富,年降水量2758.3 毫米,集中于5月到11月之间,降雨量为全省之首。年平均气温15.3℃,无霜期319 天,最热月平均气温在17.3℃—24.4℃之间,最冷月平均气温在9.7℃—14.2℃之间。③《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 页。
在表面上看来,佤族居住的地方气候湿润,气温并不是很高,全年的降雨量也十分充沛,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但是,佤族居住的地区降水的季节性强,造成雨季时大雨滂沱,雨水量过多,光照量过少,旱季时光照量虽然多,但降雨量又少。降雨量和光照量的季节分配不均衡,对于作物生长造成了不利影响。仅从气候条件来看,农作物在阿佤山区全年都可以生长,但降雨量因为旱季和雨季的分布不均匀,过去主要的粮食作物只能在雨季时种植一季。而且因为阿佤山地区沟壑纵横,大部分的土地因为水利条件的原因不能复种。
人们对财富的利用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凭此积累更多的财富; 一种是用于各种目的的消费。①李文钢:《佤族传统社会支持的人类学研究》,《普洱学院学报》 2013年第1 期。在佤族的剽牛活动中,所消耗的黄牛和水牛既是一种有形的财富,也是一种协助人们劳作生产的工具,是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因此,在佤族社会中,牛的作用和价值要么是被用于日常生活消费,要么是被用于投入农业生产,据此获得更多的财富。很显然,在佤族传统社会中,人们选择大量消耗黄牛和水牛,而不是将黄牛和水牛投入农业再生产,因而形成了大量宗教活动都必须剽杀黄牛和水牛的文化要素。
从前文对佤族居住区域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描述来看,在佤族分布的很多地方,一年只能种植一季粮食作物,且作物品种十分单一,也没有任何的经济作物存在(近代以来鸦片的传入是例外)。由于佤族村民耕种土地的时间有限,主要是依靠人力耕种土地,对畜力的使用需求并不强烈,黄牛和水牛作为有形财富的价值超越了它们作为生产工具的价值。也就是说,佤族社会并不需要黄牛和水牛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帮助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更多的财富,黄牛和水牛存在的意义就只能是在大量宗教活动中被宰杀。因此,富裕的佤族村民通过在宗教活动中大量剽杀黄牛和水牛来换取社会声望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
另外,佤族居住的群山之中,尽是山径小道,崎岖难行,个别河道上架有竹藤小桥和独木桥,运输主要靠人背,有些地区,主要是边缘地区,也用牛、马、骡等畜力。②《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 页。由于使用牛作为犁耕的动力对土地的平整程度和地形、地势都有一定要求,佤族居住在群山之中,土地主要是分布在山坡之上,这样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合采用犁耕的方式耕种土地。我国著名的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在最近的研究中就指出③尹绍亭:《我国犁耕、牛耕的起源和演变》,《中国农史》 2018年第4 期。:
贵州一些山区耕作梯田,因梯田面积太小,使用牛耕转不过身,难以操作,所以采用人力替代。又如云南大理洱海周边,20年前笔者前往调查,水田几乎都使用锄耕而不见牛耕,如果据此认为当地不知牛耕技术,尚处于犁耕前的锄耕阶段,那就大错特错了。……当问他们为何不使用犁耕,答曰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使用犁耕了,原因很简单,饲养耕牛太麻烦,成本太高,还不如用锄头耕种。
综合上文所述的气候条件、雨量分布和佤族生活区域的地形地势条件来看,生态环境因素在强烈地制约着佤族村民使用黄牛和水牛作为生产工具的动力,黄牛和水牛对于佤族村民而言,最大的价值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不是作为劳动生产工具而存在。
(二)佤族的生产技术
除了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佤族对牛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佤族在农业生产中所拥有的技术也制约着他们对牛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也就是斯图尔德所说的,当我们在做生态人类学分析时,必须分析用特殊的技术手段开发特殊地区中的行为模式。农业是佤族的主要生产部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且过去佤族的农业比较单一,以农耕为主,其他的经济活动也多依附于农耕而进行。在西盟等地,生产比较落后,水田很少,主要是刀耕火种和挖犁撒种,所以长刀等简易的生产工具最为实用。佤族在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总的来看比较单一:
使用与掌握生产工具的熟练程度,视不同生产工具和不同地区而有所区别。使用最为普遍和使用时间最久的长刀,能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锄的使用时间不长,还不十分普遍,因此用起来效率不高,每人每天只能挖1/8 亩土地。有些甚至还习惯于用锄。犁的使用技术更差。因缺乏经过训练的犁牛,犁地时还需要一人牵牛,犁行之间间隔很宽,往往还不能把中间的生土盖住。边缘区的一些寨子,由于锄和犁的使用时间较长和较为普遍,使用的熟练程度和效率都较中心地区为高。①《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 页。
(西盟大马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缺乏板锄和犁,自有的条锄不多,加上大部分人还不会使用耕牛,所以用人挖的地不多,用牛犁的地就更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以来,政府无偿发放了大批板锄和犁,人挖地和牛犁地的面积就迅速扩大。1956年全寨人挖地和牛犁地已占全部旱地播种面积的3/4,1957年又扩大至4/5。②同上书,第63 页。
佤族生产工具比较简单,耕种程序比较少,显得比较粗放。即使是阿佤山边缘地区的佤族在耕种水田的情况下,用工量相比善于耕种水田的周边民族傣族和汉族而言都要少。
以沧源县班洪寨为例,100 斤籽种的水田面积(约合10 亩),整地中的草木烧掉和修理田埂,需人工20 个,放水泡田需人工4 个,犁第一遍需人工20 个,牛工20 个,犁两遍需人工20 个、牛工20个,再修田埂需人工15 个,拔秧、插秧需人工35 个,中耕共需人工30 个,收割需人工25 个,脱粒需人工15 个; 此外,用于10 亩的秧田耕种护理,需人工5 个; 总计需人工189 个,牛工40 个。平均每亩水田用人工19 个,牛工4 个。③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 页。
与劳动生产程序较为简单相伴随的是,劳动力的使用率相对而言变得很低:
一个劳动力一年用在生产上的时间,一般是一百七八十天,包括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及种园圃、大烟、找野菜等在内,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宗教活动等上面。以马散为例,每一个劳动力,平均每年用在全寨性宗教活动,如拉木鼓、做水鬼、盖大房子和砍牛尾巴等的时间达53 天。每日出工的迟早与劳动时间的长短,一般每天上午9 时左右出工,下午6 时左右回家,出工9 小时,有的寨只有7 小时。由于田地离寨远,除去途中往返和吃饭的时间,实际劳动时间每天只有4—6 小时。①《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 页。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阿佤山核心区的佤族农业生产技术比较简单,农业生产程序比较单一,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作物,导致了没有充分掌握使用牛辅助犁耕的技术,那么黄牛和水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价值就不大,进一步凸显了黄牛和水牛的消费价值。另外,即使是在使用简单的耕种技术和比较单一的耕种程序的情况下,佤族的劳动力使用率仍然是很低的,村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没有动力将黄牛和水牛用于生产劳动,以减轻人的劳动强度和加快土地耕种速度,所饲养的黄牛和水牛最大的用途就是宰杀之后获取动物蛋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三)佤族的社会支持机制
在生态环境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之下,核心区域的佤族粮食生产能力变得很低:
马散的稻谷产量,水稻平均等于籽种的30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300 斤; 旱谷平均为籽种的25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250 斤。产量最高的永广,水稻产量平均为籽种的50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500 斤;旱谷平均为籽种的25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240 斤。一般是水田产量为籽种的30—40 倍,每亩产量为300—400 斤,旱地产量为籽种的15—25 倍,每亩产量为150—200 斤。②同上书,第16 页。
粮食生产能力低下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是社会成员常常会面临缺粮的困扰。在粮食产量本来就很低,再加上全年不断的宗教活动要消耗大量粮食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富裕的佤族村民外,其他村民都面临着缺粮的困扰。在1956年时,西盟马散全寨平均每人一年缺40 天的口粮,上中等户要缺粮一两个月,贫困户要缺粮三个月。①《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8 页。风险与灾难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它既关乎群体的生存与延续,又影响到群体在数量上的稳定与发展,任何社会都会发展出一种社会支持方式。社会支持是人们在长久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一种抵御风险、共度灾难的方式,它是生态环境与文化要素的复合体。②李文钢:《佤族传统社会支持的人类学研究》,《普洱学院学报》 2013年第1 期。因此,佤族频繁宗教活动中剽牛就成为一种有力的社会支持方式。
例如,岳宋佤族剽牛分肉吃的规定③《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 页。:
剽牛后分牛肉的方法是:牛头留给主人,四条腿分给父母、岳父母和兄弟,杀牛多每家分一只,杀牛少则每家分一点。同姓分肋骨和屁股肉吃。凡参加者都可分一份肉吃。大人分一碗,小孩分一竹盘。
在宗教活动频繁季节分得的牛肉、猪肉等又补充了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动物蛋白,帮助缺粮的村民渡过难关,是一种社会支持方式。当牛作为财富的象征时,如果牛的所有者只是将牛据为己有,宰杀之后仅供自己消费,那么牛的主人并不能因此而获得社会中其他成员的认同,反而会因自己突出的财富遭受社会成员的嫉妒。如果是牛的主人能够慷慨地将自己的财富与村落社会中其他村民共享,帮助处于饥饿边缘徘徊的其他村民渡过难关,那么牛的主人就能因此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和赞赏。
五 结 论
在佤族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剽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造成了大量的财富浪费,也阻碍了佤族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宗教活动中的牺牲浪费也被认为是造成佤族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是,已有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通过某种仪式性地活动短期内集体性地消耗某种财富时,这样的活动其实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机制,也就是众多人类学家讨论过的著名的“夸富宴”。在这种财富的再分配机制中,少数富裕的社会成员为了获取他人的认同和社会地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积累的财富通过仪式的方式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共享,客观上而言是缩小了贫富差距,弥合了富裕者和贫困者之间的社会裂痕,达到了社会整合的目的。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对佤族剽牛活动中大量宰杀黄牛和水牛的看法呈现了由单纯地认为是浪费,到理解为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机制,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对此,笔者也表示赞同。但是,学术研究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本文从著名生态人类学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分析框架出发,通过对历史民族志资料的梳理,从佤族所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环境,佤族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及佤族在面临社会危机时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支持制度三个维度对佤族在宗教活动中大量剽牛这种现象做出了详细解释。期望本文的解释能够加深和扩宽人们对佤族剽牛活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