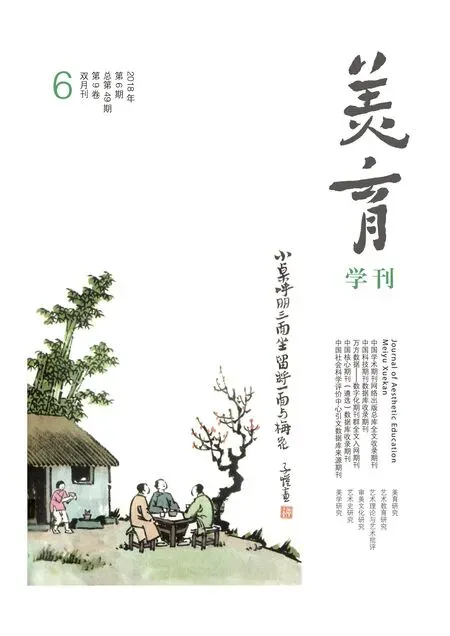欧阳修之琴缘、琴境、琴用
刘弋枫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欧阳修(1007—1072)一生与琴相随,是宋代“江西琴派”代表人物,也是宋代文人琴之典型。爱琴,善琴,藏琴,“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1]147,晚号“六一居士”,其中之“一”有“琴”。是琴人,亦是琴论家,有若干论琴诗文传世,在中国音乐史、中国美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一、琴缘
(一)一生缘琴
欧阳修《三琴记》云:“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1]147少时习琴。在天圣五年(1027),21岁下第南归时,就写下“挥手嵇琴空堕睫,开樽鲁酒不忘忧”[2]3773的抚琴感怀诗句。天圣九年(1031)初入仕途,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时,流连于古寺名泉之间,夏日在普明院避暑,“拂琴惊水鸟”,爱于“林泉清可佳”,“浮瓯烹露芽”。[2]3782明道二年(1033)赴随州省亲,作《江上弹琴》诗:“江水深无声,江云夜不明。抱琴舟上弹,栖鸟林中惊。游鱼为跳跃,山风助清泠。境寂听愈真,弦舒心已平。”[2]3731景祐三年(1036)被贬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拂尘时解榻,置酒屡横琴”[2]3787,以琴为乐。庆历五年(1045)因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再次被贬,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环滁皆山也,琅琊诸峰林壑尤美。其间游山玩水,琴酒悦心。庆历六年(1046)作《游琅琊山》:“止乐听山鸟,携琴写幽泉。”[2]3603-3604庆历七年(1047)与好友梅尧臣的书信中更直呈胸臆,“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3]。皇祐元年(1049)回朝,随着官职升迁、政务繁杂,弹琴时间弥少,却仍念念不忘。皇佑二年(1050)《寄圣俞》书稿中,对梅尧臣表达“优游琴酒逐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2]3626的愿望。皇祐三年(1051)《答杜相公宠示去思堂诗》云:“惟以琴罇乐嘉客,能将富贵比浮云。”[2]3693至和二年(1055)《忆鹤呈公仪》诗云:“归休约我携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2]3698嘉祐二年(1057)《送郑革先辈赐第南归》诗云:“试问尘埃勤斗禄,何如琴酒老云岩。”[2]3702治平二年(1065)《初寒》诗云:“篱菊催佳节,山泉响夜琴。”[2]3713熙宁二年(1069)《读易》诗云:“饮酒横琴销永日,焚香读易过残春。”[2]3721
可见,自少而老,不论忙时闲时、得意失意,欧阳修总是琴与身随。竹林小饮,“鸣琴泻山风,高籁发仙奏”。[2]3758留题佳处,“琴觞开月幌,窗户对云崖”。[2]3779酬待友人,“鸣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过一春”。[2]3802病中闲居,“琴书自是千金产,日月闲销百刻香”。[2]3801《六一居士传》中,欧阳修自叙了在琴中所得的快乐,可谓“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1]205可见琴悦之深。
欧阳修爱琴亦藏琴。藏琴三张:一传为张越琴,金徽,其声畅而远;一传为楼则琴,石徽,其声和而有余;一传为雷氏琴,玉徽,其声清实而缓。虽有年代存疑,然三琴皆布满蛇腹断,属上百年“古”琴,时人得一已属至宝,欧阳修却兼有之。此三琴乃欧阳修在不同时候所得。早年任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几,此为常琴;后做舍人,又得琴一张,此乃张越琴;及至做了翰林学士,又得琴一张,此则雷琴。其中雷琴尤为珍贵,据欧阳修自述:“余家旧畜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会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声清越如击金石。”[4]唐代西蜀雷琴声名显赫,雷会正是雷氏家族的成员。该琴在当时就属珍宝,何况到欧阳修时又有250年的历史。
欧阳修一生弹琴、藏琴,然而认为关键不在于琴贵,不在于曲多,是在于内心的快乐与满足,他说:“琴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琴亦不必多藏,然业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弃也。”琴曲中,欧阳修犹爱《小流水》。其谓“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寝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1]147
(二)江西琴派
欧阳修琴缘之深,乃至于成为江西琴派的领袖人物。
欧阳修爱《小流水》类纯琴曲,亦提倡以辞入曲、既弹且唱之琴歌。以歌入弦乃为宋代江西琴派之特质,江西庐陵人欧阳修正是其领袖人物,对江西琴派及琴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时因地域、师承、传谱及审美观念的不同,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古琴流派。宋代琴坛主要有京师、江西、两浙三派。北宋政和年间成玉在其《琴论》中言:“京师、两浙、江西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南(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5]可知三派在政和以前就已形成。
江西琴派是文人琴的群体,而非艺人琴的群体。宋代江西地区文化发达,江西籍文人能琴者众多,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朱熹、文天祥皆堪称宋代文人琴家的代表人物。
江西琴人整理、创作琴曲,形成了“江西谱”。至南宋时,“江西谱”盛极一时,与当时京师琴派之“阁谱”抗衡。元袁桷《琴述赠黄依然》文曰:
自渡江来,谱之可考者,曰《阁谱》,曰《江西谱》。……曰江西者,由阁而加详焉。其声繁以杀,其按抑也,皆别为义例。秋风巫峡之悲壮,兰皋洛浦之靓好,将和而愈怨,欲正而愈反,故凡骚人介士,皆喜而争慕之,谓不若是不足以名琴也。方杨氏谱行,时二谱渐废不用。或谓其声与国亡相先后,又谓杨氏无所祖,尤不当习。[6]
与唐迥异,宋代帝王多有好琴者。皇家御用琴谱藏于秘阁,名曰“阁谱”。据成玉之评,阁谱“过于刚劲”。而江西谱“由阁而加详焉”,指法与乐曲都比阁谱更加复杂而富于变化,且风格既有悲壮之声,又有靓好之音。一时文人雅士皆慕之。迄至宋末,江西谱走向衰落,虽入元后在民间仍有流传,然继之而起的是浙派琴谱盛行,亦即袁桷所谓“杨氏谱”。
浙派继京派、江派之后而兴,源于北宋,兴于南宋,全盛于明初。南宋浙派琴人是在初学阁谱与江西谱的基础上发展浙谱,从琴学传承上,南宋浙谱不仅与阁谱颇有渊源,亦有可见江西谱的质素。
江西琴派与浙派的最大区分,就在于浙派专事琴曲,注重古琴的高雅化,追求静远、飘逸、空灵的琴声。而江西琴派则偏重俚俗,提倡以辞入曲、既弹且唱之琴歌。江西谱最大特质在于既有琴曲又收录琴歌。琴歌在宋代一度风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欧阳修正是江西琴派代表人物,主张以歌入弦,并以琴会友,形成了一个艺术群体。道人李景仙、潘道士,琴僧知白、义海,文人苏轼、梅尧臣、刘敞、沈遵是其琴友。与欧阳修颇具渊源的琴歌《醉翁吟》也成为江西谱的代表作。
庆历年间,欧阳修谪任滁州太守,作《醉翁亭记》,广为流传。太常博士沈遵读其文,“闻而往游焉。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2]3634,作《醉翁吟》一曲,并数年后有幸弹与欧阳修听。欧阳修甚喜,“醉翁吟,以我名,我初闻之喜且惊”[2]3634,“嘉君之好尚,又爱其琴声”[2]3634,因作两首琴诗赠与沈遵并给琴曲《醉翁吟》填词。《醉翁吟》辞曰: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蹊。咿嘤啁哳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贤哉沈子兮,能写我心而慰彼相思。[7]
此琴歌一出,在当时琴坛甚有影响。既争传《醉翁吟》琴曲,又有好事者纷纷为欧阳修所作《醉翁吟》歌词谱写新曲。欧阳修《醉翁吟》词自是大手笔,然调不主声,“与琴声不合”[8]164,难以唱诵。好事者欲为其《醉翁吟》词谱新琴曲,“虽粗合均度,而琴声为辞所绳约,非天成也”[8]164,皆不理想。
30余年过去,欧阳修、沈遵相继谢世,江西庐山道人崔闲曾师从于沈遵,特妙于琴,爱《醉翁吟》且能奏之,“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8]164。
苏轼与欧阳修为琴友,与欧阳修相似,也注重古琴通俗的成分。苏轼曾有“琴非雅声”言,曰:“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者,乃皆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独弹,往往有中华郑、卫之声,然亦莫能辨也。”[9]47-48
故受崔闲相邀,苏东坡欣然从之。东坡本精通琴律诗文,于是崔闲弹曲,东坡谱词,少顷而就。东坡《醉翁吟》词曰: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唯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篑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曲在人间。试听徵外两三弦。[8]164
苏轼填词后,在给俗家为沈遵之子的本觉禅师法真的信中谈起《醉翁吟》的创作:“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10]东坡认为此次创作是词与曲妙相契合,可见对《醉翁吟》作品的满意,也见出其认为赞同江西琴派以歌入琴的艺术观念。东坡之后,北宋郭祥正《醉翁操·效东坡》词,南宋辛弃疾、楼钥皆有《醉翁操》词,南宋周文璞《欧阳琴歌》:“呜呼个是文忠琴,呜呼此琴今尚存。堂中图书散失尽,留得七弦传子孙。……今来再听七弦琴,南薰遗制喜复见。浮云流尽白日逃,何用广陵与离骚。谱成只度欧家曲,秋声赋人庐山高。”[11]皆可看出,文坛与琴坛对《醉翁吟》的喜爱,欧阳修在琴坛的影响,亦可窥知。
二、琴境
琴境,即琴艺所载之意象与意境。意象即意与象、主观心意与客观物境的交融相契,是艺术的本质。意境即是艺术意象之内涵具超逸、无限、永恒之意味,即为意境。“意境”较之“意象”外延更窄,内涵更广。
欧阳修之琴境,一言以蔽之,即是“古境”。“古”本为时间概念,但中国艺术中所言之“古”有三层意涵。过往形式之“古”、古今同然之精神之“古”、形上性超越韵致之“古”。
(一)君子古德
欧阳修推尊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在琴中所追求之“古”主要为第二个涵义,即古今人心同然之精神,欧阳修处具体为儒家精神。此类琴境,承载琴人主观的生命情调,是文人心境,亦是一般意义上之艺术意象。在《送杨寘序》中,欧阳修明确说道:“其(琴)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心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12]24-25琴境“纯古淡泊”,因其寄托儒家贤圣的理想,故与儒家经典无异。《江上弹琴》诗亦曰:“用兹有道器,寄此无景情。经纬文章合,谐和雌雄鸣。飒飒骤风雨,隆隆隐雷霆。无射变凛冽,黄锺催发生。咏歌文王雅,怨刺离骚经。二典意澹薄,三盘语丁宁。”[2]3731琴声是要寄托文王《雅》、屈原《离骚》、《尚书》中《尧》《舜》二典、《盘庚》三篇,兹为“道器”。
欧阳修认为,琴为“道器”,是要载“古”,亦即儒家人格理想。此理想仍可追还。《弹琴效贾岛体》诗云:
横琴置床头,当午曝背眠。梦见一丈夫,严严古衣冠。登床取之坐,调作南风弦。一奏风雨来,再鼓变云烟。鸟兽尽嘤鸣,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时,未远可追还。[2]3615
《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13]1534《孔子家语·辨乐解》曰:“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14]《史记·乐书》言:“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15]欧阳修追还儒家之道德理想,亦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思想。
(二)万古无穷
欧阳修乃典型儒士,具纯正中和之儒家气象,以追求儒家道德理想、高尚人格及淑世情怀为生命重心,其琴境之“古”主要为儒家精神。然而,《赠无为军李道士》诗中,欧阳修之“古”亦有超越韵致之意涵。
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诗云:
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2]3614
三尺琴器,悠悠琴韵,使人意会“万古无穷”,忘乎形骸。无穷之韵致,心领神会,不可言传。可知欧阳修之“古”亦有形上性含义,追求琴中超越之韵致。
宋代琴僧亦最求琴中“古”意,与欧阳修之“古境”有相通之处,其“古”之境界皆有超逸无累的韵致。
宋代禅师潜山文珦《琴泉》诗云:“泠泠太古音,在此幽涧泉。全流如碧玉,老僧不足听。”[16]雪窦重显《赠琴僧》曰:“太古清音发指端,月当松顶夜堂寒。悲风流水多呜咽,不听希声不用弹。”[注]高楠顺次郎等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第698页。禅师之琴中“古”意,是无限、永恒,是超逸无累、心领神会之超越意境。
欧阳修本是排佛之人,然在宋代儒释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其与佛教僧人们有密切的交往,尤其贬谪滁州期间优游山林泉寺、与禅师谈经讲道,时有林泉清音禅意的熏染。欧阳修与琴僧知白相过从,在《送琴僧知白》诗中,欧阳修赞扬了知白高超的琴艺:“吾闻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无其传。夷中未识不得见,岂谓今逢知白弹”,“酒酣耳热神气王,听之为子心肃然”,“负琴北走乞其赠,持我此句为之先。”可知其佛缘甚深,也可见古琴艺术无门户藩篱。
欧阳修“古”之琴境有层次之别、内涵之别,主要指中正平和的儒家精神,也具超尘脱俗的禅宗逸趣。
(三)知音会意
欧阳修言:“琴声虽可听,琴意谁能论。”[2]3615琴意即琴之内涵。会得琴中之意,鉴赏琴中之境,是为知音。知音在于心领神会,不在言传。欧阳修言:“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12]77-78心领神会者,可遇不可求,欧阳修感慨世多俗子、知音之难,他道:“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2]3634又道:“戏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叹知音难。君虽不能琴,能得琴意斯为贤。”[2]3653能描绘琴声并不稀罕,可贵者在于听出琴意。故欧阳修对韩愈的听琴诗提出质疑。韩愈听琴僧颖弹琴后,曾作诗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9]47诗中以三种不同的意象来描绘韩愈的审美感受,欧阳修却认为此诗是写琵琶,非是写琴,韩愈并非颖师知音。苏东坡很赞同欧阳修的评论,道:“欧公谓退之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耳。余深然之。”[17]
得琴意者斯为贤,能得诗意亦为贤。诗与乐内涵相通,妙处又都在可感受而道不出,要人心领神会。欧阳修探讨诗乐关系,其认为诗乃乐之“苗裔”,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12]77-78,诗与乐都有感人心灵的力量,“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12]77-78与乐相同,诗也需要妙悟会心、不在言传,欧阳修言,“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12]77-78。知音难求,欧阳修看来,他与梅尧臣互为知音,“今将告归,余因求其稿而写之。然夫前所谓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听之,不相语而意相知也。余今得圣俞之稿,犹伯牙之琴弦乎?”[12]77-78诗中以伯牙、子期自喻,可见欧梅相交之深。
三、琴用
(一)养心养身
欧阳修重视知音,却不必要知音。对于古琴功用,其最为注重的乃是对心灵的安顿与自适。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作《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诗,明确表示喜爱陶渊明无弦自乐的境界,诗云:“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君子笃自信,众人喜随时。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为。寄谢伯牙子,何须钟子期。”[2]3655陶潜无弦之乐,是自在之乐、安顿之乐、心灵之乐,是琴之真乐。既得真乐,何必知音,何必有琴音。
《书琴阮记后》中,欧阳修也表达了类似思想,其言:
官愈高,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在夷陵时,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萧然自释。及做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盈前,无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乃知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适,无弦可也。[12]78-79
早年谪居夷陵时,虽是地僻琴不佳,但风景优美,无尘俗牵绊,意趣悠然。后官位屡迁,却是俗务缠身,无复清思,琴意昏杂。可知琴之乐在心不在器,若得内心明澈、快乐,无弦可也。欧阳修此无弦自适之陶潜琴乐,深得梅尧臣赞赏,有诗赠之:“知公爱陶潜,全身衰弊时。有琴不安弦,与俗异所为。寂然得真趣,乃至无言期。”[18]
欧阳修在琴中所得乐受至深,然而琴中之悦,非狂喜,非盲爽,是心清神明、心平气和之后所得的澄明之乐、平和之乐、自在之乐。琴中心思平和自在,是养身疗疾之良器。欧阳修在《送杨寘序》中表达了这一思想: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12]24-25
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中医八纲辨证,失序失调失衡则为病。心为身之主宰,心烦意乱、忧虑万分常易致病。中医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悲伤肺,惊恐伤肾”的说法,称为“七情内伤”。反之,心气平和、心思安定则有助于调摄七情,使身心顺畅。琴韵静定清雅,有助于心平气和,“心而平,不和者和”,故“幽忧之疾”可忘也宜。这一思想,欧阳修在道士李景仙处得到印证:“我怪李师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问胡以然笑语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又云理身如理琴,正声不可干以邪。”[2]3614“养其根”正是养其心。
琴可疗心因疾病,亦可直接治疗身之疾病。欧阳修《琴枕说》云:
余家石晖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两手中指拘挛,医者言唯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者,谓唯弹琴为可。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物理损益相因,固不能穷至于如此。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1]190
不难看出,欧阳修“琴养身心”的思想有道家思想和道教理论的痕迹,此应与其和弹琴道士们相过从有关。欧阳修《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诗云:“爱酒少师花落去,弹琴道士月明来。”[2]3802《赠潘道士》诗云:“寄语弹琴潘道士,雨中寻得越江吟。”[2]3802《赠无为军李道士》诗云:“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李师琴纹如卧蛇,一弹使我三咨嗟。”[2]3614
然而,欧阳修对道教神仙方术却是持批判态度,《琴高鱼》中可以看出:“琴高一去不复见,神仙虽有亦何为。溪鳞佳味自可爱,何必虚名务好奇。”[2]3760《赠无为军李道士》亦曰:“胡以然笑语我,慎勿辛苦求丹砂。惟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2]3614
事实上,欧阳修之琴养身心的思想虽有道家成分,根本上仍源自儒家“中和”的音乐观,是儒家“中和”基础上与道教“养心—养身”思想的结合。《乐记》曰“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13]1536,又云“致乐以治心”。[13]1543欧阳修言:“盖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1]57这与乐记的思想一脉相承。显然,他认为众器之中,琴最有“和之”“节之”的作用,所谓“(琴)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12]24-25,“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12]24-25。
(二)乐教淑世
欧阳修为儒家士大夫,淑世爱人,注重音乐“自娱自适自养”之功,亦将己之所欲推及于人,重视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不论从个体、从群体,欧阳修都主张“音之移人”。
《国学试策·二》载:
盖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夫顺天地,调阴阳,感人以和,适物之性,则乐之导志将由是乎;本治乱,形哀乐,歌政之本,动民之心,则音之移人其在兹矣。[1]57-58
欧阳修好正声而斥郑卫,主张艺术载德,强调音乐的中和之气、教化之功。对于民心,音乐有“和之”“节之”的功能,使人们得以感发,具有内在的规范作用。
欧阳修是典型的儒家音乐观。儒家提倡音乐的“中和”之道,追求仁美合一的境界,以雅乐、正声和乐人心、和谐社会,将乐与礼并为教化之双璧。《尚书·尧典》载,舜命夔典乐,“教胄子”。[19]荀子《乐论》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20]《孝经·广要道》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1]《乐记·乐施篇》曰:“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13]1534《乐记·乐化篇》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13]1545
琴正是处于传统乐教的中心地位。显然众器之中,欧阳修认为琴最有“和之”“节之”的功能。概因重视琴之乐教功用,故宋代琴派在高雅与通俗、琴曲与琴歌之分之争中,欧阳修更偏向琴歌、注重通俗。需知清微淡远、飘逸空灵的琴曲琴韵,虽意境高古,却多为处士逸人所喜,大众难于鉴赏。琴曲与琴歌的区分,是琴乐与歌乐的区分,也是高雅与通俗的区分。以歌词入琴,明白晓畅、平实通俗,更易于教化。
——纪念欧阳修逝世950周年活动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