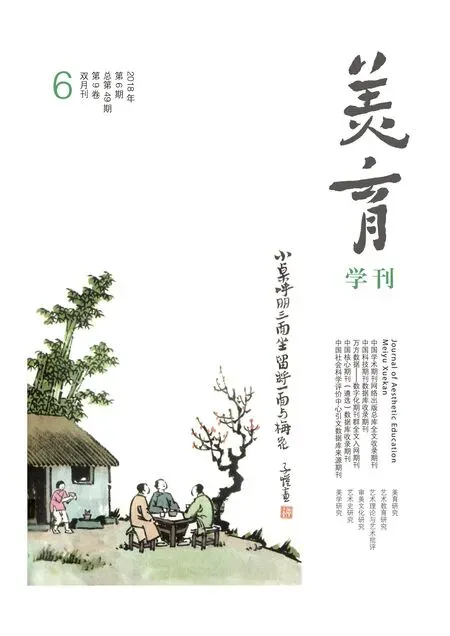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比较
杜立 刘晨晔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扩大的欲望和需求,同时也伴生出众多的人性问题,尤其是人性异化及人性分裂等现象,无不引起当今世界人们的高度关注。面对人们信仰和道德的缺失,开展人性教育的任务日益紧迫,使我们开始考虑重建公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实现人性的和谐发展。回望生活在18世纪末的席勒和20世纪中期的马尔库塞,二人都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弊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并提出以审美实现人性解放的思想,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现代人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审美乌托邦的建构
席勒和马尔库塞都是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美学家,他们的思想以实现人性解放和人性自由为旨归,在深刻剖析自身所处社会背景基础之上,以审美视角解决出现的人性问题,以实现人性的完整,建构理想中的审美乌托邦。
(一)弥合人性分裂——审美乌托邦的建构基础
人性的完满何以成为可能?这是典型的席勒式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面对的问题,它揭示了每个时代所显露出的社会弊病,成为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席勒所处的时代是德国动荡不安的时代,18世纪的德国现实社会出现了种种弊端,“社会经济体制的僵化和落后,统治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宫廷生活的腐化堕落,以及下层民众的极度贫困”。[1]这样一种独裁专制背后潜藏的是德国封建专制带给民众的人格压抑,恩格斯曾经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18世纪的德国:“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消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2]这是当时席勒所处的18世纪的德国最真实的写照。可以看出,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渗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时环境的逼迫之下,人性出现严重扭曲。席勒将这些人性问题归结为人性的分裂,他认为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没有走向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性的堕落,人们也试图寻找各种途径改变国家的现状。席勒和当时德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力图找到一条中庸的改良道路,那就是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来改变社会,从人性、人的心灵的改变来实现对社会的改变”。[3]
马尔库塞作为西方社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样特别关注人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步摆脱贫困状态,给人们带了来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然而,人们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却被无限膨胀的欲望所掌控,技术理性控制下的社会为人们营造了一种潜在的异化环境,不断腐蚀着人的内心世界,使人们一步步堕落为技术的侍从,思想出现严重的偏颇。人们追求快乐原则的本能也随之被个人欲望所代替,只顾眼前看似繁华的物质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却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资本家也开始转变对公民的剥削方式,在一片看似祥和的社会背景下对人进行肆意操作和控制。由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引起马尔库塞的关注,他深刻批判了现代发达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弊病,指出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这种病态社会使所谓的现代文明束缚了人的本性,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原来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完整的人变成了只追求无止境物质利益的“单向度的人”,人们追求精神自由与发展的爱欲本能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和压抑。在这种情况下,马尔库塞在吸取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并且指出科技理性主导的社会用现实原则替代了快乐原则,人们在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蒙蔽下逐渐丧失纯真本性,人性开始出现全面异化。
由此可以看出,席勒和马尔库塞都是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基础之上深刻揭示了现代文明对人自然本性的侵犯,在人性分裂和人性异化的严酷形势下,只靠变革社会政治制度很难实现人性解放, 所以另辟蹊径以真正实现人性完满和本能解放成为最重要的任务。
(二)树立审美之维——审美乌托邦的建构途径
席勒和马尔库塞在时代所带来的困境中逐步认识到,单纯的社会制度无法挽救人性,因为正是国家制度与现代文明造成人与社会的日益疏离。在此背景下,席勒和马尔库塞选择以审美来解放人性,实现人性的复归。在他们看来,审美的本质是“审美产生于人的心灵对于自由的渴望,也激发着人的心灵对自己的渴望;审美体现了人的追求自由的本质,也强化了人的追求自由的本质;它永远站在不自由的现实人生的对立面,呼唤着人们向自由的人生挺近”。[4]虽然二者在美学道路的具体实施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审美之维始终是贯穿其美学思想的主线,这对于解决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问题及现代社会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8世纪的德国是人心涣散、环境极其恶劣的国家,人的本性被腐败的封建专制无情剥夺,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表明,狂妄的杀戮暴露了革命的粗暴和野蛮,现时的国家制度和现实状况成为人性分裂的祸根,焦虑和彷徨成为那个时代公民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社会背景下,席勒始终向往古希腊人美好的人性,他认为古希腊人的完整性就在于他们将自己的人性与现代文明做到恰到好处的相融,他们处在一种单纯进步的文明状态中,并且将感性和理性自然地融合到一起。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们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保存自己的尊严与智慧,以至人的本能由于封建的国家制度遭到严重扭曲。所以席勒提出:“为了解决经验中的政治,人们必须通过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5]4对席勒来说,现实的人性分裂严重阻碍了人性自由的实现,而只有审美道路才可以使碎片化的人格实现完整。“美所以能成为一种手段,把人从质料引向形式,从感觉引向法则,从一个受限制的存在引向绝对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它帮助思维(思维包含着明显的矛盾),而仅仅是因为它为思维力创造了自由,使思维力能按照它自己的法则来表现自己。”[5]58
在马尔库塞生存的时代中,文明的进步反而镇压了人的爱欲本能,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性的绝对力量,国家及社会如同牢笼一般紧紧束缚着人性的自由发展,公民在无形之中将自己屈服于这种特殊的统治形式下,逐步丧失自主性,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奴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抑,马尔库塞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家同样认为唯有审美才可以将人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复归。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本能的解放之路,实质上是一条通往审美的道路”。[6]9于美所表达的是快乐原则,它与人的精神与本能紧密相关,所以美的原则可以使爱欲得到真正解放。这里的爱欲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动物性欲望,而是指在人格完整的基础上使人得到真正自由与快乐的完整的本能,马尔库塞认为,“爱欲是使生命体进入更大的统一体,从而延长生命并使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努力”。[7]193所以马尔库塞提出爱欲解放论,他认为恢复人性纯真本质就应该解放爱欲,实现爱欲本能的解放就要以审美克服现实原则的压抑,消除现代工业文明带给人的额外压抑,使人摆脱人性异化的困境,建立一种自由的非压抑文明。
(三)追求自由解放——审美乌托邦的建构目标
席勒和马尔库塞都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并且据此提出用审美解决现代文明对人自然本性的侵犯。人性问题之所以能引起他们的重视是因为自由作为美学思想的目标不仅能解决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问题,更是人性教育不可避免的话题。无论是席勒的游戏冲动说还是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其本质都是人自由本质的显现,自由的实现在人性解放中始终具有根本意义。
席勒认为,封建腐朽的国家严重阻碍着人性的全面发展,所以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在批判国家制度对人性的压迫中揭示了自由是人性得以全面发展的核心,并提出只有通过审美道路才能实现现代社会与人性自由的真正结合。在审美消除人性异化的过程中,人的自由本质开始显现,人开始进入一个自由王国,人的双重天性得到内在和谐统一,“这种和谐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自由显现:在人格的显现中有着丰富多彩的人的状态,在人的状态的显现中充满着人格的光芒,人和他所呈现出来的生活世界作为自由显现的主体及其对象共同构成了人的作品——人不再只是自然的作品,而是他自身的作品”。[1]85席勒的审美思想是医治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专制造成人性创伤的良药,使人性的内在自由本质战胜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对人的压抑和束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人才会实现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与协调,实现人性完整,摆脱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压迫与统治,将人从封建愚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高度发达的科技虽成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但是这种“进步”不再强调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成为人性异化的工具,人的肉体、精神和思想出现全面异化。马尔库塞倡导的审美之维的革命就是以实现人性自由的复归为根本目标消除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压抑,建立一个自由的非压抑社会,使人按照美的规律生存,“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由于贫困和劳苦的消除,一个新的天地诞生了,感性、娱乐、安宁和美,在这个天地中成为生存的诸种形式,因而也成为社会本身的形式”。[6]100非压抑社会的实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非压抑社会中以人性的自由解放为目标,人的爱欲在快乐原则下得到真正的解放,人在恢复本能后得到真正的自由,克服物质利益的无限度需求以改变单向度的人性状态,使现代文明与自然本性实现真正融合。
二、审美乌托邦的实现活动
(一)感性解放——感性冲动与新感性
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都提及对感性的认识,这对实现人性完整和自由起着重要的作用。感性在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审美之维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但由于生活时代的不同,二者对于感性活动的理解也存在诸多差异。
在席勒看来,封建的国家制度是造成人性分裂的重要因素,封建制度的愚昧和残暴使人逐步丧失意志和道德,造成自身双重人格的分裂。基于这样的现象,席勒从人的感性本性和理性本性两种相反的自然天性出发提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对于感性冲动,席勒认为,“它来自人的肉体存在或他的感性本性,它努力要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中,使人成为质料,而不是把质料给予人,因为把质料给予人毕竟是属于人格的自由活动,人格接受质料,并把质料与它本身,即与保持恒定的东西区别开来”。[5]35席勒认为感性是人的一种自然法则下的感受性,是人的自然天性,“感受性越是得到多方面的培养,越是灵活,它给各种现象提供的表现面越多,就越多地把握世界,就越多地在他自身之内发展天赋”。[5]39感性冲动可以唤醒人的自然天赋,刺激感官的感受力和思维力,意识到自身源于本性的尊严与自由,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与渴望成为反对封建专制最直接的形式,从而改变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人性分裂状态,实现人的本性解放与自由解放。所以感性冲动是通往席勒描绘的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并且与理性冲动一起发挥作用以实现人性的完整。
马尔库塞对于感性活动的理解和席勒不同,他从人爱欲本能的角度出发,竭力张扬被理性压抑的感性,提出新感性思想。“于是,一种崭新的现实原则就诞生了,在这个原则下,一种崭新的感性将同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的造物中,结合在一起。”[6]99马尔库塞认为,新感性是一种在理性压抑状态下的“活”的感性,是马尔库塞在技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实现本能解放的新的手段和工具,他将新感性定义为:“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6]98它唤醒人对原始本能和自由的重生欲望,使之从技术异化造成的人性异化中逃离。这种新感性包含着人对自由和新生的渴望,表达了长期遭受工业机器束缚的人的自我突破,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新感性的解放状态下,艺术革命和审美方式超越现实原则对人爱欲本能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二)审美活动——游戏冲动说与爱欲解放论
席勒从德国现实情况出发,提出腐败的封建专制使人完全丧失了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与协调,人长期处于两种情感的各执一端中走向分裂,这种分裂使人最终不是走向兽性的粗暴就是走向道德的颓废。席勒以古希腊人美好的人性为蓝本,倡导将时代特征与人自身的尊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实现人性完整与和谐。所以他从人性的自然本性入手,将有限本质的人划分为人格和状态两种概念,由此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法则,即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形式冲动)。由于人是人格和状态的有机统一,席勒将这两种冲动进行整合,提出游戏冲动说,这是席勒提出的通过审美实现人性完整的重要思想。游戏冲动是人对物质需求和内在法则的统一,是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统一,“游戏冲动作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集合体,作为实在与形式、需求与自由、情感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既是人性的圆满实现,同时也是美的发生和完成”。[1]59席勒将游戏冲动说的对象定义为“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总而言之,用以表示在最广的意义上称为美的那种东西”。[5]45显然,席勒从游戏冲动中深刻挖掘人双重天性的统一,并且使之在美的形象中使人的自由本性和审美自由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既消除了感性和理性的矛盾性,同时突破了封建制度对人的统治性,克服人性分裂,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实现人性自由的复归。“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整的人,使人的双重本性一下子发挥出来。”[5]47
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是其美学思想的中心,这与席勒的游戏冲动说相比,虽然都是对人自由本质的追求,但与游戏冲动说所主张的感性与理性统一不同的是,爱欲解放论主张释放人的爱欲本能是实现人自由本质的重要前提和必经之路。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础之上提出,“爱欲的目标是要维持作为快乐主—客体的整个身体,这就要求不断完善有机体……这个目标还产生了爱欲自身的实现计划:消除苦役,改造环境,政府疾病和衰老,建立安逸的生活。所有这些活动都直接源于快乐原则,同时,它们也是把个体联合成更大统一体的努力”[7]193。马尔库塞提出的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相似,但马尔库塞的出发点是提倡爱欲的全面解放而不只是劳动的公平。由此,马尔库塞提出解放人性异化下爱欲的途径就是消遣,“消遣的基本特征是,它是自在地起满足作用的,除了本能满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7]195。消遣功能的产生和运作是人性异化的解脱方式,消遣作为一种心理满足手段使人感到极大的放松与愉悦,实现爱欲解放。
(三)自由王国——审美王国与非压抑社会
席勒对人性异化提出的美学思想始终以审美为原则实现人性的复归,在他看来,“美是现象中的自由,人同美只应是游戏,审美和游戏在本质上都是非功利性的,人和美在自由显现的非功利游戏中所具有的状态就是美的王国。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显现既摆脱了物质自然力的束缚,也摆脱了理性法则的专制。自由显现使人成为活的形象,使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结合为游戏冲动,使人从感性和形式的对立、冲突中进入和谐的审美王国。”[1]120审美王国是通往美的自由王国,“通过自由来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2]95。在审美王国里,人无需遭受国家制度对人自然本性的制约,也无需感受工业机器的喧嚣带来的人心险恶与纷杂,人基于快乐原则下生存,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是人实现自由的象征,曾经提出的“人性的完满何以成为可能”在这里得到了实现。这个王国的最大特征在于它不只是具有超功利性,更强调对人性尊严和天性的尊重,游戏冲动和自由显现都是其得以真正实现的重要表现。总之,审美王国就是在感性和理性相统一、客观存在和精神存在相统一中实现人性完整的自由王国。
在马尔库塞看来,要实现爱欲本能解放就要使异化的人性尊崇消遣特征,消除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束缚,实现非压抑文明,创造非压抑社会。在他看来,非压抑社会是一个超越了人现实需求的自由社会,是人实现人性解放和自由解放的重要存在环境,“在这个新的社会环境中,人类所拥有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和感受的潜能,与自由的意识和谐共处,致力于自然与人类的和平共处”[6]105。这个社会快乐原则指导着爱欲本能的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操作原则,克服人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相互脱节状态,在爱欲本能的指引下,使自身消除人性异化的被动性,恢复有血有肉的感知力,成为自己本性的主人。马尔库塞认为,要实现这样一种非压抑性社会,一要消除物质欲望对人的压迫,使之摆脱自身带来的压抑得到自然解脱,二要通过审美形式和艺术革命来突破人性异化的压抑状态,艺术和审美作为新感性的根本体现表现原则尊崇人的本能价值。“艺术的审美形式,通过赞美普遍的人性,反映着孤独的资产阶级个体的苦难;通过高扬灵魂的美,反映着肉体上的被剥夺;通过抬高内在自由的价值,反映着外在的奴役。”[6]152艺术使审美基于新感性的原则出发更好地培养人的审美灵感和审美自由,而审美作为非压抑文明的必要原则更好的实现艺术在人性中的革命,塑造具有新的本能意识的自由人。
在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中,无论是自由王国还是非压抑社会都是自由的审美国度,自由是其审美乌托邦的最终目标,在那里,人都是保持自我精神完整性的真正的自由人。
三、审美乌托邦对当下中国发展的现实意义
伴随科学技术的日益高端化,人类文明进程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期仍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对人精神生活的压迫和控制,另一方面是现代人自身愈演愈烈的贪婪和欲望,由此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步滋生出有悖于道德价值的人性分裂与异化现象。在经济上,很大一部分人在功利心理的蒙蔽下滋生出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一系列异化问题,比如追求品牌主义等现象,这样的心理使得人们将自身的虚荣心视作衡量事物的标准,将占有原则代替了事物的本质存在,这类似于马尔库塞当初所批判的“虚假需求”,即毫无节制地按照奢华的生活标准满足异化的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者这一范畴之列”。[8]在政治上,在功利主义之风下必然地滋生出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公民的思想意识愈来愈被物质欲望所侵蚀,公民在技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下出现道德价值沦丧、思想意识紊乱等问题。然而仔细挖掘这些现象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人深受资本逻辑的控制将自己推至人性分裂的状态,缺失信仰与道德,在自我价值选择中迷失方向,泯灭良知。面对这样凌乱失序的社会,席勒和马尔库塞的审美思想给中国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解决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异化问题,实现人的情感自由和审美自由,为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价值引领。
(一)审美引导当下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主体是在人性本真状态下生存发展的自然人和自由人,然而在技术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性不断遭受自己贪婪欲望的指使,人与自然的失序、人与人信任的丧失无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为现代人实现人性完整提供了重要参考。
要改变当下中国社会物化的人性状态,人们必须追求自身及群体之间的和谐生活,注重自我与社会的并头发展,追求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在自我和谐中以本能和谐最为典型,本能和谐是人和谐发展的基础与核心。由于尊严、智慧和自由是人自然天性的代表,是人作为自我完整存在必须坚守的人生原则,人的自然本性应该为其自身实现人性的完满和自由服务。人的自我和谐所追求的是按照快乐原则使其本能需求得到满足,其最大特点就是非功利性,是抛除客观外部世界的限制之后最为原本的自我需求呈现。面对已然分裂的人性,审美之维自然成为现代人实现人性自我救赎的重要思维方式,审美的非功利性与人性本我的内在本质得以融合,从而化解人性欲望与文明的冲撞,超越自我的自私状态,在理性原则的指引下实现感性和理性、状态和人格的统一。另一方面,在达到自我本能和谐的同时,人高尚的精神品格和审美情趣得以释放,每个人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全面发展,此时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便逐步超越其自身的功利性,实现自我和谐系统及社会群体系统的双重发展。由于审美的本质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审美可以弥补社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裂隙,揉合文明链条中社会发展与人性相悖的反向因素,并且激发人性审美情趣和个人生活趣味,提高人性本能的内在品质,在个体自我本能的释放之下逐步实现人与社会文明的和谐发展。在审美思维的指引下,人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找到自我存在价值,超越物质需求和现实利益对人的束缚,使之生活在一种审美化的文明方式中,实现中国社会和谐化发展。
(二)在审美中重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
在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人的物质欲望日益膨胀,许多人道德价值沦丧,人的自然本性不断遭受感性和理性的相互分离而发生改变。产生这些后果的关键的原因只有一个,即人们心中丢失了原有的精神支撑,导致道德的沦丧最终造成人性自由的缺失,人在自我束缚与技术束缚下成为毫无血肉生命的人。由此可知,要真正实现人性的和谐完整必须找到自我价值判断的引领方向,即找寻精神的力量,这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民族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引导,是国人的精神寄托,也是一个人的思想根基,民族精神在个人选择道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重塑民族精神的关键就要重建自我价值观,从而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中作出正确的自我判断和自我选择。所以,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保持人性自由始终是重塑民族精神的首要原则。席勒和马尔库塞的审美思想对于重塑民族精神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二者的核心都是找寻丢失的自由之魂,唤醒内心的信仰,对破碎的人格进行重新整合。审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性完整,民族精神的本质在于作为人自我心中的精神的支撑而存在,二者在核心发展中实现相互融合,从而消除人性异化、回归本真状态,在审美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信仰有道德的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实现自身的完整发展。
(三)在审美中渴望幸福、追求美好生活
人类发展离不开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得以成长和滋养的必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不断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十九大又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逐渐完善对于美好生活的阐释。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当下社会丰厚的物质基础大大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人们的需求也早就从基本生存转向个人发展与享受,由此有人认为,“‘美好生活’的概念是动态发展的,总的规定性应体现‘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需要相统一的原则”。[9]还有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美好社会,即“美好生活=幸福+意义”[10]。渗入到人类实际生活中的美好生活重点在于“好”和“美”,美好生活不只是“好”的生活更是“美”的生活,“好”不仅包括富裕的物质基础还有人与人这个群体之间的和谐;“美”不仅包括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美好事物,更在于由这些美好的客观存在带给主体的心灵享受与畅快,通过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相互结合引发人心底自内而外的幸福感。
席勒与马尔库塞的审美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美好生活的价值在于,美好生活并不是享有权力和财富占有等物质层面肤浅的自我满足,而是一种包蕴美感、更为高级的生活形态,审美可以在平淡朴实的日常生活中彰显出美的价值,通过各种展现美感的审美活动激发人的创造性,追求一种更为自由的生命体验,从而在单调的现实中学会享受幸福和自由,也可以说,美好生活的实质就是学会追求包含美感的生活。人一旦体验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只要人能感觉到幸福和自由,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就在无形中完成了审美的过程,像这样真正包含美感的并使得个体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所以,审美始终以实现人性幸福和自由为旨归,并且成为美好生活在实现过程中的精神指向,也是人性追求精神自由的关键环节,美好生活在审美的指引下由“好”的生活中走向“美”的生活,也就是在审美中走向真正的自由王国。
在席勒和马尔库塞的审美乌托邦中,人性问题是他们美学思想的前提,通过二者美学思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人性异化问题上,审美始终是他们美学思想的核心。但是,席勒和马尔库塞的审美思想是一场精神革命,二人的审美乌托邦虽然有现实状况作为其人性批判的根基,对资本主义制度及现实的批判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二者美学思想的局限性就在于二者的审美思想对人的解放是人内在精神的自由解放,并没有触碰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只是强调从意识形态实现人性解放,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压迫,其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空想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席勒和马尔库塞的思想是虚无缥缈的,二人不仅揭示了潜藏在人性中的贪婪懦弱和社会制度的弊端,而且为出现的人性分裂指明了解决方式和前进道路。所以席勒和马尔库塞的审美思想的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尤其对当下中国而言,它指导人们在审美思想的理论指引下不断培养本真意识,在现代文明社会的纷乱中保证内在心性的完整和统一,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中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统一。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