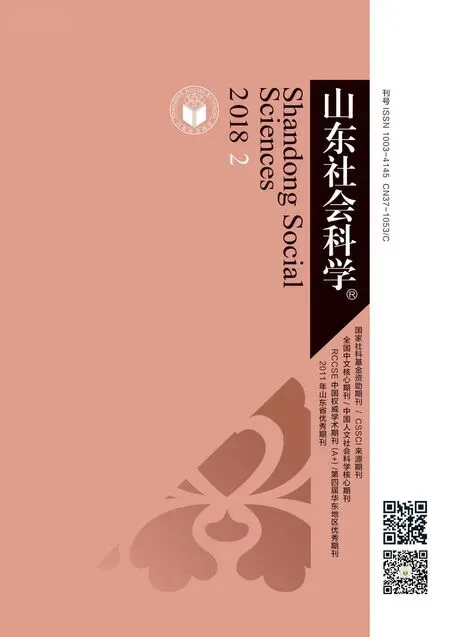左翼文学视野里的创造社同人之厄普顿·辛克莱汉译
咸立强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9.20—1968.11.25),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在校期间学习过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1904年下半年,《向真理呼吁》的编辑派辛克莱去芝加哥调查屠场工人的生活,他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屠场》。1906年《屠场》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辛克莱也因此被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为Muckraker[《天路历程》(Pilgrim'sProgress)中的一类人物,一般译为“扒粪者”或“黑幕揭发者”]。在中国,创造社同人对辛克莱文艺观念的译介引爆了革命文学的论争,小说的译介使国人认识到了资本家的本质。*梅志:《缅怀先辈和盟友》,载《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整体上来说其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为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美国因素;其次就是与胡适、梁实秋等对美国文化与文学的译介相比,为国人呈现了不同的美国面相。
一、创造社同人之前的辛克莱汉语译介
最早有意识地向国人介绍辛克莱的是郑振铎。《文学大纲》近代卷第17章“新世纪的文学”介绍了美国新世纪的小说、诗歌等方面的创作概况:“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是一个激进党、一个社会主义者,以一部《林莽》(TheJungle)得大名,然他的作品却很多很多。人称之为‘美国的威尔斯’(H.G.Wells)。”*郑振铎:《文学大纲》近代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52页。
在郑振铎之前,鲁迅的译文中也曾出现Sinclair。1925年1月,鲁迅在《民众文艺周刊》第4期和第5期上发表了厨川白村《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的汉语译文。因为辛克莱只是厨川白村文章中出现的一个案例,鲁迅并没有将Sinclair之名译为中文,也没有对Sinclair进行校注。鲁迅自言译文中“所举的西洋的人名,书名等”,虽然附注了英语原文,但他对于“英文是莫不相识”,英文的相关工作“都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许季黻四君”*鲁迅:《后记》,载《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帮忙做的。综上所述,不宜说鲁迅此时便已向国内文坛介绍了辛克莱,至多只能说是无意中将他呈现在国人面前。然而,最先翻译厄普顿·辛克莱文字的确是鲁迅。1927年12月21日,鲁迅撰写了《卢梭和胃口》一文,引用了辛克莱《拜金艺术》中的一段文字:“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对于他取了为父之劳的个人主义运动的全体怀疑,将我们带到子女服从父母,奴隶服从主人,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大学生毫不发生疑问,而佩服教授的讲义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么?”*鲁迅:《卢梭和胃口》,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9页。在文章末尾,鲁迅特别提及自己的上述引文“是从日本文重译的”,并谈到了Mammonart这个书名的含义。虽然只是摘译,又是从日文转译的,但鲁迅的《卢梭和胃口》中的这段文字的确是笔者所见最早的辛克莱文字的汉译。
创造社同人着手辛克莱的译介之前,译介辛克莱的国人只有郑振铎和鲁迅。郑振铎的介绍就像《小说月报》上的“文坛杂讯”或“文坛消息”,只是报告有辛克莱这么一个作家罢了。鲁迅真正注意到了辛克莱,并且翻译了辛克莱的一段文字,不过起因却是他对梁实秋发表在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上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不满。译介的虽然是辛克莱的文字,谈的对象却是卢梭,辛克莱还不是文章关注的真正焦点。真正隆重地将辛克莱作为整篇文章的核心,并将关键性译文用特别的大号字体凸显出来,译介于国人之前的,是创造社同人。
二、《文化批判》上的辛克莱
创造社同人中,最早翻译厄普顿·辛克莱的是冯乃超。1928年1月6日,冯乃超翻译了辛克莱的《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在为译文撰写的“前言”中,冯乃超明确宣示了译介辛克莱的因由:“以下的论文是从Upton Sinclair的Mammon art里面选译出来的。和我们站着同一的立脚地来阐明艺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从种种著作之中我们不能不先为此书介绍。他不特喝破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且阐明了今后的艺术的方向。”*冯乃超:《拜金艺术·前言》,《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同期《文化批判》刊登了李初梨作于1928年1月17日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中引用了辛克莱《拜金艺术》中的一句话,写出了英语原文同时也作了翻译:
All art is propaganda.It is universally and inescapably propaganda; sometimes unconsciously, but often deliberately propaganda.
李初梨译为:“一切的艺术,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冯乃超译为:“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它是宣传;有时是无意识的,大底是故意的宣传。”*冯乃超:《拜金艺术·前言》,《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
当时,李初梨和冯乃超都住在创造社为他们租住的房子里,朝夕相处,共同致力于《文化批判》的编辑及其他文学革命活动,他们在翻译辛克莱《拜金艺术》中的文字时,按理说应该会相互交流。《文化批判》第2期的稿子在出版前也曾放在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2月12日郭沫若就在出版部读过一些稿件:“午后往出版部,读了彭康的《评人生观之论战》,甚精彩,这是早就应该有的文章。回视胡适辈的无聊浅薄,真是相去天渊。读了巴比塞的《告反军国主义的青年》(均《文化批判》二期稿)。”*郭沫若:《离沪之前》,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6页。此时,《文化批判》第2期编辑工作已经结束,“编辑杂记”所署的日期是“二月十日夜”。既然郭沫若在出版前能看到,没有理由身为编辑的李初梨和冯乃超看不到。应该有交流的两人,为着相似的目的翻译辛克莱的同一句话,似乎并没有努力使两人的译文相似,相反地,似乎有意识地在拉开距离。个人感觉李初梨的读起来更为顺畅,考虑到李初梨文章创作日期晚于冯乃超11天,他参照了冯乃超的译文并稍微作了修饰,也是很可能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笔者都觉得两位译者译文的区别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种区别本来没有必要,李初梨的文章只是引用辛克莱的一句话而已,句式不复杂,意思也不难理解,而之前冯乃超翻译的也并没有什么错误,如果李初梨不同意冯乃超的译文,大可建议冯乃超修改,然后再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这段引文。这样,作为创造社的同人在同一期刊物上用同样的译文同时推出辛克莱,不是更显得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吗?
将All art is propaganda译成“一切的艺术,都是宣传”,还是“一切的艺术是宣传”,不同的翻译选择呈现出来的并非是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差异,也很难说是译者不同翻译风格的体现,同期刊物上出现的不同译文更像是在传达这样一条信息:这些都是著者自己进行的翻译。有意无意地显示同人们的翻译之能,这是后期创造社期刊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色。如果说前期创造社呈现了文学社团较为典型的构成模式:诗人、批评家和小说家,那么《文化批判》创刊后的创造社代表的构成模式则是:翻译家和批评家。此时的创造社翻译和批评聚焦的不是文学的趣味,而是要“把捏着辩证法的唯物论,应用于种种活生生的问题”*《编辑杂记》,《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想要通过译介引入“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新词汇,经由批评建构新的话语方式,从而实现新的启蒙运动。
《文化批判》共出版了5期,有关辛克莱的单独成文的翻译只有冯乃超发在《文化批判》第2期上的《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全译文大约3000字左右;此外,就只有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谈到了辛克莱。《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除了前文提及的那句译文,结尾谈到“暴露的无产文学”时,举了一个例子:“例如Sinclair的‘王子哈梗’”*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全文与辛克莱直接相关的就只有这两句,绝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李初梨曾经大量译引辛氏的文艺观点,冯乃超曾经摘引过辛氏《拜金艺术》中抨击传统文学的若干段落。”*葛中俊:《厄普顿·辛克莱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至于冯乃超,他也不是“摘引”,而是“摘译”。李初梨引译了辛克莱的话后说:“文学是艺术的一部门,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时常故意地是宣传。’”*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将其与李初梨自己的译文相对照,可知李初梨的文学定义并非如人所说:“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都是在有意识地模仿、借鉴辛克莱的艺术定义的基础上作出的。”*葛中俊:《厄普顿·辛克莱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不是“模仿、借鉴”,而是照搬辛克莱的定义,不过是将“艺术定义”缩小为“文学定义”罢了。“文学是艺术的一部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李初梨用“文学”二字替换了辛克莱原话中的“艺术”,所以李初梨此文并非重新定义了文学,而是引入了辛克莱的文学新定义!
辛克莱“文艺是宣传”观念的引进,是后期创造社革命文学转向中至为关键的一环。转变意味着扬弃,一方面引入新思想,一方面摒弃某些旧的思想。作为后期创造社的两大机关刊物,《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上刊载的文字也清晰地呈现出转型期的某些特点。“《文化批判》已经拖住Upton Sinclair,《创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开步走’了”*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Vigny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带有世纪末的颓废情调,批评家圣佩韦称其为象牙塔里的诗人。一方面是“激进党”的Upton Sinclair,一方面是消极颓废的Vigny,这种混杂正显示了后期创造社转向过程中内部存在的复杂的矛盾与冲突。成仿吾解释说:“《文化批判》介绍Sinclair而《创造月刊》介绍Vigny。这儿实在有绝大的矛盾;不过Vigny的介绍是去年以来的续稿。”*石厚生(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11期。一个是“续稿”,一个是新介绍,旧的渐去而新的方生,说明后期创造社在努力地实践着自身革命文学的转向。Vigny的稿件为穆木天所撰,编辑是王独清。《创造月刊》从第1卷第11期起解除了王独清的编辑职务,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后期创造社革命文学转向的内部努力。
《文化批判》对辛克莱的译介,在现代文坛上引发了持续的深远的影响。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周报》认为创造社同人不过是译介了“一点点辛克莱的‘口号’”*李作宾:《革命文学运动的观察》,《文学周报》1928年第332期。,这一批评近乎事实,而令人惊异的事情也正在于此:《文化批判》近于口号式的简单译介引爆了现代文坛辛克莱译介的热潮,使创造社成为国内辛克莱汉语译介的标牌。但是,《文化批判》第2期之后,哪怕左翼文坛为“文学是宣传”吵得纷纷攘攘,《文化批判》却再也不曾提及辛克莱,也没有继续深入阐述“文学是宣传”这个问题。甘人撰写了《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一文,质疑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辛克莱说:‘文学是宣传。’李君就鸡毛当令箭,弄成了‘宣传即文学’。”*甘人:《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北新》半月刊1928年第13期。辛克莱说的是“艺术是宣传”,由李初梨推导出的才是“文学是宣传”;至于“宣传即文学”,如果不是来自甘人对李初梨文字的恶意推导,就是传播和批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与变形。面对甘人的恶意推导,创造社同人的反应很值得注意。《创造月刊》刊发了后期创造社同人傅克兴的《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革命文学底根本问题底考察》,驳斥了甘人的文章。但傅克兴在文中只是笼统地说甘人“没有一句不暴露他自己底马脚”*克兴:《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革命文学底根本问题底考察》,《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2期。,却对甘人转述李初梨文字错误这类暴露“自己底马脚”的问题只字不提。辛克莱的原话是否就是“文学是宣传”,李初梨的意思是否就是“宣传即文学”,对于这些问题,傅克兴似乎根本不感兴趣,全文更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辛克莱。对于后期创造社同人来说,辛克莱似乎真的只是“一点点”“口号”,他们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辛克莱的文学观,而只是其中的“宣传”问题,或者说他们引入辛克莱之后不久,自身对辛克莱的态度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三、创造社同人的其他辛克莱译介
《文化批判》是《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创造月刊》1927年第1卷第8期。,后期创造社的这两种机关刊物,是创造社译介辛克莱的主要阵地。辛克莱之名首先见于《文化批判》,然后才出现于《创造月刊》。
《创造月刊》上最早出现辛克莱之名的,是1928年5月第1卷第11期上刊登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成仿吾在文中说:“《文化批判》介绍Sinclair也绝对不能是把他‘拖住’的,这可以说是十分明显。”*石厚生(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第11期。这显然是对鲁迅《“醉眼”中的朦胧》一文的回应。《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发表《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冯乃超在文章第6部分引用了N. Bucharin的一段文字,然后说:“艺术——文学亦然——是生活的组织,感情及思想的‘感染’,所以,一切的艺术本质底必然是Sagitation(原文排错,应是Sanitation,即工具的意思——引者注),Propaganda。(这不拘艺术家自身有意或无意)。”*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1期。虽然没有提及辛克莱的名字,但这句话里辛克莱的影子非常明显。不过,省略了辛克莱的名字,文字表述又是以N. Bucharin为主,辛克莱在文章中明显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同期《创造月刊》还发表了沈起予的《演剧运动之意义》,认为Upton Sinclair暴露了各种艺术定义的“虚假底面目”,但是他自身“所下的,‘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这个定义,仍然不是正确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底解释方法。”*沈起予:《演剧运动之意义》,《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1期。对辛克莱所下的“艺术定义”,沈起予也不满意,表示值得商榷,却就此打住,没有进一步展开。从《文化批判》到《创造月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创造社同人谈论辛克莱的态度和方式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此外,《创造月刊》上还有两篇文字谈及辛克莱。1928年9月3日,《创造月刊》以“编辑委员”的名义写了《资本主义对于劳动文学的新攻势》,为1月16日德国诗人J.R. Baecher被起诉一事抱不平。文章结尾处说:“其他如U. Sinclair,R. Rolland等世界著名的Intelligentsia也发送电报表示反对这个裁判。”*编辑委员:《资本主义对于劳动文学的新攻势》,《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3期。1928年12月18日,李初梨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一文中谈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不只是“为劳苦群众而作”,“在小说月报上茅盾的《从岵岭到东京》同时登载的,有一篇辛克莱的《住居二楼的人》。你看,对于一个在小资产阶级里面可说是站最高层的律师,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还可以Apeal他呢。”*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创造月刊》1929年第2卷第6期。辛克莱《住居二楼的人》是一幕话剧,由顾均正翻译,发表于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与《文化批判》相比,《创造月刊》上出现的辛克莱已经很难说是正式的译介了,至少在翻译方面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在态度上,此时的创造社同人表示“不能是把他‘拖住’”,认为“一切的艺术是宣传”这一说法也仍然不正确,这已经有点儿反思《文化批判》对辛克莱译介的意味了。何大白(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中谈到了当时非议“艺术是宣传”的一些“奇论妙言”:“主张‘艺术是宣传’,这是辱没了艺术的不敬汉;指出‘艺术的社会性’,这是什么党,什么主义的政治宣传。”有意思的是郑伯奇并没有就“艺术”与“宣传”的关系谈自己的看法,也没有为辛克莱或认同辛克莱的李初梨等辩护,反而说:“在这里,我们没有指出他们的社会背景的必要。”*何大白:《文坛的五月》,《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1期。这种宕开一笔的做法,在习惯了文坛“打架”*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创造》季刊1923年第1卷第4期。的创造社同人身上,往往意味着对所争论的问题并不怎么理直气壮。郁达夫在1928年为所译《拜金艺术》第7章撰写的“编者按”中说:创造社“忽而又要踢开辛克来氏”,指的应该就是《创造月刊》透露出来的创造社同人对待辛克莱态度的微妙转变。《文化批判》第2期大力推介辛克莱后,忽然闭口再也不谈辛克莱,这似乎也容易让人产生“又要踢开”的感觉。不待1934年辛克莱参与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创造社同人对待辛克莱的态度已经有所保留了。
冯乃超之后,更为全面地翻译了辛克莱《拜金艺术》的是郁达夫。1928年3月10日,郁达夫译完辛克莱《拜金艺术》第一章后,写了一段译后语:“听说《拜金艺术》一书,中国已有人介绍翻译了,可惜我还没有见到,否则拿来对照一下,一定有许多可以助我参考,证我拙劣的地方。”*郁达夫:《拜金艺术·译者按》,载《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20页。由此可知郁达夫先前并未注意到冯乃超的译文。翻译辛克莱《拜金艺术》第7章“阿嶷夫人出现”时,郁达夫在“编者按”中说:“这是《拜金艺术》的第七章,它的第二个主张若是真的说话,那么中国目下创造社的革命文学是已经成了范畴的艺术了。所以这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是和目下的支配阶级的南京革命政府表同情……”*郁达夫:《拜金艺术·译者按》,载《郁达夫全集》第1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李初梨等借助辛克莱的翻译倡导革命文学并展开了对郁达夫的批判,而郁达夫则通过辛克莱的翻译“悟”到创造社已经倒向了政府。郁达夫显然延续着《广州事情》的思维,没有注意到此时的郭沫若已经与南京国民政府水火不容了。作为曾经的创造社成员的郁达夫和作为现在的创造社成员的李初梨,都通过辛克莱看到了对方脱离真正的“革命”队伍的身影,这也应该算是辛克莱汉译史上值得立此存照的事了。郁达夫所译《拜金艺术》与李初梨、冯乃超相比更为丰富完整,但实际产生的影响却无法与后者相比。左翼文坛上谈及辛克莱“艺术是宣传”的话题时,一般都会提及李初梨和他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祝铭《无产阶级文艺底特质》*祝铭:《无产阶级文艺底特质——〈无产阶级文艺略论〉之二》,《青海》1928年第3期。和钱杏邨《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钱杏邨《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海风周报》1929年第14、15期合刊号。谈到无产阶级文艺与宣传性问题时,就都引用了其中的辛克莱译文及相关表述。不过,凡事无绝对,顾均正在《住居二楼的人》“译者识”里介绍辛克莱时说:“他还著了许多别的小说,但介绍到中国来的,只有一部论文Mammon art(郁达夫译,名《拜金艺术》)。”*顾均正:《译者识》,《小说月报》1928年第19卷第10号。只字未提《文化批判》对辛克莱的介绍。顾均正在1920年代一直在上海从事编辑和教育活动,在当时的语境下,如果他不是囿于文人团体的偏见等原因避而不谈《文化批判》,就只能说明译文的阅读及所产生的影响都有相当大的随机性。
辛克莱的国内译介是理论先行,《拜金艺术》中的文学观先被译介进来,然后才是小说。就辛克莱的译介来说,创造社“又要踢开”的似乎只是他的文学观念;至于他的小说,创造社同人(主要是郭沫若)却在“踢开”之后开始着手翻译。整体而言,也可以说创造社同人对辛克莱的译介重心开始由理论转向了小说。最先着手翻译的是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连续翻译了辛克莱的3部长篇小说:《石炭王》(KingCoal,1928年11月出版)、《屠场》(TheJungle,1929年7月30日译完,8月30日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煤油》(Oil!,1930年5月7日译完,1931年6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出版时署名坎人或易坎人。这是解放前辛克莱小说汉译最重要的收获,国人谈到辛克莱小说创作篇目时,大多使用的都是郭沫若的译名,如用《屠场》而不用《丛莽》、用《石炭王》而不用《煤炭大王》等。刚果伦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说:“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工人杰麦》,等等,全部译成中文了。这些译品的产生,对于中国普罗文坛的推进,是很有力量的。”*刚果伦:《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现代小说》1929年第3卷第3期。紧随郭沫若脚步、从事辛克莱小说翻译的创造社成员是邱韵铎。邱韵铎一向勤于英美文学译介, 但他和郭沫若一样,都是在创造社革命文学转向之后才注意到辛克莱,并开始着手翻译。1928年5月30日《畸形》半月刊创刊号发表了邱韵铎翻译的《肥皂箱——美国新诗人底介绍》, 1930年上海支那书店出版了邱韵铎翻译的辛克莱长篇小说《实业领袖》(TheIndustrialRepublic,与吴贯忠合译)。此外,创造社同人陶晶孙也于1930年在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翻译的辛克莱长篇小说《密探》(TheSpy)。
四、左翼文学运动中的“美国”元素
这一时期的创造社同人,对苏联新文学似乎并不怎么认可。李初梨翻译了塞拉菲莫维奇的《高尔基是同我们一道的吗》,并在译文前写了一段文字:“高尔基虽然承认了十月革命底历史的必然性,可惜他对于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底理论与实践,仍有追随不及的地方,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李初梨:《译者小引》,《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1期。沈起予在《演剧运动之意义》一文中更是直接指出:“革命期中底俄罗斯,所有艺术底部门,都表现出颓废的现象。”*沈起予:《演剧运动之意义》,《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1期。文中谈到1918—1922年俄国未来派的“标语口号文学”,认为“这时的未来派的作品根本没的站在无产阶级底立场上,只是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卖弄些文字上的专门曲艺”*克兴(傅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5期。。革命的俄罗斯在后期创造社同人们眼里,大概更多的是革命理论方面的贡献,而没有与之相称的新兴文艺创作。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来自“日本的火”*郭沫若:《跨着东海》,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最先点燃的却是美国的左翼文学。不管选择辛克莱的起因和过程是什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丰富了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在苏联、日本之外,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增添了“美国”元素。
李初梨和冯乃超看重的是辛克莱“文艺是宣传”这一思想中的“宣传”。冯乃超译完《拜金艺术》后,在“补记”中说:“以上所说无一不是依附于宣传这个名词的字义”*冯乃超:《拜金艺术·补记》,《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当他们从辛克莱那里借来“宣传”这个概念的时候,真正关注的是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当时,他们首先想要完成的工作是对文坛既定作家的批判,是要解决作为“新兴文艺”方向之基础的“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1928年第1期。的问题,因此他们着重探讨的是科学的人生观、社会观问题,并将自身的任务定位为:“确立辩证法的唯物论以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应用唯物的辩证法以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冯乃超《冷静的头脑》第六部分“革命文学”,问题“A”用的小标题是“生活组织的文学”,谈到“艺术”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表述的也是“生活的组织”*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1期。,这是Bucharin(布哈林)的思想,辛克莱在这里就只剩下了一个词:Propaganda。辛克莱“艺术是宣传”思想的译介对创造社同人来说更像是一个话题的引子。李初梨等从辛克莱那里接受了“宣传”这个词,将其与“组织”等词融合起来,紧紧抓住作家的阶级意识问题,进行“辩证法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的译介与推广工作。就此而言,辛克莱代表的美国左翼文学思想就像浮在表面的泡沫,苏联和日本的左翼文学思想才是构成创造社同人文学思想的真正底色。
与理论译介引发的热烈争议相比,辛克莱小说的译介在左翼文坛上获得了一致的认可。 “辛克莱乃美国所谓普罗作家中最享盛名者,所著《石炭王》(KingCoal)、《屠场》(TheJungle),经郭沫若译为中文,一时销行极广。”*季羡林:《辛克莱回忆录》,《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28日第1版。“辛克莱的作品,因为他描写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中国有一个时候很吃香,他的《屠场》、《石炭王》一类小说在中国曾风行一时。”*徐訏:《牢骚文学与宣传文学》,载《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8页。赵景深在1929年撰文介绍“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家”,认为辛克莱“是国人最熟知的”*赵景深:《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8期。。1930年辛克莱作品的汉译更是多达12种。*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在众多的译作里,被举为代表的都是郭沫若的译作,这说明郭沫若的翻译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郭沫若翻译这3部小说的时间不怎么宽裕,逐译逐印很是匆促,整体上来说算不上精品。但是,对于几年前就热闹起来的“革命文学”来说,却是很需要的作品。《屠场》写芝加哥屠宰场工人的悲惨生活及工人运动,《石炭王》描写科罗拉多州煤矿工人罢工事件,《煤油》抨击资本家垄断。这些小说都是大规模地表现社会、描写工人运动,对于身处上海这一亚洲最现代化都市里的左翼作家们来说,也都是可资借鉴的对象。瞿秋白在《读〈子夜〉》中说:“人家把作者来比美国的辛克来,这在大规模表现社会方面是相同的;然其作风,拿《子夜》以及《虹》,《蚀》等来比《石炭王》,《煤油》,《波士顿》,特别是《屠场》,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截然不同点来,一个是用排山倒海的宣传家的方法,一个却是用娓娓动人叙述者的态度。”*瞿秋白:《读〈子夜〉》,《中华日报·小贡献》1933年8月14日第1版。郭沫若谈到《屠场》时说:“本书所含有之力量和意义,在聪明的读者读后自会明白。译者可以自行告白一句,我在译述的途中为他这种排山倒海的大力几乎打倒,我从不曾读过这样有力量的作品,恐怕世界上也从未曾产生过。读了这部书我们感受着一种无上的慰安,无上的鼓励:我们敢于问:‘谁个能有这样大的力量?’”*易坎人(郭沫若):《译后》,载[美]辛克莱:《屠场》,易坎人译,南强书局1929年版,第406页。瞿秋白和郭沫若两人都使用了“排山倒海”这个词,瞿秋白用来形容茅盾的《子夜》,郭沫若则用来形容辛克莱的《屠场》。瞿秋白用来形容《屠场》的词是“娓娓动人”,“娓娓动人”和“排山倒海”合在一起,便是文学与宣传恰到好处的组合。就此而言,辛克莱小说打动中国左翼作家的不仅仅是“力”,还有“力”的表现方式。
1930年11月1日出版的《读书月刊》创刊号登载郭沫若《煤油》译本广告:“煤油,说起来谁都知道这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根本生产之一,这部名著就在暴露帝国主义争夺煤油生产以及煤油产地之资本剥削的黑幕,同时就在暴露帝国主义的丑恶,在暴露着建筑在这种丑恶上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机构的丑恶。作者认定了一种力量,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线的力量露出了资本主义种种的丑恶。内容非常复杂与伟大,有爱情事件的穿插,有劳苦群众的斗争,有资本家庭的压迫,且背景是世界,而其描写方面尤为深刻动人,结构是宏大绵密,波澜是层出不穷,力量是排山倒海,总之,他的这部作品,真是可以称为‘力作’。译者又是中国文坛的名士,译笔当然是可靠。全书五十万言,九百余页。平装、精装实价分别是大洋三元和三元四角。”“力”“力量”是竭力被突出的小说特征。郁达夫认为:“革命文学之成立,在作品的力量上面,有力和没有力,就是好的革命文学和坏的革命文学的区别。”*郁达夫:《断篇日记》,载《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读者们也向刊物编辑们要求“有力的作品”*R.T.:《文化问题与月刊》,《创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4期。。对于小说“大力”的审美追求,在左翼文坛上曾流行一时,但能够表现辛克莱小说那样“大力”的作品却很少见。就此而言,辛克莱小说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审美趋向,或者说为此类小说的创作树立了模仿的榜样。
五、翻译的政治:左翼、日本体验与辛克莱的汉译
翻译的政治无所不在,翻译即政治,对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翻译来说尤其如此。本文难以全面深入地讨论创造社同人翻译辛克莱的政治性问题,只是想简单地指出影响辛克莱汉译的两个重要的政治因素:首先,辛克莱的汉译选择及其盛行与大革命失败这一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其次,辛克莱汉译最兴盛的几年,正值中国和日本、美国之间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美日两国在中国的角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留日和留美两大留学生群体,辛克莱的汉语译介与两大留学生群体思想观念的碰撞也有密切的关联。
从1928年到1934年辛克莱参加州长大选为止,是辛克莱汉译风行的主要时间段,也是中国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旺盛”起来的时期。1931年,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中说:“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304页。鲁迅说的“前年”,就是1928年,创造社同人倡导“革命文学”与译介辛克莱是同步的,鲁迅分析“革命文学”旺盛原因的这段话,用之于剖析辛克莱汉译兴盛的缘起也很恰当。作为“激进党”的辛克莱,他的许多小说创作都带有革命的色彩。辛克莱谈到自己的《实业领袖》时说:“这篇东西是一种革命的文件。”*辛克莱:《原序》,载《实业领袖》,邱韵铎、吴贯忠译,上海支那书店1930年版,第2页。当时,译介辛克莱的刊物如《大众文艺》《拓荒者》《文艺月报》《文学》《光明》《杂文》等,都是左翼刊物。鲁迅和郁达夫译介辛克莱时虽然与创造社同人关系不睦,但他们都是左翼阵营中人。1930年1月,艺术剧社在上海公演了辛克莱的《梁上君子》(鲁史导演)。艺术剧社由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郑伯奇、沈端先(夏衍)、陶晶孙、冯乃超、叶沉(沈西苓)发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他们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辛克莱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被推崇,离不开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兴盛,而辛克莱的译介反过来也推动了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发展。按照鲁迅的说法,革命文学的兴起是革命受了挫折后的产物,也可以视为革命实践在文学领域里的延续,因此左翼文学界译介辛克莱的政治诉求非常明显,而辛克莱汉译著作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也就不可避免了。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说:“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的被禁止的,而且又要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家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菲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 Sinclair)……”*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1934年3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准查禁的书目中,郭沫若译的辛克莱小说赫然在目,且都有一些具体的介绍说明——现代书局出版之郭沫若《石炭王》:“内容描写一大学生投身矿坑当小工,联合工人与资本家抗争,意在暴露矿业方面的资本主义的榨取与残酷,阶级意味,极为深厚。”南强书局出版之郭沫若译《屠场》:“描写美国资产阶级在屠场里,对于工人之榨取与压迫,极力煽动阶级斗争。”*转引自倪墨炎:《149种文艺图书被禁的前前后后》,载《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203页。
1920年代早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坛缔造辉煌的时候,去美国留学的闻一多、梁实秋都曾表示亲近甚或追随之意;1920年代晚期,待到闻一多、梁实秋留美归来,他们与革命文学转向后的创造社离得越来越远。其中因由,除了文人个性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外,不得不考虑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这个外在的大环境。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排华法案。192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移民法案(ImmigrationActof1924),按照不同国籍分配移民名额同时禁止亚洲人移民。以自由标榜的美国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块乐土,但是庚子赔款“退款”却使一些情况悄然起了变化。为了加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美国国会于1908年同意将庚子赔款的“退款”用于在华办学及选派留美学生。1924年,苏联放弃了庚子赔款,而美国则决定将剩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并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受此影响,留美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学成归国后进入政界、学界,最终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的庞大群体。并非所有留美学生都因“退款”而受惠,但是美国的做法的确影响了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影响所及也就使他们对美国政治文化等更为亲近和认同。从《学衡》派到新月派,许多留美知识分子都曾是白璧德的学生,梁实秋以白璧德的思想批评卢梭,扬起了美国老师白璧德的旗帜,表现出来的是对英美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认同,也可以视为留美学生群体中许多人的共同想法;反过来看鲁迅、郁达夫、李初梨等,他们和梁实秋差不多同时在译介美国的文化与文学,不过选择的却是辛克莱。李初梨、冯乃超、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都是留日学生,且留日时间大多在10年左右。从教育背景上看,率先译介辛克莱的不是留美学生而是留日学生群体,且译介主力一直都是留日学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留日、留美两大留学生群体在美国文化与文学译介方面表现出来的壁垒鲜明的差异,超越了纯文学本身,有着耐人咀嚼回味的政治意义。
当时,李初梨、冯乃超等首先将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鲁迅、郁达夫,一时之间各种批评与反批评文字热闹非凡。不久,李初梨、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同人就跟随鲁迅、郁达夫的步伐,开始批判梁实秋的文学观。李初梨和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2期上译介辛克莱时,并没有提到梁实秋的名字,等到冯乃超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冷静的头脑》、沈起予在《创造月刊》第2卷第3期上发表《艺术运动底根本观念》时,便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梁实秋在“天才”“健康与尊严”等方面所持的观点。如果以辛克莱的译介作为观察点,可以看出貌似三国混战的论争,实可视为留美、留日两大群体间的对垒。鲁迅、郁达夫、李初梨、冯乃超、郭沫若等作为革命文学论争的敌手,只不过是留日学生群体内部不同声音的表达;他们不仅都是留日学生,也都属于左翼文化阵营,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当他们面对从美国吹来的风时,“日本的火”就有了共同的敌人,自觉不自觉地便表现出其内在的一致性。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都开始着手做辛克莱的译介工作,对梁实秋等新月同人的文学观展开相似的批判,便是其内在一致性的具体表现。梁实秋等留美学生向国内译介的,是富有绅士风度的白璧德、杜威等;鲁迅、郭沫若等留日学生译介的辛克莱则是美国的Muckraker“扒粪者”。就美国文化与文学的译介而言,两大留学生群体在这一时间段的译介活动呈现出来的是美国的不同面相,也可以视为留学生群体的日本体验和美国体验之间的一次大碰撞。鲁迅、郁达夫和郭沫若等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弱国子民的身份备受侮辱;而当时的日本在美国面前又何尝没有弱国子民的感觉?1924年5月26日美国新移民法案经总统柯立芝签字后正式生效,在日本引发剧烈反响,有民众到美国使馆门前自杀以示抗议,而日本政府都要用法律将其定为“国耻日”。因此,鲁迅、郭沫若等留日学生的“日本体验”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双重意义上的弱国子民的体验,这使他们更容易倾向于接受反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激进党”辛克莱满足了鲁迅、李初梨等从日本归来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多重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