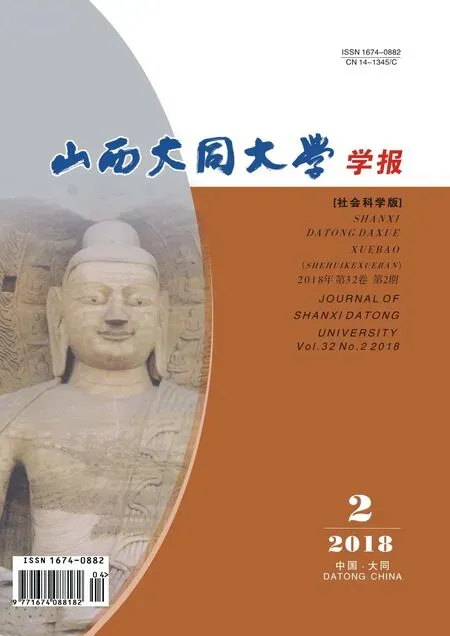近代国外关于云冈石窟的考察与记述
张月琴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山西 大同 037009)
20世纪初期,日本人伊东忠太第一次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考察和记述,之后法国人沙畹的美术摄影发表,云冈石窟的形象开始在国外传播开来。伊东忠太的《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沙畹的《华北考古学使命记》出版之后,云冈石窟成为国内外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和美术家向往的地方。云冈石窟的形象开始见诸著作和报道,不同身份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阐释着云冈石窟,逐渐丰富了人们对云冈石窟形象的认知。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近代国外学者对云冈石窟的认知、考察和研究,以发现近代云冈石窟的域外形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一、欧洲学者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和记述
近代欧洲学术界对于云冈石窟的认知首先来源于法国人沙畹关于云冈石窟的摄影作品。沙畹是一名汉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经典的研究颇为深刻。在1907年左右,沙畹在中国北方进行了十几个月的考察,收集了很多碑刻资料、拍摄了大量的图片。1909-1915年撰写并出版了《北中国考古图录》。《北中国考古图录》中刊登了云冈石窟的一批照片。这批照片成为西方世界最早了解云冈石窟形象的资料,其中的解说文字更是引起了汉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的关注。自此以后,欧洲来华人士和传教士纷纷踏足云冈,记述和研究云冈的文章和著作也陆续出版问世。
沙畹对于近代云冈石窟形象的贡献主要在于为云冈石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照片,使接触这些照片的人能够直观感受云冈石窟的独特的宗教艺术和建筑形态。与沙畹相比,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更偏重于用文字描述云冈石窟的形象,并记录了他对于云冈石窟开凿的原因、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等诸多方面的思考。
面对云冈石窟,卫礼贤首先想到了开凿石窟的鲜卑族和其建立的北魏王朝,他认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和北魏统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开国皇帝是一个精力旺盛、坚决果断的人。他禁止自己的臣民穿着原来的服装,使用原来的语言,尊奉原来的信仰。通古斯人彻底汉化了。这位统治者像满族人一样,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于是云中留下了成千上百座石雕的佛像。整个石窟都凿进山体之内,窟内的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佛。”[1](P107)在卫礼贤看来,北魏统治者对佛教的接纳和认同是云冈石窟得以开凿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云冈石窟是一座精美的艺术宝库,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那些庞大的雕像发出低沉有力的和音,而那些小的和再小的,则用优雅的曲调和着”。[1](P109)他还探讨了云冈石窟的艺术源流,认为“云冈比哥特式的建筑更进了一步:石头会呼吸了,它不仅仅具有生命,面且还拥有了灵魂。在这里,它们不仅是承担着重量和地球引力的物质,而是成千上百个不同的身体和面孔,每一个都拥有灵魂,它们一起和谐地汇入了永恒之歌。”[1](P110)卫礼贤结合自己在途中的见闻,思考了鲜卑族汉化之后,鲜卑文化融入大同地方,对地方文化形成的影响。“如果今天你在这一地区旅行,还会看到与汉人迥异的面孔。他们头上缠着布,身上穿着特殊的袍子,胳臂和很大一块胸膛赤裸在外。妇女的装束也是一样,这习俗在中国其它地方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服装是从哪儿传下来的呢?它难道是比石像或是青铜纪念物寿命更长的拓跋传统的遗留吗?……”[1](P109)
除了沙畹和卫礼贤,欧洲其他学者对于云冈石窟也作了考察和记述。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的《中国雕塑——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一书对云冈石窟雕塑艺术作了介绍。
二、日本学者视野中的云冈石窟形象
从伊东忠太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开始,很多日本学者来到中国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常盘大定、关野贞、滨田青陵、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在外国云冈石窟形象的构建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日本人对于云冈石窟的记述和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云冈石窟的主体资料。
伊东忠太,是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近代考察和记述云冈石窟的第一人。1902年始,伊东忠太开始游历亚洲各地。1906年,《建筑杂志》第106号登载了伊东忠太的《云冈旅行记》,留下了近代建筑学界对于云冈石窟最早的关注。同年,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青陵主编的《国华》杂志上登载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在文中伊东忠太详细地论述了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
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外国云冈石窟形象的构造中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曾经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辽宁等省进行了的广泛考古调查,其范围主要涉及古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二人合著的《支那文化史迹》开篇即为云冈石窟,在书中他们充分肯定了云冈石窟在中华佛教史上的地位,掀起了国内学术界研究云冈石窟的热潮。
受伊东忠太、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影响,滨田青陵来到了云冈石窟进行考察,在他的文章《从云冈到明陵》中对当时云冈石窟的研究状况作了描述,在他之前东、西方的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已经作了相当的努力,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野、常盘两位博士的调查和研究,资料详细可观。[2]
1938年至1944年间,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人对云冈石窟的调查是日本学术界对于云冈石窟的关键性调查,也是近代国外学者对于云冈石窟的集中调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云冈石窟的七次调查得到了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支持。长广敏雄参与了其中四次调查,留下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和较为可信的日记。这七次调查以实地拍摄和测绘为主。调查形成的报告《云冈石窟》16卷本,成为了目前研究云冈石窟主要的文本依据。”[3]毫无疑问,《云冈石窟》16卷本代表了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考古、研究和云冈学方面的重要成就。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在其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此次调查成果,“(《云冈石窟》)由正文篇和图版篇两部分构成,正文篇收录了详细到记录了每尊佛像的调查报告并围绕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方面考察的论证、尽可能采用拓片,还有从整个石窟到主要的佛像,都准确地以线条绘制的实测图等;图版收录的是,将所有的佛像不论大小无一遗漏地全部拍照,制成清晰的大型照片。作为这个种类的调查研究报告书,的确是极尽全面的文献,特别是照片和实测图是难以再度得到的珍贵资料。另外,涉及到细节的观察记录也甚为珍贵。”[4](P5)在《云冈日记: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中,长广敏雄对自己参与的调查实况进行了记录,其中对于云冈地方的风土人情的描述,是后人理解战争时期日本人占领下的中国北部生活的重要资料,也是近代云冈周边环境的重要描述。此外,日本学术界依据与此次调查的相关成果对云冈石窟佛教艺术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如水野清一的《云冈石窟与它的时代》(1940),小川睛旸的《大同的石佛》(1942),长广敏雄的《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等。
除了上述近代初期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和记述,还有其他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艺术作了记述和研究,形成了数量较为可观的论文或论著。如大村西崖发表于《东洋美术大观》1915年13辑雕刻部的《元魏的佛像》,1916年松本文三郎的《支那佛教遗物》,1924年丙午出版社发行的小野玄妙的《极东的艺术》。另外,1938年岩崎继生的《大同风土记》中也记述了云冈石窟。
三、国外学者知识谱系中云冈石窟形象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之前来到中国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充满着好奇,希望看到和了解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事物,并通过摄影或者文字把这些事物记录下来、传播开来。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并不是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或者文化背景出发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拍摄,对石窟开凿的原因、艺术源流、文化影响等进行了相关的思考。
随着考察的深入和摄影作品、记述文字的发表越来越丰富,外国学者的视线开始集中于石窟在佛教建筑艺术上的重要性。世界范围内类似于云冈石窟的大型建筑并不少见,但是作为四至五世纪北部中国建筑之最高成就,云冈石窟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建筑艺术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平城(大同)仍为北都,云冈作为佛教要地尚在继续,凿窟雕龛并未少歇,尽管大型窟减少了,中小窟龛却自东迄西遍布云冈崖面,甚至向西一直延续到云冈以西30里外的焦山南坡”。[5](P84)与莫高窟、龙门石窟相比,云冈石窟开凿的时间相对集中,加之平城实力的集聚使得石窟展现出了其他石窟所没有的建筑的计划性、统一性和系统性。这正是云冈石窟能够吸引近代中外学者对其进行考察、记述和研究的主要原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利用战争加紧了对云冈石窟的调查。参与调查的日本学者利用近代摄影技术和实地测绘手段对云冈石窟进行了颇为细致的记录。依据调查之后出版的《云冈石窟》16卷本,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成果。这一批研究成果既是后人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认知云冈石窟形象的主要来源。这批相对全面的云冈石窟的资料,引发了日本学术界对云冈石窟解剖式地研究和深入思考。当然,这些研究成果也中包含了鲜卑文化对中华文化影响的探讨。
四、结语
近代国内外学者对云冈石窟的形象考察和研究,构成了学术界对于云冈石窟形象的认知,是现代学术界云冈石窟形象形成的基础。近代云冈石窟的形象能够在国外广泛地流传得益于摄影技术的发展。沙畹、伊东忠太等人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有关云冈石窟的照片。无论从欧洲学者的眼光来看,还是从日本学者的眼光来看,他们来到云冈石窟就相当于进入一个充满神奇的佛教艺术殿堂。他们根据自己在云冈停留时间的长短,选择自己参观的洞窟、留下自己对云冈石窟的思考。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之后,云冈石窟形象由主要依赖于照片传播发展到了依靠文字传播。有关云冈石窟的文字记述由最初的日记或者是简单的文字描述发展成为了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们的关注点开始向纵深发展,从探究云冈石窟在佛教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发展到了深入挖掘造像艺术和造像背后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对云冈石窟的记述和研究经历了从照片到文字再到研究成果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推动着云冈石窟的形象由浅层次向深层次细腻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德)卫礼贤著,王宇洁译.中国心灵[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2](日)滨田青陵.从云冈到明陵[EB /OL].http://blog.sina.com.cn,2010-04-07.
[3]张月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云冈石窟的调查——以《云冈日记:战争时期的佛教石窟调查》为中心[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6(04):40-42.
[4](日)曾布川宽著,陈尚士译.云冈石窟再考[J].大同今古.2012(01):05.
[5]宿 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A].中国石窟寺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