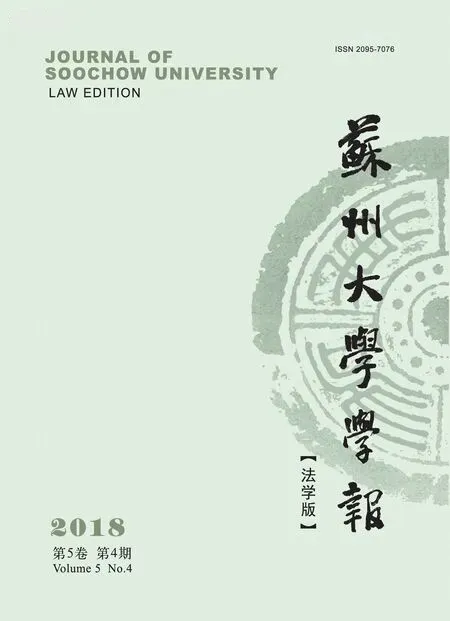组织支配与组织犯的归责基础
李 波 周建航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犯罪领域也出现了利用组织运作参与犯罪实施的新类型,即组织犯罪。组织犯在国外刑法理论中又被称为“正犯背后的正犯”“无形的正犯”,其在司法实务中容易被忽视。与传统个体犯罪相比,利用有权力的组织,充分利用其中的人财物,不仅可以提高犯罪成功的机率,在组织遮蔽之下也不容易被发现和追诉。对于组织内部握有权力、操控组织运作流程的上级而言,当其有意犯罪时,利用组织实施犯罪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只需下达命令,该命令即可透过组织内部的阶层结构最终传递至具体执行该命令的人。由于组织拥有大量下级成员可供选择,再加上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规则,下达命令的上级不需要亲自实施即可确保命令得以实现。例如,2012年11月2日,为了让开发商同意停建被老百姓投诉的车库,河南省永城市政法委书记张某委托永城市副市长和永城市住建局局长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允许开发商给两小区增高楼层。开发商拿着“会议纪要”找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主任夏某,要求给新增楼层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夏某和该中心时任用地规划股股长刘某在明知“会议纪要”违法的情况下,仍然按上级领导要求办了证。一审法院认定夏某、刘某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免予刑事处罚。夏某不服,称自己是执行职务没有滥用职权的故意。二审法院认为,夏某作为规划单位主要领导明知“会议纪要”违法仍去执行,应属滥用职权,最终维持原判。①张恩杰:《明知“会议纪要”违法仍执行 官员首次被判滥用职权》,http://www.fawan.com/2017/12/03/ 723823t18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5日。在本案中,具体执行上级“会议纪要”的夏某和刘某成立滥用职权罪并无疑问,问题是作出违法“会议纪要”的张某等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本案没有涉及该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讨论的余地。
由于组织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优势,组织往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犯对现代社会的威胁不容小觑。为了应对组织犯的威胁,我国刑法规定了许多处罚组织犯的具体规则,比如刑法第26条第2、3款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但是一方面,组织犯不仅涉及犯罪组织中组织、指挥、领导者利用下属成员实施犯罪的状况,还包括合法的国家组织或经济组织中上级利用下级实施犯罪的某些行为类型。上述刑法第26条第2、3款只是对犯罪组织中的组织犯进行了规定,而没有涉及其他类型的组织犯。另一方面,该条款只规定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要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负责,而没有明确归责的基础和形式,即对组织犯应按照教唆犯、间接正犯、共同正犯抑或其他类型予以归责。追问这一问题,并不是教义学的过度精致化,而是量刑妥当性的要求。为了在教义学上妥当说明组织犯的归责原理,刑法学者提出诸多方案,比如德国刑法教义学上的组织支配理论、社会支配理论,以及日本刑法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等。“日本刑事司法判例以及刑法理论上的共谋共同正犯包括了组织犯的情形;德国判例的通说对正犯与狭义共犯的区分采主观说,组织犯的情形作为正犯处理;德国刑法理论中的‘无形的共同正犯’或‘正犯背后的正犯’则包括了组织犯的情形。”①赵辉:《组织犯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笔者意欲比较上述理论的效果,在此基础上确定组织犯的归责类型。我们认为,在众多理论当中,以组织支配理论为基础的犯罪支配层级理论具有合理性。目前我国学界对组织归责的基础原理——组织支配理论——关注不多,学者对组织支配的实质存在许多认识误区。比如,有学者认为组织支配属于强制支配的下位概念,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页。有学者主张采用答责性原则或共谋共同正犯理论解决组织犯的归责基础问题。这些见解不仅本身存在论证上的疏漏,也没有看到组织归责的特殊之处,亦即:在组织犯罪中,下令者是通过掌控组织运作间接支配犯罪的因果流程;相反,在个体犯罪中,犯罪人是通过掌控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实施犯罪的。
二、组织犯的归责形式
在组织犯的归责形式即组织犯罪中下令者的归责类型上,主要有间接正犯、教唆犯、共同正犯、直接正犯等观点。下面主要介绍间接正犯说、教唆犯说以及共同正犯说,一方面是因为这三种学说之间争论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间接正犯是正犯的一种形态,实质上与直接正犯没什么不同。”③[日]野村捻:《刑法总论》,全里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页。
(一)主要学说
1.间接正犯说。组织犯的归责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63年,当时德国学者罗克辛在考察“艾希曼案”与“斯塔辛斯基案”判决时认为,不仅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需要被追究,幕后的下令者也具有同样的可罚性。
在“艾希曼案”中,艾希曼是纳粹党卫队的中尉,在他的策划下,大批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并予以屠杀。罗克辛认为,虽然艾希曼没有亲自实施杀人行为,也没有强迫或欺骗执行命令的组织成员,但由于屠杀命令由其下达至具体实施屠杀行为的人,基于对权力组织的支配,应认定艾希曼为间接正犯。在“斯塔辛斯基案”中,被告人斯塔辛斯基受苏联情报机构的委托,用一把毒素手枪杀死了两名流亡西德的俄国政治人士。裁判理由认为,被告人斯塔辛斯基并不是积极地执行命令,而是担心如果不执行任务就会遭到组织的报复,最终在此人性弱点支配之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斯塔辛斯基应成立帮助犯,指使斯塔辛斯基杀人的幕后下令者具有正犯意志,应成立间接正犯。罗克辛认为,该案判决结论和论证理由都有错误,法官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建立在行为人内心想象之上,是极端主观主义的表现,不符合法安定性原则。罗克辛主张,斯塔辛斯基基于杀人行为应成立直接正犯,幕后下令者基于组织支配成立间接正犯。①Roxin,Straftaten im Rahmen organisatorischer Machtapparate,GA 1963,193 ff.
学者认为,“组织支配具有以下三个成立条件:(1)命令者必须在组织的范围内行使了命令权;(2)组织必须在其具有刑法意义的活动范围内脱离了法律;(3)单个的执行者必须是可替换的,故一旦出现某个执行者停止执行命令的情况,随即有其他人可以取而代之。这三个成立条件的存在升高了直接行为者的犯罪倾向,因为:命令在权力组织的框架内产生了一种要求执行者据此调整自己行为的压力;机构的违法性使实行者认为,他不必为将来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而担优;执行者的可替代性使执行者认识到,其行为对于犯罪的实施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即便他不去实行犯罪,也会有其他人来实施。”②[德]克劳斯·罗克辛:《关于组织支配的最新研讨》,赵晨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可见,在组织犯的场合,虽然直接实行人基于自由意志负独立的刑事责任,但是幕后下令者通过对组织本身的支配提高了直接实行人实施犯罪的几率,应成立间接正犯。
2.教唆犯说。持教唆犯说的学者认为,在利用组织运作实施犯罪的场合,站在实行犯背后的下令者仅能以共犯中的教唆犯论处,不能认定为正犯。这是因为在组织犯的场合,直接实行人通常是具有规范意识和刑事责任能力的正常人,他们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清醒的认识,要负独立刑责。既然如此,幕后下令者就不可能完全支配直接实行人的行为。这种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标准,被称为答责说。答责说又分为严格答责说与缓和答责说。
严格答责说认为,如果直接实行人能够自由决定是否实行,下令者成立教唆犯,否则成立间接正犯。比如赫兹贝格认为,判断利用人是否成立间接正犯,要看在构成要件结果实现之前是否介入其他自由负责之人。③Herzberg,Täterschaft und Teinahme,1977,S. 202.雅科布斯也认为,间接正犯属于建立在优势支配基础上的优先管辖,优势支配即利用不可归责的工具提高构成要件实现的可能性。不过,即使行为人具有优先管辖的地位,但直接实行人基于完整的自由意志而独立负责时,前者不成立间接正犯。④Jakobs,AT,21/94.
缓和答责说认为,答责性大体上可以作为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标准,但有例外。在某些状况下,基于有力的事实支配,即便直接实行人属于自由负责之人,幕后下令者也可以成立间接正犯。比如被利用者基于可避免的错误实施了犯罪行为,由于可避免的错误只能减轻罪责,实行人仍然要承担独立的罪责,但是如果利用人基于信息资讯等方面的优势令被利用者陷入错误,其对构成要件事实的掌控大于被利用者,仍然要承担间接正犯的责任。⑤Roxin,in :Amelung(Hrsg.),Individuelle Verantwortung,2000,S. 55.
3.共同正犯说。持共同正犯说的学者认为,组织内部的下令者利用组织运作,责令他人代为实施犯罪行为,幕前的直接实行人与幕后的下令者构成共同正犯。一般来说,共同正犯的成立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共同的行为决意与共同的实行行为。在组织犯的场合,下令者仅仅是下达命令,并不会征求被命令者的同意,他们之间如何成立共同的行为决意呢?另外,下令者仅仅是下达命令,而不负责具体犯罪的实施,他与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成员如何成立共同的实行行为呢?既然两个条件都不满足,组织犯如何成立共同正犯呢?
就共同的行为决意而言,持共同正犯说的部分学者认为,共同的犯罪决意对于共同正犯的成立并不重要。比如,雅科布斯从客观归责的角度论证组织犯成立共同正犯,他认为共同正犯的成立关键在于犯罪人客观上的分工,而非意思与心理上的一致。只要犯罪行为具有关联性,即使一方仅具有配合的意思,幕后的下令者也能够成立共同正犯。⑥Jakobs,AT2,§ 21/43.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组织犯成立共同正犯所需要的行为决意,与其他共同正犯相比有所降低。比如,耶塞克与魏根特认为,下令者与被命令者的共同犯罪决意建立在对特定犯罪需被实行的意识上。①Jescheck/Weigend,AT5,S. 670.奥托也认为组织成员通过其实行行为默示地接纳了犯罪计划。②Otto,AT7,§ 21 Rn. 92.
就共同的实行行为而言,持共同正犯说的学者多认为,即使部分行为人没有实施实行行为,但只要其在预备阶段的行为对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有重要促进作用,或对于组织犯罪或形成犯罪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也符合共同正犯的要求。这是因为,德国刑法通说在共同正犯的成立上更加重视主观条件,对行为人之间在客观上的贡献有所降低(但不是没有)。日本通说认为,“实施了实行行为者是正犯,用实行行为以外的行为给正犯的犯罪加工者是共犯。”③[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在行为人共同策划了犯罪,但只有部分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的场合,有些学者认为,实行的行为人与没有参与实行的行为人已经结成了“共同的意思主体”,只要其中一人实行了犯罪行为,全体共犯都成立正犯。④[日]西田典之:《共犯理论的展开》,江溯、李世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还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类似于间接正犯,即没有参与实行的行为人其实是利用了他人的实行行为,因为是否具有实行行为不应仅从存在论上判断,而要从规范上予以判断。
(二)学说批评
1.对共同正犯说的批评。通过放弃或降低共同行为决意的重要性,论证组织犯罪中的下令者与直接实行人成立共同正犯的做法并不妥当。首先,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德国刑法理论的共识,也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我国刑法第25条明文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可见,共同的行为决意是成立共同犯罪必不可少的要件。德国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数人共同实行犯罪行为者,均依正犯论处”,这里似乎没有关于主观方面的规定,但共同的行为决意始终是成立共犯的重要条件。这是因为,共同犯罪的各方互相为彼此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里的归责基础就是共同的行为决意。如果行为人没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让其为他人的行为和结果负责,就违反了刑法上的罪责自负原则。其次,对于区分正犯与共犯及不同类型的共犯而言,行为决意无疑是区分标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自客观面确定归责范围会造成共同正犯的归责过广的缺失,严重侵蚀帮助犯的成立空间。”⑤Langneff,Beteiligtenstrafbarkeit,S. 118.因为帮助犯对犯罪实施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或心理帮助,如果不清楚其主观方面的行为意思,就会将其作为共同正犯论处,不当地加重刑罚。再次,认为实行人以其行为默示地接纳幕后下令者的犯罪计划,就能够成立共同行为决意的观点,也不妥当。“共同行为决意是行为人彼此间相互沟通的过程,这种相互沟通的过程是形成一致的共同行为决意的基础。”⑥Puppe,ZIS 6/2007,238.单纯接受上级命令不是共同犯罪中的意思联络,意思联络需要双方互相反馈意见,最终形成是否以及如何犯罪的决意。最后,忽略共同的行为决意,也无法区分共同正犯与同时犯。
扩张实行行为范畴,将组织犯中的下令者在预备阶段的贡献延续到实行阶段予以评价,以此证明组织犯罪中的下令者与直接实行人构成共同正犯,也不具有合理性。首先,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是将实行行为作为区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但将预备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来评价,必将导致实行行为本身的崩溃。因为实行行为原本是侵害法益的现实而紧迫的危险,如果将下令者所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来看待,认为其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显然是荒谬的。其次,实行行为作为区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也有瑕疵,其对于在组织犯罪中,下令者的正犯性、原因自由行为的正犯性等问题都很难发挥作用。以原因自由行为的正犯性为例,无论将原因行为还是结果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来加以评判都有问题。因为原因行为对于法益侵害还不具有紧迫性,结果行为虽然具有法益侵害紧迫性,但也违反了行为与责任同在的原则。实际上,区分正犯与共犯的真正标准是犯罪事实支配,只有对犯罪实施过程具有支配权的才是正犯,其他的都是共犯。最后,将下令者作为共谋共同正犯来处理也有扩张实行行为的缺陷,因为共谋本身并不会造成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其中,共同意思主体说有违反个人责任原则之嫌,间接正犯类似说则没有说明类似的基础。许多支持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学者,实际上也将犯罪事实支配权作为论证共谋行为成立共同正犯的基础。比如山口厚认为:“就共同者中的一人支配着其他的共同者的‘支配型’共谋共同正犯……是妥当的。”①[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6页。高桥则夫也指出:“是教唆犯、帮助犯抑或间接正犯,在结局上,必须依据是犯罪现象的中心形态还是周边形态这一基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犯罪事实的支配,特别是优越性支配的有无这一行为支配的见解基本上是有用的。”②[日]高桥则夫:《规范论与刑法解释论》,戴波、李世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2.对教唆犯说的批评。间接正犯原是从教唆犯中独立出来的一种犯罪类型。在古典犯罪论时代,共同犯罪的主流学说主张极端从属性说,在被教唆者具有责任排除事由时,教唆者无法成立教唆犯。在这种情况下,将教唆者认定为间接正犯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后来共犯理论采取了限制从属性说,只要被教唆者实施了不法行为就成立共犯。不过,间接正犯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保存下来了。这是因为,的确存在一些特殊状况,比如幕后的人基于强制或欺骗驱使他人实施犯罪行为,不适合将幕后主使的人按照教唆犯来处理。再如,幕后人掌控组织并通过组织发号施令,组织成员基于组织纪律或对组织的信赖执行该命令,由于幕后人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事件,将其作为间接正犯处理更为合适。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间接正犯与教唆犯之间的界限的确很微妙。
就严格答责说而言,教唆犯说对间接正犯说的批评主要有二:其一,就规范层面而言,既然在组织犯的场合,直接实行人作为自由负责之人能够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就不可能被支配。反过来说,既然直接实行人被幕后下令者所支配,他就不可能是自由负责之人,因为被支配即意味着不自由;其二,就事实层面而言,组织犯罪中的下令者不可能通过对组织本身的掌控支配直接实行人,因为在具体实施犯罪的时候,是否以及如何执行命令都由负责实行犯罪的组织成员自己决定,后者也并非随时可以替换之人。③参见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但这两个批评都有问题。对于前一个批评,幕后下令者所支配的是整个构成要件事实,实行人只是要素之一,下令者是基于对组织的掌控取得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并基于上述优势促进犯罪的具体实施。间接正犯与基于强制或欺骗而成立的间接正犯有所不同,前者既不影响直接实行人对犯罪事实的认识,也不影响其是否实行以及如何实行的自由意志。即便在强制支配或错误支配类型的案件中,利用人也很难“绝对”“支配”被利用人,后者仍有拒绝犯罪的空间。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支配”是说利用人的行为显著提高了被利用人犯罪的危险,而不是说被利用人完全丧失自由意志。就后一批评而言,其显然不符合社会经验事实。因为在组织中,下级服从上级是常识,即便上级的命令涉嫌违法,也不可能期待所有下级组织成员违抗命令。更何况很多时候,命令是否违法不能一眼看出;即便有所怀疑,也会因为上级具有权力、资讯等方面的优势而不能确定。在这些情形下,很难期待下级抗命不遵。退一步说,即便个别的组织成员拒绝实施下令者的命令,也不能证明组织支配理论本身缺乏说服力,只能说明在该案件中下令者缺乏组织支配力。
缓和答责性说虽然可以在强制支配的场合得出妥当的结论,但其并不能为该结论奠定妥当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被利用人对犯罪事实是否负责与利用人是否应承担间接正犯的责任无关。利用人承担间接正犯的责任,并不是因为被利用人被排除了罪责,而是由于利用人本身对构成要件的实现具有优势的支配地位。“由于藉由一般预防达到法益保护是刑法的核心思想,只要数人共同对于法益的完善处于关键地位,便可以得出不同正犯形式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每个人个别的负责性是依据他对法益的地位而决定,不须取决于他人的负责性是否被完全否定。”④LK12-Schünemann,§ 25 Rn. 65.由此可见,“间接正犯并不是对实行者的支配,而是对构成要件实现的支配。对构成要件实现的支配可以通过对实行者的支配而得以实现,例如利用儿童、精神病患者或者《刑法典》第35条意义上的被胁迫者的情形就是这样。但是,对实行者的支配却绝不是达到对构成要件实现之支配的唯一途径。”①[德]克劳斯·罗克辛:《关于组织支配的最新研讨》,赵晨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3.间接正犯说的优势。组织的内部结构决定了组织归责与个体归责的根本差异。探讨组织成员的刑事责任和义务分配,不能不考虑组织本身的特殊结构与功能。组织的内部结构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传统刑法归责模式适应相对简单的分工,“现代分工以及技术过程的复杂化,是与针对特定生活范围能够单独掌控、并应单独负责的自主性个人,所设计出来的刑事责任的概念并不相当。”②[德]许迺曼:《过失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捉襟见肘》,载许玉秀、陈志辉主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19页。一般来说,现代组织内部的分工包括纵向的垂直分工与横向的水平分工。水平分工主要关系到组织中不法集体决策的归责问题,此处不赘;③参见李波:《瑕疵产品生产与销售过程中不法集体决策的归因与归责》,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1期。垂直分工将组织分成不同的层级,层级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都有所不同。组织内部的成员可分为负责人和普通成员,前者又分为不同的级别,如经理、部门经理以及就某个工作任务或项目而言的直接负责人等。“在层级制的公司组织中——纵向分工——可以认为,公司管理者可以将一定的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义务授权给下级的职员。”④[德]洛塔尔·库伦:《公司产品生产中的注意义务违反责任》,徐凌波译,载于梁根林、[德]希尔根多夫主编:《刑法体系与客观归责》,江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垂直分工对组织中下令者的归责问题影响很大。由于组织内部严格的线性阶层构造,上级领导者与下属之间往往是“命令-服从”的权力关系,导致犯罪模式的复杂化。相比来说,个体归责是以相对独立的个体对法益造成损害为基础的,主体在犯罪意志或行为上都未受到组织的影响或加工,但在组织犯罪中,主体的犯罪意志或行为受到组织的加工,所造成的结果也非个体犯罪所能比拟。进言之,虽然实行者直接侵害法益,但他可能处于组织下层,其背后的命令者才是犯罪的起意者和策划者。上级领导者命令下级成员实施犯罪时,基于对组织运作的掌控,他能够控制整个犯罪计划,促使下属执行命令实施犯罪。基于对组织的支配,下令者对构成要件实现的掌控程度不亚于具体实行人:虽然相比于强制支配或错误支配,组织犯罪中的实行人具有更大的意志自由,但是下令者通过组织不法(对组织的掌控)弥补了上述不法空档;而在强制支配或错误支配中,利用人恰恰是通过强制或欺骗取得对行为人“无条件”的行为决意。可见,在意志支配类型中,被支配的对象并非完全失去意志自由,利用人只是或者通过强制、欺骗,或者通过对组织的掌控,提高了被利用人实施犯罪的危险。利用实行人的意志自由否定下令者的组织支配,是教唆犯说的致命缺陷。
其实,下令者之所以在具有组织支配时应成立间接正犯而非教唆犯,是因为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不同行为人的责任建立在其本人对被害法益所造成的损害基础之上。亦即在组织犯的场合,具体实行人与幕后下令者都造成了法益损害,只不过他们侵害法益的方式不同:实行人是通过直接的犯罪行为侵害被害者,下令者是通过对构成要件实现的支配而间接实施侵害。“每个人个别的负责性是依据他对法益的地位而决定,不须取决于他人负责性是否被完全排除”,所以,“对间接正犯而言,幕前之人的状态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取决于幕后之人对于构成要件实现的力量。”⑤LK12-Schünemann,§25 Rn. 65.
就像在上文提到的夏某与刘某滥用职权案中,被告人夏某与刘某之所以选择执行而不是违抗命令,主要是因为张某等人处于上级地位,为了政治前途着想,很难期待夏某与刘某会选择违抗命令。进言之,张某等人违法作出的“会议纪要”不仅引起了夏某和刘某的犯罪故意(教唆),而且基于其在组织中的上层地位,张某等人利用对组织的掌控确保了构成要件的实现,他们对于造成法益侵害结果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夏某和刘某,因此应成立滥用职权罪(间接正犯)而非无罪。换言之,张某等人之所以不成立普通的滥用职权,而是成立滥用职权罪,是因为他们明知违反法律,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是仍然出具了违法的“会议纪要”,并指令下级遵照执行。这就是张某等人实施滥用职权罪的实行行为,它与夏某刘某的直接实行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张某等人在国家权力组织中的地位以及手中的权力,利用了下级对上级的“命令-服从”关系,利用了上级在资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最终确保犯罪得以实施。
三、组织支配的成立要件
与教唆犯说、共同共犯说相比,间接正犯说更具合理性,为此奠定基础的是罗克辛的组织支配理论。不过,针对组织支配的成立条件,学者之间仍然存在激烈争论。比如,“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是否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要件?如何理解“直接实行人的可替代性”?如何理解“组织本身的法背离性”?
组织支配概念最初只有三个要件,亦即下令者具有命令权限、实行人具有可替代性、组织运作逸脱于法律之外(法背离性)。在“东德国防委员会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又提出一个要件——“利用实行人无条件的犯罪准备”。判决指出:“有一些场合,尽管中间行为人是完全答责地行为,幕后者的贡献却近乎是自动地导致了幕后者所追求的构成要件之实现。当幕后者利用了由组织结构所确定的框架条件时就是如此,在该组织结构中,他的行为贡献引发了符合规则的流程。……如果幕后者在行为时知道,他对直接行为人无条件地准备实现构成要件这一点加以了利用,而且幕后者希望将结果作为自己行为的结果,他就是间接正犯形式的行为人。”①[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最高法院判例集·刑法总论》,何庆仁、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在此影响下,2006年罗克辛增加“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作为组织支配的第四个要件。其含义在于,组织通过其特殊的影响力,驱使被命令的组织成员有意、积极并准备犯罪。问题是,“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在组织支配成立条件中是否有独立的必要?罗克辛后来改变了想法,转而认为“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只是从“组织逸脱于法律运作”以及“组织成员可替代性”这两个要件中导出的结论,而非下令者成立间接正犯的独立要件。相反,笔者认为“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应成为组织支配的独立要件。这是因为,无论是“组织中下令者权限”“组织本身的法背离性”还是“实行人的可代替性”,都取代不了“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的内容,下面详细论证,此处不赘。
(一)“组织中下令者具有命令权”
下令者的权限是组织支配的第一个要件。如果下令者不具有命令权,就不能掌控组织运作,也不可能有效地要求组织成员实现其犯罪意志。在“中断医疗案”中,医生与被害人的儿子共同决定中断被害人的生命维持装置,不过,在医生命令护士执行中断医疗装置的行为时,护士却通知了有关机构,导致两位被告人被公诉。②BGHSt 40,257,267 f.在本案中,正因为医生不是该医院的,护士才没听从他的指令,反而告知了有关机构。可见,只有具有命令权,下令者才能掌控组织的运作并通过组织掌控犯罪因果流程。事实上,下令者的命令权还可以降低组织成员的违法意识。“作为自然人的法人机关或从业成员,是作为组织体的手脚进行活动的,只要是作为企业业务活动的一环展开活动的话,其个人的犯罪意识便很淡薄。”③黎宏:《单位刑事责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其次,组织支配中的命令权不一定来自法律规定的权限,而是一种凭借等级森严的线性组织本身所获得的优势地位,以确保自己的命令得到执行。比如在犯罪组织中,上级头目的命令权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承认,但其命令在组织内部仍然能够藉由组织严厉的纪律确保得到执行。不过,并非所有居于优势地位者都能够成立组织支配,而是必须在组织之中。“如果一群犯罪人仅依靠个人的关系而相互联系在一起,那就不存在组织性的权力机构。所以,组织必须能够不受成员变化的影响而持续存在,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即组织中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准备投入使用的追随者。”④[德]克劳斯·罗克辛:《关于组织支配的最新研讨》,赵晨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只有在组织中,才会藉由层级的管理机制产生执行命令的动力,后者虽与针对生命、身体健康或自由的危害或威胁不同,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种潜在的压迫效果,但也能够确保犯罪因果流程的实现。
再次,组织支配是否仅限于命令的发布者?对此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罗克辛等)认为,组织支配的主体不仅包括命令发布者,也包括命令传达者;另一种意见(安博斯等)认为,组织支配的主体仅包括命令发布者,命令传达者至多只能对组织的部分流程有所掌控,因此无法藉由组织支配成立间接正犯。①Ambos,Der Allgemeine Teil des Völkerstrafrechts,2004,S. 604.笔者认为,组织支配的主体是否包括命令传达者,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其能否掌控犯罪因果流程。虽然一般来说,组织成员阶层越高权力越大,可供使用的资源越多,其对犯罪因果流程的操控就越强,但在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某个任务可能被拆解成数十道工序,单从这些工序本身很难分辨命令是否违法,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到达某个层级的上位者才能操控全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组织犯中,只有权力最高的人才能成立间接正犯,而是说只要掌控犯罪的因果流程,从下令者到具体执行者之间的命令传达者就可以成立组织支配。如果不具有对犯罪因果流程的支配,仅仅是传达命令并不能成立间接正犯。
最后,下令者下达命令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还是组织利益,并不重要。有人认为,如果下令者纯粹是利用组织结构满足个人私欲,行为欠缺组织认可,无法利用组织运作确保命令实行,只能成立教唆犯。②参见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笔者则认为,虽然一般来说命令在组织性质及下令者权限范围之内更容易得到执行,反言之,如果下达的命令既与组织目的无关,也不在组织活动范围内,则不容易得到执行,但是只要利用了组织本身的权力与运作,就足以成立组织支配。组织犯罪不同于单位犯罪,后者需要将单位利益作为犯罪目的,前者则不需要,只要形式上利用了组织运作,就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出组织犯罪的范围之外。事实上,在组织的掩盖之下,行为人的动机一般来说既难以辨认,也不影响命令的效果。
(二)“组织逸脱于法律运作”
在正式组织中,组织本身的性质不会因为下令者要求下级执行某个违法行为而变得违法,但既然如此,要求组织逸脱法律运作的意义何在?据罗克辛介绍,“这一概念远远超出了个别犯罪的可罚性的范围。因为它使得直接实施犯罪行为者无需担心自己将承担刑事责任,从而确保了犯罪行为得以顺利地实施。”③[德]克劳斯·罗克辛:《论利用有组织的权力机构建立的犯罪支配》,徐凌波译,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可见,要求组织逸脱于法律运作,目的在于标明命令行为的可罚性。关于本要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明确。首先,“组织逸脱于法律运作”中的“法律”是指什么法?显然,既然认定组织支配的下令者构成间接正犯,所依据的法律就必然是现行刑法。其次,什么是“组织逸脱于法律运作”?组织逸脱于法律运作,是指组织整体上逸脱出法律运作,还是在某种限度之内即可?罗克辛早期的回答是,组织必须整体上逸脱于法律运作方可成立组织支配。这一点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比如在国家权力组织中,即便某个官员命令下级组织成员实施了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也不能说这个国家机构整体就违反了法律。正如赫兹伯格所言,组织支配中组织逸脱于法律运作,仅限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部分。组织整体上逸脱法律运作仅限于犯罪组织中,在正式组织中无疑是不可能的。因此,“非国家性组织(例如恐怖主义运动,发生在族群纷争中的种族屠杀以及黑手党等)的活动处于法秩序的范围之外,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国家性的体系犯罪来说,这一标准只要求组织中具有刑法意义的那部分活动脱离了法秩序。”④[德]克劳斯·罗克辛:《关于组织支配的最新研讨》,赵晨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三)“实行人具有可替代性”
在组织支配的成立要件中,“实行人的可替代性”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批评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其一,罗克辛设计这个要件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下令者对犯罪因果流程的支配,实行人越具有可替代性,其本人的意志自由在犯罪实行过程中就越微不足道,下令者对犯罪因果流程的支配也就越有力。但是,组织支配都是现实的支配,用实行人的可替代性(即假设的第三人执行任务的可能性)来论证下令者对犯罪事实的支配,是利用了假定因果关系的论证法。①Renzikowski,Restriktiver Täterbegriff und fahrlässige Beteiligung,S. 89 ;Herzberg,in :Amelung(Hrsg),Individuelle Verantwortung,2000,S. 49 ff.其二,“执行者的可替代性只有在非专业人士、无执行时间压力以及有再现性的犯罪情境中才会存在。”②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比如,在具体案件中,对于一些技术水平要求特别高的专家来说,其可替代性就成问题。而在具体案件中,比如“东德国防委员会案”中,执行射杀任务的士兵在案发期间都是特定的,很难说具有可替代性。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基本的见解:具体的可替代性说与抽象的可替代性说。具体的可替代性是指在案件发生的具体场合,实行人具有可替代性,存在其他可执行任务的人员;“抽象的执行者可替代性是一种组织能力或倾向,亦即组织有能力将个别执行者视为纯粹功能要素,个别执行者对整体事件欠缺影响力。”③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
笔者认为,这两个质疑都没有道理。实行人可替代性要件是从实行人反抗命令的可能性这一角度来论证下令者对犯罪因果流程是否具有支配的一个要件。在下令者只有一个组织成员可以命令的时候,后者一旦拒绝,下令者的意图即归于失败,这时候下令者对犯罪因果流程的支配比较弱,依赖于特定的实行人的服从。如果下令者具有许多组织成员可供选择,即如果A不服从命令,还有B、C、D……等可供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实行人的反抗对于下令者命令的实现只具有微弱的影响,而不具有决定作用。这里所描述的不是假定因果关系,而是命令对象的可选择性。可选择性越大,下令者实现命令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不是一种假定,而是事实。“掌控权力机器等于间接掌控了该机器中所有可替代的执行者,是以每位执行者都是现实地处于机器掌控者的支配地位下,其服从掌控者的指示与组织的规范,并非脱离机器掌控者支配力之外而假设性存在的第三人。”④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因此,对实行人的可替代性而言,只需要抽象的可替代性就够了。具体的可替代性说仍然着眼于幕后的下令者对于直接实行人的个人支配,而实行人可替代性是用来描述下令者支配组织的强度,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实行人。换言之,实行人可替代性是组织支配的成立条件,而不是个人支配的要件。正因为实行人具有可替代性,实行人会认为“即使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以此降低执行命令的精神压力,下令者的命令才具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在某些个案中,实行人可能确实不具有可替代性,但这并不能证明实行人可替代性要件本身有问题,而是说在这种状况下,下令者缺乏对犯罪因果流程的支配,只能论以教唆犯而非间接正犯。这其实是适用实行人可替代性要件的结果,而非对它的否定。⑤[德]克劳斯·罗克辛:《关于组织支配的最新研讨》,赵晨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页。
(四)“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
“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是罗克辛在施罗德(Schröder)批评下增加的一个要件,意在说明实行人的犯罪倾向通过组织特殊的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由于组织运作在下令者的掌控之下,追究下令者的责任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与施罗德“利用实行人无条件的犯罪决意”的意义并不相同。利用实行人无条件的行为决意,是通过实行人的行为决意限缩组织支配的范围;而具有无条件的行为决意标志着实行人积极实施犯罪行为,下令者在这种状况下支配实行人,无疑就拥有对犯罪结果的支配地位。“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不是强调实行人的行为决意,而是强调组织本身特殊的影响力,正是后者让下令者拥有对犯罪因果流程的支配力。⑥参见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换言之,在具体案件中,直接实行人不一定都是积极实施犯罪行为,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可能比较积极,有的人可能是惧怕不执行的后果,强调实行人的行为决意会大幅度限制组织支配的适用范围,在实行人不具有无条件行为决意的状况下,认定下令者为教唆犯而非间接正犯。实际上,施罗德也是着眼于下令者对实行人本身的支配来确定组织支配的成立范围,但他没有看到组织支配实际上强调的是下令者通过对组织的支配间接地支配实行人,这才是组织支配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支配最重要的差异所在。
有些学者(包括罗克辛)认为,“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是从“组织法背离性”与“实行人可替代性”这两个要件推导出来的结论,而非组织支配独立的成立要件。比如安博斯认为,将执行者得到明显升高的犯罪倾向列为一个独立的标准,“与组织支配的一贯理解——即犯罪支配是把组织当作工具来加以操纵,从而确保结果的实现——不相一致,它把关注点从组织转到了——至多是间接受到操控的——犯罪实行者身上”。①[德]克劳斯·罗克辛:《关于组织支配的最新研讨》,赵晨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页。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从“组织的法背离性”与“实行人可替代性”这两个要件中实际上推不出“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组织的法背离性”强调命令的违法性,而非组织本身对执行人实行意志的提升;“实行人可替代性”虽然强调下令者支配犯罪因果流程的力度,但其着眼于实行人的反抗可能性,而非组织本身的影响力。相反,“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着眼于组织本身的特性如线性的组织结构、严厉的组织纪律等,通过这些要素提升实行人的行为意志,其与前两个要件具有不同的旨趣。
四、对反对意见的反驳
罗克辛提出通过组织支配理论论证组织犯罪中的下令者成立间接正犯这一构想之后,在1994年“东德国防委员会案”中被采纳。之后组织支配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但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批评意见。不仅如此,就目前来看,虽然主流学说认为组织犯中的下令者构成间接正犯,但不同学说的理由并不相同。
(一)四种反对意见
1.实行人决意说。1965年,施罗德发表《正犯后的正犯》一文,对罗克辛的组织支配理论提出批评:一方面,在组织犯罪中,实行人不一定具有可代替性,比如在有关毒气专家或文书伪造的案件中,实行人通常不可替换;另一方面,实行人是否可以替代,对成立组织支配并不重要,对组织支配的成立中最重要的是幕后人对直接实行人无条件的犯罪决意的利用。施罗德的观点来自对“多纳(Dohna)案”的观察。在本案中,F得知某秘密组织派杀手S预备在某时某地暗杀他。为了摆脱追杀,也为了除掉其仇人L,F想出了一个妙计:在预备的暗杀时间,F将L引到暗杀地点,前来杀F的S将L误认为是F,开枪将其杀死。施罗德认为,组织犯罪中的实行人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他的行为决意在犯罪前就已经形成。下令者利用组织成员的这种状态实施犯罪,不应成立教唆犯,因为被教唆人在犯罪之前不具有犯罪的行为决意,其行为决意是教唆犯所引起的。②Schroeder,Der Täter hinter dem Täter,S. 143 ff.,152,158,167 f.
2.强制支配说。有学者认为,在对组织犯中的下令者归责时,不需要援引组织支配的概念,通过强制支配概念也可以论证间接正犯的成立。在“东德国防委员会案”中,作为前东德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被告人通过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命令边境守卫士兵以“任何手段”阻止任何越境逃离前东德的行为,7个被害人在逾越两德边界逃离前东德时被杀害。联邦最高法院借助于组织支配以及利用实行人无条件的行为决意,认定下令者成立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德国学者舒尔茨(Schulz)认为,其实借助于强制支配概念,就可以证明下令者成立间接正犯。理由是,士兵身处严格的阶级式建构、采行军事化管理及指令原则的组织中,被灌输正统的政治理念,他们不但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合乎国家规范秩序,甚至会认为,若其反抗,会遭受职业及社会上的降级及贬低,甚至刑事制裁等生活上的不利益。由于这种心理压力与德国刑法第35条的要求相似,下令者应成立间接正犯。③Schulz,Die Mittelbare Täterschaft kraft Organisationsherrschaft-eine notwendige Rechtsfortbildung? -BGH,NJW 1994,2703,in:JuS 1997. S. 109 ff.
3.答责性补强说。德国学者霍耶(Hoyer)认为,下令者之所以成立间接正犯,是因为直接实行人答责性的降低,补强了下令者的责任所致。实行人答责性的降低是由于下令者滥用权力所引起的,因为在权力组织中,下级具有服从上级命令的规则。服从规则的内部拘束力,在合法组织中由法律与传统规则所保障,在犯罪组织中则由暴力所维系。虽然组织成员实施犯罪行为是基于服从规则,但在外部法律关系上,其仍然属于违法而有责之人,承担独立的刑事责任。不过,由于实施犯罪行为的命令是下令者所发布的,实行人的答责性由于服从规则的内部拘束力而有所降低,所降低的答责性转由下令者负责。也就是说,服从命令的内部拘束力无法正当化组织成员实施犯罪的行为,但是仍然降低了他的责任,因为服从规则导致成员本身“不自由”。霍耶认为,就实行人答责性降低的部分,下令者应成立间接正犯;就实行人实际答责的部分,下令者成立教唆犯。①Hoyer,in :Amelung(Hrsg),Individuelle Verantwortung,2000,S. 191.
4.社会支配说。德国学者戈洛普(Gropp)认为,组织犯罪中的下令者之所以能够成立间接正犯,是因为其能够操控犯罪因果流程,而其之所以能够操控犯罪因果流程,则是基于社会支配。关于社会支配概念的内涵及其与组织支配之间的区别,戈洛普没有交代太多。不过,戈洛普的学生施罗塞尔(Schlösser)对社会支配的概念进行了具体化,他认为社会支配是一种权力关系,处于上位的人员具有权威,其对居于从属关系的下位者发布命令。施罗塞尔强调,这种权力关系并非一定发生在权力组织之中,也会发生在一般社会关系中。可见,社会支配与组织支配有所区分。但他也认为,组织的规模及持续性对支配关系有重要影响,组织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长,下位者对组织规范越难持以批判态度;命令必须属于组织的权限范围,如此更容易得到执行;行动对组织来说越典型,越符合组织的价值理念,组织成员就越难发现其违法性,也就越容易成立社会支配;居于下位的行为人对自身的可替代性感知越深,上位者的命令就更容易得到执行。②Schlösser,Soziale Tatherrschaft,S. 290.
(二)对上述意见的反驳
1.实行人决意说的问题。利用实行人无条件的行为决意说具有下列问题。首先,这种观点无法适当区分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利用直接实行人无条件的犯罪预备,正属于《德国刑法典》第30条第2款所称的“接受他人犯罪请求”,这是典型的教唆犯。③《德国刑法典》第30条第2款规定:“(已经宣布、接受他人的请求或已经与他人约定)去实施重罪或者教唆他人实施重罪的,同样应当被惩罚。”其次,这种观点难以适用于合法的权力组织或经济组织。在后两种组织之中,成员通常不会在行为前就形成无条件的行为决意。再次,这种观点只能解释部分案件。在实行人事前不具有行为决意的案件中,只要下令者基于对组织运作的支配掌控了犯罪的因果流程,也应该成立间接正犯而非教唆犯。究其根本,间接正犯成立的基础是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支配,而非对实行人的支配。施罗德的观点仍然建构在行为人对实行人的支配上,其通过掌控实行人的意志确保下令者的支配,由此排除教唆犯的成立。最后,将行为人能否成立间接正犯建立在实行人主观的行为决意上并不稳固:一方面,行为人很难判断实行人的行为决意是否坚定;另一方面,在很多案例中,实行人在实施犯罪时都处于恐惧和不情愿的状态,称不上“无条件的犯罪准备”,但也不会妨碍行为人成立间接正犯。
2.强制支配说的问题。强制支配说得到一些权威学者的支持,如前所述,张明楷教授就认为可将组织犯置于强制支配的类型中。但是,强制支配说的标准并不明确,其中的心理压力与德国刑法第35条“相似”需要进一步明确化。其次,如果要求实行人的心理压力达到德国刑法第35条(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的要求才认定下令者为间接正犯,就会过分限制后者的成立范围,因为除非在等级森严处罚严厉的犯罪组织中,一般国家权力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成员都不会达到这种心理压力的水平。事实上,很多犯罪组织都是通过灌输特定意识形态,通过信仰使其成员甘为所用。在这样的状况下,下令者命令组织成员实施犯罪行为,也难以排除间接正犯的成立。再次,如果将强制支配扩大适用于被强制者未排除答责性的情形,不仅难以区分间接正犯与教唆犯,还会造成区分上的恣意。④Roxin,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8,S. 685.实际上,这种做法通过降低强制支配成立的标准,将本不属于强制支配的组织犯纳入其中,虽然在结论上符合处罚组织犯的要求,但仍存在扩张适用的风险。
3.答责性补强说的问题。答责性补强说也将下令者的归责建立在其对实行人的个体支配基础上,下令者成立间接正犯是其教唆行为经由实行人答责性补强的结果。首先,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下令者的责任实际上是建立在其本人对法益的行为与态度基础上,而不是从属于其他人。其次,霍耶只交代了实行人答责性降低的原因,却没有进一步交代服从命令规则降低答责性的缘由。服从命令何以能影响归责,何以能影响定罪,原因并不清楚。再次,既然霍耶认为实行人答责性的降低是由于下令者滥用权力所引起的,下令者成立间接正犯的理由就应该是其本人滥用权力的行为与态度,而不是他人答责性的降低转致。最后,“幕后之人若仅就幕前之人负责性‘缺陷部分’负责,该缺陷部分无论如何必定小于幕前之人‘剩余的负责’部分,幕后之人相较于幕前之人岂不因此负较低之责任?”①参见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显然,这种做法与论者将幕后下令者作为间接正犯处罚的结论自相矛盾。
4.社会支配说的问题。首先,社会支配很难与组织支配相区分,组织支配的许多特征同样适用于社会支配。社会支配本身并不具有优越于组织支配的特色,将支配关系从组织内部扩展到社会一般关系上,反而不利于说明组织犯的归责形式。其次,施罗塞尔认为,下令者的犯罪支配不仅仅是建立在其对组织框架的掌控上,还必须藉由其在组织中优势地位上衍生出来的社会支配力,实现其对组织成员的支配。这种社会支配力,标志着一种有关自由的位差关系。基于其观点的社会性质,施罗塞尔没有通过法律判断这种自由位差关系对下令者与实行者归责的影响,而是仍然在一般社会关系层面上讨论。问题是,“将自由视为一种社会事实并脱离法律上对自由的判断,无疑地会导致社会支配的认定困难。”最后,“由于社会犯罪支配这种深具‘描述性’的概念特色,采取社会犯罪支配理论者无疑地可能过度扩张社会犯罪支配的适用范围,因为社会支配的关键在于组织中是否采行阶级结构及衍生而来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还有该权力关系所引发的社会从属地位,但许多的社会组织中皆有此种社会权力支配的现象存在。”②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
需注意的是,组织支配是一种事实概念还是规范概念?“支配”是犯罪事实支配概念的“缩写”,很容易被误解。赫兹伯格批评组织支配概念“混杂了自然主义和规范主义的观点”。特拉克(Radtke)则批评,罗克辛的组织支配概念就是一种事实(自然)概念,站在这种观点上考察下令者与直接实行人之间的支配关系,由于实行人永远有放弃执行命令的自主决定空间,下令者也就不可能实现对实行人的支配。特拉克认为,应放弃事实的支配概念,支持规范的支配概念。因为下令者是操控犯罪因果流程之人,在规范上应将实行人因执行命令所引发的法益侵害结果归责给他。③参见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笔者认为,主张组织支配属于规范概念无疑是正确的。组织支配不可能是纯事实的,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是否保有支配,最终要在规范保护目的之下进行规范判断。罗克辛指出:“犯罪事实支配说从实质意义上的构成要件之实现来理解正犯。”④[德]克罗斯·罗克辛:《正犯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劳东燕等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这里的“事实支配”不是纯事实的支配,而是要在构成要件实现的意义上进行实质判断,不可能不考虑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但是认为组织支配是纯规范的概念,同样也不正确。组织支配都是现实的支配,如果不考虑事实上的差别,就不可能清晰地区分强制支配、错误支配与组织支配。“尤其当事实上的支配关系无法对下令者论以间接正犯时,透过不清晰的规范负责性分配就能使下令者由教唆犯一跃成为间接正犯,此时,规范负责性或规范观点不过沦为权宜之计。”⑤冯圣晏:《犯罪之组织支配》,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10年度硕士论文。总之,理解组织支配要从存在与规范两个层面来进行,具体判断时既要考虑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也要考虑具体的犯罪因果流程,只有在前者指引下分析和评价后者,才会得出妥当结论。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形势的严峻化,组织犯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特别是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齐抓共管,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预防和解决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突出问题。虽然我国刑法很早就规定了组织犯,但是传统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一直没有认识到组织归责的特殊之处,导致一系列疑难问题。①参见王俊平:《论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归责根据》,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 5期。组织支配理论看到组织本身在犯罪因果流程中的特殊影响力,认识到组织归责与个体归责之间的根本差异,揭示了组织犯的本质。组织归责与个体归责的差异,建立在组织结构的特殊影响力上。在组织犯的归责形式上,间接正犯说具有合理性。这是因为,组织中的下令者通过组织运作控制了整个犯罪因果流程,由此奠定了其间接正犯地位。组织中下令者的权限、组织逸脱法律运作、实行人的可替代性以及组织特殊的犯罪准备,是组织支配必备的四大要件。其中,实行人可替代性是从实行人的角度论证下令者对犯罪事实的掌控,其余三个要件都是从下令者的角度论证其对组织的掌控,提高了实行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在反对组织支配理论的诸学说中,实行人决意说、强制支配说、社会支配说、答责性补强说都有严重的理论缺陷,不值得予以支持。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探讨组织支配理论的适用范围。根据组织的不同性质,刑法上通常将组织分为国家权力组织、犯罪组织与经济组织三种基本类型。基于其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关系和严厉的处罚措施,将组织支配理论适用于国家权力组织与犯罪组织是妥当的。但组织支配能否适用于合法的经济组织,尚有争议。笔者认为,经济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具有不稳定性,不能够一概而论。除了国家权力组织与犯罪组织,其他组织要视组织本身的强制力和控制力来决定是否具有“凭借有组织的国家机关的意志控制”的组织特征。②参见尹子文、徐久生:《行为控制理论下“正犯后正犯”的边界归属》,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 6期。可见,无论在何种组织中,是否符合组织支配的成立要件是判断组织犯成立与否的基本标准。除此之外,组织支配需要达成何种程度,组织支配是行为支配、结果支配还是两者兼有,以及组织不法与个人不法的区分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