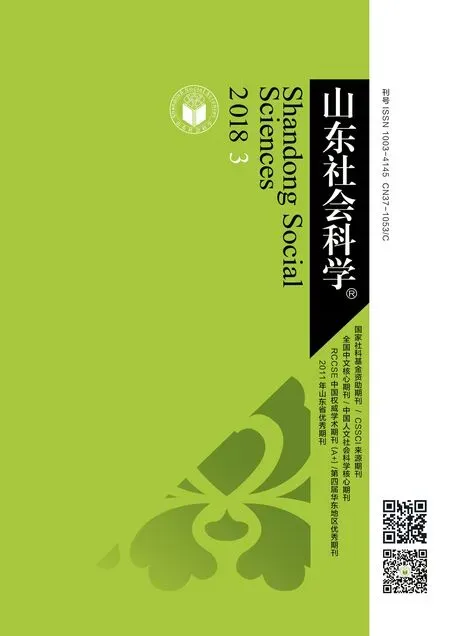政治动物与社会动物的分殊: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与回归
郭奕鹏
(东莞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表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龃龉意味着政治生活并非人们真实生活的表达,因此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必然要转到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上。而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与其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不如说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动物以劳动为基本特征,所以,社会动物又是指劳动的动物。这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动物从不劳作的判断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比政治国家更为本真的领域:社会。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是共同体内在的目的。如此看来,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似乎站在对立的两端。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古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话,两者似乎又分享着很多共同的前提。那么,该如何理解政治哲学传统中古今两位重要思想家对人性和政治基本判断的差异呢?本文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一、由政治动物转向社会动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动物”论的回应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批判“鲁滨逊”孤立的个人时,回应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在后来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又重提这个命题:“……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紧接着这一段话,马克思加了一个注释,在注释中他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注释13。(上述引文黑色字体为笔者所强调)
在希腊,只有自由民才可以称为真正的公民(市民)。人的地位由他的出身所决定,“人生人,兽生兽,所以善良者出于善良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意味着奴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他只是主人的活的工具。政治动物就是成为城邦的公民(城市的市民),所以,马克思才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实为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
但是,马克思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即使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呢?为什么他要将政治动物与社会动物区分开呢?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的”(political)等同于“群体的”或“社会的”,“政治动物”亦可译作“社会动物”*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所以,政治动物与社会动物是合一的,而马克思为何在此要强调两者的差别?
让我们先看看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分析。在《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些动物兼涉两种生活,有的群居,有的散居。*《亚里士多德全集》第4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其中“群居”一词,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希腊文的politika,罗斯的英文译本译为social。在《政治学》的一段话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和蜜蜂以及所有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单行本),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罗斯英文译本为:Now, that man is more of a political animal than bees or any other gregarious animals is evident。在其它英译本中,political animal仍译作social animal。实际上,这两个词都对应亚里士多德希腊文politika。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的”与“社会的”用的都是同一个词politika。如果按照现代的说法,politika兼具政治的、社会的和群居的三种用法。人比起蜜蜂等社会(群居)动物,之所以更是社会(政治)动物,在于人是惟一拥有logos(语言)的动物,动物仅能通过声音表达苦乐,而人明辨善恶,能通过语言表达利弊和正义与不正义。动物的“社会”(politika)性基于生存的本能,而“人的政治性(politika-引者加),不仅意味着人能像蜜蜂和蚂蚁这些所谓的‘政治性动物’一样,通过群居完成某种共同的活动,而且在于通过统治关系的建立来分享好的生活”*李猛:《在自然与历史之间:“自然状态”与现代政治理解的历史化》,《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换言之,人的社会性是高于动物的社会性,但就人自身而言,政治的亦即社会的,两者具有同等的含义。
对于马克思回应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的意义,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麦卡锡先生认为,马克思非常重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它“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尤其表现于马克思对人类本质和自由问题的思考”*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社会是人存在的先行规定,是理性和人性本身的要求。人与社会的存在关系指向了善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是为了保障人的安全与财产而创造出来的功利附属物。马克思虽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注社会和经济领域,但是他的终极目标与古典时代人的政治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和谐平衡的理想是一致的。当人从各种虚假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后,人将成为自身制度的创建者,并且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将充分实现自身的潜能。*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与麦卡锡不同,马格里斯认为马克思仅是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这一命题。但他们的共享的主题几乎不能澄清马克思理论的独特性,最多只能说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某些概念的提出起到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仅仅是基于批判十八世纪流行的孤立的“鲁滨逊”的角度才回归到人的社会性存在这一命题,但这里的联系是表面的,“寻找任何其它更进一步的联结都会完全误入歧途”*Joseph Margolis, “Praxis and Meaning:Marx's Species Being and Aristotle's Political Animal”, Geroge E.McCarthy eds., 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y-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p331.。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在于,实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要与人的先天本质一致,“人的实践必须(尽可能)符合先天理论的决定性真理。因而,只有当实践将其可变的、特殊的东西纳入其理论科学(有关人的本质的不变之物)的首要控制之下,实践活动才会是理性的”*Joseph Margolis, Praxis and Meaning,p334.。而马克思则坚持认为理论与实践活动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所谓人类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实践的结果,“人的本质由于无非是其‘生命活动’的对象,因而是可以改变的”*Joseph Margolis, Praxis and Meaning,p334.。对马克思而言,现实的世界是外在性的,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因而是其实践的产物,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一主题最终是不融贯的。
要言之,马格里斯一个基本的看法是,人的本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被先天设定好,实践只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来的开放动态的过程。考虑到亚里士多德思想中自然目的论的基本底色,马格里斯的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关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这一特点,可参见聂敏里:《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卷研究(Z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代序,第11-26页;维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目的论》,载聂敏里编译:《20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312页。但是,这是否是最关键的区别呢?或者说,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呢?王尔德就认为,在人的本质方面,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两者都没有简单运用事实的语言定义人的本质,“而是暗示它应该被完成。人的本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既定的完成, 被马克思用史诗般的语言构想为持续而漫长的阶级斗争旅程的终点”*王尔德:《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 希腊的维度》,《世界哲学》2005年第 5期。。
该如何理解这些彼此冲突的观点呢?我们还是看看马克思自身的看法。
二、政治动物与社会动物的分殊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有一个精炼的总结,他指出:“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构成国家的内容,并不包括其他的领域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古代社会是国家—家庭的二元结构,家庭的事务不属于国家的内容,因此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现代社会则不同,它建基在国家—市民社会—家庭的三重结构中。非政治国家的内容——其核心为市民社会的生活——在国家生活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政治国家必须与这一非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相适应。所以,政治动物在现代国家不仅有政治的含义,还包括其它非政治的含义。这也正是南希(Nancy)认为马克思对政治动物有更广的理解的原因所在。*Nancy L. Schwartz,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Marx on the Zōon Politikon, Political Theory, Vol. 7, No. 2 (May, 1979),p246.换言之,马克思所理解的政治动物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二是社会的动物,并且后者是最主要的含义。与政治动物相比,社会的动物更为首要。
政治动物与社会动物的差异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古代,国家就是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以达到人类至善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社会”*萨孟武:《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第六版,第44页。。台湾学者萨孟武先生(此君1946-1948年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指出,在黑格尔以前,学者多不知国家与社会的区别,以为国家只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即社会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变成国家。黑格尔知道国家与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国家不是社会,也不是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时变化而成的形相。*萨孟武:《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第六版,第248页。国家高于社会,是社会必然要发展的方向。因为“家庭注重道德,而偏少法律,是为正;社会注重法律,而偏少道德,是为反……惟在国家,一方使各人能够实践其道德生活;同时由于法律,又使各人的道德生活能与共同利益一致。即道德与法律合一而实现,此为合”*萨孟武:《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第六版,第249页。。
通过对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社会内在目的的思想,而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继承。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不仅不是社会的内在目的,而且国家是社会的寄生体,历史的发展将会把国家的权力还给社会。在写于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把社会与国家明确地对立起来:“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黑色字体为笔者所加)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社会”是与国家、政府权力相对立的概念。换言之,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看来,“国家”依靠社会的供养,但却阻碍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却又不发挥合理的职能,因此应当将其交给对社会负责的公仆掌握。
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充分表明,社会比国家更本真。用恩格斯后来的话就是:“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国家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统治工具。当阶级对立消失后,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代替国家,国家将被放到博物馆里去。所以,马克思关注社会远甚于关注国家,当最后的阶级斗争打响的时候,国家将消亡。*[美]艾莉森·布朗:《黑格尔》,彭俊平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4页。这一点正是布朗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重大区别。国家是充分发达的政治手段,社会是充分发达的经济手段。在自由市民团体那里,将无国家而只有社会。
那么,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是什么呢?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认为社会实质就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生产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交换和消费阶段,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表现形式。
如此一来,社会动物与政治动物最重要的区别表现为什么呢?不少论者将劳动作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出发点,劳动作为人的“类存在”的主要特征,将人与自然世界区别开。*Lobkowicz, Nikolaus, eds.,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p55.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动物在某种意义上是指人是一种劳动的动物。
劳动是人本质力量的象征,是人的实践活动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虽然劳动最开始表现为满足人的需要,但这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劳动的生产在人身上发生两种关系: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自然关系表现人与物的连接,而社会关系则指人的合作关系。要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必须弄清人类劳动的意义。
首先,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本质性活动。即便人的劳动显得非常笨拙,但也远远超出动物。面对蜜蜂精巧的建筑本领,许多建筑师可能会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胜于最灵巧的蜜蜂的地方在于建筑师一开始就将劳动的目的和结果在头脑中观念性地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劳动的目的性反映了人的创造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觉思维、人的意志性充分展现出来:“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通过劳动,人们在改变外在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他自身的自然。而正是通过人类这一特殊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才展示出来。所以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批评了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短视,批评他无法看到人类历史变迁的动力。因为正是人类的感性活动,创造了丰硕的历史成果。感性世界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劳动中日益丰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其次,劳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离开人类的生产劳动来谈论历史是荒谬和无知的。人类的历史都必须依靠于前人留下的东西,“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所以,所谓的历史目的论完全是思辨的抽象、哲学后思的结果。据此,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地颠倒历史,将历史视为“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的特殊目的,用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抽象词语代替历史的现实活动。事实上,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是在人类劳动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但是,人类这一创造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异化劳动。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这种劳动称为“手段性”、“瘟疫”般的活动:“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1页。
本来是一种目的性的劳动现在成为工具性的劳动,本来是创造性的活动现在成为了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性原本在于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现在这种活动却成为人类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把动物的东西变成人的东西,而把人的东西却变成动物的东西。它产生的是人与动物彻底颠倒的世界。
当然,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并非马克思的独特贡献。早在《第一体系》(写于1804)中,黑格尔就分析了屈从机器对人造成的影响,“劳动越是变得机械化,它的价值就越小,个人的辛苦就越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的价值按照同样的的比率降低……个人的能力受到巨大的限制,而工厂工人的意识,也被降低到最愚纯的程度”*转引自[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的这些著作直到二十世纪才发表,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阅读过黑格尔这部分早期著作,虽然他从《精神现象学》对劳动意识的论述中获得自己的灵感。*马克思与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关系,还可参见[美]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第193-253页。
黑格尔把这种劳动称之为“否定性的劳动”。“劳动,因为它是辛苦的;否定,因为它是破坏性的。人的这种模式,即痛苦地在各个阶段走向自我意识的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黑格尔所构想的更为宏大的人类历史运动。”*[英]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这种劳动如“一头疯狂的野兽”撕咬人的心灵。
但是与黑格尔只看到异化劳动的消极作用不同,马克思在这种异化劳动中看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采取了手术的方式:他将黑格尔主义的劳动概念从对客观精神的封闭中分离出来,并将劳动置于经济生产实践的社会语境中。”*[美]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人类不是抛弃异化劳动,而是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解放。马克思对劳动的重视离不开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关于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的影响,可参阅〔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这两次革命把传统上视为最卑贱的人类活动提升到创造力的最高级,并认为能够在闻所未闻的普遍平等状况下实现古老的自由理想。基于此,阿伦特才得出结论,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与古典政治思想最关键性的差别。*[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三、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与回归
按照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观点,人的政治性与人的劳动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人由于积极参与了政治,才获得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得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而那些从事最卑贱劳动的奴隶,则从政治领域被排除出去,这些奴隶“只是单纯的劳动者,不过从事提供生物学上必要东西的活动,被强制隶属于‘自然的物质代谢’”*[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另一方面,这种卑贱的劳作,“是没有言语交流、不进行相互对话地被组织到这样的共同体里”*[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所以,奴隶不用也不需通过言语来表达善恶,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人定义为拥有logos(语言与思想)的动物,也正是由于政治生活离不开语言与交流。政治动物的定义表明,“几乎不涉足政治的、不参与政治的奴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不是人”*[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而只有摆脱了劳动之苦,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市民,才是真正意义的人。
马克思的判断与此恰恰相反:社会动物(本质是劳动动物)表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本质性的创造活动。如果说人应该力图使自己的活动符合自身本质,那么不事生产,靠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而生存的人,显然不是真正意义的人。所以阿伦特指出,依据马克思的逻辑必然可以得出:“几乎不参加生产资料的生产,只依赖从事替代取得食物的其他劳动生活的人,是寄生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人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正是在劳动中,与人相对的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现实,人才把自然界变成他无机的身体。“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因此,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拥有logos(语言与思想),而在于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如此看来,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在人性的判断上,站在对立的两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成就人的本性,劳动属于非人的奴隶的活动。而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国家是人类社会的异化,它败坏人的本性,而劳动创造了人。当然这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却又颇具一致性,勿宁说,两者都代表对人类本质活动探讨的起点与终点。阿伦特可谓独具慧眼,她指出:“分别作为起点与终点,所谓人是政治(polis)动物的定义,与所谓人是劳动动物的定义,属于同一传统。两者许多要点是对立的,有些要点还是完全相反的。即使如此,两者的思考都在同一条线上,在回答同样的问题,密切地相互呼应。作为起点与终点的两者都涉及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或社会生活、思想的几乎全部领域。进一步普遍地说起来,这些领域中建构起西欧人生存的世界,这些领域在我们之中,是我们全体共同拥有的领域。我们传统所理解的、公众关心的共同的事务世界,就是政治与劳动的世界,从只有‘政治动物’居住开始,至只有‘劳动动物’居住而告终。于是,通过诸多的阐释,最基本的生物欲求的满足、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的与‘政治’无关的事物全都没进入公共领域。”*[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换言之,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实际仍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两者都致力于发掘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生活赋予了人现实性,远离城邦之人,要么是超人,要么是鄙夫——这种人是最卑贱的。城邦与人性乃至神性的实现密不可分。只有成为一个城邦的公民(亦即马克思所认为的定义:城市的市民),才能与动物区别开。所以,人“和蜜蜂以及所有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而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与动物一样都靠自然界生活,但是人比动物更具普遍性。自然界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成为人无机的身体,成为人自由自觉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动物与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它只片面地生产满足自己和后代肉体所需的东西,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他能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并且按照任何一种尺度和美的规律来生产。他不仅生产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还生产着满足精神世界需要的东西。所以,尽管可以根据其它标准来区别人与动物,但生产劳动这一特征才是本质性的,语言、观念、意识都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语言、思想、艺术、宗教,这些使人异于动物的内容,都是在人的物质活动与交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完善起来的。因此,与其说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产生冲突,不如说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发现了比人的政治活动更为本真的行为,并将对劳动的传统偏见翻转过来,发掘出人类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更隐密的根基。
进一步说,马克思基于历史辩证法看待劳动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诚然,人类的历史发展与劳动的创造须臾不离,但人类的劳动决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自由选择的。早期的马克思还沉浸在费尔巴哈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把劳动看作自由自觉的美学式的劳动,并将其看作人的类本质。随着理论批判的深入,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痛苦、乏味、自我折磨的劳动在人类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无法避免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
现实的个人处于活生生的历史当中,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前面历史遗留的传统与现有的物质条件。当人们自以为在演出一场新的历史活剧时,实际上是穿着过往的服装在表演。蒲鲁东正是无法看清这一点,未能从现代制度的历史来源理解现代社会制度,所以无法解释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于是用毫无价值的普遍理性假设和一些神秘的原因来解释历史,这当然是最容易的,但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所以,问题不在于用浪漫主义的词句嘟囔几句,而在于找寻一条通往实现这种自由自觉活动的途径。但是决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放弃了早期的理想,甚至制造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说马克思将其认定的人的本质推延到未来的社会来实现。在此意义上,马格里斯认为,说马克思没有一个固定的人类的本质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王尔德的说法恰当反映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在此点上的共同之处:“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马克思并未简单地运用事实性语言来定义人的本质,而是暗示它应该被完成。人的本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既定的完成,被马克思用史诗般的语言构想为持续而漫长的阶级斗争旅程的终点。”*王尔德:《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世界哲学》2005年第 5期。
因此,人类的解放既是一段曲折漫长的阶级斗争史,更是一段无法摆脱的物质生产和积累的历史。当既有交往方式不能再适应发达的生产力时,人们不得不起来改变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形式,这个时候,新的历史帷幕又将开启,人类离自由与解放的步伐又前进了一步。
如上所述,社会劳动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政治行动必然要奠基在这一基础上。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仍有莫大的关联:“如果问,合马克思心意的现代的亚里士多德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推断他的亚里士多德将会选择另一条道路。他会通过颠倒亚里士多德的各种知识的层级结构,以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向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以至于创制渗透入实践,而实践渗透入理论。这将成为名副其实地参与民主的更有利的视角。大部分人都在工作,并且不乏理性、道德、智慧或者对工作的审美上的敏感性,而不管亚里士多德有任何相反的思想。”*David J.Depew, The Polis Transfigured:Aristotle's Politics and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in George E.McCarthy, eds., Marx and Aristotle,p42.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反对麦卡锡作出的论断。在麦卡锡看来:“‘实践’这一术语在马克思著述中有两大主要意涵。第一重意涵指涉社会劳动范畴,这一方面是从其早期著作中发展出来的,仅仅代表着此术语意涵的一个方面;第二重意涵最早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并且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在此马克思开始把实践理解为一个政治范畴,而其根源则回溯到了古希腊。”(参见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第76页)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实践”一词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侧重指政治实践,而在后期的著作中则是政治实践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但侧重指社会劳动。
四、结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类的活动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等级:创制、实践和思辨。划分这三种活动的标准是“自足”。创制是最不自足的,其活动的工具和质料都来自外界。劳动作为创制活动最典型的代表,由于对外在物的严重依赖,是最不自由的一种活动。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就在于摆脱这种依赖于外在物的活动,进入到更高级别的实践和思辨活动,而人的本质就体现在这两种活动当中。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开辟了政治哲学的一条传统,即从自足性看待人类活动的层级,所以,政治动物是人作为人的起点。只有在城邦和政治生活中,人们才能建立良善的秩序,分享好的生活,实现自身的潜能。而在马克思看来,人异于动物就在于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作为社会动物的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和历史。从这一点上看,马克思是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反叛。但是,马克思同时看到了劳动在不同的制度下显现不同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并非人区别于动物的创造性劳动,劳动仍是手段性的、最不自由、与自身相对立的活动。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拒斥实质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从“自足性”判别人类本质性活动的标准。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解放以及全面发展,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制度变革,人类本质性的实现,是一个开放而不断实现的过程。这种发掘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以及人类自身潜能实现的制度性环境的思想,使得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站在同一阵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