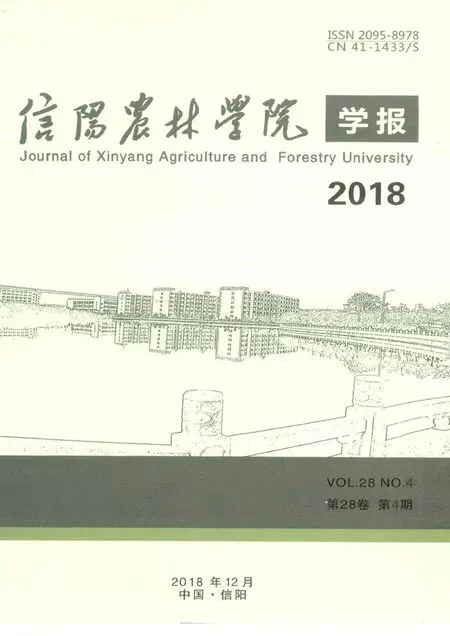环境群体性事件刑事预防机制研究
陈心哲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230000)
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的屡屡爆发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十年间,仅我国发生的重大环境群体性事件已超过三十起,部分省区更是呈密发态势[1]。这些案件涉及民众之广、社会危害之深、防控化解之难远非普通案件可比。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引发大量伴生犯罪,更会降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政治体制构成一定的威胁。环境群体性事件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群众追求生存利益的过激举动,不是恶性犯罪。如何改变当前事后的、单一的、粗犷的刑事介入方式,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刑事预防机制,将刑事法律的功能由事后惩戒提前到事前预防,不仅考验着学者们的智慧,更考验着学者们的良知。
1 环境群体性事件刑事预防的政治伦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刑事预防机制不仅是刑事法律问题,更是政治伦理问题[2]。刑事防范机制的构建,是为了确保刑法适用产生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刑法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和刑法伦理的彰显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伦理是法的内在根据,有什么样的伦理,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另一方面,刑法在根本上也是伦理的,以人伦关系中实践的道理或条理为根基。故而,讨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刑事预防机制,必须先明晰其政治伦理。“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的核心政治伦理,体现了国家把民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根本的问题,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机制,既要反映个人的利益要求,又要符合整个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只有在动态平衡的过程中,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动力。环境群体性事件,属于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应当在和谐社会这个大的政治伦理指导下,构造合适的刑事预防机制。
2 环境群体性事件刑事预防机制必须正确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
在明晰了政治伦理和刑事政策的前提下,探索环境群体性事件刑事预防机制的建立首先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正确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这不仅关系到该预防机制能否正确发挥效用,更是讨论具体路径的前提。当前的各种预防理论都承认预防犯罪才是刑罚实施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劝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其前半句即是指特殊预防,而后半句则是指一般预防,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预防对象的不同。但不论是特殊预防还是一般预防,均是任何预防机制不可或缺的。具体到环境群体性事件刑事预防机制中,笔者认为:充分发挥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适当发挥消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和特殊预防功能,才是对该机制中刑法预防功能的正确把握。
2.1 充分发挥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
根据预防对象和预防方式的不同,一般预防又被分为消极预防和积极预防,前者主张发挥刑罚的“吓阻效应”以预防潜在的犯罪人实施犯罪,后者则是塑造广大群众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忠诚以达到习惯守法的目的。罗克辛教授将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归纳为学习效应、信赖效应和平复效应三个方面。学习效应是指通过刑罚的实施以教育广大群众,塑造其对法律的自觉遵守;信赖效应是指通过刑罚这种看得见的方式,树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对守法的信赖感;平复效应则是指通过刑罚平复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使之恢复到先前和谐稳定的状态。环境群体性事件虽伴生大量犯罪,但其本身却不一定是犯罪。剖析众多环境群体性事件不难发现,事件均经历了体制内维权受阻转而寻求体制外维权这样一个过程,表明维权群众有对法律的信任感、依赖感和遵纪守法的习惯。对于这部分并未犯罪的群众,完全可以通过严惩环境犯罪、职务犯罪等形式,充分发挥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作用,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学习教育,恢复他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守法的信赖感,使之回归到正确的法制轨道上来。同时,严惩环境犯罪、职务犯罪亦可以最大程度平复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瓦解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基础。
2.2 审慎发挥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和消极的一般预防功能
特殊预防通过惩戒有罪之人达到预防其再犯罪的目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刑法预防功能最主要的内容。随着理论和实务的发展,这种预防方式的社会效果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重刑甚至所有实刑对于犯罪的预防极其有限。从现实来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往往已经有犯罪行为发生,包括导致污染发生的环境犯罪、官商相互勾结的职务犯罪以及过激维权的群众犯罪。对于前二者,虽然笔者认为重实刑对于预防犯罪十分有限,但依旧主张从重严惩。这是因为,其犯罪主体为企业、企业责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重刑往往可以造成企业的衰落、责任人商业生涯的结束或者官员政治生涯的终结。从社会效益来看,这样的严惩显然对于迅速平复群众积怨、快速化解社会矛盾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可以有效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而对于后者,则应坚持宽大处理。首先,严惩这类犯罪对于预防犯罪人再犯的效果十分有限,无法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其次,这类犯罪产生的基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及合法维权受阻,除非未来恰好又在同一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恰好损害了同一群人的人身财产权利、恰好合法维权再次受阻,否则同一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基础并不存在。最后,从社会效益来看,对过激维权的犯罪人苛以重刑,无异于火上浇油。事实已经证明,“杀鸡儆猴”式的处理方式,不仅无法起到“吓阻作用”,发挥消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反而适得其反,会点燃积怨已久的群众情绪,增加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3]。
3 环境群体性事件刑事预防的具体路径
3.1 严惩环境污染背后的职务犯罪
环境领域的职务犯罪,是环境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是引发环境群体事件及其伴生犯罪的重要原因。要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应当从犯罪的原因抓起,深挖犯罪源头。对环境职务犯罪的有效预防与严惩,特别是对涉案的主要国家工作人员及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能够迅速平息民怨,恢复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对环境群体性事件起到及时救火的作用。现阶段,我国职务犯罪存在着数量居高不下、查处率较低、适用强制措施宽松、缓刑免刑率畸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涉及环境的职务犯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既是刑法适用不平等和罪责刑不相适应的体现,也是司法不公正的真实表现。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机制,用刑事手段保持对环境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在事前预防职务犯罪;另一方面要提高环境职务犯罪的惩处力度,在环境群体事件形成之前,对于可能涉嫌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公职人员迅速立案侦查,尤其是对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应当结合侵犯群众利益和生态环境的程度,依法从重处罚。这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也是预防或及时控制环境群体事件的速效药。以盐城水污染事件为例,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在严惩环境犯罪的同时,对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官员采取强制措施,并以环境监管失职罪从重处罚,及时制止了已在酝酿的群体性事件。
3.2 对维权群众坚持宽大原则
梳理近年来重大环境群体事件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环境群体事件都经历了矛头由环境犯罪转向地方政府这样一个过程[4]。事前,群众往往都是在体制内提出惩办环境犯罪分子或抵制污染企业等合法诉求,遇阻后方才逐步转为针对地方政府的聚众、游行、打砸行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除了前文所述的渎职、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外,“打击错误”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激化作用。地方政府、公安司法机关错误地将刑事打击的重点放在“闹事”群众上,认为只要严惩个别首要分子,余下一般参加者便会因群龙无首自然散去,以强硬作风平息事态,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将本可以控制的维权行为激化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东阳画水事件为例,当地村民对污染问题维权多年无果,遂在厂区道路中央搭帐篷、拉横幅以示抗议,遭近百车执法人员强行清场并对大量村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最终导致上万群众聚集,数十名执法人员受伤,48辆车被毁的恶性事件。这样错误的措施、思路、原则,源于对环境维权的错误定性和对刑罚的过度使用。
环境污染事件中的集会、抗议、维权行为不是恶性的、有预谋的、有组织的、有卑劣目的的聚众犯罪活动,其归根结底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必要的生存利益,在体制内寻求解决遇阻后所实施的自卫的、过激的、不理智的行为,与直接危害国家、社会,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打砸抢等犯罪行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参与群众,特别是其中的组织者、领导者、指挥者往往本身就是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主要的受害者,可谓既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对于这部分群众,应该坚持宽大原则。要坚持“打击范围”和“打击方式”的双重宽大。对于“打击范围”的划定,要充分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从参与方式来看,对于静坐、上访、拉横幅等柔和的、非暴力的方式参与的群众,应当坚持同样以柔和的、非暴力的方式对待,例如领导接访、引导诉讼、民主恳谈,慎用警械、警具,慎用刑事强制措施,慎用实刑、徒刑,在量刑上与暴力维权者区分开来。从参与目的上看,对于本着维权、求生、改善、索赔等合法、合理、合情目的的群众,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使其行为较为过激,也不应轻易列入刑事打击的范围,以免激化矛盾,点燃群众情绪,必要时可以采用行政处罚方式予以惩戒。从参与作用来看,对于仅起到跟风、聚集、造势、喊口号等帮助作用的“一般参加者”,应当避免将其纳入刑罚的打击范围。对于起到组织、领导、指挥、策划等作用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则结合上述两个标准具体研判。所谓“打击方式”的宽大,不仅体现在轻罚轻判、从宽适用强制措施、充分运用缓刑免刑等方面,更体现在改变传统单一的刑事处罚措施,善于运用“刑事和解”与“刑事听证”,达到以相对柔和的方式适当惩戒的目的,充分将刑法的惩罚、教育、预防等诸多功能相结合。
3.3 善用刑事和解与刑事听证
在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问题治理中,惩罚方式从宽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治理犯罪中的合理使用,主要是指针对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人的特殊性质,适当运用刑事和解和刑事听证,以柔性方式解决刚性冲突,增强决策、处置、惩罚的科学性,对于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和解不仅可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还有利于对犯罪人惩罚效果的实现。现代刑法理念主张对犯罪人的惩罚不应只注重报应,更应注重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法益的恢复。环境维权导致的犯罪中,如果是侵害公民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类型的犯罪,并且比较轻微,应当积极适用刑事和解。另外,在环境维权中适用刑事和解,对行为人的改造也是一个更好的途径。适用刑事和解后,可以依法不追究或重新减轻对行为人的处罚,能更好地促进行为人改过自新。这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条件下做出的过激行为,有些只是过失犯罪、激情犯罪,主观恶性不大,犯罪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生存权利,不让自己居住的生存环境恶化,这种情况下的犯罪如果适用重刑,势必会造成行为人和其他维权群众抵触情绪、反抗情绪高涨,进而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恶化。而适用刑事和解,对其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减轻处罚,对此类事件的治理具有指引意义,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这类犯罪中的正确适用表现。
用刑事手段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将刑事介入的时间从事后提前到事前。启动刑事听证制度,通过环保、社会、公安特别是法学领域的专家论证,对当前的发展程度、原因、性质、未来趋势特别是发展成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及预防措施进行分析讨论。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萌芽阶段,启动专家咨询论证机制,理性分析警情和事件性质,从而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防止把不应定性为刑事、政治案件的案件定性为刑事、政治案件,导致矛盾激化;防止把应当定性为刑事、政治案件的案件定性为普通案件,导致事态失控。以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为例,当地政府紧急启动专家论证咨询程序,很快确定了镉污染直接来源及排污行为,从而成功化解了已聚集千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