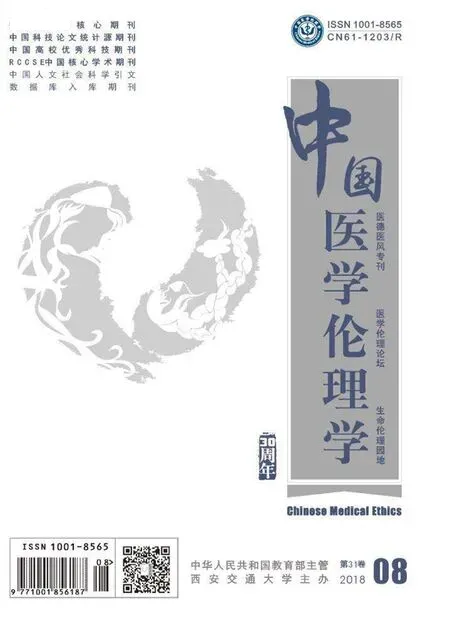儒家伦理视域下医疗决策中利益冲突之化解*
刘 涛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1436,liutao19821113@163.com)
利益冲突,是指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下一个人的某种利益具有干扰他代表另一个人作出合适的判断的趋势[1]。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医疗体制改革地逐步深入,在相关政策得到有效制定和落实前,当前医疗领域尚存在着较多的利益冲突现象。为了化解这些负面现象,我们的目光往往投向西方的经验,而忽略了自身文化传统的智慧。其实,在合理发掘、运用自身文化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当代医疗决策领域面临的许多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决。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主流是儒家伦理,而儒家伦理与医学伦理又是紧密相连的。在古代中国,医学伦理大体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据建构起来的[2]。韩愈曾将儒家伦理的内涵概括为:“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3]因此,笔者主要从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儒家所蕴含的化解当代医疗决策中利益冲突的伦理资源。
1 仁:生命权与自主权的冲突之化解
《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就是对人的爱。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是不忍别人受到伤害的心灵之善端的扩充。概言之,“仁”是关于人我关系的准则,仁的出发点是承认别人也是人,别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4]。一个人要践行“仁”,可以从忠和恕两方面去做。“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施加给他人;“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要达到的美好的境界,也要帮助别人达到。具体到医患之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5],医生首先要有爱护患者的真情。在面对患者的时候,“为医者当自存好心,彼之病犹己之病”[6],医生应该体会患者的痛苦,不忍心看到患者受苦,进而尽心尽力地医治病患,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状态。
在儒家伦理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下》),生命的繁衍与维系、生生不息是宇宙间最大的伦理准则。因此,明代名医龚廷贤以“生”来解释“仁”:“人,仁也;仁,生人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7]医之仁道的体现就是救死扶伤,使患者恢复健康,使其生命得以继续。张景岳亦云:“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人参两间,惟生而已,生而不有,他何计焉?”[8]天地最大的德是使生命得以诞生和繁衍,医者是参与天地之德、帮助生命得以更好地延续的人。由此可见,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医德思想中,“生”是至高的原则。将患者从死神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使其起死回生,是“生”;将患者从病痛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使其更好地生活,也是“生”。“生人”就是仁道、医道的本质。这种伦理精神类似于现代西方医学伦理中的有利原则,在儒家看来,“生”是对患者最大的有利,也是医者仁心的最直接体现。西晋杨泉《物理论》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只有秉持仁德的医生,才能将患者的生命视为与己一体的生命,才会将拯救患者的生命放在首要的位置。
然而,以“生人”作为首要的医学伦理,若是在与西方原则主义强调的尊重自主原则遭遇冲突时,应该如何抉择呢?也就是说,当医生面临这样的困境:患者的生命亟待拯救,但患者却并未表示同意或者表示反对医生的救治,那么,医生该如何处理?其实,这里涉及的利益冲突是由维系患者的生命权和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的矛盾而引发的。按照原则主义的伦理精神,医生应该尊重患者的选择,不对患者进行治疗。但按照儒家的伦理精神,在医生能够拯救患者的生命时,应该以救治患者为优先,在一般意义上,维系患者的生命权比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要更具伦理的重要性和优先性。这一点,隋代名医巢元方曾明确指出过:“然死生大事也,如知可生,而不救之,非仁者也。唯仁者心不已,必冒犯怒而治之。”[9]巢元方认为,拯救患者的生命是最大的事,如果能够救人性命而不救,就是不仁。有仁德的医者,即使患者不理解、不配合,也要先救治患者。这凸显了儒家伦理、中国古代医学伦理与现代西方原则主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抉择。
北京某医院发生的家属拒绝手术签字而至产妇李某及婴儿双双死亡事件,集中体现了在有利与自主的利益冲突下医疗决策过程存在的问题。2007年,李某在怀孕期间患感冒,因病情逐渐加重,在肖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某医院就诊,院方建议做剖腹产手术,而肖某坚持认为院方的治疗方案是错误的,因而拒绝签字。后几经周折,院方劝说无果,李某及其腹中的胎儿由于错过抢救时机而死亡[8]。关于这一事件,院方无疑是站在原则主义的患者自主权优先的立场来处理的,抢救必须首先要取得患者或关系人的签字,即使患者的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也不能越过自主权的雷池半步。然而,如果以儒家的仁道观念来审视,在遭遇生命权和自主权的利益冲突时,生命权是放在优先位置的,特别是对这种紧急发生的、患者往往不能或不能及时正确地做出选择的情况,更应以救治患者的生命为重。当然,该事件还牵涉关系人的利益与患者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不少患者会将自主权交给亲属或关系人。大部分时候,亲属或关系人会做出有利于患者的决定。但若亲属或关系人做出的决定侵犯患者的生命权时,其决定是不能得到儒家伦理辩护的;同样,医方也不应以尊重亲属或关系人的自主权为由,逃避对患者的救治甚至侵犯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相应地,如果医生在救治过程中没发生医疗过错,患者或其亲属、关系人也不应在被抢救过后以医生侵犯患者的自主权为由对医生进行控告。例如在一个西方的医疗案例中,医生违背达克斯的意愿对其深度烧伤进行了治疗,后来,达克斯很高兴自己还活着,但他坚定不移地拒绝认可或回溯性地同意医生当时的行为[11]。在原则主义看来,医生对达克斯的抢救违背了患者自主权,必须承担责任。而在儒家伦理看来,该医生以“生人”为目的且无医疗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责任。
2 义:谋道与逐利的冲突之化解
在儒家的语境中,“义”是所有人类给予或索取、预付或提取的行为标准[12]。对义利关系的回答,构成了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首先,儒家重义但不轻利。对于义,孔子道:“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是儒家十分重视的品德。对于利,孔子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如果能得到利益,就算去做个市场的守门卒,孔子也乐意。其次,儒家主张先义后利。孔子云:“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味地追逐利益,只会招来怨愤。只有将利置于义之后,才能消除怨愤。孟子也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孟子这里所言的“去利”,并非完全摒弃利,而是强调要以仁义为先。再次,在义利冲突时,儒家强调舍利取义。孔子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求取富贵等利益必须要以遵循道义为前提,如果不能以义求利,则利不可求,宁愿处身贫贱之中,也不能靠背弃道义来发财。
有学者指出,我国医疗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二是低收入人群享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下降;三是医疗费用的负担问题缺乏切实的医疗保障体系[13]。这三方面无不与经济因素有关。医院、医生、医药公司、医疗研究机构为利益体的一方,患者为利益体的另一方,前者为了谋取利益,往往将患者视为谋利的工具,而忽略了传统的仁义伦理精神的约束。在这种利益竞逐的医疗环境中,患者为了治病要花费许多钱。治好了病,患者认为医生赚够了钱,对医生没有感恩之心;治不好病,患者又会因花钱无果而怨恨医生,甚至发生暴力伤医的悲剧。可以说,正是经济因素引发的利益冲突,导致了许多医患冲突的产生。
反观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其中蕴藏的义利观是化解当下医疗决策中经济利益冲突的一帖良药。传统医学伦理认为治病救人的这个“义”是首要的,不应将求利作为目的。清代名医费伯雄说:“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若有疾,望医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也何如?易地而观,则利心自澹矣!”[14]“救人”是最大的“义”,医生的天职是救人而非谋利。明代陈实功也说:“贫窘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凡来看病,不可要他药钱,只当奉送。贫窘至极者,当量力资助,不然,有药无食,活命亦难。”[15]陈实功深受儒学影响,在义利之间遭遇冲突时,他的选择是取义而舍利。遇到贫穷的患者付不起药费,他也尽力施救,完全不计报酬,甚至还会补贴一些伙食给那些需要帮助的患者。相反,如果医生“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16]一旦惟利是图,医生就会为了获利而小病大治、虚开药方,反而可能加重患者的病情,这是历代有道德的医者皆着力批判的行为。因此,在现代医疗决策中,医院、医生等医疗群体应当从“利”回到“义”的轨道上,在遵循义的前提下求利,不得为了求利而忘义。此外,患者也要摆正心态,不能认为医生都是惟利是图之人,因为这种对医生先入为主的负面评价很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医疗决策。历史记载,扁鹊见齐桓侯,看出齐桓侯生病了,劝其治疗,而齐桓侯则认为“医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为功”[17],将医生都视为好利之徒,认定扁鹊是虚报病情而后假装治愈以邀功,因而不信任医生,耽误了治疗时机,最终不治身亡。并且,患者不应吝惜支付合理的医药费用,扁鹊曾言“病有六不治,……轻身重财,二不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患者吝惜必要而合理的医疗支出,其实也是自私逐利的表现,它会破坏医患之间的经济平衡,对医疗决策的过程是十分不利的。
3 礼:患者诉求与医生专业傲慢之间的冲突之化解
礼原是祭祀神灵的仪式,后来扩展为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传统习惯和需要遵守的规范[18]。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希冀用恢复礼治的方式来达到天下太平。至于如何践礼,在儒家看来有以下几方面。
《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对礼的践行,必须怀着恭敬的态度。礼的精神,首要就在于“敬”[19]。具体到医学伦理上,医生的“敬”主要体现在:其一,要敬畏生命,对患者全力施救,这一点也是与仁义精神相通的。其二,在与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色思温,貌思恭”(《论语·季氏》),态度要温和恭敬,这样患者才能易于接受。在现实的医疗决策过程中,医生只有抱持着敬的态度来“为礼”,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才能更好地“行医”。例如,前述手术签字事件中,当肖某带着李某去呼吸科就诊时,他们对于呼吸科医生让他们转诊到妇产科的决定表示怀疑,呼吸科医生的态度是:“叫你去你就去,跟我啰嗦个什么,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是我相信你,还是你相信我?你到医院来看病,就相信医生好了!”后来在抢救过程中,肖某对医生的救治行为不理解,这时医护人员又对其训斥:“你不懂,不要啰嗦,不要说话!”[20]在这一过程中,医护人员基于专业知识优势上的傲慢态度,无疑加剧了肖某的不信任感,由于医护人员在现实工作中的“失礼”而导致医患双方利益冲突的产生。或许医护人员是因为情急而然,但其也应认识到注重礼仪规范的必要性,时刻对患者保持恭敬,而不是居高临下地说教与训斥。
《论语·里仁》记载:“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礼”“让”合称,并将之视为治国的原则。《左传·襄公十三年》载:“让,礼之主也。”可见,“让”也是礼之精神的体现。根据儒家的礼让伦理,在现实医疗决策中,医生应该“让”着患者。首先,要让患者充分表述病情。医生不能为了创造经济收益来片面提高门诊量,患者的病情都未充分知晓就打断其表述,进而开药了事。其次,要忍让患者的“不专业”。术业有专攻,特别是医学领域,需要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才能成为医生,而患者往往没有医学专业知识,很多时候会就自身的病情对医生提出非专业的问题,这时医生不应对患者进行粗暴地言语压制,而是要忍让、体谅其非专业,并以较为通俗的话语向患者解释其病情,力求消除患者的疑虑。
《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儒家认为礼的作用是和谐,但和谐不应是无原则的为和而和,而是要通过礼的规范来实现。以医疗决策中的收红包现象为例,有些患者为了得到更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而向医生送红包,医生也可能由于现实工作报酬较低等原因而收受红包[21]。这种看似医患双方互利互惠的行为,实乃是儒家所言的为和而和的行为。虽然它保障了送红包患者的利益,但同时也会破坏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很可能会损害那些未送红包的患者的正当利益。对这种“知和而和”的行为必须以礼法制度来约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保证医疗决策中全体患者的利益。
4 信:知情同意与保护性医疗的冲突之化解
儒家认为“信”的核心涵义是诚信、诚实。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指出“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些是由于不诚信、刻意隐瞒事实而引发的,因此,诚信也是化解医疗决策中利益冲突的重要伦理资源。对医疗决策中的医患双方而言,诚信是相互的。一方面,患者要对医生诚信。所谓“匿病者不得良医”(《春秋繁露·执贽》),患者应如实将自己的病情告知医生,不能有所隐瞒。有些患者故意隐瞒病情,看医生能否在不被告知的前提下诊断出自己的病情,以此来考验医生的水平。甚至有的患者为了让医疗决策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刻意隐瞒或伪造病情来欺骗医生。患者的隐瞒行为往往会干扰医生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最终可能伤害到患者自身的利益,所以,对医生诚实以待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医生也要对患者诚信。首先,要将自己在医学领域存在的不足如实告知患者。宋代名医张锐在面对王秬叔夸赞其医术时坦言:“未也,仅能七八尔。吾长子病,诊脉察色,皆为热极,命煮承气汤,欲饮之,将饮复疑,至于再三,将遂饮,如有掣吾肘者,姑持杯以待,儿忽发颤悸,覆绵衾至四五始稍定,汗出如洗,明日而脱然。使吾药入口,则死矣,安得为造妙?世之庸医,学方书未知万一,自以为足,吁!可惧哉!”[22]张锐以自己曾险些误诊死其长子的案例,如实告知其在医疗诊断上存在的不足,客观诚实地评价自己的医术,反而获得了更多患者的信赖。其次,在医疗决策中如果出现了错误,也要及时向患者告知,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再次,如实将病情告知患者。宋代名医庞安时为人治病,“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宋史·庞安时传》)明代儒医万全也说:“病不可治,即宜早告,不可隐忍。”[23]对身患不治之症的患者如实告知病情,让患者做到心中有数,使其不过度治疗、不过多花费不必要的钱财,也避免了将来患者可能会因医生对其的保护性治疗而产生医患冲突。
除了诚信,“信”还有信任、信仰等涵义。就信任而言,一方面,“良药善言,触目可致,不可使人必服。法为信者施,不为疑者说”[24],患者只有在信任医生的前提下,才能配合医生共同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另一方面,对医生而言,如何取得患者的信任呢?除了要诚信对待患者外,医生还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东汉王充是一位对儒家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学者,他特别强调实践能力,痛斥虚夸的言行,王充指出:“医无方术,云:‘吾能治病。’问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医无方术,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向?”[25]只靠虚而不实的心意是治不好病的,医生只有切实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才能真正获得患者的信任,帮助患者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就信仰而言,患者应信仰医理,而不是迷信。东汉大儒王符指出:“疾病之家,怀忧愦愦,皆易恐惧,致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上漏下湿,风寒所伤,奸人所利,贼盗所中,益祸益祟,以致重者不可胜数。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26]王符批判那些装神弄鬼的骗子,也深深地惋惜因迷信巫祝而命丧黄泉的患者。他告诫患者,迷信是治不好病的。在现代社会的医疗决策中,仍有患者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例如,在前述案例中,肖某之所以认为当时医生在迫害李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他八岁时,有个所谓的“算命师傅”告诉他,他的老婆会被人害死,他养的第一个孩子也活不了,他对所谓的“算命师傅”所说的话一直深信不疑[20]。肖某的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害死了他的妻子,也害了他们的孩子,这再一次告诉人们,信任医生、信仰医理是化解医疗决策中利益冲突的重要条件。
5 智:因循与变通的冲突之化解
“智”即“知”,在儒家看来,“智”是对于事物的认知和对于道德的认知[4]。具体到中国传统医学伦理而言,特别强调智的变通性。张景岳云:“唯是死生反掌,千里毫厘,攸系匪轻,谭非容易。……不有圆通之智,不足以通变。”[8]在医疗决策过程中,医生如果不懂得变通,就无法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也就不能胜任医生这一职业。传统医学伦理中重视智的变通性,与儒家的权变精神是一致的。《易传·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切原则都不是绝对固定的,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变化。孔子也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就是通权达变,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孟子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惟义所在”的意思是“务适宜也”[27]。孟子认为,权变的目的是为了凡事能处理得适宜。概言之,作为一名医生,既要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道德观念,又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变通,使之能更好地处理医疗决策中发生的各种问题。
举例而言,在医疗决策中,当拯救患者的生命与患者的自主权相冲突时,儒家伦理和传统医学伦理主张以拯救患者生命为第一要务。但在一些特殊境况下,比如患者已处于不治之症的晚期,生命临近终点,或陷入不可逆转的长期昏迷,继续积极治疗已经不起作用甚至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身心痛苦时,从儒家伦理的视角来看,也可以允许医生根据病情劝说患方采取保守治疗或暂缓治疗的医疗决策。此种状态下医疗决策的难点在于医生需要权衡患者的预期寿命与其生存质量之间的轻重,而这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原则去机械套用。很多情况下,医生不能仅仅是为了告知而告知,而应是为了促使患者病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以不伤害患者为原则,综合权衡患者的接受度、接受方式,灵活地选择告知策略。再如,当医生和患者约定了治疗的方式方法,按照儒家伦理的诚信原则,医生应该在实施治疗时遵守此前的约定,但若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及时改变治疗方法而又暂时无法取得患者的同意时,医生就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对治疗方法作出调整。总之,医疗决策中的因循与变通,需要医生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作出判断,一切以有利于患者、不伤害患者为原则,以适宜为目的。惟其如此,方有助于化解医疗决策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