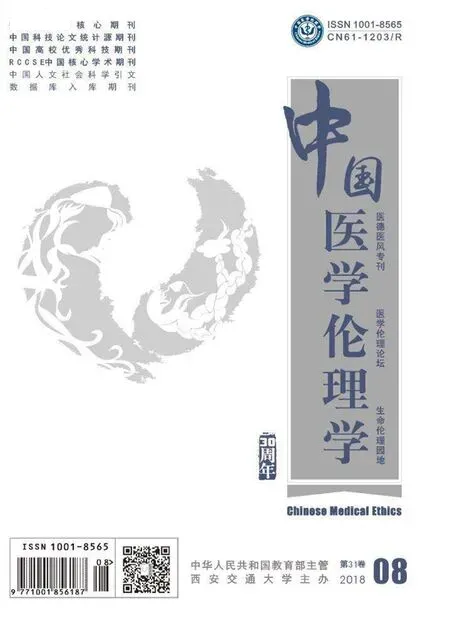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医学伦理问题及对策思考
张 雷,郝纯毅,廖红舞,陆 婷,周顺连,李 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医学伦理委员会/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42,zlei@bjmu.edu.cn)
基因编辑技术本质上是利用同源重组修复和非同源末端链接途径修复,联合特异性DNA的靶向识别及核酸内切酶完成的DNA序列改变,以靶向修饰基因组序列,不涉及外源基因导入,实现修复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等基因缺陷的目的。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相对早期的锌指核酸酶(ZFN)和转录激活子样效应因子核酸酶(TALENs),还是被《科学》杂志评为2015年度科学突破之首的基因魔剪CRISPR/Cas9技术,以及Rotem Sorek等[1]发表在《科学》杂志2018年第1期上,发现了细菌的10种新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开发出替代的新的基因编辑工具。这些技术的诞生和广泛应用对基因和细胞替代疗法及新药研发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推动。虽然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前景广阔,能够对肿瘤和某些遗传病等提供里程碑式的诊治,但是目前还面临许多法律和医学伦理学层面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距离转化为广泛临床应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 目前几大基因编辑技术潜在的风险与不足
无论是ZFN、TALENs,还是CRISPR/Cas9技术等都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有可能给相关受试者带来潜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截至目前,ZFN技术只能对从患者体内抽出的细胞进行体外操作,然后回输入至患者体内,效率比较低,而且其操作的精确程度还需要谨慎评估,否则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细胞癌变[2]。TALENs技术相对于ZFN降低了脱靶率,但是仍然存在的脱靶情况不仅仅造成目标基因的编辑失败,还有可能因为人工核酸酶错误地编辑与靶序列相似的基因而引发潜在的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3]。CRISPR/Cas9也因为其实现对基因进行编辑所依赖的crRNA序列更短而同样面临脱靶问题,而且CRISPR/Cas9对基因进行编辑,不仅仅需要上述crRNA序列的匹配,还需要前间区序列邻近基序(PAM)的配合,如果PAM无法配对或者不存在于目标序列周围,CRISPR/Cas9就无法实现基因编辑[4-5]。同时无论ZFN、TALENs还是CRISPR/Cas9都存在双链断裂后非同源末端连接修复可能随机产生细胞毒性问题[3]。
2 基因编辑技术牵涉的医学伦理问题
2.1 安全性和责任伦理主体不明确
虽然肿瘤、各种遗传病、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病在未来可能通过基因编辑其致病基因或突变基因而实现精准治疗被医学所攻克,但是目前所有基因编辑技术都必须正视医学伦理对其安全性的关注与质疑,避免因其可能存在的脱靶、错误编辑或引起基因组的不稳定增加患病风险等引起的无法预知的潜在风险和严重危害。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无论在范围、程度还是性质上都显著区别于传统医学诊疗技术,其以“生命的基石”基因作为研究对象,决定了一旦出现安全性风险都是灾难性和无法逆转的。而且,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存在尚无明确责任伦理主体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6]。
2.2 权利冲突和社会公正问题
基因组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和构成人类的基石,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针对特有疾病的致病基因,以医疗为目的的基因编辑技术,在保证安全和合理引导的前提下快速发展无可厚非,并且应该被大力鼓励和支持;其他不是以治病救人为终极目标的基因编辑技术,不但缩小不同人种基因组之间的差异,干扰人类正常进化进程中形成的多样性,对人类的正常繁衍生息产生重大干扰,甚至可以为了产生完美人类和所谓的超人类进行肆意妄为的多个或多次基因修饰,最终导致社会公正和人类各种正常伦理关系紊乱等冲突问题。
3 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医学伦理对策思考
3.1 对所有基因编辑技术研究采取乐观审慎的态度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医学伦理学家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和持续热烈的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给人类展现出“无饥饿、无污染、攻克目前存在的很多医学难题、大幅延长人类寿命”的极具吸引力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尚且存在一定比例因细胞内的误切割等隐患所带来的诸如基因突变引起肿瘤或未知疾病发病率增加等相关潜在风险,而且目前尚无相关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规范来合理引导和约束这些研究。因此,对基因编辑相关研究既要保持支持前沿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同时必须非常严格和审慎的进行和开展。对于肿瘤晚期患者等特殊人群,安全性还没有明确的前提下,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临床试图挽救和延缓受试患者生命是否应该获得伦理辩护而被批准?对于一些目前尚未被许可,未来有可能成为非常有效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如何进行监管,都需要相关科学家、科研机构及政府审慎管理和推动。同时,对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技术等存在巨大商业利益诱惑的研究,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学伦理学家都必须严守科学道德底线和生命伦理学的原则,最大限度的弘扬基因编辑技术未来可能解决诸多医学难题的“善”,阻止和抵制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引发的潜在的“恶”。
3.2 尽快制定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截至目前,世界各国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态度尚不统一,有部分国家已经出台禁止对生殖细胞和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相关法规。欧洲国家早在1997年就出台了《欧洲人权和生物医学理事会公约》以规范基因编辑尤其是对生殖细胞和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采取明确禁止的态度[7]。美国作为科学技术进步一直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虽然还没有出台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法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明确禁止和资助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和人类胚胎系的研究[8]。早在40年前NIH就出于大众对于基因新技术尚且存疑,成立了顾问委员会,专门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科学性和医学伦理方面的评估。宾夕法尼亚大学Carl June教授负责的CRISPR团队就被该顾问委员会要求对受试患者提醒说明研究属于试验性疗法,有失败的可能,尤其是对于晚期肿瘤患者,不但研究的干预比较痛苦,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而且研究可能存在无法逆转的不良反应。该团队还被这个顾问委员会要求将其对研究的描述“基因治疗”替换为“基因转移”,以免误导受试患者。
目前,我国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应用市场需求巨大,却处于相对无序状态,相关法律法规和医学伦理规范等监管和约束机制相对滞后并且亟需加强,甚至已经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和争议。相关权威专家建议和指出,根据目前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和相配套法律和医学伦理规范的现状,国家层面应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尽快制定并发布适合我国国情的《基因技术法》和《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伦理指导条例》等为核心的法律和伦理规范,对基因编辑技术研究设定严格边界,进行合理引导和监管,对无明显伦理争议或能够获得伦理辩护且有重大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可以给予大力支持,让其在安全有序的基础上进行临床前和临床试验。但对于诸如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和胚胎基因等具有明显伦理争议或无法获得伦理辩护、可能引起潜在严重社会问题的研究,应明确禁止和严格监管。
4 展望
基因编辑技术为人类攻克医学难题的美好愿景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虽然目前为止对于基因编辑技术产生的医学伦理和科学问题尚无明确定论,各方妥善解决基因编辑技术相关的医学伦理难题任重道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医学伦理学家和相关部门需要通力合作、资源共享,尽快制定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国际化技术标准和适合各国实际国情的医学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