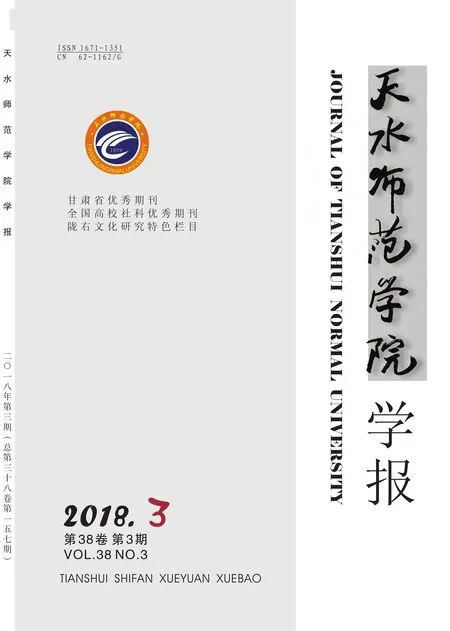“不规规形似”与“正脉”:对陈洪绶装饰图像模式的生成探讨
王一潮
(天水师范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少年时即博得画名,崇祯间召入为舍人,后因时局更易变乱,避乱山中为僧,移居绍兴卖画至殁。其四子儒桢结集诗文稿《宝纶堂集》梓行于世,后世画史、画论对其研究一直不断。评价其“不规规形似”则见于周亮工《读画录》:“章侯画得之于性非积习所能致,……章侯儿时学画便不规规形似,渡江拓杭州府学龙眠七十二贤石刻闭户摹十日尽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则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则更喜,盖数摹而变其法,易圆以方易整以散。”[1]948周亮工作为陈洪绶的赞助人,与其父二人均和陈洪绶有交往,①[1]948其对陈洪绶评价应为切实之语。陈洪绶晚年《画论》认为:“然今人作家,学宋者失之匠,何也?不带唐法也。学元者失之野,不溯宋源也。如以唐之韵,运宋之板,宋之理,得元之格,则大成矣……老莲愿名流学古人,博览宋画仅至于元,愿作家法宋人乞带唐人,果深心此道,得其正脉。”[2]468其说应是对当时董其昌、陈继儒等人鸣高“南宗”派别名目的反击,也是开启其画学理念的密钥。陈洪绶画作的“不规规形似”有何过人之处?若以变形论,与陈洪绶同时期的吴彬、丁云鹏、崔子忠等人在形象夸张上都做了积极探索,难道远离形似、过分夸张、怪诞就更胜一筹?本文试图通过对陈洪绶画作“不规规形似”的特征与画学“正脉”理论的分析,梳理其视觉图像的范式来源,探索其风格图像的符号典型化与画学“正脉”艺术主张的关系。
一、归纳图像的概括典型化
“规规”意为浅陋、拘泥原貌,“不规规形似”理解为不拘泥于原貌的形似,不以摹写细节为尚,拉开与原本的距离,好像必然走向了“变形”、“怪诞”;另一方面“不规规形似”与“重神轻形”的传统审美鉴别有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卷五:“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睹精奥,若取其意外,则方厌膏腴。”[3]15,65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等理论都认识到绘画不仅限于再现和模仿自然,将“形似”等同于低水平的绘画修养,周亮工认为陈洪绶画作“不规规形似”的特征,应是在这种美学观念延续认知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绘画谨守形似则“意”有局限,强调“取之象外”,则能反映“显现与隐蔽的同时发生和不可分离性”。[4]142
周亮工解释世人对陈洪绶作品的“讶其怪诞”,仅仅以笔墨方面“不知其笔笔皆有来历”进行辩解,表面上“不规规形似”是导致陈洪绶图像装饰性的“怪诞”缘由。陈洪绶实则是把原本物象用“易圆以方易整以散”的手法进行了图像处理,概括、归纳、提炼对象的趣味特征,使图像达到“似与不似”、虚实合一的“秩序感”状态,让图像在形式上具有了象征、暗示、比喻意义的指向性。陈洪绶在早年渡江拓杭州学府李公麟七十二贤石刻,“数摹而变其法,易圆以方,易整以散”,可以看出其对古图式的提炼和融汇智慧。如陈洪绶对画作中人的脸型与服饰、花与叶等形象,在轮廓形的表现处理上,体现了方圆对比性与统一性,即圆中带方,方中带圆。处理后的图像,既强化了图像的个性特点,又提炼了图形上的典型特征。
概括、归纳、提炼等思维方法是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达到简明的效果,接近于西方哲学的从特殊的感性事物显现出普遍、本质、一般的典型论。虽然“近代艺术哲学的典型观已经把重点转到特殊性,重视普遍与特殊的统一”,[4]139但是基本上还是以典型论为指归。同样中国传统美学也有自身特质的典型论,杨星映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的典型既有抒情性,又有叙事性。抒情艺术的艺术形象是意象,其艺术典型是意境。……周人的‘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既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因为‘言不尽意’,故‘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从具体到达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5]18“观物取象”既有对物的再现与观视,又有对物强调“取舍”的选择、提炼与概括。
有学者在研究陈洪绶绘画的特点,如“高古奇骇,俱非耳目近玩”、“讶其怪诞”时,论述较多与画家的性格境遇、精神郁结等心理状态联系起来,但陈洪绶功名理想的幻灭与悔恨并未使其放弃对生活的热情。①《宝纶堂集》卷八《入云门化山之间,觅结茅地不得》其四: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偷生始学无生法,畔教终非传教材。柴屋大都随分去,莲宗小乘种因来。定来金界和银界,永去歌台与舞台。[6]77崇祯十五年(1642年),陈洪绶45岁,“是年先生挟策入赀为国子监生,试辄高等,召入为舍人,使临历代帝王图像,因得综观内府画,艺事益进”。崇祯十六年七月,“接家书慨然沿运河南归”。[7]68,72如果仅以陈洪绶9岁丧父,16岁祖父去世,18岁母亲病逝,26岁妻子来氏病逝等遭际,而得出“造就出陈洪绶这类在理想与现实差距甚大下所形成多重矛盾性格的文人画家,并激荡出当时特有的文艺形态——‘变形画风’”[8]161的结论,就显得过于简单。这种解释忽略了时代的画学背景与画家的个性对画作的改造,且画学程式风格在传承过程中也会发生矫饰和变异。
浙江钱塘为南宋院画画风发源地,工丽精致与水墨苍劲两种画风并行传承,分别以赵伯驹、刘松年、李嵩等笔尚细润,色主青绿一派与马远、夏珪水墨苍劲风格为代表。工丽风格在元代由钱选承绪,毛奇龄《陈老莲别传》记载了陈洪绶学习钱选画风:“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花草法黄检校、钱选”;[8]283苍劲风格在明代有“戴进(钱塘人)出于马夏之流派而兼郭熙李唐之所长,遂开健拔劲锐之浙派”,[9]49蓝瑛(钱塘人,被誉为浙派殿军,陈洪绶与其有亦师亦友的关系)晚年画风趋向笔力苍劲,说明两种画风从南宋至明在浙地有流传。翁万戈先生分析陈洪绶中期笔墨认为:“陈氏的笔墨沿着两条大路发展:一是多用粗笔、折笔的放纵路线,一是多用细笔、中锋的工整路线,其中当然有不同程度的羼合。”[10]110陈洪绶继承了两种风格的优点,并且发展了院画工丽的装饰感风格,由于院画工致、装饰的特点限制了其用笔豪放的自由,陈洪绶通过“形”的夸张把苍劲画风进行了继承,是“形”的放纵与秩序的统一。
周亮工评价陈洪绶画作的“雄奇凸凹”与现代“装饰特点”、“晚明变形主义”、[10]102“概念化”、图案化、秩序化等概念相类似。从视觉结构来看,陈洪绶绘画的“简略化、模式化[8]98、特征化、平面化、类型化”特点,②王正华认为陈洪绶画中男女人物身份并不确定,是某一类型的人物,而非特定的个人,人物动作也较为类同。[11]9确切地说是艺术语言的提炼与概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九经题《陈洪绶花鸟扇》曾引用陈氏自评“余画至老虽绝笔墨之溪,然欲反而为壮时所为,则又不能,以老近略而壮必求详也”。“略”可看出陈洪绶自己对晚年画风概括、提炼的肯定。
有学者认为陈洪绶绘画造型源自于其天生对装饰性图案的敏感与喜爱,也有认为其古怪奇异的造型来源于九世纪末禅僧贯休所画的罗汉形象。笔者认为陈洪绶装饰化、概括化的绘画形式有其更深层的地域文化传统及潜在渊源关系,如古代传统纹饰图案符号本是对物象提炼、概括地模拟,显现了“概念化”符号特征。罗樾认为:“风格的变化是生活的记号,它们一次次地出现,通过多少代多少世纪,在经由风格序列产生的传统中,未曾有任何重大或根本的中断。这个风格序列很可能不是由一个
最终目标的幻象引起的,而是由一种潜在的长远趋势激发起来的。”[12]73,74南宋皇家器物纹饰与浙地民间器物的遗风持续流传,陈洪绶接触了这些纹饰图案,并从中找寻到概括、提炼物象“形”的启示,或者是传统器物纹饰的装饰趣味激发了陈洪绶造型的创造。当然装饰性绘画风格在晚明不是孤例,相比之下,被称为“南陈北崔”的崔子忠与丁云鹏、吴彬等人都出现了夸张的纹饰化的人物造型,但是缺少图像的归纳与提炼而显得语言单一和矫饰。艺术上如果一味照搬、模拟、夸张物象则会缺少“意”的指向性,因此概括图像是对纯粹写实与变形风格的纠偏。陈洪绶因学养深厚,使图像在造型上提升了哲理性与典型性,使图像具有方圆并用、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的归纳、概括、提炼等特点,同时强化了图像语言所表达的“意”。
二、立意隐喻的取象夸张化
“不规规形似”并不意味着陈洪绶不重视形似,实际上陈洪绶具备职业画家所应有的形似基本功。陈洪绶在《自题抚周长史画》以文比拟画道:“吾试以为文言之,今夫为文者,非持论即摭事耳。以议属文,以文属事,虽备经营,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邪?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含豪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行于前,舍夫论与事,而就我之法而文亡矣……故画者有入神家,有名家,有作家,有匠家,吾惟不离乎作家,以负此嗛也”。[13]139陈洪绶的自谦也认同自身“作家”身份,又强调“作法秩然”的“持论”、“意”是创作的核心,“论与事”的结合才能体现“象外”的“画意”。据张岱《陶庵梦忆》卷六水浒牌:“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章侯自写其所学所问已耳,而辄呼之曰宋江,曰吴用,而宋江、吴用亦无不应者,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矣。”[14]56《水浒叶子》反映其“所学所问”,即对水浒人物形象所理解“意”的明确与深刻表现。陈洪绶兼备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双重的优秀品质,因此在题材的画面形式处理上,能采用文学的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这是陈洪绶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不同所在。陈洪绶在《题画赠内生禅者》诗中就对暗示手法有明确阐释:“笔墨合成姿态,人心想出色香。画师粗粗举示,禅者细细商量。”“粗粗举示”体现在笔墨合成的暗示上,以借物寓意的象征来引导观者进入画境。
高居翰认为陈洪绶怪诞离奇的创作表现承袭了大量古老素材:“在固守传统的画匠夸张做作的绘画中,看出了其中有开创新风格的潜力。被职业画家画老了的格式,古老的原作因一再重复无意中形成的变形,却和业余画家崇尚抽象的品味、反写实的偏好不期而遇了。”[15]87,88“图式”的改良与“修正”,即在重复的题材中发明提炼新风格、新趣味、新样式的语言,源于中国绘画重于笔墨程式的传承,因此风格一再被重复而变为普遍的通俗的技艺。这也是认为陈洪绶绘画风格或许来源于民间之说的理由之一。①裘沙和王璜生都对陈洪绶风格来源于民间之说作有论述。[16]61-62[17]88-117
对于陈洪绶绘画艺术的“奇”、“怪诞”,学者大多认为似乎是“扭曲的人生”造成审美趣味上的“怪”与“狂”。笔者认为陈洪绶采用的是寓意象征等手法来深切体察人物内心世界,“奇骇”是其谙于“意”而有节奏的“胆张”。《周易·系辞》卷七:“兆见曰象,见乃谓之象者,前往来不穷,据其气也,气渐集聚,露见萌兆,乃谓之象。”[18]288这个“象”是有预兆和寓意,包含虚实合一,非具体的实。陈洪绶在造型上“离奇”的“象”正是为了“意”而拓展“象”的表现自由度,因此创造出“图写贯中所演四十人叶子上,额上风生,眉间火出,一毫一发,恁意撰造,无不令观者为之骇目损心”[8]290的感人形象。陈洪绶在《水浒叶子》人物形象旁边还有像赞题词,这是对图像文本的“持论”点评解释,也是为了使创造形象人物与“意”的“应”,因“识明”而有笔墨“胆张”的艺术魅力在陈洪绶画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高居翰在其著作《山外山》中用“矫饰”一词探讨了陈洪绶山水画放弃宋代山水画处理空间所采用的晕染法,而采用装饰性的平面化处理的造型手法,高氏认为:“陈洪绶在作品当中,运用了矫饰造作的笔法及扭曲变相的造型,这些原本一直都是造成仿古风格或仿古伪作之所以令人难以下咽的原因所在,但是到了陈洪绶的笔下,他却刻意加以使用,也因此,他才能够与复古人士层次较高的审美意图相契合。”[19]255高居翰在肯定陈洪绶的贡献中也批评了这种画风的刻板。造型上的过度夸张,一方面是艺术语言对比的需要;另一方面与强化形象的象征意味有关,深化形象气质的特点是艺术的高度概括与提炼,让所表现的形象具有显现与隐蔽、实与虚的统一。但是陈洪绶绘画造型的过度夸张“矫饰”所引起的弊端为其风格带来了争议的口实,美术丛书本(依董乐闲旧写本刊)方薰撰《山静居画论》载:“惟崔、陈有心僻古,渐入险怪,虽极刻剥巧妙,已落散乘小果,不若丁氏(丁云鹏)一以平整为法,自是大宗”。①《画论丛刊》(知不足斋丛书本)有不同记载:“陈章侯、崔子忠皆出群手笔,落墨赋色,精意毫发,僻古争奇,各出幽思。章侯山水、花卉,类有平淡天然之作,点染得元人遗意。僻古是其所能,亦其所短也。”[2]1498《宣统诸暨县志》载:“恽南田跋陈洪绶画两则,其一云,陈待诏抚王叔明亦有致,画云用细勾,太刻画耳?其二云,待诏写生虽极工整,犹有士气,与世俗所尚,大有径庭”。[8]286“险怪”和“刻板”的装饰风格与当时主流文人重平淡、幽秀的笔墨画风格格不入,陈洪绶坚持以持论立意创造图像,不趋同于时流,既有图像的归纳与概括化,又有因“意”取象的夸张和象征化。
三、“正脉”观念的传承系统化
陈洪绶在其《画论》中陈述:“老莲愿名流学古人,博览宋画,仅至于元,愿作家法宋人乞带唐人。果深心此道,得其正脉,将诸大家辨其此笔出某人,此意出某人,高曾不观,曾串如到。然后落笔便能横行天下也。老莲五十四岁矣,吾乡并无一人中兴画学,拭目俟之”。[2]468“正脉”显示出陈洪绶对画史系统性的传承思路,陈洪绶对“古人祖述理法,无不谨严”的苛求成为奠定自身以后画风“大成”的基础。《画论》是对董其昌贬抑浙地南宋画院遗风的纠正,为“大小李将军”、赵伯驹、李成等“北宗”正名,同时也有振兴越地画坛之意。《画论》批评了一味“主宋”的“作家”“不带唐流”,以及“主元”的“名流”“不溯宋源”之偏见,承认“虽千门万户,千山万水,都有韵致”,“都有部署纪律”的宏观看法。关于陈洪绶《画论》“正脉”的研究,高居翰、王正华等人做了细致而有深度的研究,[19]338,339[8]233-251笔者认为陈洪绶画学的“正脉”更多是从刘宗周理学“诚意、慎独”的正观得到了隐性启示。
陈洪绶十八岁(万历四十三年)时师从宋明理学的殿军蕺山先生刘宗周(此时先生三十八岁)学性命之学。[7]15此时是刘宗周讲学初期,其《论语学案》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是居家期间的授课讲义,[20]17大量引用《周易》、《中庸》、《孟子》及宋明等大儒为《论语学案》进行注解。影响陈洪绶思想的是此书成书之前刘宗周的讲义内容,理学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思潮,革新思想必然产生争议,寻求义理考据开始发挥作用。“思想理论上的冲突最后也不免要牵涉到经典文献上面去”,“义理是非无可避免地要逼出考证之学来”,“晚明的考证学是相应于儒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起的”。[21]334,335浙江省图书馆藏陈洪绶手稿本《筮仪象解》表征了其有志于经学抱负的一面,尽管也有人怀疑以陈洪绶嗜酒狂放的天性及性格,很难长时间地接受刘氏理性的学术精神约束,但是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人格精神与刘氏理学重德行的治学思想深远地影响了陈洪绶。经学举业与绘画创作看似不相干,实则进学态度相类似,陈洪绶绘画的“正脉”观念与刻意追古,应该是对正统绘画的法统来源所进行的诉求。高居翰认为:“随着较高的文化水准便出现了崇古的心态,……而在文学或艺术创作中,便也喜欢将古圣先贤的作品旁征博引一番,因为这些文人的教育是以先秦经籍与后世大量的注疏为基础,出现这种心态也是自然而然的”。[15]5这也是毛奇龄在《陈老莲别传》中大量叙述陈洪绶多种技法的师承缘由,既是体现这时期学术上对于寻源考据要求的共识,也是对陈洪绶绘画技法多样性的“正脉”肯定。
陈洪绶画作“不规规形似”的特征似乎在传承上存在对“正脉”观念的反叛,但实际上“不规规形似”在图像上消解传统的“细节形似”,而非忠实的模仿,依据传统图像,进而“修正”传统形成的典范和程式,求得传统以另一种形式的新生,复兴绘画正统的“道”与“正脉”。巫鸿先生阐释了三种复古模式特点:“跨越时间断裂以今观古的基本概念和感知方式;把往昔系统地分割为独立时间单位,赋予其不同政治、道德和艺术价值的尝试;重新发现、回归并重建某一特殊历史时刻的执着愿望。”[22]25这种观点涵盖了艺术家情感理念、道德依归、艺道重构的思考,从经典阐发新义,以复古探寻未来,进而获得艺术新生的灵感。陈洪绶的“刻意追古”可以理解为对“正脉”艺术主张全面、系统的继承,是通过清理“源”来探寻未来“流”的可能性。
陈洪绶画风是否受到戴进及其浙派画家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不过陈洪绶早期作品“有许多蓝瑛的痕迹,尤其是山水和人物画的背景树石,花鸟写生也有蓝的气息”。[17]74两人的持续交情,从陈洪绶后来写的《寄蓝田叔》三首诗可以看出,二人画风有互相影响的可能。陈洪绶画风精工而典雅的设色特点与蓝瑛相似,蓝瑛晚年作品出现了重彩而装饰感的画面,应该是同样受到南宋院画笔尚细润、色主青绿一派在浙地的影响。王璜生先生是对陈洪绶受浙派影响较早提出者,认为时代相近的画家“群”,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影响。[17]72陈洪绶早年画作采用的“易圆以方”,可能与吸收马远、夏珪用笔方硬挺拔的遗风有关。在浙派用笔纵情挥洒的动势感方面,陈洪绶则采用了近乎矫饰而夸张的运动感造型得到继承,但在线条行笔慢,转折变化多样而富于含蓄隽永上,则消解了浙派用笔浮躁感的负面因素。虽然陈洪绶在《画论》中提到“若宋之可恨,马远、夏珪真画家之败群也”,对马、夏风格进行了否定,但是陈洪绶工整古雅、高古奇骇的画风可能是其规避马夏用笔简捷劲拔带给浙派的流弊,其行笔过程中则显得较为矜持。陈洪绶对南宋院画与浙派遗风的继承和超越,有着强烈的历史连续性的新生特点。陈洪绶“开启了新的表现模式,以及处理传统包袱的新法门”,[19]339因此其在造型上开拓了表现手法的新境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陈洪绶在晚明董其昌横扫画坛的影响下,能够保持特立独行的绘画风格实属难能可贵,浙地文化氛围的土壤滋养与陈洪绶个人才能的“识明胆张”,造就了陈洪绶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使得其风格流派在后世绵延不断。陈洪绶绘画美学中归纳图像的概括典型化、持论立意的取象夸张化、“正脉”观念的传承系统化等特点,在今天的艺术实践中仍在发挥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