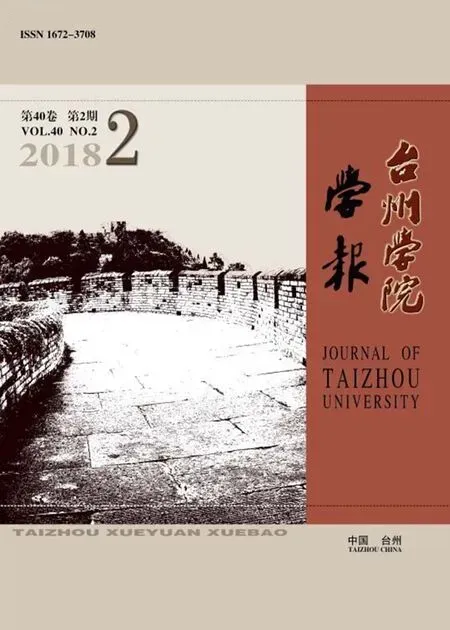试析“黑人力量”运动的源泉:“黑豹党”及其社区基层组织行动
黄逸云
(美国 田纳西大学历史系,诺克斯维尔 37996)
一、前 言
“黑人力量”运动(the Black Power movement),尤其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可以被视作美国当代史中最受争议的政治团体之一[1][2]。以“黑豹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为代表的“黑人力量”组织通常被视为鼓吹革命和武装自卫,并且曾数次与警察发生致命的冲突。长久以来,“黑人力量”运动都被视作是民权运动“邪恶的孪生兄弟”(evil twin),是黑人因为不满于民权运动的缓慢进展,而宣泄自己的愤怒的运动。一些学者将“黑人力量”运动与1960年代出现的数次骚乱相联系。在通常的叙述中,“黑人力量”运动被认为阻碍了民权运动在社会正义的层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权运动时期”过早结束。但是近十多年以来,以历史学家皮奈尔·约瑟夫(Peniel Joseph)为代表,美国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黑人力量”的贡献,以及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这个被称作“黑人力量研究”的子领域,涌现了不少专著,关注点不一,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战后美国史,并拓宽了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研究者的视角[3]。
这些学者不再将目光仅仅局限于“黑人力量”运动的少数几位领袖和他们的言论,而是从多个不同的关注点出发,以求呈现出“黑人力量”运动的不同面相。重要的关注点包括:1.“黑人力量”组织的基层和草根属性(社区组织以及基层黑人政治“机器”的构建);2.“黑人力量”组织中的女性贡献;3.以全球性的视角审视“黑人力量”,将其与亚非的独立解放运动相联系。4.“黑人力量”运动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贡献(音乐,美术以及美国高校非洲研究学科的建立)。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探讨“黑人力量”基层组织对“黑人力量”运动的作用,聚焦于“黑豹党”这一核心组织的基层运动及其对于美国社会和黑人族群的影响[4]。
毫无疑问,在“黑豹党”活跃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其始终无法与暴力和革命等字眼相分离,但是从“黑豹党”的社区控制和社区组织计划可以看出该组织务实的一面,这一面不应该被忽视。“黑豹党”的社区组织,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提升黑人族群,另一方面亦是为了降低革命的调门,可以被理解为去激进化。因而“黑豹党”深耕社区,可以说既是在计划之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理清“黑豹党”在基层的行动,就必须先明确其以社区为导向的政治思想来源,及进行社区组织和控制的具体方法,进而探寻社区组织和深耕社区对于“黑豹党”、黑人社群乃至美国社会与政治的意义和影响。
二、黑豹党以社区为导向的政治思想来源
最近十多年以来,在“黑人力量研究”这一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黑人力量”组织的基层组织行动和其草根属性。随着“黑人力量”研究的进一步细分化,学者们发现“黑人力量”运动的组织及其成员,既有理想主义和激进的一面,但同时也十分现实,扎根于基层,解决一些与黑人民众切身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仅仅空喊口号或者唆使与警察的武装对抗。社区与草根属性在“黑豹党”这一“黑人力量”运动的中坚身上有着极强的体现。
“黑豹党”由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鲍比·西尔(Bobby Seale)于1966年在加州创立。这两位创始人深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希望在美国通过革命行动方式,建立属于黑人自己的国度。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之中,他们只是鼓吹革命和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至始至终,暴力与革命可以说都是“黑豹党”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忽视他们在社区组织和社区控制方面的务实努力。以创始人牛顿为例,尽管他一直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的鼓吹者,他始终没有放弃通过社区控制和社区服务,来提升黑人族群的努力。当然简单地将“黑豹党”定义为激进暴力的或是深耕于社区的都是不准确的。甚至在70年代,社区服务被认为是“黑豹党”的支柱,尤其是其意识形态在1971年发生了转变,由支持暴力转变为提升社区[5]。“黑豹党”的目标之一即为建立“广泛的,大规模的,属于人民的政治机器”来满足不同黑人社区差异化的需求[6]。
我们先考察“黑豹党”为何关注黑人社区和争取社区的控制,即“黑豹党”的政治思想及其源头。“黑豹党”的创始人牛顿和西尔在仔细研读了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等人的思想之后,总结出黑人想要赢得真正的自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而他们确信黑人社区正在遭受政府的袭击,而黑人社区就像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一般,占领军就是警察。若要赢得真正的自由,黑人社区就应该一方面抵抗占领军,另一方面实现自己的民族自决。先前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黑豹党”武装抵抗和鼓吹革命的一面,而新的研究发现,“黑人力量”运动的核心组织,“黑豹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的地方分支,都曾经在提升社区和带来进步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黑豹党”等“黑人力量”组织的社区组织和社区控制的尝试可以追溯到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和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
在与“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决裂之后,马尔科姆将自己的政治哲学定义为“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即黑人须通过控制社区的政治与经济来改善自身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马尔科姆也认为黑人精英们所推崇的“融合主义”思想是行不通的,住房和学校的融合尤为如此。白人可以通过搬离来轻易抵制这些融合的努力,因而在马尔科姆看来,大多数黑人居住社区的主体都将是黑人。对于黑人来说,自助(self-help)是唯一可行的手段。所以黑人应该对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命运负责。“黑豹党”将自己视为马尔科姆思想遗产的继承人,因而该组织创立之初亦带着浓烈黑人民族主义色彩,追求黑人政治自决的组织,与马尔科姆一样,他们的目标之一也是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实现对黑人社区的控制,已达到提升整个族群的目的。
当然,马尔科姆亦曾提出黑人实现政治自决与社区控制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武装自卫。这一点与罗伯特·威廉姆斯的思想不谋而合。后者领导了“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在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市(Monroe,North Caroli⁃na)的分支。在面对白人至上主义和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时,威廉姆斯和他的组织并没有选择用非暴力等手段来回应,他认为武装自己和团结自己的社区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威廉姆斯认为在现有的由白人主导的司法体制之下黑人并不能真正地赢得公平与正义。黑人只有自己成为执法者,才能通过司法体制外的其他手段(建立自己独立的司法体制或者私刑)去惩戒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以“黑豹党”为代表的“黑人力量”运动参与者也深受影响。“黑豹党”始终认为对黑人社区的最大威胁就是被他们称作“占领军”的警察的存在,因而只有武装起来进行自卫,才可能消除这一黑人社区的最大威胁[7]。
作为上述二人的推崇者,不难理解牛顿和西尔为何最终会走上争取社区控制的道路,从他们的“十点计划”(Ten-Point Program)中即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对于社区的关注。在这个纲领性的计划中,他们谈到黑人需要有“决定黑人社区的自由”,需要有充分的就业,像样的住房,一定的教育,免除兵役的自由和黑人陪审团等等。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黑豹党”的政治思想亦可追溯到一些为黑人争取自由的先行者如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和杜波伊斯(W.E.B Dubois)身上。杜波伊斯曾提出黑人斗争的第三条路径,即黑人为了赢得完全的平等和民权,应该建立部分“分离”的经济来支持黑人自己的教育,卫生,法律和住房事业。[8]杜波伊斯和华盛顿均认为黑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可以为自己争取政治自由铺平道路。此外,二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独立的浪潮,使得黑人民族主义渐渐高涨,支持者们,包括“黑豹党”的创始者,坚信要真正实现黑人的平等与自由就应该从经济和政治层面控制黑人社区。在这一背景下,“黑豹党”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改变黑人社区的努力。除此之外,“黑豹党”社区控制的行动与两位创始人的背景也有关系,他们都是出生于黑人社区的工人阶级后代,父辈从南方移民至加州,他们都不相信所谓的黑人中产阶级或是知识分子,也不认为非暴力的抗争手段能行之有效。
“黑豹党”的矛盾之处在于,包括“十点计划”在内的纲领均为改革性质的,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纲领的手段却是进行革命。而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其实也可以见于“黑豹党”的社区服务和社区控制的行动之中。
三、“黑豹党”的社区组织行动
“黑豹党”的总部设在加州的奥克兰(Oakland),而各个地方分部的构架均依照总部设立,并且从属和听命于奥克兰。据不完全统计,“黑豹党”一共支持了二十多个社区服务的行动,而“早餐计划”,传播解放思想的学校以及“诊所计划”是这些行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豹党”的社区行动是为了降低鼓吹革命和武装对抗的调门,从而使这个组织在政府的严密注视底下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尝试都或多或少从实质上改善了黑人社区。对于“黑豹党”的领袖来说,这些社区组织的行动旨在切实改善黑人的生存环境,以及培养黑人,尤其是下一代年轻人更高的革命觉悟。
在社区组织活动中,“黑豹党”开展的“免费早餐计划”(Free Breakfast for Children)既富有创意特色,又极为实际有效。第一个“免费早餐计划”开始于1969年的奥克兰的圣奥古斯丁圣公会教堂。而关于志愿者的招募则在1968年底就已经开始。黑豹党会组织志愿者在各个中小学附近坚守,鼓励碰到的孩子们加入这一“免费早餐计划”。只要一些孩子来到这个教堂领取早餐,消息就会在学生和家长中传开,因而在短时间内参与的学生数量就有比较大的增长。此外,黑人区内的商家也被动员捐赠资金,食品以及烹饪和餐饮器具。这样一来,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免费早餐计划”,黑人社区内的一些资源,包括人力和财力都被有效调动起来,为本社区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从加州开始,据统计有多达22个“黑豹党”分支机构实施了“免费早餐计划”。截止1969年,这些“黑豹党”的成员们一共为近2万名黑人学童提供了免费早餐,这就意味着一个“黑豹党”基层组织一个月给688位黑人学童提供了早餐。而这些分支组织基本上都分布在拥有庞大黑人人口的城市(比如芝加哥、纽约市、洛杉矶、费城、巴尔的摩、堪萨斯城、旧金山、纽黑文和波士顿),这些城市都设有不止一个的免费早餐提供点。
“免费早餐计划”成为了“黑豹党”社区组织行动中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计划。而黑人商人在“免费早餐计划”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助于“黑豹党”“十点计划”政治纲领中第三点的实现。而“免费早餐计划”的成功实施也证明了,当黑人社区内部的人力与资金被合理调动时,是可以发挥改善社区面貌的作用的。
除了“免费早餐计划”之外,“黑豹党”从1969年开始还开办了名为“解放学校”(Liberation Schools)的教育机构。事后证明这些学校成为了“黑豹党”社区组织行动中的重要一环。这样的学校在黑人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方的“解放学校”起着向社区成员解释民权运动,在黑人中普及投票权等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黑豹党”的“解放学校”借着“免费早餐计划”的势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以旧金山的“解放学校”为例,每天有多达75位的学童参与教学。一周的课程安排如下:周一,历史日;周二,文化日;周三,实地考察;周四,革命电影;周五,时事。除此之外,学校中的歌曲和游戏也都肩负着传递“黑豹党”意识形态的使命。比如,学生被要求背诵“黑豹党”的政治纲领,即“十点计划”。
在所有的“解放学校”之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创立于1971年的奥克兰社区学校。这所学校不仅提供了高质量的私立教育,同时也会向学生灌输一种自我价值感。学校招收从两岁到十一岁的学童,开设的课程包括语言艺术,西班牙语,数学,社会科学,环境研究,体育,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学校有16名教职工和15名志愿者,其中校长艾瑞卡·哈金斯(Ericka Huggins)同时也是阿拉梅达郡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学校发展最好的时期,在校学生多达450人,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族群。值得一提的是,奥克兰社区学校在“黑豹党”解散之后仍然继续运营,最后一届学生于1982年毕业。可以说奥克兰社区学校是“黑豹党”最后的遗产。
除“免费早餐”和“解放学校”之外,“黑豹党”的“免费医疗计划”(People’s Free Medical Centers)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黑豹党”认为美国城市的医疗制度反映出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因而有必要建立黑人自己的诊所,来改善黑人社区的医疗状况。因而“黑豹党”下属的医疗团队接手了给黑人社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任务。专业的医疗人员向其他的成员传授基本的医学知识和急救常识,以期可以扩大在社区的医疗服务。尽管社区医疗服务在“黑豹党”的社区服务中占有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学界并没有太多关于“黑豹党”的社区医疗计划的研究。[9]
“黑豹党”的医疗小组在几乎所有大城市的黑人社区中开展了行动。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在芝加哥和波士顿的医疗服务。芝加哥的诊所被名为“杰克·温特斯医生”,以纪念一位在1969年死于警方枪下的“黑豹党”成员。该诊所在“黑豹党”芝加哥分部和志愿医务人员的努力下,开设了妇产科、儿科、牙科以及眼科的诊疗服务。同时,志愿者和医学院学生也积极动员黑人社区来加入医疗服务或是传播相关信息。据统计,该诊所在开业2个月之内就收治了多达两千患者。而位于波士顿的“波士顿人民免费诊所”则开业于1970年,直接诱因是一名黑人患者在1969年被警察枪杀于波士顿总医院。该诊所除了提供与芝加哥类似的诊疗服务之外,还负责培训医疗技术人员,助理护士和医疗秘书。除了运营根植于社区的医疗诊所之外,“黑豹党”还资助了一系列针对特定疾病的医疗研究项目,比如镰刀形细胞贫血症。“黑豹党”的社区医疗服务计划对于黑人社区有着持久的影响。经过培训的医疗志愿者具有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能够在“黑豹党”解散之后仍然服务于社区。
可以说,虽然“黑豹党”的行动并未覆盖全美的所有地区,持续时间也比较有限,但是像“免费早餐”和“免费医疗服务”等都切切实实地给黑人社区,尤其是中下层的黑人带去了福利。同时社区组织的开展,对于“黑豹党”本身形象的改善也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黑豹党社区组织行动的影响与意义
受限于“黑豹党”的规模与参与人数,其社区组织行动只在全美黑人人口较多的地方进行,因而似乎对黑人乃至整个美国难以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但若就其对黑人社区的作用而言,其意义和影响是值得肯定和关注的。
首先,“黑豹党”的社区组织对于黑人社区来说有着积极的作用。“黑豹党”社区“生存计划”的本意就是服务于黑人基本的需求,通过多种方式改变黑人的命运。无论是“免费早餐”还是“免费校服”等,这些行动都解决了黑人社区的燃眉之急,真正帮助了中下层黑人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黑豹党”来说,这些社区组织行动并不只是单纯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其中包含了政治信息,以期提升普通黑人对于自身命运和政治的敏感度。尤其是对于“解放学校”来说,“黑豹党”的成员们时常会向黑人学童讲述黑人历史,并向他们灌输一种作为黑人的自豪感以及提升整个族群的必要性。
“黑豹党”的社区组织行动对于黑人社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行动本身,更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黑人社区,并且向世人证明,即使是曾经的罪犯或者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士,只要给予机会,也是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黑豹党”多达40个的地方分支成员基本来自于当地,而以年轻人居多,这些年轻人(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敢于去挑战现有不公的制度和当局的压迫,为社区注入了活力,也给更多人带来了政治觉醒。如果说民权运动促使了立法方面保障黑人的平等,那么“黑豹党”为代表的“黑人力量”运动的社区组织行动则在精神层面给予了普通黑人以信心和力量。此外,这些社区组织行动的成功进行,也给黑人提供了一个如何有效利用社区内资源来解决问题,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范例。以芝加哥为例,尽管“免费早餐”等社区服务计划持续的时间不久,但是都对这些社区孩子的成长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当芝加哥的“黑豹党”组织被瓦解之后,一些黑帮很快就重新占领了社区。因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黑豹党”也起到了阻止黑帮渗透的作用。
其次,“黑豹党”的社区组织行动对于其本身来说,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经历了因为宣扬暴力革命和武装对抗而被政府严密监视和被媒体妖魔化之后,社区服务行动帮助“黑豹党”降低了革命的“调门”,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其政治活动的风险,也降低了与联邦政府直接对抗的可能,为自己的生存争取了一定的空间。早在1969年,就有一些“黑豹党”的领袖认为武装起义没有任何胜算,并且他们意识到黑人更希望通过改革而非革命来改善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因而相比于武装革命,对“黑豹党”来说,社区服务无疑是更为现实和可行的道路。“黑豹党”因为其激进性在吸收了一些忠实的成员加入的同时,其实并没有赢得大多数黑人的支持,反而因为几次与警察的暴力冲突之后,造成了成员的流失。转而深耕于社区,通过几项卓有成效的服务行动的进行,得以被重新认识,从而能够吸收更多的黑人加入。毫无疑问,若“黑豹党”只是单纯地组织步枪队,与警察对抗,他们很可能会被列入危险分子的名单,而早早地被联邦执法机构所剿杀。
“黑豹党”的社区服务计划代表着黑人民族自决的思潮,这也是其政治纲领中的应有之义,此外,社区组织行动在黑人社区可以顺利开展,与“黑豹党”成功的招募和培训的计划是分不开的,这些在社区层面进行组织和教育的经验,民众的召集和宣传以及一批能力突出的骨干的培养,为艾伦·布朗(Elaine Brown)等日后参选地方选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黑豹党”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颇深,也将社区服务计划视作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比如从黑人商人处募集到资金然后用在底层黑人的身上,也是一种所谓的从有产者到无产者的财富再分配。
总的来说,社区服务计划代表了美国黑人对于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尝试,对于黑人社群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难以成功,但是对于后来者,尤其是对黑人政治领袖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培养了新一代黑人政治活动家,从基层为黑人政治力量的觉醒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