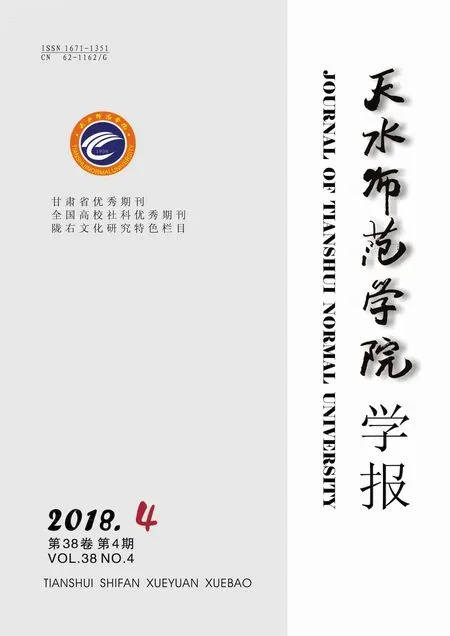“文化磨合”视域下延安文学前期的丁玲写作
——以《“三八节”有感》为例
马 杰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古今中外大尺度的时空范围内,多种形态与介质的文化在中国场域内不断磨合而来的。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或是命门,关乎着整个中国社会的趋势与走向。前者是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五四,后者则是以中共中央抵达肤施①旧县名,今天的延安市主城区为其辖境。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肤施后改名为延安,自此肤施地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为标志的“延安”。五四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相当开放性的文化场域,既有因袭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古保守主义或本土主义,又有被知识分子从西方“拿来”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民主的启蒙姿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等,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派别。“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化本身就是古今中外文化交汇、磨合的结果,其中有文化冲突、摩擦,也有文化互动、激活”,[1]从而呈现出了众声喧哗的五四“文化磨合”的历史图景。而由于历史原因,“延安”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则是一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区域性的文化场域。通常学术界都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将延安文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呈现出多元文化形态相互磨合交融的景象,而后期则是将这种较为繁复的局面以政治力量的强势介入而试图整合为“一种基于国家意识形态统制的‘党的文艺’观念”。[2]
一、“文化磨合”与“延安文人”
事实上,从文化层面上看,文化磨合的前提就是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之所以需要‘磨合’也恰恰反映了文化理念与文化环境的冲突。由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往往较难在短时间内与异质文化相兼容,甚至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状态,形成敌对关系。”[1]149而以“文化磨合”的眼光来审视延安文学,就需要重新勾勒延安文学传统:“文化磨合”以或隐或现的形态贯穿于延安文学,其前期以深刻沁浸了五四文化传统的左翼知识分子文化、延安本土文化、党领导下的军事革命文化及民族大众文化之间相互适应、交流、对抗与融合,表现为一种显性的主动地寻求“文化磨合”的姿态;而后期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文化运动所建构而成的“党的文学”强势背景下,转而为一种隐性的沉潜于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矛盾纠缠的“文化磨合”形态。
而奔向延安的文人的到来,则是这一“磨合”得以成立的前提。“延安文人是个较为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奔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是复杂的,但大致可归纳为: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3]而在这些生活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未抵达陕北之前,边区的文艺事业相当匮乏贫瘠。中国共产党深知文艺与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于1939年12月1日曾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4]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事无巨细,相当周全地考虑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其求才之切可见一斑。时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于1941年6月10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一方面豪情满怀的宣扬:“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但又坦率承认:“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条件,边区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文化上落后的地区。”故“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5]边区政府真诚热情地呼吁全国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以丰富、发展边区的文艺事业乃至于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储备人才资源,虽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工具化或是功利性的态度来看待知识分子,但这种热情欢迎的姿态实则表现出一种主动寻求“文化磨合”以发展壮大边区科学文化事业的追求。
丁玲是从南京国民政府特务机构软禁之下逃亡的叛逆者,也是对党组织怀着无限虔诚与向往的追求者。她“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3]5而丁玲之“典型”在于,她在身份上既不同于萧军作为一个党外人士①延安时期的萧军并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无所顾忌,在命运上也不同于王实味早夭的惨剧,她是“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6]她出身湖湘名门望族,官宦之后,家道中落后随寡母寄人篱下,后外出求学,四处奔走,在五四的浪潮中她执着于女性解放的事业,追随过无政府主义的号召,结识革命人士瞿秋白、冯雪峰、胡也频,她一步步向革命靠拢,但却遭飞来横祸,身陷囹圄三年,在逃离南京后便辗转上海以谋划奔赴陕北,革命波折叵测,丁玲往后的命运亦是大起大落。到“新时期”她又以革命的“孤影”立于时代潮流的对面,革命话语的式微而启蒙话语的粉墨返场,三十年“风雪人间”,她又面临着时代的拷问与立场的抉择,但她亲手为自己贴上了“左派”的标签,这是众人始料未及的。或许是历史的吊诡与鬼魅,“左”“右”皆能加诸其身,但丁玲却仍以极强健的生命力奉献于她的革命事业,究其根源,全在延安之于丁玲是有着“涅槃重生”的意味,自此便造就了她与中国革命的难解之缘。正如解志熙所言:“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就在于此——这是一种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甚至必有抵触和磨折的复杂关系”。[7]
丁玲到达陕北后,“经过了初到解放区的激动惊喜,初尝了军旅生活的粗狂豪迈,率领过一支军事宣传团体亲历紧张复杂的斗争,又经受了组织严厉审查、恋爱招来的闲言碎语,加上萧军等人强烈的影响,有着了这种种丰富经历的丁玲,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俯瞰延安,作品也变得深刻厚重,显出战斗的锋芒。”[8]从而在1940年底到1942春整风运动始,丁玲有了一段较为安稳的创作年月,迎来她在延安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包括: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杂文《开会之于鲁迅》《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干部衣服》《我们需要杂文》和《“三八节”有感》,散文《风雨中忆萧红》等。从作品表达的主题内容层面看,“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由开始时的单纯的歌颂鼓动转变为对现实更真实更深刻的描写。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对革命队伍内部那种消极腐朽现象的揭露和针砭上”,[9]但从“文化磨合”的视域去审视,丁玲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期后,深刻认识到现实的延安与理想的圣地之间相距颇远,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中所铭刻的个人主义、启蒙主义以及现实批判立场的五四文化传统与延安的革命集体文化、大众文化以及封建传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与冲突,“文化磨合”就随之浮现。《“三八节”有感》是丁玲在复杂的思想情感郁积下不可抑制的倾泻,是她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她因其得名,又屡次为其所累。
二、个人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启蒙立场与党的立场
在老中国,“个人”之语自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五四的实绩之一就在于培育出了“个人主义”的萌芽,所谓“人的发现”就是对人的“个性”的肯定。但中国革命的波折叵测却难为这株“个体”的秧苗提供培育的土壤,任其在风雪中飘摇。就延安的革命文艺“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论,几乎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与伦比,而它加诸文艺的规定、限制、磨折以至伤害,也可以说是前无先例后无过者”。[7]32深究其因,在延安领导的革命事业所统摄下的文学有其鲜明的内在规定性——即“党的文学”,“党的文学”一定是要为革命胜利的目标而服务,而革命本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行为,其所倡导的大众文化与所要求的集体主义原则必然会摒弃个人主义文化在延安的滋生蔓延。在整个革命集体强势话语的笼罩下,个体只有作为“螺丝钉”消融于集体架构之中,才能确立其价值存在,但却湮灭或重新装置了自我的个体意识,这确然是无可回避的矛盾。这种自我个体与革命集体的矛盾关系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所内在要求的,而延安文人对党的立场的斥离与服膺实则呈现出文化上的个人主义与革命集体主义的“磨合”之态。但五四发掘出的这种基于个体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启蒙立场早已成为不可磨灭的意识镌刻于知识分子心中,定然会循着革命集体的话语缝隙来实现个体自我的话语表达。当时延安的文艺政策与文化氛围是较为宽松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倡导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1941年5月21日《解放日报》社论《施政纲领——到群众中去!》指出要:“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0]但社论所谓的“自由”乃是党的文化意识形态下的有限的自由,这与丁玲理想中自由的限度存在着相当大的错位。“丁玲的性格与精神核心是坚守自我,追求自由,是以自由理想为前导的个性主义。”[11]而《“三八节”有感》便是她借节日的语境来排遣郁积情绪与个人话语的出口。
自从1942年3月9日《“三八节”有感》刊登于《解放日报》第四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篇杂文使丁玲受到了数次严厉的批判,并且还被定性为丁玲的反党材料。从丁玲作此文的立场来看,她是以一个延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与启蒙立场下对于延安的现实批判,对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以丁玲为代表的延安文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立场下的批判与讽刺是与延安文学的根本立场——党的立场是相违背的。这不仅仅是“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五四文化传统与延安革命文化传统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与“磨合”。
丁玲在受到批评后反思这篇杂文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那篇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那里只指出了某些黑点,而忘记了肯定光明的前途”[12]她在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是极力抨击王实味,“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12]72将王实味的问题与自己的问题相区别开来,①当时文艺界常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放到一起批评。她认为王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12]71但比较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他们的立场无二,揭露与讽刺的气力也颇丰,甚至丁玲的锋芒更胜一筹,还颇有鲁迅杂文的尖锐辛辣之感。但由于丁玲与毛泽东的私交等复杂的原因,“毛主席还是保了我”,[13]而王实味却因文获罪,只因康生一言,便酿成悲剧。丁玲是极为聪明的并具有很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积极表态:“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14]
但在丁玲的内心深处两种文化传统的“纠葛”与“拉扯”仍在继续,时刻折磨着她。“当我第一次听到别人批评三八节有感时,我的确非常伤心过,我以为那只应该有它的积极的作用的,我勉励她们自强。”[15]丁玲肯定自己站在个人的现实批判的立场与关怀女性的启蒙立场,“我非常感到受委屈,我的确只以为我的那些想头都是对的。”[15]110但她已经意识到环境的转移(从国统区到解放区)要求作家的角色与立场的转变,意识到她“失败的原因”在于“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不分开来看”。[15]110从而丁玲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下达成了某种妥协,“这不是好文章,读文件去吧,你们会懂得这话的意义。”[12]75但在丁玲的言语缝隙间,似乎显出一缕无奈与彷徨,这是她处于两种文化激烈的“磨合”下,必须要做出抉择的困境。“虽然个性主义在她的头脑中比较坚定,但由于《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的被批判,由于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的被牵连,特别是由于审干抢救运动中南京那段历史的被怀疑、被审查,她头脑中的个性主义还是发生了松动,产生了一定的量变。自此以后,个性主义在丁玲的头脑中开始处于一种矛盾状态,理智与本然相矛盾的状态。”[11]125终于,丁玲看清了自己之于革命所存在的矛盾,幡然悔悟:“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12]75
以丁玲为代表的承袭了五四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因其秉承的个人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启蒙立场与党的立场在文学创作与评价中的尺度和标准皆存在一定的偏至,从而在延安的文化场域内,在现实的惶惑忧惧之下对自己的文化立场重新定位。这是一种剥离之痛,但更是每个延安文人都要经受的文化“洗礼”。
三、女性解放意识与革命男权文化
“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察觉到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16]在民族解放与国家革命这样更为宏大的话语架构压制下,妇女解放事业便被“合理”地遮蔽,被置于较次级的地位。相比于五四时的浓墨重彩,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事业就黯淡得多。但却并非全如李陀所言“妇女‘解放’从来不是针对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而是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语域内,以男性为主体的革命力量在全面掌握革命话语权利的基础上,与革命达成默契的“合谋”,从而在延安确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民族革命文化,即革命男权文化。而这种革命男权文化本就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层面上占尽了先天的性别优势,又利用手中的革命话语权利去强调“民族解放”的优先级,诸如“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以期规避延安妇女问题的涌动与膨胀。
丁玲身世浮沉漂泊,幼年丧父,从小便随寡母于曼珍暂居舅父家中,尝尽寄人篱下的辛酸与封建大家族的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桎梏。但母亲的坚韧、自强以及九姨向警予、好友王剑虹等人身体力行的影响与熏染,加之在当时五四时期此起彼伏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丁玲自觉要肩起女性解放的重担,女性自强独立的意识便深刻铭写于她的生命,充盈于她的文学观念与作品。而丁玲后来向党组织靠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对妇女解放工作的重视。但当丁玲怀着五四的旧梦与革命的希冀进入延安后,觉察到了“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的幼稚,就不能不激荡起她那早已融入生命的女性意识,从而挣扎与呼号。
《“三八节”有感》是丁玲有感于当时延安两起离婚事件①一为陈学昭与何穆,一为朱仲芷与萧劲光。中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与现实困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为延安女性的发声之作,锋芒毕露地展现出她对延安妇女解放状况的强烈不满。开篇立题便质问:“‘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17]她以逆向逻辑去质询这种“重视”与“特别提出”实则是对女性问题的忽视与遮蔽,并以“什么时代”去质疑延安既成为革命圣地,却并未真正替妇女卸下这几千年的枷锁,这背后确乎存在着对延安极为理想化的期许,使得用情极切,笔力极深。丁玲欲扬先抑,揶揄地指出:“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但这种“幸福”仅仅是“吃得红胖”、“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但女同志仍要“幸运”于“应得的诽议”与“严重而确当的责难”。女同志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被物化成了男同志的附属品,无论是“骑马的”还是“穿草鞋的”,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总务科长”,女同志总要依附于她的丈夫而得以存在。[17]60
延安女性聆听着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17]60-62丁玲在此转述的话语显露出延安的女性地位与男性地位极不平等,这不仅是传统伦理观念下对女性的压抑与束缚,更呈现出五四文化的女性解放意识与延安的革命男权文化发生了尖锐的对抗与冲突。她以己自况,“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17]62丁玲反抗延安这种革命集体主义与男权主义话语下,女性只能作为生育工具、饭后谈资并为革命牺牲自我的存在,强调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女性有其自身的价值追求与理想抱负,她们本“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但却在革命集体的中必须去扮演“回到家庭的娜拉”。而革命者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表现出对“娜拉”们的轻蔑与不屑,“娜拉”却只能听之任之。但丁玲在文末对延安女同志的企望:“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这是她所秉承的女性独立自强的精神以鼓动延安女同志们的性别认同与独立意识,而文后附及所言:“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17]63但丁玲仍将其发表,这也确是在这极不平衡的文化力量的“磨合”中,对革命男权文化的强势地位进行挣脱的努力。
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磨合”的大背景下,聚焦延安这个相对特殊的文化场域,来审视进入延安的左翼文人所承袭的五四文化与延安在战时背景下所建构的党的革命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复杂纠葛的“文化磨合”关系是研究延安文学的一个新途径。“丁玲作为‘作家’与‘革命者’的生命历程,同时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践性的主体构造过程,即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开放性展开过程。”[18]作为“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在延安时期这种“文化磨合”下所激荡的文学才华就足以照耀文坛;作为革命的“圣徒”,延安无疑是她“净化”灵魂的“圣地”,怀揣着对革命宗教般的虔诚,她深入农村,终于写出了革命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这“磨合”之路伴随着惊心动魄、彷徨惶惑,丁玲“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12]75但这并非是一种所谓的文化上的“断裂”,文化于人的深厚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割裂”的分析模式更多是给予研究者以话语的便利,而知识分子在“文化磨合”中既无法放下五四的“身段”,又必须追随“延安”的“召唤”,从而以一种文化“中间物”的姿态对自我进行主动抑或被动地“创造性的转化”,最终在精神文化层面完成对自我的“超越”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