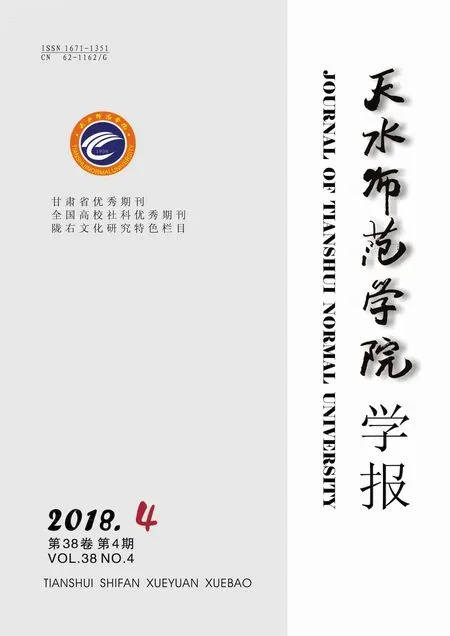批评家笔下的历史
——雷达先生散文创作的历史维度
张大琴
(兰州城市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散文,这些散文无论形与质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视野,不仅为他赢得了多项文学奖,也为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笔者大致将其分为这样几类:(1)童年及故乡记忆;(2)有感而发,是心灵在场和生命体验的产物,这部分包括许多篇旅行记;(3)亲历者的历史记忆,这是雷达先生独特的个人经历对历史的贡献,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凡引用雷达先生作品皆出自《雷达自选集-散文卷》、《皋兰夜语》和《黄河远上》,下不一一注出。
一
在讨论第三类之前,笔者先来谈谈第一和第二类。《还乡》应该属于第一类:童年和故乡记忆。文章记录了一段回乡经历,从记忆中的童年到如今乡村的现状,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拳拳之心。扯不断的亲情血脉,20年分离的隔膜,乡民自足生活中的新鲜脉动,尤其打动笔者的是一种朴素、真挚,贴合我们西北人情感表达特点的含蓄、内敛又心动于中的情怀。“乡贤第二”在故乡感到的隐隐的失落感与长期留居京华前呼后拥的反差,乡亲敬酒之后自顾自聊闲天的隔膜,以及本家侄女的新想法都鲜活地描画出了北方农村不变中的变,变中的坚守。《新阳镇》、《多年以前》等均属于此类,叙述儿时记忆,叙述父亲和母亲,叙述对故乡天水和兰州的种种认识,家族记忆与民族记忆交织,铸成一种独特的生命密码。
雷达先生散文的第二类是有感而发,与历史人文紧密相连,是心灵在场、生命体验的产物。我们常说,真正的文学应是生命体验的产物,是来自生活深处的心灵在场的情感表达。雷达先生散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作品都可归入此类。如《论疼痛》,“疼痛是灵敏的,它是生命发出的尖锐警报”,“谁藐视生命,疼痛就出来干预谁”;“疼痛又是公正的”,大人物和普通人的疼感并无二样;“疼痛还是智慧的”,让近于迷失的心灵如醍醐灌顶,学会重生轻物,顺乎自然;“疼痛更是多情的,它能使人变得敏锐、清醒,唤起人道情怀,回复本性良知,哪怕只是一瞬。”现代医学的进步是否使人类的抗击打能力大大退化了呢?“疼痛之袭来,与其说是在提醒人注意疾病,毋宁说在提醒人注意以灵魂为主的生命状态若何。”“我一向有种探究人的内心奥秘的欲望”,“文化传统和精神根基才是更稳定、更深层的支撑力”,“精神的存在有待一双精神的眼睛去发掘。”《论幽默》、《论尴尬》、《论牢骚》等均属此类。
雷达先生不但探究国人,也探究洋人,《置身西西里》恰似一次精神遨游,作者遨游在意大利文化的海洋中,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甚至历史传说,脑子中的诸多储备这时一起参与了这次文化之旅。体悟“任何一个民族,要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前行,就必然有它的文化根系。精神动力和宗教信仰,这些东西沉埋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虽然时移事迁,它那基本的框架却不会改变,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不会绝灭。”
雷达先生曾借用胡适先生“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名言来阐述自己对散文内容选择的见解。“听从心灵的呼喊,这就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但这并不排斥开掘、提炼、升华的重要。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天上的扎尕那》开篇提到曾为某作者写过序,当年因为其风格介于先锋和寻根之间不好把握,是硬着头皮写的,如今再见面却好像已成了一种功劳,双方都感慨万端。这个细节让笔者动容,没有粉饰,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朴质真切。作者和同行朋友流连在扎尕那的美景之中,“然而,尘世的另一只手从山外伸来,轻轻地拍打我们,小声说,快回去吧。”诗情画意流淌于字里行间,年过花甲的作者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激动,竟直接抒情了:“啊,高耸入云的扎尕那”,这声呼唤中蕴含着多少惊叹与感喟,“我的心是多么矛盾:我写文章,希望人们知道扎尕那的美,但我深知,一旦知道的人一多,蜂拥而至,它立刻就会变色变味。”既惊叹于扎尕那的美,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又怕知道的人多了会毁损她。一颗真挚透明充满了矛盾与犹疑的心宛然呈现于读者面前。他“希望知道扎尕那的人越少越好,迭部的变化越缓慢越好”,“但愿我的笔不要无意中伤害了你的纯洁无瑕和绝世之姿。所以我决定,关于你,只写此文,再也不写了,看不到的人就不要看了。”决绝之心中包含了多少未尽的情谊和爱惜,对此读者只能细细意会了。
雷达先生擅长从自我体验的角度,发现独特的美学体验,如对硅化木的观察:“若说它是石头,分明呈现着树的形貌,那弯曲的树干,鼓突的树皮,回旋的年轮,以至树节结,都跟真正的树桩毫无两样;若说它是树桩吧,其硬度、质地、重量分明又是一块道地的顽石。”对此他不由感叹到:“这真是生命与石头的绝妙交合,生命钻进了石头,遂化为永恒。”“这生死之谜作为极大的悬念,作为永恒的悲剧美,久久郁积在我的心间。我迷化石,主要就是迷的这种不可索解的美感。”硅化木“不可索解”的绝世之美对作者造成一种心灵的冲击,作为读者的笔者心灵也同时被冲击,“看啊,一批物种灭绝了,另一批新的物种又崛起了,开拓,发展,变异,进取,真是前仆后继,生生不息。谁的抗灾变能力强,谁就是胜利者。”他由硅化木联系到人类的宿命,“知道了这一宿命的人类,至少应该学会尊重规律,善待生灵,强化自身,切莫过早地被文明阉割了生机。”在《我在埃及拜谒法老》一文中他感慨:“任何一种生活都有它的意义,就看能不能感悟到一点人心的真实和生命的韵味。”是啊,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关键看你有没有一颗顿悟的心,人心的真实和生命的韵味是世界生生不息的源泉。
二
雷达先生创作的散文中,有一部分可归入亲历者的历史记忆,这是笔者前面所分的第三类,也是雷达先生半生经验的积累,是他阅人阅事无数而积攒的宝贵财富,独此一家。笔者也最看重这一部分散文的历史价值。这部分散文的代表作包括《王府大街64号》、《听秦腔》、《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悲情山川:废墟上的联想》、《皋兰夜语》、《黄河远上》、《费家营》、《韩金菊》等,数量不是最多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饱满而沉郁的生命体验用厚重质朴的语言呈现出来,自有一种打动人心魄的魅力。
《王府大街64号》记录了那一个历史瞬间,“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晕眩。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一切似乎没什么异常,可作者心灵中的一幕却蓦然出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巨响。”“我”本能地抗拒这个回忆,这和大多数国人目前对待历史的心态一致,遗忘、逃避,直至埋葬。可批评家的心智和良知没有抛弃他,他的笔缓缓流向那个记忆,流向那场情景。“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作者的思绪渐渐回到那个特定的时代,“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22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藉,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他回顾了那个年代的荒诞,“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他的梦想也在一点点被打破。涉世未深,心有余悸,但他的眼睛在这些现实中掠过,记录下了那一刻的画面。周扬、廖沫沙、冰心、田汉、臧克家等,有20多个人名吧,都是作协的人,有的很有名,有的我们未可知也,但这么一大批人受到冲击正是那一时代的缩影。他们受到冲击,惶惶不可终日。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注意到另一个年轻人的遭遇——作协一个年轻人的“意外”死亡,“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是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无独有偶,《南方周末》也刊登了杨匡满先生的文章《朱学逵之死》,[1]详细回顾了朱学逵负冤而死的细节,可叹可惋。此文跟雷达先生的文章形成呼应,是对历史的记忆和还原,也是控诉。除过记载朱学逵的死亡,他还记录了冰心等人被斗的场景,尤其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用有毛泽东主席画像的报纸包鞋,被作为罪证检举,那位检举者举鞋痛打刘芝明的情形历历在目,尽管这个人的名字和模样他已记不大清,但亲历过的人中总有人会记起这些身影,作为历史的阴影它会留存。“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作者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在自我扪问,在这样的时刻,“我”在做什么?最为怵目惊心的是批斗田汉的过程,“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一代宗师式的人物最终被逼迫跪下,那一刻,不仅作者心目中的一座圣像坍塌了,而且我们民族的脊梁也断裂了,“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滴血的心灵在呼喊。如果只是记录,那当然还不够,作者把王府大街六十四号看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吧。”雷达先生做的正是这种历史反思,“我心中的困惑并末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当年的“小将”“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至今并未见到一位干部、知识者、文艺家站出来为这场批斗披露自己当时的心迹,现场那么多人呐,人心的幽魅部分并未被照亮。“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当年疯狂攫取权力的人和今天疯狂攫取金钱的人并无二致,人性是一个多么幽深的潭渊啊!雷达先生的思索在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鼠疫》中找到了共鸣,“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2]里厄医生的担心正是加缪的担心,加缪的担心正是雷达先生的担心,这是人类的警钟,“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的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2]是的,“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雷达先生想挖掘历史幽暗处人的心灵,想探究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秘密,这也使他的亲历记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努力。真正的文学应是生命体验的产物,是来自生活深处的心灵在场的情感表达,《王府大街64号》有这个特质。
《听秦腔》是抒发作者心性的一篇散文,但由于秦腔在西北地区的特殊地位,此篇散文又有为秦腔存照的意味。“秦之声”属于陕西,但在甘、青、宁、新,秦腔的生命力更旺盛,他认为,“要揭开秦腔的生存之谜,必须站在整个西部的高度,不能光在西安老城墙周围打转。依我之愚见,地理结构重要,历史结构更重要,浑茫的历史感才是秦腔魂魄。说穿了,秦腔迷人,乃在‘苍凉’和‘悲慨’二点上。它善悲剧,不善喜剧;善伦理戏,悲欢离合的苦情戏,不善政治戏和理性戏。”他从西部苍凉悲慨的历史发展演变角度探讨秦腔风行的原因,“寻根乃是人类固有的情结,历史意识是现代人直观自身的表现,秦腔便是满足着这种欲求。可以说,秦腔是西部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伦理方式的艺术化、抽象化、程式化,只是人们不自知罢了。当今研究西部文学的,倘不知秦腔为何物,便无从研究,只能隔靴搔痒耳。”雷达先生从历史文化的高度探讨秦腔风行西北大地的奥秘,同时辅以自己痴迷秦腔的经历和茶园子里名角窦凤琴一腔震撼全场的插曲,让秦腔的地域生命力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作为文学评论家的雷达先生写了许多篇关于茅盾文学奖得主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是得奖作者尚未出名作品刚问世时的及时之评,返身再看竟有一种英雄识于未达时的欣喜,这当然反映了雷达先生在文学批评上的敏感与睿智。因为多次参与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雷达先生把他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的根根茎茎、枝枝叶叶写成《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这篇文章虽然收录在《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论文集中,但笔者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篇散文,因为它也是亲历者的叙述,充满了质朴感与历史感。雷达先生不厌其烦地把茅盾文学奖的相关方面一一娓娓道来,从设奖来由、获奖作品概况,直到这个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内部构建所起的方方面面的作用,如茅盾文学奖与关注中国社会广阔人生的多个层面、茅盾文学奖倚重宏大叙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对茅盾文学奖的未来期待等,既给读者介绍了茅奖设立的缘由,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也阐释了茅奖的文学品格追求,为这样一个国家大奖走向读者、走向大众提供了一个视角,也为茅奖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点,立此存照的意味很浓。
《悲情山川:废墟上的联想》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唐山大地震后山河破碎、生命荼毒的惨状,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取舍、提炼、拔高,这是地震后雷达先生作为记者在第一现场亲眼目睹的,这样的文字让我们对生命的本质重新认识。唐山和汶川,见证了中国的变迁,读者在雷达先生的笔下也见到了一个曾经的荒诞时代。知情权、透明度、允许国外的救援等,这一切的到来竟等了整整三十年。“经历过两次大地震的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对生命的高度尊重。一切为了人,人是高于一切的。”生命的珍贵,生命的平等从没有这样迫切地震撼过我们的心灵。
三
雷达先生晚年的散文书写越来越趋于一种化境,他挣脱了羁绊心灵的诸多顾虑,自由书写他的心灵史,在个人记忆中融入了家国、时代变迁中的密码,他写的“是活文,有生命之文”,是“平静下的汹涌,冷峻中的激活,无声处的紧张”。
《费家营》中那个边抬着石头走路边睡觉的少年,那个敢跳入黄河游泳的少年,那个因顶撞权威而被迫害的少年透露出一位幼年失怙的孩子心灵中永远的痛,但跟《新阳镇》《多年以前》中有所节制的叙述不同的是,在个人的惨痛记忆中增大了对周围事件的观察,借助一位少年的眼光,把“文革”前那长长的预备期展现于后世读者面前。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这应该是第一篇。“文革”并不是1966年才横空出世,早在1957年就已经开始预演了,只是规模不及1966年之后那样波及全民罢了。工农速成中学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当时时局的缩影。雷达先生最有见地的地方是把整人者最后又被整的历史循环呈现于读者面前,整人者中有天生的坏人,但也有最最真诚的信仰者,这提供了一种震撼心灵的脉冲波。校长赵奋生,那样一位左得离谱的坚定信仰者,最终并没有善终。有感于这篇文章,笔者查阅了工农速成中学后身的兰州城市学院的相关校史,竟然查不到赵奋生的任何资料,曾经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一任校长,就这样无声无臭地消失在历史无情的记忆中,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也是多么大的失落啊。
古人云:人生70从心所欲不逾矩,雷达先生70岁后的散文正体现出铅华洗尽后的历练、深入心扉的穿透力和回望历史的洞察力。这是个人记忆,更是民族记忆。发自心田,独抒己见,用自己的亲历作为基布,再加上宏观认识上的广阔,使他的散文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大气和深入历史核心的穿透力。《黄河远上》和《费家营》等已经在逼近这个核心,《韩金菊》则更加敞开心扉,袒露这个悲怆、悲愤、悲伤事件中个人的无助。初恋女友韩金菊一家和她个人的遭遇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际遇。先生用朴质的文笔和朴质的心情回忆过往的一切,将时代加于一个文弱少女和才女身上的重压一点一点呈现出来。令人心酸的是,这个女孩一直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适应生活加于她身上的不公,学习成绩优异却不被大学录取,退而求其次她参加了工作,工作中积极努力靠近组织,积极努力改变自己,但现实并没有给她留下一条活路,她心目中的救星自身也泥菩萨过河。她的死亡是必然,叹惋和追悔都不可能改变她生命的轨迹,这正是此文如迫击炮重创人的心坎的地方。雷达先生过了五十多年还保存着韩金菊当年写给他的信件原件,读着图片上朴质痛切的字句,看着那发黄发皱纸张上娟秀的笔迹,心中的痛不是言语所能表达。《韩金菊》可以说是先生的绝唱。
纵观雷达先生的散文,真挚贯穿于其散文创作的所有种类和始终,是雷达先生散文生命力强健的基础,他的所感、所思、所爱、所憎都掺杂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他的疑惑也是所有生命个体在时代狂潮中的疑惑。雷达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好散文》一文中提出写好散文主要还看“精神个体有无足够的感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摆脱传统压力的能力和辟创新境的能力,一句话,关键还在‘说话人’身上。”,他认为散文应该表现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原生性、流动性,而不是套话、假话、空话、大话,“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雷达先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他自己的散文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