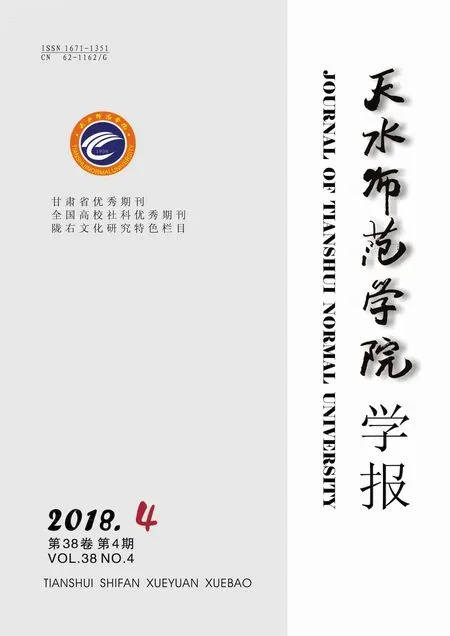雷达散文的小说笔法
薛世昌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雷达的小说评论,指点小说丛林之虎狼,啸傲小说江湖之风云,独步中国当代文坛,成就辉煌,有目共睹。雷达的散文虽较晚出手,但一俟亮剑,也是力道不同凡响,声名迅速鹊起。雷达的散文直出心源,胸臆纵横,酣畅淋漓而语言朴素,大有气定神闲之“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老衲”气度。古耜评价说雷达“他将忧患的思绪化作遒劲的笔力,叩问历史与现实,对话社会与人生,力求以饱含哲思与激情的审美化言说,实现精神自救,同时为喧嚣扰攘的物化世界,留下一片可以安置心灵的绿洲一一这庶几就是作为散文家的雷达。”[1]2但是“作为散文家的雷达”,却是一生读着小说、评着小说,而在常年累月的小说阅读与小说思考中,雷达对小说的笔法无疑会耳濡目染、深有所悟,当他进行散文写作时,无疑会自觉不自觉地汲取之并运用之。雷达散文的小说笔法,和雷达先生深刻的人生体验、深厚的人生情感、深湛的语言功力一起,共同营造出雷达散文细节生动、形象饱满、情节饶有趣味的散文世界。
一、雷达散文的小说笔法之一:“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雷达散文的小说笔法丰富多样,非止一端,举凡对人物语言、人物动作、事物特征等等的描写,其实处处显示着雷达深厚的刻画功力。比如他在《新阳镇》中就这样精准地描写老家当年的织布声:“……手则不停地抛掷着梭子,发出咔嗒-呱嗒-夸嗒的声音。”[2]5并生动地描写那些纺织娘:“见来客人了,她们会走下织机,腼腆地默立一侧。”[2]5这样的描写堪称绘声绘色。再比如他这样描写“铁路上的人”:“是穿四个兜儿制服,别钢笔,戴手表,用多节长手电筒向夜空中扫射的人”,[2]9三言两语,就抓住了人物特征,表现出雷达对小说笔法的心追手摹。
散文与小说同属文学文体,同样要写人叙事,但散文的写人叙事向称“非虚构”而小说的写人叙事也从来离不开“虚构”——虚构与否,是散文与小说的一个主要界限。虚构权的确立,自然为小说的人物塑造特设了前往“典型化”的绿色通道,也为小说的情节安排铺设了通往“传奇性”的红地毯,而“非虚构”也自然成了散文言说一条“细细的红线”,要求人们务必谨守。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所谓“非虚构散文”的概念,这种对散文“非虚构”品质的特意强调,在隐射我国当代那些“不真实”的散文这一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在本来就不能虚构的散文面前冠之以“非虚构”字样,这样的命名,不无重三沓四之嫌。当然,散文对“虚构”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同时也拒绝了“人物”以及“人物性格”、“故事”以及“故事情节”。有性格的人物和有情节的故事,并非小说的专利,也并非全都来自于虚构。事实上,生活本身时时刻刻都在化育着那些无需“典型化”而天生“典型”的人物,也往往会滋生出不必“传奇化”而本就“传奇”的人间故事(这让那些优秀的小说家也感到有所不逮、惊叹叫绝)。那些优秀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以及报告文学,甚至新闻与历史,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类天生尤物与天籁之音的存在。所以,如实地讲述这样的现实生活,如实地描写这样天造地设的人物,如实地进行这样“非虚构”的叙事,其实并不影响和伤害散文的写实品质。。雷达先生写作了大量记人叙事的散文作品,他的这类散文从来没有跨越“非虚构”的言说红线,这是雷达对散文本分的谨守;但有时候,我们仍然会在他的散文中与那些不无波磔的情节、非同凡响的人物邂逅相遇,这又是他的散文中小说笔法的运用。
比如雷达在《新阳镇》中就说到过这样一个“意外”:“小时的我会盯着水磨一动不动,听水声喧嚣,看浪花狰狞。四岁时,热衷观赏水磨的我,终于滑入了水渠;人进入磨道,不但必死,还得血肉横飞,但我幸运地被人救起了,成为乡间一佳话。”[2]5这是颇具传奇性的讲述。他这样讲的时候,几乎“站在了小说边上”。如果往前再走几步,比如他“听说”救他的竟然是一个他家的仇人,他们两家因此而冰释前嫌,那就俨然是小说了;如果他甚至“听说”是一位来无踪去无影的过路僧救了他,那简直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了。当然,雷达并没有这么做。他及时地“悬崖勒马”而未出散文之疆域。还是在《新阳镇》中,雷达又说到一件事,这个就更奇了,然而终归是真的:“1949年冬,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某部进驻新阳镇,后又撤出。我当时虽只六岁,记忆清楚。团部设在阎家场,连部就设在我家。解放军改善伙食爱吃粗粮饺子,用木桶装,每次总不忘用马勺给我盛上一碗。但春节之夜却出了大事:那晚军民联欢,院子里吊着汽灯,军队演一活报剧,剧情高潮时,‘革命者’要用枪‘打死’‘叛徒’。谁知那天枪里有真子弹,砰的一声,对方真的被打死了。当时一片混乱。死者被用门板抬向团部急救未果,而开枪者当即被控制起来,就关押在我家的小耳房里,日夜有人看守。第二天,被打死的那位文化教员,装了棺材,在广场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而那个开枪的人,一周后在山根下被枪毙了,定性为故意杀人。这支部队的老战士们,料应记得这一段公案。”[2]8在读到这段叙述之前,只听说有当年的陕北有战士在看《白毛女》时开枪打死了“黄世仁”,却没有想到在偏僻的陇上小村新阳镇竟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对此白纸黑字的记述,人们难免半信半疑。雷达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也估计到了人们的怀疑。他的“虽只六岁,记忆清楚”八字,就是说给怀疑者听的。这仍是一次“站在小说边上”的叙事。雷达一定是这样认为的:散文叙事当然不应该“为文造情”而去编造杜撰,但如果真有这般的“准传奇”,为什么不能顺水推舟、因“奇”就“异”呢?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卷首“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有言:“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雷达不是小说家,他无意于“寻找传奇”,但要是他正好碰上了传奇,他显然并不惧于传奇主人之普通,他显然乐于为普通人传扬其奇。而且这并不影响雷达对散文的理解。他识得散文之大体,知道在那个叫做散文的世界里,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怎么说,不能怎么说,他也知道如何借鉴小说的笔法而让散文拥有某种“小说味”,并知道如何适可而止地保持散文与小说应有的距离。
但是雷达的这种分寸感并非机械呆板,当情形需要,他也会勇敢地越过雷池。一般而言,我们都应该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但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在讲述对待自己近乎是母亲一般的大嫂谢巧娣时,雷达却偏偏放笔写来:“大嫂……为人刚强,泼辣,能吃苦,敢踢敢咬……”,[2]10这“敢踢敢咬”四字,雷达用语果断、大胆,几无顾忌。还有接下来的描写:“一次在陕西,她用土布和一件旧皮袄换得一些粮票和一小袋面。不料这家人忽然要她留下来当‘女人’。嫂子哭着说,我家有哑巴男人和快饿死的儿女呀,陕人却不放;其人与嫂子在土坑上‘相持’了很久,实为一场搏斗,陕人竟不敌。嫂子趁势扛起面袋夺门而逃,不顾恶狗追咬,连夜扒上运煤的货车。下车时人乌黑得与煤炭无异,当然也就躲过了检查。嫂子说,她再也想不起那是陕西的啥站啥地方了。”[2]10-11如果是一般人,如果是道德至上的伪君子,他必然会在这些地方下笔踌躇甚至遮遮掩掩,但雷达却表现得雷厉风行、率真果敢。毫无疑问,雷达秉持着另一种更为深刻伟大的道德,那就是真实。雷达知道,他必须叙述出生活那种连泥带水的原生态,也必须描写出人物那种可歌可泣的血肉形象。只有写出了这种真实,才是对自己那位可敬的大嫂最高的敬意。雷达知道真实的意味,也知道真实的价值,他更知道平凡人的尊贵之处,绝不只是尊贵于那些可以言说的事迹,同时也尊贵于那些难以言说的事迹。
二、雷达散文的小说笔法之二:适度的延宕叙事
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几乎可以说也是延宕的艺术,优秀的叙事,几乎都是延宕的叙事。美国剧作理论家悉德·菲尔德说:“一切戏剧都是冲突。如果你已清楚自己人物的需求,那就可以设置达到这一需求而要克服的种种障碍。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就成了你的故事本身。”[3]他所谓的“障碍”和“克服这些障碍”,简言之,就是叙事的延宕。雷达的散文虽然没有讲述过多么激烈的戏剧式矛盾冲突,但是他的延宕叙事却仍然随处可见,且运用娴熟。比如他的《还乡》,讲起让他唏嘘再三的回老家故事,就是延宕再三。
《还乡》是雷达散文中小说味较浓的一篇。一次平常的回乡之旅,被雷达叙述得颇不容易,一路上充满了艰辛,风未息,水又起。先是坐火车遇到意外的艰难,然后是见到亲房侄子后感到意外的失望,然后是见到村子里人时那种意外的隔膜……,故土渐近,然而故人渐远,乡音渐近,然而真情渐远……雷达以最后的离开结束了自己的讲述,且隐隐地传达出这样一种可称之为“现代乡愁”的忧郁:家乡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如此人物的意愿与实现这一意愿之间的重重障碍,既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理应延长”的“感受的难度和时延”[4]亦即金圣叹所谓的“极忙极热之文,偏要一断一续而写”。[5]这一路写来摇曳生姿的延宕文字,无不表现着雷达对小说笔法的深谙。
延宕,虽有暂时的搁置这一语意,但它并非就是中止,而是“一断一续”、断断续续,它其实指的是写作行文时摇荡多姿、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动作特征。在散文写作中,运用适度的延宕,无疑可以让散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义理自然,姿态横生。”[6]获得散文之“散”那种“思骛八极”、“视通千载”、随体赋形的言说风度。雷达对此,显然是心照不宣,多有尝试,比如他的《梦回祁连》有一段,写几个人轮流批判他,“第一个骨干发言,他严正指出……”,“第二个骨干是对我比较了解的人,发言的分量比较重……”,“第三个发言者却不是骨干,但脸色更加严重”,树欲静,然而风不止,他的老师还要来一个“简短的总结”——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总结……。在这种堪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相媲美的叙说中,雷达几乎对小说家笔下常见的“延宕”手法心领神会,运用自如。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延宕理解为行文时流变过程中的“曲折”,则雷达对此“曲尽其妙”的笔法有着更为深刻的领悟。他在《走宁夏》中讲到过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曲折过程。他先是说:“许先生是考古专家,也是最早的岩画研究者,据他说,贺兰山岩画的发现过程还有段曲折呢。那是……,最后岩画毕竟找到了,但是否还是那条山沟的,已不得而知。这过程很有趣,我怕是许先生的小说家言,追问确否,他咬定是真的。”[7]这段话可以证明雷达对“小说家言”的理解之一,是“虚构”,否则他不会“追问确否”;理解之二,就是“曲折”,否则他不会说“这过程很有趣”。正是在这般艺术认识的明确导引下,雷达的散文才会有逶迤的文字,才会有一波三折的叙事,也才会有如沐春风的审美愉悦。
叙事的河道里奔跑的是情感的水流,雷达散文的情感之河一般都是缓缓汩汩而轻快的,但也不是没有风云突变的时刻与艰涩滞重的变调。雷达感人至深(须端坐敛衽而读之)的散文《韩金菊》即是如此。此文前半,作者尚在给天下读者讲述他和韩金菊的故事,到了后半,不知不觉,雷达的读者从大众变成了一个人——韩金菊。公开的讲述变成了私密的倾诉。细心的读者应该能注意到,在《韩金菊》的后半,雷达的语言甚至变得不那么通顺了,造句也涩滞迟疑,甚至有衍文及词不达意的现象。这看似与著名小说评论家的语言能力有些背悖,但恰恰契合着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艺术直觉。《韩金菊》的后半能让人联想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二者有着情感与行笔的多端相似。它们都是“天下之至文”:情奔意突,心悲手颤,脚步踉跄而语有哽咽——踉跄与哽咽是生命本能的延宕,是延宕中最天籁的延宕,是延宕中的“元延宕”:世界上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呢?生活最真切最真实的呈现,不只是粗粝的,而且是延宕的。我们对此并不缺少感受,我们只是对此缺乏认知。
和雷达散文对传奇叙事的分寸感相呼应,雷达对延宕的追求也适可而止,并不刻意地吞吞吐吐。相反,我们在散文中看到的,常常是健笔纵横的雷达:放纵着自己的思绪,任从着意识的流动。用古耜的话说,就是“敞开着内心,袒露着灵魂。”[1]4这让雷达的散文获得了轻快的节奏,读来感觉灵动。虽然他不时地借用小说的笔法,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故事叙述得像小说一样风声四起、波诡云谲;虽然他识见渊博,但他也没有把自己的随笔写得评论一样引经据典、思辨圆通。作为以腾挪闪展为言说追求的散文家,他没有在任何一个有可能陷入的地方多加留驻,而是及时地抽身离开,在点到为止之后,马上逸笔他往,脱身而去——或叙述,或描写,或抒情,所以他的散文写得不滞不呆也不累,极显笔力的洒脱与劲健。
三、雷达散文的小说笔法之三:合法的自叙冲动
莫言曾讲述过他对小说的一个顿悟故事。他说他在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创作谈《小说的方法》时,看到大江健三郎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一句话:“我是唯一的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圣经·约伯记》1∶15,或译作“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莫言说他看到这句话时突然对小说有了一个感悟:“自信的口吻”。[8]所谓“自信的口吻”,即讲述者认为自己且只有自己是知道真相的,于是自己就是那个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讲述者,换言之,莫言感悟到的,就是古往今来作家们神圣的责任感:你是那“唯一的一个”,你要是闭口不说,真相就会湮没而风流云散。
其实曹雪芹早就意识到了小说家“当仁不二”、“舍我其谁”的这一言说使命,《红楼梦》第一回落笔伊始,就透露出它的写作动机:“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我末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红楼梦》第一回)。显然,曹雪芹为了让那些“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的“闺阁中”奇女子其人其事不致“泯灭”,于是就“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曹雪芹分明地已经认识到:自己就是那“唯一的一个”。自己要是不说,有点对不起那些“水做的骨肉”。
曹雪芹、大江健三郎、莫言,他们的事业就是这种挑战“泯灭”的事业,他们或“虚构”,或“敷演”,奋其一生讲了许许多多“别人的故事”,却往往疏忽了“自己”,且常常落入到那个人生的魔咒:编席的,睡光床。作为一个专门讲故事的人,他们常常却顾不上讲述一下那个不无生动的自我,或者在讲到自己的时候不知如何措词。悬念片大师希区柯克拍了那么多“别人的影像”,他是如何让“自己的影像”跻身他的电影的呢?他会扮成公共汽车上一位与剧情无涉(但也格外特写的)乘客,他会把自己的头像嵌入到主人公喝咖啡时阅读的那张报纸上(当然得有一个特写)。希区柯克这种幽默的标志式地闯入和镶嵌,其实泄露出艺术家一个心底的秘密:他们其实有一种“自拍”的冲动——有一种自己讲述自己的冲动,有一种自叙传式的冲动。许多红学家都认为《红楼梦》其实就是曹雪芹的“自传”,他们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曹雪芹的自叙冲动。甚至有人宣称:“一切艺术家所作,无非自传。”[9]这样的说法显然夸大了艺术家自拍的愿望,但也有艺术家自拍事实的根据。然则小说家可以借助叙事的方便在作品中给自己弄一个“化身”,导演们可以把自己悄悄地塞到电影里来个亮相,那么其他人呢?比如学者们呢?比如一生都在给他人写作小说评论的雷达先生呢?夜深人静之时,风烟俱净之处,他难道不也想说一说自己吗?
人的自叙冲动源自于人生一个强大的“原欲”:对“生活在别处”的渴望。美国散文家和牧师塞缪尔·麦考德·克罗瑟斯专门写过一篇随笔《人人想当别人》,来表达他对“人人想当别人”这一“人类的通病”多方位的观察。他当然说到自己对文字工作者所谓能诗又能文现象的认识:“人人想当别人这一事实,也是艺术家和文学家频频跨界的原因。”[10]495当然他也深入地分析了“人人想当别人”的深层心理。他说,甚至“在最成功的人心里也有这样的私密空间,那里隐藏着他未酬的壮志、未竟的心愿、未能践行的诺言。他所有有望实现的梦想都隐藏在心底。他说什么也不会愿意让公众知道他多么在意那个不曾大显身手的自我。”[10]498也就是说,“人人想当别人”,是因为“人人都认为还有另外的一个我”——如果我自己不说出那个另外的我,那个另外的我甚至那个真相的我,就将湮没无闻。塞缪尔所说的“人人”中,当然应该包括雷达。
和其他人一样,雷达也有着自拍的愿望与自叙的冲动,而且他也早已将这一愿望付诸了行动:他的那些记叙自己生平事迹、行踪心思的散文与随笔,就是他自拍的证明,就是他的自叙式写作。而且雷达的“自拍杆”就是散文。散文,自古以来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之最方便的文体,散文家毕其一生的创作,就是要塑造出“自己”这一个“人物形象”。之所以散文家的队伍是成员最为复杂的队伍,之所以科学家、教育家甚至政治家、商人等等几乎所有的人,当他们有话要说,有事要讲,有情要抒,有意见要表达,他们不去碰小说,不去碰诗歌,却来给散文添乱,就是因为他们看中了散文的这一大好处。甚至小说家有时候也会赧颜来借用散文这个“自拍杆”,来给自己搞些“自画像”。这一切都是因为散文之于自叙冲动的实现,是那样的堂堂正正,合法合规、合情合理,而且多所兼容——医生的手术刀般的精准、教师的循循善诱的口才、画家的飘逸线条与浓墨重彩、外交官的闪烁其辞和语言逃脱术……种种笔法,其于散文,不仅无妨,而且有助。当然也包括小说家的笔法。
雷达散文中涉及到“自叙”的篇章不少,涉及到“自叙”的段落更多,它们分别描述着雷达人生的一些碎片,或童真,或纯情,或机智,或深刻,当然有时候也狡猾,也老好,也吞吞吐吐……,但是把这些碎片合起来,一个“人生的确证者”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一个平时在对他人小说的评论中确证自我的人,现在,他要在对自己生活的记叙中确认自己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散文写作,呈现给人们与后世一部关于自己的“写真集”,他要讲述出真实的时代里、真实的世界上、真实的人群中,那一个真实的自己。甚至我们都可以这样推想:雷达之所以要写作那些涉及到生地、故乡、父母、亲友等等的散文,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些话(有些不能在小说评论里说的话)要通过某个合法的适当的方式对人世也对后世做出必要的交代。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雷达也许觉得:散文被认为是一个人公开的留言。
北岛在谈到他之所以要写那些行旅散文时曾这样说:“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代不清的。”[11]诗歌说不出北岛的全部,小说评论也说不出雷达的全部;只有诗歌传世的北岛是有所担忧的,只有小说评论传世的雷达也是有所担忧的。有朝一日,我们都会搁笔闭嘴而失去话语权,有朝一日,关于我们的那些事情,人们不知会如何胡乱地猜想与描述,于是,自拍的、自画的、自叙的冲动也就成了必然,散文的自传性也就应运而生且成为合法。虽然雷达说:“我写的并不单是我,我写的是一种生存相。”[12]200雷达这是看到了散文与小说共同的概括性,但雷达也看到了散文不同于小说的个别性——雷达同时也说自己十分认同蒙田的这句话:“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无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12]200其实,散文即使写了他人,那也是间接地写了自己。苏珊·桑塔格说:“(诗人的散文)向别人致敬,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对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入粗俗的自我主义。”[13]她说的虽然是“诗人的散文”,但她所说的道理却也适用于“小说评论家的散文”。
“粗俗的自我主义”当然是需要避免的,但对“自我主义”本身却不必讳莫如深。散文天生就具有私人化的色彩并一直坚守着这样“自已”的本分:自己有什么,就写什么;自己有什么样的,就写什么样的;自己没有的,却并不从别人那里或窃或借。小说可以借鸡下蛋,散文是自己的鸡下自己的蛋。散文要站稳脚跟,不能迷失了自己的这一本性。近年来,有些作家虽然占据着“典型化”与“虚构”两大神器不用,却在小说中喋喋不休地述说着个人的、私人的东西,有的散文家也偏偏要相向而动,要去从事小说家的“未境之业”,去别人家里搞什么“跨文体”。但是雷达先生却是心明眼亮看得明白,雷达在说到鲁迅散文的时候曾谈过这么一个认识:“那数不清的星斗般的篇章,到处都会遇到直接源于生命和实践的感悟,它们是一次性的,只有此人于此时此刻才能产生,因而反倒永远地新颖,历久而不褪色变味。”[12]196从空间上看,散文是“个人性”的,从时间上看,散文也确乎是“一次性的”,是属于此时此刻的此人的。产生于此时此刻此人,偏偏却获得了永远的新颖、不褪不变的色与味,散文迷人的魄力之一,宜乎此也。
四、结 语
散文的文体边界最为模糊,最具大象无形、有容乃大的风范,是故散文也是一种最稳定的即最不谋求什么“现代性”或者“探索性”的文体,最适合那些真正的探索家来此“与世无争”地休憩,于是也最适合于雷达。雷达自己也说:“我写散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兴来弄笔,兴未尽而笔已歇,没有什么宏远目标,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于是零零落落,不成阵势。我写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12]200他的这一认识与诗人于坚的看法款曲暗通。于坚曾坦陈:“在散文上,我是后退的。我是要回到最基本的说话。”[14]雷达可能对于坚的诗歌及其文学观点了解不多,但是他们对散文的这一保守性认识,却是英雄所见大致略同。他们之所以敢于“后退”,敢于“创作的因素较弱”,自然地有着他们言说的自信。于坚的自信源自于他举世闻名的诗歌,雷达的自信无疑源自于他雷声隆隆的小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