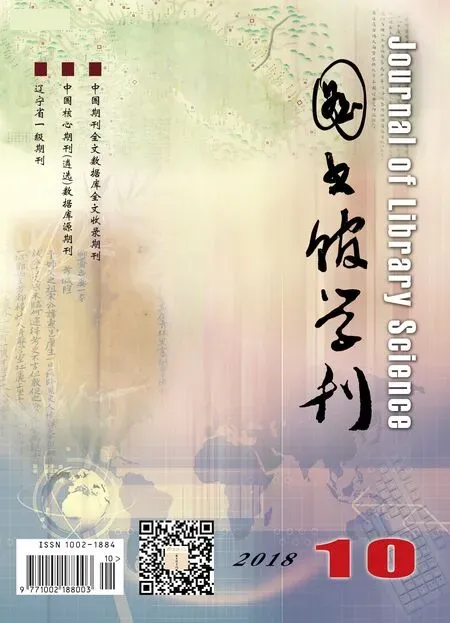金毓黻与民国《奉天通志》的编修*
曾沁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420)
金毓黻(1887~1962),字静庵,辽宁辽阳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东北文献学家及考古学家,曾任奉天图书馆馆长、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国史馆纂修、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等职。1928年11月起,金毓黻担任奉天通志馆纂修,“九一八”事变后临危受命,出任《奉天通志》总纂。他将修志视为志业,曾主持编修《东北文献征略》《辽海丛书》和《渤海国志长编》等史志,辑录《大元大一统志》等志书,并通过学界交往与学术传承,推动修志理念革新与方志体例创新。而在伪满当局的高压下,金毓黻带领奉天通志馆人士,克服种种困难,奋力编修志稿,历时七年终于完成民国《奉天通志》的编修与印行工作,为东北地方文献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 从纂修到总纂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统一局面,为全国修志机构的创办提供了客观条件。次年10月,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呈文,提出各地通志“应令行各省设局修理”的建议。[1]此议直接推动了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出台。1929年12月,《修志事例概要》正式颁布,要求“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2]《修志事例概要》以国民政府训令形式下达全国各地,由此构建了一套国民政府内政部统一管理,地方政府直接负责的通志馆运行体制。
就在国民政府发起修志之时,奉天通志馆于1928年11月1日率先成立。白永贞、袁金铠分别出任奉天通志馆正副馆长,王树楠、吴廷燮、金梁三人担任总纂,金毓黻被聘为通志馆纂修。[3]奉天通志馆人士采取“合县为省”办法,大规模征集各县资料,为志稿编修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而经过广泛延聘人才,通志馆已将诸多“史志专家”聚集到一起,为编修志稿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4]
时至1930年,正当通志馆的资料征集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编修计划却因时局动荡、人事调整、经费削减等原因而被打乱。是年1月21日,金毓黻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次年5月,金毓黻补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5]与此同时,辽宁省又因1930年4月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以及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面临日趋严峻的动荡时局,通志馆被迫闭馆。
伪奉天省政府成立后,奉天通志馆于1932年2月恢复办公。复馆后,鉴于全志“门类太繁,材料太多,整理编订极费时日”,而多达一百余卷的志稿编修重任,更与修志经费的锐减形成强烈反差,对此总纂吴廷燮与馆内职员均“望洋兴叹”。在此背景下,通志馆不得不调整人事与编修方案,遂增聘精于“文献掌故之学”的金毓黻为总纂,同时制定“增聘纂修专员,缩短成书时日”的办法,期以“最短期间可望成书,更拟于略事整理之后,筹备付印。”[6]
需要指出的是,金毓黻出任总纂一职,虽为增聘,并且要求“与吴总纂协同办理”,但由于各种原因,金毓黻成为《奉天通志》编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据郭君的《东北文献学家金毓黻》称,“由于编辑人员大多离去,余下的少数人年已皆老,馆长白永贞六十八岁,总纂吴廷燮年过七旬,很难承此重任,急需得力人员从事志稿后期工作,否则志稿有散佚之虞。此时金毓黻年方四十有六,正当壮年,又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修志经验,在白永贞、袁金铠的推荐下,担任了通志的专职总纂。”[7]
2 志稿编修与印行
作为通志馆总纂,金毓黻奋力编修志稿,此举调动了通志馆上下的积极性,大家按照分工协作,夜以继日地编修志稿,由此使志稿编修的进度与效率大幅提升。根据金毓黻日记记载,7月14日,他收到奉天通志馆的邀请函,次日即与原总纂金梁、馆长白永贞等商讨“人物志”编纂问题。[8]而从8月8日开始,金毓黻“逐日到通志馆办事”。[8]自8月11日起,他“逐日整理通志稿”。[9]随后,他将工作重心放在“大事志”、“沿革表”的纂辑上,至 12月初,“大事志”10卷全部完成。可见,金毓黻主持编修工作后,《奉天通志》成书有望。
资料是地方志编修的基础,历来为修志者所重视,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广泛搜集。奉天通志馆人士在金毓黻主持下,大力开展资料征访工作。1934年成立的国立奉天图书馆收纳“东北大学、冯庸大学、萃升书院等各处藏书”,并将沈阳故宫博物馆所藏书籍移至图书馆,由此使图书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旧档史料”、“善本书志”以及新购“殿本”、“满蒙文”、“八旗人著作”等图书总量达2080种,88344册。[10]值得一提的是,奉天通志馆馆长袁金铠、总纂金毓黻分别兼任图书馆馆长、副馆长,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为编修《奉天通志》奠定良好的资料基础。
与此同时,金毓黻以撰辑“大事志”为契机,广泛参阅奉天通志馆所藏《清德宗实录》、《宣统政纪》等文献,并借来馆之机不时与吴廷燮、金梁等通志馆前辈相商。如在给吴廷燮的书信中,金氏以弟子身份,报告其“近来赶修《通志》,将旧稿加以增补,大约大事、沿革两志不日即可定稿”的情况,并就“疆域、山川、选举、职官、金石、艺文诸志”所遇资料缺失问题,恐“为人指摘”等忧虑,请吴氏给与指点,由此为志稿编纂的质量与进度提供了重要保障。[8]
在撰辑志稿期间,金毓黻一度“宿于志馆”,持之以恒,加以撰稿,“日尽十纸,偶有寸得,郁抱为开,书卷之外,别无所乐”。[8]可见,金氏以修志为业,表现出专心编修《奉天通志》的敬业精神。事实上,金毓黻之所以将修志视为志业,与他所处环境有一定关联。据金氏自称,他一生志趣所在,不在政治,虽误入政途,但一心向学,尤其是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后,不愿为伪政权所用,遂借编修通志之名,辞去伪政府的所有职务。
然而,受时局动荡与政局更迭等所限,志稿编修进度并不尽如人意。时至1934年9月17日,尚有119册“应缮之稿”,约297.5万字,全部志稿清缮完毕,其工作量以字数计,约为727.5万字,据此可知,修志任务仍十分艰巨。[6]为加快志稿编印速度,金毓黻等人决定采取“且编且印办法”。而在纂辑“大事志”的同时,他还对吴廷燮等人所编“东三省沿革表”“人物志”“沿革志”“艺文志”“金石志”等加以校阅或补录。
经过金毓黻与通志馆上下的共同努力,至1935年6月,《奉天通志》的编修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沿革志、氏族志、田亩志、礼俗志、职官志、物产志、实业志均已校成定稿,拟提请付印;大事志、山川志、民治志、选举志、交通志、人物志也“行将脱稿”,而艺文志、金石志、建置志、疆域志、财政志、教育志、军备志则由金毓黻召集馆内同人加以“补辑”。为确保志稿质量,金毓黻亲自承担“艺文志”的纂辑工作。[6]
按照“编印兼行”办法,《奉天通志》编修与印行预计“需二年期限。即使积极进行,提前完成,至少亦需一年半之期限。”[6]然而,伪满当局以志稿编修延期为借口,于1935年编制政府财政预算时,却未将修志经费列入其中,后虽经金毓黻等人再三催请,伪满当局勉强答应补拨经费,但明确表示修志经费自1936年1月以后“即不支给”,通志馆工作“势难再行延期”,不得不“及早办理用资结束。倘届期不能完竣时,亦决于本年十二月底实动封闭。”[6]
在伪满当局的逼迫下,通志馆人士惟有克服各种困难全力编修志稿。经过通志馆上下共同努力,1935年历经波折的《奉天通志》编修工作终于完成。成书后的《奉天通志》,共刊印260卷10函100册,洋洋数百万言,是一部关于东北地方历史与文化记载的重要文献。
3 学界交往与理念革新
围绕《奉天通志》的编修,金毓黻与全国各地修志人士鸿雁传书、函电往来,大家就志书编修问题相互请益,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逐渐形成方志学界交流互动的良好风尚,并有力推动了修志理念的革新。
1935年,张国淦所撰《中国方志考》脱稿。是年5月,张国淦置身于“北平图书馆阅览室”,撰写《中国方志考》叙文,其时,他对“方志之义例”、“方志之学”以及“方志目录”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1]而在主持《奉天通志》编修工作期间,金毓黻经了解得知,远在北京的张国淦“近年专研方志之学”,遂与其保持书信往来,就志书编修问题互相探讨。据1935年11月15日金毓黻在其日记中称,“近得来书谓所撰《地方志考》已脱稿”,遂与张氏联系,请其“寄来《辽东志》补页二张,此系自顺德李氏藏本钞出,日本红叶山文库本缺此页,兹得补出,则成完璧矣。”[8]
在方志界交流互动良好风气的推动下,大量有关方志研究的论著应运而生,这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方志理论的创新与发展。1935年,李泰棻《方志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十四章的篇幅,论述方志“定义”、“定名”、“沿革”、“编体”、“用途”、“内容”和“资料”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李氏对《武功县志》《朝邑县志》《吴郡志》等在内的七种旧志进行评判,并详述章学诚修志的六个“不当”,目标直指章氏修志“志例驳议”。[12]显然,李泰棻以近代方志转型的理念,批判地继承前人修志思想,对方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无怪乎当时有书评称:“方志之本质安在,迄今罕有论述;有之,自李泰棻之《方志学》始”。[13]瞿宣颖在评论李氏《方志学》时,亦不无赞叹地说,“李君这部书,还是讲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14]
这部堪称“讲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引起包括金毓黻在内的广大修志者的高度关注。金氏通读全书后,认为李泰棻阐述的修志理念“颇有助于修志”。[23]同时,金毓黻还注意到李氏“颇精于古代甲骨金石文字之学”,但书中关于“记录的资料之鉴定法”、“记录以外的资料之鉴定法”、“记录资料之整理方法”以及“记录以外的资料之整理法”占据四个章节,虽“谈甲骨,文字极详”,但所述内容竟达整部专著的一半之多,以至令读者产生“似方志学之所重在此者,则失之喧宾夺主矣。”可见,金毓黻在借鉴和吸收李泰棻方志学理论之时,还根据其自身学识与修志经验加以审视。而其日记所述“近日又读李泰棻《方志学》”,以及数度记载阅后感想,则进一步表明金毓黻对方志学理论的关注与重视。[24]
无独有偶,1935年另一部关于方志学研究的专著,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年12月,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以篇章结构系统阐述方志的名称、种类、起源、发展、性质、功用、价值、地位等,为构建方志学理论体系进行初步尝试。[15]金毓黻通览全书,并将其与李泰棻《方志学》进行对比,认为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其分疏之明,条理之密,实胜于李泰棻之《方志学》。盖李氏之作,纯任主观,属于方志学之要项,多未道及,不若傅氏之多任客规,取材较为丰富也。”[8]
可见,金毓黻在借鉴方志学家的修志理论之时,并非毫无取舍地通盘吸收,而是根据自身修志经验与时代特色、地方特征等,在《奉天通志》编修实践中辩证地运用。同时,他注意与方志学界保持交流与互动,通过互相请益、相互借鉴、各取所需,使方志编修理念推陈出新,进而实现修志理念与方法的创新发展。
4 学术传承与体例创新
金毓黻主持《奉天通志》编修工作期间,积极倡导尊师重道的良好风气,他不仅拜通志馆内前辈为师,向他们虚心请教学习,逐渐形成敬重方志学界前辈的良好风气,这不仅有利于志书的编纂,而且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得以传承。
在奉天通志馆中,总纂金梁是总裁张学良的老师;馆长白永贞既是通志馆总裁张学良的恩师,也是继任总纂金毓黻在辽阳求学时的县立启化高等小学堂校长,有师生之谊。同时,金毓黻曾以“弟子”自称,拜通志馆首任总纂吴廷燮为师。
早在主持编修“大事志”、“沿革志”之时,金毓黻曾就编纂体例革新问题进行过一番探索与思考。由于历代修志多采用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其中纪传体仿正史而作,体例遵循目以类归,层次较为明晰;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史事,常见于史书、大事记、沿革志中;纪事本末体则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加以汇集。由于“大事志”和“沿革志”等最初由总纂吴廷燮负责,金毓黻续任总纂后,虚心向前辈请教,在体例上延续吴氏沿袭“旧稿而略有增损”之法,并不时就编纂方法与体例问题向吴氏致函,请其“予以督教”,这体现了奉天通志馆人士敬重前辈的良好风气。[8]金毓黻虚心接受吴氏教导,在“大事志”的编纂体例上“用编年体”,由此使全志体例“颇有条理可寻。”[8]
与此同时,金毓黻广泛翻阅和参考旧志,研习旧方志学家修志方法与方志理论,并结合自身修志经验,对相关理论的优劣进行评判,在此基础上,辩证地借鉴与吸收前辈修志理论,由此使《奉天通志》编修体现出求“新”求“变”的特征。
首先,金毓黻既借鉴和吸收前辈修志思想,又因地制宜地加以革新与改造。金毓黻颇为看重章学诚的方志思想,认为章氏在《方志立三书议》中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等,“此虽创论,实洞制作之原”。为此,他不仅提倡史志合一,还在章学诚三书(志、掌故、文征)之外,创设“四例”,即专著、杂志、文征、存目,认为“三书立而方志之体始备,四例创而丛书之用始宏”。[8]
其次,金毓黻十分注重方志体例的革新。早在1934年主纂“大事志”时,金毓黻就在志书体例上求“新”、求“变”。他注意借鉴清代谢启昆所修《广西通志》的体例形式,认为“《广西通志》大变旧体”,以“人物志”取代“列传”,“宦绩志”取代“宦绩录”,“此诚创举,亦厘然有当于人心也,《奉天通志》亦用此体,以示不泥旧法。”[9]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泥旧法”,大胆求变的修志理念,促使《奉天通志》体例有所创新,而以金毓黻为代表的修志思想与理念的革新,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近代方志转型的历史面相。
此外,金毓黻将其体例创新方法与理念运用到《奉天通志》编修实践,取得修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效应。如在编纂“沿革志”时,他积极借鉴“近代考沿革者”,其中既参考杨丕制“表”之法,又吸收李兆洛、杨守敬等人设“图”之法,以达到“考辨颇详,体裁亦善”的目的。
总之,从1928年启动到1935年编竣,《奉天通志》的编修工作历时七年之久。金毓黻作为纂修人员,为编修志稿不遗余力。担任总纂之后,他更是将修志视为志业,通过学界交往与学术传承,推动修志理念革新与方志体例创新。而在伪满当局的高压下,他带领奉天通志馆人士,克服种种困难,全力编修志稿,终于完成民国《奉天通志》的编修与印行工作,为东北地方文献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