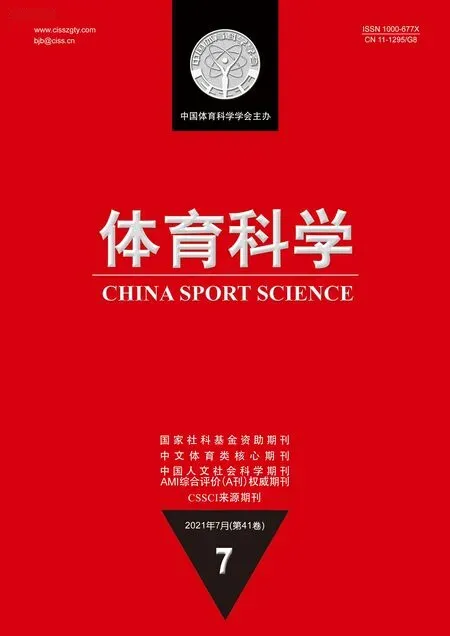从体育媒介到媒介体育——对体育新闻传播发展的思考
郝 勤
从体育媒介到媒介体育——对体育新闻传播发展的思考
郝 勤
(成都体育学院)
自19世纪末体育赛事在世界各国成为一项影响广泛的公众观赏性活动以来,以赛事报道来满足受众需求的体育媒介(指报道体育的媒介,当时以报纸杂志等纸媒为主)就出现了。一直到20世纪中叶,作为体育赛事的文化衍生品,体育媒介一直是体育赛事的配角和附件,其作用就是做比赛的“麦克风”与“拉拉队”。
由体育媒介向媒介体育的变革萌动于20世纪60年代。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租借了美国的“辛巴姆”地球同步通讯卫星对赛事进行直播。从那时起,有线电视技术与卫星技术结合,一举改变了19世纪末以来“媒介是体育的宣传工具”这一纸媒时代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尤伯罗斯创造的洛杉矶奥运会运营模式与传媒大享默多克以天空电视台(SkyTV)收购英超转播权模式成为“媒介体育”(mediasport)臻于成熟的标志。
在中国,体育赛事转播从20世纪80年代的无线电视到有线卫星电视只经历了短短的十余年时间。1978年,央视首次以无线电视转播了阿根廷世界杯的决赛录像。1982年,央视首次对西班牙世界杯赛事进行了直播。1995年,依托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技术,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的开播。随后一批地方电视台体育频道陆续开播。中国的体育媒介发展进入了“纸媒+电视”阶段。
20世纪末互联网媒体骤然崛起,深刻地改变了现代社会,重构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对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奥运会为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网媒首次介入奥运会报道。2000年悉尼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网媒报道权并首次发放网媒记者采访许可证。此举被视为体育报道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2005年温哥华冬奥会首次实现手机端和网络直播平台播出奥运赛事。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全球迅速普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背景下首次在所有比赛场馆和配套设施中配备了免费互联网,因而被称为“社交媒体奥运会”。2014年索契冬奥会因全世界超过半数的受众从移动终端上获取比赛信息而被称为“数字化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媒体运营部负责人安东尼·艾德加(Anthony Edgar,2018)在2018国际体育大会媒体论坛上指出:数字化、移动化以及社交化趋势将成为奥运媒体运营发展的未来。
在中国,1997年四通利方首次在“利方在线”采用网上视频、音频技术直播了1998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首次授权网媒进行赛事视频直播,在各项奥运资讯内容获取上,互联网首次全面超越传统媒体,这标志着网媒开始取代传统媒体的体育传播地位和影响。2009年,3G手机在中国发牌。由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技术、卫星技术以及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所打造的新媒体终端为中国进入“媒介体育”时代搭建了强大的媒介技术平台。
劳伦斯·温内尔(1998)指出,“媒介体育”(mediasport)是媒介技术革命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体育形态。在此之前,虽然国际赛事与职业体育赛事早已出现,但在“看台+纸媒”时代,其影响仅限于少数国家和城市。而有线卫星电视拆除了体育场看台的三维空间,也拆除了体育与媒介的篱蕃。世界进入了媒介体育时代。
媒介体育的出现使体育分裂为“媒介的”和“非媒介的”两大类。萨马兰奇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指出:将来的体育会简单的被归为两类,一类是适合电视(媒体)的口味,另一类则不适合。体育项目只有在属于第一类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发展,其它的要么衰落,要么踏步不前。其实,所谓“媒介体育”虽然声势浩大,影响广泛,但只是部分“符合媒体标准”的竞技体育项目与赛事而已,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英超、温网、NBA等。而大量“非媒介体育”项目与赛事,如大众健身活动、体育教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极限运动、体育旅游等,它们可能不入媒体法眼,但却是现代体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媒介体育”推动体育实现全球化。卫星电视技术与网络技术能使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同步看到一场奥运会比赛或世界杯足球赛。而这在看台时代和纸媒无线电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媒介体育将体育场看台无限扩大,它推动奥运会及各类国际赛事变成全球文化,使英超、意甲、温网、NBA等国内赛事实现全球传播,让原本属于某个国家的赛事、俱乐部、体育明星成为全球品牌和世界偶像。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体育文化霸权与话语霸权问题。
“媒介体育”向公众提供的是所谓“拟态化”或“镜像似”的体育赛事产品。观众在电视或网络上看到的体育赛事并非真实的现场比赛,而是经由镜头追踪、回放、慢放、特写、解说等技术处理与编辑“再创作”的媒介产品。这意味着,观众从媒介终端上接收的赛事音视频信号不仅仅是比赛实况,还有媒介的思想、态度、立场与感情。
媒介体育催生了新体育概念,也改变了体育运动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媒介体育的运动者不再像20世纪上叶参加奥运会的业余选手为了自身健康或兴趣投入比赛,而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满足球迷需求而工作。全球数以亿计的媒介体育消费者并不以“身体活动”来参与体育,也不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目的。他们或在看台上激情呐喊,或半夜坐在电视机与电脑前观看地球另一端的精彩赛事,为了自己心仪的运动项目、赛事、球队和明星而倾情投入,大喜大悲。媒介体育缓解了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与节奏带来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使现代人重获内心渴求的社会归属感。他们通过媒介体育满足的是约翰·奈斯比特(1982)所说的“高情感需求”而不是身体的需求。
媒介体育创生出以赛事IP营销为核心的体育产业。当数以亿计的观众同步观看一场比赛时,插播一条广告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效应。媒介组织通过购买体育组织的赛事IP而在广告和赞助市场获利。体育组织则通过向媒介组织销售赛事IP来维持联盟运转,经营球队、购买明星以吸引更多的球迷与观众。媒介体育是好莱坞影视娱乐产业的体育版。体育组织相当于电影制片商,传媒组织是电影院线商。体育组织提供高品质的赛事产品,而媒介组织则通过购买赛事转播IP在媒介终端播出,再以出售广告播出时段来获取利润回报。现代体育是如此离不开媒介,以至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国际赛事以及各国职业赛事的媒介转播权销售都至少占据其总收入的50%以上。
媒介体育改变了体育与媒介的关系。在体育媒介时代,媒介是体育的衍生品与附属物,体育组织通过对媒介发放采访许可证而拥有话语权。但在媒介体育时代,体育组织在观众资源与资金来源上高度依赖赛事转播权营销,媒介组织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力图获得话语权,在比赛时段、赛季场次、甚至规则制订(如2018足球世界杯决赛引进VAR技术)等方面以媒体标准与规则影响体育。
媒介体育在操作层面上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媒介组织向体育组织购买赛事转播IP,这是媒介体育的主打方式。二是媒体利用自己手中的媒介资源打造赛事与活动,如央视的《武林风》《中华龙舟大赛》《谁是球王》等。但这些赛事与活动基本上是按照电视节目形态制作的,其组织力、影响力与传播力无法与体育组织提供的国际性赛事及职业体育赛事相比。三是体育组织利用手中的赛事资源打造属于自己的媒介平台,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及其旗下的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共同打造奥林匹克网络频道。但由于市场资源、技术平台和专业人员等方面的局限,体育组织打造的媒体无法与专业的跨国性传媒集团相比,一般只是专业媒体的补充。
今天,媒介体育以“互联网+”与“体育+”超文本链接为特征,推动全球进入了体育文化大时代。围绕高度组织化、商业化、职业化和全球化的赛事表演,体育与电视、网媒、纸媒、出版、广告、影视、表演、艺术、博物馆、会展、电子竞技、动漫、纪念品等文化形态融合链接,衍生出丰姿多采的体育文化形态,为现代社会提供大量体育文化产品,以此来满足现代人的精神与情感需求。
在中国,“体育宣传”是各级政府体育部门的重要工作。它是由政府(体育与教育部门)、媒介、公众三者之间构成的一个单向性传播系统。通过这一系统,政府利用媒介向公众宣传有关体育的方针政策,媒介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喉舌”与“桥梁”。20世纪90年代,足球甲A联赛为刚刚兴起的市场报、都市报等纸媒和有线电视提供了丰富的报道题材与内容,造就国内体育媒介的黄金时代。但2002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决赛后,受联赛体制改革滞后及黑哨假球风波影响,中国足球跌入低潮。受此影响,体育媒介因内容缺失,受众离去而严重萎缩,报纸体育版面骤减,地方电视台体育频道纷纷关闭,体育记者严重流失,加之网络的冲击,体育媒介短暂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媒体在中国短时间内迅猛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的数据,截止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为体育传播和媒介体育提供了空前强大的技术终端平台。但与此同时,国内的赛事市场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体育赛事转播营销市场持续萧条,体育与媒介的融合发展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双方仍然维系着体育组织搞赛事,媒介组织搞转播的传统格局。
对比国外媒介体育的兴盛,国内有关方面争论不断。从体育组织立场看,国内电视媒介一直央视一家独大,形成对国内电视体育转播权的长期垄断,导致国内体育转播市场难以发育,不能像国外一样通过赛事IP营销为体育组织提供必要的发展资金。而从媒介立场看来,体育界未能提供本土高品质赛事转播产品,迫使包括网媒在内的国内媒体不得不大量购买国外赛事IP。而更重要的是,国内体育组织与媒介组织无法实现在市场机制层面上的深度融合与超级链接。而这正是媒介体育与当今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结论是什么呢?从体育与媒介的关系来看,国外发达国家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业已完成由体育媒介向媒介体育的变革,由此形成规模巨大的体育赛事娱乐产业并推动体育文化大时代的到来。这是世界体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在中国,从20世纪80~90年代,体育与媒体的关系经历了体育宣传到体育媒介的转变,但体育媒介向媒介体育的变革却步履蹒跚。国内体育与媒介的行政化条块分割与改革滞后阻碍了两者的融合链接。而这需要通过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才能得以解决。
1000-677X(2018)07-0022-03
10.16469/j.css.201807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