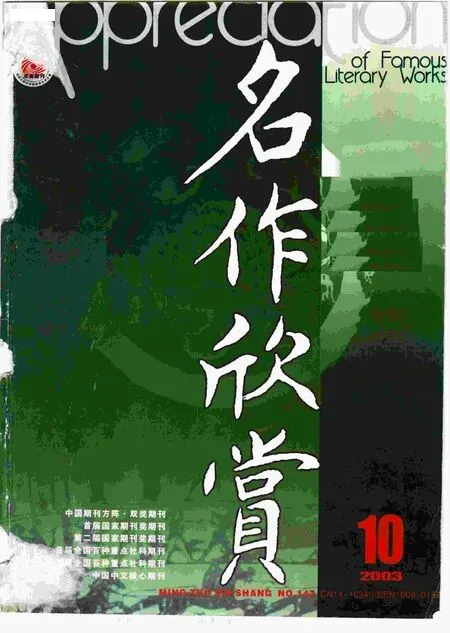逆 行
程水金先生述及晏殊词时引到一段轶事:晏殊赴杭州,过扬州时,于大明寺小憩,寺庙壁上留有不少文人墨客的题诗,晏殊闭目徐行,让随从仅诵壁上诗,而不念诗人姓名籍贯官品。最近读文,参差有似晏殊阅诗的端倪,喜欢掩去作者,清清爽爽品文字,然后溯流而上,倚着文脉的波痕纹路勾勒出写作者的依稀模样,态貌行止也略有隐约。呵!有意思得很!
其实,概如人,文亦有心,有貌。——有格调的貌和有温度的心,终究是能让文章清晰起来的。终究的事,仿佛除了伤疤的疼痛,可以理所当然地交付与时间去消退,其他的,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的,何必止于爱情?文字一如。偏爱那些内蕴波澜的文字,是因为它们让书写赢得了“清晰度”,进而让我们可以幻想到那些写作者独特的依稀风貌。人因文章而立,而显,而彰,而被读者想象。
恰如孙绍振先生,他谈《三国演义》,聊《红楼梦》,是一个常常喜欢拿老友“开涮”,风趣得“狠”,幽默得“狠”,心态年轻得“狠”的可爱的老先生;还有莫砺锋先生,他谈苏轼,谈中国古典爱情诗,是一位温润谦逊又古雅内敛的长者;再有如曹文轩先生,他谈儿童文学,脑海中总浮现着他盘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的样子,温和而笑容盈溢;再有王珂先生,他讲诗歌疗法,严谨周全又极具感染力……很多很多这样“逆流而上”的想象。真的,只是穿过文字的一种想象。
其实,与各位尊者先生从未面见,更奢求相识,然而,他们为文之心与作文之风的“清晰度”却不禁令人思忖着、想象着、勾勒着他们的行止神貌。——如此不同,却如此生动。模糊的文字是断然没有这样的魔力的。
近几期的编读,这样的“逆行”越发地有趣味,有意思,品读着那些拥有清晰灵魂的文字,勾勒着一幅幅写作者的画像,一本平面的杂志倏然立体起来,清朗起来了。一本杂志的生命也因着这样那样的文字,有了温度,有了格调,有了清晰的面孔。
诸君也来“逆行”一次!
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