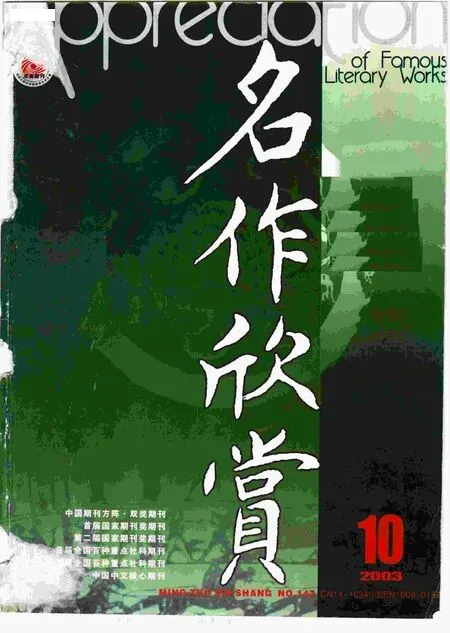回归古典与民间的“先锋”
——论周朝军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广东 管季
作 者: 管季,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一
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所有作家无法回避的一道多选项考题。倘若我们据此将作家的创作风格做一个简单而略显任性的划分,那么,当作家追求形式上的表达而降低了在内容上的笔力,我们姑且称其“先锋”;当作家给予形式与内容一视同仁的对待,其“所见即所得”的现实主义风格势必呈现;当形式失宠,内容当道,一种“尽在不言中”的古典主义风格就走向了前台。
“先锋”派文本为读者设置重重阅读障碍,这种表达上的策略,导致中国本土先锋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难以为继。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是对“先锋”有意忤逆,陈晓明曾指出:“那时的所谓现代派文学中,很多现实渴望、文学反压抑的创新欲望、摆脱旧模式的愤懑,等等,都只能找出一个足够大、足够叛逆的词语去容纳——现代派。”①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特定文学流派的历史“功能”和角色,而时至今日,“现代派”这个词因为包含了过于巨大的内涵而被人们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学创作与评论中,成了一种俯拾即是的被过度消费的理论资源——于是它就不再具有20世纪80年代历史语境下的叛逆特质。而“先锋”——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今日的先锋已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在内涵上相去甚远。“先锋”派的后继者企图站在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等人的肩膀上,在叙事手法与文本形式的领地里开疆扩土,可惜他们磅礴的野心,在今日这个充斥着虚无主义和戏谑模仿的“后时代”,换来的最多是某种“后先锋”罢了。
于是,当昨日的“先锋”沦落为今日的传统,创新的幽灵又再次作祟。“形式”既已过度消费,突破的重任就落在了“内容”的肩上。“五四”以降,文学与古典一刀两断,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至“寻根文学”发轫,古典或者民间传统复又得到宠幸。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点上最自觉的,依然是最早的一批先锋作家,格非等一批作家在小说中越来越多地尝试古典的写法。学者郭冰茹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对于格非等尝试过“先锋实验”的作家来说,当中国古典文学成为一个束之高阁的传统,如何确定自身/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中的身份,便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负面因素的显现,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和守成不仅成为应对这些负面因素的可能,也成为部分作家确立其身份认同的思想起点之一。②暂且不论格非等人对古典传统的再发掘究竟是先锋的真正回归,还是现代文学以更为中国化的面貌呈现,其本质都是作家对于自身创作困境的反思与突破。这同样让人联想到“寻根文学”思潮中早就提及的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定位问题。可见,在某个可以考量的时间段内,作家的创作周期是循环往复的,探索也是不断循环深入的,没有任何一种流派或理论能够代表创作的全部内涵和最终高度。我们需要的,也许只是某种打破自身局限的可能性:在先锋派的尝试下,对小说形式的探索给予了我们新的可能性。在寻根派眼中,文化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包括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在不断丰富着文学中关于当下现实的记载。时至今日,文学确已遭遇无法创新的悲哀,也许尝试某种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杂糅”,就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青年作家周朝军就是这样一个将“杂糅”感发挥到极致的作家。作为一位“90后”作家,他创作的年头却并不短,甚至很可能是90后作家中最早在正式期刊发表作品的一位(从他2004年在《钟山》发表小说处女作到如今已有13个年头,而如果从他在《沂蒙晚报》发表豆腐块算起,就还要再早上一个年头),因此他得以在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时就已越过一个作家的稚嫩期,走入相当成熟的“先锋”创作中,他文风老成又略带“痞气”,在同龄作家中自成一家难能可贵。但文坛并未给予这位青年作家足够的关注,他的一系列带有颠覆性的作品,未能在文坛之坛中荡开其应有的涟漪。周朝军作品中呈现的新的古典传统和民间特质,其意义显然是被低估的。如前文所说,当一个作家在“形式”上的功力已炉火纯青,“内容”就会成为衡量一个作家创作高度的重要标准。周朝军的作品中,从来不缺乏先锋文本的特质——如在小说《抢面灯》中用字母代替人名,设置大量隐喻,颠倒、重复、置换,模糊情节,零度叙述视角等,“实验性”色彩较之老一辈“先锋”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其作品中古代传奇、话本的风格也同样运用自如,如在由二十一篇短篇小说组成的系列笔记体小说《沂州笔记》中,就讲述了二十一个俗世奇人的传奇故事,他们中有乞丐、方士、长工、盗墓贼、和尚、牙婆、媒婆,也有神医、侠盗、义士、私塾先生、驿站邮差,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到语言,几乎已经完全回归了古典的范畴。而在短篇小说《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中,其将现代派写作与古典审美结合的特质就更为明显,甚至还带有了某种神秘的科幻气息。在完全现代题材的作品《左手的响指》《12盒红塔山》《回头是暗》中,他还将悬疑小说和心理小说很好地嫁接在了一起。难得的是,这些杂糅,并没有模糊作者本人的思想追求,他坚守的始终是一种古典的义理、一种深刻的理想主义和对人性的坦率态度。这种对义理的追求是不动声色的,是掩藏在复杂的文本之下的,这或许是周朝军的小说相比同龄人更为深刻的地方。
在看似不经意间设置的重重阅读障碍中,作品被读者不断解读成一个个的概念和隐喻,作者的态度出现了缺位,周朝军的很多作品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较为明显的是短篇小说《抢面灯》中这种没有态度的“学术性”或者“纪实性”写作——虽说有玩弄形式的嫌疑,但假如忽略隐喻,单从故事出发,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反讽背后作者深深的怜悯。这种怜悯包括对饥饿的怜悯,包括对那些必须靠说谎来维持尊严的人的怜悯,还包括对消失的民间传统的怜悯,更包括了对这种传统的被解构、被讽刺的命运本身的怜悯。也就是说,戏谑和讽刺只是表象,所有的阅读难度都来源于作者的叙述手段,人性依然是作品阐释的核心。这些颇具阅读难度与精神追求的作品,在当下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异类。谢有顺曾总结过:“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经验、身体和欲望成了创作的主角,故事只要好看就可以,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慢慢地,读者也就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也就是单一的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③在先锋派主流过又边缘过的今天,对形式本身的追求或许又算是新一轮的先锋行为——毕竟时下“期刊小说”都是想方设法让故事好读、好看的,而周朝军的几篇代表,可谓篇篇“好看”却篇篇不好读的,甚至在某些作品中,他的半文言写作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压抑的绵密的快感。他将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融汇在作品中,如在短篇小说《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中,“我”在书海里拾级而上:
在第六十四层,我背着牍先生读完了《杂事秘辛》《飞燕外传》《控鹤监秘记》《汉宫春色》《河间妇传》《痴婆子传》《闺艳秦声》《海陵王》《杏花天》《绿野仙踪》《游仙窟》《帘外桃花记》《倭袍记》《如意奇缘》《玉蜻蜓》《绣榻野史》《灯草和尚》《桃花庵》《如意君传》,本以为牍先生毫不知情,隔夜卧榻上竟多了一摞线装珍品,乘兴翻阅,依次是《昭阳趣史》《呼春稗史》《春灯迷史》《浓情快史》《隋阳艳史》《禅真逸史》《株林野史》《禅真后史》《巫梦缘》《金石缘》《灯月缘》《一夕缘》《五美缘》《万恶缘》《云雨缘》《梦月缘》《聆痴缘》《桃花影》《梧桐影》《鸳鸯影》《隔帘花影》《石点头》《清风闸》《蒲芦岸》《碧玉狮》《摄生总要》《杵杌闲评》《豆棚闲话》《弁而钗》《宜香春质》《僧尼孽海》《芍药榻》《人中画》《洞玄子》《五凤吟》《咒枣记》《引凤箫》《蝴蝶媒》《幻中游》《凤凰池》《赛花铃》《贪欢报》。在第六十五层,我重温了《齐物论》……根据脚注,这些书中亦有条目引自《坤舆志》。
让读者“开眼界”的方式有很多,但像这样眼花缭乱地罗列古典书籍,是极具颠覆性的。这类搜寻资料式的“学术性”写作同样见于《抢面灯》:
1998年12月至2004年3月,W先生与日本性学专家M先生有过数十次通信。在通信中,W先生企图在男性阳具大小与夫妻性生活和谐程度之间找出某种联系,并就此假设了数十种数学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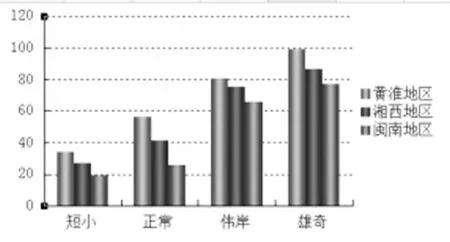
在上图所示的模型中,X轴无须赘言,Y轴则指示着在两性生活中女性的满足程度。无奈这数十种天才的数学模型都被W先生在随后的通信中逐一批驳——W先生在科学面前这种知错能改的精神,至今无人论及。W先生始料未及的是,M先生对其研究思路大为激赏,并将W先生视为国际性学界模型化性学研究的鼻祖。
当作者使用这类极其具体的资料或意象时,作者表面是在讽刺,但让人惊诧的是,读者却在这讽刺中生出了敬畏之心。这种阅读与理解之间的张力是一种错位之美,它让人重新反思古典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之间的某种深刻联系。如果说“用严谨的现代学术方式去研究性满足”和“在神圣的书籍殿堂中阅读的至高境界居然是阅读野史和艳情书籍”,同样都是讽刺,但在这讽刺中,读者却又生出了对于“大”与“小”、“无穷”与“有限”的思考与敬畏。自以为能通过科学了解一切的人们,最终发现所有的一切也许都只是谎言。与其说它蕴含了深刻的哲思,不如说它是对既往文学作品的一次无理的冒犯。
二
曾有学者如此判断“80后”写作:前辈们颇感为难的真正的城市写作,在“80后”这一代作家的笔下变得轻松无比,“缠绕中国几代作家的乡村记忆荡然无存”④。诚然,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年轻一代早已脱离了“传统”的话语圈,他们甚至不知什么是传统。如果说“80后”如此,那么对城市生活更为熟悉的“90后”就更是如此。对于一个没有传统概念的代际来说,写传统,尤其是民间传统,无疑是一种挑战。周朝军的作品,除了植入古典意象,另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对民间传统的承接。这种民间传统,或者民间精神,早已经被众多作家描绘和阐释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派,一派以批判民间劣根性为目的,代表是鲁迅;另一派主张回归民间传统,代表是沈从文。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寻根文学中,对民间的态度也有相当明显的分野,也依旧是向往/审视的二元对立。当然也有如贾平凹一类的作家,对民间传统和乡村生活态度暧昧。相对于以往的“民间”与“乡村”的天然等同,现在的“民间”应该还包括城中村、城市中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出租屋以及城乡结合部。但周朝军似乎对这样的“民间”并不感兴趣,他将目光伸向了更为久远的年代,实现了某种对于古典民间传统,乃至于文化根源的阐释。
“民间”是个隐喻,周朝军以此来观照现实。如《抢面灯》中对于抢面灯这个民间传统的颠覆性阐释,小小的面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中,被野蛮地哄抢,当饥饿消失,面灯又先后与男性伟力、生殖甚至图腾崇拜等同起来,给因食色而起的集体械斗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和文化意义。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史。这样的文明进化过程,放到远古时代也并无不妥,柏拉图很早就提到过人的兽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天性中的狂放不羁和兽性在我们吃饱喝足之后,会突然跳出来,赤身裸体地到处乱跑,因此人们需要音乐,需要运动,需要宗教——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相信神灵才会强盛。⑤通过对“抢面灯”这样一个类似图腾崇拜的过程的提炼,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的产生过程。正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需要食、色,所以通过这种仪式性的争夺,将现实中对食、色的渴望大大降低,维持最低限度的理性,这大概就是民间仪式或节日的必要性。
当然,对于这种美化残忍的“传统”,作者是持讽刺态度的,于是在描绘传统的同时,又顺势解构了传统。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对民间传统的诗性坚守,有的只是对民间文化的某种落寞的想象。这种想象一下子将这部作品抬高到一个同龄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它既是一种对自我的审视,也是一种对人性、对谎言、对民间集体狂欢、对文化本身的批判。
当然,在批判中,也可以有建构。如周朝军的两部短篇小说中,同时出现了同一个情节:在小说《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里,“算得半个和尚”的贾先生精通医术,被某师长以全体村民的性命相要挟,给他的九姨太看病。贾先生先给九姨太看好了病,最后又以看病的名义毒死了九姨太,并遣散了乡民。
原来这墨西哥舞娘并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而是暑天里随管家下河洗澡,不习水性,误吞了带有蚂蝗卵的河水。蚂蝗幼虫在其肚子里安了家,天长日久把她吸干了。那日贾先生切脉,料定是这毒物干的好事,便寻来泥巴蒸作药壳,里面尽是填了些滋补之药。这蚂蝗有个土名叫地龙,喜欢在河泥里闹腾。那舞娘服过河泥后,蚂蝗便钻入其中。待这河泥随五谷轮回被排出体外后,病自然也就好了。
而在系列小说《沂州笔记》中《贾郎中》一篇,贾郎中却救了某师长的独子。
原来这熊定中并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而是暑天里随管家下河洗澡,因不习水性,误吞了带有蚂蝗卵的河水,蚂蝗幼虫在其肚子里安了家,天长日久把他吸干了。那日贾郎中切脉,料定是这毒物干的好事,便寻来河泥蒸作药壳,里面尽是填了些滋补之药。这蚂蝗有个土名叫地龙,喜欢在河泥里闹腾。熊定中服过河泥后,蚂蝗便钻入其中。待这河泥随五谷轮回排出体外,病自然也就好了。
几乎一模一样的描写,而两个贾郎中却似乎并没有身份上的关联,作者只是在描写两个人物的时候借用了同一个事例——也就是治病。这也许与作者本人的医学背景有关,但也显示出作者对于民间文化的偏爱。两个贾郎中,都带有“义士”色彩,他们或为拯救乡民性命而牺牲,或为家国大义而甘为盗贼。在后一个故事中,贾郎中身上还有了明显的文人色彩:
(贾朝宗)来到画前,指指点点感慨阵阵。至动情处,干脆取下墙上的古琴,弹了一曲《胡笳十八拍》,边弹边唱。
好一幕名士风流,命悬一线之时,为了心爱的琴和画,竟可以忘却性命之忧。如果说为盗者有侠骨是作者民间想象的反映,那么为盗者的文人做派就是作者在向传统文化致敬了。贾郎中这个兼具民间气质与名士风骨的人物,形成了周朝军作品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周朝军意图建构的古典理想主义的标志。
在对古典传统进行再现的同时,周朝军还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造。比如短篇小说《灯笼》,小说中写了乡绅之女春草和小乞丐根子的爱情,男主人公是庄稼汉不是秀才,但是依旧逃不过“落难才子遇佳人的古典模式”,这既让我们想到《卖油郎独占花魁》中那种身份不对等的爱情传奇,也让我们想到《受戒》里明海与小英子那种纯净的萌芽中的爱,甚至可以让我们想到《人生》中刘巧珍对高加林的执着付出。春草丝毫不介意根子的身份,并且对其表达了大胆的爱意,春草这一人物,兼具传统的节烈与现代的叛逆之美。无独有偶,在短篇小说《赵二愣子》中,掘墓为生的赵二愣子,人如其名,胆大痴情,他爱上了一位张小姐,在张小姐死后盗走她的尸体,做了三天夫妻之后又为之殉情。单纯从痴情程度来说,根子和赵二愣子毫不逊色于《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这种极端浪漫、极端传奇的叙事,构成了周朝军《沂州笔记》系列小说的主要风格。
古典、传奇、民间,这些关键词都能在周朝军的小说中找到,他尝试将各种小说元素进行杂糅,其实也是在为写作寻找某种突破的出口。基于此,周朝军作品中还会呈现出一些矛盾和犹疑。比如说,在对民间精神的阐述上,他一方面解构了民间文化传统,对民间这个词语本身所代表的某种神秘性进行“祛魅”,让其变成简单的食、色、性与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又表现出对于民间传统的某种深深眷恋,如侠义文化和殉难的传奇叙事。这种矛盾并不是偶然的,假如缺乏这种矛盾和犹疑,那么作品中对于古典价值观和民间叙事资源的借鉴,就完全变成了模仿,缺失了一种现代性的审视。
至此,周朝军作品中的荒诞、戏谑、隐喻和反讽,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周朝军不批判古典与民间,但也不寄希望于古典与民间;他自始至终都在用一种现代性的反讽来探寻自身存在的维度,这种反讽恰如哈桑所说,表现出“多重性、散漫性、或然性甚至荒诞性”⑥。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和不确定性,包括这种情节的重复和散漫的叙述,让周朝军的小说更像是一种杂糅了现代写法的“传奇”。这种传奇,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它与唐传奇一样,并非单纯的叙事文体,而是一种“原生混沌状态的小说文体,是一种不像小说的小说,它是多文体的杂糅”⑦。他不止承继了古代传奇的写法,也承继了传统与民间视角。越是理解这种现代与古典的联结,就越能发现周朝军小说中被低估的价值。一直以来,中国作家都在试图寻找自己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努力去打通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如果说周朝军的尝试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种范式写作,短时间内还难以被接受,但是说周朝军完成了“90后”一代与古典文学传统的衔接却是可以理直气壮的。
三
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样的题材,或是借用了什么样的传统,都不会改变他(她)立足于自身现实所做出的精神思考。说到底,一切创作首先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作家的表达囿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又囿于他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充斥了数字化的信息和浮躁的审美,现实的语境已经大大改变,这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难度。走向古典的写作,其实并不能真正瓦解这种时代性难题,因此,那些已经进行了写作转向,或是正打算进行转向的先锋派作家,或多或少也遇到了书写现实的难题。他们不可能永远沉浸在古典的书斋中,也不可能永远进行着夸张的反讽和戏谑。正如周朝军在一次访问中谈到的,他最喜欢的作品其实是《平凡的世界》。也许,有很多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曾影响了他的写作,但真正让他走向写作的,却是这样一部现实主义色彩十足的作品。
在虚构与现实的关系上,周朝军也给出了他深刻的思考。如短篇小说《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是一篇探讨“虚构”的作品。小说中,“我”是一个作家,讲述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来自日本神奈川的砚商拜会了逐水镇博学多才的周汝霖,然后写了一部《西洲怪谈》,并通过他的孙女,将书呈现在“我”的面前。在这部书中,周汝霖的故事与砚商扭结一处,他讲他自己如何去淼一楼做图书管理员,又如何得以博览群书。最后,在读了各个年代的各科书籍之后,他在接过牍先生递来的一面镜子之后,失明的他看到了人类的所有历史与真相,这时,淼一楼爆炸了。有趣的是,“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赫然看到自己成了一部书籍。
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读者分不清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我”,还是砚商,又或是周汝霖先生。砚商和周汝霖是“我”的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人物,虚构人物周汝霖口述了一个故事,经砚商记载,作者“我”转述加工,才最后构成了小说本身。这种故事中的故事,也为情节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也许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虚构”观念:一切皆可虚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天才,他在经历了漫长的阅读过程后,进入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他双目失明,却又洞悉一切,知识的增长给他带来了智慧,也带来了诅咒。他在照镜子的那一刻才发现,人对于自身,是不可知的。这也是一种隐喻,照镜子代表着人类的某种自省,在人类开始审视自身的时候,一切都灰飞烟灭了。这种创作,有着近乎科幻的表现手法。通过一种极限的想象,对人类自身的现实和局限加以思考。如电影《超脑》,同样表述了人的智力开发到极限之后,人何去何从的哲学问题。当然,电影会以更为直观和娱乐化的方式去呈现,而这篇小说终究只能走向两条路——一条是以爆炸来寓意人类思考的徒劳,一种是以虚构来否定整个故事存在的基础。小说中的字母条码,其实也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反讽,在全部信息都数字化的今日,网络上可以存储无限的图书,各种信息根本不需要记忆,只要动一动手指就可以找到——也是因为如此,人类成了信息的奴隶,成了字母编号和条码,成了信息时代最为尴尬和悲哀的存在。每个人都在重复他人的命运,在无限的虚妄的欲望中忘记了反观自身,这是一种深刻的荒诞。
周朝军在这里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思考:现实就是荒诞。我们的现实,已经不是孙少平的现实,它包含了某些更为沉重的东西。我们不仅面临着意义的丧失、精神的虚空,也面临着创作资源的贫瘠,在这个人类走向技术化、信息化和同质化的现实中,已经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可写了,而文学的虚构注定走向虚无,严肃的思考终是徒劳。正如雷达所说,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走向了世俗化,日常化,去精英化,走向了自然经验的陈述和个人化写作,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⑧。这并不是路遥的初衷,也不是周朝军的初衷。在新的现实中,写作成了一种个人的退守。无论是理想也好,欲望也好,都被包裹在“人性”的框架中,作家在写作时,他的世界是被无限放大,也是被无限缩小的,他只对自己的想象负责。这种写作的退守,其实也是对于自身精神边界的坚持,它区分开外面那个现实而浮躁的世界和文学中那个充满了古典理想主义的世界。但周朝军并不直接表达这种理想,就如同作者并不直接表达内心那些曲折的暗面与暧昧模糊的道德领域,而是用一种看似冷漠的叙述来引领读者走向共同的困境,揭开生存的谎言。周朝军的创作,恰是这种创作中较为高明的一种。他擅长写虚构和谎言,他并不直接表述自己的喜恶,甚至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情结也是转瞬即逝,读者往往会在那片暧昧模糊的领域中踟蹰不前。这种创作,经得起读,也经得起“误读”。在此前那个充斥着革命话语的时代,作品是不能够被误读的,文字表达的必须是“正确”的思想,读者所解读到的也必须是“正确”的口号;而周朝军的作品,无论如何误读,他始终可以镇定自若。
总而言之,用一种固定的、确定的风格去总结周朝军的创作,是有难度的,正如阅读他的作品也是有难度的。但毫无疑问,他的创作极具特色而且潜力巨大。他不仅有着文体的自觉,也有着一个写作者难得的自知。在对古典叙事语言和民间叙事资源的传承上,他表现出一个典型的先锋作家的特质,相信假以时日,这种颠覆性的杂糅的“先锋”创作,将在对传统文学脉络的继承中,开辟出一片全新的与现实相接的创作领域。
①陈晓明:《乡土中国、现代主义与世界性——对80年代以来乡土叙事转向的反思》,《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
②郭冰茹:《回归古典与先锋派的转向——论格非回归古典的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文艺争鸣》2016年第2期。
③谢有顺:《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④江冰:《论“80后”文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⑤〔美〕威尔·杜兰特:《西方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⑥〔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景观中的多元论》,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⑦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⑧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