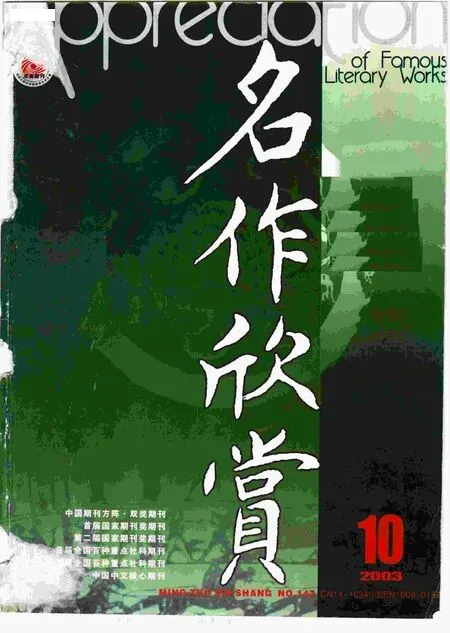一首给人幸福的抒情政治诗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疗解读(中)
江苏 王珂
作 者: 王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事实上,舒婷1977年3月27日写的个人爱情诗《致橡树》也成了1979年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诗”。尽管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举成名后的舒婷也成了官方与民间都期待的“国家的诗人”“人民的诗人”“时代的诗人”,她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使命”,她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情感”和“道德情感”。诗风也有了大的变化,有时不想再以“普通人”的身份写“安慰自己的诗”。当时理论界经常批判“小资产知识分子”写作,罪名是“沉湎于个人情感,不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诗评家常用的批判语言是:“你个人的痛苦与别人无关,更与社会和时代无关!”舒婷在1979年4 月创作了“关心祖国”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同月,舒婷写了“关心友人”的《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两首诗都是写“身外之物”,关心“祖国的命运”与“诗友的前途”,也是在关心自己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发展,是“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这种“助人为乐”获得的“道德情感”及“道德愉快”有利于诗人的身心健康,是一种比较好的诗疗方式。
《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全诗如下:“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只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不,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舒婷写于同一时期的两首诗异曲同工,都强调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如诗的最后两句所言:“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希望”一词同样出现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前面却加上了“痛苦”做定语,后面用了感叹词“啊”,整个诗句为:“——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诗中还出现了多个抒写悲哀情绪的诗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诗中甚至还出现了“迷惘的我”。同一时期写的两首诗有同样的主题,都可以称为“励志诗”,一首是为“别人打气”,一首是为“自己加油”。劝别人振作是劝自己不消沉的重要方式,当然自己更应该斗志昂扬,精神振奋,所以《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有些“激进”,甚至有些“左”倾。劝自己振作就可以更遵从内心的感受,没必要当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所以可以在诗中出现“迷惘的我”。
这句诗在当时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政治意义”,大胆承认并公开讲出也有利于那代青年的“创伤自疗”。如果把它与1980年发生的“潘晓事件”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当时产生的“政治启蒙价值”和“精神治疗价值”。纪宇“慷慨激昂”的《风流歌》也是在1980年“举国传播”,影响了很多青年。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刊发了一封署名“潘晓”的长信,写出了那一时代青年的“困惑”及“迷惘”,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长达半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题目是“潘晓讨论——人为什么活着”,《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了六万多封来信,写信的绝大部分是有同样人生困惑的青年,如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迷惘的我”。一个有追求的时代也往往是一代人容易迷惘的时代,如1980年前后几年是中国颇具活力的黄金时代,是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创业时代。从各省团委办的刊物名称中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风貌,如《新青年》《时代青年》《风流一代》。
在心理治疗中,“示弱”常常比“逞强”更有治疗效果,如同俗语所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男子汉伤心时流泪是正常的,有利于心理健康。有迷惘并敢于说出迷惘的人才是心理健康甚至人格健全的人。一个有追求的人往往会产生迷惘,“胸无大志”的人过的往往是庸庸碌碌的生活,麻木而没有困惑。我在大学是公认的事业心超强的好学生,信奉的名言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进校就决定要考研究生,立志要当大诗人或大学者,高强度的学习生活导致精神生活的不稳定,时而亢奋,时而低沉。“郁闷”“困惑”“迷惘”几乎是“常态”,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但是最后都振作起来。从大一开始,每学期写一本日记诗,先写的是《追求集》,然后写的是《困惑集》,再后来依次写的是《浪荡集》《幻灭之春》《希望之春》。这些诗集的名称就可以呈现出波动颇大的心理状态。六百多首诗完整地记录了爱的萌发、爱的朦胧、爱的欣喜、爱的迷狂、爱的绝望等爱的历程,记录了一个男孩(17岁到21岁)在追求中困惑,困惑后浪荡,浪荡后幻灭,幻灭后新生的“奋斗”历程——在爱与知的追求中成长,在追求与迷惘中成熟。写诗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幻灭也没有让我真正灭亡。本科毕业时我跨专业考上了中文专业的研究生,还成了一位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男子汉”。当时在大学校园,很多有志青年都有我这样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经历。而且我在诗中最喜欢用的意象是“僵尸”,绝大部分诗都很消沉,正是唱着“忧伤又美丽”的歌安慰了我的“寂寞”,驱逐了我的“迷惘”。我写诗从来不发表,纯粹是为了抚慰自己的心灵写作。那种写作如同我现在研究的诗歌疗法中的“书写表达”——通过写诗使自己的心理更健康。我的写诗经历可以用来理解《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消极词语或阴沉意象,它们可能比流行的爱国诗采用的积极词语和明快意象,更能引起人的情感共鸣,更有诗疗效果。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蔡其矫的结论:“沃兹涅先斯基写的是‘我’和战争的关系,用圆周句式强化对战争的悲伤和愤怒。舒婷写的是‘我’和祖国的关系,也用了这种句式,增加痛苦和挚爱的深度,但又有创造性的发展。圆周句式大多出现在抒发强烈情绪的作品中,悲伤痛苦的情调最宜用它来渲染。”①诗人写悲伤痛苦并不能说明诗人的“软弱”,诗的“悲伤痛苦情调”更不能说明会削弱诗的“宣传鼓动力量”,而是有“以柔克刚”的效果。诗人这样写既是为了更好地抒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以自己的情感来打动读者,也是一种避实(政治)击虚(情感)的写作策略。
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可以轻易读出北岛《一切》中的“悲观”情绪,只是北岛的《一切》呈现的情绪更“绝望”,全诗如下:“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此时我比较在同一个月(1979年4月)舒婷写的两首诗,尤其是把两首诗与北岛的《一切》比较,试图还原两首诗的创作生态,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假设”:从作者的写作目的上看,是作者的“书写表达”而非“政治诉求”,两首诗并非“政治诗”而是“诗疗诗”,都是作者为了安慰自己、抒发甚至宣泄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的诗疗诗。情感既有个体情感,也有社会情感及政治情感。不可否认的是,政治情感与政治热情使他们的以诗疗为目的的“抒情诗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味成以诗教为目的(启蒙甚至宣传目的)的“政治诗写作”。或者说,诗教目的是“显性目的”,诗疗目的是“隐性目的”。舒婷在写这两首诗时,尤其是在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两种目的“纠缠不清”,导致这首诗的多种功能。
“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②北岛、舒婷那一代诗人更愿意接受这个激进的浪漫主义诗观,争当雪莱所言的“立法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多年以后,北岛回忆了那一代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的诗歌生态及政治生态:“在70年代,个人命运与国家甚至世界的命运连在一起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当时面对的现实。”③“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文化革命成了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正是一群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④
正因为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鸿鹄大志”,才会常常处在心理学上所说的“亢奋状态”甚至“躁狂状态”,极端的希望也会带来极端的绝望,也容易出现“郁闷”“消沉”“困惑”“迷惘”,因此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大胆承认“迷惘的我”,这句诗真实地呈现出那个时期青年人的心理状况。它的含义及表述方式如同北岛的《回答》所说的“我不相信”,也如北岛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是烟云”,“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政治的动荡更容易让青年人产生幻灭感。查建英曾问北岛:“你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那么,你曾经有过一个虔诚的信仰期吗?是甚么经历触发了这种迷失感呢?请谈谈你的少年时代。”⑤北岛回答说:“除了阶级路线的压力外,由于我数理化不好,‘文革’对我是一种解放——我再也不用上学了。那简直是一种狂喜,和革命的热情混在一起了。‘虔诚的信仰期’其实是革命理想、青春骚动和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的混合体。由于派系冲突越来越激烈,毛主席先后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控制局势。最后他老人家干脆把所有学生都送到乡下去。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一代人——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⑥舒婷不像北岛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北京,但是仍然如那一代所有青年一样,受到了政治的冲击,仍然有政治热情与政治敏感。
两首诗采用的是诗疗诗中的一种特殊诗体——唱和诗。《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是与诗友北岛的“唱和”,是与别人的“对话”,作者在对话中获得了友情与自尊,给别人鼓劲也是在为自己加油,可以获得自信。《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是一种“对话”,作者与“祖国”的对话实质上是与自己对话,是一种自言自语式的“唱和”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内心独白”,比与别人对话更自由,诗中也出现了“自由”一词,更能够自由地宣泄自己被压抑的情感和思想。《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更像是舒婷应该给北岛的《一切》写的“劝世诗”,既是当时舒婷的“心里话”“真心话”,更是那一代青年人的“心声”。《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中有一些假大空的诗句,当时的舒婷绝无诗中呈现的作者那般“自以为真理在手”的自信,那么“理直气壮”。到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了一年多,青年人爱国的热情和参与改革的激情已经被激发起来,觉醒后学会了思考,便有了更多的迷惘,很多有志青年都成了“迷惘的我”,同时也是“希望的我”。1980年张枚同在《词刊》发表了《八十年代新一辈》,谷建芬很快为歌词谱曲,以《年轻人朋友来相会》为歌名,这首歌成为年轻人十分喜爱的流行歌曲,激励了一代人,堪称那个年代最励志的“爱国歌曲”。这首歌少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迷惘”,原因是那一代人的“迷惘”,可能是经过1979年北岛、舒婷等诗人作品的“暴露”性治疗,1979年的“迷惘的我”成长为1980年“希望的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希望”越来越多,1981年元旦前夕,陈晓光把他作词、施光南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送到了中央电视台,由杨淑清领唱,1982年彭丽媛带着这首歌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这首歌很快唱响全国。以上三首诗和两首歌可以呈现出那一代人的成长轨迹,甚至可以呈现出那一代青年的思想历程,反映出那几年的思想生态及政治形势。
“唱和诗的治疗作用”是我的“诗歌欣赏与诗歌疗法”课程中的专门章节,我总结说:“古代汉诗具有特别的唱和功能,和诗是文人群体的诗疗方式,‘唱和’过程即心理治疗过程:1.写诗宣泄了情感。2.写诗过程对文字、格律的追求转移了注意力,化解了悲伤。3.把诗传出去等待友人回信,也转移了注意力,化解了悲伤。4.读友人回诗既重视情感又重视语言艺术技巧,化解了悲伤。5.友人的诗增加了生存的信心。”这是我结合个人写唱和诗的经历与感受,在研究诗疗时得出的重要成果。它有助于理解《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疗功能,1979年4月舒婷处在写“唱和诗”的创作生态中,可以把她写的两首诗都视为诗疗诗中的“唱和诗”,通过两首诗的写作,她获得了友情与爱国之情,获得了自尊与自信,获得了自由与幸福。
老文艺理论家黄药眠于1982年7月16日写的《关于朦胧诗及其他》,有助于理解1979年北岛的“绝望”与舒婷的“迷惘”。他说:“现在再想谈一下这些朦胧诗理论的思想根源。为什么全国解放以来都没有这类诗出现,而现在却出现这些诗和歌颂这些诗的理论?这里肯定有它的社会根源……我认为它的主要思想根源,是由于对于目前形势主流认识不清,对于造成目前形势的历史原因,既不认识也不理解。他们只看见缺点,只看见困难,只感到忧郁和苦恼……他们这里所写的自然界的大灾祸,实际上只具有象征的意义,他所指的明显的是属于人世间的动乱,所以他们要站着愤怒,站着思考,站着迷惘!……茫茫然丢失了希望,只好彷徨于黄昏的郊野而无所归宿。自然在这些人眼中,一切都只好朦胧了。”⑦但是他并不像当时很多老人那样极端否定朦胧诗:“有人问我:‘你看朦胧诗可以写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写?没有任何人要限制作家以什么风格什么手法写诗的。而且就中国的艺术文学传统来说,从来没有人说要反对朦胧诗,反而有人赞成写诗在某种情况下,要有点朦胧的意境……但我并不主张只有朦胧诗才是好诗,更不赞成一个诗人只会写朦胧诗而不会写别的风格的诗。”⑧“在刊物上发表的诗,只要情绪健康,读了以后能令人奋发,令人深思,令人有新的感触,那就是好诗,应加以提倡。即使有点朦胧意味的诗也还可以,但对于那些思想意义不明、情绪灰暗、词语不通,令人费解的诗,那就只好对不起,送回原作者去自我欣赏了。”⑨
从黄药眠在当时极富有代表性的批判性话语中,也不难看出朦胧诗人的政治反叛性和诗学独创性,更可以理解《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给人的思想解放带来的诗疗价值。1981年,舒婷写的《神女峰》中出现了“新的背叛”一词,全诗如下:“在向你挥舞的各色手帕中/是谁的手突然收回/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当人们四散离去,谁/还站在船尾/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江涛/高一声/低一声/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为眺望远天的杳鹤/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首诗纠正了四年前写的《致橡树》的极端爱情观,受到了世俗男女的热烈欢迎。“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成为舒婷最有名的诗句,至今还在青年中广为流传。
1979年《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问世后,像《致橡树》一样成为“朗诵会的保留篇目”。《致橡树》成为“朗诵会的保留篇目”更多是因为人们尤其是女性的自发性喜欢,很多女青年还在酒场饭局等友人聚会的私人场所主动朗诵这首诗,它甚至是女青年谈恋爱时向男朋友“表白”的最佳诗作。几十年过去了,我还遇到多位中年女性在饭局中背诵这首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更多是受到官方的支持,成为“主旋律”诗作的代表作,还获得了1980年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作品奖。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官方诗歌大奖。在公众场合的朗诵会,尤其是由团委、工会、学生会等官方部门主办的朗诵会,这首诗必定是用来对听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灵丹妙药”。如果是妇联举办的朗诵活动,《致橡树》可以用来强化女性的“独立意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可以用来唤醒女性的“爱国情感”。即使进入了新世纪,它仍有“爱国主义第一朗诵诗篇”的地位。200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节日朗诵诗选》的“七月一日十月一日唱给党和祖国”栏目中,这首诗雄居首位,第二首是郭沫若的《太阳礼赞》,第三首是闻一多的《祈祷》,全栏目共18首。它的后面加了一段“朗诵提示”,配了由著名语言表演艺术家乔榛和丁建华的“朗诵示范”录音光盘。在封面上标明是“影视院校考生必备书”。这本书是《诗刊》副主编、女诗人李小雨编选的,朗诵提示的作者是路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这本书中的重要位置和“朗诵提示”都说明这首诗具有强烈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这一功能不“时过境迁”。在同一时代也有一些例外,如诗人杨建民做总筹划的中央电视台2007年的“新年新诗会”的“祖国之恋”栏目中没有出现这首诗,甚至整场朗诵会都没有出现舒婷的诗作,包括《致橡树》与《神女峰》。在东南大学“诗歌欣赏与诗歌疗法”通识课上,在各地做的诗疗讲座中使用这首诗时,我采用的方式是让受众听著名女朗诵家丁建华的朗诵,或者让听众集体朗诵,我明显发现受众不仅因此获得了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受到启迪,甚至灵魂受到震撼,还获得了美的(辞藻的美、意象的美、朗诵声音的美等)享受,还获得了审美快感、心理快感,甚至生理快感。
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明显发现作者的身份感几乎由独善其身的“穷者”变成了兼职济天下的“达者”。这首诗虽然写到了苦难,却有当时的“伤痕文学”少有的亮色,它的写作根本不是怨天尤人的“怨妇写作”。因此弄清它的写作时间十分重要,所以在2018年1月23日,我在写本文的过程中特地发短信向舒婷的丈夫、诗评家陈仲义求证:“陈老师,我正在为《名作欣赏》诗疗专栏写解读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文章,急需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写于1976年,发表于1979年吗?王珂”。陈老师的短信回复是:“写于1979年4月,发于1979年《诗刊》第7期。”
他的回答证实了我的“此诗应该写于1978年或者1979年”的判断,这个判断来自我的个体阅读直觉,还有我将这首诗称为“诗疗诗”进行群体传播的经验。1977年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是思想大解放年,不仅中国想通过改革开放在世界上获得“身份感”,每一个中国人都想获得“身份感”,尤其是获得“中国公民”及“现代中国人”的“身份感”。当时每个中国人都想获得幸福,人的幸福的两个基本要素是“自尊”与“自由”。这些正是这首诗的写作动力,也是它在今天能够被人喜欢,即使在诗疗中作为爱国教育的诗作,也不会被强调个性解放的青年大学生抵制的重要原因。在诗疗教学或诗疗讲座中,我使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来培养高级情感,具体为培养受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受众却能如同“寓教于乐”“寓教于疗”,在诗疗中完成诗教,没有对我这位“革命的‘左’派老师”产生抵触感。这种“歪打正着”的教学成果令很多“德育老师”羡慕。我的通识课居然被列为东南大学2017年立项的十门在线课程之一,2018年录制好后放在网上,推向全国的大学生。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内容上产生诗疗效果,主要原因是它可以让人获得身份感及自我意识。尤其是诗中“我”的运用,说明诗人对身份感的渴望,证明诗人是一个有能力“说‘我’的”现代人。“人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能说‘我’的动物,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身。动物与自然是合为一体的,尚未超越自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得到身份感的需求。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自我的概念,需要说和需要想:‘我就是我。’因为他不是活着,而是生活着……他必须有能力作为他的行动的主体来感受自我。与关联性、根源性和超越性的需要在一起,这种身份感的需要是如此重要和紧迫,试想,如果一个人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的话,他一定会发疯。人的身份感是在从母亲和自然的‘基本纽带’解脱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个仍然与母亲具有一体感的婴儿是不会说‘我’的,他也没有说‘我’的需要。只有当他把外部世界看成独立于自身而且与自身不同的时候,他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最后学会使用的词汇之一就是‘我’,也就是指他自己。在人类的发展中,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的程度取决于他脱离其部族的程度和个体化发展的程度。一个原始部落的成员可能会用‘我是我们’的形式表达其身份感;他还不能把自己视为一个‘个人’,存在于他的集团之外。……‘我怎么知道我就是我’这是一个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是由笛卡尔提出来的,他是这样回答了这一身份感的问题的。他说:‘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⑩“身份感的问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或者是一个与我们的头脑和思维有关的问题。了解身份感的需要源于人类存在的状况。而且,这种需要也正是人尽力奋斗、追求的源泉。由于没有‘自我’感就无法保持人格健全,因此,我便尽一切努力来获得自我感。这种需要驱使着人们竭尽全力去争取社会地位,求得与社会协调一致。有时,这种需要比肉体生存的需要还要来得强烈。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要,放弃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为的就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与群体协调一致,并由此获得一种(哪怕是想象的想象的)身份感,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⑪
人有身份感才能有自我意识,才能获得自由感。“自有诗歌以来,诗人和诗论家就给诗歌开列了数不清的功能,诸如美感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武器功能、陶冶心灵的功能、提高艺术修养的功能、交际功能、医疗功能等。就假定这一切功能都是诗所具备的,那么也不是诗歌自身能直接取得的,而只有通过影响读者的自我意识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发现自我,进而达到自我与世界的融合,使心灵获得空前的自由感,这才是诗歌最根本的心理效应。”⑫“认识自我不是被看成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它不仅仅是好奇心或思辨的问题了,而是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⑬“每个具有创造力的人都是合二为一的,甚至是异质同构的复合体。他既是有个体生活的人,又是非个人的、创造的程序(creative process)……他的艺术性格承受了过多的反对个人性的集体心理生活。……他是一个具有更高意义的人 一个集体人(collective man)。他承担和呈现着人类的无意识的心理生活。”⑭由于人的集体人特性,社会生活给予个体的人的自由是相对的,人必须生活在自由与法则的对抗与和解中。社会人或集体人的自由空间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总是被社会的法则制约着,使人不得不压抑着狂欢的天性,过着被他律和自律双重限制的生活。“不仅在哲学的语言里,而且在政治学的语言里,自由都是一个最为含糊不清的术语……即不管是在个人生活里还是在政治生活里,自由经常是被看作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特权。”⑮《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有助于人正确理解“自我”和“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含义。它的作者或读者都可以获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社会精英”身份,这种身份感可以给人自由和自信。诗疗的最大目的正是培养自信,有身份感的人是自尊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也是有社会感的人,这种人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好的社会角色意识和社会协调能力,可以更好地保持心理平衡,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协调能力是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健康的三大指标,后者是前两者的基础和保证。
“人的自主意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⑯人的身份指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为职称或职务的高低、年龄的大小等,本质是人在社会团体中受尊重的程度,即重要性。所以把身份感与社会感可以相提并论,把身份感视为社会感的重要内容,也有必要弄清两者的差异。“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⑰如果采用阿德勒所说的个体心理学的观点,把一切人类问题分为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三类问题,具体为现代人必须有一个职业,是某个企业或团体中的一员;必须参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员;必须有一个家,是家庭生活中的一员。那么良好的身份感及社会感有利于解决这三类问题。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就是解决这三类问题的具体方式,目的是确立“封建社会”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福柯这样描述任何社会运作系统的存在方式:“起源于三个宽阔的领域:控制事物的关系,对他者产生作用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中的任何一组对其他都是完全无关的……但是我们有三个特殊的轴心:知识轴心、权力轴心和伦理轴心,有必要分析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⑱伦理轴心与权力轴心异曲同工,在社会生活中都可以确定人的身份,通过确定人的身份感来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甚至规训。如福柯结论说这种社会道德规训惩罚行为有可能导致人患上精神病,成为“疯人”,被关进“疯人院”。这与弗洛伊德研究出的人类病态的起因相似:“精神分析开始于对关系到心灵一切内容的东西的研究……人类不仅是性生物,而且还有比性更高贵更高级的欲望冲动……人类的病态,是起因于本能生活的要求和人类本身所产生的反对本能生活的抵制之间的冲突……”⑲弗洛伊德还提出了自我、本我和超我理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可以呈现出人的自我、本我与超我的复杂关系,呈现出三种情感方式和处事方式。
阿德勒更明确地总结出精神病的病因是缺乏社会感及生命意义:“社会感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错误的‘生命意义’的共同之点和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的共同之点。所有失败者——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同类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处理工作、友谊和性生活中的问题时,都不相信这些问题能通过相互合作得到解决。他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一种个人所有的意义。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从个人成就中获益。这种人成功的目标实际上仅仅是谋求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而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⑳阿德勒所言的“社会感”“生命意义”与许又新的“道德情感”“道德愉快”有相似之处,我在诗疗中强调“高级情感”“诗教”,正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作为培养高级情感最重要的诗疗诗,正是看到了这首诗的写作和阅读,都可以让人获得“社会感”及“道德情感”,让生命更有意义,既获得一种“个人优越感”(身份感),又获得“社会优越感”(社会感)。
积极心理学最关注的是自尊与自由,给人自尊与自由才能给人自信。由泰勒(Talben Shalar)主讲的哈佛大学《幸福课》(Positive Psychology)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幸福感最重要的要素是自尊,总结出自尊的六大支柱是:有意识的生活、自我接受、自我负责、自我保护、有目的的生活和个人诚实。《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与这六大支柱都有关系。说出自己的弱点,如承认“迷惘的我”对应“自我接受”和“个人诚实”;“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对应“有目的的生活”“有意识的生活”“自我负责”和“自我保护”。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写作行为和阅读行为都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学上的“认同”行为,尤其是族群认同,这种认同与文化心理有关,认同的目的也是确立身份感及社会感。“认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存在将社会划分为‘我们’与‘他们’类别的一种强烈的心理或情感成分……族群认同是人们与不同起源和认同的人们之间互动的产物……个体的族群认同并非是绝对的,特定个体取决于社会情境而有着一些不同的族群认同。认同既可以是自己选择的,也可以是强加的,如政治社群对成员的归属感和共同目标的灌输。这种族群认同的情境性,表现为具有不同层级性、等级化的认同……尤其是‘历史’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它可以被选择、失忆与重构。实际上,族群实体是不断被发明和想象的,关键在于这一认同是如何被建构和操控的,有时会体现出认同研究的心理分析倾向。”㉑写作或阅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都是在“发明和想象”“族群实体”,通过诗歌重新塑造了“祖国(中国)”的形象,确定了爱国情感的特质,甚至可以说在教会人们,尤其是当时的“迷惘的一代”,如何振作起来,“爱我中华”。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提出的爱国策略具有“强烈的心理或情感成分”,与当时的爱国诗篇迥异。当时诗人的爱国方式有“歌德”式(歌颂)与“缺德”式(暴露),前者可以称为“政治抒情诗”,后者可以称为“政治讽刺诗”。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并不细分,在当时及现在的新诗研究界,把两者统称为“政治抒情诗”。由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就流行歌功颂德的诗作,连胡风、徐迟、艾青等人也写了“颂歌”,尽管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一些诗人,尤其是中老年诗人因为习惯了“歌德”式写作,仍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天真歌唱”,引起了部分青年诗人的反感和反叛,有些“偏执”地采用了当时被“歌德派”骂为“缺德派”的针砭时弊的暴露式写作,产生了一批在民众中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北岛的《一切》、骆耕野的《不满》,最有影响力的是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新诗诗人,尤其是朦胧诗诗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以当时的“朦胧诗论争”也几乎由“艺术之争”变味为“政治之争”。在这种复杂的诗歌生态及政治生态下,诗人不得不通过“站队”或“表态”的方式来获得自己在诗坛或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身份感”,甚至身不由己地写“政治诗”——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其实写两种诗都有利于诗人的心理健康,那时的诗人很容易“激动”甚至“激愤”,很多诗人还迷信“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因此写歌颂的诗与写批判的诗都常常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都可以说是宣泄压力的心理治疗行为,都可以说“无可厚非”。
舒婷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女诗人,生存境遇的巨变让她的抒情视野及政治视野扩大了很多,写作的目的和生存的意义也变得“伟大”起来,使她有了新的写作压力和写作动力。习惯并擅长“诗缘情”的她想当“诗言志”的“大诗人”,当时从官方到学界提出的“大诗人”的“标志”都是“为祖国而歌”,“为人民而歌”,那时大学中文系使用的文艺理论教材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其中一节专门讲“文学的党性原则”,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甚至主张文学是政治的“传声筒”,是“宣传工具”。虽然舒婷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文学理论教育,但是她在1977年成名后已经受到了作家协会的重视,受到了作家协会的“教育”甚至“规训”,自然会受到“主旋律”写作观念的影响。但是当时的作家协会,尤其是她所在的福建省作家协会比较开放,“三崛起”之一的孙绍振正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福建省的主要领导项南也是著名的“改革派”。爱国主义题材是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都喜欢的“主旋律”题材。所以舒婷由“诗缘情”的“爱情诗人”向“诗言志”的“爱国诗人”的诗风转变并不奇怪,转变不彻底更无可厚非。正是这种转变的不彻底,让我们获得了一首当代新诗史上难得一见的“抒情政治诗”而不是“政治抒情诗”,更不是“政治讽刺诗”。
这种“抒情政治诗”的写作目的和阅读目的首先是“抒情”,然后才是“政治”;先是“诗疗”,然后才是“诗教”;先是“启蒙”,再是“宣传”。“诗歌的三个功能与心理危机的三种干预方式很相似。首先,诗的‘言志’功能有利于改变人的观念。……‘言志’的诗可以催人上进,让人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其次,诗的‘缘情’功能有利于改变人的体验。缘情的诗可以宣泄人的压抑情感,稀释孤独。再次,诗的‘宣传’功能可以改变人的行为。……很多人就反感诗歌的‘宣传’功能。甚至有人认为,1949年后‘十七年诗歌’是无价值的。我并不这么认为。”㉒不同类型的诗产生了不同的功能,有的一首诗具有多种功能,为诗疗创造了条件。《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具有多种功能,可以产生多种治疗效果的诗。
受时局影响,舒婷确实也想完成由“个人化写作”向“社会化写作”,由官方意义上的“小诗人”向“大诗人”的“华丽转身”,尤其是完成由业余的诗歌爱好者向专业诗人的“职业转变”,但是她很快发现写宏大题材,写当时流行的那种“主旋律”的政治诗或哲理诗不是自己的长处。她写于1980年2月的《一代人的呼声》“踌躇满志”地宣布:“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为了百年后的天真的孩子/不用面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她发表于《福建文学》1981年第2期的《生活·书籍与诗》一文“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成不了思想家,哪怕我多么愿意,我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大信任思想的加减乘除。”㉓但是这种转变还是在以后的诗作中留下了痕迹,如1981年写的《神女峰》几乎是将两者结合的“爱情哲理诗”,寻找出爱情的“真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由抒情诗诗人向政治诗诗人的转变不成功的原因是她本质上是一位纯粹的抒情女诗人。尽管舒婷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表于《今天》的《中秋夜》中有这样的诗句:“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但是当时的《福建文学》围绕舒婷的诗展开了“争鸣”,一些评论家指责她的诗“思想格调低沉”,甚至还有人认为她的诗作“缺乏时代精神”。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因为评论家的思想僵化,更是因为舒婷在诗作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女人意识”。如徐敬亚在1981年8月写的《她的诗,请你默默读——舒婷〈心歌集〉的艺术构成》所言:“像每个当代青年一样,舒婷,这个以表现感情的细腻微妙见长的年轻诗人,也与我们一起分担生活所给予的情绪、偏见和误会,以自己的人格的力量来承担这个时代深深的烙印……她诗中蕴藏着的女性的真挚、柔美和凄楚动人,为30年来的诗坛所绝无仅有。”㉔徐敬亚对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中的爱情诗也不太满意,认为社会性太多个人性太少,太重视心理性情感忽视生物性情感。他在1986年11月说:“今天看来,朦胧诗人们,其实是十分可爱的善男信女……他们饱满而充满质感的自我和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使他们鄙视和忽略了性的体验。他们的爱情诗压缩了人的生物本质因素,没有生动真切和强烈的性感受。多是对人类普遍情感的暖调歌颂,基本上没有超过人伦道德的范围。在当时‘爱’与外部世界毫不相容的情况下,他们无暇体味爱的内部微妙,或者说,还有点放不下社会批判者的勇士风度,无法性恋起来。”㉕
舒婷1977年写了《致橡树》,1979年写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81年写了《神女峰》。三首诗都被认为是她的代表作,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新诗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比较三首诗的写作风格,不难发现她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为北岛那样的“政治抒情诗人”,事实上,百年新诗史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政治抒情诗人。但是三首诗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所以都被视为“宣言书”,如《致橡树》与《神女峰》被吴思敬、吕进等权威评论家视为“女性人格独立宣言”。直到今天,我也赞成我的两位老师的观点。但是从诗疗写作角度,即把舒婷写这些诗的目的还原到她是为了心理治疗而写作,来探讨三首诗的写作动力,我发现舒婷的一大写诗特点:她把爱情诗当政治诗,结果把爱情诗写成了“宣言”;把政治诗当爱情诗写,结果把政治诗写成了爱情诗。此处用“特点”更多是指代“优点”而非“缺点”。所以有人认为《致橡树》不是爱情诗。关于这首诗主题的多样性和接受者的反映的复杂性,可以从1999年吕进的这段言论中看到。“不少人认为《致橡树》是一首情诗。在80年代的朦胧诗争鸣中,还有不少论者将‘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说成是性事描写。其实,诗的本文并非如此。但诗歌鉴赏是一种复杂的诗美创造活动,一些读者要把它当成情诗来读,甚至乐意在婚礼上朗诵,这是读者的权利。对女性独立人格的追求,是舒婷诗歌的常见主题。”㉖
此文为2015年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新诗功能学”和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诗现实功能及现代性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百度百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http://baike.sogou.com/v7562611.htm?fromTitle=祖国啊%2C我亲爱的祖国
②〔英〕雪莱:《诗辩》,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7页。
③陈炯、北岛:《用“昨天”与“今天”对话》,北岛:《古老的敌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 Limited,2012.p.66.
④田志凌、北岛:《今天的故事》,北岛:《古老的敌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imited,2012.p.102.
⑤⑥查建英、北岛:《八十年代采访录》,北岛:《古老的敌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imited,2012.p.71,p.72.
⑦⑧⑨黄药眠:《关于朦胧诗及其他》,陈学虎、黄大地:《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第650页,第641页。
⑩〔美〕埃里希·弗罗姆:《健全的社会》,王大庆、许旭虹、李延文、蒋重跃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8页。
⑪〔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8页。
⑫吴思敬:《诗歌鉴赏的心理效应》,《诗学沉思录》,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⑬〔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⑭G.G.Jung.Psychology and Litreature.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1972.pp.185—187.
⑮〔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338页。
⑯Denys Thompson.The Uses of Poet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3.
⑰〔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周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1—12页。
⑱John McGowan.Postmodernism and Critic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34.
⑲〔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程小平、王希勇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5—56页。
⑳〔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周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13页。
㉑庄孔韶:《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㉒王珂:《新时期30年新诗得失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89页。
㉓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㉔徐敬亚:《她的诗,请你默默读——舒婷〈心歌集〉的艺术构成》,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215页。
㉕徐敬亚:《禁地的沉沦与超越——现代诗中的性意识》,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㉖吕进:《女性诗歌的三种文本》,《诗探索》1999年第4期,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