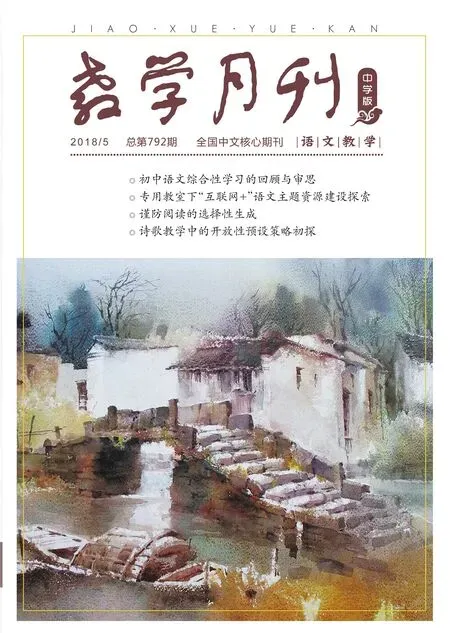从两个“醉”看柳宗元的自我救赎
黄勇智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嘉兴南湖高级中学,浙江嘉兴 314000)
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永州。地处偏僻、风景秀美的永州山水由于柳宗元的到来被引入了文学殿堂。《始得西山宴游记》就是著名的“永州八记”的第一篇。全文共2段,凡306言,其中,“倾壶而醉”之“醉”与“颓然就醉”之“醉”最值得斟酌玩味。
一、“倾壶而醉”之情态
文章一开篇,作者便点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心情。“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惴,惴惴不安;栗,战栗。两个词连用,表明恐惧程度之深。而“恒”字,则表明恐惧之情的长久,并非偶尔出现。他为什么成为“僇人”?为什么如此恐惧?
公元805年,王叔文、王伾等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但不到半年便宣告失败。参与这场运动的二王八司马被一一发配僻壤。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到了永州,他的政敌仍然没有放过他,继续对他诽谤,攻击,加上王叔文、王伾相继死于边地,因此,柳宗元深知其间之凶险,恐惧是正常的。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说:“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可见这种恐惧的心理一直延续萦绕在他的贬谪历程中。
“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施施”“漫漫”,描摹出了行走的状态——缓慢且漫无目的,这完全是一副消磨时光的心情与姿态。旁边的风景与“我”无关,“我”只不过是消解内心的痛苦而已。柳宗元自己曾说:“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他和大多数失意文人一样,被迫到山水里寻找安慰。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请注意“日”字,每天都要去高山深林,可见其出游之频繁。真的是每天都有美好景色吸引着他吗?“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此句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到了一处地方,就拨开草坐下来,拿出酒壶,一饮而尽,然后大醉。“倾壶”写出了作者“上”“入”“穷”等皆为醉而来。义无反顾的醉流露出作者根本不是来看景的,他不留恋景而只是为了醉。他消沉苦闷,他发泄逃避,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一切都无所谓,但貌似洒脱的内心却极度痛苦和无奈。阮籍,“竹林七贤”里那个“穷途末路”之人,或放声大啸,或登临山水,天天沉醉于酒中。那种文人且恐且忧、且避且躲的无奈与痛苦,让阮籍处世一直如履薄冰。阮籍醉酒,既是自我麻醉的良方,也是自我保全的手段。[1]此时的柳宗元不正和他一样吗?
二、“颓然就醉”之救赎
但是,发现西山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我们先看看作者笔下的西山:“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作者居高临下,从形、色、态多角度描绘了所见的景色。群山万壑好像争着、挤着奔赴眼前,重峦叠嶂,美不胜收;青山白水相互萦绕,天地合一,浑然一体。这样的美景一下子让他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作者之所以在此处重笔泼墨,并把西山之游看作是“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是因为他在西山风光的饱览中领悟到了它与“我”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的契合点,即山的高大——人格精神的傲然独立。它被弃置僻地无人知晓与“我”被贬蒙辱而无人理解是一致的;它“特立”超拔与“箕踞”兀傲的“我”是相通的。西山,不类培,卓然不群,自成高格,是“我”柳宗元的写照。在对山水的发现中,“我”发现了自己,体察到作为“人”的地位与尊严。作者在叙记山水中清洗着自己的灵魂。在以后的一发而不可收的山水游历中,作者继续如饥似渴地寻觅着存在于自然中的真善美,以此实现自己所崇尚、所具有的完美人格的再现。如《钴姆潭西小丘记》中对“石”的描写,“其石之突怒堰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石头峥嵘、怪异、嶙峋,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给人以硬之感、力之美,象征正直文人信心十足地接受挑战,不媚世俗,精神独立。明人茅坤曾指出柳氏是“借石之瑰玮,已吐胸中之气”[2]。作为身处逆境之时坚贞不屈品格的写照,作者正是在对自然美的发现和创造中,以对自然美的超越,完成了对理想人格的比附。
“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作者的神思悠悠然与天地之气相应,而无法找到它的边际;作者的情怀浩荡与大自然共游,而不知道它的尽头。看来,他着实放松和释然了。西山的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天性灵秀、洞察万物、与世无争、隐而不显,才是柳宗元真正看清楚想明白的地方!高贵而谦和的生命体验终于化解了他心中巨大的忧愤和哀伤,是西山教会了他应该如何看待生活、如何处于逆旅而不倒的要诀!
再看这次的醉态,“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颓然”,描述出了一种似醉非醉、将醉未醉的状态。此时的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倾壶而醉”的“麻醉”,而是一种“此中有真意”的自得其乐的“陶醉”了。《赤壁赋》中说喝酒喝得“不知东方之既白”,这里的柳宗元喝得“不知日之入”。傲岸的人格尊严与“特立”的西山相融,忘形亦忘情,于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此时的柳宗元心神凝定,形体仿佛已经消散和万物融合为一体。他感到了超脱而旷达,忘却了自我,也忘却了烦忧,获得了精神慰藉。先前的“惴栗”之情荡然无存,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心旷神怡的境界,与苏轼笔下的“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是何等一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次心灵的救赎,也完成了他生命的反转!
两个“醉”,两种心态,两种境界,在作者自身情感力量的凝聚中,升华为具有独特内涵的审美对象,鲜明地昭示了作者的理想、愿望及其人格光辉。
[1]米舒.阮籍之醉[N].新民晚报,2013-2-1(B06).
[2]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