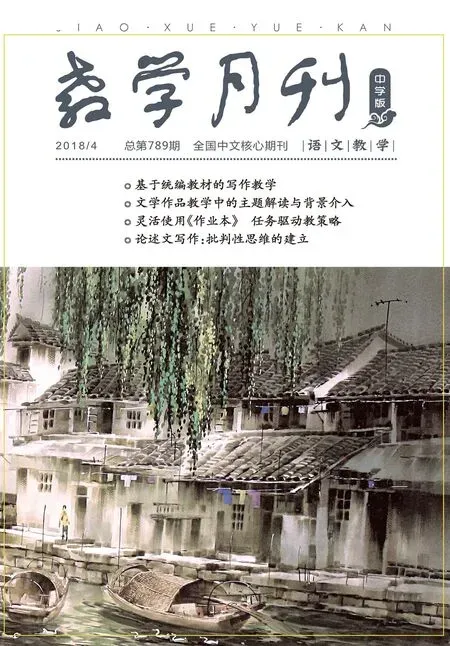《祝福》中的经济因素
首作帝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阅读鲁迅的乡土小说《祝福》,不应当忽视经济因素。多年以来,人们从不同视角剖析文本,却遗漏了经济因素。《祝福》中存在各类经济因素,从中可以窥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浙东农村的社会现状。经济因素真实地反映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准确衡量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砝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或冲突往往取决于经济因素。从语言审美考察,《祝福》中的经济因素与叙述语言之间富于默契和融通,使得小说呈现出精确、透明、简洁的语言风格,达到了和谐的境界。《祝福》中的经济因素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形成与内地乡土小说最本质的区别。
一、小说中存在的经济因素
《祝福》最突出的经济因素书写在于:鲁迅揭示出了极为深刻的贫困问题,它从旧道德观念中延伸出了新的含义,即贫困与人的懒惰无关,哪怕像祥林嫂这么勤劳和能干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堕入贫困的深渊;同时,贫困向农村蔓延,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突发事故,都会导致贫困的必然爆发。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出现贫困绝非偶然”,“行乞是贫困的结果”,“贫困已成为一种经济现象”。[1]祥林嫂沦为乞丐,这是贫困的结果,它具有无法避免的趋势,以她为代表的行乞行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普遍经济现象。鲁迅为此运用逼真的描写手法:“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两个分句,描写祥林嫂的行乞肖像,竹篮、破碗、拄杖,皆为行乞的标准工具,再加上苍老的年纪和褴褛的衣裳,没有任何人比她更能代表现代国人乞丐形象。故而紧接着,鲁迅以一个兼具解释性和概括性的中心句子结束这个段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心句子极为独特,鲁迅居然连用三个属性和作用完全相同的程度副词,“分明”“已经”“纯乎”,这简直不可思议。按照常理,“她分明是一个乞丐了”,“她已经是一个乞丐了”,“她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三个句子在表意上没有任何差别,均是强调人物身份,而且内容明晰,毫无歧义,因此可能的解释是:鲁迅借此不仅表达祥林嫂的贫困,而且表达底层民众的贫困,贫困的经济现象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和广泛性。
贫困,意味着商品和金钱的匮乏,这是一种与商业、农业和工业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非常符合这种贫困现象,以至于无法被视而不见和保持沉默。别说是具有启蒙色彩的知识者“我”,以及象征权力的统治者鲁四老爷,就连和祥林嫂属于同一阶级的鲁四老爷家的短工,也有对这一贫困事实和现实的朦胧认识。祥林嫂死后,鲁四老爷骂她“谬种!”“我”连珠炮询问短工三个问题:“祥林嫂?怎么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短工最后回答:“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短工说到祥林嫂死亡的原因,显得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祥林嫂和短工都给鲁四老爷做工,在身份地位上是一致的,很显然短工对这一判断有所保留,但同时又看清了本质,因此只得进行折中回答,摒弃了关于贫困的清晰思考。这使得消除贫困和解放国人的任务愈发艰巨,也体现了鲁迅小说中国民劣根性的普遍存在,以及作家对这一传统陋习的严峻批判。其他贫困的经济现象还有,祥林嫂的小叔子娶不起媳妇,贺老六患伤寒无钱治疗,透射出农村的经济凋敝、观念落后和医疗薄弱等社会现实。
《祝福》中的经济因素隐藏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当中,从而具有了历史和民俗文献资料的功能和特征。日常经济因素包括做工薪酬、会计记账、商品价格、货币换算、婚恋财礼等等,极为丰富和翔实。例如,祥林嫂的做工薪酬为“每月工钱五百文”,尽管比较低,但是至少体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原因是她不偷懒,很卖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从中可以看见社会的平等和进步倾向。在小说中,祥林嫂的做工薪酬从来没有支取过,而是记在账簿上,必要时候一并支付清楚,共有两次:一次是祥林嫂的婆婆带她回家,“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另一次是祥林嫂为捐门槛,“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从中可见现代中国与西方接轨,盛行会计记账的方式。商品价格不再是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以物易物或锭银估算,而是明码标价。“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这个是城里的价格,农村根本消费不起,“价廉物美”揭示了城乡的巨大贫富差距,“增价”又涉及价格变动和通货膨胀,包含着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祥林嫂捐门槛的价格也相当明确:“价目是大钱十二千。”后来,祥林嫂还把它换成墨西哥银元,“换算了十二鹰洋”,可见货币流通的多样化,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行政区域的各自为政和四分五裂。婚恋财礼方面的经济因素,城市和农村,山里和山外,堪称天壤之别。祥林嫂嫁到山里去,她的婆婆“到手了八十千(财礼)”,而给她的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这当中也折射出人们善于盘算、计较和谋划的经济观念。
鲁迅为《祝福》中的经济因素留下了大量标记,作为一个连标点符号都用到极致的伟大作家,经济因素不应当只是普遍认可的时代背景,而是上升到与人物、主题、情节相提并论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二、经济因素反映人际关系
《祝福》中的经济因素反映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类社会产生于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中,“它受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2]。可以说,经济因素是准确衡量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砝码,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或冲突往往取决于经济因素,它带来的既有看得见的身体行为的变态,也有看不见的心理情感的变异。
对金钱的渴望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人们背离言行,一切以赚钱作为衡量标准。祥林嫂是《祝福》的主人公,但是当牵涉经济因素的时候,她往往成为行动的傀儡,任由别人摆布的棋子。卫老婆子为了赚取荐头费,反复几次推荐祥林嫂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又厚着脸皮带着她的婆婆来辞工。祥林嫂的婆婆更是奸诈、残忍和厉害,明明确定祥林嫂已经辞工,并且占有她工作几年的全部薪酬(“一文也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在河边淘米的祥林嫂绑架走了。原因无非是,这家的工钱已经到手了,没有剥削剩余价值的底料,不如早点把她卖到山里,实现商品价值,“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做聘礼?”不把祥林嫂当人,而把她当“注钱”,交换“聘礼”。祥林嫂的生命于是被牺牲,她的独立生命价值也被毁灭,为了满足他人对金钱法则的绝对要求,她俨然成为了原始社会的某些可怕仪式的牺牲品。可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仍然停留在愚昧和吃人的凶残时代。
寺庙作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清规戒律的圣净之地,也沦落到了向金钱势力低头的丑恶、可怕地步。祥林嫂去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应当跟祥林嫂的寡妇身份和“不洁”品行有关,但是后来又答应了,鲁迅为此单独写下了一个句子:“价目是大钱十二千。”小说中“钱”字出现6次,组成的词语统计如下:“大钱”1 次,“讨钱”1 次,“注钱”1次,“工钱”3次。其他5次都是比较客观的说法,唯独“大钱”投注了鲁迅的主观情绪:现实中不存在“大钱”“小钱”计量单位一说,“大”作为形容词体现了强烈的夸张和讽刺色彩,佛门和僧人也已蜕化为染指经济因素的帮凶;“价目”系商品买卖明码标价行为,与传统的“布施”“化缘”美德完全背道而驰;另外,鲁迅擅长创制短句,这个孤零零的短句则突显了金钱经济因素的膨胀和变形。鲁迅最终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功能,以否定“传统美德”为目的来达到震撼人心的美学效果。
嫌贫爱富带来心理情感的变异,导致人们将贫困和罪孽混为一谈。短工提到祥林嫂的死亡“是穷死的”,鲁迅接着写道:“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短工和祥林嫂本为同一阶级,却因为不在同一条藤上,完全漠视生命,“淡然”表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抬头向我看”,不屑于对祥林嫂之死发表更多言说和交流,而将其归结为“罪有应得”。镇上的人们对祥林嫂的态度也是如此,跟她讲话的时候,“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大家都以无法感受和想象的方式来理解祥林嫂讲述“阿毛之死”的悲惨故事,彼此之间的心理鸿沟在不断地扩大,随之而来的结果也是将其定性为“罪有应得”。柳妈恐吓则将这种“罪有应得”的恶果具体化:“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正是普遍存在的心理变异,祥林嫂一步一步被推进经济骗局和生命毁灭的现代悲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冷漠和残酷的想法来塑造世界和决定他人,而祥林嫂做了无谓的牺牲品。
《祝福》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们沉沦于经济因素而进行的立体描绘,揭示了向金钱看齐和以贫富作为衡量标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体现了鲁迅在洞悉社会民情和心理深度方面,尝试作出的艰难探索。
三、经济因素影响语言风格
《祝福》中的经济因素与叙述语言之间富于默契和融通,使得小说呈现出精确、透明、简洁的语言风格,达到了和谐的境界。“每一种语言,其唯一的意图在于期待,以语言的和谐为起点。”[3]鲁迅极为细致地打磨《祝福》的语言,力图融经济因素与叙述语言为一体,哪怕是焊接也做到天衣无缝。
鲁迅从浙东地区日常话语中挪用极为流畅和清晰的叙述语言,来传达经济因素镜射出来的时代语境。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超越了个人的回忆,结合集体的经历,使得作家的个人智慧与独特的历史内涵有效碰撞,微妙而准确。“我”回到鲁镇的当天,遇上沦为乞丐的祥林嫂询问“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问题,“我”以“说不清”作为敷衍,且自我安慰:“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紧接着以“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填塞不安和无聊。“我明天决计要走”,不仅是美食的经济诱惑,同时也是逃离行乞的经济苦痛。前者是个人的享受和记忆,它更多联结身体感官;后者是集体的遭遇和烙印,它更多联结精神思索。这样,“我”在心灵中真正体悟到的,语言不仅是实现互相理解的交流渠道,而且也反映一个真实的世界,那是一个创造自身的精神和联系外部的事物互相建立起来的世界,以此不断地从语言中汲取新的东西,又不断地把新的东西赋予语言。
在中国文化语言中,与死有关达几十种说法,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地区,各各对号入座,约定俗成,形成言说的机制。鲁四老爷说的是“谬种”,使用了死亡语言禁忌,表现了对祥林嫂作为家族之外的“异类”的排斥和厌恶心理。鲁四老爷家的短工说到祥林嫂之死,使用的词语是“老了”,系来自民间的死亡语言禁忌。显然,同为死亡语言禁忌的“谬种”和“老了”有本质区别:“谬种”具有专用性和针对性,充满了审慎和煎熬,必欲除之而后快;“老了”相对具有通用性和普适性,充满了随意和平淡,完全置之事外。“我”对祥林嫂之死,使用了最通用的词语“死了”。统计这三种死亡词语出现的频率:“死了”总计5次,“谬种”和“老了”各计1次。这说明,死亡语言禁忌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遭到消解,而以正常的词语取代。这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含有鲁迅一以贯之的反抗精神。贫困和行乞作为经济现象出现在小说中,死亡则是这种经济现象的后果,不同的说法透露出不同的思想境界。正如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说:“语言仿佛由此增加了透明度,我们透过它可以窥测到讲话者的内在思想。”[4]这样,哪怕是三种不同的叙述语言,当它们受制于经济因素,自然碰撞出金石火花,最终变成赤裸裸的光骨头,塑造了成熟的现代文学语言。
阅读《祝福》,就是接触一种记录经济数字无比丰富而又相当精确的语言载体,就是接触鲁迅从中传递出来饱含丰富创造能量的语言模式。我们说话的语言似乎是单个音符,而《祝福》的叙述语言前后呼应,循环往复,构成一部完整的交响曲。祥林嫂刚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每月工钱五百文”,直至她被婆婆绑架走,中间经历多少时间,小说没有具体标注。当中有“日子很快的过去了”“新年才过”“此后大约十几天”等模糊时间语言,但是并没有显示词源意义。只有随着“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句子的出现,“每月工钱五百文”才被盘活,赋予词源意义。算下来,祥林嫂做工时间总计三个半月,然而小说故意忽略了这一时间细节。后文祥林嫂捐门槛,“价目是大钱十二千”,这显得语焉不详,但是接着交代她捐门槛的经济细节,一切清晰透明起来:“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读者不仅明白了具体“价目”,而且明白了祥林嫂捐门槛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被忽略的“三个半月”与具体的“快够一年”,冗繁的经济数字“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与简洁的经济价格“大钱十二千”,鲁迅将语言的基本意义和隐含意义水乳交融,从而产生参差可感的效果,语言也具有更加现代的含义和确切的力量。这样,鲁迅使用语言的时候,表现出彼此之间的经济关联意义。
总而言之,《祝福》中的经济因素具有相当的创新和革新质素。正是因为有了经济因素的渗透和作用,《祝福》作为一个惩恶扬善的小说文本,更显批判性和说服力。可惜长期以来,这一重要的因素在评论界和教育界是缺席的。今日予以索引,重在挖掘新义,产生新见,为重读经典的艺术魅力添砖加瓦。
:
[1][法]米歇尔·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M].孙淑强,金筑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207.
[2][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小逻辑[M].李智谋,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39.
[3][意]乔吉奥·阿甘本.潜能[M].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40.
[4][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10.
——祥林嫂的悲剧原因解读
——以《祝福》中三处细节描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