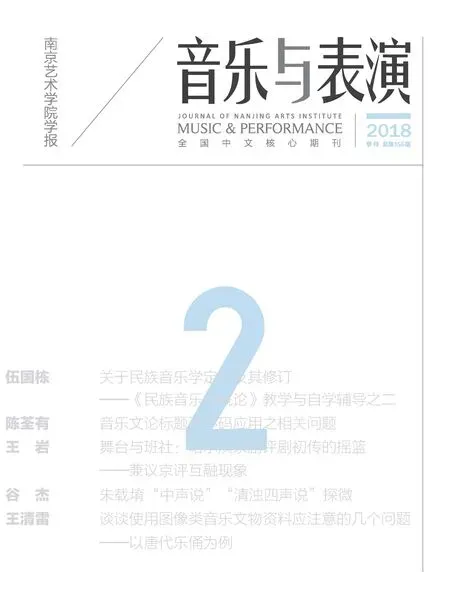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乐志》校勘商榷①
南朝梁沈约所撰《宋书》有《乐志》四卷,是现今流存的继《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之后又一部正史乐志,重点记载了东汉、魏晋及刘宋时期的音乐历史与歌辞,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文学史研究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是目前最通行最权威的《宋书》版本,在校勘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时代条件等主客观原因的局限,该书在校勘上还有诸多不完美之处。笔者在对该书《乐志》进行校勘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存在异文失校、校改不当、出校不当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中失校问题最多。现将这些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以供参考,期望于研究和使用《宋书·乐志》有所裨益。不周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本次校勘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1974年10月第1版、2008年12月北京第10次印刷)为底本,通校了以下7个《宋书》版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宋刻宋元明递修本(简称“三朝本”)、明南京国子监本(简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本(简称“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清武英殿本(简称“殿本”)、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商务印书馆影印三朝本(简称“百衲本”)。
一、异文失校
所谓异文失校,主要指重要的异文没有被发现,无法对文献错误做出校改,主要原因在于版本及他校资料利用不充分或校勘不够细致所致。
(一)
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534/4)②括号内斜线前数字为校勘摘句所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页码,斜线后数字为行次。下同。
“中”,各本同。按《宋书·乐志》关于汉代河间献王刘德献《乐记》的一段文字,当是本于《汉书·艺文志》。“内史中丞”,《汉书·艺文志》作“内史丞”,无“中”字。除《宋书·乐志》外,后世其他典籍引用《汉书·艺文志》这段文字,均作“内史丞”,不做“内史中丞”。考察《汉书·百官公卿表》等文献,汉代王国设有内史一职,其下内史丞,但无内史中丞一职。综此,《宋书·乐志》“内史中丞”乃“内史丞”之误,“中”字系衍文,当删,并出校记说明。
(二)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五行舞》曰《大武舞》。(534/倒4—倒2)
“黄初二年”,各本同。按《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四年八月之下,裴松之注引《魏书》补充一事:“有司奏,改汉氏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五行舞》曰《大武舞》。”[1]83裴松之所引《魏书》,除无“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一句外,其他文字相同,《宋书·乐志》之文或即本于此《魏书》,或是与此《魏书》史源相同之书。又,《晋书》卷二二《乐志上》《册府元龟》卷五六五《掌礼部·作乐》记载此事作“黄初三年”。因此,关于曹魏改宗庙乐名的时间,文献有黄初二年、黄初三年、黄初四年三种不同记载,目前难以确考何者为是。按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魏书》为曹魏时期王沉、荀顗、阮籍等人编撰,所记为当朝之事,《魏书》成书时间也较《宋书》《晋书》《册府元龟》为早,应更为可信,“黄初二年”“黄初三年”或为“黄初四年”之误。因无足够依据,难有确论,故可存疑待考而不改字,同时出异文校记予以说明。
(三)
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541/4—5)
按:此段文字中,前有“何承天曰”,后又言“承天曰”,用语重复,不符行文规范,后面“承天曰”三字或衍或脱或讹。宋陈旸《乐书》卷一七六《乐图论·俗部·舞·吴蜀乐舞》载有这段话,中间无“承天曰”三字。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三《何承天集》中将这段话视为何承天两篇《论郊祀不设乐》之内容,亦即:都是何承天所言,但不是同一篇或同一次所言。清《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八二《乐制考五》引用沈约《乐志》之文,作“何承天云”“承天又曰”。综合诸家所引,都认为这段话是何承天所言,而非他人之文字,则后一“承天曰”或在“天”下脱“又”字,根据《宋书》引文体例,当作“承天又曰”为宜。
(四)
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542/6—7)
“降杀”,各本同,《册府元龟》卷五六六《掌礼部·作乐二》作“隆杀”。按:“降杀”之“降”“杀”二字词义相近,难言“迭运”,与上句“损益”反义相成的结构也不对等。而“隆杀”之“隆”与“杀”二字,其义刚好相反,可与“迭运”相配,其结构也是反义相成,恰与上句“损益”对等。“降”与“隆”字形相近,“降杀”之“降”应是“隆”之误,当改并出校说明。
(五)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 (546/3)
“舍利”,南监本作“含利”。“舍利”所指为僧人佛骨,那么“含利”又是何意?《文选·张衡<西京赋>》“含利颬颬,化为仙车”薛综注云:“含利,兽名。性吐金,故曰含利。”[2]59下薛注很清楚地说明了“含利”之性质及其得名原委。《宋书·乐志》这段文字中的“舍利”是否即是张衡《西京赋》之“含利”呢?《汉书》卷九六《西域传》颜师古注云:“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四库全书本《汉书》作“含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潄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燿日光。”[3]3929-3930颜注表明《宋书·乐志》的“舍利”即是张衡《二京赋》之含利兽。这种说法也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如宋王应麟《玉海》卷七一《礼仪·元会》“汉德阳殿朝贺、元会仪”条、卷一〇四《音乐·乐二》“汉九宾乐”条亦均作“含利”,且卷七一“含利从西方来”注云:“含利,兽名,即《西京赋》所云‘含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4]1337上至此已很明确,作为后汉正旦之日的幻术表演者,“含利”是一种野兽,与佛骨舍利毫不相关。《宋书·乐志》“舍利”当是“含利”之形误,应予改正。本志下文“舍利从辟邪”(627/倒3)亦同此,“舍利”当改作“含利”。又,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云:“舍利,梵语。原为人名,此泛指幻术、杂技表演者,以其来自西域,故称为舍利。”[5]140此说因未见到“含利”异文,而牵强附会,曲为“舍利”说,看来没有根据,不足为信。
(六)
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硃生善琵琶,尤发新声。(559/倒3—倒2)
“郝索”,各本同。《艺文类聚》卷四四《乐部四·筝》引晋人傅玄所著《傅子》曰:“郝素善弹筝,虽伯牙妙手、吴姬奇声,何以加之。”[6]785此处作“郝素”。此后《白孔六贴》卷六二《筝》、《通典》卷一四五《乐五·杂歌曲》、《太平御览》卷五七六《乐部十四·筝》、《册府元龟》卷八五六《总录部·知音》、陈旸《乐书》卷一四六《乐图论·俗部·八音·丝之属》、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七八《乐部·乐器·筝》等均作“郝素”而非“郝索”。按:《宋书·乐志》紧接以上这段话之后,又云:“傅玄著书曰:‘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7]559这里尽管没有明言傅玄所著之书为何,但其所言“此六人”,与上段话中孙氏、宋识、陈左、列和、郝素、硃生六位音乐家人数刚好相合。虽然《傅子》今存佚文中仅见论及郝素而不及其他五位音乐家,但既然有“此六人”之说,则当分别对此六人有所介绍,所以“傅玄著书曰”以下引文很可能是出自《傅子》。只是因为《傅子》原书早已失传,今天我们所见《傅子》是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文字,已残缺不全,无由睹其原貌和全文了。根据以上推测,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宋书·乐志》以上的这段话源自原本《傅子》的相关记载。傅玄为晋朝人,当朝人记当朝事,应该可信。综此分析,《宋书·乐志》之“郝索”或是“郝素”之误。此处可不改字,出异文校予以说明。
(七)
宾出入奏《肃成乐》歌词二章。(597/倒5)
“肃成乐”,他本同,局本作“肃咸乐”。按:《南齐书》卷一一《乐志》、《乐府诗集》卷八《郊庙歌辞·宋章庙乐舞歌》亦作“肃咸乐”,歌词相同,且《乐府诗集》明确标示其文献来源为《宋书·乐志》,说明宋代流传的《宋书》版本即作“肃咸乐”。此外,《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亦云:“众官出入,宋元徽三年《仪注》,奏《肃咸乐》,齐及梁初亦同。”[8]292此说亦见于《通典》卷一四二《乐典二》、《太平御览》卷五六六《乐部四》、卷五六七《乐部五》。以此可见,“成”字应是“咸”之形讹,当依局本、《南齐书》《隋书》《乐府诗集》等改“成”为“咸”并出校。
(八)
皇帝还东壁受福酒奏《嘉时》之乐舞词。(600/3)
“嘉时”,他本同,局本作“嘉胙”。按《南齐书》卷一一《乐志》、《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通典》卷一四二《乐典二》、《册府元龟》卷五六六《掌礼部·作乐二》、陈旸《乐书》卷一六三《乐图论·俗部·歌》、《乐府诗集》卷八《郊庙歌辞·宋章庙乐舞歌》亦作“嘉胙”,其中《乐府诗集》明确标示文献来源为《宋书·乐志》。又,《通典》卷一四二《乐典二》云:“皇帝饮福酒,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胙》。至齐不改,梁初改为《永胙》。”[9]3609此段文字又见于《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 《太平御览》卷五六六《乐部四》、《文献通考》卷一二九《乐考二》等处。《隋书·音乐志》“胙”作“祚”,“胙”与“祚”通。综合以上文献可知,“嘉时”应是“嘉胙”之误,当予改正并出校。
(九)
却走马以粪其土田。(606/8)
“土”,北监本、南监本、殿本、局本同,他本作“上”。按本句文字为《对酒歌太平时》歌词,语本《老子》:“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10]186“粪”者,粪田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有道,天下太平,兵甲不用,退走马以务农田。“土田”指田地,而“上田”亦可通,其意即上等田地。《吕氏春秋·上农》曰:“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11]916《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3]1119即是其证。此处可不改字,但出两通校予以说明。
(十)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珪瓚、秬鬯、肜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609/1)
“肜”,百衲本同,三朝本字迹漫漶不清,他本皆作“彤”。按《尔雅·释天》云:“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12]2609下《尚书·高宗肜日序》:“祖巳训诸王,作《高宗肜日》。”孔颖达疏:“祭之明日皆为肜祭。”[13]176上据此可知,“肜”是商代祭祀的名称,指祭祀之后第二天又进行的祭祀。查诸典籍,未见“肜”与“弓”联用作“肜弓”者。而“彤”意为朱红色,“彤弓”即朱红色的弓,“彤弓”一词在典籍中则很常见。《宋书·乐志》此处所云“晋
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之事,见载于《尚书·文侯之命》:“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13]253下-254上文中正作“彤弓”,不做“肜弓”。故“肜”为“彤”之误,当予改正并出校。
(十一)
志士思立功。……右《秋风曲》凡十五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四字。(657/倒4—倒2)
南监本在“思立功”三字之下有重文,即有两句“思立功”,他本不重。《乐府诗集》卷一八《鼓吹曲辞·吴鼓吹曲》所载与南监本同。又,“十五句”,他本同,南监本作“十六句”,《乐府诗集》亦作“十六句”。“一句四字”下,南监本多出“一句三字”四字,他本无,《乐府诗集》亦有“一句三字”四字,不过位置在“一句四字”之上而非其下。按点校本未见这些异文,属于失校。至于是否当据南监本及《乐府诗集》补“思立功”“一句三字”两句并改“十五句”为“十六句”,存疑待考,可出异文校予以说明。
二、校改不当
所谓校改不当,主要指原本中的文字并无不妥,校改后反而错误。或者有些文字是两通异文,两说可以并存,只出校说明即可,而无须改字。
(一)
《安世哥》本汉时哥名。今诗哥非往时之文,则宜变改。(536/倒4)
“往时之文”,各本均作“往诗之文”。点校本改“诗”为“时”,并出校记云:“‘时’各本并作‘诗’,据《元龟》卷五六五改。”[7]560今查《册府元龟》卷五六五《掌礼部·作乐》,其文为“往诗之文”而非“往时之文”[14]6489,点校本所据《册府元龟》不知是何版本。此外,《南齐书·乐志》亦作“往诗之文”,《通典》卷一四一《乐一·历代沿革》、《文献通考》卷一二八《乐考二·历代乐制》作“往歌之文”,“往歌之文”与“往诗之文”同义。按:“往诗之文”指过往歌诗之文字,其意可通,点校本改“诗”为“时”,既无版本依据,也会枉解原文之意,殊为不当,应据各本改回。
(二)
《前溪哥》者,晋车骑将军沈充所制。(549/倒3)
“沈充”,各本均作“沈玩”,点校本据《晋书·乐志》《通典·乐典》改作“沈充”。按:《通典》北宋本、傅增湘校南宋本、明抄本、明刻本、清武英殿本等均作“沈玩”,浙江书局本作“沈充”,王文锦等点校的现今通行本《通典》将“沈充”改作“沈玩”。此外,《初学记》卷一五《乐部上》、《通志》卷四九《乐略第一》等亦作“沈玩”。《晋书·乐志》作“沈充”,很可能有误,因为沈充在《晋书》中虽然有传,但本传并未载其曾任车骑将军之职。我们知道,今传《晋书》为唐时所撰,其中很多史料即来自于《宋书》,《晋书》的“沈充”或是编撰者误抄《宋书》“沈玩”所致。总之,点校本据《晋书·乐志》《通典·乐典》改“沈充”为“沈玩”的证据并不可靠,当改回原本作“沈玩”,并出异文校,说明《晋书·乐志》等处作“沈充”。
(三)
夫川震社亡,同灾异戒,哀思靡漫,异世齐欢。咎征不殊,而欣畏并用,窃所未譬也。(553/倒5)
“同灾异戒”,各本均作“同灵毕戒”。点校本校勘记云:“据《元龟》五六五改”,今查《册府元龟》卷五六五,未见“同灾异戒”之文,其文在卷五六六,点校者在抄录文献时小有失察。按《宋书·乐志》各本作“同灵毕戒”,于文义并无不通之处,而且在结构上与“异世齐欢”严密对仗,不必据《册府元龟》改为“同灾异戒”。
三、出校不当
所谓出校不当,是指必须出校的而未出校,不该出校的却出校记,都是有违出校原则和体例的表现。
(一)
庆归我后,祚无疆。(638/7)
在此两句文辞之后,点校本出校记云:“按此诗宋明帝所制。‘烈武’谓临川烈武王道规。‘景王’谓长沙景王道怜。‘南康’谓南康郡公刘穆之。‘华容’谓华容县公王弘。‘左军’谓赠左将军王镇恶。‘三王’谓王华、王昙首、王敬弘等。‘到’谓到彦之。‘丞相’谓江夏文献王义恭,义恭死后明帝追赠丞相。‘沈’谓沈庆之,‘柳’谓柳元景,‘宗’谓宗慤。‘司徒’谓始安王休仁,‘骠骑’谓晋平王休祐。‘江安’谓江安侯王景文,‘殷’谓殷孝祖。‘刘’谓刘勔,‘沈’谓沈攸之。”[7]668通观这段文字,其内容系为歌辞中涉及到的人物作注释,与校勘丝毫无涉,有违本书校记体例,殊为不当,当予删除。
(二)
《圣人制礼乐》一篇,《巾舞歌》一篇,桉《景祐广乐记》言,字讹谬,声辞杂书。宋鼓吹铙歌辞四篇,旧史言,诂不可解。汉鼓吹铙歌十八篇,按《古今乐录》,皆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666/倒1—667/2)
按:此段文字是《宋书》卷二二《乐志四》卷末的注文。丘琼荪先生认为:“此识语乃陈以后人所记而误刻之,非休文笔也,其引《古今乐录》可证。”[5]299王运熙先生进一步考证说:“最后一卷末尾有一段后人识语……《景佑广乐记》系北宋官修之书,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古今乐录》,陈释智匠撰。按宋本《宋书》已有此段文字,当是出宋人之手。”[15]311总之,此段文字并非沈约所撰《宋书》的原始注文,而是出自宋人之手,也即《宋书》流传到赵宋时,整理者或阅读者在卷末添加上去的文字,不是《宋书》原书所有。因此,应对此段文字的性质和原委出校加以说明,否则会对读者造成严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