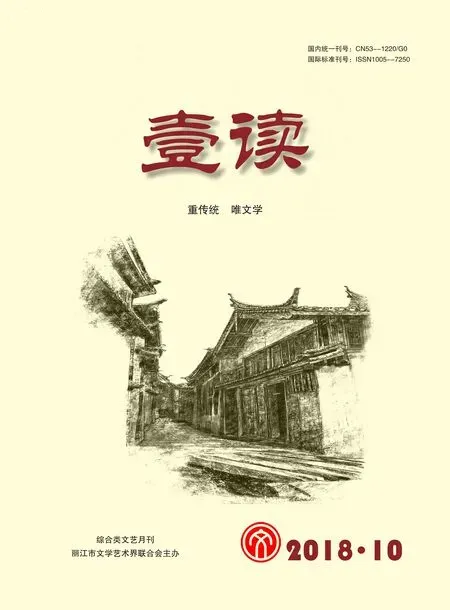短章(组诗)
阿卓务林
种子
我是一粒不慎被风
吹走的种子
落回大地
仅仅为了把爱还给你
把恨赎回去
天书
所有长眼睛的动物
都做过它的读者
所有生耳朵的植物
都当过它的听众
——这大自然
这五彩缤纷的世界
露珠
整整一夜的梦
翻越万水千山
去听万籁鼻息
不料惊了漫天星辰
落满身后草丛
重量
翅膀,飞越珠穆朗玛峰
黄金,沉入马里亚纳沟
孰轻孰重,风说了不算
雨说了,也不算
疯子
如果一觉醒来
他便疯了
不必怜悯他
从此,受了伤
他也将浑然不知
今天
请不要把今天
看得过于漫长
再花几分钟
把剩下的几句废话
说完,天也就黑了
明天
明天尚未到来
世事难以预料
对于明天也许可能抑或
注定发生的变故
此刻,你我尚无所知
钥匙
我的心扉
锁着一把锁
能把它打开
只有你
我多么希望
一把钥匙
只开一把锁
荒原
空出树
空出树林的兽
空出草
空出草丛的虫
空出人
空出人间的烟火
空出万物
眼睛
用悲观的眼睛看世界
世界是个地狱
用乐观的眼睛看世界
世界是座天堂
用现实的眼睛看世界
左看左是茫茫人海
右看右是海阔天空
信
桃花是春天写的信
荞花是夏天写的信
浪花是秋天写的信
雪花是冬天写的信
而我写给你的信
因短暂,久久心痛
在夜里,在雨中
暗号
不放过一个字
不让一个标点符号逃跑
甚至把信笺右下角
看似无意的墨点
当作蛛丝马迹
研究了多年
凭借这封信的暗号
我终于找到阿依阿芝的家
敲开下午五点钟的门
石磨
拉基河谷的那阵巨响
不是雷声,不是火车的轰鸣
不用人证物证,也不用眼睛勘探
我也知道那是石磨低沉的问候
牵引它的那人多年不见了
我俩攀谈过亲戚
象形文字
一个文字,一把火
一声呼唤,一句甜言蜜语
一次争吵,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一滴水,一夜漫无边际的梦……
火塘烤裂的胛纹,漂亮的胛纹
祖先该是花了多少不眠之夜
才发现其中像样的一个……
泪水
多少车辆放开油门从桥上急速驶过
风驰电掣的声音究竟有多沉重
多少眼睛放大胆子从脚底打量到脑门
四面八方艳羡的目光比阳光
究竟有多毒辣——立交桥下
打湿肩头的泪水,泪水打湿的呼吸
路人肯定忘了,我没有忘
竹海
翠竹,清风,墨溪
忘忧谷深处,海中海源头
仙寓洞岩下,如影随形的
阿芝呵,全是你甜甜的笑
只怪春雨不懂事,洒下
纷纷情,乱了眼前的路
无边无垠的静啊
听,大海拍岸的声音
史记
天堂滑落的黑曜石
坠入处女湖,荡开鲜血
荡开全世界的爱
当太阳撞上地平线
群山策动万马奔腾声
母亲的呼唤,茅草屋的喧嚣
一切回归原始,回归俗世
小溪旁升起袅袅炊烟
血汗
有谁知道族人花了多少代父亲
才终于把他们的血液
注入我们的心脏
有谁知道其中溅飞的汗水
曾浇灌出何等硕大的果实
请把欲燃未尽的那部分疙瘩
尽量烧干净:血和汗
一旦凝结成冰,着凉的
不仅仅是他人
夜的颜色
一只蘸染夜色的鹰
被披风引向雪豹的领地
一条顽皮的猎狗
踩着老人的故事闯进来
让猎人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一把解说生活的口弦
煽动火塘内心的热情
一颗珠子被岩石击得粉碎
但正好涂亮了我们的肌肤
祷辞
你的绚烂,一直在眼里
一直像朵花。你的泪水
一直无缘见,无缘轻轻
帮你擦。但愿背地里他面前
你都没哭过,他也没有机会
帮你擦。但愿晴天时雨天时
你都盛开着,开心的伤心的
思念的爱恋的,泪
一滴不给他,一滴都不给
历史
美酒,满了一杯又一杯
像怀旧的人撞见儿时
砸破自己额头的小伙伴
脸颊,因激动而夸张地红
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啊
多少误会尽在一声坏笑里
弥散,那些无聊的话题
也全都变得重要了起来
有的将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有的将载入一个地方史册
信仰
东坡的棕榈树迎风招摇
啄木鸟的喙骨,不由分说
南山的菩提树暗藏玄机
白头鹰的趾爪,指点山河
太初的爱情,母亲急促的呼吸
山崖的壁画,咬紧牙关的佛
那惊愕无语的,是谁的符咒
叩首膜拜的,是谁的头颅
花蕾绽开的痛,信仰
无从逃遁的门
纪念日
诞生,死亡。始初,终结
名氏,谱牒。纪念碑,墓志铭
割断脐带的血红与啼哭
卷飞青烟的神灵与悲歌
鹰翅仗风扇云,爪印微凉
猛虎越江过峡,背影微亮
整整一年,斯人脸色发黑
目光蛮野——他牢记那人
临终遗言,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抢先应答
春光
童年的牧场,牛肥羊壮
风笛翻过了山梁,儿时的伙伴
各奔东西,偶然碰见的那位
已年轻地老去,脸上戳满
风霜的唇印。童年的荒坡
花红叶绿,鸟语漫过了溪涧
儿时的阿芝,已远嫁他乡
而那片红,那片白
那片紫,那片蓝
只有杜鹃花固执地开着
阿芝
从家到办公室,至少有
一万条路,供我自由通行
有的很近,只需几分钟
有的很远,足以绕地球一周
而我经常走带拐角的那一条
那个拐角,一直坐着卖冰棒的
童年的阿芝。前几天当我
再次路过那个拐角
那个拐角,阿芝不见了
阿芝会不会是被哪个坏蛋
给拐走了呢
时间
红苹果火红。一场洪水
卷走蛮荒,带来无边无垠的风
一把锁,锁住大地的眼睛
残忍至极的纸,横在刀刃之上
一堵墙,堵住偷情的路
时间战胜谎言,留下废墟
马蹄,车轮,翅膀
热血沸腾时的快感,打开
门扉时的甜蜜,生命如此脆弱——
人群攒动的广场,谁的枪口
又对准了谁
衰草
我曾思念,整日整日思念
你手托离愁,睫毛哀伤地晃
落瓢泼大雨,决堤眼眶
羊群泅渡金沙江,领头的喉咙溺水
我曾失眠,整夜整夜失眠
你唇含娇羞,嘴角无邪地美
害一场心病,深陷骨髓
雁阵没入玉龙山,衔尾的翅膀染血
我曾整日整夜傻傻发呆
残梦未醒,而你消隐远山
迁徙的路,脚印衰草青
黄金之河
黄金之河,母亲的河
一心向着大海,奔流不息
纵是激情万丈,也把翻滚的梦
埋在心底,低头赶路
乍一看,恰似密林深处的湖面
波澜不惊
黄金之河,母亲的河
那么谦卑,那么热烈
谁忍心拒之门外
何况大海
纺锤
女人织布,耕耘北坡
男人开荒,赛马南山
夫唱妇随,祖先分的工
多合理,很少有人反对——
一只眼睛亮着,另一只
不会进入黑夜
而纺锤涡旋如浪花
一座山的女人
跟着他疯了似的转
跟着他昏聩一生
家谱
山谷,没有远方的石臼
彝人的依恋在这头
雄鹰,在那头盘旋
洪水肆虐,山遥望山
发呆。能歌善舞的女子
丢了魂魄,瘫软在地
伸出手,我们虚幻地滋生
蔓延。毫无抵抗地接触的快感
离神如此近,如此远
忠于爱情,忠于信仰
史诗的可能,宗教的可能
一个人的家谱,飘向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