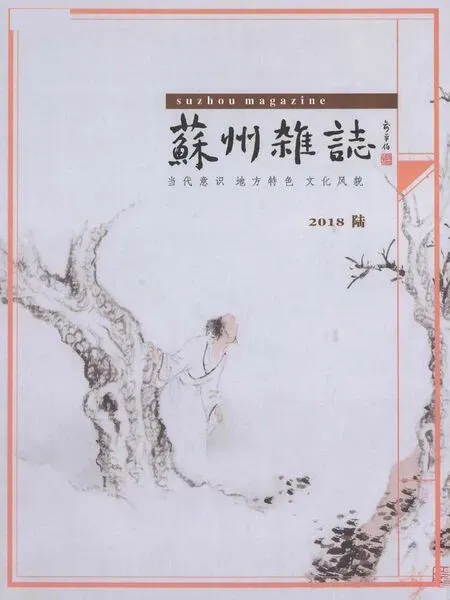民间想象力
苏童
谈论传统这个话题,可能是在谈论古人与前辈,也可能只是在谈论你自己。我想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写作立场,无论你是传统的致敬者还是叛逆者,终其一生,不过是围绕着传统这幢巨大的建筑忙碌,修修补补,敲敲打打,其实都是传统的泥瓦匠。
传统给人滋养,其滋养的方式与途径千变万化。当人们在感恩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的时候,潜台词往往是感恩李白杜甫,感恩苏东坡与李清照,感恩《红楼梦》与《金瓶梅》,这其实都是感恩正典,也就是传统这幢建筑雕龙画凤的华彩部分。我们很少去探寻这幢建筑的地基,地基怎么样了?地基当然是被建筑覆盖了,它一直都在,只是不被注意。地基里有什么材料?当然多得不胜枚举。我想,应该有通常被列为另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甚至未被文字记录的某些儿歌、山歌、民谣。那里有人类对世界最原始的文学想象力,来自民间,它究竟是如何滋养我们的?我们其实快忘了。换句话说,当一个作者对世界的想象以最杰出的训练有素的文字呈现,并且结出正果的时候,当人们高喊一部杰作诞生了的时候,可能也正是一支山歌失传的时候,在伟大作家越来越多的时代,很多来自民间的想象之花正在山野间默默地枯萎。
在这个前提下,探究民间想象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得很重要,那也是探究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角度。
我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民间想象力有实用主义的目的,它的最大特点是背对现实,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强烈的情感色彩是这种想象力的靠山,首先它是以一种情感安慰另一种情感,目的在于排遣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适感,所谓的民间生活不推崇思考,却极其需要发泄。类似怨恨、愤怒、惶恐、迷惘这样的情绪累积在一起,使得生活沉重,生活本身不提供彻底排遣的出口,只有寄托在想象上,只有想象,可以否定一个无望的现实,然后制造一个有希望的现实。
从源头看,我们的民间想象力最初体现在神话传说里,是对冷酷的现实采取的快乐抵抗。比如《大禹治水》。人们被水患折磨了,就去想象大禹治水,大禹不管用,民间不甘心,不放他走,就改变他的身份,继续想象,人和神混起来想象,于是有了水龙王,中国各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几乎都有水龙王的故事。这样民间的想象力对水患有了最后的裁定,从此把一切都交给水底下的龙王了,他们最终是把想象落到了实处,修龙王庙,去祭祀它,也让自己不倦的想象修成了正果。我们现在所说的许多迷信,其实不是迷信别的,是迷信自己的想象力。愚公移山的例子现在被赋予很多的寓意,但我觉得,这样一个故事,当它首次被民间描述时,不一定是为了张扬和歌颂人的意志,是从恶劣的生存环境出发的,愚公是一个问号,也是一个愿望,但民间并没有把愚公继续神化,放他走了,说明愚公最后仅仅是一个问号,既然是问号,就被民间暂时搁置了。而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我一直认为是民间想象力的一个特别完美的说明文本,有一个最强力最丰满的想象过程。最初从《左传》杞梁妻为亡夫要尊严这一点点事情出发,民间把这个女人的形象一点点地放大,扩充,几百年后这个女人成了孟姜女,人是一个凡人,情感是凡人的情感,身上却已经背负了一个巨大的使命,是一个神的使命。百姓把几百年来遭受的劳役和暴政之苦,浓缩在一个女人的泪水里面,他们派了孟姜女去,派了那些眼泪去,去把长城哭塌了。他们用这一次天斧神工的想象,逾越了令人窒息的现实空间,在安全中反抗,反抗成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享受,也得到了解脱。
早期的民间想象力比较务实,这种想象力针对大自然的时候,还是充满善意的,你大自然为难我们,我们还是得和你在一起,只是要想办法,要修补你的缺陷,要你合作。但是针对统治者和权力时,想象是不客气的,是要破坏什么摧毁什么的,民间在现实生活中会揭竿而起,在想象的时候姿态更加强硬,有时候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态度。
从文本的流传上考察,看看民间想象力从强悍到柔软的过程也有意思。从干宝的《搜神记》开始,到南宋《太平广记》再到《镜花缘》《封神演义》《济公传》,到蒲松龄的《聊斋》故事,无数的文本记载了民间想象力的泛滥,我们发现随着时代变化,也许是民间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现实之重,意识到想象力从现实出发,最终还是落在虚无中,民间想象力的重心渐渐地有所漂移,渐渐开始回避现实,更多的是神狐妖仙的主题盛行,情感分量似乎反而是轻了。济公手里的一把扇子是一个例子。好多人鬼共世的故事,鬼是一个对立面,有时候又是一个民间的补充面,而聊斋故事干脆是人狐共世了,让狐仙替冤屈或者梦想说话。当然你可以说,一切仍然与现实抱得很紧,是一种想象力的策略调整,但有一个无法证明的疑问是,民间对自己的想象力是不是也越来越看淡了,看轻了?
我的印象,在对待民间的立场上,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民间被作为一个关注对象,成为文学的描述方向,是以人群出现的,作家们暗示自己站在这个人群里,描述这个人群的生活,是多少年来创作的主流。另一方面,作品里这个人群在场,生活在场,情感也在场,他们的思维和想象力不一定在场,在许多指向民间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民间的思维方式也许是缺席的,这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创作问题,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本身也来自民间,只是在写作过程中,他为自己虚拟了一个写作立场,这个立场有时虚伪有时真实,更多的时候他在游弋不定,寻找与时共进的捷径。所以,谈论这个话题的关键之处是,当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科学化,是不是也就注定失去了最原始的力量?当我们在长城上想象外星人,想象僵尸或者想象一场旷世绝伦的爱情时,我们还能想象孟姜女的那滴眼泪吗?
这是我的一点困惑,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