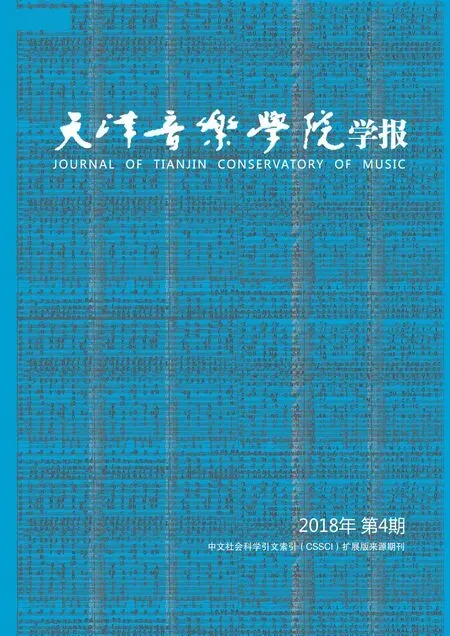孙继南治学理念和方法探析
屈怀凯
孙继南(1928.1.31—2016.11.5)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和音乐教育方面均有着突出贡献。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黎锦晖、李叔同等专题领域,著作《中国音乐通史简编》(1991,与周柱铨共同主编)《黎锦晖评传》(1993,下文简称《黎评》)《黎锦晖与黎派音乐》(2007,下文简称《黎派》)《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 1840—2000》(2000 初版、2004“增订本”、2012“新版”,下文简称《纪年》)及大量学术论文,均为音乐史学领域学习、研究中的重要遗产。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自上世纪90年代始,不断有学者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视角引入音乐史学写作,这些理论的立论基础多与传统“史料学”脱离,或是使其处于从属地位,显然有违史学学科性。孙先生的治史方法一贯坚持从史料出发得“信史”,其史学实践与诸种“另起炉灶”的新理论恰恰相反,是在传统“史料学”的基础上,欲求“更上一层楼”,此条路径正是在新史学理念、方法不断涌现的当下,值得学界关注与反思的重要命题。2016年11月5日,孙继南先生因病霍然仙逝,笔者曾有幸在先生离世前一年多时间里与其保持着频繁、融洽的接触,从治学到做人、做事均受教匪浅,怀着悲痛的心情,因着先生的诸多贡献及于笔者之良多教诲,遂辟此文对其治史理念、方法展开拓展性研究。
一、孙继南学术生涯简介
1950年,孙继南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曾随刘质平学习音乐理论,1953年初毕业留校并被推荐至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进修,旁听了丁善德、黎英海等理论家的音乐理论课程。1955年进修结束返校后,除声乐教学外,他同时担负起部分理论课,该校“名曲欣赏”和“民族民间音乐”均由其较早开设,其讲义《名曲欣赏》(1958)之“附件”辑录了大量批判“黄色音乐”的文章,体现了此阶段其史学理念中的革命性、阶级性。也是因为所开设的课程,1960年他获得赴京参加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班”的机会,并参与研讨、编写《民族音乐概论》一书,其作为音乐理论工作者的身份第一次超越了之前声乐教育工作者为主的身份。亦是此阶段,他开始了文论写作,由音乐创作研究起步并逐渐进入到音乐史教材的编写,《中国现代音乐史讲义(1919—1949)》(1961,下文简称《讲义》)体现出其日后秉笔直书的史学气节,孙继南在“文革”中曾遭受迫害、抄家,被迫停止了一切教学和研究活动,就连之前积累下的宝贵资料亦被洗劫一空,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大批牛鬼蛇神隐瞒政治历史、改头换面创家史、续家谱’,‘把黄色歌曲鼻祖黎锦晖封为儿童歌舞剧创始人’”①曲文静:《史料是史学的精髓——孙继南采访录》,《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3期,第7页。。1978年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②1958年,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与山东省文化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孙继南随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入该校从教。1974年8月,他还曾被调入“山东文艺社”艺术组任音乐编辑、组长。后,其研究成果更多地注重了对音乐作品文化背景的解读,以及对历史线索中的重要作品作综合性对比分析。
在1961年《讲义》的基础上,1980年8月孙继南又编写了一本《中国现代音乐史讲义(1840—1949)》,该教材“结束语——中国现代音乐史给我们的启示”通过1919至1949年间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史实,对其中“丰富的宝贵意见和启示”作了三点极具革命性、阶级性批判意识的总结,而次年12月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讲义(1840—1949)》则删除了该“结束语”。再结合其后期的研究成果而论,孙继南史学理念的转折点正是1981年,其中的革命性、阶级性逐渐弱化,而更多地开始注重对社会背景的分析以及对人性的拷问。
1984年9月,孙继南寻得李叔同编《音乐小杂志》,是其从音乐作品研究向音乐史学研究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这一年,除了对该杂志的介绍、分析外,亦开始进入黎锦晖研究领域。次年,调入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师范系后,其音乐史学研究又有了全新的进展,仅此一年即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编写,接下人民音乐出版社《黎评》约稿,精改发表论文《我国最早的音乐期刊——李叔同编<音乐小杂志>》③孙继南:《我国最早的音乐期刊——李叔同编<音乐小杂志>》,《人民音乐》1985年第3期,第57—58页。等。进入21世纪后,他的音乐史学研究又有了一个更为明显地提升,即在史料分析、辨伪的基础上,以小见大,针砭时弊地批评一些不好的社会、学术现象,或从某个角度阐发个人史学研究理念、方法,这尤其体现在其最后的三篇学术论文及在中央音乐学院、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举办的两场学术讲座中,这些文论也是本文研究其史学理念、方法的主要论据。
二、孙继南史学理念认知
孙继南的史学理念源于几十年的具体史料搜集、整理、考辨等音乐史学实践。因而,在对其史学理念展开研究时,必当结合音乐史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其所研究课题本身的理论需要,同时更应全面结合其学术成果。
(一)“史学只是史料学”
在《音乐史料之疑、考、信》①孙继南:《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大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第5—10页。一文及晚年的两次讲座中,孙继南一再引用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单从理论层面来看,他是认同“史学”等同于“史料学”的史学本体论理念的。然而,正如桑兵对傅斯年史学观念的阐述:“主要是为了标举史语所的学风,而不是针对一般史学的全体……在历史教育的层面,傅斯年认为……中国史更应注重政治、社会、文物三事之相互影响。”②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36—37页。历史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史学家的理论研究成果,由于各自知识结构及目的性的不同,其侧重点亦多有不同,绝不可简单地将史学家的理论阐述当做历史哲学家或史学理论家的分析、论证,而更应充分思考在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由于史学家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性格和观念特质,加之学科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一代人便只能做好一代人的事。就孙继南所处的时代而言,正是中国音乐史学学科奠基、史料积累的阶段,因而作为从事具体史学研究为主的史学家,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较以理论思辨为主的历史哲学家有着根本的不同。诚然孙继南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乃是以史料考据为重的《纪年》,但《纪年》之外,还有从《黎评》到《黎派》两部充满了思辨、分析、评论的重要著作及其他相关文论。因此,其所坚持的“史学只是史料学”不能简单地当做史学理念来看待,而是其出于自身作为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实践需求,所提出的阶段性要求。
此处所言之“阶段性”大意有二。一方面是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而言,自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1959)及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1961)的问世,也才不过60年光景,中间还出现“文革”停滞期,当下仍处于史料积累的阶段,工作的重心仍是史料搜集、考辨。另一方面,就学界整体学风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起西方大量现代、后现代历史理论、方法不断涌入中国,新观念的注入本身是好的事情,但在此过程中却滋生了过度强调思辨而匮乏史料考证的浮躁现象。孙继南一再强调“史学只是史料学”亦如当年的傅斯年,乃是为了标举学风。
再者,从孙继南所强调“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文论及讲座中可见,其所针对之研究对象均为微观性的个别对象,一旦涉及范围性的历史人物、事件,则不时闪现出思辨光彩。笔者在其生前,亦曾拟定黎锦晖相关评论性文章提纲,寻求指教,先生言:“你们这一代人也确实应该做一些更细致地分析,只是一定要依据信史!”也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他彪炳傅斯年史学理念的良苦用心,这并非其行为之结论,而是其言行之目的,乃是为解决一时之研究风向,为奠定学界尊重史实、勤勉考证之学风。
(二)决断于“一手史料”
基于对“信史”的追求,孙继南的史学研究便自然导向对原始资料的追索,其研究成果之结论无不是决断于“一手资料”。当然,史料学所追求的确信无疑之史实,只能是就单称对象的研究而言,孙继南的史料学观点亦是针对单称对象而提。就原始资料的重要性,他曾言道:“原始资料(作者手稿或原始出版物),是直接证据,具有确凿无疑之可证性,后者(引者注:第二手资料)为旁人或后人所提供,为间接性证据,是否完全符合原貌,还难以定论。”①孙继南:《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大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第7页。对于未能找到原始资料证实的史事,他绝不轻易下结论,对于未得原始史料证实的已有结论亦是“疑”而后“考”,在寻得一手史料支撑后方见“信”史。
以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研究②孙继南:《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大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第7—10页。为例,大量的“据情分析、按理推测”均是为了最终获得原始资料。作者首先对丰子恺抄谱产生疑问,此抄谱是否为丰氏抄录?其抄录凭依是否为大师真迹?在咨询了材料提供者刘雪阳及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后,未能解决,便依据丰子恺1958年所编弘一大师歌集及相关回忆文章,用“排他法”排除了此手抄谱为一手资料的可能性,从而开始了对原始资料的寻觅之旅。后来,偶见2008年2月24日《厦门日报》文章《1937年厦门运动大会弘一大师谱会歌》,提及歌谱发表时间、出处为1937年10月9日之《华侨日报》,经过与丰氏手抄谱的对比及新见歌谱作者严谨程度的考量,推测此谱极可能为首发稿。至此,作者并没有盲目下结论,而是继续发问:发表时间距活动时间怎能相差百余日呢?再次踏上破“疑”之旅。在学界友朋的协力帮助下,辗转北京、福建各地,最终获得了1937年5月13日《华侨日报夕刊》所载之《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原始稿,如此,一应问题便有了确切答案。从整个考证过程来看,作者虽然运用了排他、比较以及其他思辨性方法,甚至有借助心理学层面的歌谱编辑者素养的洞察,但其目的性是相当明确的,即一切手段均是为原始资料的寻觅服务,欲得明确结论必须依靠一手史料。
(三)以“史家生命”治史
孙继南常以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阐述其史料寻觅心得,史料无处不在,浩如烟海,且其存在形式往往是零碎地分布于天南海北。史料寻觅一靠敏锐的洞察力,二靠手脚的勤勉。就史学家的勤恳而言,并非盲目出傻力,史学家之间的通力合作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学界众所周知孙继南是一位更乐于享有独处空间的深居简出的学者,作为弘一大师再传弟子,他深受大师影响,甚至离世前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亦是“‘我可以走了……’……‘出家’”③刘再生:《低调人生 学界楷模——孙继南学术人生追思录》,《人民音乐》2017年第2期,第27页。。然而,在其文章中却不时读到寻觅史料的过程中来自各界同仁的帮助:深居简出与同仁如林的共时存在,正是缘于史学家的“入世”之需要,此矛盾乃是个体生命与“史家生命”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诚然,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入世,但历史学家对集合体的演变有着职业上的兴趣,这是在相同文化水平的人群中,历史学家这个行会的入世比例大抵要高些的一个原因。”④[法]安托万·普罗斯特,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史学家的入世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个体性的生命体验,一是群体间的交流互助。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而“人”又是所有研究对象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亲身体验、思考、感悟是史学家理解生命、贴近史实的有效途径。史学家群体之间的通力合作则既可以大量减短史料寻觅的路程,又可以加强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提升写作质量。
史学家之间的合作大大加强了工作效率和质量,而形成此种合作机制的条件乃是作为个体的史学家的真诚。孙继南始终对史学信息、资源共享抱以主动性,无论多么罕见的高价值史料,毫无保留地分享于学界同仁,一起研究,共同思考,正所谓“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道德经》),其能够获得诸多同仁帮助正是因其无私。仅就笔者阅读所见,除李叔同《音乐小杂志》外,项阳《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①项阳:《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黎锦晖的探索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启示》,《音乐艺术》2003年第4期,第33—37页。;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②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49页。;冯春玲、冯长春《勿忘 <国耻>》③冯春玲、冯长春:《勿忘<国耻>——关于“五三”惨案的几则音乐史料》,《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3期,第55—58页。;彭丽《黎派音乐再认识》④彭丽:《黎派音乐再认识——关于黎锦晖的十本歌集》,《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第93—98页。等文论中所用史料均来自于孙继南先生的馈赠……同样,孙继南查找《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三宝歌》《诚》等史料的过程中,也在这些学者的身上得到了相应回馈。无论在研究过程的任一环节曾给予帮助的同仁,他均在文章中注释清晰以致谢忱,一来是对诸多参与者应有的尊重,二来亦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查找信息。
(四)书写“人文音乐史”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随着“文革”浩劫过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之前的阶级分析方法开始被重新认知,西方的各种现代、后现代史学方法论也陆续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如系统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法、数学方法等,尤其1990年代初心理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探索,使历史中的“人”的因素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音乐学界,1991年郭乃安发表了论文《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⑤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第16—21页。,呼吁中国音乐学界在研究中务必关注其中的人文因素,同期,蔡仲德亦开始对“士人格”展开研究。孙继南的《黎评》则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把目光投向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且从《黎评》到《黎派》不断以更为人性化的批评视野为研究对象“正名”,对弘一大师《清凉歌》的研究亦是以人性化的分析、考证⑥孙继南:《中国佛法歌曲经典——弘一大师“清凉歌”初考》,《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1期,第12—20页。,还其“佛法经典歌曲”之原貌。这些成果中的人文性,一方面体现为作者对历史细节真实的追求,以及对历史场景中的人格、人性的还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作者对自我的人性化批评。
历史研究脱离不开人的因素,历史事实只能存在于历史细节之中,即便是微观对象研究,也要对其在史学家所选定的研究视角中的历史价值有所把握,这也便必然要与其他相关对象发生关系,关系的内部必然就会存在人为因素。通过对孙继南史学文论的分析,结合梁茂春《“人文音乐史”浅议》⑦梁茂春:《“人文音乐史”浅议》,《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1期,第19—20页。一文的阐释,笔者深感“人文音乐史”的书写尤其应该把握好以下几点:1.在叙述方式上力求以言行等为据突出对历史人物的人格考察,并将其作为检验历史真实性的重要辅助手段、补充材料;2.无须回避史学家与写作对象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但最好在文中适当“交代”清楚,如此,既可保持特有写作背景下阐释的个性化,亦可增强文字的可读性;3.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务必保持人性化的批评态度,以开阔的视野避免狭隘的批判,结合人性化的思考避免机械化的逻辑推理,不能以严苛的政治评价和脱离现实的技法要求审视研究对象;4.要敢于讲真话、吐真言,不以个人喜好“挑挑拣拣”,一味鼓吹或是一味“棒杀”都是有违历史真实的且缺乏人性的;5.“人文音乐史”的书写“特别重视的是音乐史研究的创新思维,即史学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①梁茂春:《“人文音乐史”浅议》,《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1期,第19—20页。,作为书史者的“人”,必须要有高度的自省意识,在思考历史的过程中,对自我的审视亦是对写作对象尊重的过程。
三、孙继南治史方法缕析
郭树群基于孙继南在《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②孙继南:《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大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第5—10页。中所提之“疑、考、信”,加之后来《佛曲<三宝歌>源流始末考》③孙继南:《佛曲<三宝歌>源流始末考》,《音乐艺术》2015年第4期,第6—12页。中针对“考”而提之“细”和“精”,将其史料研究路径归结为“疑”“考”“细”“精”“信”的五字箴言④郭树群:《几个学习有得的中国音乐史史料研究个案》,《中国音乐》2016年第4期,第61—66、84页。。“疑”“考”“信”明显是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四大流派(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后来学者将“古”字转换为“史”字,具有了更广泛的应用性)中综合、演化而来。孙继南提出的“疑”“考”“信”将前三个学派的特点作了综合。其对待史料保持“疑史料派”的怀疑态度(此处之“疑”包含两点,一方面是对未考“资料”之“疑”;另一方面是对未经证实的新“史实”之“存疑”),破“疑”之途径唯践行“考史料派”的考据精神不可,“考证翔实,方具可证性,用之于史学研究,才会有‘信史’产生”⑤孙继南:《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第6页。。
对于“释史料派”的观点,孙继南并未纳入自己的史料学视野之内,如前文所述这主要是因其自身之史学研究侧重史料考辨,且深感所处之时代能够做好此一点已深为难得之故,并不意味着反对对历史地解释。恰恰相反,其对黎锦晖的研究正是在史料的“疑”“信”“考”基础上所作之“释”,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所作的“编年”成果,亦是为了“乐史有传人”,他铺垫下的正是前三点,为他人的解释有一个可据信服的史料基础,《纪年》中的条目现已被学者们大量引用,也可算是其“释”史理念之实现。因此,笔者之见,结合孙继南的研究成果考量,五字箴言基础上加上“释”而成为六字箴言似更为完整,且能避免后学者在研读、借鉴孙继南史学方法时,进入只重微观史料考辨而排斥历史解释的另一种极端。
佛法有云:法无定法,非法法也。历史细节的考辨因史料的碎片化存在方式以及其间掺杂的各种人事关系,情形最是繁琐、复杂,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亦仅能思考自身所持之史学理念对于历史真实及人类进步之得失,却难有一成不变之法理。“史学观、方法论、史料学是历史研究理论上的分类。在写作实践中,三者很难截然分开。”⑥曲文静:《史料是史学的精髓——孙继南采访录》,《中国音乐学》2015年第3期,第11页。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史学理论,思考的目的终是为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服务,切不可简单以理论之“新”而求选题之“偏”,无论何种方法论都不过是史学研究的手段而已,就实践者而言,理论研究的目的正应在于打破理论的限制,不拘一格地择取适当方式为实际课题研究服务。
结 语
孙继南毕生的音乐史学研究基本都是埋头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辨等具体工作,晚年对自身史学理念的思考、总结虽多为对前人成果的再阐发,但其明确提出的“疑”“考”“细”“精”“信”治史方法对当下的史料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透过孙继南的学术文论来看,他并非只是从事于单称性史料研究,尤其在黎锦晖专题研究领域,随处可见思辨性内容以及对人性的思考,因而理解其史学理念、方法必须要与其研究成果及其所处时代相结合。
通过对孙继南学术生平、成果的研究以及对其史学理念、方法的思考,尤其在黎锦晖专题研究方面,笔者深感“历史细节”在史学研究中尤为重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有几分史料出几分货,“史料学”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持任何史学理念的学者首要必备的基本研究技能,舍史料无以言其他。无论是“社会史”还是引进“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展开史学研究,牵涉到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诸多层面的叙事、分析、评价,无不是基于对史料的疏理、运用,且其中所涉及的史料信息较微观史料研究牵涉面更广,在个别史料的考辨中“历史细节”往往是寻觅“一手史料”的关键,就这些“新”理论而言“历史细节”则更是构建文章的主要材料。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重写音乐史”争鸣至今已持续了近30年,经过对“左”的史学观念的批判后,音乐史学界越来越注重音乐史书写中的人文性,要尊重、理解历史中的“人”必定要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也只有依凭大量“历史细节”才能完成,只有从各个层面上获取了足够史料,才能更为客观地把握历史。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论辩中,孙继南坚持“史料学”方法,其他学者们也争相提出了各自心中“新”的史学理念、方法,如“科学的唯物史观”(张静蔚)、“社会史”(常晓静、李方元)、“历时的民族音乐志”(洛秦)等等,这些新思想的产生或介绍、引进,无疑都将在不同层面上对接下来中国音乐史的书写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然而,在诸多理论涌现的同时,是否也要从传统“史料学”的基础上思考一条音乐史学的写作路径,以在前一阶段史料积累为主要任务的研究基础上,进入到与“释史料”相结合的阶段,“历史细节”或许是一个具有一定可行性的突破点。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