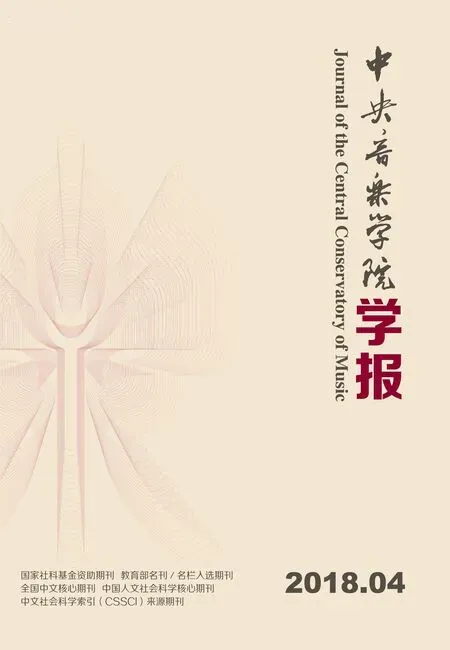回首“新潮音乐”40年
姚亚平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热烈地张开双臂,拥抱久违了的世界。这个开放的姿态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上层建筑的文化和艺术上。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思潮的涌入。在音乐领域,随着思想自由、观念更新,一批才华横溢的新生代青年学子充满激情,掀起一股“新潮音乐”的巨浪,引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音乐的争论,在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创作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40年过去了,激情已经退去,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辩慢慢平息,批评和质疑之声也逐渐稀疏。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人们似乎已经对此话题没有了兴趣,大家各干各的活,各忙各的事,彼此相安无碍。但是这桩“公案”真正了结了吗?有关艺术认知上的巨大隔膜真正化解了吗?争论双方彼此的心结真正打开了吗?在很多私下场合,在很多“不经意”的、“话中有话”的言谈和议论中不难看出,不少人对现代音乐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似乎不屑于谈论它,也没有再去争辩的愿望和动力,他们对现代音乐的困惑、茫然、不解甚至愤怒如今转化成无声的心绪,静静地在社会舆论中潜伏下来,只是偶尔,在遇到刺激时,做出些许微不足道的反应。
40年过去了,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并不想再去翻过去的旧账,把过去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再去争论一番。事实上,回过头去看,过去的争论之所以如陷泥潭,一些问题永远也扯不清楚,最根本的问题是观念问题。如果观念不同,各自立场不一样,大家各执一端,各说各的理,结果永远是南辕北辙。今天,回首“新潮音乐”40年,激情已经平息,很多历史的尘埃已经落下,更重要的是,今天人们在观念上可能更加统一或接近,可以用更冷静和理性的眼光,更平和的心态,从更宏观(而非就事论事)的大视野来客观地看待中国当代音乐走过的一段历史。
有以下几个问题现在是可以回头想一想的。
一、要不要接纳西方现代音乐?
中国要不要接纳现代派音乐?在今天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更确切的问题应该是,中国为什么接纳了现代音乐?因为无论从民众的音乐修养还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国情,都没有接纳现代音乐的理由。正因为如此,在要不要接纳现代音乐问题上40年前存在尖锐分歧,有很多人持坚决排斥态度,对现代音乐非常反感甚至厌恶。当时的反对之声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感性的、听觉上的;一种是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这两种声音都很大。但是就凭着中央音乐学院的一群年轻学子的满腔热情,现代音乐的波涛在中国掀起,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是什么力量在改变着中国音乐历史的走向?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许多激烈争论,都是表层的、非决定性的,在最终决定要不要接纳现代音乐上,有一个深层次、背景性的大的国际潮流,这股潮流很难抗拒。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所步入的世界正面临全球化时代。而当时国人的眼界大多停留在国内,对全球化浪潮的袭来浑然不知,一直到90年代中期,除了少数文化精英外,很多人对全球化其实是没有什么认知的。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做出一个很郑重的抉择,即要不要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经济全球化来看,意味着要不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一个西方人主导的、西方人作为规则制定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俱乐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经有过犹豫、疑虑,但最终还是迈出了一大步,勇敢地投身于全球化浪潮(中国于1986年正式提出申请,历经15年努力,2001年正式加入)。今天来看,这一步是正确的。但是全球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它也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对于音乐,也面临同样的抉择,要不要加入音乐的国际体系,要不要加入由西方作为规则制定者并主导的艺术“WTO”,即泛国际的世界音乐俱乐部?同加入世贸组织一样,这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人能强迫你,但是一旦你参加进去,就得按照西方人制定的规则,就得符合和遵守西方人主导的国际音乐俱乐部那一整套美学秩序和话语体系,也就绕不开现代音乐,因为现代音乐语言是当代国际音乐俱乐部的主流话语,如果你还在用18、19世纪的音乐语言去同别人交流,是没有人理会你的。
另一方面,在是否接纳西方现代艺术上,中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也非常关键。对于西方现代派艺术,改革开放前我们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但是在开放大潮下,政府做出了开明和正确的决断:拥抱全球化,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全面开放。可以这样说,现代艺术在中国得以合法化,是得到官方的默认甚至支持的。本来,根据中国的国情,抵制现代艺术并非难事。但是新的时代,国家有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和对外部世界的更深刻认识:现代艺术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还是一个事关融入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艺术创造上的不断更新、变革这种源于西方的价值观,已经上升到人类文化和精神发展的高度。既然,中国要加入全球化,就要接受现代新文化的创造理念,就要与国际主流的价值体系保持一致,因此绝不会封杀现代艺术。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大的全球化背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我们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强烈反对现代音乐的声音喊得也很响亮,有些人甚至将现代音乐视为对“革命音乐的宝贵传统的对抗与挑战”[注]石城子:《评新潮交响乐》,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第86页。,但围绕新潮音乐的争论基本保持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官方对现代艺术并没有过多实质性介入,即使是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现代艺术看似很吃紧,但也是外紧内松,大棒好像已经高高举起,并没有真正落下。反而,由于艺术现代化是一股国际潮流,代表世界性的精神和价值理念,政府对现代艺术予以扶持、资助,使其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以上情况,三四十年前,人们一般不会看得很明白,但现在应该会看得很清楚,关于新潮音乐的争论,到底要不要接纳现代派音乐,绝不是人们当时争论的话题,如好不好听啊,刺不刺耳啊,有没有旋律啊,大众能不能接受啊这类零碎的感受所能决定的,它的后面其实有一个宏大的、深刻的全球化问题,也就是要不要融入世界的问题。就这个意义来看,现代艺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势不可挡。在全球化时代,眼光不能仅仅盯住国内,要考虑整个国际潮流和国际趋势。这个时候,艺术问题就已经不是单纯从艺术角度来考虑了,这里有国家意志和国家走向的力量。
二、关于“西方”与“民族”
在关于“新潮音乐”的争论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即“西方”与“民族”。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涌入,新潮音乐正是作为西方文化“闯”入中国,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产生了诸多冲突。如有人认为,接受西方现代音乐,是放弃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现代音乐与我们的民族感情格格不入。近代中国,“西方”与“民族”一直是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又被重提。但是在新的时代,“西方”“民族”的内涵错综复杂,其中包含着吊诡的转变。不过这也是事后才看清楚的。
改革开放之初,在人们的讨论中,其实存在着两个“西方”概念,一个是传统的西方,一个是现代的西方,二者是冲突、矛盾的,彼此不兼容。与此相应,也有两个“民族”概念,一个是过去30年政治的民族,“民族化”的民族,一个是当时还不显著的,去西方、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民族,二者也是不兼容的。
80年代,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进入新时期,出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持久热潮。当时刚刚入学的“第五代作曲家”,也是抱着学习西方的心态步入校园的。与此相对应,这批青年学子对过去30年的“民族化”道路普遍反感。这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即这批制造“噪音”的反传统音乐家,是西方的追随者,他们唯西方马首是瞻,是西方中心论的信徒,完全背离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然而正当这种批评声铺天盖地,事情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新潮作曲家在经历了初期的、短暂的西方崇拜,以及一时的彷徨后,特别是在接受了西方现代音乐理念之后,渐渐走向相反的方向。事实上,人们只是看到新潮作曲家努力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现代音乐技术的一面,但却没有注意到其背后隐含着的非西方、去西方的精神趋力。新一代的新潮作曲家内心深处服从的其实并不是“西方”“民族”这类概念,而是现代音乐的声音感觉,正是在追寻这种声音感觉中,使他们与“西方”渐行渐远。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现代音乐的技术语言中包含着一种充满悖论的西方的现代观念,这种观念本质上要走向反传统、去西方、反西方中心论,它更迎合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相对论,以及多元文化的全球理念。新潮作曲家的观念转变是潜移默化的,但绝不是无头苍蝇般的乱撞,而是服从一种深刻的思想和历史逻辑。
80年代,正当国内掀起学习和追逐西方现代作曲技术的狂潮,绝大部分人都在盲目地尾随时,在极少数的作曲精英,在第五代作曲家中的一些佼佼者的言论中,我们却可以捕捉到另一种气息,这种气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由衷推崇,在李西安与三位新潮作曲家的《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中隐隐散发。在这篇关于现代音乐的对话中,有很多篇幅并没有谈论现代音乐本身,而是在大谈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这种现象可能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但是在随后2005年李西安、瞿小松的对话录《走出西方的阴影》,特别是瞿小松2011年的《虚幻的“主流”》中,就可以看出有一条符合逻辑的思想发展走向。
读过《虚幻的“主流”》,一定会让很多对新潮音乐仍留有陈旧的刻板印象的人,心理上有些猝不及防,昔日的先锋派形象仿佛在陡然间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在该文中,作者对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术和艺术理念颇有微词,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赞叹有加,钦佩得五体投地,认为中国的新南音、评弹、京韵大鼓、京剧、川剧、秦腔,完全不是西方歌剧可以比拟的,“从韵白到唱,它的声音过程是非常丰富的”,“这里面有太宽阔的天地了,而我们却睁眼不见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数不胜数的精妙,已经是可悲的无知”[注]瞿小松:《虚幻的“主流”》,载《中国音乐》,2011年,第2期,第24页。。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该文的批评枪口直指先锋派的现代主义,这和当年批评新潮音乐的人的口吻如出一辙:“可叹,如我一般的中国当代作曲家,迷失在西方无节制的激情与现代主义病态的造作而不察。”[注]瞿小松:《给罗忠镕老师的信》,载《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第114页。作者尖锐批评道: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千人一面,越来越变得一片灰色,一片乏味的色彩,很多人还在往这里面钻,好像必须这么写才叫现代音乐,其实这种现代音乐“不过是学院作曲系狭小空间里头一个自恋的梦幻,它已经萎缩为一个极小极小、极细极细的支流。而现今中国的学院音乐人拼命要与之‘接轨’的西方,已经早就有人意识到这个自恋梦幻的困境”[注]同注②,第22页。。
应该看到,瞿小松不是个例(但也许是最极端的一例),中国现代主义作曲家群体中有很多人都是从西方崇拜开始,却最终与西方渐行渐远。谭盾、郭文景、何训田都表达过强烈地去西方化的情绪和愿望。另一方面,在对待“民族”问题上,他们也大多从反感“民族化”开始,最后蜕变为最热情的新民族主义。所有这些,都与他们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有关。现代派音乐语言本质上是去西方的,但是这种极端地去西方化所导致的先锋主义激进运动,使中国作曲家看不到未来,他们自然地转向自己的本土,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语言出路,出人意料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忠实的崇拜者和捍卫者。这样的转变完全是合乎逻辑的,也是自然而然和由衷的,人们丝毫不应该怀疑他们的真诚度。
三、“大众”还是“个人”?
新潮作曲家的真诚被公众领会和接受了吗?这中间肯定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现代作曲家和大众之间横亘着一层厚厚的隔膜。
现代音乐经常被评以“刺耳”“听不懂”“难听”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音乐刚刚登上中国的音乐舞台,这个问题尤其尖锐。有人批评道,现代音乐“片面地强调出新,追求突破,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离奇的旋律、荒诞的节奏,这种‘新’实则成为‘怪’了”[注]廖家骅:《既要出新 又要出美》,载《人民音乐》,1981年,第9期,第19页。。但是好听与不好听这个标准谁来定呢?回答是:大众!而谁是大众?谁能代表大众?这里就大有歧义了。从当时的争辩中可以看到,“大众”可能有三种内涵,即政治的大众、专家的大众、普通人的大众。所谓“政治的大众”内含于过去的年代喊得特别响亮的一个词语——人民。在这里,“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围绕新潮音乐的争论中这个词语经常介入。所谓“专家的大众”,是一些批评新潮音乐的专业人士,他们常常以“大众”为武器批评现代音乐,这种“大众”常常与政治的大众有关联,他们的审美趣味往往停留在比较传统的音乐。对新潮音乐不满的人中也有很多普通人,即“普通人的大众”,但他们属于圈外人,其实对现代音乐知之甚少。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当年批评新潮音乐,认为音乐应该考虑大众、考虑多数人,其实这里的所谓“大众”“多数人”也只是特定人群,这个人群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大众,但却常常自诩为大众。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一个人群的音乐,即人民的音乐。改革开放以来,音乐人群出现分化,在中国音乐中可以找到分属两种鲜明对照新兴人群的音乐,即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这两个新兴人群都扔掉了过去的“大众”。现代音乐属于非常小众化的人群,属于象牙塔里的少数文化精英,一般公众无法靠近。但是社会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忘记多数普通人,也给他们留下宣泄渠道,使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流行音乐。这个人群极为广大,他们是真正的大众。但是正是这两类音乐,遭到当时那些心中有“人民”的人的攻击,认为前者贵族化,后者庸俗化。这类保守之人,仍然坚守过去单一人群的观念,看不到中国社会已经在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新兴的人群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大众”,这种“大众”,即单一人群的概念化的“人民”。而正是这个虚幻的存在,在八九十年代,成为批评新潮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武器。
回看过去,围绕新潮音乐的“大众”和“个人”的争执,显得很没有意义。现代音乐本来就是一个小众化的艺术形式,大众化的标准并不适用,对它要求大众化等于是取消它。因此,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如何看待这种小众化的、个人至上的艺术现象。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如果艺术家不考虑别人的看法,认为艺术只是为了个人,就是很错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艺术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地就应该给广大人民带来美好的享受吗?对于很多过去的人,以及今天乃至未来的人,艺术家的特立独行都会是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
四、现代音乐的社会责任
一说起艺术的“个人”,一个连带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当年新潮音乐争论的一个话题。
如何看待只顾自己,不考虑公众的现代音乐作曲家?他们的那些难懂的音乐对社会有何意义?他们难道不应该考虑艺术家的社会职责吗?这类逼问,现代艺术家确实不好回答。
这些问题与前面提到的“大众”和“个人”相关,另外,还涉及“中国”和“外国”。因为与现代音乐的社会责任紧紧联系的“大众”,是“中国”之大众,现代音乐应该首先考虑为中国而不是为西方人做了什么。当年经常听到的一种批评声音是:中国的现代作曲家们总是跟在西方人后面,总是为了取悦西方,即使一些现代作品在国际上得了奖,获得好评,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它并没有为中国做出什么贡献。这种看法当时非常普遍,叶纯之在《给叶小钢的一封信》中提醒现代作曲家,“若专为迎合外国人的趣味,我看大可不必。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国内,首先为自己的听众”[注]叶纯之:《给叶小钢的一封信》,载《人民音乐》,1986年,第4期,第17页。。沈洽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中国现代音乐的“趋势是走向世界”,但它“对我们这个国家能起什么作用,则考虑较少”[注]高为杰主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器乐创作研究》下卷,中篇第三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结项报告,第29页。。上面这些看法,有时代局限性,没有看到中国人已经走出去,中国已经开始步入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的年轻一代作曲家,已经非常国际化,他们求学于西方,穿梭于国际音乐舞台,接受国外的创作委约,作品首先在国外上演,与国外作曲家有密切的学术上的交往和交流……他们已经融入国际音乐俱乐部,他们必须要利用,也只有利用这个平台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这样的一批作曲家单纯地只是用“奉献国家”的眼光来看待,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与此相应,对这样一批中国的现代作曲家提出“社会责任”,也应该有新的内涵。对他们的审视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国内,看他们为中国到底做了什么。中国现代作曲家当然应该考虑中国,但绝不仅仅是中国,他们还要考虑国际贡献,考虑在国际舞台上去发出中国声音,考虑为“作曲”这样一项国际化的音乐事业中国人能做点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为此努力。事实上,中国现代作曲家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这里,涉及一个重大的观念性问题,即从西方发源,并长期由西方主导的音乐创作事业,巴赫、贝多芬、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是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现代艺术是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人就不应该缺席,就理应加入进去,并努力在这项人类事业中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那么中国人能不能留下足迹?凭什么能够留下足迹?对此很多人是有疑虑的。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来看,即使在西方主导的环境中,中国也是可以有所收获和有所作为的。对于艺术“WTO”,我们理应有所期待。中国作曲家要想在国际化的音乐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唯有凭借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现代作曲家越来越表现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依赖的原因。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国人的充分理解,甚至阻力重重,很多人认为现代作曲家只是在利用中国元素,多是些噱头、表面文章,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些“怪异”的声响同中国音乐传统有什么关系。这里,存在学科隔阂,很多国人,包括很多专业音乐人,对中国现代作曲家缺乏了解,他们对这类作曲家的印象只是通过一些他们很不习惯的音响获得,至于这些作曲家的所思所想,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学习、钻研,以及他们通过“作曲”这项活动所注入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是西方作曲家绝对做不到的),并不能得到多数人的领会和认同。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即所谓的“相向而行”来解决。
(本文由“中央音乐学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中国当代音乐与音乐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