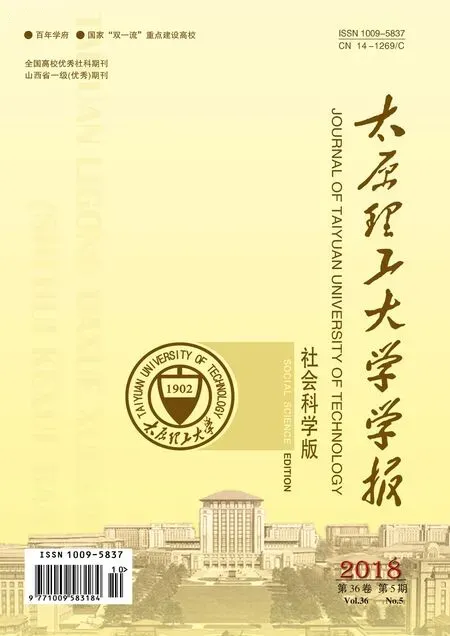“汉道”与汉代政治文化
刘博予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汉魏禅代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汉献帝刘协的禅位诏书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却常被当作汉室为曹氏父子歌功颂德之作,从而受到大多数史家的忽视。当时的曹魏已成为黄河以北的独立国家,其与汉帝国已非郡国与朝廷的从属关系,而是处于与汉帝国平行之地位[1]。“天子让贤”,本是《尚书》与《礼记》等儒家经典记载中的上古圣制,献帝诏书以“追踵尧典”之名义,将魏武王曹操的功德与尧舜圣王相提并论,此种书写模式将汉魏禅代的复杂政治斗争以儒家的理想粉饰,成为后代王朝鼎革的书写范本。禅位诏书对于曹魏政权合法性之建构具有关键意义,为了证明曹魏继承汉家天命的合法性,诏书用大量的篇幅去追溯汉家“失德”之过程,认为安顺二帝之后的东汉帝国已然“汉道凌迟”,而冲帝、质帝、桓帝无嗣导致国统三绝之根本原因亦在于此[2]。事实上,东汉帝国之衰落有着广泛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因素,亦与帝国内陆边疆的羌胡叛乱息息相关。禅位诏书是一种高度礼仪化与程式化的文字,“史实”与“史相”在此产生了巨大鸿沟。
诏书的细致描述,为我们观察汉帝国以“汉道”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的参照点,也为深入理解“汉道”提供了可能性。“道”最初的含义指交通道路,许慎将其解释为:“道,所行道也”[3]。在本义之外,“道”还是中国哲学里最核心的一个概念,表示某种具有神秘属性的道理规则。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道”衍生出一整套处理宇宙、社会与人生问题的知识与技术。先秦道家甚至将其看作宇宙万物之本源,儒家亦“于道最为高”[4]。考究“汉道”一词,“汉”为汉帝国之国号,萧何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4]。将神秘而伟大的“道”与国号相连,可知此“道”是帝国意识形态之指导,其中包含着汉帝国的立国精神与制度设计。陈苏镇将“汉道”解释为汉朝治国治天下之道,认为《春秋》是汉帝国统治者确定“汉道”的重要理论依据[5]。笔者赞同陈苏镇的观点,本文将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对“汉道”这一词汇的内涵作进一步阐发,以期揭示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意义。
一、从“周道”到“汉道”
王国维将殷周之际看作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6],但张光直等学者却反对此说法,认为商周同样源于龙山文化,两个时代的思想世界同多而异少[7]。探究殷周之际“礼制革命”思想的源头,可以发现这种认识的形成与孔子有关。儒家创始人孔子始终认为西周以“文”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优于夏代和商代,因而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感慨。后世儒家思想家普遍崇尚“赫赫宗周”的完备礼乐文化,对夏商二代的文化认同远不及西周。此种史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为西周王朝制礼作乐的周公,亦被史籍书写为尧舜禹一样的圣人,乃至于被唐代学者韩愈等人看作儒家道统的传承者。梳理汉代基本史料,可知在汉代人的思想世界里确实存在一个“周道”,而“周道以隆”盛况的实际缔造者正是周公。春秋以降,“周道”已然呈现出“浸坏”的特点,周天子的地位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汉代人普遍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春秋霸主的相继而起,以及孔子写《春秋》褒贬史事,皆是“周道”衰落的结果。董仲舒指出,虽然厉王与幽王使得“周道”衰落,但周朝治国治天下之道本身仍然有值得汉帝国学习之处[4]。儒家学者的书写,把周朝树立为充满礼乐精神的理想之国,“周道”在汉代君臣的思想中亦具有永恒价值。
在认同“周道”的同时,汉代史籍也屡见“夏道”与“殷道”,如果我们继续按陈苏镇的思路将其理解为夏商二代的治国治天下之道,可以将其与“周道”“汉道”作书写模式上的比较。如:“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8],“殷道衰,诸侯或不至”[8],“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8],“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4]。司马迁与班固的书写,往往将“夏道”与“殷道”置于“兴”与“衰”的历史循环之中,此种模式与“周道”完全相同,仿佛王朝的治国治天下之道是天命更替的体现,其兴衰的质变过程亦常处于大历史的节点之上。无论是武丁还是箕子,都凭借自身之圣德成为商王朝治国治天下之道的文化符号,其固定的书写模式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德治色彩。在汉代人的思想世界里,夏商二代的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传世文献中也很少记载其治国治天下之道的具体内容,至多是大而化之的歌颂之文。因此,《史记》《汉书》中的“夏道”“殷道”远没有“周道”那般深入汉代人的历史认知。
秦帝国统一天下,依靠的是制度与文化上的军国主义传统,这本就不符合儒家元典崇尚的德治精神。秦帝国在农民起义与贵族叛乱的时局中迅速灭亡,更让汉初社会的“过秦”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汉代人相信,曾经不可一世的秦帝国是“无道”的。从商鞅到秦始皇,秦帝国以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失败的政治实践。从表面上看,“汉道”以“周道”为效法对象,一是因为秦帝国之“无道”,二是因为“夏道”与“殷道”的实际内容在典籍中找不到文字依据。事实上,“汉家法周”的真正因素在于周代的历史书写极其具有吸引力。布克哈特认为,西方人向往的古希腊文明并没有那么美好,它只是一个“由幻觉组成的黄金时代”,而对过往时代的过度赞美是一种“愚蠢倾向”[9]。此种情况类似于汉代儒家对“周道”之向往,真实的周朝与历史书写中的“赫赫宗周”定然存在差距,孔子称颂的礼乐文化在周代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商榷,文明与野蛮夹缝中的早期华夏国家也肯定不是儒家元典中的理想国形象。
《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了汉帝国宫廷政治中的一段对话。窦太后宠爱幼子梁王刘武,欲使景帝刘启立刘武为帝国储君。景帝已有数子,废子而立弟实在有违帝国祖制。碍于母亲之情感与颜面,景帝不得不询问朝廷群臣的意见,群臣坚定地认为“汉家法周”是既定国策,应该遵循周代典籍中的宗法制度。众人的坚持使窦太后最终屈服,她让梁王刘武回到封地,再未干涉朝廷立储[8]。汉帝国建立之初,朝廷的制度设计大都沿袭秦代的帝国旧制,但君臣上下服膺的治国理念却是“汉家法周”,此种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正是汉初社会复杂面貌的反映。如果我们抛开对“秦政”与“周道”固有的刻板印象,仍然可以在史料中找寻到周秦政治文化之间的延续性。景帝宫廷事件言及的周代宗法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秦国的制度,虽然林剑鸣等学者认为秦国宗法制不严格[10],但却不能否认秦国公族在宗法制度上对周朝的效仿。从秦献公开始,秦国国君基本上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传承,张海云认为这是秦国收留周遗民之后受到的文化影响[11]。宗法制只是周秦共有制度的一个例子,二者在礼仪与文化等诸多层面还有融会贯通之处。“汉家法周”与“汉承秦制”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后世学者想象的那样大,周秦文化在历史书写中的泾渭分明也只是层累构造的结果。
秦帝国的文化政策曾使“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盛况戛然而止,汉帝国初期的宽松无为让归于死寂的各思想流派重新活跃起来,雷戈据此将汉初称之为“后战国时代”,以形容诸子百家之学术在汉帝国官方制度建构中的多元共存[12]。汉初君臣虽极力提倡“汉家法周”,却很难通过历史书写完全复原周代礼制,更无法将其运用于国家治理。武帝时代的思想家通过理论建构,终于在“奉天法古”的《春秋》之道中找到了“汉道”的根基,并促使皇帝以尊崇儒术的方式开创出武昭宣时代政治文化的新局面。然而,在帝国蒸蒸日上之际,仍有一股暗流涌动在儒生的思想世界里。历史书写中的周代礼乐文明是如此充满魅力,以至于儒生对“周道”的崇拜一刻也未曾停息。他们幻想着恢复宗周礼制,亦希冀有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改变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吕思勉将此称之为“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13]。王莽对“周道”有着宗教般的迷狂,力求让帝国的典章制度符合经书纬书之记载,阎步克认为这是“制度文明”内在倾向性的极端表现[14]。新朝的崩溃比秦帝国来得更为迅速,王莽复兴“周道”之举亦成为理想主义之梦幻泡影。在西汉帝国的中后期,儒生群体中有许多人与王莽有着同样的信仰,他们推动着元帝、成帝、哀帝三朝的制度改革,并成为新莽复古改制事业的中坚力量。班固的历史书写对王莽及其支持者多加贬斥,却很难掩盖他们受到社会上下广泛支持的事实。“周道”的影响力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从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介入帝国政治的实践,并最终发酵为颠覆汉室天下的力量。
《后汉书·祭遵传》收录了博士范升给光武帝刘秀的上疏,在一系列充满儒家神秘主义修辞的表述中,有“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的语句[15]。“受命”之说源自先秦,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屡见“文王受命”“王受命”“文武受命”等言语[16],汉代帝王亦常以政治神话之方式渲染“受天之命”的过程,这是王朝建构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常见书写模式。商鞅曾以“论至德者不和于俗”为理由向秦孝公力推变法,王子今认为商鞅所说的“至德”与东方诸国的“德”在文化内涵与文化基点上有所不同[17]。若秦之“至德”从属于秦国政治文化的特殊语境,光武帝刘秀之“至德”则与汉朝治国治天下之道有关,范升的上疏在“道”与“德”之间显现出汉帝国的政治逻辑,刘氏皇帝与汉帝国以一种形而上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从舂陵起兵到入主洛阳,光武帝刘秀将天下人厌弃新莽之政、怀念“汉道”的心理充分转化为政治力量,通过广泛的社会基础重建汉帝国,以汉室中兴之主的身份开启东汉之新局。陈苏镇指出,刘秀“坚持将东汉的建立说成西汉的复兴”,是为了获得“政治文化优势”[5],这种优势的实质正是“汉道”书写所具备的强大吸引力。从“周道”到“汉道”的演变,不仅是战国思想家与帝国统治者的思想演变,更是早期中国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变迁之见证。
二、奉天法古:“汉道”的核心思想
汉武帝“尊《公羊》家”的政治决策使董仲舒成为帝国改制的理论奠基者,徐复观认为董氏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推重,都与汉帝国的现实问题紧密关联[18]。从土地政策到宗庙礼制,从赋税徭役到抗击匈奴,董仲舒皆能在经典中找到理论依据,将《公羊》学融汇在帝国政治的实践之中。治《公羊》学的汉代儒生,无不希望《春秋》这部孔子制定的“拨乱反正之法”能成为汉帝国受命改制的指导思想。事实上,经过董仲舒的不懈阐发,《春秋》之道正是“汉道”的主要思想源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写道:“《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19],明确地将奉天法古作为《春秋》之道的精髓。董仲舒的奉天法古是儒家王道政治体系中的帝王之学,其本体只能是高高在上的君主。帝国统治者无法在黄老学说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正好给《春秋》之道上升为汉朝治国治天下之道提供了历史契机。当儒家王道政治扎根于长安宫廷,表明了“汉道”也必然要以奉天法古为核心思想。
在中国文明初始时期,“天”即是构建先民宇宙观的一个极其深奥玄远的概念。葛兆光在探讨商周时代的思想世界时,认为从殷商到西周,“天”的意志始终是“价值的终极依据”[20]。在周人理性的世界观里,天是一个客观抽象的本体,如《论语·阳货》篇里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同时天还具有道德审判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人的命运。因此《泰伯》篇里孔子又说:“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子夏也发出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感叹。可见在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那里,天已然具有宗教本体性质。王子今讨论了汉代民间社会的“苍天”崇拜,指出汉代民众对“天”有着强烈的信仰,此种文化特征体现在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17]。为了利用臣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宗教情怀,夏商周三代君主皆自称为“天子”,以此将自己放置于宇宙秩序的中心。他们凭借“天子”身份主持祭天仪式,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垄断神权。在世界古代各大文明中,皆存在此种神权与王权的互动。古埃及的太阳神创世神话建构了国王与众神的密切关系,神权与王权在国家政治中互为依靠。埃及人认为神界与民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拥有神性的国王则是与诸神交流的中介人[21]。在希伯来王国,上帝被视为王权的终极来源,王权也不得不受到神权的强力制衡,从而成为一种“有限君主制”[22]。即使是毗邻华夏的内亚草原,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社会亦产生了强大的神权。史籍中屡见匈奴贵族祭祀的记载,霍去病曾将“修屠王祭天金人”当作出征的战利品,沟通天人的“胡巫”甚至出现在“巫蛊之乱”中,成为汉帝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单于与华夏君主一样,皆自称天神之子,后世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亦有敬天与祭天的文化习俗,并最终影响了蒙古人对“腾格里”的崇拜。华夏世界与内亚世界对“天”的信仰如出一辙,我们很难断定其起源究竟在何处,却能以此为线索探讨族群文化交流与帝国政治的多重互动。
儒家自诞生之日起,就因对“古”的推崇闻名于世,《汉书·艺文志》概括儒家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其向往的乃是唐虞、殷周、仲尼之功德[4]。可知儒家把历史传统看作立论之本,极力抬高上古圣王之地位。孔子在很多场合里表达了自己对古代的向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儒家渴望恢复宗周礼制,孔子及其弟子门人也积极参与了当时史书的编纂。西汉中后期,儒学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好古”的氛围里。在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时,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是在历史传统中寻求解决方案。
“天”和“古”在董仲舒的理论里得到了统一,二者皆成为汉代意识形态里极为重要的元素。在汉代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奉天”主要体现在朝廷对天人感应思想的崇信。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上天用灾异警示君主,用祥瑞表扬君主。人间帝王的一言一行都在上天的注视中,因而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政策。“法古”则体现于对古代的效仿,武帝时代修郊祀、定历数、协音律、绍周后等改制措施都可以看作是在效法古代贤王。探究文景时期未进行改制的原因,除了与国力有限相关,还因为推崇“法古”的儒家在决策层里未占主要地位。“奉天”可以看作儒教对宗教本体的敬畏,“法古”则是对历史传统的崇尚。徐复观通过考察《左传》等经典,认为祭神、卜筮、解说灾异等具有明显宗教性质的事务,在春秋时代也属于史官的职责范围[18]。由此可知历史与宗教联系紧密,最早的历史学也是从宗教中诞生的。故而“天”与“古”在儒家学者心中是相通的,“奉天”和“法古”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障碍。
三、后世典范的治国治天下之道
在汉帝国灭亡之后,“汉道”却并未消亡,而是作为一种帝国政治的典范受到后世推崇。五胡十六国时期,第一个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匈奴汉国就自称是汉帝国的继承者,祭祀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追谥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求以异族身份获得正统地位。《晋书》记载,刘渊即位为汉王时,就曾下令追述汉朝诸帝之功德,下诏先后赞扬了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数位君王,其中认为汉文帝是“重以明德,升平汉道”的皇帝[23]。相比马上取天下的汉高祖和开边兴利的汉武帝,汉文帝以仁义圣明的形象闻名于世,因而刘渊对其极为推崇,试图以此消弭匈奴残暴的形象。刘渊推崇“汉道”,不仅是因为汉帝国统治中原的时间长于魏晋王朝,更是因为四百年汉祚使汉帝国的治国治天下之道深入人心。当三国战乱的硝烟还未弥散,西晋宗室诸王的纷争又使天下重新陷于战火,当时百姓自然十分怀恋曾经强大繁荣的汉帝国。刘渊在建国过程中,与其部下常讨论汉代典故,对汉高祖、汉光武帝征战天下的历程烂熟于心,并将其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与此同时,他在官制建设上也效法汉代,即位为汉王时,他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称帝后改三公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可见其对汉代制度的迷恋。刘渊创立的匈奴汉国,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晋人未必同我”的情况下建立的,他标榜“汉道”意在凝聚人心,其具体内容与昔日汉帝国的治国治天下之道相去甚远。由于当时战乱的环境和刘渊集团的族属,匈奴汉国不可能真正施行“汉道”,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汉帝国深远的影响力。
除了自称汉朝继承者的匈奴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政权也时常追述“汉道”:“今既无善律,则大齐所尚,亦宜依汉道”[24],“汉道方盛,黄、绮无闷山林”[25],“汉道既登,神仙可望”[26]。十六国和北朝政权大都与匈奴汉国一样,是由入主中原的胡族建立,他们统治的中国北方是昔日汉帝国的核心区域,也是汉文化最繁盛之地。永嘉之乱后,许多未南渡的北方大族纷纷筑坞堡以自保,形成与胡族朝廷抗衡的割据力量。在文化上,这些大族仍然承袭汉代的经学传统,保留着华夏文化传承的火种。为了笼络这些大族及更多的汉族百姓,胡族朝廷不得不从汉帝国的治国治天下之道里吸取经验,以“汉道”稳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南渡的东晋南朝政权在文化上已经发生了大转变,第一流的学者早已不像汉代学者那样钻研儒家经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玄学与佛学。但玄学与佛学大多关注繁杂的哲学思辨和遥远的彼岸世界,极少涉及现实的治国治天下之道。因而东晋南朝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依然遵循“汉道”,这不仅带来了成熟而理性的政权建设,也表明了自己才是正统的华夏政权。
儒学是“汉道”的理论基础,崇尚儒学也是“汉道”对于后世最大的影响。东吴陆抗在上疏中说:“汉道未纯,贾生哀泣”[2],引用了汉初儒生贾谊的典故。“汉道未纯”之原因是汉初儒学还未兴盛,贾谊的哀泣可以理解为他看到了儒家政治理想与汉初现实的巨大落差。贾谊是荀子的三传弟子,其学说兼有儒家、道家、法家之色彩,但最主要的思想还是儒学。汉儒有“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两种政治学说,贾谊和申公是前者的代表[5]。虽然最终成就“汉道”的是董仲舒的公羊学派,但贾谊“定制度,兴礼乐”的思想也对汉代政治有着很大影响,而他提出的应对诸侯王和匈奴的策略,也成为汉代治国治天下之道的一部分。《汉书·扬雄传》所载《法言》序里,也提到了“汉道”:“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4]。扬雄生活于儒学昌盛的西汉中后期,深受元帝、成帝以来改制运动的影响,他心中的“汉道”已然是纯粹的儒家之道了。“汉道”从汉武帝时代发展到王莽时代,再到刘秀复兴汉室,其中儒学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入了古文经学和谶纬等新内容,但其对儒学基本理念的尊崇是一致的。汉代人对儒家提倡的孝道更是极力推崇,累世皇帝谥号都冠以“孝”字,也由此开启汉代治国治天下之道。自汉代开始,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后世思想文化的新变革大都在汉代学者的基础上作新阐释。后世王朝的政治改革也能看到“奉天法古”思想的痕迹。这些都是汉帝国治国治天下之道给后世的财富,在这一层面上,汉帝国树立的典范意义超过了作为华夏第一帝国的秦帝国。
综上所述,秦的统一使早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昔日周朝治国治天下之道在秦人的战车下粉碎,但秦却未制定出自己的治国治天下之道,秦帝国也因此土崩瓦解。汉帝国建立之后,逐步探索自己的统治策略,在吸取“周道”礼治主义的基础上,由董仲舒等思想家根据《春秋》制定出“汉道”,并最终在汉武帝时代成为立国之本。“汉道”的核心思想是奉天法古,这源于儒家对宗教本体和历史传统的崇敬,汉帝国统治者也通过天人感应和复古改制彰显自己的政权合法性。除此之外,四百年国祚也使汉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王朝之一,后世王朝不断从“汉道”中吸取经验,其典范意义已使其上升到“中国之道”的层面。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