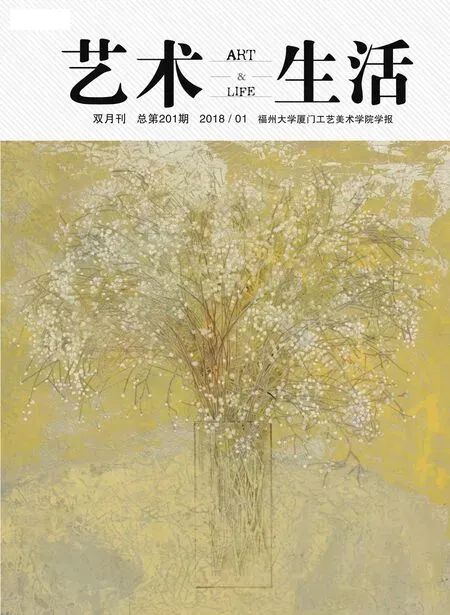传统徽墨研究综述
陈艳君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蚌埠 233041;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徽州在唐初至宋中叶称为歙州,宋徽宗宣和年间,歙州更名为“徽州”,元代称徽州路,明清为徽州府,该地所产之墨便称为“徽墨”。“天下墨业,尽在徽州”,徽墨在中国制墨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闻名中外的中国“文房四宝”之一,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徽墨具有深厚的科技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对传统徽墨的记载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徽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已有的学术积淀值得我们进行细致地整理与总结。
一、徽墨的起源
徽墨创始于唐末,当时由于藩镇割据和连年战乱,易水(今河北易县)著名墨工奚超、奚廷圭父子南迁到歙州,不断改进捣烟、和胶、配料等制墨技术,创制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经久不褪,香味浓郁”的佳墨。南唐后主李煜视为珍宝,封奚廷圭为墨务官,并赐国姓“李”,李廷圭成为徽墨鼻祖。后来易水著名墨工张遇之子张谷也迁到歙州,带来了先进的制墨技术,歙州制墨业的地位逐渐取代了易水。“徽墨”之名由此而得,并且逐渐发展,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种徽墨起源说。[1]
二、徽墨发展的原因
学者们都认为徽州制墨业兴盛是诸多综合因素决定的。高淮强指出,徽墨的兴盛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分不开;徽墨得以发展之时大多是“太平盛世”;徽州地区古松、桐子油、和胶用水等自然资源优势,保证了徽墨的高质量;徽商的活跃为徽墨的流通创造了优越条件。[2]林欢强调河北墨工特别是易水墨工南迁之后对唐宋以后徽州墨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李廷珪被推崇为徽墨宗师,他使易水制墨技术在徽州获得空前发展,“以‘易水法’为基础的河北制墨技术既是宋元以前中国传统制墨经验的总结,也是明清徽墨独领风骚的起点”。[3]梅娜芳认为徽商将徽州制墨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最初的原料到最终的市场,无不有赖于徽商之功”;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技术传承方式的变迁对徽墨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家传世袭”的传统制作模式逐渐被产业化的雇佣模式取代,成功的墨工开始招收徒弟,雇佣伙计,“各种家传的制墨方法不再为少数的墨工所垄断,师徒各立门户的做法进一步促进了制墨法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制墨业”。[4]
三、徽墨的制作工艺
徽墨之所以有“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丰肌腻理,砥纸不胶;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香味浓郁”[5]的美誉,就是因为其制作原料种类丰富,制作工序十分繁杂,不同流派又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精湛的工艺,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沈鹏飞的《制墨法》,详述徽墨的桐烟制法,尤其是对徽墨制造法的记述比较翔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6]高淮强介绍了不同历史阶段徽墨的工艺特点:南唐李廷珪用黄山、黔山、松萝山的古松烧制成优质松烟,加工时规定要“十万杵”;宋代潘谷墨中加了麝香,冰片、沉香等增香剂;张遇的“龙香剂”,“用一种油烟和脑麝、金箔制成的墨”,专供御用;明代罗小华利用当地盛产的桐子油烧烟,得烟较多,制成的墨色黑有光;明代程君房“在桐油中加漆烧之,得烟极佳,墨名漆烟”,他通过在桐油烟中加入珍贵配料,创制了“超漆烟”。[2]李雪艳指出,随着松树的匮乏,油烟墨原材料的不断扩展以及技艺的成熟,松烟墨“自魏晋以来的主导性地位逐渐被油烟墨替代”,明清以后,徽墨都是以桐油为主的油烟墨。[7]王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制墨工艺研究——以松烟墨、油烟墨工艺发展研究为例》,多处涉及到李廷珪、方瑞生等徽墨名家的制墨工艺,文中特别指出,许多研究者认为油烟墨始创于南唐墨工李廷珪或宋初墨工张遇,实际上,油烟墨的出现“应当在南北朝时期,略晚于松烟墨”。[8]林欢强调河北墨工南迁的一支,以唐末易水人李廷珪和张遇为代表,“讲究以‘十万杵’为代表的‘易水法’和原料新配方,开创了徽墨发展的新时代”,留居本地的一支则以张滋、陈瞻等为代表,“他们在‘和胶’技术上的新探索,同样为日后徽墨制造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四、徽墨流派
由于市场的定位和目标的不同,徽墨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各个流派有不同的顾客源和生产目的,其制墨风格与墨品及其艺术特色也有很大差异。徽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主要形成了歙派、休宁派、婺源派三大派别,歙派主要是为服务于宫廷权贵而生产,“以隽雅大方、雍容华贵见长”;休宁派生产的徽墨多受富豪喜爱,所制墨“样式繁杂、华丽精致”;婺源派的市场份额最广,其大部分墨品是为“满足社会底层市井、未及第书生生活学习之需”,但也涉足高端消费市场,在设计中,更加贯彻“俗”的原则,“写实性题材摆脱了权贵与士绅们关于自我身份‘高层次’定位的局限,而与整个社会共同的思想情感相互作用,促进了婺源派徽墨题材创作的无限丰富和普及化”。[9]何建木简述了婺源虹关詹氏墨商世家的经营状况、墨品特点、墨业兴衰等问题。[10]此外,他还分析了婺源墨商在空间和家族的分布及其产销活动,揭示了婺源墨商经营活动及其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11]
相比较而言,对歙派、休宁派的研究则比婺源派深入得多。周玄就其见闻所及的材料,略考了曹素功制墨情形和制墨的种类。[12]张广文指出乾隆初期宫廷曾进行的三批整理、鉴选主要藏墨,其中得到程君房、方于鲁制墨近四百件,还出现了仿程君房、方于鲁等人的作品,流入宫廷后又被识别。[13]蒋樹成对上海博物馆所藏十数锭明代程君房款墨的雕刻技法、书法款识、墨色质理和图案纹饰进行了考辨,定出真伪。[14]而关于程君房、方于鲁两家墨店的竞争,尹润生认为未出争名夺利的范围,实质就是商业竞争。[15]蔡鸿茄也认为程、方二人的竞争“不应看作只提‘私愤’”,而是具有带有资本主义竞争色彩的社会性,为了达到“高人一筹的目的,他们会使出各种恶劣的手段,这是资产者以强凌弱、贪婪罔极的丑恶本质所在。”[16]但是,我们也不能将因程、方两家恩怨而加剧的徽墨业竞争的特例归为晚明徽墨业竞争的普遍现象,墨匠与墨匠的关系“并不全然如程、方间的对立;甚或可能在彼此学习与褒扬间,寻得墨业贩销之较大空间”。[17]
学术界对于休宁派的研究,尤以胡开文墨业的研究为细致,汪启茂墨业接替叶玄卿,胡开文墨业又接替汪启茂,胡开文墨业是明代徽墨“休宁派”的嫡系传人。[18]目前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是胡开文墨业的创建的时间、创建者、名号的来历等。
关于创建时间主要有“乾隆三十年(1765)说”与“乾隆四十七年(1782)说”两种:主张“四十七年说”的如穆孝天、李明回等[19];更多的学者主张“三十年说”,如陈平民[20]、朱世力[21]、黄秀英[18]、胡云[22]、林欢[23]等。关于创建者主要有“胡天注说”与“胡余德说”两种:鲍杰[24]、黄秀英[18]、胡云[22]等人都认为胡天注开创了“胡开文”墨业,以胡余德为首的第二代传人继业发展了“胡开文”墨业;而徐子超认为“胡开文”的奠基者、草创者是胡天注,草创时的店号也是需要考证的,而创“胡开文”名号的是胡余德。[25]关于“胡开文”名号的来历,学者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是,当年胡天注租赁墨店时,往返休城、屯溪途中,在居安村西石亭歇息喝茶,见石亭门楣上刻有“宏开文运”四个大字的石匾,头尾两字不认得,见中间“开文”二字作墨店号甚佳,于是就树起了“胡开文”的招牌。[20]此外,徐美玲[1]、林欢[23]、徐子超[26]、胡云[22]、胡毓华[27]等还从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角度对胡开文墨业的墨品、题款、工艺特点、传承、发展及家族内部激烈的商业竞争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
五、徽州墨工研究
随着徽墨的不断发展,涌现出大量技艺高超的著名墨工。陈爱中根据初步收集的史料,辑录了清代婺源部分墨工。[28]林欢以《鸿溪詹氏宗谱》中涉及虹关墨工的部分谱碟史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于虹关詹氏历代墨工们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初探;同时指出,以《鸿溪詹氏宗谱》为代表的大批婺源詹氏谱牒资料,保存了婺源詹氏宗族每一族每一支谱碟史料,对于婺源整个墨工、墨商群体发展和流动状况的研究极有助益。[9]汪圣铎、胡玉考察了徽墨宗师李廷珪的世系传承。[29]李氏渐趋衰落后,更多的墨工脱颖而出,黟县的张遇、黄山的沈珪、歙州的潘谷、新安的吴滋以及戴彦衡、柴殉等人,都是10世纪到11世纪徽州制墨行业的著名人物。[30]
学者们还对明清徽墨著名制墨家的生平及其制墨进行考证和分析,如周绍良考证了曹素功所制墨和曹素功家世[31];翟屯建[32]、王俪阎[33]考述了程君房的生平及其传世之墨;胡毓华则介绍了胡开文制墨世家“单传”世袭制[27];张子高考证了程一卿(即程瑶田)及其所制的墨[34];林欢考述了胡子卿的得名、选料特色、制墨原则、墨品造型、销售对象、与胡开文家族的渊源,以及胡子卿墨业的兴衰过程等问题[35]。
还有学者对墨工与文人之间的互动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汪圣铎指出宋代文人经常将墨工请到家中制墨,在制墨的过程中进行探讨和交流,墨工往往将自己的墨作赠与文人,以其共同喜爱的墨“作为其交谊的桥梁”,文人则往往用诗句表达自己“对墨的认知与喜好”。[29]徽州的一些著名墨家,不仅制墨,还兼营其他相关行业,同时具有一定的文才,“他们同时兼具了工匠、文人、商人的身份”[17]。然而,梅娜芳指出,那些得到文人认可,与文人交游、并坐论理的工匠,真正凭借的并非他们在墨作方面“的一技之长,而是他们的文才”,纯粹的工匠身份,“其地位的提高是有限的”[4]。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旅居上海的安徽婺源帮制墨工人发动了一次过程曲折复杂的罢工运动。刘石吉先生指出,这次罢工运动“可视为二十世纪工业城市中所产生的一次典型的传统手艺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36]
六、某一特定类型徽墨的研究
徽墨的种类丰富,根据社会各阶层对墨的不同要求可分为书画墨、贡墨、仿古墨、药墨、素墨;根据形制可分为零锭墨和集锦墨;根据原料质地可分为松烟墨、油烟墨、特种墨、包金墨、朱砂墨、五彩墨等;根据用途可分为观赏或收藏墨和实用墨。[5]林欢从徽墨配料变迁的角度,对历代制墨的配料沿革进行考察,同时就传说中的“八宝五胆墨”以及徽墨的药用功能进行探讨。[37]
从唐代到明代,“龙香”御墨的制造地点“经历了由北到南的转变过程。”清宫旧藏大量明代“龙香”御墨,标志着其制作技术已经完全成熟,更表明了明代“以歙县、休宁为代表的徽墨生产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制墨中心。”[38]林欢从历史文献角度对唐宋至明清以来“龙香”墨的命名、成分及其发展等方面进行考证。[39]
清代御墨除了由御书处墨作承制外,还向安徽墨工订制。林欢通过光绪朝《棉花图》贡墨探析了晚清徽州贡墨的一些情况。[40]周绍良指出,徽州贡墨,在康熙时期大多数是由曹素功艺粟斋承制,“可能后来还有汪近圣鉴古斋制者”,咸丰、同治以后,则“完全是胡开文一家承担了”。[41]
集锦墨是带有装饰的成套丛墨。按其类别有三种:每锭墨形式各殊,图案各异;每锭墨形式相同,而绘图题识互异;选用不同的名品,聚集在一起,各墨的形式、图案、名称都不相同。[42]“集锦墨”是在中国制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商品经济发展、行业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出自不同派别墨家之手的“集锦墨”风格明显不同,休宁派以雍容雅致取胜,歙派则以富丽华贵而见长。[43]李晓峰等介绍了济南市博物馆所藏清光绪年间胡子卿所制的《棉花图集锦墨》。[44]
明代,文人兼作制墨成为风气,清代,文人自制墨达到高潮。大批文人自己设计墨的款式、图案和造型,再交由墨店生产。这些“由刻工高手制模、由墨家精心制作,工艺非常考究的自制墨”,既是文人情感的一种寄托,同时也“丰富了墨的品种内容,存世量较小”。[45]
徽墨不仅是书写绘画用具,而且集合了中国传统绘画、书法、雕刻乃至医学等多种工艺于一体,逐渐成为集实用与鉴赏为一体,甚至单纯用以鉴赏的艺术品。近年来从收藏、鉴赏的角度对徽墨的研究不断增加,综合性研究如赵正范的《清墨鉴赏图谱》[46]。另外,刘冀分析了苏轼的藏墨、制墨和品墨的观点,探讨了中国古代文人的藏墨观及其对历代墨工制墨的影响。[47]林欢就周作人《买墨小记》所描述的一些墨品,对当时文人藏墨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地论述。[48]马起来[49]、郝颜飞[50]等介绍了安徽省博物馆和博物院珍藏徽州古墨。张丽[51]、马起来[52]、杨海涛[53]、王健丽[54]等分别介绍了程君房、程怡甫及胡开文墨中的一些珍品。
七、关于徽墨墨模与墨谱的研究
墨模,是制墨业中的关键技术之一,“是压延墨坯的外框和里嵌的木扣并用来扣印版的总称。与印版组合后便是造就墨的形体和外表装饰图案的工具”。[55]墨谱,是制墨名家所独创的精品墨的图录,以及“独家制墨秘笈的荟萃著作”,用作墨庄“秘档、精品展示、薪火传承与炫耀励志”[56]。徽州文化为墨范图的创设“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徽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则是墨范图“得天独厚的蓝本”;徽州众多的博学文人、丹青妙手和民间艺人使墨范图“进人了更高的艺术境地”。[57]石谷风[58]、徐子超[59]、吴春燕[60]、汪超国[61]、张明泉[62]分别解读了徽墨墨模印版雕刻工艺及其在徽墨发展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在徽墨墨谱的研究方面,史正浩从艺术传播的角度,对《程氏墨苑》图像传播的过程进行深入研究。[63]赵硕从艺术设计的角度,以《程氏墨苑》为例,对明清墨谱设计的特点与变化进行了梳理,对墨谱设计中涵括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进行了分析与总结。[64]梅娜芳探讨《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的编纂与推广和成就。[4]
台湾学者林丽江的《图像的增生与扩散:<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中的墨样与编印》对两部墨谱进行了比较研究。[65]海外学者对徽墨墨谱的研究,主要有史景迁(Spence,Jonathan D.)[66]、 吴光清(Wu Kwang-Tsing)[67]等人,他们多是从中西文化交流史及版画史的角度,通过《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探讨晚明世人的审美品味及西洋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比较了《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并且梳理了为《程氏墨苑》撰写题赞的文人的姓名、籍贯和身份。[68]
八、徽墨衰落的原因
从清代后期开始,历经千年之久的徽墨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解析,认为徽墨的衰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1.战乱频繁;2.吏治腐败;3.传统书写工具被自来水笔以及墨水取代;4.科举制度的废除等。徐美玲在此基础上又补充几点:一是经济方面,清代后期,徽墨业的市场竞争性凸显,现代化机械和化工产品“不断取代传统的加工器具和原料”。二是政治方面,民国以后,一些徽墨世家在混乱的时局中追求政治上的保护网以保存实力,顾不上徽墨的发展。三是传统技艺的经验不足,近代纸张的制作技艺比徽墨的发展成熟,“对徽墨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达到‘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要求极其困难”。[1]林欢也认为,徽墨不能满足现代纸张的印刷要求逐渐遭到淘汰,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基础已经不复存在”。[48]民国时期,外国资本输入与现代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使得中国典型的手工制造业之一的徽墨业生存环境日渐艰难,传统的手工技术和工具“无法生产出因消费习惯变化而被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固有市场不断萎缩,徽墨“由原来的大众消费品变成了小众消费品”[69]。但黄秀英和汪庆元也强调,虽然从书写工具的变革来看,墨“无疑已经处于边缘化”。但是,作为中国书画创作艺术不可替代的材料,墨“仍将会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徽墨将与书画艺术一起流芳百世。[8]
九、总结与展望
综合古今有关文献论述,对传统徽墨的研究主要是从徽墨的起源、沿革变迁、衰落的历史到徽墨的种类、鉴别、价值到徽墨名家和墨工的生平、墨品风格、制作工艺、名墨鉴赏及徽墨的文化内涵等方面的整理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研究的深度和资料的拓展来看,仍存在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缺少对徽墨制作工艺的系统研究
受传统儒家文化的重道轻器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轻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创新,甚至斥之为奇技淫巧。由于中国重道轻器的文化传统,传统文人士大夫很少记述徽墨的具体制作工艺流程。而墨工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直接关注生产过程的文献稀少。部分研究对徽墨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梳理,但一般仅限于古代记墨文献的整理,缺乏对不同徽墨流派、不同制墨家工艺的比较分析,对徽墨的制作工艺发展、制墨原料的变化等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这和徽墨在科学技术史和工艺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十分不相称。
(二)墨工的研究尚薄弱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抑商”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工商业被视为末业,工商业者从各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手工业者一直处于被贬抑的地位,一直处于社会下层。传统文人士大夫很少记述工匠的活动,墨工与其他能工巧匠一样,大多都是没有留下姓名。同时,徽墨史上的能工巧匠多为墨肆业主的雇用人员,并无在产品上署名的权力。由于以上原因,使我们对一大批徽墨墨工的生平及其制墨知之甚少,徽墨研究主要是重制墨名家和名号及其墨品考述。墨工资料的缺乏和分散,造成墨工研究的层面简单,缺乏对于墨工的制作能力研究,徽州墨工的辑录工作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
(三)大量研究偏重于提供徽墨鉴赏的相关知识,学术性有待加强。
徽墨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诗歌、绘画、书法和雕刻等多种艺术元素,兼具实用性、装饰性和观赏性,同时浸蕴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和徽州地域文化,徽墨一直都是文人士大夫热衷的主要收藏品。因此,相当多的徽墨研究都是着眼于徽墨收藏、鉴赏,尤其是一些研究者本身就是藏墨爱好者,他们多通过现存徽墨墨锭实物,结合文献,偏重文物鉴赏,关注实物形式多于理论形式,缺乏结合已有的实物和现实的实践推进若干理论问题的历史考证。
(四)深入挖掘史料,用现代科学方法推进徽墨研究
对徽墨文献挖掘的深度不够,缺乏徽墨文献整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固然是由于传统文人不重视生产实践,此外,徽墨文献整理也有来自文字和制墨技术方面的难度。墨谱、文集、笔记、方志资料结合家谱、族谱世系解析,以及通过田野调查抢救性挖掘资料,将分散的徽墨史料丛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辑录出来,进行校勘标点,为徽墨研究者提供便利,在徽墨研究中十分必要。
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徽墨,既要掌握文献史料,还要将现代考古学与徽墨史研究相结合,以实证科学为依据,进行实际调查与发掘工作,以考古发现和博物馆的文物资料为依据,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使徽墨研究脱离狭隘的清赏雅玩。
(五)从更广阔的视野深化徽墨研究
民国以前,墨一直都是文人书写的必备工具之一,墨更多地是作为重要的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徽商的出现,将徽州制墨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些徽墨名家本身就自产自销,兼具商人身份。尤其是,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为徽墨的流通创造了优越条件,徽墨的市场,也是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远及海外。徽商与徽墨的生产、外贸直销,徽墨业的生产关系等都值得关注。此外,徽墨的起源、发展与移民、与地区开发、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密切联系,对徽墨的研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徽墨对当时的社会又有什么影响和作用?研究徽墨对当前徽州传统工艺传承创新及徽州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借鉴和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徽墨研究的深入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材料,需要历史学家,文博和考古系统的专业工作者,徽墨收藏家、鉴赏家,古玩商业工作者,徽墨生产工作者,乃至美术工作者的共同参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