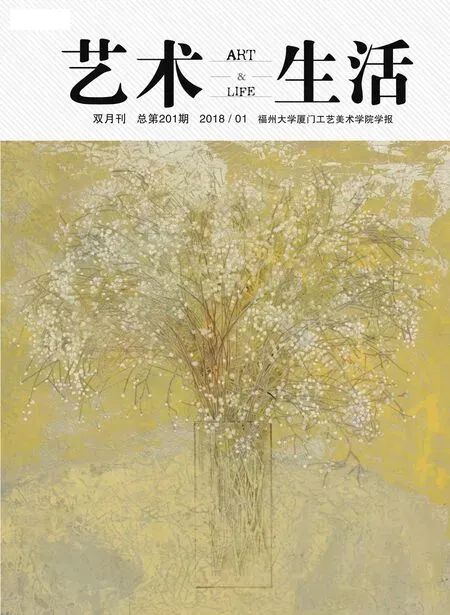艺术人生无际涯
——由齐白石陆俨少诸大师创作说起
潘丰泉
(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
一幅好的画作或一个成功的画展,总是能长时间留在观者的脑海里,给人挥之不去的念想和深入人心的启迪,就如前不久在厦门举办的《丹青之华·近现代十二家绘画大展》那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作一样。
这十二位大家,大多是晚清时出生的,如齐白石、黄宾虹,或民国初像陆俨少等,不够也基本上是成名于20世纪的艺术大家。他们都是在一片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度过少年、青年和中年的艺术生涯,个别画家甚至到了晚年才画名声起。那时,外有强敌对中华民族虎视眈眈,内有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但,就是这些艺术家,以他们一生对艺术追求的一腔热忱,以他们一生所从事探索民族艺术的激情,将个人的内心情感真实广泛并有趣呈现在世人面前,使得这一段绘画史,因为有这样美不胜收的一幅幅画面,让人如行走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也由此感受到那时由外族制造发动的一场场战争,妄图灭我中华民族艺术的狼子野心终成为泡影。虽然,这一段段伤痕累累满是伤痛的家国历史,让无数中华儿女们不堪回首,但这其中因有了大师们这一幅幅画作的精彩之处,透过其深沉的文化内涵和璀璨夺目的艺术光芒,再一次显示出华夏文化艺术的旺盛生命力,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似枝繁叶茂一般生生不息开来,从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身上和他们所创作的无数作品中,中国画这一艺术得以长成参天大树。
比如,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先生是在50岁后才真正进入大写意花鸟画这一领域的。这多少得益于他五进五出的经历,才得以眼界大开,最终决心告别乡关,从此一脚踏入京城就再没有回过故乡。正因为齐老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写意画艺术探索的领域中,于是,由他个人进入到写意画艺术这一华彩的序幕,便彻底拉开了。从齐白石先生出身的社会背景看,确实十分平常,本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间赤子,什么家学渊源根本无法与其后来所成就的一番笔墨事业联系一起,甚至相差甚远。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年轻时对于中国画的感觉认识,也只是前半生为了生计干起了木匠这门手艺活,间接有了一些了解而喜欢。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国画修习。所以把他描述为近代的文人画代表,似乎不十分妥当。
齐白石后半生在写意花鸟画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很快便在京城画界站稳了脚跟,此后便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像他这样属于草根阶层,无过硬的社会背景可以依靠而走向发达的画家来说,实属不易。但不要以为那一堆成就的取得,就同那些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所谓文人画修养全面的传统型画家一样,可以一蹴而就。恰恰是他那些让人百看不厌的充满了乡野风味的题材画面,以及从早年学过的雕花手艺那里感受到的某种似拙似熟的线条穿插、既平面又有些微立体的厚度等等,恰好给了他创作上的灵感,这多少摆脱了传统的程式化束缚。这或许是人们喜爱齐白石作品的理由所在吧?远胜于那位曾给他无数次建议甚至指出唯文人画道路才是正确的陈师曾先生个人画作的价值所在。那么,从齐白石这一艺术机缘追寻,所谓家学渊源之深之广也决非一定是获取艺术成功的关键所在,更多情况是每个人只要通过自身努力以及个体艺术天赋独特之处的极致发挥,同样可以在画坛上取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另一位在岁数上小了齐白石近半个世纪的山水画大家陆俨少先生,年轻时在专业院校学习过中国画,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一位科班出身的画家。同历代文人画家一样,陆俨少先生在他年轻时就较为系统扎实地学习了中国古典诗词的那些文化基础知识。由于长期致力于传统笔墨研究,更体味到“读书、作画、练字”这三者对于中国画创作的作用和功能所在。综观大师一生的山水画艺术轨迹,不难看出,他的每一幅作品无不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这无疑告知我们,一个人在艺术上要有大造化,对于与艺术相关各种不同的文化修练不仅是需要的,更须长期锤炼,一切有助于绘画表现的知识结构,它们将潜移默化地提升画家作品的表现层次和内涵。比如,陆俨少先生个人对杜子美律诗绝句中透出的意境的酷爱之情,是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与家人躲避一场场战乱,经历了惊涛骇浪中的长江之险境和所到之处那些触目惊心的内心情感,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中,更深刻体味杜诗境界的独特韵味——那一种苍茫厚重的美,尤其将它引入其山水画的构思创作之中,使他个人山水画因文学上特有的养份而耐人寻味。从这一幅幅画面看,陆俨少山水画艺术之所以在当下为画界所倚重,特别为那些艺术创作上更注重文学修养发挥的学者型画家所钦佩,无疑,与他一生的艺术追求即与一般人不同的更强调读书学习和重视与绘画一切相关知识的积累所分不开的。他的这些极富个人风格的山水画面,自然而然地为业内人士所欣赏,因为,由他构造的画面处处表现出极强的文学内涵,故作品里自上而下流露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养气息和一派温文尔雅的艺术感觉。
前面所评述的这两位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探索精神,某种程度上反映并代表了此次展览中大多数艺术家的绘画历程和生活方式。不过,在另一位艺术家身上——黄胄和他的人物画创作,不仅个人风格表现独特,而且与那个时期大多数人物画家的一些做派截然不同,虽然也是强调以写生手法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画题材,但传统人物画一些表现法则,仍然在他们长期大量的人物画创作过程中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当然同时也存在着“老瓶装新酒”或“依样葫芦”式地描绘新时代人物题材的种种不足。
而黄胄笔下的新时代人物画,拒绝了那些几近相似的做法,比如一开始先临摹古代人物画,到对象写生,再到整理加工为一幅幅作品,而是以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锐气,直接运用写生法则去创作,尤其在表现现代题材的人物画,包括像反映新疆少数民族人物的一幅幅风情画面,借鉴速写效果表现了这些生动感人的画面。或者说正是基于这一与众不同的艺术探索方式,使得其人物画创作充满了一种对应新时代的鲜活的文化生机与气息。故,黄胄大量的现代人物画面,既有清新活泼的艺术语言又有一种充满表现活力的视觉画面呈现,尤其是淡化了以往人物画里一些消极陈旧的东西,用生气盎然的艺术风貌成就了20世纪人物画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绘画精神和表现高度。总之,黄胄的现代人物画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一扫几百年来传统人物画多以仕女高士或道释题材为绘画内容且毫无时代气息的陈旧面孔。
展览中还有其他几位大家的作品。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花鸟画,每一幅画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观赏性。比如石鲁先生大量创作于中年时期的水墨画,特别注重作品的立意构思,无论在形式追求或风格表现上,都有强烈的时代性及探索特色,可谓独树一帜,是一位走在艺术前沿,用当下流行的形容说法即最“前卫”的风格型画家。但一场十年浩劫,他也同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无端迫害,一生命途多舛,使得后来一些作品逐渐失去原先有的艺术光泽,对这样一位在艺术追求上有高度的画家来说,这多少让人叹惜不已。
——黄胄画猫贺岁展
- 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贡布里希论西方历史中的漫画
- 传统徽墨研究综述
- 生态人类学视角下苗族“百鸟衣”的审美探究
- 县域文化产业现状调查与发展研究
——以连城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