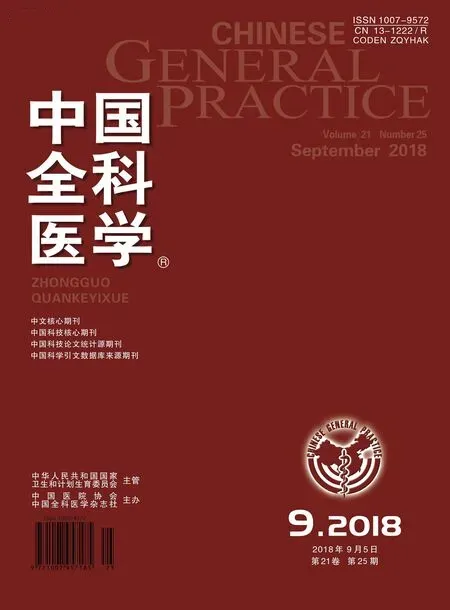激励与薪金
杨辉
1 内在的动机和外部的鼓励
激励或鼓励,指的是对一个人或一组人的态度、认知及行为改变的动力。通常可以通过改变一个人(或一组人)的外部环境或条件,来达到促进其行为养成、维持和改变的目的。政府对于全科医学的支持在于政策层面的鼓励,包括学科发展、就业前景规划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8〕3号)提出的“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显著提高,城乡分布趋于合理,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即是指让医学生愿意选择学习全科医学专业,让全科医生愿意从事全科医学工作,让全科医生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居民提供有质量的全科医学服务。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1)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人(或一组人)的行为与其内在动力或动机密切相关,内在力量产生的行为是真实的行为。因此,需要通过了解和激发个体的内心动力、动机及需求,为个体或组织提供帮助和支持,从而达到改变行为的目的。(2)外因与内因是互动的,其各自又有促成和阻碍2个方向。内因和外因的互动,产生了结果。如果结果未达预期,或者对结果不满意,那么就需要从内因和外因入手,从而改善结果。
2 鼓励农村全科医学的发展:中国的案例分析
中国全科医学最需要激励的是农村全科医学发展。农村基本医疗服务是中国基本医疗服务系统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没有农村全科医学的健康发展,就不能说中国的全科医学是成功的。
全科医学服务在中国城乡之间分布不合理[1],是一个长期以来内因和外因互动的现实结果。中国有大量在县级以下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专业人员:(1)从内因而言,乡村医生在农村执业的内在动力可能包括作为乡村医生的基本生活和收入依赖、对环境和关系的熟悉和渊源、对乡里村中居民的情感维系、村民对治病救人者的尊重、为乡里乡亲服务的理想追求。但乡村医生的内心也很纠结,如与城市医生相比收入水平低、学历不高、自我认可差、职业晋升机会少带来的不安全感,医学领域对乡村医生的“另册”治理,村民感知其医学服务胜任力较低,自身的年龄老化,实现自身价值的差距等。(2)从外因而言,毋庸置疑,农村卫生和乡村医生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如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医生服务的支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提供农村全科医生培训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沟通渠道的扩展,也给乡村医生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与此同时,乡村医生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少、如医学教育不足、进修机会少且工作条件较差、缺乏同行和专家支持、缺乏转诊资源、村民认可度低等。
中国基本医疗服务的土壤是适应中华传统特征乡村经济和中医文化,其近代的实践是被国际社会视为初级卫生保健经验的赤脚医生。如何发展农村的全科医学,激励在于通过加强外部的促成因素、减少外部的障碍因素,从而达到增强内部优势和减弱内部劣势的结果。这是一幅很大的画面,涉及的不仅是医学和健康系统自身的演进,也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息息相关。《中国全科医学》将持续关注对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发展的激励研究,路途虽漫长,但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收入水平的比较
收入是鼓励医生有效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不是唯一因素。收入水平和支付方式均可以影响医生的执业行为。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收入可以是一个位于需要金字塔底部的“生理的需要”,就如同人们需要获得食物、水、空气、房子等,是医生生计的基础。不过无论中外,收入大都是一个“避讳的话题”。在中国,不仅是医生行业,大部分行业的准确收入都是不可知的。医生的收入水平尤其敏感,因为“生意人”可以在商言商,而医生的收入却与治病救人的道德期望相悖。即使知晓了医生的准确收入,也不能直接根据汇率折算后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因为每个国家货币的购买力不同。中国各地区间、各城市间、城乡间的收入水平也不同,医生收入也如此,同样存在人民币面值与实际效用(购买力)不同的情况。因此,对于收入水平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平均值(集中趋势),还要关注其差距(变异程度)。进行相对比较是较为恰当的方法:在医学领域内,比较全科医生与其他临床医学专业间的收入水平;在社会层面,比较全科医生与各社会阶层间的收入水平、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城乡间的收入水平。这种相对比较,实际上也是医生们的“心算”(职业定价),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医生职业的主观价值。
(1)临床医学各专业间收入差距较大。墨尔本大学研究者于2008年在54 750名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中选取10 498名进行长期随访调查(MABEL研究)[2],将其收入按年龄、工作经验、工作时间进行调整后,发现所有医学专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为31.6万澳元[3],当年澳大利亚劳动者年平均收入为7.54万澳元[4],即澳大利亚的医生收入是劳动者平均收入的4.2倍。同时,研究发现自我执业的医生收入较受雇于医院的医生高27%;临床医学各专业间的收入也是“苦乐不均”的,收入较高的是诊断放射科、骨科及其他外科、妇产科、重症监护医务人员,收入较低的是精神科、儿科、胸科医务人员[2-3]。
(2)全科医生并非医学领域的高收入者。以澳大利亚为例,全科医生为私人执业,全科医生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粗略地估算,一名有经验的、全职全科医生的期望税前年收入为20万~30万澳元,超时工作的全科医生期望收入约为40万澳元[5]。MABEL研究对3 906名全科医生进行调查,发现全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为17.79万澳元,较其他临床医学专业医生的平均收入低30%[3],但全科医生的收入并非所有临床医学专业医生中最低的。
(3)全科医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影响全科医生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医学教育成本(教育成本越高则收入较高),工作年限和经验(年资高的医生收入较高)、专业资质〔获得澳大利亚全科医生学会(RACGP)会员资格的收入较高〕,性别(男医生收入较高),工作地点(农村医生收入较高),所在省份(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较高),工作类型(动手操作性质的服务收入较高),工作时间(超时工作的收入较高、全职工作收入较高),诊所性质(合伙制或合作制的收入较公司制的高),患者特点(病情简单患者的医生收入较高),市场需要(供不应求的收入较高)。
(4)与很多国家类似,澳大利亚的全科医生拥有其他非金钱收入的价值或收获。全科医生较其他临床医学专业医生具有更多的社会交往,工作时间弹性较大,可以选择兼职工作实现混合的职业生涯,具有较少的急诊或紧急的工作。相较而言,全科医生的工作性质更适合于女医生,虽然女医生的收入低于男医生。年轻和女性全科医生的收入是相对较低的,这也是其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的结果。SHRESTHA等[6]对澳大利亚3 906名全科医生的调查结果显示,53%的全科医生认为个人生活与职业之间是平衡的,年轻医生(X一代)和女医生认为个人生活与职业平衡的比例,较年龄较大者(婴儿潮一代)和男医生高。年轻医生和女医生的每周工作时间明显较少,休闲活动较多。该研究结果值得思考,全科医生之间(包括师生之间)是有明显代沟的,婴儿潮一代、X世代、千禧一代这3个代际跨度,显示出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对收入的态度。
中国全科医生的收入应该是多少?这可能是没有办法简单回答的问题。但可以研究全科医生收入的客观测量值,如教育和培训成本加上提供服务的投入等,也可以研究相对的收入水平、全科医生的期望收入,还可以比较全科医生与其他临床医学专业医生的收入水平、与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
4 支付方式的比较
目前,对医学服务提供者的付费方式,大致包括按服务项目付费(fee for service,FFS)、按病种付费(pay per case)、按人头付费(capitation)、总额预算(global budget)等几种主要类型。(1)FFS是一种按服务活动的后付制,即按照诊疗次数和服务内容来支付,是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门诊服务的主要支付方式。(2)按病种付费是一种按服务活动的预付制,即将患者按照病种和费用相似性原则分到诊断相关组,在服务提供前预先支付费用,是目前很多国家对住院医疗服务的主要支付方式。(3)按人头付费是一种总额预付制,即按照既定服务范围内与医生签约的居民数量支付给医生费用,部分国家将该种付费方式应用于对全科医学服务的支付。(4)总额预算也是一种总额预付制,即对既定的活动按照实际服务量来支付费用,在一些国家用于对医院服务的支付[7]。
因此,对全科医学服务的支付方式主要包括两类,即FFS(如澳大利亚)和按人头付费(如英国)。FFS是最传统的对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式,特点是刺激医生多提供医学服务,从而提高收入。按人头付费有控制医疗卫生费用的效果,但也可能导致医生较少地提供服务,甚至可能低于必要的服务。实际上,多数国家对全科医学服务的支付方式并非是单一的,而是有各种变种和组合。可以在现行主要的支付上叠加(add on)一些特定的激励,如英国在实行按人头付费的同时加上按绩效的激励(fee for performance);或者采用混合支付(blending payment),如在实行FFS的同时对几种慢性病管理实行按人头付费,从而达到改善服务质量和控制费用的双重目的;再或者按社区人口数量支付费用,从而达到从宏观上保障服务质量和费用控制的目的。
综合而言,多种支付方式的“七巧板式”组合可能是更合适的方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单一支付方法的缺点,兼顾人群的全体(公平和可及)和特殊(弱势人群)部分,兼顾服务质量和费用控制,兼顾医生利益和社区居民利益。当然,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式也与传统沿袭方式和社区接受等因素有关。而且,支付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动态调整,寻求支付叠加或混合策略的平衡点。
中国的全科医学服务支付方式应如何组合?这正是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欢迎有识之士对此做出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同时,《中国全科医学》也会关注到支付系统的管理和环节问题。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是医疗保险资金〔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或Medicare〕直接支付(无论是预付还是后付)给全科医生的,而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是通过主办医院进行二次分配的,同时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因此直接分配与二次分配的激励作用显然是不同的。
5 收入激励的局限性
如果追求的是收入,那么全科医学并非医生最“聪明”的选择,甚至有些医学领域之外的职业也较全科医生的收入来得更高更快。医学生在选择自身未来的职业方向、医生在决定坚持自身工作岗位的时候,考虑的因素的确包括收入,但绝不仅仅是收入。
一项针对德国5所医学院1 299名医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未来想要选择的职业方向为儿科、内科、妇科、外科、麻醉科、全科的医学生分别占19%、12%、10%、9%、8%、7%;将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和职业因素两类,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个人抱负、未来发展前景,工作-生活平衡,职业因素包括工作的多样性、以患者为中心、在工作中实现抱负、职业形象;与其他专业学术相比,选择全科作为未来职业方向的医学生更关注个人抱负和工作-生活平衡,认为以患者为中心是最重要的吸引力,而自身未来发展前景并不十分重要[8]。该研究结果提示,希望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医学生往往并不擅长在复杂和结构化的医院里工作,其更希望有施展自身才能的一片天地;既要工作,也要生活,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前辈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榜样;他们喜欢与人打交道,喜欢平等地与他人交往和互动,对别人更加充满爱心,也善于使用同理心。
中国也有类似的研究,宋小燕等[9]对51名临床医学5年级学生的医学二级学科选择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发现最主要的考量因素是个人兴趣爱好,其次是实习轮转、课堂学习、公众/家庭影响、教师影响、就业压力。其中,就业压力可能与收入有关系,但其他因素却是收入之外的,研究者认为当前医学生的职业方向选择“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利性”。李伟明等[10]对300名全科转岗培训学员的意愿进行调查,超过70%的全科转岗培训学员不愿意注册为全科医生,主要原因是担心自身达不到注册条件、对全科职业发展缺乏信心、政策落实不到位、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等。显然,对于“曾经沧海”的转岗医生而言,要考虑到工资和工作条件,也要顾虑到自身的岗位胜任力、全科职业的发展前景、政策的落实。
对全科医生的激励,也在于医生自身对职业的认同以及系统和社会对全科医学的认同。“我要成为一名专科医生,或仅是一名全科医生?”(Am I going to be a specialist?Or just a GP?)这个问题是很多医学生和年轻医生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问题中的“仅是”反映出了职业认同问题。当向别人介绍“我是一名全科医生”的时候,别人也会反问“你不想做一名专科吗?”这个反问反映了社会甚至医学领域对全科医学的误解。社会对全科医学的认识和认同,也明显地影响了医生对全科职业的选择和坚持。有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认为“我也知道预防很重要,但在居民心目中,家庭医生都算不上真正的医生”[9]。
全科医生的自我职业认同在于认为全科医学本身就是医学专科,很多全科医生在此基础上发展自身的扩展技能。全科医学的专,在于在第一接触中应对早期未分化疾病的各种表现,采取主动或机会性的预防措施,通过连续性的服务对慢性病进行诊治、对复杂多病共存状况进行管理,有智慧地和有效地使用医疗服务资源,对医疗服务团队、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协调。这些都是其他医学专科无法替代的全科独特性[11]。更为重要的是,全科医学服务能够给居民带来更好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是全科医生认识到的自尊和自我完善。
当然,系统也应该支持医学生和全科医生建立和巩固职业认同,从医学教育早期潜移默化的社会化过程,到对全科医生职称评定的政策。职业认同不等于收入高和职称高,关键在于全科医生自身、医学领域内及广泛社区对全科医学服务的认识与认可。其中,行业组织的倡导必不可少,RACGP的倡导是:“我不仅是个全科医生,我是你生活的专家”(I am not just a GP,I am your specialist in life)。当然,做出这种对社区居民的宣称,还需要打铁者的自身硬。
欣喜的是,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在关注和探讨全科医学的激励问题,涉及对全科教育的激励和对全科服务的激励。《中国全科医学》期待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反思。进一步的工作需要通过政策措施和职业发展,探索新的教育和管理方法,让更多的医生喜欢成为全科医生,让更多的居民认可全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