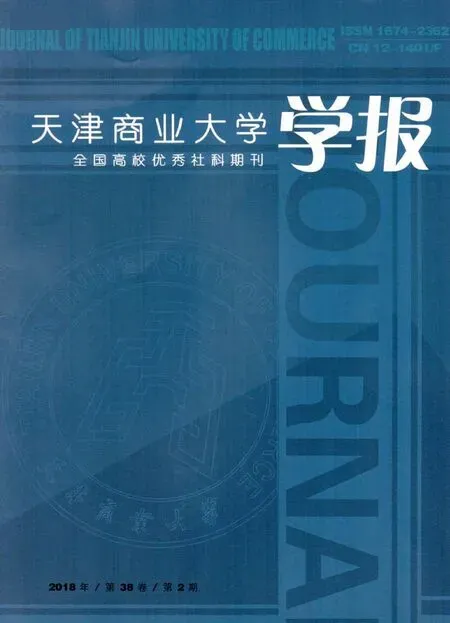独立担保欺诈例外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王 涵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350)
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强,国际间经济贸易的不断增多,传统的从属性担保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需求,独立担保(independent guarantee)①应运而生。独立担保克服了传统担保方式从属性的固有缺陷,由于其独立于基础合同,担保人不能以基础合同产生的原因进行抗辩,在受益人提出索款请求或提示符合独立担保合同要求的单据或文件时,担保人承担无条件的绝对的付款义务。独立担保的这种与基础交易分离的独立性特点加之单据化的业务处理模式,使其在富有效率的同时,却难以兼顾安全性的价值,极易产生受益人欺诈索赔的风险。因此,各国纷纷确立了独立担保欺诈例外原则,以弥补独立担保的固有缺陷,即在受益人欺诈索款时,担保人有权进行拒付,如果申请人认为受益人的索款存在欺诈,其可以向法院寻求禁令救济,止付担保合同项下的款项,避免遭受损失。
欺诈例外原则作为独立担保独立性的限制,能够通过担保人拒付或者申请人请求法院颁发临时禁令对受益人欺诈索款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该原则也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过分限制独立担保的独立性会严重损害独立担保便捷高效地提供可靠担保的功能。因此如何能够更好地适用欺诈例外原则,在维护独立担保独立性价值的同时兼顾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即将债权保障与欺诈防范有机结合,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
本文主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各国不同的司法实践,同时结合《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的统一规定,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为落脚点,研究有关独立担保欺诈例外原则司法适用的三个核心问题,即法院对欺诈情形的认定问题、法院对基础交易的审查限度问题、法院适用欺诈例外原则的证据要求问题。三个问题联系紧密,环环相扣,共同致力于完善我国有关独立担保欺诈例外原则的司法适用的相关规定,保障我国独立担保业务的良性发展。
1 法院对欺诈情形的认定
对欺诈例外原则进行司法适用的前提便是法院必须明晰这一原则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即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受益人的索款行为可以称之为欺诈。欺诈情形的认定可以决定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而决定该原则对独立担保独立性的限制程度。
1.1 与欺诈情形认定的有关问题
1.1.1 受益人的主观状态对欺诈认定的影响
欺诈的成立是否需要受益人出于欺诈索款的恶意,或者说受益人如果是善意的,但在客观行为上已经构成欺诈,法院是否应当认定欺诈。针对这一问题,各国有不同的认识。荷兰的法院认为受益人应当具有主观上欺诈的或恣意的恶意,且这种恶意以诚信的一般人为标准[1]。英国法院十分重视对受益人主观欺诈恶意的证实,如果申请人不能证实受益人的主观恶意,即使证实受益人的付款请求确无根据,法院也不能认定受益人存在欺诈的事实而颁发禁令[2]。而根据法国最高法院的观点,在认定受益人是否构成欺诈索款时却不需要考虑受益人的主观状态,仅仅把受益人实行的客观行为作为欺诈成立的标准[3]。同样美国的多数法院并不把认定受益人是否欺诈的重心放在受益人的主观因素上,而是考量受益人的具体行为[2]。此外,《公约》也秉承着客观主义的界定标准,相较于欺诈者的主观状态或者欺诈者的身份,《公约》更关注于欺诈者的客观行为[4]。
笔者认为,在认定受益人是否构成欺诈时应以受益人的客观行为为标准,受益人的主观状态不宜作为认定欺诈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原因在于,其一,受益人的主观状态本身很难证明,这无疑加重了申请人的举证负担。其二,受益人的主观状态不同并不会对其客观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造成实质性影响,欺诈例外原则的确立是为了更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受益人实施欺诈的结果使得独立担保制度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造成申请人利益的损失。受益人的善意并不能扭转这种危害的发生,本质上还是对独立担保功能的严重损害。其三,受益人在向担保人进行索款时本身便负有按照担保合同的要求提交相应正确单据的义务,仅仅因为其不知情银行便要依据不实的单据付款这显然是荒谬的。
1.1.2 受益人违约或不当行为对欺诈认定的影响
当主债务人违约,即主债务人未能按照与受益人基础交易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时,受益人可以向担保人提出索款要求,请求担保人支付独立担保项下的款项。但是受益人的这种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主债务人有证据证明其不履行义务是由于受益人违约或其他不当行为导致的,法院即可以认定受益人的索款存在欺诈从而阻止担保人的付款[5]。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主债务人的合同义务的履行以受益人合同义务的履行为前提的情况下,例如在加工合同中,如果受益人未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债务人便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
在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Rockwell International Systems股份有限公司案中,受益人基于主债务人违约向担保人请求支付独立担保项下的款项,而法院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主债务人的不适当履行是由于受益人的不当行为所致,因而认定受益人的索赔存在欺诈,“法庭不允许受益人造成了错误还能从错误中获益”。此外荷兰法院认为如果受益人基于申请人在基础交易合同中违约进行索款,但是申请人的违约并不是由其自身原因导致的,这时受益人的索款行为便是欺诈性的[6]。《公约》中所列举的受益人付款请求没有可信依据的情形中也包括受益人故意不当地阻止申请人基础义务的履行这种情况。但这并不代表一旦受益人在基础合同义务的履行中存在违约或不当行为就一定会成立欺诈性索款,如果受益人的违约行为与申请人义务的履行无关,申请人便不能以此为理由申请法院止付。如果由于受益人的违约或不当行为导致了申请人无法完全履行其基础合同中的义务,这时的受益人索款才能被认定为欺诈性索款[7]。
1.2 我国欺诈情形规定的完善
在总结各国司法实践和借鉴《公约》规定的基础上,我国“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的第12条明确规定了适用欺诈例外原则的具体情形②,以指导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但笔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该规定仍有一定的完善空间。
应坚持欺诈的客观行为判断标准。法院在认定受益人是否构成欺诈时应以受益人实施的客观行为为准,受益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欺诈行为的成立。我国的规定中采取了“受益人明知没有付款请求权”的叙述,即要求受益人主观上必须是恶意的。这便给法官在司法适用中留下了难题,如果受益人是善意的,或者申请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受益人的主观状态,但受益人的客观行为已经构成欺诈,这时法院应不应该止付?笔者认为在处理独立保函欺诈案件中应当以受益人的客观行为为准,受益人的善意与否并不影响欺诈行为的成立。这是因为受益人的主观状态一般很难证明,否则将大大增加申请人的举证难度,影响止付令及时止损的功能。其次,如果仅仅因为受益人的主观善意而忽略了客观上的欺诈行为造成的实质结果将会严重损害独立担保的公平性。
应严格区分受益人违约对欺诈认定的影响。我国“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第14条规定“止付申请人以受益人在基础交易中违约为由请求止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并没有将受益人违约是造成申请人违约的原因这一情形明确排除。这样就会使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困惑,如果受益人违约与申请人履行合同义务无关,法院不颁发止付令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由于受益人违约或其不当行为造成申请人无法完全履行基础合同义务的情况,受益人的索款行为显然是不正当的,法院如果依旧不颁发止付令将会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将“申请人违约是由于受益人违约或不当行为所致”这一情形列入“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第12条的与基础交易有关的情形之中,与第14条的规定严格区分,给予法院在处理受益人违约情况时以明确的指引,增强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
2 法院对基础交易的审查限度
独立担保具有独立于基础合同的本质特征,因此法院原则上不能对基础合同进行干涉。但是,欺诈例外原则作为独立担保独立性的例外,可以干预担保人无条件的付款义务,在申请人提出受益人存在欺诈性索款行为时,法院无可避免地要审查基础交易合同以判定受益人的索款是否正当,进而决定担保人是否应当支付独立保函项下的款项。各国普遍承认法院对基础交易审查的必要性,但对审查限度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
2.1 “必要的有限审查”与“全面审查”
大多数国家坚持在解决独立担保欺诈纠纷时只对基础交易合同进行“必要的有限审查”。所谓“必要的有限审查”是指限制法院对基础交易合同的介入程度,法院只能就基础合同中与受益人索赔声明相关的部分进行审查,不能对与索赔声明无关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审查和认定。英国本着严格维护独立担保的独立性特征的目的,不允许对基础交易合同做过宽过深的调查[8]。此外,法国、荷兰、德国的法院均不允许在处理独立担保欺诈案件时对基础合同做深入的调查[1]。而美国并没有限制法院对基础交易的审查限度,其主张可以对基础交易做深入全面的调查,以查明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是否对整个基础交易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甚至可以通过推迟审判进行进一步调查[2]。
2.2 我国应坚持“必要有限审查”限制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最高院征求意见稿”)第27条中明确指出法院对基础法律关系只能进行必要的有限审查。但是,我国出台的“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中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或者处理止付申请,可以就当事人主张的本规定第12条的具体情形,审查认定基础交易的相关事实”。该条明确了我国法院在处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时可以对基础交易合同进行审查,但是并没有限定介入的程度。笔者认为,在法院处理独立担保欺诈纠纷案件时坚持对基础交易合同“必要的有限审查”是极其必要的。一是维护独立担保独立性的必然要求。独立担保的独立性要求担保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只遵循担保合同的约定,不受申请人与受益人的基础交易合同的影响,因此法院原则上只能就担保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不能审查基础交易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但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必须审查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确定受益人是否拥有向担保人索款的权利,从而决定是否应当认定受益人存在欺诈行为。但在独立担保独立性的限制下,法院要限制对基础交易合同的干预程度,只能就涉及受益人索赔声明部分的基础交易关系进行审查,不能涉及对基础合同其他权利义务关系的判定[9]。二是对审理基础合同争议的法院的管辖权和当事人仲裁协议的尊重。法院在处理独立担保欺诈纠纷时审理的法律关系是独立担保法律关系,其与基础合同法律关系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使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必须涉及到基础合同的审查,也应尊重日后审理基础合同法律争议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法定管辖权。这就要求法院在审理独立担保欺诈案件时对基础合同的审查不能影响日后的审理和仲裁,例如不能进行鉴定、现场勘查或者对于无关索赔声明部分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认定。
基于此,笔者建议我国应当明确对基础交易合同“必要的有限审查”的审查方式,约束法院对基础交易合同的干预程度,维护独立担保的独立性。
3 法院适用欺诈例外原则的证据要求
3.1 法院颁布临时禁令的证据要求
法院作出颁布临时禁令的决定止付担保款项的时候,应该对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进行衡量。但是究竟申请人的证据在何种程度上证明受益人欺诈行为的存在法院才能颁布禁令,国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定。
3.1.1 “明显清楚”加之“立即可得”的证据要求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欺诈的证据必须是明显的、毫无异议的、有根据的且可以立即获得[10]。同样,法国的法院在欺诈的证据方面要求欺诈必须被毫无疑问地证实,或必须是明白的、清楚的、明显的且证据必须被立即提出[3]。英国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将独立担保与跟单信用证相同对待,极不愿意去干预银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付款义务,坚定地维护独立担保的独立性,因此对独立担保欺诈的证明标准要求很高[11]。英国有关欺诈证明标准的确立始于著名的Eward Owen一案,Denning勋爵对证据的要求须是清楚的、毫无疑义的且可立即获得的,同时该证据不仅要证明欺诈行为确实存在,还应证明银行对此是知情的。美国也为申请人获得临时禁令救济设置了很高的障碍,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必须能够明白地、确实地证明受益人确无获得相关款项的权利[12]。由此可知,大多数国家对欺诈的证据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法院尽量避免干涉担保人绝对的付款义务,这是维护独立担保独立性的要求,有利于独立担保在商事交往中发挥出强大的债权保障的作用。但这种严格的证据要求也遭到了批判。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认为清楚明显的证据要求会使法院越过中间阶段,直接进入最后的判决[13]。过于严格的证据要求虽然有助于便利国际交易,但是中间禁令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客观上会助长受益人的欺诈行为,使独立担保流于形式。英国的法院也在逐渐反思这种严格狭窄的证据要求的合理性,考虑应用较为灵活的证据标准[14]。如Ackner法官在The United Trading Corporation一案中指出绝对严格的证据要求将会使法院颁布临时禁令极其困难,“欺诈使一切无效”将会沦为空谈。
3.1.2 “高度可能性”加之“立即可得”的证据要求
《公约》同样认为“明显清楚”的证据要求对于申请临时禁令措施的申请人未免太过苛责,因此规定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只需要证明受益人欺诈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high probability)即可,不需要该证据能够明确清楚地证明欺诈行为的存在。同时《公约》明确提出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应是立即可得的强有力证据(immediately available strong evidence)。《公约》的“高度可能性”加之“立即可得”的证据要求较好地处理了维护独立担保独立性价值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高度可能性”标准能够使法院中间禁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避免申请人利益的损失;而“立即可得”的证据要求意在避免法院对独立担保的独立性的过度干涉,即这些证据必须是不需要经过繁琐地调查即可立即获得的。
3.1.3 我国应增加“立即可得”的证据要求
“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中明确我国法院裁定中止支付独立担保项下的款项所需要的证明标准为“高度可能性”标准,即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需达到证明受益人欺诈情形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法院方能止付,此外并没有对证据的其他要求。“最高院征求意见稿”第24条对欺诈的证据要求有两种意见,其一便是“高度可能性”要求,意在采纳《公约》中“high probability”标准,同时也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③。其二是“明显存在”标准,意在采纳如德国荷兰等国的“明显清楚”标准。最终“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采取了《公约》中的证明标准,但是《公约》中对证据须是“立即可得”的要求并没有在规定中得到体现。
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高度可能性”标准是较为合理的,但同时应该对提交的证据做出一定的要求。我国在“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中初步承认了独立担保的国内效力,如果最初便采用诸如英国等国的高标准,独立担保的独立性能够得到充分的维护,但是受益人欺诈行为就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不利于我国独立担保业务的良好发展。“高度可能性”标准与法院禁令这一临时性措施相契合,其不要求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能够毫无疑义地明显地证明欺诈行为的存在,减轻了申请人的证明负担,能够及时地避免申请人利益的损失。但同时这一标准难免会产生侵害独立担保独立性的诟病,法院有过于干涉担保人绝对的付款义务之嫌,因此在高度可能性标准下对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做出一定的要求是必要的,如《公约》中规定的证据需是“立即可得”的,这样可以避免对基础合同过多的介入,进而达到维护独立担保独立性的目的。
3.2 法院作出终局判决的证据要求
3.2.1 各国法院的证据标准不相称
独立担保欺诈纠纷进入法院判决阶段时是依据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在这一阶段各国法院的证据要求是依据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定的。如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要求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达到“盖然性优势”标准,这种“盖然性”应理解为证据所证事实的存在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15]。美国针对有关欺诈的民事案件和某些涉及刑事的民事案件,提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标准,是一种较普通民事案件“盖然性优势”标准更为严格的要求,原因在于这些案件情节较为严重,需要更高的证明程度相适应。虽然美国法院对于民事欺诈案件提高了证明标准,但是该标准适用于特殊的独立担保欺诈案件的终局判决中依旧存在着标准不相称的问题。这种不相称表现在法院颁布临时禁令所需的证明标准与终局判决的证明标准的不相称。诸如英国、美国等国的法院对独立担保申请人申请临时禁令的证据要求是“清楚明显”的,严格的要求旨在限制法院对于独立担保独立性的干预,使得独立担保能够维持其强大的债权保障功能,由于一般申请人的证据很难达到这种要求,法院很少颁发临时禁令止付。而在终局判决时的证明标准为“清晰而有说服力”甚至英国降低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这就会导致终局判决的证据证明形同虚设,中间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院最后的判决。因此标准不相称问题不仅会导致临时禁令及时止损的作用无法发挥,造成申请人利益的损失,丧失制度设计的初衷,而且会直接影响法院的终局判决,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3.2.2 我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仍需细化
“最高院独立保函解释”第20条中规定了我国法院在审理独立担保欺诈纠纷案件作出终局判决时所需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④。“排除合理怀疑”一般理解为对于认定的事实,法官已经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事实上已达到确信的程度[16]。这一标准的应用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的规定⑤。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要求比高度可能性证据要求更为严格,根据“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法院颁发止付令需要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达到证明受益人欺诈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这是由于止付令只是法院的临时禁令,意在中止担保人支付独立担保项下的款项,给予申请人以临时救济,随着程序的进一步深入,止付令可能被撤销。而申请人若想获得法院的最终救济理应需要更高的证据要求,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应使法官排除合理怀疑地认为受益人存在欺诈,这时法院才能判决受益人欺诈成立,从而终止担保人支付被请求的款项。这体现出了我国对待独立担保欺诈例外原则的审慎态度,有利于维护独立保函的独立性,尊重担保人无条件的付款义务。
虽然在理论分析层面,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是较为合理的,但在实践层面,由于该标准依赖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加之其与临时禁令的“高度可能性”要求之间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可能会造成司法裁决的不统一。此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也要衡量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能僵硬适用[17]。因此法官在实际应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可能会面临不小的挑战。笔者建议应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解释,约束法官适用该标准的主观恣意性,如法官必须就其证据判断给出相应的理由,对事实判断给出有效的说理,综合全案的证据和事实揭示其心证形成的基础,保证裁判的质量。
4 结语
独立担保欺诈例外原则作为独立担保独立性的例外来对抗担保人绝对的无条件的付款义务。但在欺诈例外原则的司法适用过程中,维护交易公平的同时必须重视独立担保的独立性价值,否则会产生矫枉过正的后果。我国“最高院独立保函规定”首次详细规定了欺诈例外原则的司法适用的有关规则,旨在引领欺诈例外原则的统一适用。笔者结合《公约》规定以及有关国家成熟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为该规定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以下建议:在欺诈情形认定上宜采取客观行为标准,同时应当区分受益人违约对欺诈认定的影响,严格欺诈情形的认定;在法院对基础合同的审查限度上应该表现出对独立担保的独立性价值的充分尊重,建议对基础合同审查进行“必要的有限审查”限制,更好地处理独立担保合同与基础合同之间的关系。在法院适用欺诈例外原则的证据要求方面,颁发临时禁令的证据要求建议增加“立即可得”要求,和“高度可能性”要求并用,以维护独立保函独立性特征。法院作出终局判决认定欺诈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应当进一步细化,与高度可能性标准的适用相衔接,保证法院裁判案件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注 释:
① 本文指称的“独立担保”是一个概括的概念,用于与商业信用证相区别,主要包括独立保函(demand guarantee)、备用信用证(standby letter of credit)以及具有独立担保性质的其他法律文书。由于各国独立担保制度的实践各异,名称也各不相同。独立保函广泛使用于欧洲国家,而美国早期由于受到银行监管的限制,产生了备用信用证制度以替代银行独立保函并逐渐延续下来。二者虽名称不同,但在法律性质上是相同的,都具有独立担保的独立抽象性、单据性等共同特征。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独立保函欺诈:(1)受益人与保函申请人或其他人串通,虚构基础交易的;(2)受益人提交的第三方单据系伪造或内容虚假的;(3)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决定基础交易债务人没有付款或赔偿责任的;(4)受益人确认基础交易债务已得到完全履行或者确认独立保函载明的到期事件并未发生的;(5)受益人明知其没有付款请求权仍滥用该权利的其他情形。”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人民法院经审理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地认定构成独立保函欺诈,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情形的,应当判决开立人终止支付独立保函项下被请求的款项。”
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参考文献:
[1]周辉斌.国际银行保函欺诈产生的原因及其法律认定[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2):75-82.
[2]GAO X,BUCKLEY R P.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andard of fraud required under the fraud rule in letter of credit law[J].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International Law,2003(13):293-336.
[3]赵蓓.独立担保中“欺诈例外”规则比较研究[J].中国外资,2012(12):220-222.
[4]KELLY-LOUW M.International measures to prohibit fraudulent calls on demand guarantees and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J].George Mas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2010(1):74-113.
[5]李国安.国际融资担保的创新与借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7.
[6]FEDOTOV A.Abuse,unconscionability and demand guarantees:new exception to independence[J].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Law Review,2008(11):49-82.
[7]翟红,杨泽宇.独立担保欺诈例外的分析与认定[J].人民司法,2015(13):63-68.
[8]郭德香.国际银行独立担保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91-192.
[9]翟红,余希.独立保函纠纷审判难点研究[J].人民司法,2012(3):30-33.
[10]NIELSEN J,NIELSEN N.The German bank guarantee:lesson to be drawn for China[J].George Mas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2014(5):171-212.
[11]陆璐.独立担保欺诈例外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J].法学论坛,2016(2):31-37.
[12]BARRU D J.How to guarantee contractor performance on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s:comparing surety bonds with bank guarantees and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J].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2005(37):51-108.
[13]李燕.独立担保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77-178.
[14]BUCKLEY R P,GAO X.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aud rule in letter of credit law:the journey so far and the road ahead[J].University of Pennsyl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2(23):663-712.
[15]吴泽勇.“正义标尺”还是“乌托邦”——比较视野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J].法学家,2014(3):145-162.
[16]肖沛权.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司法适用[J].法律适用,2015(9):104-108.
[17]霍海红.提高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J].中国法学,2016(2):25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