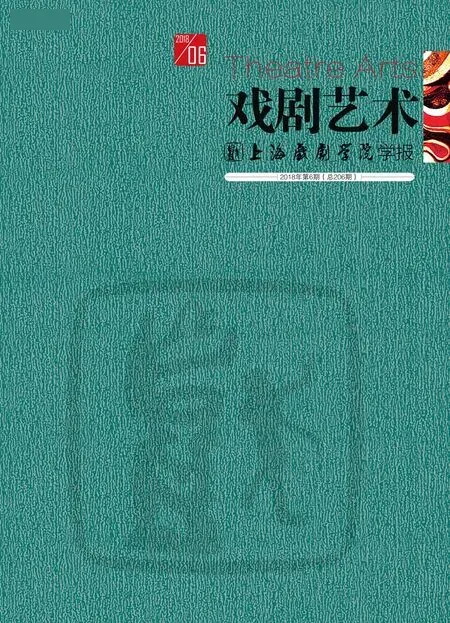陈明正戏剧表导演艺术思想的三个向度
■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陈明正教授从事戏剧表演教学和导演工作六十余年,培养了大批表导演艺术人才,执导了七十余台中外戏剧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被戏剧界誉为“南方话剧的一面旗帜”[注]参见《舞台形象创造论》《表演教学与训练研究》《以镜照镜》《五十年守望——迟到的〈钦差大臣〉》等陈明正撰写或主编书籍的作者简介或主编简介。另参见戴平著《海派戏剧的一面旗帜——论陈明正的导演艺术》,《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在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的同时,他深入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现实主义表演理论体系,并辩证地吸收了其他多种表导演流派的精髓,形成了自己深厚的表导演艺术思想与独特的表演教学方法。2016年,陈明正教授近七十万字的专著《舞台形象创造论》分上下两册出版,这是他在耄耋之年为戏剧表演艺术的理论和学科建设做出的又一杰出贡献。他高超的表导演艺术和学术水平,他正直、真挚、大气的人格与高尚的师德深深感染着戏剧界同人。
一、学术深度:对斯坦尼体系的深刻理解与“再度体系化”
陈明正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表演教学与导演实践,以现实主义的“表演天性规律”,也就是“人的有机行动的自然规律”为重心,全面、深刻地探索与“化解”了斯坦尼体系,使之 “再度体系化”。这个“再度的体系”以“舞台有机天性”为核心,以解决“演员矛盾”为关键,以元素训练、单人(至双人、多人)小品训练、观察模拟人物与动物训练等基础教学为经,以剧本角色分析、片段教学、形体行动分析法等人物形象创造为纬,结合大量实例分析,融入创新思维,是现实主义表演艺术体系在新时代的深入发展。
斯坦尼的著作中对表演元素的现象与本质、表演元素之间的关系有着复杂(甚至“庞杂”)的论述。陈明正教授剥茧抽丝,全面梳理与深刻理解了这些论述,并根据数十年的表演教学实践,按照“行动的任务”“规定情境”“注意”“动作性想象”“有机交流”“语言动作”“性格化和再体现”等七个部分论述“舞台有机天性”的养成规律。他论述的“行动的任务”以角色的任务、目的为着眼点,通过对“单位任务”“贯串动作”与“最高任务”的阐释,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地揭示内部任务与外部动作唇齿相依的关系,强调舞台行动在“最高任务”召唤下的升华,使看似主观的“任务”和“目的”有了外部动作的客观性。对于“规定情境”,他认为,“广义地说,所有和角色有关的事务,都是角色所处的规定情境”[注]陈明正:《舞台形象创造论》(上),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因此“掌握规定情境技巧要从元素训练开始”[注]同上,第58页。。另外,“规定情境”的具体性和流动性,及其由外部条件开始对角色的内部心理的刺激作用也是他探讨的重点。他强调舞台注意力训练,从心理学角度把注意力和感受力、想象力联系起来。他通过大量的无实物练习训练演员的想象力,用无实物练习把想象力与真实感、信念感、目的(任务)、注意力、感受力等其他元素都贯串起来,把看似主观的想象力训练结合到“肢体空间的控制力”“严格的动作顺序和逻辑”“行动中的思考判断”“舞台节奏和自我感觉的掌控”等外部行动中。[注]同上,第106-109页。他强调“有机交流”在戏剧表演元素中的核心地位,认为“舞台有机交流时所有元素都要参与”[注]同上,第124页。,舞台上不间断的交流互动以及与对手的“交锋”是舞台有机性的关键。由于“舞台已知性是舞台有机交流的主要障碍”[注]陈明正:《舞台形象创造论》(上),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他大胆采用即兴交流练习,激发学生即兴的适应与交流能力。他强调“语言的行动性”“词的视像性”“语言的潜台词功能”和“语言行动中的第二计划”,使文学的语言转化为舞台行动的语言,又使舞台行动的语言折射出诗情、画意与文学性。他把表现力纳入体验派表演训练中,挖掘斯坦尼体系中“性格化”和“再体现”的精神要义,并倡导斯坦尼后期的“形体行动分析法”,以内外结合地体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他所倡导的“有机的舞台行动”,正是上述所有元素的彼此依存、交融和贯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大胆、即兴、有逻辑的行动往往是激发有机天性的起点与支点。
解决两对“演员矛盾”(“生活真实和舞台真实的矛盾”“演员和角色的矛盾”)是陈明正教授现实主义表演教学的重点。他把这两对矛盾与“舞台有机天性”规律、“从自我出发”“表演创造的下意识”等学说联系起来。进一步地,他探究了表演艺术“三位一体”(即创作者、创作材料、创作工具彼此无法分开)的创造前提,由此辩证地分析“从自我出发”学说对于演员和角色这对矛盾统一体的意义。针对上述“两对演员矛盾”,他又提出了表演创造下意识的化解作用,从心理学、合乎逻辑的有机行动、舞台交流等角度探讨了“下意识创造”的现象与规律。
在基础教学中,除舞台注意、舞台想象、舞台交流等元素训练外,陈明正教授还特别强调了单人(也包括双人、多人)小品训练的功用。他认为小品阶段是训练演员组织舞台行动的重要阶段,针对某些忽视小品训练的现象,他提出,“各种分割的元素训练不能代替有任务、有规定情境的行动小品训练”[注]陈明正:《舞台形象创造论》(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页。,“循序渐进,不断提高,让学生懂得抓行动逻辑的原理,不要随意地跳过任何一个环节”[注]同上,第379页。。他鼓励演员“到现实生活中去捕捉形象”[注]同上,第394页。,继而进行观察模拟人物与动物的训练,强调此类练习对人物的“职业、性格、生理、习俗”的捕捉,矫正形式主义、“走过场”式、猎奇式观察模拟训练。他反对“形似”和“神似”的割裂,而是以“有效地提高演员内外部性格化能力”为教学任务。[注]同上,第426页。他的小品训练和观察模拟训练不以“编小品”“模仿与模拟”为根本目的,而是借用这些训练提高演员的组织舞台有机行动和性格化的能力,挖掘此类练习对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性作用。
到了剧本人物形象创造训练阶段,陈明正教授强调元素训练、基础训练与人物形象创造训练的衔接与融为一体。他指出,历时两年的片段教学,在表演本科教学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中心环节地位。片段教学需要演员把“元素、技巧、技能”全部“带进创作角色当中去”,因此,“片段教学”需要的不是“片段的教学观”,而是“教学整体观”。对于片段的挑选问题,他强调选用“人物性格鲜明、行动积极、思想脉络清楚、内涵完美、人文品格高的片段”[注]同上,第439页。,尤其强调选用中外优秀剧作中的片段,让演员在“有深度、有挖头、值得精耕细作”[注]同上,第440页。的剧作片段表演中提升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素养。他认为片段教学要“因材施教,进行各类角色的尝试”[注]陈明正:《舞台形象创造论》(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441页。,以培养演员全面的创造角色的能力。而在自选片段阶段,他又鼓励学生大胆创作,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精神。他要求演员重视对剧本“客观”与“主动”两方面的分析与挖掘。“客观”的分析与挖掘是指静下心来读书、查资料,以理解与把握时代背景、规定情境、事件前因后果、人物关系等剧本中提供的一切;“主动”的分析与挖掘是指主动划分“单位任务”,“捋顺情节和事件、人物矛盾的发展线索”,“不刻板,不机械,不烦琐”,发挥演员的主观能动性。[注]同上,第457-458页。在从剧本到剧本人物形象创造的过程中,他认为斯坦尼的“形体行动分析法”“能消除‘心灵’与‘形体’的分离状态”[注]同上,第462页。,符合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中“人的心理形体过程是统一的”[注]同上,第463页。之思想。他要求做“形体行动分析”练习时从时代、地理环境,以及人物职业、性格、生理等特征入手,通过“进一步分析人物关系和规定情境(包括人物前史)”[注]同上。,“进入人物行动的逻辑、人物性格的创造”[注]同上,第476页。。为防止进入剧本排练时因“过度设计”而走上“演形象”“演设计”“演结果”“演情绪”的僵化道路,他主张在片段教学和剧本大戏排练时一以贯之地使用“形体行动分析法”。另外,他还注重内部心理活动与外部语言动作的相辅相成,无论是元素训练、基础训练还是人物形象创造训练,他都把“人物的内心欲求、内心独白、内心视像、潜台词”与“角色的语言活起来的基本功”联系在一起。[注]同上,第509页。
因此,陈明正教授对斯坦尼体系和表演训练体系的论述,是一个各表演元素相互关联、各基础训练和创造人物形象训练相互促进、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行动的总谱”,是一套推陈出新的、网络状的艺术思想和教学体系,并且带有鲜明的启发式、诱导式、交流互动式教学特点,为演出大戏时“立起来看剧本”[注]戴平:《海派戏剧的一面旗帜——论陈明正的导演艺术》,《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打下相互交流、相互启迪的基础。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他既有所坚持,又有所变通,最终以“有机性”“实践性”为检验表导演艺术与教学的标准,充分发扬了实事求是、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
二、学派广度:立足现实主义的辩证吸收与兼收并蓄
陈明正教授的表导演艺术“立足现实主义,多种流派兼容并包”[注]参见陈明正:《导演艺术随想》,待发表。。术有专攻和兼容并包在他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辩证的发挥。这使得他培养出既功底扎实、技术全面又触类旁通、独具特色的演员,也使得他的导演作品既大气厚重又风格多样。
其实,他对于其探索的重点——斯坦尼体系及其支脉就采取了有重点、讲综合、持特色、不僵化的辩证性策略。除斯坦尼本人的著作外,由于瓦赫坦戈夫与丹钦科等大师的著作代表了斯坦尼体系后续发展的不同方向,因此这些著作也是陈明正教授悉心研读的对象。另外,在1950年代苏联戏剧专家的指导下,他还从实践中汲取当时代表斯坦尼体系不同侧重点的艺术家的思想精华。“斯氏嫡传代表、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列斯里”,“瓦赫坦戈夫学派的学人”“强调斯氏体系和梅氏(梅耶荷德)体系结合”的“史楚金戏剧学校校长库里涅夫”,“斯氏体系后期实践‘形体动作方法学派’的专家”“列宁格勒戏剧学院功勋艺术家列普科夫斯卡娅”,这三位专家的理论与实践教学都对陈明正教授早年学习斯坦尼体系发挥过重要作用。[注]张生泉:《跋——论陈明正的戏剧教育思想》,陈明正:《舞台形象创造论》(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706页。上戏老校长熊佛西先生在“戏剧编导演和舞美”等方面“研究实验的精神”[注]同上,第704页。,上戏前教务长朱端钧先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民族化表导演思想方法,上戏老专家胡导教授在“性格化”“第二计划”“内心视像”等方面的研究,都对陈明正教授的斯坦尼体系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除向中外导师学习外,他还向成功塑造各种人物形象的演员们学习。他研究严翔塑造人物时“复合型情感色彩”[注]陈明正:《舞台形象创造论》(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666页。的运用;他研究胡庆树既“善于构想自己的角色”,又“能进入创作的自由王国”[注]同上,第676页。的奥秘;他研究娄际成“‘内外部性格化’地‘寻找人物的最佳体现’”[注]同上,第679页。的表演艺术。他主编的《以镜照镜》第一辑至第三辑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了多位“老戏骨”的表演艺术,是研究斯坦尼体系之下不同风格与特色表演艺术的重要资料。对于斯坦尼体系在美国继续发展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支脉或学派,比如“方法派”表演、麦克尔·契诃夫的理论与实践等,陈明正教授也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斯坦尼体系像一张埋在地底的巨大的网(有些地方还有待细化),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往下深挖,往往将先挖到的那部分作为其细化后的学派的重点,而如果顺藤摸瓜,就可以发现相互之间几乎都是走得通的。因此,陈明正教授眼中的斯坦尼体系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成就了现实主义体验派表演艺术的复合型体系。
陈明正教授发掘了表现派理论家对于表演艺术的真正贡献——表演“控制”和表演基本功,同时又纠正了其中有失偏颇的地方。“演员要有控制地表演”,“‘投入’‘体验’‘动情’和‘控制’不是对立的”。[注]同上,第510页。他从哥格兰那里挖掘到的宝藏是演员表演“双重性”、 剧本与作者意图的深挖、模仿力、完整的构思、可塑性等,进而他由演员表演“双重性”向“矛盾统一性”进发,而与此同时,他又纠正道,演员第二自我“不是‘奴隶’,要理解它,才能掌握它”[注]同上,第599页。,“表现派的症结”是“把感受动情和监督放在可怕的对立境地”[注]同上,第607页。。他赞赏狄德罗的“创造性模仿”“用理性照亮自然,达到艺术的真实”等思想,认为狄德罗的“理想范本”学说对演员提出了“超越自我,达到理想”的高要求,认为该学说与斯坦尼的“人物的行动总谱”“贯串动作与最高任务”“角色的远景与演员的远景”等理论有相通之处。[注]同上,第618-619页。同时,他又能辩证地看待狄德罗所谓的“冷静”“理性”,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揭示了狄德罗强调“理性”而自身却多愁善感这一悖论的原因。身为立足斯坦尼体系的现实主义戏剧教育家,陈明正教授没有将表现派理论方法置于比体验派更低等的地位,也没有强行要求二者合而为一,而是强调既站稳“立足点”又因地制宜地奉行“拿来主义”,体验派和表现派“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不需要融成一派,个人保持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创作个性”。[注]陈明正:《舞台形象创造论》(下),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641页。
在导演艺术方面,陈明正教授赋予了“现实主义”以丰富的层次,这是因为他既对斯坦尼体系有深刻的理解,又对斯坦尼体系之外的另两大学派——布莱希特理论和中国戏曲美学有辩证性借鉴。对于演员如何参与布莱希特式的叙事性戏剧表演,陈明正教授认为综合、完整、辩证地认识编导相应的意图与手段是成功的关键。“‘陌生化’‘间离效果’的重任,并不全在演员身上,更多体现在剧作本身。在于导演的处理。”[注]同上,第521页。“陌生化的效果从编剧的‘布局’‘结构’‘对比’中开始,而且导演、布景、化妆、音效、舞蹈都参与陌生化。”[注]同上。他把“间离”的任务更多地交给编导,反对在表演上“故意阻止动情”,反对将“正常的内外统一硬性分裂”。[注]同上,第532页。另一方面,他看到布莱希特式的剧本本身必须具备哲理的深度,而导演要用“具有表现力的导演语汇”进行“有意识的出色的处理”[注]同上,第531页。,要学会使用“寓言性”“象征性”的“点题”处理和外化手段。他本人执导的多部作品,如《小市民的婚礼》《四川好人》《阴谋与爱情》等,或显或隐地融入了布莱希特式的手法。另外,他的导演艺术深受中国戏曲美学影响。他从未将戏曲与斯坦尼体系对立起来,而认为戏曲是“再现基础上的表现”,是“夸张、变形、虚拟化、节奏化、舞蹈化、美化、艺术化的再现”,“是体验与表现、内与外、写实与写意的有机结合”,“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假定性的写意戏剧”。[注]同上,第568页。一方面,他呼吁话剧演员学习戏曲演员“把‘感受’落实在‘形体行动上’”[注]同上,第582页。的“以形传神”“立象尽意”之技艺。另一方面,他纠正了“把戏曲归为表现学派而不是体验学派”的错误倾向,因为“戏剧艺术的‘假定性本质’仍然需要体验”。[注]同上,第587页。他执导的《牡丹亭》《白娘娘》《黑骏马》《芸香》《庄周戏妻》等戏曲与话剧,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戏曲写意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体验与表现、内与外、写实与写意的有机结合”。
除此之外,陈明正教授还以开放的心态吸收现当代多种表演流派的训练方法。他主编的《表演教学与训练研究》,除涉及斯坦尼体系研究与俄罗斯当代表演教学研究外,还涉及多位学者对麦克尔·契诃夫、“方法派”、格洛托夫斯基、铃木忠志和谢克纳之表演训练方法的研究,为相关领域的教师、导演和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
正因为“既站稳立足点又兼容并包”,所以在陈明正教授的表演课上,学生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大大提高了在舞台上的感受能力、适应能力、判断能力、有机交流能力、控制能力、可塑性、创造力和综合能力,学会了相当的组织舞台有机行动的能力,很快就能胜任不同历史背景和流派风格的戏剧演出。也正因为陈明正教授立足现实主义的兼收并蓄,所以他导演的七十余台戏剧作品,囊括了古今中外的“悲喜正闹”,现实主义中交织着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写意性、风格化、风俗化和民族化,生动而有机,深刻而丰富,大气而厚重,极富舞台张力。
三、艺术与人格高度:“最高任务意识”“真善美”与“戏入诗格”
陈明正教授的艺术探索始终伴随着人生的回响和人性的光芒。他认为“戏剧要看到人”,戏剧必须围绕人的命运、人的悲欢、人的行动、人的思想灵魂展开。[注]参见陈明正《导演艺术随想》,待发表。在舞台人物形象创造过程中,“他永远用一颗真挚的心努力发现和赞美生活中的‘真’‘善’‘美’,揭露和抨击生活中的‘假’‘恶’‘丑’”。[注]伊天夫:《通往诗意的现实主义之路——陈明正导演艺术中的“真”“善”“美”》,《戏剧艺术》,2013年第1期。在导演的二度创作过程中,他既不照本宣科,也不过度解读或肢解剧作,而是“依据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标准或鲜明的善恶标准”[注]同上。,深刻揭示戏剧矛盾的社会、历史与心理因素,充实、完善人物的性格特征与舞台行动,并实现人性的升华与诗意的自然流露。套用鲁道夫·斯坦纳的书名《更高的世界以及如何达到它的知识》,陈明正教授的戏剧艺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化解和升华,达到了“更高的世界”——诗一般高远辽阔的境界。
陈明正教授善于“删戏”,也善于“添戏”,善于“隐”,也善于“显”,能精妙地将导演的二度创作与剧作“无缝对接”,并使作品占领艺术与思想高度。这缘于他对剧本主人公的“任务——贯串动作——最高任务”的挖掘,缘于他自觉地在演出中纳入导演的“最高任务意识”。[注]斯坦尼体系中角色的“最高任务”,更多地是指剧本中带有剧作家精神理想的那个角色的“最高任务”。而在有的戏剧中,没有哪个具体的角色肩负“最高任务”(比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此时,导演的“最高任务意识”尤显重要。即使在“没有具体角色的最高任务”的情况下,导演也要保持舞台创造的“最高任务意识”,如此才不负全剧的精神要旨(比如排演《钦差大臣》时导演保持的批判意识甚至“审判”意识)。在这些作品中,“最高任务”不仅是主人公行动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全剧的精神理想之所在,因为导演已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全剧的精神理想、主人公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他使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向上伸展,让主人公的动作逻辑、心理逻辑伴随着对最高任务的追求而发展,让剧中的矛盾斗争在全剧的精神理想的召唤下变得紧张激烈,使得演出在保持统一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变得气势磅礴、极具思想高度。他导演《哈姆雷特》时的“最高任务意识”,就是要展现一个秉持理想主义的高贵王子在黑暗的现实世界里的悲剧,因为他认识到哈姆雷特的最高任务不局限于“复仇”,而是“拯救丹麦、重振乾坤”,由此他阐释了哈姆雷特在“复仇”问题上犹豫不决、错失良机的深层原因:“哈姆雷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一心想重振乾坤的高贵王子。在面对险恶世界、面对那些不择手段的阴谋家时,他想用最‘完善’、最‘公正’、最‘光明磊落’的方式去应对‘阴谋’和‘奸诈’,这造成了他最终的悲剧。”[注]陈明正:《一个追求完美的王子之悲剧——〈哈姆雷特〉的导演解读和舞台处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研究中心编:《戏剧学》第5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陈明正教授为奥斯特洛夫斯基19世纪下半叶的剧作《大雷雨》担任艺术指导,他把剧作家的社会历史使命转化为导演的“最高任务意识”——以最大的力量撕开“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因此,他强化了女主角卡捷琳娜热爱自由、向往光明、追求健康人生的舞台行动线索,重点渲染了新生力量、科学精神对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宗法势力的不满与反抗。他把卡捷琳娜与鲍里斯幽会的情节变成了两位“春之神”在薄雾笼罩的绿色森林里尽情舞蹈与奔跑的场景,把这种纯洁的爱情和《雷雨》中繁漪、周萍间的“扭曲的恋情”区别开来。他“外显”了原剧作结尾处“卡捷琳娜跳河”的间接叙述情节,让浑身是伤的卡捷琳娜跳窗逃走,最后站到舞台中央的平台上,在烟雾迷离的河边岩石处义无反顾地跳下去,挖掘出她“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他让懦弱的卡巴诺夫最终向其专制的母亲爆发出怒吼:“是你毁了她!我恨你!”有了“冲破黑暗、追求自由和光明”的最高任务,主人公的任务和贯串动作逐渐趋向理想的高度。
主人公对最高任务的追求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障碍,面临各种矛盾。陈明正教授导演作品中的戏剧矛盾,有些以解决自然条件、物质条件、落后思想、两难境地等问题为主,如《大桥》《公用厨房》《美国来的妻子》等;有些以主人公的自我思想斗争、自我反思为主,如《黑骏马》;而他更多作品中的戏剧矛盾,则突出主人公对“黑暗势力”的斗争——或进一步说,体现了导演本人对“恶”的痛恨。他从不将黑暗势力轻描淡写地带过,而是使其成为戏剧矛盾的强大的“黑暗的一方”,以更好地展现“抗争的一方”的勇敢与顽强,以更好地展现或期待“公平正义”的来临。怀着导演的批判意识,他又将黑暗势力置入众目睽睽之下,层层深入地揭露、解剖、鞭挞、讽刺它们。在他的执导下,《阴谋与爱情》中宰相受到儿子斐迪南的反击后与秘书密谋陷害露易丝的场景,由剧本中的“宰相大厅”改为舞台阴暗的一角。“华丽的道具被抽掉,台口的一束光把宰相和秘书的影子投射在墙上。这是因为导演想到,‘希特勒及其党羽在失败前也是蜷缩在地下室里密谋的’。”[注]吴靖青:《化解与升华——话剧〈阴谋与爱情〉的导演再创造》,《上海戏剧》,2007年第1期。他在上海师范大学执导曹禺1930年代的剧作《日出》,指出这部戏是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批判”。[注]陈明正:《〈日出〉要日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研究中心编:《戏剧学》第4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页。到了潘月亭和李石清为了各自的利益凶相毕露、相互斗殴时,陈明正教授认为,“这场戏惊心动魄,深刻揭露了那个社会的‘丛林法则’”。[注]同上,第264页。他强调,“不能把这场戏演成闹剧”,“要一层一层地剥,一口一口地咬,不到节骨眼就不要发威,一旦发起威来,就应置对手于死地”。[注]同上。剧作中有纸醉金迷的张乔治对陈白露“说噩梦”的情节,陈明正教授让张乔治在台口惊恐万状地对观众描述噩梦,把“我梦见这一幢楼里全是鬼……这个楼要塌了……可怕……可怕……” 这段话加上音效,“引起大厅的回响和震动”。[注]同上,第265-266页。作为导演,他要让旧世界崩塌,他要像曹禺那样对“这帮荒淫无耻,丢弃了太阳的人们”大喊:“你们的末日到了!”[注]转引自陈明正:《〈日出〉要日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研究中心编:《戏剧学》第4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65-266页。为了突出重点、加快推向高潮,他大胆整合、删改果戈理1830年代剧作《钦差大臣》的第五幕,称第五幕的结局是“魔鬼的末日”。在演出中,就在告状的商人们被抓捕、“市长”做着“将军梦”、其余“官员”一边假惺惺地高呼“将军万岁”一边偷偷地对着观众席嫉妒地下咒时,一封私人信件被具有偷窥癖的“邮政局长”公开,变成了辛辣的揭露信。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画面出现了,在尖利的狂笑声中,一个女巫从人群里出来,嘲弄地、一个接着一个地瞪着“以‘市长’为代表的一群丑类”。[注]陈明正:《〈钦差大臣〉导演手记》,陈明正主编:《五十年守望——迟到的〈钦差大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这群丑类相互指责,“歇斯底里,绝望地呼喊着”,当真正的钦差大臣将要来临时,“他们静场四十秒,都成为了僵尸”,“光与电已经劈开了这个魔鬼的宫殿”。[注]同上,第182-183页。现实主义的反映与揭示功能、布莱希特式的批判与间离效果、表现主义的放大和外显效应,在这些鞭挞黑暗势力的场景中发挥到了极致。
在揭露“假恶丑”的同时,陈明正教授用泼墨堆金的方式为“真善美”注入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色彩,体现了他在“美好的事物被扼杀”后的悲愤与痛惜,也体现了他对自我牺牲精神、革新力量、“人性之美”[注]陈明正教授即将出版的有关导演艺术的专著,书名就叫《人性之美》。由衷的赞美与期望。他导演的《家》中鸣凤投水的那场戏,与其说是悲惨,不如说是悲壮。蓝色的灯光打在满是莲花的池塘里,“粼粼的波光又反射到鸣凤的脸上”。[注]参见陈明正著《导演艺术随想》,待发表。她站立在舞台乐池上搭起的那块木板上,向觉慧遥祝平安。“这时,天打起了雷,鸣凤脚下的那块地板‘哗’地往下降,直到她整个人陷入地下,‘沉入水底’。”[注]同上。长长的寂静之后是觉慧的哭喊:“鸣凤,是我害了你!鸣凤就死在这里,可是池水为什么那么平静?!”[注]同上。又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生命离开了人世,带着对封建专制的控诉,也带着对恋人的纯洁无私的爱。在《阴谋与爱情》的结尾处,舞台背景正中的那座“被高压的、非正常的年代压得向侧面倾斜的十字架徐徐朝正前方倾倒,倒到一定的倾斜度停了下来,似乎在悲悼它下面的那对不幸的恋人”,但是,“灯光渐渐由白转红,变成一种介于鹅黄和草绿之间的颜色”,“照在死去的男女主人公身上”,因为这种嫩绿色灯光“代表着和平、宁静和希望”,“即使是悲剧的结尾,也要怀着一种美好的希望”。[注]吴靖青:《化解与升华——话剧〈阴谋与爱情〉的导演再创造》,《上海戏剧》,2007年第1期。在《日出》中,他贯串、连缀了方达生的“傻子精神”和“斗争行动”,突出方达生对陈白露的思想拯救、对小东西的救援,以及对那帮堕落的“有余者”的厌恶。在结尾处,陈白露带着“对过去堕落生活的否定”、带着“自尊”和“美”离开人间,然而整部戏并没有停留在“陈白露之死”上,因为“《日出》要日出”,因为“屋内是黑暗,屋外是光明”。[注]陈明正:《〈日出〉要日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研究中心编:《戏剧学》第4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68页。在添加的尾声处,“景片升起,一片灿烂的红光充满舞台”,在劳工们的号子声中,方达生大步走到台口处,对着观众呼喊陈白露年少时的名字,“太阳出来了,太阳是属于我们的”,以及“要和金八斗一斗”之声在剧场里回荡。[注]同上,第269页。在《白娘娘》的结尾处,白素贞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十个赤膊和尚,各执一根布条,拉成塔形”,“在鼓声中旋转”,“配以咔咔发响的绞盘声”,合力绞杀白素贞,“但她儿子那清脆的童声‘我要我的妈妈’震撼着铁塔,最后终于将塔哭倒”。[注]安振吉:《陈明正导演艺术研究》,《戏剧艺术》,1992年第4期。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人性终于战胜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法理”。
伴随着对“真善美”的追求,陈明正教授把作品引入诗境。他没有刻意地把诗歌拼贴进剧中,而是做到了“戏入诗格”,“把生活积聚、概括和浓缩所形成的舞台戏剧,提高到诗的格调上来演出”。[注]安振吉:《陈明正导演艺术研究》,《戏剧艺术》,1992年第4期。这与他学习中国戏曲的方法是相通的。“这种‘溶化’的过程,是一种高难度的再创造过程,陈明正向中国戏曲‘拿来’的,不是具体的一招一式,而是戏曲的精髓——写意性。”[注]戴平:《海派戏剧的一面旗帜——论陈明正的导演艺术》,《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写意性与诗情画意之外,外国文艺中的诗性寓意与意象、平凡生活中错落有致的节奏感与诗趣,也都被他拿来“溶化”进戏剧中。《白娘娘》用几条简洁的绿色条片,配以灯光、烟雾和空灵的舞台演出调度,就展现了西湖“空翠烟霏”“水光山色”的意境。《黑骏马》中“空旷的舞台,可是山,可是水,可是帐篷,可是草原,可是马场,甚至可是产房”,“一个大车轮,象征一辆马车,一个无实物动作,可表现喝一杯酒,掀一次门帘”,假定性、写意性的舞台空间与主人公的上下求索精神有了诗意的契合。[注]安振吉:《陈明正导演艺术研究》,《戏剧艺术》,1992年第4期。《阴谋与爱情》中,“当差别的界限打破的时候——当一切可恶的身份的外壳从我们身上剥掉的时候——当人就是人的时候”作为台词和画外音,带着不同的剧场音响效果先后三次出现,一次比一次震撼人心。《海鸥》中彷徨青年柯思佳开枪自尽后的舞台静默、被灯光加以渲染的海鸥的标本、风吹开窗户的声音、受过伤害的宁娜匆匆而来坚定而去的“马车声”,所有这些画面与音效都反衬、烘托了宁娜的勇敢与顽强,勾勒出“一只受伤的‘海鸥’仍旧奋力飞翔”的诗性意象。《公用厨房》《大哥》是生活的谐谑曲、生活的奏鸣曲。前者“微言大义,寓庄于谐”,“将滑稽与崇高结合起来”[注]戴平:《海派戏剧的一面旗帜——论陈明正的导演艺术》,《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后者从生活中提炼诗意,让胸怀宽广的男女主人公打开“鸽子笼”一般狭小房屋的天窗,爬上屋顶拥抱夜空,达到“手可摘星辰”的境界。
陈明正教授除了继续活跃在表演教学和导演实践的第一线外,如今依旧笔耕不辍。近年来他的听觉受限,但通过对剧本的全面整合与了然于心,通过观察演员的口形、动作和情感体现,通过用“通感”把握整体的节奏和戏剧的“总谱”,在剧组全体成员的协助下,他以年轻人般的创作激情,成功地执导和指导了《日出》《大雷雨》等大戏。他说:“我现在虽然听觉不好,但我心中却听得到优美的音乐。音乐家贝多芬晚年双耳失聪却为《欢乐颂》谱写出交响乐章,我要向他学习,也要把心中感受到的这些美好的事物呈现出来、记录下来。” 他在向更深处、更宽广处和更高处探索戏剧表导演艺术之真谛的同时,获得了心灵的解放。
[本文为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项目(编号:SH1510GFXK)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