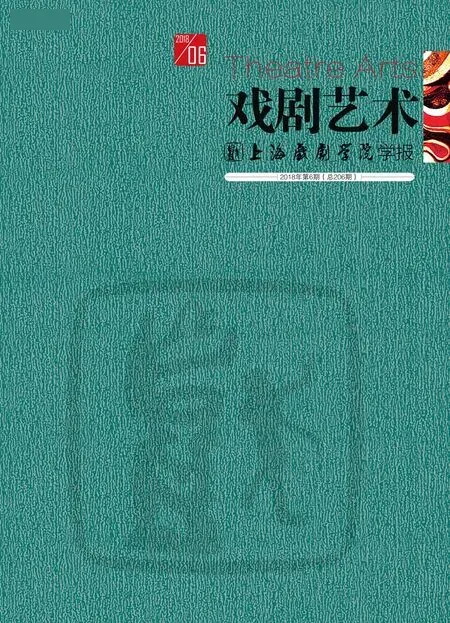论林兆华的先锋主义戏剧观
■
林兆华是一位用“先锋”之概念并不能完全涵盖的戏剧艺术家,且他本人也不愿挥舞“先锋”这面旗。确实,他的那些上演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戏剧,其意义远远大于一个流派所能散发的能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是当代中国采用戏剧舞台形式向著名而权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说“不”的人,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导演的第二主题”“表演的双重结构”“流动的布景”“空的舞台”等不同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兆华确实又是位货真价实的“先锋”人士。基于这一现实,本研究将聚焦于“先锋”视角,探讨一下他在当代戏剧观念方面所做出的创新与贡献。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集中探讨“导演的第二主题”“表演的双重结构”的理论内涵及其所形成的内在逻辑原因。
一、颠覆剧本:反剧本的戏剧观念
林兆华常标榜自己是没有什么戏剧理论观念的人,“我没有理论”,“对理论是蔑视的”。[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与那些专门喜好从某个具体理论或体系范式出发的人相比,他确实是个更多凭借艺术直觉与生命本能从事艺术活动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林兆华果真无戏剧思想和理论观念作支撑——他不过是为把自己从传统戏剧理论体系中淡化、疏离出来而采取了一种策略。
纵览中外戏剧史,不难发现凡是能被称为“大家”的,必定会拥有一套独到的理论逻辑和逻辑的展开方式。林兆华也不例外。综观他自1980年代以来的先锋戏剧观念,不难察觉,如何对待剧本问题是贯穿其整个戏剧艺术实践的最核心环节。他的戏剧思想有过几次重大的转变,而每一次重大戏剧观念的转变几乎都与剧本有着难以解开的渊源。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是,他在1980年代初期之所以从现实主义戏剧跑道切换到先锋戏剧的表现范畴中来,与高行健的那两个不是剧本的剧本《绝对信号》(1982)、《车站》(1983)的冲击有着密切关系。
高行健是林兆华先锋戏剧的最早合作者,在戏剧观念方面曾给林兆华带来过不少启发。他后来曾总结说,他与高行健的合作正是从对戏剧的重新认识开始的,高行健的那些“不按套路写的剧本,给了我很大的挑战和刺激,逼着我去找不同于一般的舞台表现方式”。[注]同上,第61页。显然,林兆华在导演中所实施的那些“不同于一般的舞台表现方式”,与高行健的“不按套路写的剧本”有关。问题在于,“不按套路写的剧本”在此是什么意思?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简略回顾一下高行健的创作实践。曾从事法语翻译的高行健,一直痴迷于写剧本。然而他所写下的十多个剧本,包括被林兆华搬上舞台的《绝对信号》和《车站》都不被人所认可。不知为何,大家一致认为高行健不会写戏,他写下的那些戏根本就不是戏。今天看来,在当时出现这些非议也不奇怪。在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念中,一个好的剧本必须要有动人的故事情节、复杂的人物性格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等,而出自高行健之手的剧本恰恰缺少这些要素,因此人们才敢断言这些剧本根本不是剧本。而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林兆华则具有超越性的视野,他认为这就是剧本,只不过是不按固有的套路,即不按传统套路写就的剧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剧本,或者说“反剧本”的剧本一下子引爆了林兆华创造新戏剧的激情,让他在发出“戏剧还可以这么写”的感叹之余,也进行了“戏剧还可以这么导”[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的试验。而且,他的试验非常成功,经他排演的《绝对信号》和《车站》两剧获得极大成功,以至于连国外的报纸都惊呼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先锋戏剧。
这两个破常规的剧目所引发的社会轰动以及艺术上的成功,似乎给处于探索期的林兆华带来了这样一种启示:越是那些看上去不像剧本的“剧本”,或者说“反剧本”的剧本,越可能排演出好的舞台效果。这就让原本就对剧本有独特兴趣的林兆华变得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早期在排演前“收拾了剧本”“改得我自己都看不懂了”[注]同上,第51页。到“在排练的过程中改剧本”[注]同上,第86页。,再到对世界经典剧本大刀阔斧地删改与拼贴,乃至最后在文学剧本缺席的情况下排演戏剧,林兆华走出了一条用“反剧本”的方式来革新戏剧的新道路。
在此不要误解了“反剧本”的含义。所谓的“反剧本”并不是真的不要剧本(即把剧本的作用和地位从戏剧体系中取消掉),相反,对写不了剧本的林兆华而言,剧本在很多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诚如他说:“我不像有些导演没有文本也可以排戏,我不会那种方式。”[注]同上,第64页。可见,剧本在林兆华的戏剧观念中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因此说,“反剧本”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指反叛传统剧本,绝不是说林兆华不重视剧本;第二层含义则是指林兆华的剧本观,与传统的剧本观是两套互不兼容的剧本观,即双方虽然都围绕着剧本来排演戏剧,但是在对待和使用剧本的理念与方式方面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大致可作如下总结: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传统戏剧思想框架中,所谓的戏剧表演(而且也只能是围绕着“剧本”所提供或者说所规定的价值维度前行),主要是对剧本思想的一种再现和阐释。无疑,在这种表演模式中,剧本是首要的,它不但决定着演员的表演,也决定着导演自我能动性的发挥。一句话,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都是为剧本服务的。而在林兆华的戏剧观念中,剧本是重要的,一般也是必须的,可这种重要和必须并不表现在对剧本权威性的遵循方面,而是主要表现在对剧本的为我所用上。
其次,传统现实主义戏剧以表达剧本的思想为目的;林兆华的戏剧则是借剧本的思想来表达其本人,或者说作为一名戏剧导演的思想。正如他说,“我不喜欢对剧本看图说话的排戏”,“我透过别人的剧本去建立我自己的东西、说自己的话,我自己没有能力写原创的剧本,我的兴趣只在导演上”,“在剧本的基础上,我可以添加我的东西,或者是把我想要的东西抽象出来,我常常把剧本的故事和性格减弱”。[注]同上。从这些引文中可以得到两个重要信息,即他不排按剧本说话的戏;剧本主要是激发他本人思想的一个媒介。也就是说,他是借他人的剧本来说自己想说的话、抒自己要抒的情。这就意味着经林兆华之手所编排的那些戏,与剧本的原本风貌已经相去甚远。
综览林兆华这些年来所编排的戏剧,发现他不但对国内剧作家的剧本进行为我所用的删改,而且对待世界经典名剧也如出一辙,甚至更甚。自1990年代以来,林兆华重新排演了包括像《哈姆雷特》《樱桃园》《伊凡诺夫》《建筑大师》《浮士德》等一系列的世界经典名剧。通常说来,在面对这类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时,导演想到的往往是如何把剧本的真实风貌反映出来,即考虑的首先是舞台文本与文学剧本的对应关系。然而林兆华则走了另一条路——有意识地撇开剧本的内容,而去追求剧本之外的东西。譬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一个著名戏剧,了解莎士比亚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剧本讲述了一个长大成人的王子要为父复仇的故事。然而林兆华所编排的《哈姆雷特》偏偏不沿着这条现成的线索走,而是演绎出这样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面对哈姆雷特,不是面对为了正义复仇的王子,也不是面对人文主义的英雄,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自己。能够面对自己,这是现代人所能具有的最积极的、最勇敢的、最豪迈的姿态。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在此认识基础上,他为这部戏剧开辟出了一条“人人都是哈姆雷特”的新主题。[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页。
从哈姆雷特个体人的困惑转向整个现代人的困惑,如果说这种演绎或者创造还有其顺理成章的一面,那么他对布莱希特的《二次大战中的帅克》一剧的处理则算得上是惊世骇俗。这个剧中出现了一个“大人物”,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对这个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纳粹头目,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幅肖像——冷酷而残暴。林兆华却独出心裁,即他安排了一位手拿一个大气球、头上梳着个小辫子、唇上还贴着一撇小胡子的“小女孩”来扮演希特勒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种极端背离剧本的舞台效果可想而知了。面对纷纷而来的批评和质疑,林兆华的解释是:“我根本就没有特意去塑造形象,就是以我的方式给学员排一个布莱希特的戏。”[注]同上,第354页。显然,从一开始林兆华就没有着力去塑造一个真实的希特勒,其目的在于借布莱希特的这个剧本来构筑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其实是他的一贯作风,诚如他说:“我排名剧经典,(如)《哈姆雷特》,不是莎士比亚的,我明确它是林兆华的。”[注]同上,第311页。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林兆华的这种从“A”演绎出“B”的剧本观,与传统的剧本观有着根本性分野。他的这种剧本观是对传统剧本观,也就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种颠覆与解构。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提倡道:“一个演员全部想象的思想、情感和动作,应该汇合起来去实现剧情的最高目的。”[注](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自我修养》,郑君里、章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85页。林兆华并不掩饰这一点,在改编契诃夫的《樱桃园》时,他曾坦言:“我不敢说颠覆不颠覆,只是要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传达出来。就是颠覆经典,又有什么不可以?”[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林兆华的这种任何剧本都可以颠覆的思想,在排演鲁迅的《故事新编》时达到了顶点:这是一部只有原小说,而没有文学剧本的剧场作品。林兆华在此只是给演员规定了一个基本的表演框架,至于如何演,则由演员根据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中所设置的故事情景自由地发挥。而他只负责最后片段的选取与组合。
二、导演:新戏剧观念的引领与缔造
林兆华解构、颠覆文学剧本的目的是什么?要谈目的的话,自然不会只有一个,譬如从对剧本的拆解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也是目的之一。不过,我认为诸种目的中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消除传统现实主义戏剧表演模式给人们思想上所带来的禁锢。换句话说,林兆华通过解构剧本之方式来解构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从而为中国当代戏剧开辟出另一种戏剧精神和表演向度。
这种解构与取代当然并不意味着建立在传统剧本观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表演模式排演不出好的剧目。相反,现实主义表演模式不但已经排演出了不少优秀剧目,而且还造就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剧作家。林兆华尽管说他这个人生性不喜欢现实主义的表演和导演,对天马行空的舞台表现方式更觉得亲切,但这也并不影响他对现实主义流派的崇敬之情。他公开说:“我不反对斯氏和易卜生,他们都是戏剧史上的大师,我们没有他们的功力。”[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敬佩归敬佩,但是中国诺大的戏剧表演舞台上,长期以来只有现实主义戏剧一枝独秀,这种现状令他深感不安,所以他不由自主地发问,“中国的戏剧文学、表演、导演、舞台美术有不同的流派吗?我看有,也没有!过去只知道一个主义,叫做现实主义,一个体系叫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现实主义可以永世流传,可戏剧多一些主义有什么不好”。[注]同上,第58页。毫无疑问,林兆华理想中的戏剧舞台应该是多元共生、共竞发展的舞台。
当然,作为一个流派,传统现实主义戏剧在反映现实和人生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重要的是,它还能最大程度地维护、保证和弘扬剧作家本人的思想个性,这或许也是现实主义优秀剧目的背后,总会拥有一个好剧本和好戏剧家的原因。然而,如果把一部戏的成功与否完全寄托于剧本和剧作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如下问题:首先,排演戏剧的过程也就变相地成为寻找剧本的过程——碰上一个好剧本,就能编导出一出好戏。通常所说的“戏抬人”就是这个意思。同样,剧本不好,戏也就砸了。其次,戏剧原本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剧本之外,还应该是与导演、演员等一起合作、演绎的结果。但是这种以剧本为上的思想,就从某种程度上把导演和演员的自主能动性封闭了起来,即他们的生命激情、艺术创造力,乃至自我的想法都必须服从于剧本的要求。
这种紧密围绕文学剧本搭建起来的戏剧表演观念,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把一种原本完全是可以依靠合力取胜的戏剧表演,人为地简化成了依附于剧本的表演。长此以往,就使原本丰富多彩、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戏剧艺术变成了照本宣科的“死艺术”。正是为了突破戏剧表演长期以来被剧本所捆绑的窠臼,或者说是为了让导演、演员从剧本和传统表演程式里解放出来,林兆华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是“戏剧的核心和本质问题是表演”[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另一个是“导演是演出形式的创造者”[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应该说,这两个命题的提出非常重要。前一个把戏剧的重心从剧本问题转移到了“表演”的问题上,即指向了“到底何谓戏剧”的问题;后一个把“导演”与“演出形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提出了“作为一剧之导演应该何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林兆华开始彻底地反思这些年来中国戏剧所走过的道路:“实践这么多年下来,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什么是戏剧。搞了几十年,居然还不懂戏剧是什么。”[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显然,在林兆华看来,以往占据着舞台中心的现实主义戏剧观是有缺陷与不足的,它使人们变得越来越不知何谓戏剧,即离着戏剧的本源越来越远。[注]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戏剧是诸多种戏剧中的一个种类,它的“种类”就要求它不但要有这样的戏剧观,而且还要如此表演。也只有如此,它的存在才有价值。中国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把这一戏剧流派的美学思想当成了戏剧唯一正确的思想,即几乎用现实主义戏剧替代了整个戏剧艺术,所以林兆华感慨说搞了这么多年的戏剧,竟然不知道戏剧是什么。
正是出于让戏剧回归到戏剧本途上的考虑,林兆华才提出了上述这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的最大功效是,使戏剧的主体性发生了移位,即由原本对剧本的阐释,转向了对导演,包括演员思想的张扬。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原本按照剧本所规定线路走的戏剧艺术,一下子变成了导演手中的戏剧表演。这就意味着一部戏剧能否成功,将主要取决于导演的功力,即导演的权限大幅度地增加。林兆华显然意识到了导演所迎来的这种身份转换,所以他反复说,导演“应该创造自己的舞台语言,发现新的表现手段。导演也应该是新戏剧观念的创造者”。[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把“导演”与“新戏剧观念的创造者”等同起来,应该说是一种很大胆的举措。因为在以往的戏剧分工中,负责创造“新戏剧观念”的一般都是剧作家,而导演多半是这种新观念的执行者。他在1980年代初期与高行健的合作基本上也属于是这种意义上的合作。
林兆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从高行健的那些不像剧本的剧本中,很快体悟到戏剧观念的创新并不单单是剧作家的工作,也应该是导演的职责,即导演不应是被动地等待“新观念”上门,而是要主动出击,去寻找和创造“新观念”,导演也应该成为创造“新观念”的那个人。因此他反复强调,导演需要“顽强地建立起一个独立于剧本文学的导演语言”[注]同上,第275页。,“我一直认为导演应该建立自己的独特的导演语汇”[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该处所说的“导演语言”“导演语汇”,无疑指向的都是那个“剧本文学”,即林兆华把导演的自我创造性,作为一个独立元素彻底地彰显出来。
这种通过强调“导演语言”的方式,把导演从“剧本文学”的依附中分离出来的思想非常重要,它标志着自此以后的中国戏剧艺术表演模式不一定非要沿着复制或再现“剧本”的路数走,剧本由原来的绝对主角变成了配角,也由原本的精神纲领变成了一个为演出所用的文字纲要。
毋庸讳言,单纯从学理层面上讲,解构文学剧本,甚至放逐文学剧本,并非是解救戏剧的正途,至少不是唯一的途径。说到底,戏剧艺术是一种表演的艺术,但这种表演艺术归根结底离不开一个创意,而这个创意就是剧本。事实上,林兆华也并非截然反对剧本和剧作家,相反,他认为,一个导演在一生中如果能够有幸碰到一位志趣相投的剧作家,那是上帝赐予的幸福。显然,对一名导演而言,这种需要上帝赐予的幸福并不是经常能够碰到。从这个角度说,他的解构与放逐其实不过是一种策略,即通过此手段来解构、放逐已经固化了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念与表演模式。
解构固然重要,建构则更为重要。林兆华在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戏剧观念的同时,又建构起了哪些新的戏剧观念?应该说,他的建构是多方面的,甚至从某种层面上改变了戏剧舞台的诠释模式。譬如以往的戏剧表演几乎就是一种话剧表演,即语言充当了主要的表演媒介。而林兆华则坚决反对演员在舞台上喋喋不休,所以他说:“我希望剧作家们写一些沉默的戏剧,语言将不是主要的表现手段。”[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把“语言”从主要表现手段中抽离出来之后,又该用什么手段来加以补充与取代?林兆华认为是“动作”。在他看来,人的形体语言才是最高妙的舞台语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几乎从排演《绝对信号》和《车站》开始,林兆华就致力于发掘人的形体方面的表现力。等到排演《野人》(1985)和《樱桃园》(2004)时,更是把“形体”解放问题置于首位。为了让演员忘掉以往在学校中所学的那套朗诵式的舞台腔,他把“剧本撂到一边”,让演员们“从做游戏开始”[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页。。为了达到最佳的放松效果,他甚至让演员们在舞台上疯跑,无数次地重复一个动作。这番努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训练演员的“中性状态,破除掉他们身上固有的表演模式,不让他们进入所谓现实主义的‘泥坑’”。[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32页。
显然,林兆华认为一些现实主义戏剧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话”太多,什么都是靠嘴“说”出来的,而不是靠全身“演”出来的。因此,林兆华试图用全身心的“演”来替代现实主义戏剧的“说”。所以经过他这套方法训练出来的演员,不但可以在舞台上扮演各种人物角色,而且还可以表演以往所不能表演的东西,如人的意识流动、内心的情感波澜、动物、植物等。总之,过去需要借助于大量的布景和道具才能够完成的,现在仅靠演员的形体就可以展示出来。
当然,林兆华最大的理论建树是“导演的第二主题”和“表演的双重结构”概念的提出。前一个概念是用戏剧思想的多义性、模糊性,取代了传统戏剧思想内容的单一性、统一性;后一个概念则把文学的戏剧,演变成了以舞台为中心的戏剧,即试图通过演员自身的表演,尤其是那些即兴的表演,恢复戏剧这门艺术原本所具有的一些功能。有关这两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将在下文论述。
三、“导演的第二主题”与“表演的双重结构”
正如前文所论,把“导演语言”从“剧本文学”语言中独立、分裂出来的结果,就使导演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假若说以往的戏剧表演主要是依靠“剧本”来掌控方向,那么在林兆华的这种以“导演”为核心的先锋戏剧理论中,导演(也包括导演领导下的演员)的自我能动性发挥所占的比例则大为加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导演的第二主题”“表演的双重结构”的提出是必然的——是以“导演”为戏剧表演中心的必然逻辑结果。
何谓“导演的第二主题”?这个概念的提出,针对的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的戏剧观念。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现实主义戏剧中,“主题”问题历来是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一部戏剧,如果没有一个中心议题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议题,那将会是一部失败的戏剧。林兆华对这类阐释主题性的表演模式非常不满,他借契诃夫的戏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过去我们对大师的经典大多停留在戏剧文学的解释上,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契诃夫戏的主题是什么、契诃夫的情调是什么的层面上,今天我面对契诃夫,不是为他服务,是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观众服务。”[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林兆华借这段话欲表达的意思是:文学剧本的原本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读者面对这部戏会产生何样的感想?也就是说,林兆华注重的是从原剧作中引申和阐发出与当下生活相关的新资源。而且,他把这种演绎出来的“新资源”命名为“导演的第二主题”,诚如他说,“不完全照着剧本走了”,“除了剧本内容,还应该有导演自己的主题”。[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这个所谓的“导演自己的主题”,也就是“导演的第二主题”。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导演的第二主题”的两大特征:首先,它与戏剧文学的主题,也就是剧本的主题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也符合逻辑,否则也就没必要区分第一、第二主题;其次,“第二主题”的捕获与“戏剧文学”的主题又是密切相关的,即是导演在阅读了戏剧文学后所涌现出的一种感想或体悟。正如他说,我改编名著,“不为表现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的理想,为的是传达我自己的主题,我把这个叫作导演的‘第二主题’”。[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无疑,“第二主题”又是由原剧本主题衍生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又不能截然砍断它与原剧作主题间的渊源关系。
显然,“导演的第二主题”与原剧作的“第一主题”间的关系是较为夹缠的,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清楚的。不过大致说来,可以这样阐明其内涵:所谓的“导演的第二主题”也就是导演从原剧作出发,但又超脱出原剧作思想的束缚,而赋予了剧作一种全新的精神内涵。这部分内容是导演独立于文学剧本之外的思考,属于导演个人思想的构成部分。
这当然并非是主观揣测,林兆华本人也曾明确地说:“这第二主题是我的。第一主题是文学的。比如我排莎士比亚的剧可以不改他的台词,只作一点删节,可以按照他原来的台词去演。但我强烈地把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把我独立的一些思索、独立的状态,放在这个戏当中。这是导演的第二主题。每排一个戏,我都这样,我追求这个。”[注]林兆华:《戏剧的生命力》,《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为一部已完成的剧作增加上“第二主题”,就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导演的工作职责:在传统的戏剧观念中,导演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剧本的思想反映和阐释出来,至于好还是不好,尽管有导演的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可以归结于剧本。而在林兆华所提出的这个以导演为中心的表演框架中,剧本基本上也就是仅供参考的文字线索。这就意味着主要的思想——包括现实意义上的思想和美学层面上的思想均要出自于导演本人。换句话说,排演戏剧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了,而是掺入了导演本人对世界与人生的所思所想。
林兆华所彰显与实施的“导演的第二主题”构想,就决定了演员的表演也将会面临一个挑战。这也容易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演员既是导演思想的承载者,又是呈现者。缺少了这一环节,导演的思想无论有多深刻,也无法变成现实。因此林兆华说:“只要当演员的表演具有大自由和丰富的多重性时,导演才能建立起不同于剧本文学的第二结构。”[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无疑,“剧本文学的第二结构”,也就是“导演的第二主题”的实现,是建立在演员的表演基础上的。这也是林兆华紧接着“导演的第二主题”之后,又提出了“表演的双重结构”的内在逻辑。
与“导演的第二主题”一样,“表演的双重结构”这个概念的提出同样是针对于现实主义戏剧观念的。诚如我们所知,在现实主义戏剧表演体系中,对演员的最高要求就是“逼真”,哪怕是“谎言”,演员也必须要演成令人不可置疑的“真理”。[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涯》,杨衍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4页。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验派”表演。这种表演意味着演员和角色必须是合一的,即演员的天职就是把角色的性格生动而真实地还原出来,让观众觉得表演者本人就是剧中的那个人物。
作为一种表演模式,这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表演方式自有其价值,但是由于该表演过于强调演员的角色化,即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掩盖了演员自身的精神特质,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抑制了其演技的发挥,弱化了表演时演员对自身的“控制”技术。林兆华并不热衷于这种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逼真”表演,认为这种表演过于情绪化,反而有做作之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扮演和体验是两码事”[注]林兆华:《戏剧的生命力》,《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的说法,并坦言在“人物的思想和性格”之间,他“宁可舍弃性格”[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扮演”并不一定直接等同于“体验”;“体验”也不一定直接导向人物角色的性格。林兆华所提出的这两点显然都是针对现实主义戏剧的“逼真”说而言的,诚如他说:“本来就是在舞台上搭的布景中演戏嘛。这是戏剧艺术的前提,首先得认清这一点。”[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认清这一点”就是要让演员心中明白,自己此时此刻完全是在演戏。换言之,首先要让演员承认这个戏剧表演是假的,是“我”在舞台上装扮某个角色。在肯定这一前提之下,再让演员通过表演技巧把“假”的变成“真”的。所以林兆华说,“表演的双重结构”就是一种“极大的假定性和极真实的表演的结合”。[注]同上。显然,林兆华提出的这个“表演的双重结构”与传统现实主义戏剧的根本分野就在于,现实主义戏剧的表演出发点是把“假”的事实当成“真”的事实;演员也是把“假”的人物当成“真”的人物来演。林兆华则不同,他是直面这种虚假,即在正视戏剧艺术的本质就是虚假的前提下,再来构筑演员的表演体系。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林兆华为何格外重视演员与角色之间的那种疏离感,诸如演员的表演“不是纯体验也不是纯跳出”、演员在舞台上“既是人物又不是人物”、演员与人物的关系是“既在戏中又不在戏中”[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75-76页。的原因了。由此可见,林兆华的“表演的双重结构”,和哥格兰的演员“第一自我”完全操控“第二自我”的理论并不等同,关键是因为林兆华追求的表演“不是纯体验也不是纯跳出”。
毫无疑问,林兆华反对演员在舞台上无条件地一味向“角色”靠拢,主张演员在面对其所扮演的角色时,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多元的状态”[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理性的审美状态。为了能更清楚地诠释出这一表演理念,他还采用“提线木偶的状态”来隐喻这一理论:“斯坦尼的体验艺术,常常演的是那个木偶,我认为演员既是提线者又是木偶。演员在舞台上应该意识到‘我’要这样演,‘我’要这样表现,这样演员会有极大的自由。”[注]同上,第77页。斯坦尼表演框架中的演员基本上可以与“木偶”本身划等号,并不强调表演时的“操控”;而“表演的双重结构”中的演员则既是木偶又是木偶后面的那个“提线人”。另外,林兆华提出的这种“既是提线者又是木偶”的表演状态既不是纯粹的“演员与角色的疏离”,又不是纯粹的“演员与角色合而为一”。
这种双重性要求,就决定了演员在舞台上不但要把角色扮演好,同时还要超脱出角色的束缚,“自由地表达出自己对人物、对客观世界的态度”。[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做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页。除了是角色和演员自我之外,“我”还是个潜在的高于这二者之上的评判者,即在“表演的双重结构”框架中,演员其实是身兼三职。有关这一点,曾与林兆华有过合作的剧作家过士行概括得非常准确。他说林兆华“要求演员不仅有角色的自我,还要有演员的自我,更要有一个审视者的自我。演员在角色、自身和评判者不同的身份中穿行”。[注]林兆华口述,林伟喻、徐馨整理:《导演小人书·看戏(全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页。林兆华“角色的自我”“演员的自我”“审视者的自我”这三个“自我”的理念,显然也与哥格兰的“第一自我”“第二自我”这两个“自我”的理念形成对照。林兆华把他这一类戏剧风格的演员表演职责进一步细化了。与纯体验式表演相比,林兆华所要求的表演,或者说“导演的第二主题”框架下的表演,其表演的难度更大了,演员不但要把原有的剧本思想表现出来,同时还要调动各种手法把导演的思想演绎出来——与其说演员是“角色”的扮演者,不如说演员是一些会在舞台上思考的思想者。这也是林兆华在挑选演员时除了重视其天赋如何之外,还重视其思考能力的原因。
毋庸置疑,在任何情况下,戏剧艺术的美学理念和表现手法都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在很多时候也难以断言哪个更先进,哪个更落后。但是林兆华所提出的“导演的第二主题”和“表演的双重结构”等命题,在当代中国则包含特殊的意义:这些命题的提出和确立——该处的“双”也不仅仅是代表“两个”,它其实更具有无限多的隐喻功能——把戏剧艺术从单维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让戏剧成为一种多声道的表演。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但把文学的戏剧转化成了以舞台为中心的戏剧,而且还使戏剧艺术表演成为一种每一场次都不可重复的“活”艺术,使戏剧表演的现场性和创造性都得到了空前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