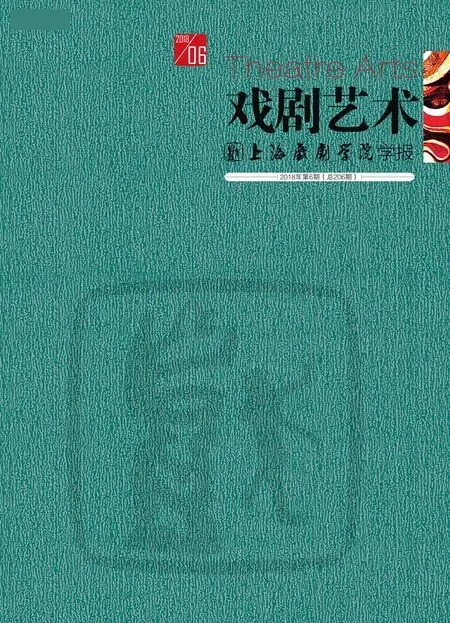论新潮演剧中戏曲新编的现代意义及其历史缺憾
■
一、本文的缘起
清中后期以降,中国经历了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24,新北市: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1页。。至19世纪末,饱尝半个多世纪内忧外患的大清帝国,社会政治经济陷入日益深重的危机之中,终于催生了一场“尽革旧俗”[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1898年1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7页。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甚至进而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其间,包括戏剧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也随之相继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革。“新潮演剧”也便由此而勃兴。众所周知,“新潮演剧”的内涵,一方面是“戏曲改良”运动的兴起,一方面则是文明新戏的诞生。然而细究起来,两者之间,究竟是孰先孰后?两者是各自为阵,还是相互启发?究竟何者对于20世纪的中国戏剧的形态及进程影响更甚?诸如此类,却似乎一直未能得到学界深入的探析。
就戏曲而言,“改良”的观念与实践不仅在清末民初酿成一股风潮,而且对于20世纪的戏曲生态及命运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相对于传统戏曲,“改良戏曲”不止是提出了一种“以戏曲改良社会”的创作理念,更主要的还在于形成了戏曲“新编”的创作模式。或者说“新潮”之下,人们已普遍地不再满足于旧有剧目的搬演,而是追求在一种新的创作理念之下的新剧目的创编。这种“新编”随着海派京剧以及新兴地方戏(如评剧、越剧、黄梅戏等)的兴起,特别是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之下,几乎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世纪性的戏曲创作现象。1950年代随着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展开,“新编”的现代戏或历史剧的创作更是堂而皇之,风行一时。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新编”戏曲,无论是时装还是古装,无论是现代题材,还是历史故事,实际上都是属于所谓戏曲“现代化”的一种有效的实践和尝试。换言之,所谓戏曲“现代化”,也就是需要在遵从传统的前提下为当下的观众所重新编演、当下呈现。
本文正是基于对清末民初新潮演剧当中的戏曲新编创作历史进程的具体考察,着重分析其对于20世纪戏曲生存样态及其命运的影响,揭示发端于新潮演剧的戏曲新编的两种基本路向及其内在的文化矛盾,进而总结戏曲新编的现代意义及其历史缺憾,阐述戏曲新编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与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二、“新编”何为:改良戏曲的生存样态
事实上,清末民初所兴起的“戏曲改良”运动,在变法维新乃至辛亥革命的时代要求之下,不仅催生出一种新的戏剧观念(如梁启超之“戏曲新民”观),而且带来大量新编戏的涌现(如汪笑侬之戏曲创作实践)。这里的所谓“新编”,乃是相对于戏曲传统戏的传承而言的,是指戏曲采用新的题材、新的样式来进行新的舞台呈现。前者是老戏的传承,后者是新戏的编演。因为,面对晚清社会深刻的历史危机,觉醒的国人已不再是满足于旧调重弹而必须锐意创新。戏曲改良派也便乘势而兴,因为不能照搬老戏,让观众沉浸于老腔老调之中,“新编”也势必成为实行戏曲改良的唯一行之有效的策略和选择。从而,作为戏曲求新求变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新编”,一方面是传统戏曲自身内部变革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戏曲面临着一种急切的社会变革的危机情势之下所不得不然的选择。
故而,自梁启超、汪笑侬开始,便是顺应着社会变革的大潮,各种“新编”剧目不断涌现,成为改良戏曲的主要生存样态。从而,20世纪之戏曲“新编”,既然是相对于既有的老戏而言的重新创作,就必然要在传统戏曲原有的题材、格调、主题之外另辟蹊径。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不仅大声疾呼戏曲改良,而且身体力行,躬身新编粤剧、传奇的创作,前后共创作出《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传奇三种、粤剧班本《班定远平西域》一种,试图为改良戏曲探索出一条新路。他以“新民”为己任,以提倡“积极破坏”、提倡爱国热诚、提倡尚武精神为其新编戏曲的主要内容。正是受其影响,包括诗人柳亚子在内的更多的文人都参与到新编戏的创作当中。有资料统计显示,从1896年到1911年,其间戏曲改良派团结一些热心戏曲改良的同道,创作传奇、杂剧计有105种,地方戏9种。这些新编剧目不仅多以唤起民众投身社会变革运动、救亡图新为主题,而且在题材上,也多与救亡图存相关,其中有直写时事者,如描写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烧杀抢掠的《武陵春》、宣传变法维新的《维新梦》、提倡女权的《广东新女儿》《松陵新女儿传奇》、控诉鸦片毒害的《招隐居士》等;也有取材于历史故事者,如歌颂岳飞、文天祥爱国英雄事迹的《黄龙府传奇》《爱国魂》等。有别于传统文人借度曲以抒情言志,改良派文人的戏曲新编多是胸怀变革图新、挽救民族危亡的心志戮力而为。他们竭力鼓吹戏曲的社会教化的意义,但是,因为他们当中多数对戏曲舞台演出不尽熟悉,其中的许多作品还只是属于生硬鼓喧,并不适合舞台演出,只能在报刊发表,成为案头剧作,未能走进剧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它们虽然引发了戏曲观念甚至形态体制上的巨大变化,同时,却由于创作者过分强调了戏曲的宣传鼓动功能而显得急功近利,强化了戏曲高台教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些新编作品难免显得鼓噪有余而审美不足,并且由此也带来了20世纪一股过分强调戏曲服务于时政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在20世纪戏曲现代化的进程中,某些历史阶段甚至成为一种常态和主流。
而被梁启超称为戏剧改良之“实行家”的汪笑侬,则是直接投身于梨园,又编又演,不仅直接推动了海派京剧的形成,而且给整个清末民初的京剧舞台实践带来了一种清新的气息。有诗为证:“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化身万千倘如愿,一处歌台一老汪。”[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号,1904年。其实,汪笑侬可谓是那个时代京剧演员中的知识分子而有别于那些梨园世家出身的伶人。汪笑侬不仅深通文墨,而且作为伶人中的文人,有着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关注时代变革。他不能满足于谭鑫培、汪桂芬们的《洪洋洞》《卖马》《哭灵牌》等骨子老戏,并且深知自己要在上海码头立住脚,光靠老三派的唱腔和几出骨子老戏是绝对不行的。于是,汪笑侬不仅大胆的借鉴徽调、汉调创编新腔;而且,积极编演新剧、另辟蹊径。从而,他将自己一腔爱国之情、亡国之恨化作慷慨激昂的唱腔呈现于新编剧目当中,借以抒发心中的郁闷与悲怆。由此也便有了《哭祖庙》《瓜种兰因》《波兰亡国惨》等一系列汪(笑侬)派独有的剧目,甚至形成了悲愤激荡的汪(笑侬)派独有的表演风格。
在当时戏曲改良的风潮之下,伶界艺人也都不免受其裹挟。光绪末年,京剧名家田际云与著名票友乔荩臣等设戒烟会,编演《黑籍冤魂》《拿罂粟花》等剧,筹款救济吸鸦片者。1905年,田际云还根据杭州惠兴女士为兴学自杀事件而编演新戏《惠兴女士》,自饰惠兴,颇有影响。据称被奉为“伶界大王”的谭鑫培还曾与田际云同台演出该剧。1911年,田际云又因邀请新剧演员王钟声、刘艺舟等在其经营的天乐园演出,还被清政府以“编演新戏,诋毁朝廷”罪拘禁百日。当然,真正体现戏曲“新编”实绩的,当属随后欧阳予倩的“红楼戏”以及梅兰芳的“时装新戏”的编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海派京剧的兴盛。
而伴随着新潮演剧影响的深入,评剧、秦腔、川剧等地方戏也由趋新改良而得以崛起或振兴。可以说这些地方戏的振兴之路却无不伴随着大量新编作品的出现,甚至就是以出色的新编创作而得以兴盛起来、称雄一时。
譬如清末民初的评剧之兴盛,也离不开成兆才的大量新编戏的创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成兆才受其影响,不断有新编作品问世,连续写出了《花为媒》《杜十娘》《王少安赶船》《占花魁》等借古讽今的爱情剧目,使得评剧在冀东莲花落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相对成熟且广有影响的地方剧种。其中,《花为媒》作为成兆才早期的代表作,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寄生》篇,描写王少安之子王俊卿与李月娥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他们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间生活的色彩。特别是成兆才根据1918年直隶滦县(今河北省滦南县)高家狗庄地主兼资本家子弟高占英谋杀妻子,农家女杨国华(杨三姐)不畏强权,为其二姐申冤告状的真实故事,新编创作出代表作《杨三姐告状》。该剧在艺术上粗犷、豪放、泼辣、明快,不仅具有浓厚的冀东乡土风味和鲜明的时代气息,数十年间常演不衰,而且还被搬上了银幕,成为评剧经典保留剧目。成兆才的剧作构思大胆、奔放、复杂多变,内容切中时弊,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唯其如此,成兆才的新编作品直到今天还一直活跃在评剧舞台上。
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陕西西安“易俗伶学社”(简称“易俗社”)的成立,也就是以“移风易俗”为目的,“拟组新戏曲社编演新戏曲改造新社会”。在“易俗社”的组织大纲里,第一章便开宗明义:“以编演各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认为“旧日戏曲优良者固多,而恶劣淫秽足以败坏风俗者亦属不少,因发起编演新戏,以补社会教育之不足”。[注]孙玉仁:《陕西易俗社简明报告书》,《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戏剧、民间文学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其间,孙玉仁编剧的《新女子顶嘴》《三回头》《白先生看病》等,因其选材都贴近生活现实,关注民众疾苦,都成为秦腔的新编保留剧目;李桐轩的《一字狱》,其本事乃是源自清人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其舞台呈现则是以注重在人物的心理性格中挖掘动因见长,已初具一种新喜剧的形态;而像范紫东的《三滴血》,更是以娴熟的编剧技巧将三条剧情线索交错编织,创造出一种跌宕起伏、奇峰突起的舞台喜剧效果。无疑,这些秦腔的新编作品不仅体现出新的戏剧精神,而且为古老的秦腔带来了全新的面貌,而使得以新编创作为主的“新秦腔”别开生面。
值得一提的还有川剧的“改良公会”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黄吉安等人的新编川剧的创作,更是全面促进了川剧的革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随着“戏曲改良”运动风靡全国,“改良戏曲”亦成为四川社会改良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开始纳入了官方主导的议事日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先后担任四川巡警道、劝业道的周孝怀就极力主张“改良戏剧,辅助社会教育”,倡导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并自任主办兼总管。川剧“改良公会”的活动不仅使得长期散流民间、各自衍化的四川戏曲通过“政府行为”而开创了官方出面组织、社会各界参与的新局面;而且,该会还特别邀请黄吉安、赵熙等文人名士编写“改良剧本”,经周孝怀亲自审阅后以“公会”名义刊印并颁发各戏班排演,从而使得川地戏曲的新编创作和演出从此比较自觉地趋于一致而顺应了“改良戏曲,辅助教育”的时代潮流,有效地激发出近代以来川地戏曲的主体意志与时代精神。
总之,戏曲改良的新潮之下,“新编”创作蔚成风气,大抵完成了20世纪新戏曲几乎所有的体制和形式的革新尝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戏曲新编,并非新潮演剧中戏曲求新求异的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为20世纪的戏曲带来一种新的生态样式,提供了一种新文化参与戏曲现代化改造的可能性的方式和路径。唯其如此,戏曲“新编”得以成为20世纪戏曲现代化的一条十分必要的路径,却也使得此一路径布满荆棘、充满曲折。
三、政治与时尚:戏曲新编的两种路向
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当中,戏曲新编明显体现出表达急切的政治诉求与迎合世俗娱乐趣味两种路向。这两种路向,实则体现出影响戏曲生存的两大体制性因素——政治与市场——对于戏曲的巨大影响。一方面,对于时事和政治的关注,既成为戏曲改良的契机,也是戏曲新编的重要驱动力;而另一方面,追求时尚,满足人们趋新求变的审美需求,则成为戏曲新编的另一驱动力。两轮驱动当中,如果说,前者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是梁启超和汪笑侬,那么,后者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就是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特别是后者,成为海派京剧的新潮涌起当中的中坚人物,其影响所及,更是为20世纪戏曲“新美学”的生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具体说来,一方面,从戏曲新编的政治诉求的表达来看,戏曲改良派力图依靠戏曲“建独立之国,撞自由之钟”,声称通过戏曲新编创作“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注]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号“发刊词”,1904年。。1905年,汪笑侬在上海“春仙茶园”排演新编的《波兰亡国惨》等戏之时,也曾在与熊文通致曾少卿的信中表明自己对改良京剧的主张,“取波兰遗事,……以证波兰亡国原因”,进而“鼓舞激扬”,启蒙民心。其实,戏曲改良派对于“移风易俗”等社会现实功用的强调也一直是戏曲价值功能的重要体现。而新潮演剧当中,在汪笑侬、梁启超等的推重下,这一点明显得到了刻意的强化。由此,这一时期的戏曲“新编”就曾大量利用包括欧洲近代的历史题材在内的各种时事编演时装新戏,显然都是着眼于强化戏剧对于社会的针砭与改造功能,即所谓“采泰西史事,描写新戏,以耸动国人危亡之惧,起爱国之念”[注]陈去病:《致汪笑侬书》,转引自《中国京剧史》上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所以者何?应该说,肇始于20世纪之交的“戏曲改良”,确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清季“优伶结交三教九流,与政治从来渊源甚深,清季民初的名伶田际云即是显例。此公一面登台亮相,与文人票友从事戏剧革新,一面广泛交游,凭借出入宫廷内禁之便,相继与维新革命活动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而戏里戏外,情景交融,真假虚实,浑然一体”。[注]桑兵:《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事实上,戏曲与政治的渊源,不仅是源自于艺人们对于政治的个人关注与群体交往,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时代风气使然。或者说,更主要的还是与晚清民初急切的社会变革有关。无疑,这种政治导向与道德教化的强化,一方面可以使得戏曲新编“紧跟时代”,反映时代主题,显示出戏曲舞台对于时代政治的特殊敏感;另一方面也确实由此而开启了20世纪为适应急切的现实政治需要而“新编”戏曲之先河。
然而,戏曲新编的时政导向之下,过分的功利化与实用化,却也可能由于其急功近利而使得戏曲成为一个时代的简单的“传声筒”,很容易造成“概念化”与“公式化”,使得舞台沦为说教的“讲台”,表演成为“演讲”,或者只是成为政治甚至政策宣传的应时应景的工具,更可能因其“紧跟时代”“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而丧失其应有的艺术价值与美感魅力,难免沦为准艺术甚至反艺术的文本现象。
另一方面,从戏曲新编的世俗娱乐的趣味取向来看,时尚乃是以市民趣味为根本,体现了戏曲的市场行情对于新编创作的决定性的影响。其间还包括市民报刊在内的大众媒介的参与,更使得这种市民趣味渐趋放大。或者,也正是由于大众的热情参与才足以营造出戏曲观演的热潮。应该说,海派京剧的兴盛,无疑与此有关。而一些地方剧种,如越剧、黄梅戏等,艺人们从走街串巷、撂地为场到冲州撞府、走进城市,也无不以大量的适合市民趣味的新编剧目为号召,形成相对稳定的城市观众群。
以审美娱乐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如欧阳予倩在从文明新戏的沦落之后而投身皮黄,新编出一系列的“红楼戏”,在上海一炮走红),某种意义上,走的就是一条回归到审美娱乐的价值本位之路。再者如梅兰芳也曾经历了一个从热衷于新编“时装新戏”到专注于古装戏的编演的回归;梅兰芳所编演的新戏(包括古装戏和时装戏),演出后有的成功也有的相对不成功。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无论是其中《邓霞姑》《一缕麻》等“时装戏”,还是《洛神》《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古装戏”,其创作的动因与其说是用来“醒世易俗”,还不如说是与时代的审美风尚更为直接相关。自1914 年7月始,梅兰芳首次尝试编演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接着又陆续编演了《宦海潮》《一缕麻》《邓霞姑》等。直至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梅兰芳还排演了最后一出时装戏《童女斩蛇》;其后,就不再编演时装戏,而转向了专注古装戏的编演。其中,特别是齐如山所主持新编的一些剧目(如《西施》《洛神》《晴雯撕扇》等)几乎都成了梅派的经典保留剧目,而那些也曾经有着不俗的演出记录的时装新戏则基本上绝迹于舞台。其实,不仅是梅兰芳,“四大名旦”都曾有为数不少的新编时装剧目,如程砚秋就有《花筵赚》《女儿心》《风流棒》等,但由于各种原因几乎都没能流传下来。所以者何?也大概都是与都市京剧观众的以审美娱乐为中心的趣味选择有关。
相比较而言,欧阳予倩所编演的“红楼戏”更是基于沪上审美娱乐的价值导向而得以风行一时。一方面,它既保留着传统戏曲的诸多品格,如人物自报家门的叙事性特色,另一方面,在剧本结构等方面汲取西方戏剧的特点:情境集中,戏剧性加强,并采用了新的演剧形态而自创一格。如欧阳予倩谈到自己的“红楼戏”在分场分幕上的特点时就指出:“我所演的红楼戏,虽然是照二黄戏编的,却是照新戏分幕的方法来演。因为嫌旧戏的场子太碎,所以就把许多情节归纳在一幕来做,觉得紧凑些,而且好利用布景。”[注]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正是由于欧阳予倩在总结自己从事文明戏及时装新戏的编演经验的基础上,有效借用“文明新戏”的艺术经验和编剧形式,才使他的“红楼戏”唱做俱佳,结构严谨,感染力强,极一时之盛,为海派京剧探索创新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所以,政治导向和趣味导向,构成了新潮演剧以来戏曲新编的价值取向与艺术追求的两种不同的路向,而体现出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当然,这两种路向又不是互不相干,而是互有影响且纠缠不清,左右掣肘,互为轩轾,甚至某种情况下还可能表现出一些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戏曲的现实走向与历史进程,成为20世纪戏曲似乎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
四、内在张力:戏曲新编的文化矛盾
与20世纪以来“唯新是尚”“不断革命”的时代风潮相一致,由戏曲改良而来的新编创作也一直在政治和艺术、教化与审美之间摇摆不定,构成了政治与市场等二元对应的张力格局,制约着20世纪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走向。在这一历史进程与逻辑进程当中,如果说,新潮演剧中的戏曲“新编”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地适应新的时代、征服新的观众的过程,那么,随着历史的演进,在政治或市场的二元格局中,由于思想启蒙、抗日救亡等各种现实的权力因素的介入,戏曲新编更是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意识形态或观众趣味的顺从或者反抗。
其实,由清末民初新潮演剧所开启的戏曲新编,正是顺应着这一历史潮流而兴起的。但是,它所隐含的文化矛盾也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当“新剧”作为代表西方文明的新的艺术样式传入中国时,不仅满足了沪上观众趋新求异的观赏欲望,而且即使在“文明戏”因趣味低下而趋于糜烂之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还是对永远只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虽然这种批判对于民间传统深厚的戏曲观演的格局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触动,但对于其后的戏曲新编的思想倾向还是有着明显的影响的。
如前所述,京剧舞台上随着梅尚程荀等“四大名旦”的涌现以及欧阳予倩、田汉等新的戏剧工作者的加入,他们始终都在进行着戏曲“新编”的尝试。其中,既有着对传统剧目的再创作,也有着新题材新剧目的大胆编演,比如欧阳予倩就是以“红楼戏”等“新编”而享誉海上;而梅兰芳则是以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的“新编”创作而盛极一时。到了1930年代,为了宣传抗战,田汉等新剧家更是进行了“旧瓶装新酒”式的大胆尝试,当然这种“新编”表现出如此急功近利的色彩,以至于艺术上几乎乏善可陈,但是却为延安平剧院《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新编戏”的创作开了先河。
与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遥相呼应,1950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为适应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的需要,展开了包括“戏改”在内的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其中“戏曲改革”运动也就是对于中国戏曲自身的艺术传统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清理。随着“戏改”的深入,戏曲新编得到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及体制上的支持,从“一曲戏救活一个剧种”到“大写十三年”,无疑都透露出戏曲新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现代戏”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新编历史剧”也明显地被赋予某些急切的现实政治宣传的使命。虽然诸如《李慧娘》(孟超)及《海瑞罢官》(吴晗)甚至同时期的《海瑞上疏》等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但是在创作模式上它们原本都是响应领袖号召,属于政治引领与观念先行一类。而这种新编创作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取向与艺术追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样板戏”创作当中得到空前的强化。“样板戏”的新编,无疑延续了戏曲改良以来的政治教化先行的价值取向,以现代革命题材的“新编”来表达鲜明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典型的政治文本。“样板戏”作为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杰姆逊语),已然深深地打下了戏曲改良以来的历史烙印。它以表现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为导向,以“革命历史”题材作为当时典型的政治文本,显示出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巨大裂痕,成为所谓“政治实用化”的显例。其间,现代革命题材之所以在新编创作中一直被强调,也是与这种过分“实用化”的价值取向分不开的。其实质也就是为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舆论的导向而加以“新编”。可以说,这种实用化之“新编”主要服从于外在目的而不是来自于创作者的内在的表达的需求。或者说,其实用化的立场选择,根本上就是属于“工具论”的。从而,这种“新编”创作就难免给20世纪戏曲带来明显的历史缺憾。
与“样板戏”相反,随着“改革开放”与拨乱反正,新时期以来的戏曲新编,则秉承了新潮演剧以来的市民趣味价值取向,既积极传承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传统,又明显呈现出对于个体精神觉醒的诉求,从而在文人参与及市场导向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和创新。以《曹操与杨修》《金龙与蜉蝣》《董氏与李生》《骆驼祥子》《西施归越》《金锁记》等为代表,在文人情怀、历史观念以及女性意识等诸多方面都为戏曲新编开拓出新的境界,显示出戏曲现代化的努力与实绩。当然,这里的所谓“戏曲的现代化”,既不能等同于服从当下意识形态需要的“政治化”,也不应等同于贴上“现代主义”标签的“形式化”。就当今的戏曲生态而言,需要背负传统而艰难前行,它既离不开传统的认同,也离不开直面当下的观众。
如果说,戏曲的传统需要继承,那么可以说,戏曲的创新更离不开新编。从而,与传统戏的传承同样重要的,是新编戏的不断的编演。以新潮演剧为开端,20世纪的戏曲新编,既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无数的历史缺憾。进入21世纪,伴随着昆曲、京剧等戏曲样式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充分尊重戏曲传统的同时,对于新编创作也无疑提出更高的要求。
五、结 语
很显然,新潮演剧中的戏曲新编,对于后世的启示价值,不仅在于剧目的新变,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所代表的戏曲现代化的立场与姿态。京昆艺术通过新编创作得以传承,一些地方剧种(如秦腔、川剧、评剧、越剧、黄梅戏等)也通过新编创作而得以振兴或焕然一新。因而,其影响所及,就不仅限于戏曲创作实践经验上的得失,更有历史经验上的启示,美学观念上的更新。所以,尽管“新编”情形多样、性质有别,但是,自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以来,“新编”已然成为一种戏曲创作常态。至今,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的洗礼之后,戏曲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面对当下以至未来的观众?与传统戏的“原汁原味”的搬演有别,“新编”,似乎更应该成为戏曲现代化实践的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