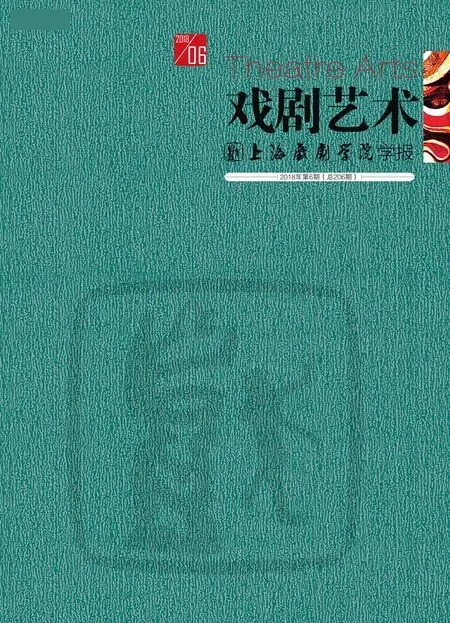清代乡约族训禁戏的次权力话语与传播禁止
■
清初以来,接续明代依托士绅展开的地方性正俗禁戏,基于乡社自治、族群教化而展开的礼俗禁戏,不仅在苏州、杭州、南京、松江、山阴等江南地方不断发动起来,在山西、徽州、河南、福建、江西、广东等戏剧撰演重地亦蔓延开来。这种禁毁戏曲演剧的文化政策,于基层社会的推进实施,呈现了强弱起伏的递减过程。地方政府、乡约保甲、家法族训发出的禁毁演剧舆论,对民间戏曲所依赖的乡社公共活动空间及演剧人群进行分层切割与约禁。这些存在于地方文献中的禁戏言论,虽有王利器、陆林等一些学者做过部分辑录[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列有乡约类;陆林:《宋元明清家训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有家训类辑录。,但尚有大部分史料隐没在戏剧史的边缘地带,尤其是禁戏的规约应力之于演剧事件产生的文化分际与社会影响尚未引起更多关注。由此出发,考察作为官方文化政策的辅备的禁戏,对基层社会的文化控制,进而追踪不断从禁戏语境中溢出的基层社会生动丰富的世情面相与民间生活的日常愿景,以及广播生息、禁而不止的民间演剧传统的生成过程,可以进一步拓展道德教化、礼乐下行与戏曲传播禁止的诸多问题思考。
一、农本社会的崇简安生与禁戏的次权力话语
在中国古代农本社会里,戏曲为基层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公共交流的空间,对于被捆绑在土地上耕种收获、辛苦操劳维持营生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个被打开的自由空间里,普通人有了一定的闲暇可以暂时释放积存的劳顿和人生煎熬——忙过了之后如何应付“闲”,才成为下层人安生立命的大问题,而戏场提供了某种精神出口。如何安顿在土地上劳作的下层人、穷人的闲暇生活,一直是地方政府的盲点,也是困扰教化下行的一大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往往就演剧带来的社会问题,借力于地方官的“清明”、农本社会的崇简安生之论,辅以处罚惩治之策,来进行禁戏劝惩。这种扰乱农事、破坏风俗的老调重弹,虽一时一地或许有震慑,然大部分时候,似乎也很难起到抑勒作用。
康熙后期的江西南安,有迟荆山司马《劝民歌》之十二劝,其中的“劝尔民崇俭朴,无益事休妄作,搭台演戏费空丢,延僧礼忏风殊恶……从今后崇俭朴,丰衣足食家家乐”[注]陈奕禧修、刘文叒纂:《南安府志》卷二十,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推导的即是演戏无益、简朴维生的化民之“术”。又如乾隆初年湖南宁乡令李杰超发布《告示》云“为禁约事,照得本署县莅任宁邑,已经月余,一切风土人情应兴应革事宜,靡不悉心”。在其列出的应革陋习中,“居丧之家,纠集亲朋,男女杂沓,或演戏开宴,或修斋设醮,演唱夜歌以图欢乐”[注]李杰超修、王文清纂:《宁乡县志》卷五,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欢声闹语颠倒日夜、孝事亲者全无哀戚,即被列为亟宜禁革的浮费蔑礼之举。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贡震《禁淫祠》细数:“建邑人民好鬼,祠祭纷繁,祠山之庙,城乡多至数十处。每元宵有会,二月初八有会,而各处神会集场,无月不有张灯演剧,宰牲设祭。每会数十百金不等,此外如五猖会、龙船会,俱系妖妄之鬼;观音会、地藏会,亦大开戏场,名目极多,浮费尤伙……知县到任三年,熟闻此风,历经谕禁……时届穷冬,恐故态复萌,现在禀请立石永禁,合再详悉晓谕……知县为地方人心风俗起见,仰遵功令,俯宽民力,不惮恳切开示,士民当共相戒勉,尽洗前此好鬼恶习,庶不负谆谆示戒之意……现已训示委曲开导,伏祈宪台给示立石永禁。”[注]胡文铨修、周应业纂:《广德直隶州志》卷四十三,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本。由此可知,建平一地“社会”繁侈,不仅正月有四十八会,有五猖、龙船、观音、地藏之会;而且逢会必集场演戏,举凡元宵会、神童会、冠子会、七圣会,以及高井庙、分流庙、高塘庙、鲁班庙集场,几乎无戏不成会;甚至按户科派、岁岁盛举,轮月集场,昼夜不息,甚至一姓排酒八百席,一族宰鹅二千双,买灯、宰牛、祭品置办一掷千金,穷极美观与醉饱。作为其地百姓打发日常闲暇的娱乐活动,演戏观剧成为缔结“社会”最有力、最热闹的核心事件。历任知县,总是从维护农事秩序出发,强调地瘠民贫,所产有限、雨愆米贵、年荒食歉、节俭撙节。殊不知这种冻馁无衣、破产穷愁、无益温饱的物力禁限,并不能对症解决下层社会普通劳作者的精神匮乏问题。人性释放的张弛之道,既作为教化下行治理生民的盲点,也同时作为基层社会禁戏的焦点,成为戏曲演出的一大禁忌。

举凡庙会、出殡、婚庆、赛神演戏,都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百姓日用节度的大事。一些在任地方官不仅严明教化、设法劝禁,甚至将斥禁演戏观剧作为方策要略禁锢人心、震慑民情。如高邑县江启澄曰:“信奉神佛,焚香设供,演剧征歌,费数十缗不惜也,谓之庙会。每乡村妇女连袂接踵,杂沓骈阗,闺阁为空,实为陋俗……停丧迎娶、出殡演戏,往往村愚习以为常,此尤大悖乎礼法者。”[注]陈元芳修、沈云尊纂:《高邑县志》卷二,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又如秦安县令打着圣谕广训旗号,以邑民才识短浅为由,将“每至三四月间,由城而镇,轮流演戏,遍集优娼”事,目为“广设陷阱,引诱良家少年,废业荡产、辱身败名……百务不胜其弊,四民咸罹其殃”[注]严长宦修、刘德熙纂:《秦安县志》卷一,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的大宗罪,重申教诚,严禁永绝。而光绪年间宜兴竟有治理地方者因“民以狡致贫者四:讦讼、呼卢、演戏、扮会”,公然宣称“民愚则使之智,民智则使之愚”[注]阮升基增修、宁楷增纂:《(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之一,光绪八年(1882)重刊本。。这些地方告约,总是将演戏扮会视为致贫取祸的唯一诱因,作为司风教者严禁力挽的治贫大任、愚民之策,不遗余力加以推行。
如此看来,上层的集权统制,利用教化下行,常常会借助禁戏的次权力话语,来辅政治乱、驭民治生。然而,在官方无法掌控的世俗闲暇生活里,通过基层社会组织下行的道德教化、礼俗整顿与抑勒世道人心之失的禁戏舆论,往往权力消隐、虚应故事。维系于一地官长到任、有心治乱之方官的行为,其制约与钳束限力或许在一时之任、一地之域产生影响,却很难维系长久抑勒、传播禁止的持续效应。一方面,礼上法下、礼遮蔽法的政策机制,对传播前点——与庙会、出殡、婚庆、赛神并存的演剧活动的禁止,与僭越守土衣食本分而“非分”演戏观剧行为形成了对垒,禁阻无力。另一方面,端心立耻、理政慑民的崇简安生之术,对接受后点——对闲乐、闹热、游赏、祈福的戏曲受众的禁约劝惩,与在地成俗的演剧传统形成一定规约限力,却无法抵挡日常习俗与民间观念的力量。
二、乡约保甲禁戏与地方自治应力
当地方政府注意到,由官长发布政令、下达告示、宣谕教导,无法有效管控隐没在权力结构网罗中的一盘散沙式的“个体子民”;要达到教化下行与禁戏舆论的相辅相成,还需要通过以乡约保甲制度缔结更为致密的基层社会组织力,方能形成禁戏合力,维持治政秩序,使得庶民遵从礼法。掌握基层社会舆论话语权的乡绅与地方文人,对地保里甲在演戏活动中的角色与作用的吁请与训导,就成为地方自治借重的重要中介话语。保甲制度,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为保障乡社生产生活秩序而形成的刑罚庆赏相及相共的地方管理组织。其所提倡的家族闾里日常相保相受、来往相周相宾、有难相救相葬的约条,作为一种上层权力下行的辅助手段,带有更多的伦理约束和自治色彩。演剧是践行还是毁坏保甲制约条?成为禁戏舆论发声的一个切口。
如雍正末年针对朔平一境违背文公丧礼,“置幡楼、设徘优、陈百戏”的悖礼之举,对随俗拜墓“多聚会敛供,各庙演戏,四时不绝”[注]刘士铭修、王霷纂:《朔平府志》卷三,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的祭扫习气,地方修志文人责以近党伤财、废业荡志而力主当道裁酌。除了这种醇化祭俗、维护乡社“生理”的地方禁戏言论外,明确针对演戏害农事而责成地方官禁戏的,是康熙中期余钰在陕西发布的一道输粮文——《邑侯花公上苑劝谕合邑输粮檄》:“就尔等积习相沿,最为糜费……如赛会迎神,穷工极巧,亦可已矣,而必欲演戏何为?天生为圣贤,没为明神,岂愿见侮俳优受嗤拙?……况赍盗诲淫,种种未便,官府明禁,捍然不顾,合巿乡计之,每岁不下万金……妙舞清讴、酣歌达旦,而一逢比较,尽皆挽之不前、呼之不应,以急公则称窘而不支,以自娱则垂槖而不惜,何尔等之不知义也!教化不行,风俗日漓,皆尔令之责。”[注]陈鹏年修、徐之凯纂:《西安县志》卷十一,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这一段话言在此而意在彼,名为劝醒“赍盗诲淫”,实为终饱上官口腹;名为教化知义,实为夺小民娱乐权利;名为禁戏劝奢,实为替县令催租纳粮。谆谆之下其实唯唯,督责之外别有用心。
乾隆十六七年(1751-1752),建平修志文人即提出,“夫阀阅名家,举动为一乡取法,果其公费赢余,用以设义学,请师训课子弟,赈鳏寡、恤孤独、周贫乏……较之以前人蓄积、族姓脂膏,浪费于神庙中,博数日酣嬉之乐,其得失何啻万里!望族果能行此,众姓自必从风。神会银谷,原系众姓赀财,即以分借众姓,薄收利息,积少成多,公择乡党中忠厚老成人主其事,有无可以相通,丰凶由此有备……地方去一大害、兴一大利……何用穷奢极侈,邀福于渺茫之鬼神为也?……伏祈宪台给示,立石永禁”。[注]胡文铨修、周应业纂:《广德直隶州志》卷四十三,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本。为去庙会演剧之“害”,兴士民百世之利,广德当地文人不仅督请当道训示开化、立碑宣禁,还希望发动地方望族、乡间名宿,节俭用度以周贫、捐出盈余以助学,为众姓取法;并建议推举持重有威望之老诚人居间调停,以神庙赛戏之公摊银谷,为有无丰凶之互助资金。从这条材料看,以里社人情与乡俗礼法约禁演戏,以保证庶众不虚掷钱财、一族清和祥瑞、子弟耕读有方,以转移嬉游流荡风气,是治理地方实务和稳定底层秩序的不成文法。礼虽不成文,但却高于法,这种礼上法下的约禁,显示了戏曲向下一路传播中礼俗禁戏、法不责众的具体情形。
在山西孝义,祀关帝赛戏亦被责为冒渎不义事,“邑人动则祀天地,村社多祀关帝,是犹庶人而渎公侯也。神岂歆乎?他淫祀不能悉数,公事固不宜懈,若如赛神演戏之类,则虽公不义。夫知敬神明,而不知敬祖宗,知畏官法,而不知畏父兄,则亦不辨之故耳”。[注]邓必安修、邓常纂:《孝义县志》卷一,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而《潞州府志》修纂者周再勋因“优伶怙势,横辱衣冠矣;土蠧枭张,倾危绅宦”,而引长子知县王巨源列禁条十二,其中“七禁因社敛钱,八禁夤夜诵经,九禁丧葬演戏”[注]张淑渠修、姚学甲等纂:《潞安府志》卷八,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都与禁戏相关。这些说辞都将演戏视为与乡社秩序背离的不轨行为,将参与人众视为失伦犯禁、毁坏乡风的不守法者,而加以儆戒责惩。
演戏对晚辈读书人的“危害”,也经常被作为戏曲的罪状罗列出来。乾隆年间江西《石城县志》曰:“邑中祠祀,春之日群集馂余,必演戏剧,遂至读书少年,就塾未及一月,借祭祖之名以观剧为事,诗书之气荡于浮邪,吟诵之声废于靡曼,失古人敬孙时敏之意,至袯襫之俦,尤以失时为戒。顾当农事方殷之日,废其耕耨、林立观剧而农荒,工商之伦,居肆贸?平时亦无敢舍业以嬉,一旦呼朋结伴,谑浪场下而工商荒。且院本多亵狎,观之适足诲淫,或曰‘演剧不限于祠’,何必祠之哓哓欤?……况以演剧之钱,于祖先嗣裔,照丁给发,益足以昭神庥,崇礼敦俗不两得欤?”[注]杨栢年修、黄鹤雯纂:《石城县志·舆地志》,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钞本。此论不仅认为观剧会导致读书人心志荡逸,学风萎靡,且以演戏造成失时废农、舍业浪荡之“危险性”,从演剧淫祀、观剧淫亵的角度一竿子打倒梨园。而《宁都直隶州志》亦有同样论调,“祠祀饮馂,必演戏剧,遂至读书少年就塾未及一月,借祭祖之名,以观剧为事,农事惰而工商荒,失时废业,皆由于此”。[注]黄永纶修、杨钖龄纂:《宁都直隶州志》卷十一 ,道光四年(1824)刻本。光绪前期陕西同州府更有地方舆论述及“少年子弟方在学舍,便已窃睹,或近地十余里有名优,则公然相率往观;及一上进郡城都省,以此二者为风流矣;及一宦达私署官廨,惟此二者为快乐矣……茶园非斋日无不演戏者,堂会则弗可计其数,通计一日戏费约不下四五千金……即此而推赌与戏之耗费,无益于世”。[注]饶应褀修、马先登纂:《(光绪)同州府续志》卷九,光绪七年(1881)刊本。这里指出子弟好戏、上进宦达以优伶为乐,造成戏费赌资耗费情况。县志的记载,看得出演剧对地方社会的深层渗透与无所不在的影响,引起了地方教化言论对禁戏的关注;也同时显示了演戏观剧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务自治的重头和难题。
嘉庆年间,曾有团会演戏被责查:“聚众之风,应严禁也。教匪久靖,团练久撤,查有好事之徒,仍然设立团会,敛钱演戏,吓诈乡愚,肆行无忌,凡有此等,该约保即赴县首报,据实严办。”[注]纪大奎修、林时春纂:《什邡县志》卷十,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明代取消了源于唐代的团练使,改以按察使、兵备道分别统管团练事务。清代广设团练,职官却无团练使之设。因嘉庆间白莲教起义,八旗绿营腐坏扰民,合州知州龚景瀚曾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建议设团练乡勇,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编查保甲以自保地方。应该说,团会在历史上,是保甲制度的一种有力支撑。保甲制度所依赖的训导劝化一旦无所奏效,团练组织乡勇就成为一种半军事化的地方社会管理保证。而此处所言敛钱演戏,则被认为是借团会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仅不能借团会敛钱,团会之公费更不能随意挪用做无益事,如咸丰年间《平山县志》《团练事宜》附录曰:“每庄旧存公项,均宜提归团练经费,不得演戏以作无益之举,如违禀究”[注]王涤心修、郭程先纂:《平山县志》卷二,咸丰四年(1854)刻本。,演戏因其无益营生、浪费钱财而被屡禁。清代后期,一方面,禁戏施之以文武并重的情形在不断收紧;另一方面,以乡约保甲辅之以团练乡勇的措施,亦未能遏制戏曲在乡间社会的传播。如湖南益阳“乡村淫祀,藉祭杀牛,一神数祭、或数十祭。一祭杀数牛、或十余牛不等。又有上痞招集匪徒,假敬神为名,演戏赌博……其害有不可胜言者。节经前县示禁,其风稍息。犹恐故习未能尽除,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各里团甲、衿耆人等知悉,嗣后务直实力稽查……如容隐不报,察出一并重究,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注]姚念杨修、赵裴哲纂:《益阳县志》卷六,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而遍及乡里、依年节习俗和民间祭祀而几无时歇的神会演戏,则成为乡社保甲重治的对象:“春秋祈报,季冬行傩礼也;而乡曲间藉此诵经演戏,致无业游民,开场诱赌,此岂复礼意耶?近则严饬保甲,申明连坐之条,庶稍知儆。”[注]高大成修、李光甲纂:《嘉禾县志》卷十三,同治二年(1863)刻本。祈报乡礼中的合法演戏,因带来地方无法管控的流民赌博等社会问题,被冠以非法祸乱魁首罪名,成为地方官礼下法行、武力弹压,整治农功物命、匪贼盗源的切口。
以乡约保甲做禁戏呼吁,江苏无锡人余治(1809-1874)用力最著,其五应乡试不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开始收集善书章程成《得一录》,后得同道资助于同治八年(1869年)辑刻。《得一录》收录数篇乡约戒戏、保甲禁戏之文,《宣讲乡约新定条规》云:“行书本局奉宪收毁淫书、淫画,吊销板片,酌量给价。另立一碑,奉宪永禁花鼓、摊簧演戏,并禁诲盗诲淫等戏,如违立提严办。”[注]余治:《得一录》卷一四,同治己巳年(1869)刊本,第14页。《保甲章程》云:“乡间聚赌渔利,引诱愚民、草窃奸宄皆起于此,甚者唱演摊簧,聚引博徒,外来奸民,尤易混迹,最为可恶,永宜禁止。”[注]余治:《得一录》卷一四之二, 同治己巳年(1869)刊本,第2页。这些村规乡约、立议呈文,都提及敦促保甲禁戏情形。余治殁前数月致江苏廉访应公《教化两大敌论》,谓淫书宜毁,淫戏宜禁,“是二端者,一则登诸梨枣,毒固中于艺林,一则著为声容,害且及于帷薄。在作之者固属丧心病狂,在刊布点演者尤属寡廉鲜耻……此夏廷之洪水也,此成周之猛兽也,此人心之蛊毒,政治之蟊贼也,此圣道之荆榛,师儒之仇寇也”。[注]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二,同治己巳年(1869)刻本,第13页。余治禁戏不遗余力,或代笔呈公文、或议立禁锢局,或删抽换戏本,禁戏章程尽为地方政务发明设局禁戏助力:“江苏巡抚部院丁奏请严禁淫书,缴版焚毁,沪城又增设安怀局、扶颠局,其规约大抵皆先生所条陈也。”[注]卢冀野:《朱砂痣的作者余治》,《文学》五卷1号,1935年7月,第276-284页。
时至清末,基层社会的乡约保甲虽未形同虚设,其对乡社生活的规约与应力也大大减弱,而民神崇拜因庶众寻求精神庇护而风从蚁附,民间祭祀演戏依托各种会社活动依然异常活跃。如吴思祖《香会谣》所言:“堪骇颓风专尚鬼,香会纷纷干法纪……一人纠十十纠百,百千亿万将无极……连村金鼓鸣不绝,竖标建长扬旌旗。俨如军行限时刻,分行列队刀枪列……更敛民财灾土木,神祠十里一嵸巃。每逢一庙神诞节,高台演戏镫篷结……打降白占寻常事,不怕官司百度过……呜呼!赤眉黄巾与白莲,皆从此等为之先。”[注]夏宗彝修、汪国凤纂:《金坛县志》卷十四,光绪十一年(1885)活字本。虽然忧心地方风俗者厉责香会尚鬼,土豪霸市,演戏会带来盗赌酿祸、打降白占,甚至地方暴乱,但不可否认的是,神戏、台戏、宗戏在乡间风靡,恰恰说明随着集权瓦解、地方势力崛起,滋生于底层社会的民权意识,渐渐凝聚成一种不可阻挡的社会力量。深忧恐虑者不得不搬出上谕广训来镇服,如“国家律典,禁烧香聚众之行……与其以有用之钱,妄祀泥形木偶、杳冥不可知之神,何如积谷贮粮、救荒歉于不可必之天乎?夫神道设教,古有明训,宁禁尔等之不祈报耶?……纵日日设醮演戏、建庙念经,神方降之百殃,又何福之能祈也?”[注]樊增祥修、田兆岐纂:《富平县志稿》卷四,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这种站在上层立场声讨愚民祈神求福之陋,搬出屯粮救荒之策统御民生的老调重弹,已无多大规戒意义了。
因为“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典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清光绪中吴县潘氏刊本。湖南文人刘献廷这一番言论,其实道出了观剧作为庶众性天之乐、演戏作为世间正当一事、祀神演戏作为人心顺道之“春秋”“典礼”的道理。当民间生活的闲暇逸乐,在禁戏语境中不断鲜活可感地涌现出来;也就是说,演戏观剧不断浸润世俗生活,既作为日常游戏娱乐方式,也同时内化为下层民众的精神依赖和文化传统,建构了属于底层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社群图景,禁戏实在也难以发挥什么作用了。
三、方志载记族群演戏与礼俗禁戏悖论
中国古代的族训文化,作为一种与基层舆论相辅相成的次权力话语,对族群、族事、族风有着一定规范和约束力。而鉴于俗变风移而带来的世道之失、人心之乱,明清家规族谱及与宗族相关的方志史料,对族群关系的有序建构,宗族文化的传统保持,族人子弟的行事作为,显现出较之前代更强的教化规训意味。在族群聚会性活动中,演戏以及演戏场所的开放性可能带来的危险祸乱,带来各种家庭问题、甚至灾难悲剧,引起治家者以及地方治政者的关注和重视。通过族训及地方文献的族群活动记录,可以从当地文化传统、宗法观念中了解祭祖演剧和迎神赛会对家族生活的影响——演戏作为敬神拜祖的一种形式,增强了家族凝聚力,扩大了宗族社会地位,所以宗族的老宅家院里,有祠堂即多有戏台,而撂地为场、搭台演戏,更为常见。演戏作为敬神拜祖的一种形式建构了当地的宗法观念和族群信仰;与此同时,演戏带来的逸乐嬉游、甚至盗赌奸宄,也成为族训禁戏的由头,这就形成了演戏与禁戏的一种悖论。
一些地方史料中,记录着乡绅大族的演剧活动情形,族群成员成为蜂拥而至的观剧者,地方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闻风倾动、观剧痴迷,如江西瑞金“有钟翁者,喜观剧,闻某处演戏,虽远在十数里外,盛暑行烈日中,或天雨泥泞,衣冠沾渍”而不惜也,且每入戏场必从头看到尾,“从朝至暮,或自夜达旦,目不转睛,人与之语,皆若勿闻,可谓有戏癖矣”。[注]郭灿修、黄天策纂:《瑞金县志》卷八,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而方志载记族群活动中,亦多有观剧演戏之逸乐、与族训禁戏绳之逸乐相伴随的现象。如乾隆时李调元曾作《七月初一日入安县界牌闻禁戏答安令》:“言子当年宰武城,割鸡能使圣人惊。前言戏耳聊相戏,特送弦歌舞太平。昔日江东有谢安,也曾携伎遍东山,自惭非谢非携伎,几个伶儿不算班。”[注]李调元:《童山集》诗集卷三十六,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1825)增修本。这首诗借孔子于武城听琴瑟唱诗之音、与言偃戏言僻地俗淳不用礼乐教化事,以及谢安隐于山阴之东山、携妓嬉游事,调侃自己比不上谢安风流。言下之意是,他在安县界牌处听闻地方发布禁戏令,不禁想到要给县令呈书一封,告白自己只有几个伶人,连戏班都搭不起,哪里值得禁呢?
除了外来戏班演戏有禁忌,禁宗族成员子弟染指戏曲外,一些方志载记地方演剧活动时,亦将演戏带来的风俗丕变与生事窘困,作为礼俗教化的儆戒以达族人庶众。如“儒门世教相承……惟尽哀尽敬,发乎天性,设致祭,一遵家礼……比岁以来,有富家沿袭营伍他方之习,集群演戏,累主家供其饮啖,哗于庭堂,谓之孝剧……随淫朋而欢笑,伤教败俗,莫此为甚,是亟宜惩革者也(以上增订府志)”[注]陶易修、李德纂:《衡阳县志》卷五,乾隆二十六(1761)刻本。,此论以儒家哀敬之说,提倡尊家礼、革淫风,强调家族内部事务管理,要从五服宗亲守丧之制,指责集群演戏,孝剧不孝。而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讲到一位理政绍兴的顾淡如先生遇一老妪,问其官贤否,妪答官好却有一件恶处,就是每年春日演戏,此官到来禁不复作。顾先生安慰老妪说,不要怪他禁戏,因兵燹惜物力故也。与其看一日戏,费钱数百文,不如冬日制一新棉袄,身着敝衣的老妪一笑而去,可见地方官以禁戏维生劝民之一斑。正如地方文人论《禁戏》所言,“盖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戏以取乐?无论向隅者所不愿闻,恐天地神明亦必不佑矣”,此论不但以神明昭昭告诫,申言禁戏是为省飞济民,且明令搭台燕宾演戏者,每日罚谷十石,入救济仓,“既可化无用为有用,亦可变游惰为勤慎矣”。[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十一,乾隆刻本;又见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户政》十六,光绪十二年(1886)思补楼重校本。其实,这种制衣罚谷的禁戏言论本身既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是穷勿演戏?还是演戏致穷?演戏则衣食乏、禁戏可饱暖丰?正如《聪训斋语》所言,不喜观剧者之老妻,想为其六十寿搭一台家庭戏场,其以“一席之费,动踰数十金,徒有应酬之劳而无酣适之趣”,建议以此费制衣施道路饥寒。但述者接着又说不演戏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优人为“轻儇佻达之辈”,潜移默夺流于匪僻,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注]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二,光绪九年(1883)序仁和葛氏刊本。所以,相比于演戏致穷对观众的有限警戒,似乎将优伶演戏酿乱作为禁戏由头,具有更明显震慑意味。如康熙间广东新会的许万可“佣保于谭时,谭有戏班,呼可随行,入北洋贼寨演戏,适官兵捣贼巢,可混死于兵”,其妻张氏“闻变,同翁姑寻至寨所,求可尸不得,归绝饮食,哭不欲生,姑从容劝慰之,张惟泣而已,至可卒哭日,遂以缝衣线结绳自经死”。[注]王永瑞纂:《新修广州府志》卷四十四,康熙钞本。丈夫因喜欢看戏,追随戏班陷落贼巢,死于乱兵交战。其妻欲寻丈夫全尸不得,亦绝食自经。这种因嗜戏观剧导致连环家难,被县志记录在案,对于一般乡人庶民具有较强的劝诫作用。而演戏间隙发生奸盗拐骗之祸患,更在市井乡间引起舆论大哗和人心震荡。又如“许氏,名萓英,金山乡人,素习女红,不苟言笑,年十九适载升。甫二月,载演戏,姑嫂辈邀出观,英谢不往。独处一室,升堂兄龙乘机欲淫之,英怒喊不从,泣诉夫姑,耻污妇节,必欲一死见志。防护者七日夜,一夕沐浴更服,瞰夫鼾睡,潜行自缢,竟如初志”[注]宋良翰修、杨光祚等纂:《乐平县志》卷九,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虽然后来推官、知县详具抚台知府,载龙置法毙于狱,许氏得旌表,但女性因演戏遭侮不得不寻死的事实,名节对女性身心、生死的操弄绑架,对乡庶或有更多心理慑服。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因演戏观剧而发生轰动大案、酿成大狱。如浩歌子《萤窗异草》所述光绪年间的定州大狱,“直省定州……时届秋成,其岳家村中演戏侑神,适民母疾小愈,岳浼人言,欲迎女归母,许之,妇遂盛妆而往”,贪看剧不愿返家,“时杂剧正盛,金鼓雷鸣,满场喧哄。妇凝睇已久,渐忘形骸,频以一足垂下,民知其无备,仰而企之,竟褫其只履”,失履之妇归家,遭到丈夫诘问怒骂而悬梁自缢。[注]浩歌子:《萤窗异草》二编卷三,清光绪中申报馆排印本。官府行案,一桩少年杀僧劫妇、觅鞋被捕的凶案方浮出水面。这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一桩广为流传、事有所本(直隶定州当地村民严阿大受不了酷刑终于招供)的民间公案。初读此段,觉是风流加公案套路,却没想到演戏观剧成为故事的重要介入因素。岳家村演戏侑神,新婚少妇有风姿,盛装归宁,贪恋观剧。丈夫潜行戏场廊庑下,趁少妇凝睇观剧,伺机拽下一只绣花鞋拟以羞辱泄愤。不曾想到这只戏场里失窃的绣花鞋,引发一连串蹊跷怪事,酿成悬疑大案。少妇失履,以为是轻狂荡子调戏,情急中佯告父母遣仆牵驴送回,以免妇节大失。鱼龙混杂的戏场,给女性观剧带来不测和风险,已将少妇推入险境,更加返家遭丈夫喝问谩骂,无地自容至悬梁自尽。可悲的是,妻子悬梁的一刹那,丈夫竟想到移尸投井、要挟岳父、反控县衙。更其意外的是,助救少年竟色胆包天,以巨石砸死老僧,威逼诱拐少妇。人算不如天算,寻履少年中计被捕方真相大白。
此段记述后有“外史氏”评论:“一履之微,遗祸至此,要皆欢场,实阶之厉也。盖妇不贪欢,则夫不至于窃屦;夫不窃屦,则妇亦不至于投缳;妇不投缳,则僧与少年皆可以无死。然非贤宰官得此一钩,则僧以救溺而死,妇且背夫而逋,狱将不可解矣。卒以履之故,破此疑团,古人有绣履传奇,犹不若此事之诡异。”[注]浩歌子:《萤窗异草》二编卷三,清光绪中申报馆排印本。一只绣花鞋引发的大案,虽然对乡人庶众戏场贪欢起到儆戒作用,但岳家村演戏祭神,小媳妇看戏贪欢,村丈夫戏场施计,奸恶人夺命连环,都因乡间演剧活动引起,可见戏场对庶众生活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定州大狱,一方面作为礼俗禁戏的失控案例,看上去强化了演戏致祸的礼法规约;另一方面,也作为观剧逸乐的民间生活和戏场活动的另类趣闻,形成从民间传闻到奇事公案的书写序列和传播效应。
道德教化作为家国同构的隐性社会机制发挥的一种作用,是在礼乐下行的过程中建构覆盖民间的意识形态。然而,礼乐下行的过程,在民间社会很大程度上存在礼乐分离的现象。强调和推行礼制,成为族训乡规当然的伦理支撑。而当乐溢出了礼与法的藩篱,甚至在上层看来与礼法背道而驰时,以祭祖、合社、睦邻、息讼等禁戏措施教化族众、维持基层社会的秩序,即成为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谋求乡邦和谐、族群永续的次权力选择。然而传播前点和接受后点的管控失效,礼大于法、公权私权的借位混淆,不仅带来次权力话语的应力减弱;治生预防与道德追惩的逻辑悖论,案例新出与旧规重申的隐性困局,亦并未造成演剧活动的传播禁止,反而使得礼俗禁戏舆论传而不播、禁而自止。而演戏观剧,作为乐的一种独特形式,寄生于民间社会,不仅在礼乐下行中明显分野,而且在礼乐、礼法、礼俗之间不断迁移剥离,游走在家国意识形态的边缘,生成族群活动的流动景观和移风易俗的鲜活镜像。演观风从、越礼逾制、群聚狂欢、游艺逸乐、玩日闹夜、嬉谑无度,形成特定的民间演剧传统,虽受到来自上层的禁毁、地方教化的贬抑,却依然在民间广播生息、禁而不止。而不断从禁戏语境中溢出的基层社会生动丰富的世情面相与日常愿景,则从另一层面显示了闲暇逸乐之于庶众生活的意义、并缔结了乡社文化的某种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