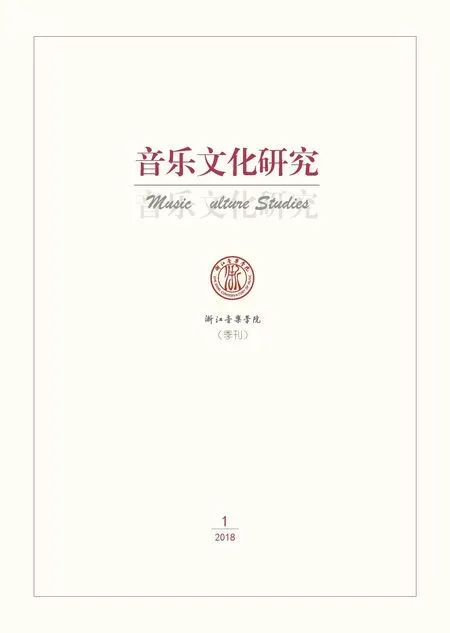《浙江戏曲音乐》序言
洛 地
本书,题名《浙江戏曲音乐》,是一部按“戏曲音乐腔调系统”编写的戏曲音乐专著。
按“戏曲音乐腔调系统”对戏曲音乐作总体性考察,对戏曲音乐进行梳理、分类、别种,我们不清楚以前是否有人曾经这样做过及做得如何,至少对我们来说,是无前例可循的“新”的尝试。今天,在本书完稿,提笔写这篇《序》的时候,回顾这四年多的历程,面对这部书稿(未能称尽我们之意的书稿),想象今后的可能,愿将我们曾遇到和还想着的一些问题,陈述于诸位师长、同道和读者前,以求讨论、共同思索和批评指正。
戏曲音乐,是戏曲音乐,本书既是一部戏曲音乐专著,当然是著述戏曲音乐,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它恰恰成了问题。在这四年多时间内我们首先遇到的、也是使我们大耗心神的就是这个问题:一部著述戏曲音乐的专著或者说“集成”,是不是、应该不应该或者可不以立足于戏曲音乐本体,从戏曲音乐实际出发,按戏曲音乐自身内部结构进行分类别种,反映其发展脉络、结构层次及传流现状等来编写?具体地说,是可以或应当按“戏曲音乐腔调系统”编写;还是只能按所谓“剧种”编写?经过几番周折,由于同志们的工作实绩,浙江艺术研究所(领导陈西斌同志)的理解,同意我们在编写一部按“剧种”分类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的同时,编写一部按“调腔系统”分类的《浙江戏曲音乐》——就是本书。过程间的种种,今天已不必赘述。从学术上来说,是对事物的认识,对戏曲音乐的类别及如何进行分类的认识问题。
(一)事物,一大群体事物之有类种之分,是事物自身所具备的。对事物进行分类,并使与事物实际趋相一致,是人们正确地认识事物,即对该事物的认识进入“科学”的第一步及其归结。
分类,对戏曲音乐与对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其目的是使事物系统化,即对事物的“系统”的认识。
“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历史性等特性”,其中最根本的,决定系统之为系统的是“结构”——“结构是系统的本质方面”——事物的整体构成、层次等级、历史征象等都取决于其结构。戏曲音乐是一大群体性事物,对其自身具有的系统的认识,即对它进行分类,只能按其结构,也就是我们时时所说的“透过现象求本质”。当我们将尽可能齐全的戏曲音乐资料,透过其各种繁复斑驳的现象探求其结构的时候,也只有当我们明了其结构的时候,我们就能也才能对它进行分类。结构——系统——分类,是认识事物及其类别的应有的思维或者说基本的知识。
戏曲音乐,其本质构成是音乐,其结构即为音乐结构,其系统为音乐系统,其分类当然是音乐之类别。
(二)一事物之成为该事物,在于它具有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征。一事物的特征是他事物所不具有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特征了。对事物的类别、种别也同样,事物的每一类、类下的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特征,此特征在该类、该种是必具的;而在与其同层次的其他各类、各种则是不具有的。事物类别的本质特征是其结构特征。如“高腔”“一人滚唱,众口接腔”的腔句构成为其结构特征,“昆腔”以“‘字腔’与‘过腔’的组合”的腔句构成为其结构特征,二者相区别;而“高、昆”二腔又以同用长短句文体曲牌、同以“腔句构成”为其音乐结构特征而为一类“南北曲腔”,从而与以“唱调及唱调连接”为其结构特征的“乱弹诸调”相区别,与以“起平落”为其结构特征的“(唱说)摊簧”相区别,等等。
共同的音乐结构形成一个音乐系统,不同的音乐结构形成不同的音乐系统,包括大系统和小系统、母系统和子系统,无不以结构为其特征。我国戏曲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剧唱往往用“腔”或“调”作为称谓,不同的剧唱往往称为“某腔”“某调”。音乐结构的异同,形成有层次的、有类别种别的“腔系统”“调系统”,统称“腔调系统”。并不是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所有的对戏曲及戏曲音乐的称谓都具有“系统”的意义,然而,历史已为戏曲音乐的类别即“腔调系统”提供了可资应用的某一些称谓。事实上,历史对戏曲音乐已曾作了某种程度的归纳,使某一些称谓实际上已渐具有了一定程度上“腔调系统”的含义。如:“高腔”“昆腔”“乱弹”“摊簧”等。然而,它们往往是自然状态下趋成的一种笼统的概念,未曾在理论上予以确定和规范,更不曾从“结构”这个“本质方面”去把握戏曲音乐“腔调系统”的层次性和整体性;更者,又有近几十年来尚未科学化的“‘剧种’论”逐步在归纳、形成过程中的系统化的自然趋势受到了干扰。如“高腔”原本是个“腔系统”概念,其下有各“路”高腔(如“西安高腔”“西吴高腔”“松阳高腔”等),它可以单独成班,也可以与他者合班,其关系本是很清楚的。然而,在“‘剧种’论”,每一路高腔都可以成为一个“剧种”,又都可以不是“剧种”,前者如“松阳高腔”,后者如“西吴高腔”;而在某些“剧种”中,又可以包含着有高腔,如“婺剧”。在“婺剧”中,高腔成为一种“声腔”(“婺剧”有所谓“六个‘声腔’”),而且在“婺剧”的“高腔声腔”种又可以有三至四种“声腔”:“西安高腔”“西吴高腔”“侯阳高腔”和“松阳高腔”。于是,松阳高腔便成为:既是一个“剧种”,又是一种“声腔”,又是另一种“剧种”(“婺剧”)的六种“声腔”中的一种“声腔”(高腔)中的四种“声腔”中的一种“声腔”。又如“昆腔”原本也是个“腔系统”概念,因是否运用“水磨”而区分出“正昆”“草昆”两支,各支下有多路昆腔,可以单独成班,也可以与他者合班;本来也是很清楚的。然而,在“‘剧种’论”,它是一个“剧种”昆剧的别名;同时,这个“剧种”中又有许多“剧种”,曰:“苏昆”“北昆”“浙昆”“金昆”“甬昆”“武昆”“永昆”等;同时,它又是许多不同“剧种”中的一种“声腔”,如“婺剧”“瓯剧”“台州乱弹”“平调”等;又者,“金昆‘剧种’”全同于“武昆‘剧种’”,又全同于“婺剧‘剧种’”中的昆腔“声腔”等。以上仅举高腔、昆腔两例(也还未说全其纠葛),其他都无不如此。
事实是,我们之所以会按“腔调系统”编写这部《浙江戏曲音乐》,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打算的,也不是从“分类学”角度提出来的,而恰恰是先按“剧种”“剧种音乐”编写《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因遇着了如上所述的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才对编写体例问题、概念限定问题、特征问题等引起讨论和考虑。考虑的基点是什么呢?是《集成》总部对编写《集成》提出的总要求:“史料性、全面性、科学性。”按我们的理解:
“史料性”,不仅是指资料的翔实可靠,而须使本书具有“系统的‘历史性’”。“全面性”,并不是罗列现象,而是须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科学性”,就是“分类”——“系统”的“层次性”和“结构性”。从结构——层次——系统——分类,才能反映历史,通贯整体;从而反映总体面貌,“类”,是“整体”内的“类”;“种”,是“类”下的“种”。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去罗列一个地域内(如浙江省)有哪些个由“剧团”组成的所谓“剧种”和把诸剧团使用的音乐称之为所谓“剧种音乐”;无论该著述是不是题名为“集成”。
(三)戏曲音乐、浙江戏曲音乐的类、种。
这里首先的问题是,浙江戏曲音乐是否具有“整体性”?回答是肯定的。
众所周知,我国民族戏剧的成熟,其标志是南宋时的戏文,戏文首成于浙江——宋元之际的刘勋(公元1240—1319)其《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有云:“至咸淳(1240—1319),永嘉戏曲出。”这是“戏曲”“永嘉戏曲”在文籍中的首载。元灭南宋(1276)后,元曲及元曲杂剧兴起,浙江杭州是其中心——今存《元刊杂剧三十种》,其“大都新编”者仅四种,在“古杭新刊”者有八种,而“大都新编”四种之一的《东窗事犯》系据《西湖旧本》①;这可为说明元曲杂剧以杭州为盛之一斑。集“南戏、北剧”于一身的我国民族戏剧之大成的传奇,其“鼻祖”是浙江人高则诚的《琵琶记》,其“绝唱”是浙江人洪升的《长生殿》,在自明至清(初)的“传奇时期”,署名剧作家中浙江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浙江又是我国戏曲理论的中心地,有我国第一部及第一批戏剧评论集——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有我国戏剧学的奠基人李渔及其著作《闲情偶寄》。清中叶后,“乱弹”渐起。浙江“南北十一府”民间戏剧蜂拥勃兴。直到近代,产生势淹江河南北的“越剧”。
至于戏弄性质的“民间小戏”,自唐五代以下直至如今遍布全省。②
在戏曲音乐,古代无乐谱传留,按现今有实际演唱可据的,浙江有元曲杂剧的“北曲”唱,有由“昆腔”演唱的《单刀赴会〈训子〉〈刀会〉》《昊天塔〈会兄〉》《金貂记〈北诈〉》《渔樵记〈北樵〉〈寄信〉〈相骂〉》《马陵道〈孙诈〉》《东窗事犯〈扫秦〉》《西游记〈认子〉〈胖姑〉〈借扇〉》及其他等等,尤为可贵的是,在“调腔”等“高腔”中,至今犹能演唱《北西厢〈游寺〉〈请生〉〈赴宴〉〈拷红〉》《汉宫秋〈游宫〉〈饯别〉》,这是在全国仅存的。
明清传奇,自《琵琶记》至《长生殿》,又有许多民间“无名氏”剧作演唱着。至于民间戏,向来以实际演唱而传存着。总以上,浙江的戏曲及戏曲音乐,庶几可反映我国民族戏剧史的全过程及我国戏曲音乐的整体面貌。
其实,这也不是浙江才如此,全国许多省(市)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因此,以著述一个足够大的地域如一个省份内的戏曲音乐为课题的一部专著,就当着眼于戏曲音乐的“整体性”及“系统性”。
我们将浙江的戏曲音乐“腔、调”,根据其结构分为三大类、九种(套),种下以其音乐形态特点分支、以地区差异分路,并按其兴起的历史时序排列,为:宋元至清初的“南北曲腔”,其下为“高腔”“昆腔”;下为各支、各路。清中叶勃兴的“乱弹诸调”,内含:“三五七——二凡”“芦花——拔子”“二簧”“西皮”四套;下有各路。清末民初后流行的是“摊簧”,有:“南词摊簧”“唱说摊簧”,其中又歧发出“越剧(唱调)”;亦有支和路。
以上三大类、诸种(套)及其下的众多支、路(详见该书),以各自共同的又与他者相区别的结构,构成堪反映戏曲音乐历史邅递、层次等级的“腔调系统”的戏曲音乐整体。这样地述说浙江戏曲音乐,庶几才能使这部《浙江戏曲音乐》具有浙江戏曲音乐“总集”的意义;同时,是不是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具有了提供师长、学者、后人编纂中国戏曲音乐“总成”时作参考的意义。
(四)然而,本书毕竟是《浙江戏曲音乐》,只能对浙江戏曲音乐中的“腔、调”进行考察,探求的是浙江的诸“腔”众“调”的结构而作归纳——故为“腔调系统”;而不能更进一步,从更大的宏观角度、更高的学术层次,完全以音乐构成、音乐结构学角度去考察戏曲音乐,即不能完全从“结构系统”去梳理“腔、调”。这使我们不得不只能对“腔调”进行分类——即用不能反映音乐结构性质的“腔”“调”名称以至许多非音乐性的名称作为“腔调系统”类别种别的称谓;而不能以“音乐结构”体式进行分类,即不能用音乐体式作为戏曲音乐类别种别的称谓。具体地说,最使我们为难的是,本书不得不使用“越剧(唱调)”的说法,而不能用其音乐结构“两段(四句)式”作为戏曲音乐的类种。
思维是由概念反映的,概念是用词语来表达的,合乎逻辑的思维要求有明确的概念和有限定指义的词语。
然而,由于汉语词语的多义性,由于民间音乐用语的方言性和任意性,由于我国自古至今对音乐理论包括其术语往往欠缺严格的论证和确定;以及在近代西洋音乐及其理论输入时使用的译语,近几十年来偏于“就俗求便”倾向等影响;使我们在使用词语、确定概念、表述问题时遇到不少的困难。本书的做法是——
(一)对一些一般不致发生歧义的原有的词语,尽可能地沿用。如:“高腔”“昆腔”等,“接腔”“腔格”“旋律”“乐句”等。
有一些词语,本具有明确指义或者原系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只是在戏曲音乐界很少使用而往往被忽视着,本书按需要而沿用之。如“散声”“正昆”等,“真戏剧”(王国维)、“戏弄”(任半塘等)等。又有一些词语,从词语构成角度说或有欠妥,只要使用较普遍而又不致发生概念混淆的,也沿用之。如“散板”“伴奏”等。
(二)对一些多义的及使用时常常发生或容易发生概念混淆的词语,本书按其基本指义或其规范趋势,力求加以限义、规范而使用。
如,“曲”这个词,通常又指文体文学又用指音乐,混淆一起,其实在我国民族文艺,宋元以下,“曲”的指义主要为文,③故有“南曲”“北曲”之异、“散曲”“剧曲”之分;其音乐即唱,则有“曲唱”“歌唱”之别,“清唱”“剧唱”之分。因此,本书使用“曲”这个词,一般只用指文体如“曲牌”“律曲”“南北曲”等;本书用“乐体”这个称谓指称音乐体裁以取代通常使用的容易引起概念混淆的“曲体”一词。
又如“腔”与“调”,此二词很经常地被混用而致混淆。本书采用此二词的本义而分别用之。“腔”,在音乐,是为唱中的特殊的或特定的旋律片断或局部,如“接腔”“帮腔”“字腔(腔格)”“过腔”“润腔”等,“腔”的要领最大止于一音乐个体的旋律部分,如“腔句”,如某唱调的“唱腔”等。“调”,在音乐,是在某种限定条件下按一定关系组成的乐音排列,如以律位为限定条件为“调高”,以主音为限定条件的为“调式”,以散声为限定条件有“笛调”“小工调”“正宫调”等,以及用作为对包括节拍、旋律、调式、首尾齐全的完全的音乐个体的一种称谓,如[芦花调][二簧调][弦索词][烧香调]等,又有用其“指法调”作为其具体音乐个体的称谓的如(“越剧”的)[四工调][尺调]等。因此,本书不用概念含混模糊的“声腔”一词;也不用与文体概念相混淆的“曲调”一词④,而用“唱调”作为对完整的音乐个体的称谓。也因此,本书将以用长短句曲牌为文体、以“腔句构成”为韵结构特征的一类定名为“南北曲腔”——以腔句构成为其音乐结构特征的南北曲的唱腔;将以唱调及唱调连接为音乐结构特征的一类定名为“乱弹诸调”——“乱弹”是沿用的称谓,“诸唱调”包括唱调组合是这一类的特征。等等。
(三)当我们从戏曲音乐本体结构运河梳理其腔调系统的时候,有时发觉词语的不足敷用,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使用一些精炼而成的“新”的词语或词组。如上已述及的“乐体”“唱调”及“南北曲腔”“乱弹诸调”等。
本书按“腔调系统”著述戏曲音乐,提示戏曲音乐的本体结构,并据此对戏曲音乐进行分类别种。人们对事物及其系统分类认识,是“从个别到一般,从普遍到特殊”不断反复验证的过程。人们对事物系统分类的结论及其表述方式,一般是从整体到类、类到种即大系统到小系统、母系统到子系统“从整体到部分,从一般到特殊”为次序;而人们对事物系统分类的认识的获得过程,则是从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开始的——从事物的外部现象进而考察其内部结构,从小系统到大系统以至对事物整体认识。然后将认识付与验证,再“从个别到一般”,再“从普遍到特殊”,反复验证……对本书而言——
(一)首先,要求我们尽可能齐全地掌握戏曲音乐原始资料,以“事实的全部总和”作为基础,从这里开始进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的探索;同时,要求我们的认识——对戏曲音乐腔调系统分类的认识与戏曲音乐实际趋向一致。我们以“宁滥毋缺”为要求,集印了约2000万字篇幅的浙江各市、地戏曲音乐资料本60卷。参加编写这60卷资料本的有浙江省四十多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戏曲音乐工作者,他们是参与本书工作的“大班子”。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对戏曲音乐系统分类的大小各个课题,及直接编写本书的“小班子”。要求“小班子”的每一个成员都须能对戏曲音乐三大类有所掌握,能运用逻辑思维,不仅熟悉浙江戏曲音乐的外部现象,而且探索其内部联系。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由“小班子”分工,各领课题,互相合作,“攻关”、撰写;然后提交“大班子”共同讨论、通稿;再然后“水磨”,以“宁缺毋滥”为要求,写出初定稿。在讨论、研究、撰写时,提倡“学术上‘求异存同”’,各抒己见;“工作上‘求同存异”’,集体合成。如此,逐步地使我们从感性向理性认识推进,使本书摆脱现象罗列,向戏曲音乐的结构、腔调系统、分类别种探索。
(二)事物的现象是斑驳繁复、变化无定的,而事物的结构则是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稳定的因素即本质。本质在现象之中,但本质并不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正如文体谱中的《词谱》《曲谱》著述词牌、曲牌的文体结构,并不包括介绍每一具体作家风采、每一具体作品意境一样,本书著述戏曲音乐的结构、系统分类,并不能介绍每一具体唱段的“音乐形象”以及每一具体演唱上的具体特色。然而,也如同《词谱》《曲谱》阐述每一词牌、曲牌文体结构时必引用某些具体作品作例一样。本书在阐述每一腔句、每一唱调等时也须引用某些具体乐谱作例。引例只为了说明结构。亦如一首具体词作的文辞不能与该词牌的文体结构相混同,一段具体乐谱不能与该腔句或唱调的音乐结构相混同一样。在这里提出这一点,又为了要说明、强调说明我国文艺包括戏曲音乐在构成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一个特点——“据本而演文”:
本,是本体、是本质;文,是具象、是文饰。戏曲音乐每类、每种以至每一唱调都有其“本”,“本”是事物内在的质,即其结构——结构是事物成为该事物稳定的因素,“结构的稳定性”为其“本”;依据此“本”演化为具体的“文”——发于唱者之口、入于听者之耳的声、音,反映在书面为具体的乐谱,具体的唱(乐谱)即为其“文”,“文”是其数无定又变化无穷的,任何一唱调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段具体的唱,而不论有多少以至无数的变化无穷的不同的唱(谱)都是依据该唱调的稳定的结构而演化出来的——这,反映为戏曲音乐构成上的“使用上的通用性”。
以上,便是“据本而演文”。本质在现象之中,现象并不就是本质,罗列现象并不能反映本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明[二簧调]的结构,即使将其所有具体的唱谱收集罗列,并不能说明何为[二簧调],不探求戏曲音乐的结构系统,即使将戏曲音乐所有的乐谱收集罗列,并不能知何为戏曲音乐。
(三)本书对戏曲音乐的结构、系统、分类,只是一种探索,探索的初步。
本书不是一部理论研究性的专著,至少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本书所做的,只是按戏曲音乐本体结构、腔调系统对戏曲音乐、浙江戏曲音乐的类别种别及诸支路作一些我们可能做到的介绍和阐述而已。
本书的目标是希望能使读者“知其然”——知戏曲音乐、浙江戏曲音乐腔调之“然”,这目标未必很轻易地能达到,本书只是在求“知其然”上的一个开端,还有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如果本书有幸正式出版了,还是一本“初稿”;至于“所以然”即真正进入对戏曲音乐规律性的理论研究,只能有待于今后,有待于同道诸贤了。
以上为序。
《浙江戏曲音乐》编著组
1992年9月
注释:
①另外18本未标明地名。
②(南)宋杂剧及金元院本之段数(院本)名目,唯浙江人周密、陶宗仪所撰《武林旧事》《辍耕录》中有载乃传世。
③如《钦定曲谱》,何良缘、徐复祚等人的《曲论》,王骥德《曲律》,臧晋叔《元曲选》,吕天成、祁彪佳等人的《曲品》以及《曲海总目》等无数文著,其所称“曲”明确地皆专指文——文体文辞以至剧作。
④“曲调”,在民族文艺原系指韵文文体学中与“词”相对的“曲”文体中的个体的称谓,即俗称为“曲牌”者,明王骥德《曲律》“曲之调名,今俗曰‘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