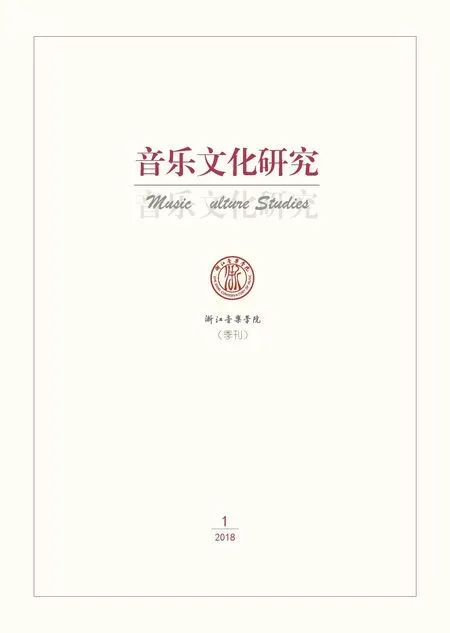从《体源钞》看中国典籍与日本乐书的关系
王小盾 宁 倩 刘 盟
《体源钞》是对雅乐作综合论述的乐书,是日本“三大乐书”的第二种。全书13卷20册,由京方笙乐家丰家本流第22代的代表乐人丰原统秋(1450-1524)撰成于永正九年(1512)。此时正是经过应仁、文明(1467-1477)大乱,雅乐衰败的时候,丰原统秋感于乐道将绝,遂作此书。书中多方引用中日各种典籍,对当时的日本音乐文献资源作了较全面的反映。本文拟考察它征引中国文献的方式,来探究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典籍与日本乐书的关系。
一、《体源钞》对中国乐书的引用
《体源钞》共引用了八种中国乐书,即汉蔡邕所撰《琴操》、南朝陈释智匠所撰《古今乐录》、唐武则天敕撰《乐书要录》、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赵惟暕所撰《琴书》、佚名所撰《律书乐图》、五代窦俨所撰《大周正乐》、宋陈旸所撰《乐书》。
在以上这些书籍中,陈旸《乐书》的情况比较特别:《体源钞》大量引用此书,引文完整。比如《体源钞》卷八对乐器的记录,其中至少有49条来自陈旸《乐书·乐图论》中的“雅部”,而且引文与原文较少出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乐书》在日本影响最大,因为《体源钞》引用《乐书》时仅引其“乐器”类;而且《体源钞》乐器记录有四卷,仅卷八(末卷)引用陈旸《乐书》。这就是说,对于《体源钞》,陈旸《乐书》其实只有局部的影响;或者说,对日本乐书影响较大的,是唐代传入的乐书。
对于唐代传入的其他七种书籍,《体源钞》共引用了31条,其中《律书乐图》13条,《乐书要录》9条,《乐府杂录》3条,《古今乐录》2条,《大周正乐》2条,《琴书》《琴操》各1条。尽管引用量不甚大,但引用方式却颇为丰富,包含以下几种引录情况:
(一)直引,即照录,引文较完整地对应于今本原书。例如《体源钞》卷一“七声”引《乐书要录》:
《乐书要录》曰:“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变宫,变宫生变徵。”①
又曰:“即有七声以成音调。五声二变,经纬相成。未有不用变声能成音调者也。故知二变者,宫徵之润色,五音之盐梅。”②
(二)转引,即间接引用,引文未见于今本原书,而见于类书或其他书。例如《体源钞》卷八引《古今乐录》和《大周正乐》:
《古今乐录》曰:“琵琶出于弦鼗。注:杜挚以为秦末盖苦长城役,百姓弦鼗而鼓之,盖琵琶之所起。”③
《大周正乐》曰:“今缶八,永太初司马滔进献广平乐兼此八缶,具黄钟一均声。”④
(三)略引、译引,引文与今存中国书有较大出入。例如《体源钞》卷八引《琴书》:
《琴书》云:“昔者至人伏羲氏ノ天下ニ王タリシ。仰观天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远ハ诸物ニトリ,近ハ诸身ニトル。始テ八卦ヲカイテ桐ヲ制メ(或削テ)琴ヲツクル。”⑤
这段引文实际上是译引,所以其中出现了汉字假名化的现象。
(四)编引,即在引用时加减乘除,重新编排。例如《体源钞》引《乐书要录》共9条,其中5条采用了以五音对应五行的方式。其文如下:
《乐书要录》曰:“夫金,刚健而能断。其位西方,以法制恩,不畏强御,不侮鳏寡,赏赐不违所憎,诛罚不阿所爱。乐当宫于南吕,用钟和乐于西郊。”(平调)
《乐书要录》曰:“夫木,阳气盛则而茂荣,内有仁恩。其位东方,其时主春,其声主角。是故仁君好生而恶夺。见人饥寒,则心为之悲。事之劳苦,心为之哀,与人同忧。乐当于宫夹钟,用鼓和乐于东郊。”(双调)
《乐书要录》曰:“夫火,精阳炎于上,挍然有尊卑之别、贵贱之序。其位南方,其时夏,声中徵。故礼,君在上,制尊卑,定贵贱,别亲疏,殊内外,使家家有礼仪。乐当宫于蕤宾,用弦和乐于南郊。”(黄钟调)
《乐书要录》曰:“夫水,修理归下,进退不解,日夜不已。其位北方,其时主冬,其声中羽。故智君在上,昭然犹见化道之原,得失之几。乐当宫于黄钟,用管和乐于北郊。”(盘渉调)
《乐书要录》曰:“土者为四方中,位有中央,其声中宫。四方不土不宁,木不土不生,火不土不荣,水不土不清,金不土不成,八音不土不调,味不甘不和,色不黄不正。乐当宫于林钟,用磬和乐于中郊。”(壹越调)
以上这种五行纳音理论,在《体源钞》中有很多表现,比如书中所记,有金音商、木音角、火音徵、水音羽之说,有八调子配八方之说,有十二调子配十二月分、十二时之说,有以毛、皮、肉、骨、髓五常配五声之轻重清浊之说。这些学说,基本上是通过编引中国典籍语录而形成的。以上五条正是这样:第一条乃据《乐书要录》所引《月令》文“仲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南吕”与《五行大义》“金者,禁也”“金居少阴之位,西方成物之所”云云编引;第二条乃据《乐书要录》所引《月令》文“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夹钟”与《五行大义》“木者,冒也”“木居少阳之位……以温柔为体,曲直为性”云云编引;第三条乃据《乐书要录》所引《月令》文“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宾”与《五行大义》“火者,炎上也”“王者向明而治,盖取其象”云云编引;第四条乃据《乐书要录》所引《月令》文“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黄钟”与《五行大义》“水之为言演也……其时冬……其位北方”云云编引;第五条乃据《乐书要录》所引《月令》文“季夏之月,其音徵,律中林钟”与《五行大义》“含黄中之德,能苞万物”“土居中,以主四季,成四时”云云编引。
(五)其他引用法,即引文未见于今本中国书而不知其来源的引用法。例如引《律书乐图》13条,均未找到原文。事实上,在能够找到出处的引文中,也只有4条引文见于今本原书,7条见于今本《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这说明,在日本乐书和中国乐书之间,还有一些未明其源流的关系。
二、从《体源钞》看中日乐书的关联
以上最末一句话的涵义是:如果撇开陈旸《乐书》不计,那么,在以上四种引用情况中,最多见的是第四种情况。这是因为,《体源钞》所引录的中国乐书,大部分——《琴操》《古今乐录》《琴书》《律书乐图》《大周正乐》等五种——已经亡佚。其中《琴操》曾被魏晋唐宋著作频繁引用,体裁分类与排列顺序大致可以考订;《古今乐录》篇制宏大,影响广泛,所以这两种书都有现代人的辑佚之作。⑥但《律书乐图》《琴书》《大周正乐》却是原貌不详的,各有文献学问题值得讨论。
(一)《律书乐图》的问题,究其实质是乐书与乐书之关系的问题;或者说,主要是三部书——陈旸《乐书》和日本乐书《体源钞》《教训钞》——之关系的问题。陈旸《乐书》200卷,征引书籍很多,较多地保存了《律书乐图》的佚文。据研究,“陈旸《乐书》所存《律书乐图》的佚文以记载唐鼓吹仪仗乐为主”,包括鼓吹、羽葆、铙吹、大横吹、小横吹五部。⑦但《体源钞》所引《律书乐图》的内容,却是比陈旸《乐书》所引要广泛得多——在《体源钞》“乐器”“乐曲”“音乐理论”等部分均有引用,包括隋炀帝造《泛龙舟》曲、马融善吹长笛、铜钹出自西域、大鼓即建鼓、清乐磬调高于雅乐三律等内容。由此可见,《体源钞》是从另外的来源引录《律书乐图》的。这意味着,《律书乐图》虽然亡佚于中国,但在日本列岛却有较长时间的流传。关于这一点,可以举出旁证。
旁证就是:除陈旸《乐书》外,日本乐书《教训钞》也保存了《律书乐图》很多佚文。比如以下几条:
1.关于《泛龙舟》,《教训钞》卷四引《律书乐图》云:“隋ノ炀帝所造ル也。”按此条亦见于《体源钞》卷二,不过《体源钞》在其后有“《明暹谱》云:赞《法华经》乐博雅卿谱序(拍子十六)入破(拍子十八)”等文字。
2.关于宴乐曲调,《教训钞》卷六《越天乐》引《律书乐图》云:“宴乐之林钟州(又林羽越殿)。”今按:《教训钞》引《律书乐图》六条,仅这一条不见于《体源钞》。
3.关于觱篥,《教训钞》卷八《管弦物语》引《律书乐图》云:“大筚篥、小筚篥(二音和云比知里木)。”按《体源钞》亦引此语,只是“和云”作“俗云”。
4.关于揩鼓,《教训钞》卷九引《律书乐图》云:“皆皮(揩摩也。俗云寸里豆豆美。此鼓高野姬之御宇始テ我朝出来云云。事ノ发リ笑样ニ,申传如何,可寻之)。”按此条亦见于《体源钞》卷六《打物事》。
5.关于铜钹,《教训钞》卷九“铜拍子”引《律书乐图》云:“出自西城,无柄,以皮为纽,相击以应节,今夷乐多用之。”按此条亦见于《体源钞》卷六“打物事”。不过,《太平御览》卷五八四《乐部》也有相似的引文,署书名为“宋乐志”。
6.关于大鼓,《教训钞》卷九“铜拍子”引《律书乐图》云:“《尔雅》云:‘大鼓(今案,俗或谓之四鼓,小鼓有二三名皆以应节次第取名,八鼓者谓行道大鼓云云。)’”按此条亦见于《体源钞》卷七“大鼓(付铮鼓)”。
在这里,《教训钞》《体源钞》对《律书乐图》的引录,出现了大幅度的重复。这不免让我们推测:《体源钞》中的《律书乐图》文字,有两个可能的来源:首先,直接引自在日本流传的《律书乐图》;其次,从《教训钞》或其他日本乐书转引。相比之下,后者更有可能,因为根据我们的校对,《教训钞》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见于《体源钞》。不过这两种可能性都意味着,失传于中国的《律书乐图》,曾经长期存活于日本;流失了的中国乐书,是不妨求之于日本的。
(二)《琴书》问题,其实是唐五代琴书的关系问题。古琴艺术发展到隋唐五代,出现了流派化的倾向;古琴文献蜂拥而出,产生了很多琴书。其中较著名的有李勉《琴说》、李良辅《广陵止息谱》、吕渭《广陵止息谱》、蔡翼《小胡笳十八拍》、刘籍《琴义》、陈拙《琴籍》《大唐正声新徵琴谱》、赵耶利《胡笳五弄谱》《琴叙谱》、陈康士《琴谱叙》《离骚谱》《琴调谱》《琴书正声》《琴调》、僧辨正《琴正声九弄》、玄宗《金风乐弄》、萧佑《无射商九调谱》、李约《东杓引谱》、僧道英《琴德谱》、沈氏《琴书》、孔衍《琴操引》、崔遵度《琴笺》、郑文佑《琴德》、崔亮《琴经》、蔡逸《阮咸谱》、谢希逸《雅琴名录》、佚名《琴集历头拍簿》《琴杂说》《琴曲词》《琴谱三均手诀》《琴略》《大胡笳十八拍》《琴论》《琴谱》《正声五弄谱》《降圣引谱》《三乐谱》《阮谱》《琴传》《隐韶集》《琴阮二弄谱》《琴声韵图》。⑧这些作品都可以泛称为“琴书”,也的确被古代人称作“琴书”。比如《玉海》卷一一○引《中兴书目》论李勉《琴说》云:“《琴书》一卷,唐工部尚书李勉撰,凡琴声、指法、操名、琴操悉载之。”可见李勉《琴说》曾被人称作“琴书”。那么,我们说《体源钞》所引的《琴书》出自赵惟暕之手,理由在哪里呢?在于《玉海》卷一一○引《中兴书目》的一段话,云:“《琴书》三卷,唐翰林待诏赵惟暕述制琴律吕、上古琴名、弦法共十二篇。”⑨另外,《崇文总目》也说过:《琴书》“略述琴制,叙古诸典及善琴人姓名”。⑩这和《体源钞》引文所说“《琴书》云:‘昔者至人伏羲氏ノ天下ニ王タリシ……桐ヲ削テ琴ヲツクル’”云云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有证据判断《体源钞》所引录的就是赵惟暕的《琴书》;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中日古乐书有一种结构上的对应,比如在这两地,“琴书”既是某种乐书的专名,也是某类乐书的通名。
(三)《大周正乐》的问题,主要是《体源钞》与唐宋类书之关系的问题,因为《体源钞》卷八所保存的《大周正乐》佚文共2条,均见于《太平御览》一书。其中论“缶”的一条,又见《太平御览》卷五八四《乐部》;论“抚拍”(《体源钞》误作“抚相”)的一条,又见《太平御览》卷五八五《文部》。考虑到《体源钞》有大量引文同《初学记》相重合,可以推断:类书是保存乐书的文献形式;除乐书外,唐宋时期的类书也对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下文再作专门讨论。
三、关于《体源钞》中的《醉乡日月》
《体源钞》所引用的中国书,除乐书外,有一种觞政之书,即《醉乡日月》。这书的地位很重要:除《通典》和《新唐书》外,被《体源钞》引用最多的中国典籍便是《醉乡日月》。
《醉乡日月》为唐朝皇甫松所撰,原书已残,仅在《说郛》《永乐大典》《类说》等书中存有部分佚文。《说郛》记其篇目为:《饮论》第一,《谋饮》第二,《为宾》第三,《为主》第四,《明府》第五,《律录事》第六,《觥录事》第七,《选徒》第八,《改令》第九,《令误》第十,《骰子令》第十一,《详乐》第十二,《旗幡令》第十三,《下次据今》第十四,《闪擪令》第十五,《上酒令》第十六,《并著词令》第十七,《按打》第十八,《手势》第十九,《拒泼》第二十,《逃席》第二十一,《使酒》第二十二,《勤学》第二十三,《乐规》第二十四,《小酒令》第二十五,《杂法》第二十六,《进户》第二十七,《酿酒》第二十八,《风俗》第二十九,《自序》第三十。⑪根据现存资料,《醉乡日月》收录了大量与唐代酒令相关的乐曲;只可惜这些记录多已散佚。由此来看《体源钞》,便知它另有两大学术意义:其一,有助于对《醉乡日月》的辑佚;其二,有助于唐代酒令研究。请看《体源钞》所记以下内容:
1.《三台盐》:“《醉乡日月》曰:高宗后则天皇后所造也。”
2.《皇麞》:“《醉乡日月》曰:景龙中,西戎叛,宰相王孝杰征之战于黄麞谷死,中宗念其忠,故作也。”
3.《甘州》:“《醉乡日月》ニ云ク:乐之精,莫过玄宗朝,然者玄宗作尤取信欤。又玄宗既ニ知音律又酷爱法曲。”
4.《鸟》急:“或云:《圣明乐》异名《势明乐》。又《醉乡日月》云,《大常乐》ト云,或又本胡乐ト云。有咏,其词云:由彼向陶门,眼晴〔四〕皆与青。”“《醉乡日月》云:唐开元中太宗(或太常)乐人马顺作之明白也。”
5.《倾坏乐》:“《醉乡日月》ニ曰:此曲贞观元年中ノ内宴ニ长孙无忌所作也。”
6.《天长乐》:“《醉乡日月》曰:大百岁老寿注曰‘改为《天长乐》。开元中,宁王进普乐工康摩勒等五人造之’。”
7.《涩河鸟》:“《醉乡日月》云ク:隋炀帝作,新古兼。”
这些记录都是关于唐代酒令曲的记录。它们说明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其一,唐代酒令曲曾经成规模地传入日本;其二,中日典籍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换言之,在历史上,中日典籍处在同一个汉文化圈当中,所以既有相近的书写方式,也往往在内容上彼此容纳。以乐书身份来记录酒筵曲,来援引《醉乡日月》,正是这一关系的表现。
四、从引书看《体源钞》的文献学性格
除专门的乐书外,中国的音乐文献大致分布在以下三类图书当中:其一为正史(《史记》等)乐志和律志,其二为政书(《通典》等)和会要之书,其三为类书。这几类书,都是《体源钞》的引录对象。比如《体源钞》引《史记》《汉书》《新唐书》近五十条,引《通典》36条,便是显例。至于《体源钞》对中国类书的引用,则集中表现在其“乐器”部分。
据统计,《体源钞》引中国类书有以下56条:
1.引唐徐坚所编《初学记》乐部共11条:卷一3条,关于笙和雅乐;卷五1条,关于笛;卷六2条,关于壹鼓和钟鼓;卷八5条,关于琵琶、筝、琴和笛。
2.引唐虞世南所编《北堂书钞》乐部1条,见卷五,关于横笛。
3.引唐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5条:卷一、卷十关于律吕;卷六关于鼓。
4.引宋陈元靓所编《事林广记》音乐类2条,见卷四,均关于“乐制”。
5.引宋李昉等所编《太平御览》乐部共37条:卷四、卷六各1条,分别关于笙和柷敔;卷五3条,关于横笛和筚篥;卷七2条,关于鼓;卷八30条,分别关于琴、五弦、六弦、七弦、雅瑟、筑、准、太一、竽、管、箫、笳、籥、埙、缶、角、柷敔、钟、錞于、铎、壤、春牍、抚相、铜鼓、节鼓、都昙鼓、毛员鼓、担鼓、马上之鼓、方鼓。
以上所谓“条”,指的是类书的某一段落,每段落所含引文并不止于一则。例如在《体源钞》卷七中有如下引文:
鼓者(付大鼓)公戶ノ切。又始古ノ反。……
《帝王世纪》ニ曰ク: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百里。……
《风俗通》ニ曰ク:鼓谁カ造ルトコロトシラス,鼓ハ郭ナリ,春分ノ音万物皆郭皮甲ニシテ出,故ニコト鼓ト云。……
《后秦记》曰ク:姚泓永和元年,天水石鼓鸣闻数百里,野雉皆雊。……
据考,这些引文都出自《太平御览》卷五八二乐部“鼓”类,在本文的统计中算作一条。如此看来,《体源钞》引中国类书的数量其实很大,占据全书引中国典籍总数⑫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体源钞》作者是重视中国类书的——在若干中国文献中,他更倾向于阅读和引用类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图书。另外,《体源钞》在转引类书时,往往不是成片引用,而是选用其中若干条,并对顺序有所调整。这又说明:《体源钞》作者在引用中国类书之时,其实也参考了类书所引用的原典;说明这些典籍同样在日本流传。在多种文献资源当中选择类书,这种做法,并不止《体源钞》;因此,它表现了日本乐书重视综合性图书的文献学性格。
至于《体源钞》对《通典》的引用(共引36条),则表现了它对政书的倚重。这36条引文大多标注了《通典》之名;但也有一些引文,虽标注其他书名,其来源却是《通典》。例如《体源钞》卷二云:“《汉书》云:‘《安世房中歌》云“神来宴娱”,《诗》ニ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遹归”,注ニ云“归于天也”’,盖言神有来则宜送迎明矣。以尸象神,故《仪礼》有‘迎尸送尸’。”这段话便出自《通典》卷一四七“宗庙迎送神乐讥宋梁”条。⑬引《通典》而不明言《通典》,原因是《通典》在日本流行较广。这一点可以从另一迹象看出来,即:在《体源钞》的《通典》引文中,汉字假名化的现象很普遍。这说明《通典》的记录已大量进入口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通典》之流传于日本,这同它的诸方面特点有关。第一,它产生在唐代贞元十七年(801)前后,这正是中日文化交流最兴盛的时期。第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性政书,详细记录了唐天宝以前的各种典章制度;其中乐典七卷,含历代沿革、十二律、五声八音、旋相为宫、历代制造、乐悬、歌和歌曲、舞和舞曲,以及清乐、坐立部伎、散乐、前代杂乐等项目,“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⑭。这恰好可以满足人们系统掌握文化史、礼乐史知识的需要。第三,《通典》在编成之后,立即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学术经典。比如当时人李翰说:此书“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后晋人刘昫说:此书使人知“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掌”。⑮也就是说,人们公认此书是掌握学问的利器。考虑到这三点,可以判断,日本乐人对《通典》的重视,是和唐代人对《通典》的重视相关联的。或者可以说,《体源钞》对《通典》的引用,反映了中国音乐史学观念对日本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影响,《体源钞》在编纂时也采用了接近于类书或政书的方式——通过较细致的分类,对笙和各种乐器,对歌舞曲和各种乐人,作了全面记录。
《体源钞》还有一个引文特点值得注意,即它收录了许多中国的传说和典故,例如奚仲造车、货狄造舟、素女五弦琴、周穆王吹笛止雨、瓠巴鼓琴、弄玉吹箫、季札挂剑、王乔骑凤、王子晋吹笙、鲁阳挥戈、伯牙与钟子期、阳春白雪、陶答子妻等上古故事,淮南八公、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王昭君、马融梦食花、魏文帝与郦县菊花、向秀邻家吹笛、玄宗与罗公远等中古故事。这些故事是伴随着典籍东传而流播日本的。例如《体源钞》所记王子晋故事:
《武陵七十二仙传》ニ云ク:“马融梦ニ一ノ林花ノ锦绣ナルヲミル……”或云:“《霓裳羽衣》トハ舞ノ袖ノ霓ノヤウナレハナリ。王子晋仙ヲエテ后候氏山ニ返来テ笙ヲ吹シニ,此《霓裳羽衣ノ曲》ヲナン吹ケル。”
这个故事显然是在口传中被改造过的;因为据中国古籍所记,王子晋吹笙是东周之事,《霓裳羽衣》则是产于唐代的乐曲,二者并无关系。考虑到《体源钞》另外载有“王子晋吹笛”的故事,并把“周穆王吹笛止雨”的主人公改称为“南阳王”,我们判断,《体源钞》所记王子晋吹笙故事乃是在新传说的影响下形成的。从以下几首诗歌可以窥见这种影响:其一是唐代诗人厉玄所作的《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中有“紫府参差曲”句;其二是唐代诗人钟辂所作的《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中有“清杳异人间”句;⑯其三是白居易诗《王子晋庙》,云“子晋庙前山月明,人闻往往夜吹笙。鸾吟凤唱听无拍,多似霓裳散序声”⑰。《体源钞》说:“《文集》五十八ニ云ク:子普ガ祠ノ前ニ山月明ナリ,人闻ハ往往夜笙ヲ吹。鸾吟凤凰昌听ニハクナシ,多ハ《霓裳》散序ノ声ニニタリトイヘリ。”明确表现了白居易诗对日本的王子晋传说的影响。
以上这件事,反映了《体源钞》另一种文献学性格,即重视口传文献。正因为这样,书中多有“秘书云”“口传云”“古说”“或云”“又云”等提法。这种引述口传的方法当然不止于针对中国文献,对日本文献也是这样。比如该书卷六引《教训钞》卷一○云:“打物案谱法(口传记录)。”又卷一一云:“以上左近判官代孝敏口传也。”这说明它不仅循用《教训钞》等乐书的口传记录,而且自行采用了口传记录。据统计,《体源钞》引录了一百多人的口传语录,甚至引用了长篇对话。这一特点,提醒我们注意到日本乐书的另一性质,即在某一音乐世家代代秘传的性质。其实,音乐文献的秘传,本质上是音乐技艺的代代秘传。《教训钞》《体源钞》等书的“钞”字,以及这些乐书频频使用的“秘说”“秘记”“秘口传”等语汇,都是上述传承方式的表现。我们于是可以得出结论:日本乐书具有音乐口述史的性质;日本乐书对中国乐书的引用,隐藏了由典籍进入口述这样一个传播过程。日本乐书的假名化、其材料来源的模糊性,正是这一过程的书面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日本乐书对中国典籍的引用,可以理解为两种文化的结合。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体源钞》中有九十多条引文来自八种中国乐书。这些乐书在《体源钞》中所占篇幅不同,经比较可知,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乐书是《乐书要录》和《律书乐图》。其中《乐书要录》是唐代的一部乐律学著作,武则天敕撰,天平七年(735)由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带回日本。所以,它曾经被《三五要录》《声明用心集》《类筝治要》《阿月问答》《音律通致章》《丝竹口传》等日本乐书所征引。⑱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是:《律书乐图》亦曾在日本流传,因而被《教训钞》等日本古乐书征引。这就说明,《体源钞》对中国古乐书的引录,的确可以反映中国乐书在日本流传的情况。《体源钞》对七种乐书的引录方式——直引、转引、略引、译引、编引等方式——便代表了中日乐书相关联的几条途径。
考察《体源钞》对中国乐书的征引方式,可以发现两个问题:其一,这些乐书大部分从唐宋之际开始陆续在中国消失,但它们却长期存活于日本。《琴操》《古今乐录》《琴书》《律书乐图》《大周正乐》都是这种佚书。其二,中日古乐书有一种结构上的对应,比如都把“琴书”用为某种乐书的专名和某类乐书的通名,都重视对唐代酒令曲加以记录。这两个问题意味着:东亚汉文音乐文献其实是一个整体,拥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是在拥有共同文字的基础上相流通的。正因为这样,中日乐书既有相近的书写方式,也往往在内容上彼此容纳。由此看来,考察中日乐书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礼失求诸野”的工作。对于中国音乐文献辑佚学来说,日本乐书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考察范围放大一点,那么,从《体源钞》对中国典籍的征引方式,还可以了解日本乐书的文献学性格。第一个性格是:以《体源钞》为代表的日本乐书,特别重视对中国类书、政书等综合性图书加以利用。这反映了中国音乐史学观念对日本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影响,《体源钞》对中国类书、政书的体制有所模仿。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教训钞》《续教训钞》《丝管钞》《乐家录》等综合性乐书,因此可以说,在日本乐书发展史上,中国的类书、政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个性格是:在《体源钞》的引文中,汉字假名化的现象很普遍。此书既用假名记录了许多中国的传说和典故,也用假名记录了《将军家进上信秋奥书》《秘说日记》《大神景范家记》《〈苏合香〉说日记口传》《村上日记》《弁内侍日记》等许多由日本人书写的文书和秘记。由于文本和口传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在日本,凡是流传广的典籍,其中便有较大比重的假名。由此判断,日本乐书是具有音乐口述史的性质的;日本乐书对中国典籍的引用,隐藏了由典籍进入口述这样一个传播过程。日本乐书之所以有此性格,原因在于,它们是为保证音乐技艺在某一家族代代秘传而创作出来的。第三个性格是:《体源钞》和它所引用的中国古籍有一个时间差:其书完成于16世纪初期,相当于明朝中期,但它所引汉籍基本上成书于宋代以前。比如《体源钞》引中国诗赋数十条,所涉作家有汉武帝、张衡、马融、蔡邕、杜挚、曹植、阮瑀、傅玄、嵇叔夜、夏侯湛、李峤、储光羲、杜甫、皇甫冉、皎然、王建、白居易、贾岛、杜牧、李远、韩偓、郑谷、林清和、苏轼、陆游、何失等,除林清和、苏轼、陆游、何失而外,都是唐代或唐以前人。与此相应,《体源钞》习以“汉家”“汉土”“大唐”“唐国”等名称呼中国,并把齐闵王称作“唐の齐の闵王”。这说明,日本人相当尊重来自中国的传统知识,尊重由这些知识建立的表达习惯;同时说明,汉籍东传以后,有一个被消化吸收的过程。在《体源钞》的汉籍引文中,可以看到两种特殊现象:其一是在原来的汉字旁加上大量训点,或将其假名化;其二是对同一段汉籍引文作不同的字体表达。这两种现象都说明,这些汉籍在日本已经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消化。
关于《体源钞》引汉籍研究或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另外还有三件事值得注意。首先,各种音乐都是依靠三个载体传播的:其一是人,具体说来是乐工;其二是物,具体说来是乐器;其三是语言文字,具体说来是乐书。离开这三个载体,旋律、节奏、音乐观念等都是无所附丽的。由此看来,要说清楚丝绸之路音乐以文献为载体的传播,就要对所有相关的音乐书写进行考察。因此,《体源钞》具有作为突破口的意义。但限于篇幅,本文未涉及乐工、乐器两方面,尚有待补充。其次,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有阶段性的特点:从8世纪末到12世纪,汉籍东传的主要载体是贵族知识分子;从13世纪到16世纪,汉籍东传的主要载体是僧侣和乐人;从17世纪到19世纪,汉籍东传的主要载体是商人和商业。⑲本文所讨论的种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第二阶段,既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时限性。再次,《体源钞》在写作中,引用了很多书籍文献,除上文所说到的几种乐书外,仅中国典籍即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月令章句》《世本》《山海经》《穆天子传》《国语》《左传》《道德经》《论语》《孟子》《晏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孝经》《孔子家语》《周易通卦验》《毛诗纬》《韩诗外传》《三礼义宗》《三礼图》《通礼义纂》《五经通义》《五经要义》《五经析疑》《乐纬》《苍颉篇》《尔雅》《说文》《释名》《切韵》《蒋鲂切韵》《广雅》《帝王世纪》《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仲尼游方问录》《孔子三朝记》《续后汉书》《晋书》《新唐书》《五代史记》《宋史》《贞观政要》《帝王代记》《国史纂异》《高祖实录》《文士传》《列女传》《西征记》《风土记》《西域传》《通典》《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唐会要》《金楼子》《淮南子》《司马法》《风俗通》《白虎通》《蒙求》《初学记》《太平御览》《白氏六帖》《事林广记》《编珠录》《翰苑》《兼名苑》《洽闻记》《语林》《西京杂记》《王子年拾遗录》《世说》《国史补》《博物志》《神仙传》《武陵七十二仙传》《列子》《列仙传》《蔡邕独断》《勇子》《新论》《游仙窟》《醉乡日月》《洞真记》《荆州记》《要览》《李氏五运图》《混天图》《唐令》等百余种。因此,本文只是一个借管窥豹的工作,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来扩大其意义。
注释:
①原文见丛书集成本《乐书要录》卷五“七声相生法”。
②原文见《乐书要录》卷五“论二变义”。
③原文见于《初学记》卷一六《乐部下》。除以上内容外,《体源钞》前后文还引用了《风俗通》《释名》《琵琶赋序》《琵琶赋》等文献,内容亦见于今本《初学记》。
④原文见于《太平御览》卷五八四《乐部》。
⑤原文见《太平御览》卷五七九《乐部》,云:“琴书曰:‘昔者至人伏羲氏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削桐为琴。’”
⑥例如吉联抗:《琴操两种》,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吉联抗:《古乐书佚文辑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刘跃进:《〈古今乐录〉辑存》,附见《〈玉台新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⑦参见亓娟莉:《〈乐书〉所见〈律书乐图〉辑考》,载《乐府学》第1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
⑧参见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第267-270页。
⑨[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第4册第2013页。
⑩[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916册第20页。
⑪《说郛》(涵芬楼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887页。
⑫按据陈鹏《日本四大乐书引汉籍研究》,《体源钞》所引汉籍(明确给出出处者),除集部外,共计123种535条。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⑬[唐]杜佑:《通典》卷一四七,中华书局,1988,第4册第3755页。
⑭[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中华书局,1994,第373页。
⑮[唐]李翰:《通典序》,中华书局,1988,第2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中华书局,1997,第1021页。
⑯[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一八四,中华书局,1966,第2册第901页。
⑰《全唐 诗》卷四五一,中华书局,1960,第5091页。
⑱参见赵玉卿:《〈乐书要录〉的留存情况考证》,载《交响》,2001年第1期。
⑲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58页。
——豫东琴书
——论唐代类书编纂的特点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