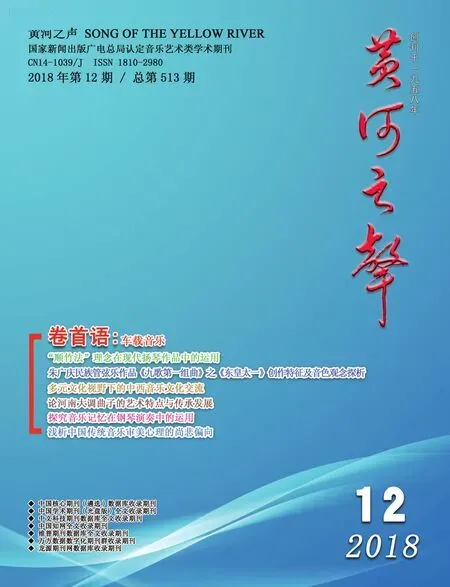试从哲学联系与发展的角度阐述土家族舞蹈“肉连响”的发展规律
陆南西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一、地理、人文要素是肉连响产生的必要因素
(一)地域环境的特点及影响
土家族肉连响发源于湖北省利川市,此地处于巫山和武陵山的交汇处,千沟万壑,纵横交错,沟谷幽深,道路崎岖。东临恩施,南连咸丰,西南、西北接重庆。在古代,此地为楚蜀的屏障,历来便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这些地形要素决定了在行走爬山的过程中,同手同脚有利于在狭窄的山间小道上安全行走。而常年征战的民族生存需求也是形成土家族“肉连响”强劲有力、豪放粗犷舞蹈风格的重要因素。利川县由于山脉阻挡,光照不足,温度偏低,这为肉连响的赤裸上身表演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增强了舞蹈的观赏性。
(二)文化习俗与精神追求
“肉连响”是土家族舞蹈的一个分支,土家族的文化和习俗都对肉连响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土家族有多神信仰,如猎神、土地神等。土家族的动物崇拜在舞蹈中体现较为突出。由此出现了很多因模仿动物而衍生的舞蹈,比如“茅古斯”里的“兔儿跳”;又如“撒页儿嗬”(跳丧舞)的“夜猫上树”等。土家族聚居在交通闭塞的山地,长期保持着传统的农耕习惯,通过这些舞蹈可调动人民的生活、生产积极性。利用不同的动物形态来表现生命的动态,用智慧创造多种舞蹈,这是生命性的内在体现。土家族人们热爱生活,崇尚自然,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及以人为本的生命意识。
二、用哲学联系的观点看“肉连响”
(一)“肉连响”的多种起源观点既独立又统一
关于“肉连响”起源的说法众多,在形式上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民间传说,相传在古代农历5月22日,城隍菩萨和小鬼们来人间挨家挨户地进行民情巡视,并在巡视的过程中用手有节奏地拍打全身。为感激其体恤之情,百姓们会在门前摆上食物以迎接,并应和着一同起舞,从此便形成了“肉连响”。第二种,赢战庆贺源于商周时期,“武王起兵,前歌后舞”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巴师锐勇,歌舞以凌,殷兵大溃”。[1]而巴人正是土家族人民的先祖。周武王伐纣大获全胜,将士们为庆祝胜利,以手击打身体的各个部位舞蹈,发出即富强劲节奏又欢乐动听的声响。这便是“肉连响”。第三种,乞讨求生,也被称为“泥神道”,这种说法被更多的学者认可。据说在新中国解放前,一些乞丐行乞,赤裸上身,涂上稀泥,口中念词,拍击全身,响有节律。来到富裕人家门前,以此乞讨。如遇慷慨之人,得施舍后会说些吉利话便离开。若遇吝啬之人,便使劲拍打全身,使泥浆飞溅至门前各处,直到主人施舍方止。以上三种说法独立存在,看似并无联系,但是,如果按照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可将以上三种说法分为三个时期。远古时期的民间传说;古代时期的赢战庆贺;解放前期的乞讨求生。因此片面地认为肉连响只是源于“泥神道”并非是最科学的观点,“泥神道”的出现必然与古代传说和赢战庆贺有关,笔者认为:“肉连响”在时间上更接近“泥神道”。因此,“肉连响”是源于三种观点时间上的独立和内容上的统一。
(二)“肉连响”的形成与多因素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
肉连响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它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肉连响闻名于世得益于一位伟大的艺术热爱者吴修富先生,吴先生自幼热爱艺术,并向当地艺人学习,刻苦练习,经过反复的思考、练习、琢磨。在原始“泥神道”的基础上,将以前学到的耍耍、莲湘、秧歌等元素加入到舞蹈中,最终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舞蹈动作——肉连响。
肉连响舞蹈风格古朴,表演时用手掌拍打自己的头、肩、、腰、足等。主要动作有“鸭子步”、“双打”、“十响”等。舞蹈风格幽默风趣,粗犷豪放,即富有娱乐性又饱含古朴之风,不论是观赏还是跳动都令人身心愉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丰富舞蹈形式,吴先生将击鼓与舞蹈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土家族人认为鼓是原始宗教的“法器”,用鼓可与神沟通,体现了土家族“天人合一”的思想。肉连响的音乐借鉴了汉族曲艺《莲花落》,其中唱词通常是即兴而为。这种方式在当地称之为“见子打子”,一人领唱,其他人应和,从而形成一唱一和的舞蹈音乐形式。
肉连响的形成秉承了兼容并蓄的原则,在以本民族文化为根本的基础上,借鉴其它民族的优秀成份,在舞蹈语言、音乐构成等方面逐步完善。肉连响的形成是文化、艺术、风俗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艺术,特别是古老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进步绝不是一个完全自然和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必须有人自觉参与和引导的过程。[2]因此,在自然变化的基础上加上人主观能动性的改造,肉连响才得以日益丰富。
(三)舞蹈功能的时代变化是“肉连响”形成多样统一的结果
在肉连响形成的过程中,舞蹈的社会功能变化对舞蹈形成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远古时期,为祭祀祈祷;古代时期,为战斗象功;解放前期,为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现代社会,为传承与发扬传统文艺。在现代社会中肉连响的舞蹈功能可分为内外两种:外是人们希望通过“肉连响”锻炼身体;内是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已经从最初的自然崇拜转向本体意识,更强调人的重要性,这种由心而发的生命本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社会中的肉连响是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它既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是人们运用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闻一多先生曾说“原始舞蹈的目的在于以律动的形体来表现生命,以社会性的功能来保障生命,以实用性的功能来强调生命”。[3]因此,不同时期的舞蹈都具有社会性,只是每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功能不同,在舞蹈形成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看待,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同时可以理性地借鉴其他舞蹈优秀的成份以丰富自己舞蹈的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精神需求。
三、用哲学发展的观点看“肉连响”
(一)“肉连响”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肉连响之所以被人们所熟知,离不开吴富先生60年来的辛苦积累。自1986年,肉连响开始正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以来,后经过吴先生的弟子刘守红的积极推广,肉连响成功申请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传播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看似发展顺利的过程中,肉连响的传承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肉连响传承容易,传神难。肉连响是吴先生耗费60年心血,点滴积累而成的。在传承人的选择上,吴先生重视点与面的结合,面即指人数上的多;点则是指学生的质量。吴先生的学生大多来自武术学校,在身体素质和“灵性”上都更符合标准,也能更快领会舞蹈要求的神韵均备,浑然天成的要领。然而在肉连响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吴先生的个别弟子在肉连响中不断加入武术的元素,使舞蹈的韵律逐渐转变成生硬的武术模式。想必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肉连响的发展初衷。肉连响作为舞蹈的一种,在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既没有形成系统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纳入到专业院校教学体系中。“肉连响”本属舞蹈范畴,舞蹈能使“肉连响”在不失本真的同时,更大限度地得到美化,成为更符合大众审美的高雅艺术。肉连响作为舞蹈的形成完善的教学体系还需时日。道路虽是曲折,前途却是光明。
(二)可遵循的舞蹈发生、发展规律
土家族肉连响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四个时期。在此过程中肉连响豪放、粗犷、流畅的舞蹈风格韵律自始至终都未改变。”肉连响”在时间上最接近“泥神道”,但是,泥神道动作单一,只有不断融入其他元素才能使肉连响舞蹈丰富起来。这种融合并不会破坏肉连响舞蹈的本质,曾有知名老专家说:“民间舞蹈与民间音乐不同,音乐有乐谱记录,在传承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一成不变’,而舞蹈不同,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只能依靠图像、文字等记录,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才能将舞蹈文化传承下来。虽然无法做到一模一样,但是只要民族独有的舞蹈风格韵律不变,便可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需求,社会功能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适应这种变化。因此,要尊重土家族舞蹈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高度的舞蹈热情与严谨的科学态度相结合。不因循守旧,不安于现状,不断创新,推进舞蹈的发展进程。
四、结语
土家族舞蹈肉连响从远古至今,在经历了时代的洗礼之后愈发地显现其珍贵。从哲学的角度上看,肉连响一直保存的古朴之风,是从远古时期到现代社会中始终联系的结果。肉连响的发展是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更趋完整,道路坎坷、前途光明。肉连响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老一辈艺术家的刻苦钻研;离不开新一代舞蹈爱好者的极力推崇;更离不开国家政策上、经济上的支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舞蹈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富足是支持舞蹈艺术发展的根基。在如此优厚的社会条件下,小至土家族肉连响舞蹈,大至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其发展道路都会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