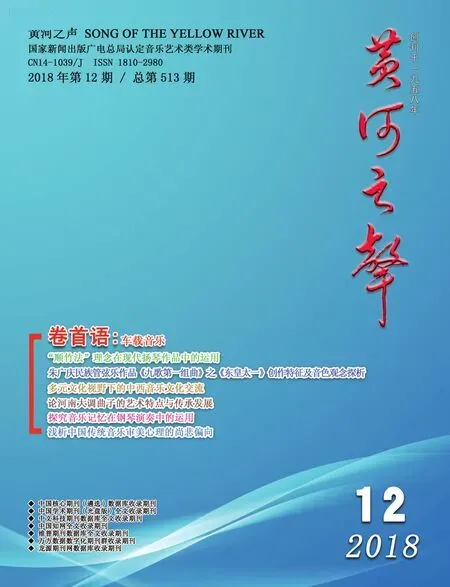二胡二重奏《中国花鼓》的演奏分析与启示
林欣欣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作品创编背景
花鼓是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歌舞形式,其曲调是在各地小调和山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作曲家克莱斯勒曾于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旅行时欣赏过当地中国移民表演的“华埠音乐”,于是有感而发运为小提琴创作了这首具有东方风格的小品。作品采用了花鼓节奏特点结合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音调而创,乐曲快速的节奏变换发挥了小提琴的跳弓、顿弓等高难度技巧。由于其独特的中国韵味而具高超的难度技巧,经过二胡演奏家姜建华移植到二胡中后逐渐被改编成二胡重奏的形式而广为流传。
二、二胡重奏版演奏分析
全曲是以G羽五声调式为主的带再现的复三部曲式结构。A段共91小节,B段共33小节,A'段共91小节。移植改编后的二胡重奏版本曲式结构和旋律基调依然保留小提琴版原貌,改编者在结合胡琴的音域的通过双声部的齐奏、对位、和声、旋律的交接等手段来展开改编。其中,二胡Ι旋律在主旋律发展的在过渡部分上进行微小的变奏,而二胡Ⅱ则基本以主旋律为主,形成了以主旋律为基调的双声部音响效果。
A段音乐主题明确而活泼欢快,采用双声部齐奏引入的方式使乐曲的主要动机得到强调。旋律主题进入的装饰音类似于模仿花鼓活动前唢呐的过门音乐,装饰音统一为上行二度加花,双声部均采用跳弓的演奏技巧来演奏,此阶段双胡琴的齐头并进应注重弓子的颗粒性。随后旋律的发展由半音的上行模进向十六分音符三连音进行推进,为20小节处的转调进行准备。此处的转调、八度大跳音程中注重音程对位和音准统一。在27小节处改编者对原有音乐材料进行解构,胡琴双声部开始构成和声上的叠置,二胡Ⅰ以上下四度的音程跳进,二胡Ⅱ以主旋律为主。在音响效果上形似鼓乐鼓点打击中的附和。要求演奏者在双声部重奏时听觉不互受干扰,坚定各自声部旋律的同时而又能聆听与其他声部构成的纵向和声。
B段从节奏和旋律较为舒缓,与A段形成鲜明对比。在音乐材料上依旧沿用于首段,旋律发展上富有叙事性和流动感,音乐结构上相当于主题再现前的一个插部。胡琴重奏版中采用的是二声部横向对话的手法来展开。该段由二胡Ⅱ先奏出,再由二胡Ⅰ进行重复。在演奏上运用了大量的附点、连弓演奏的方式,在规整的节奏中不乏为重奏预留自由发挥的空间,要求重奏者结合内心的律动调度各自胡琴本身的音色来进行发挥。整个段落对于弓法和弓段都要求合理,尽量使用内弦演奏,弓幅根据音值长短进行调整,弓毛贴弦度厚而左手揉弦浓密,演奏出醇厚而抒情的音响效果。此段旋律结尾为自下而上整体速度由慢渐快的流动型的华彩乐句。演奏中除了把握半音的音程关系及音准外,双声部的solo配合应注重音量的整体感和音色的统一性。由于二胡Ⅱ旋律先进行乐句结束后应渐慢渐弱的处理将律动顺延给二胡Ⅰ声部,而二胡Ⅰ在衔接时要把握与Ⅱ声部对话的语气感和整体协和感。因此,在两乐句音色统一外,双声部还应把握气息内在律动的衔接与默契配合,避免造成听觉效果上的脱节。
A'段部分则沿用A部分的素材,相当于A段不完全再现。在演奏上与A段一致,笔者在此不做详述。
三、《中国花鼓》对胡琴重奏的启示
(一)调性关系的明确
《中国花鼓》全曲调性色彩灵活变化,在乐曲发展的过程中频繁地进行同宫系统和近关系调的转换。全曲的调性规律对于重奏中多声部音响效果的融合具有非常高的要求。例如在A段第22小节处进行了G羽五声和降B宫五声的同宫系统转换后又分别在E徵、G商、G羽、降B宫做近关系转调。要求重奏者对于各自声部调式调性的切换要明确,在把握不同调性旋律的音程关系以及作品曲式结构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分声部的单向练习,明确调性关系进而在重奏中树立外部听觉的音准观念。
(二)音乐表现中共性与个性的平衡
《中国花鼓》全曲运用了大量切分、附点、十六分三连音、颤音、前短后长等音值节奏组合,力度由弱渐强地表现典型花鼓乐的音乐特征,在双胡琴重奏中应运用共性技巧来塑造其音乐表现特性。在齐奏的部分时,双胡琴应随着音值组合的疏密、节奏的变换、调性的转换来统一配合。此外,还需统一齐奏时的弓幅的和弓段来把握重音和节奏的共性特征,在由弱渐强的模进中塑造花鼓声层层递进的音乐表现。在华彩乐段的对话乐句中双声部虽得以各自solo,但在自由发挥的空间内不能过分超脱节奏限制。同时,由于胡琴材质、演奏者演奏习性的差异,胡琴重奏时主旋律与复旋律声部应把握各自的旋律特性,各个声部在个性体现时应从音色、音量上寻求双声部最佳的平衡点,在共性与个性中寻求多声部音响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