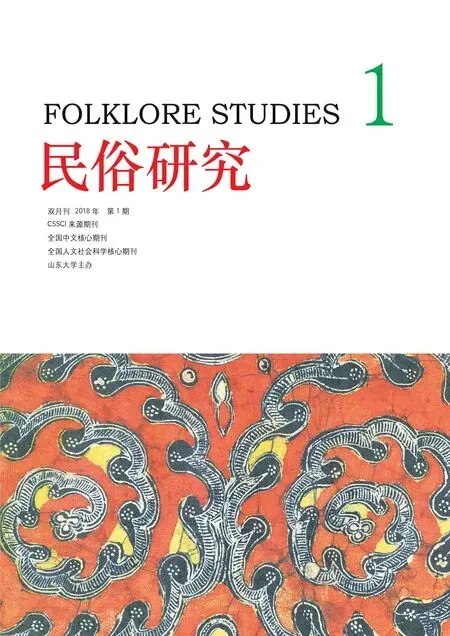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
张举文
一、引 言
中国文化之所以独特于目前世界上的其他文化(除了犹太文化之外),延续不断地发展了几千年,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的文化自愈机制所展现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并在该文化陷入危机时,驱使其寻根,从中获得自觉和自信,然后达到文化自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便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实践史和发展史:她在经历了各种内忧外患的大动荡后,最终因其内在的文化自愈机制,得以在其根文化之上获得再生和发展。因此,对文化自愈机制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能延续如此长久,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文化史上有许多文化没能得到延续。
仅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当前的社会和文化实践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个机制的运作。从1840年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化一直在危机和困惑中寻找出路。从十九世纪末的“变法”运动到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直至二十世纪末的“寻根”运动,中国文化开始从困惑中获得自觉,开始认识并回归到自己的根。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自觉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非遗”运动,使得不同背景的平民百姓有机会、有权力回归到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文化自信,激活了中国文化内在的自愈机制,通过新时代的“本土化”或“中国特色”,最终获得新的生命力。
本文力图从日常实践,即民众的民俗生活,寻找和梳理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内在逻辑及其文化自愈机制;从表面无序的日常实践中认识其有序性;从似乎不合理或无意义的实践中理解其合理性或意义的形成与维系;从民众的日常生活角度来理解抽象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通过提出文化自愈机制等新概念,本文期待引发同仁思考,特别是针对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持续性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实践问题。但在探讨文化自愈机制前,有必要说明本文中几个相关的关键概念。
“中国文化”是泛指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融合了历史上诸多族群文化的、广义的中国文化。“中国”本身犹如“一条河”或“一棵树”,所以,这个动态的文化也是杜维明的“文化中国”*Weiming Tu,“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Wei-ming Tu (ed.),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34.概念的核心部分。而这“河”或“树”的源头,便是对“久”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中国文化延续的驱动力,表现在“心性”这个概念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参见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民主评论》;《再生》新年号,1958年;另见《唐君毅全集》(卷四之二),39卷本,九州出版社,2016年。对应于这些哲学概念的日常生活实践处处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根基,即“核心信仰与价值观”,比如灵魂不灭的生命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儒家天下“大一统”的世界观,入乡随俗的文化共存与适应变通的生活态度,和而不同的生活哲学,趋吉避凶、积极主动的生活实践,等等。*参见Juwen Zhang,“Cultural Grounding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oon Man’ Figure in the Tale of the ‘Predestined Wife’ (ATU 930A)”,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7 (503), 2014, pp.27-49(另见中文译文《“定亲”型故事中“月老”形象传承的文化根基》,桑俊译,《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Juwen Zhang,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Making: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Diasporic Folklore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28 (510), 2015, pp.449-475(另见中文译文《美国华裔文化的形成:散居民民俗和身份认同的视角与反思》,恵嘉译,《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
基于这些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而展示出的文化传承发展力便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传统传承与演变机制”的核心力量。它驱使一个文化从自觉到自信,从危机中获得康复,达到自愈和新生。它不仅体现在一个具体传统事象或一个文化体系的传承进程中,同时也表现为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是维系该传统的动力。“传统”便是日常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流动的进程,不是静态的结果,所以它的存在本身表明了它具有不断适应和吸收新文化元素的能力和进程。这样的“传统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中。由此而形成的“持续性”本身也证明了“文化创新”(“第三文化”)的过程——在多元文化冲突的困惑中,基于其“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而获得“文化自觉”(其实质是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根的认同),进一步展示“文化自信”(其实质是在跨文化或多元文化交流中,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建设和维系“文化平等观”;把握不好或错误认识这个平等观,便会导致“文化自卑”或“文化自大”,引发新的“文化危机”),从而达到“文化自愈”。这个过程就是“文化自愈机制”:一个文化不仅能在危机中重新回归其根本,更突出的是能吸收新文化元素,达到文化创新,从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有关“生命力”与“有效性”,以及“核心符号”与“随机符号”概念,参见拙文《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有关“民俗认同”和“第三文化”等概念,参见拙文《美国华裔文化的形成:散居民民俗和身份认同的视角与反思》,《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
二、从陷入文化危机到走向文化自觉的曲折历程
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延续展示了螺旋式上升的“过渡礼仪”式进程。*有关“过渡礼仪”的理论概念,参见[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有关“过渡礼仪”的“社会阈限”意义及其分析应用,参见拙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Juwen Zhang, “Recovering Meanings Lost in Interpretations of Les Rites de Passage”, Western Folklore, 71(2), 2012, pp.119-147.从一个文化陷入危机到寻根,再到获得自愈和新生,这可以被视为一个“过渡礼仪”周期;不是仪式意义的,而是以此形式分析来认识社会发展进程。但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不是突变的,而是渐变的。每个阶段的变化动因或是来自内部,或是借助外力。每一循环的过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构成特定的进程形式和内容,达到特定的目标。无论是对一个仪式,还是对一个社会和文化,如此的过渡都必须是基于对其核心信仰和价值观体系的认同,只有这样才有所谓的文化发展。否则,一个个体、群体、社会或文化便会在阈限期的剧烈社会和文化震荡中失去“自我”,以致“消失”(人类文化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能够从困惑的边缘阈限期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文化,最重要的是能从自己的文化中获得自觉,发现内在的生命力,并藉此内驱力,启动其自愈机制,重构有生机的新“认同”。
(一)陷入危机:从社会阈限到文化阈限
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标志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彻底陷入困惑和危机,陷入社会和文化的“边缘”和“阈限”期:国家被瓜分,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战乱饥荒等动荡而彻底进入“非日常”。这是一段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文化毁灭期。而此前的近三百年便是从日常逐渐“分隔”到非日常的过渡期。此后又是从“非日常”向“新日常”的逐渐过渡期。在此社会边缘阈限期,文化精英感到极大困惑,挣扎着寻求自觉的出路,而这样的文化挣扎直至二十世纪末才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目标和途径,也就是对文化之根的自觉。*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3期。另见,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而这段历史也证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以及传承都离不开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二)在危机中寻求文化自觉
虽然上述那个阶段的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没能达到所希望的目的,但每一次都为达到最终目标向前过渡了一步。这些努力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在国家层面,即,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精英所推动的“变法”。在面对西方政治军事和文化强力“取代”中国本土力量时,他们坚持的是当时诸多精英“发现”的“以夷制夷”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本身是没有中国文化根基的:一方面,中国文化失去了话语权;另一方面,“以夷制夷”的意识形态根基不是“共存”和“和而不同”,而是在“生”与“死”的对立中求生。同时,他们所坚持的“国粹”不是有适应和变通的生命力的那部分核心信仰与价值观。这一切显然注定了整个精英和国家以及他们自己的悲剧结果。中国文化哲学之根是在社会和精神生活等方面,通过“共存”和“和而不同”以达到“久”。哲学家张君劢在1936年就提出,“自内外关系言之,不可舍己循人”,也就是不可全盘西化;“自古今通变言之,应知因时制宜”,也就是对新文化做的和而不同。*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元代和清代尤其明显。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借助武力的意识形态侵略下,中国人在极大程度上“失败”了:不只是武力上的战败,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失去了“自觉”,陷入了“自否”和“自卑”,也就谈不上“自信”了。
其次,从精英阶层看,即,“西学”影响下的精英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其高峰是“五四”运动。这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大影响的运动,是一场比较彻底的文化革命,包括引进马克思主义。但是,新文化运动是基于西方的思维,而不是中国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体系,其逻辑是:导致中国当时局面的原因是政府无能,那就必须彻底推翻;控制中国统治者的是西方强势,那就必须以流血的代价赶出侵略者;导致中国落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那就必须用西方先进文化取而代之,包括将汉字彻底罗马化,等等。这些都充满了二元对立的“革命”气势,其中对儒家的彻底批判同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出现。这一系列的文化革命没能确立或回归到中国文化之根,没能从传统文化中激活自身的自愈机制,也就无法走出阈限的危机。
第三,精英对民俗传统的关注。“五四”时期的“走向民间”征集“歌谣”无疑奠定了中国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基础。但是,这阶段对“民俗”的关注显然是因为“西学”中的“民族主义”影响,关注的不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之根,而是从燃眉之急中拯救中国,激发爱国热情,建立一个可与西方同日而言的现代国家。这一系列有关民俗与民族主义的活动都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有关系,而他是当时留(访)学德国并关注“民族学”的精英代表。所以,中国现代精英文化,包括民俗学,从其形成初期,即使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思辨,也都深深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那时的“民”不是平等的“平民”或“公民”。直到21世纪,民俗学仍在努力从“民族文学”或“民间文学”的狭隘根基范畴走出,将眼光不再“向下”,而去探索每个“民”的“日常生活”新天地。*例如,2016年9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民俗学与人类学‘日常生活’专题讲演”;2016年11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论坛”,以及日益增加的有关日常生活的论文。
这几个层面的危机和困惑期的共同点就是国人对自身传统或自我文化的否定,“反而自鄙夷其文化”*张君劢:《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在寻求构建新的国家和国家认同时,精英们没能更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华民族”?谁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何以存在如此之久,还会有希望吗?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寻求不断,但得到符合历史文化逻辑的答案不多。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有国家和国际影响的文化“宣言”中得到证明:1935年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年元旦,哲学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在《民主评论》上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其中,只有1958年的宣言才揭示了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根,指出了符合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中国文化之路。显然,只有在深入思考和弄清“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是什么,并能回归到这个根时,才能为文化自信找到出路,达到文化自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质问这些同样的问题中,精英们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清醒的自觉,以致构建起文化自信。
(三)从自觉到自信的过渡
从1976年到2003年“非遗”在中国的出现,中国文化在经历了艰苦的反思和寻根后,开始从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二元对立革命论中觉悟到中国文化的包容共存观,在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中找到了自觉和自信。这是从边缘阈限的危机困惑期向获得新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过渡,是从“非日常”过渡到“新日常”的阶段,也是从自我否定走向自我肯定的阶段。
由于国家的关注点从政治和文化转移到经济建设,这阶段也提供了中国文化的“休养生息”的机会,使精英们更深刻地反思过去的自觉努力,有目的地构建新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现的“文化热”,不但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如,“翻译热”所传播进来的西方思想),而且是比上一次(新文化运动)更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二十世纪末的文化热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和逻辑: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落后;中国文化的落后是因为有不同于先进的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依此逻辑,中国的“黄土”文明在“基因”上就是落后于西方的“海洋”文明;必须“全盘西化”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这些“革命”思想,都是根植于西方“对立论”和“中心-边缘论”:新的必须取代旧的;革命就不能协商、不能共存。
然而,此后几十年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证明那不符合中国内在文化机制的逻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中国人觉悟到:只有回归和守住传统文化之根,包容多元文化,才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在生活实践上,以“并置”(而不是排斥)来接纳外来文化,在共存中将其“本土化”,并在此进程中,与时俱进地融入世界文化发展之大势。正是这样的自觉才引发出随后的文化自信的建设,并激活文化自愈机制。
三、作为中国文化自信与自愈的一个转折点的“非遗”运动
2003年传入中国的“非遗”概念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当然,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始于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通过“非遗”这个转折点,中国人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理性的自信认识过程,也开始激活其内在的自愈机制。最核心的自信表现是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并置”,而不是全盘接受或全盘排斥的“革命”行为。这是进行“中国特色”的改造,将异文化和新文化“本土化”。但是,“非遗”本身并非灵丹妙药,因为它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也揭示了人类多元文化价值的矛盾体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非遗”概念中的“普世”价值观完全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非遗”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世界文化背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但是,该《公约》执行的“标准”是基于西方的价值观;只有反映西方价值观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才能被列入此名录。经过四十年的实践,对“遗产”的选择和评定的“普世”价值标准愈来愈受到非西方国家的质疑。于是,2001年,联合国有关组织发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成为《文化多样性公约》,其目的是修正之前的“普世”标准。*Sophia Labadi, UNESCO, Cultural Heritage, and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Value-based Analys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3;Lourdes Arizpe and Cristina Amescua,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Y: Springer,2013.基于同样的目的,2003年,该组织发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公约》(2006年生效),即本文所指的“非遗”或《非遗公约》。至此,这三个公约(1972,2005,2006)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公约。但是,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没有加入这些公约。其原因不仅仅是价值观的判定标准,也有相关的经济利益问题,同时,也说明在“文化多样性”和“非遗”等概念上,西方世界内部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2016年,颁布《非遗公约》的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这充分说明在整个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
无论如何,“非遗”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特别唤醒了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加强了在世界范围上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接受和保护,并使发展中国家为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这些方面都极为明显地体现在中国的实践上。当然,必须承认,中国的“非遗”运动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非遗”中的许多问题常常被掩盖在对GDP的追求之下。或者说,不应该忽略经济基础对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没有经济基础的文化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四、文化自信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文化自信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从中还能够辨析自己历史和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而发扬精华,进而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找到共生共存的出路,达到文化自愈。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最终表现是“本土化”,即,通过吸收包容,在“和而不同”中将异文化融合为自己的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渡过社会阈限和文化阈限期,最终建立新的日常生活模式。这些表现可以从国家、精英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国家层面
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正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大国”(世界级非遗有50余项)。具体表现在这些行动步骤:2004年,中国加入《非遗公约》;2005年,国务院《通知》设立“文化遗产日”(2017年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0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至2015年已经有五批);第一批传承人名录(至2015年已经有五批);201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些动作,对建立国家、省、市和县四个级别的“非遗”名录和保护制度,都发挥了指挥棒作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个困境,与其说是经济的,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更具体地说,是关于“传统文化”的,因为,整个辩论的焦点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
作为这个时代的最有智慧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化自愈机制的表现,中国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持续发展至今。这个模式便是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同时,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历史上看,这显然是中国文化多元“并存”模式的再实践。可以说,如果不是这个制度,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
对应于这个经济模式,最突出的政治政策是针对香港(1997)和澳门(1999)“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的实施。这是极大的政治自信的表现。世界上任何国家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中的“有容乃大”与“和而不同”思想,中国的政治局面不会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国两制”均是把在西方智慧看来完全对立的两个部分,并置于一个结构之中,使它们不仅能够并存,还可以相得益彰、有机发展。
在涉及到核心信仰和价值观方面,中国政府与梵蒂冈的关系经过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发展,以及之后三百多年的对立(即“礼仪之争”),至今已经有了很多的缓和。*“礼仪之争”是天主教教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直到1939年,梵蒂冈,即罗马教廷,才撤销对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隔离和紧张。1954年,中国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在国务院下成立“国务院宗教事务局”。1980年,“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成立。这是中国基督教会的全国性教务组织,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依法管理和国家民政部的社团管理监督。1988年,中国基督教协会正式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98年,国务院决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下设不同部分负责主要宗教。经过这些年的紧张关系,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迹象表明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有所缓和(如,2014年,新教皇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互动;2014年8月14日,罗马教皇方济各对韩国进行5天的访问,罗马教皇第一次被允许飞越中国领空(过去都是被拒绝的),并向飞经国的领导人发送电报表达问候(http://news.qq.com/a/20140814/047164.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中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和教堂数量有了极大增加,而同时,其他信仰场所和机构及其信徒也不断增多。中国政府有关信仰的政策也有了明显调整。*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另见,Fang Xiao, “The Predicament, Revitalization, and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Western Folklore, 76 (2), 2017, pp.181-196.
从国际文化交流层面看,在各国举办“中国文化节”和“孔子学院”便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自信表现。例如,美国的“史密森民间生活节”是其唯一国家级的年度多文化庆祝活动,其2002年和2014年的主题都突出了中国文化。从中国的内部历史与文化发展来看,因为儒家思想是上述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待其代表人物孔子的态度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向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变化。
有关信仰方面的政策变化是“非遗”的重要影响结果之一。在保护“非遗”中,具体的做法是对非遗的分类,但是,现有的十个分类中没有“信仰”。而本文所论及的最关键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那么,如何理解“信仰”没有被界定为一个“非遗”类别的现象?答案就在遍及全国乡镇和都市的“庙会”和类似的实践之中。
例如,河北石家庄赵县范庄的龙牌会是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范庄人自认为是勾龙的后代,视范庄为勾龙的故乡,并制成“龙牌”来敬仰供奉。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范庄都要举行盛大的祭龙活动,周围十余个县的各式民俗艺术家也前来助兴演出,共同表达对龙的崇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地方传统被视为迷信,被禁止。之后,得到恢复。但是,在“非遗”运动中,为了被视为“遗产”,地方政府利用过去举行崇拜仪式的寺庙建立了当地的文化博物馆。于是,出现了一个建筑物有两个名称的现象。*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通过这样的策略,这个活动项目在2007年被列为省级文化遗产之一(目前在申报国家级)。至今,许多地方的“庙会”已经成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遗项目。
与“双名制”类似的另外一个事例是北京地区最有名的“妙峰山庙会”活动。它是二十世纪初一些民俗学精英用来论证中国信仰实践的“试验地”。民俗学者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九十年代期间,妙峰山庙会一直被视为“封建迷信”。1993年,妙峰山乡政府出面举办了第一届妙峰山庙会。*包世轩:《妙峰山庙会》,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Haiyan Lee, “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 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 (1), 2005, pp.35-65.而在2009年,这个庙会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作为“民俗”类下的“庙会”小类)。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个庙会的确是越来越吸引人,成为北京地区一个重要的信仰场地。这样的实践例子正是中国文化的运行机制,尽管这被视为是“实用主义”的做法,与国家政策“打擦边球”;利用“香会”和“庙会”两种不同的名义举行以信仰为中心的活动。*李华伟:《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妙峰山庙会之影响——以妙峰山庙会申报非遗前后的活动为中心》,《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6期。这样“双名制”或类似的“多名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兼容”和“并置”,是文化自愈机制的一个重要运作行为。*民俗学家吕微(《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高丙中(2006)有关“龙牌会”的“双名制”讨论发掘出了“民众”的作用,也是构建“公民社会”的极好例子,并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哥白尼式”的发现。
(二)精英层面
在精英层面,最大的变化是通过二十世纪末的文化思辨而出现的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体系的再认识和回归:精英们认识到“全盘西化”不是符合中国文化逻辑的出路;只有对异文化进行“本土化”后的“和而不同”思想才能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文化自愈机制运作的开始。在此过程中,借助公共媒体,精英们前所未有地参与了国家文化政策的修改和制定。例如,中国政府在民俗学者的建议下,于2007年将部分传统节日纳入国家节假日体系,这便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极端“西化”行为的修正。*参见中国民俗学会编辑的《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和《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学苑出版社,2007年);另见,Fang Xiao, “The Predicament, Revitalization, and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Western Folklore, 76 (2),2017,pp.181-196).例如,当1912年开始新的纪元时,西方的格里高利日历被定为官方日历。但是,中国传统的日历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根:从信仰到农耕作息。于是,作为“并置”,西方的“新年”在新的日历中不变,但传统的中国“新年”以“春节”并存。这便造成中国有了两个“新年”(高丙中:《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之后,“革命”的意识形态将传统的节日定为“封建”的,即使是最重要的“春节”也被改造成“革命化春节”。于是,传统的“清明”和“中秋”等以“家”为核心的节日不被列入国家的“节假日”体系。借助“非遗”,民俗学者使得政府接受了建议,促使这两个曾被“忽略”的传统节日又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正是这些节日才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重新强调这些节日,毫无疑问,是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的表现。
民俗学者参与“非遗”运动,也创造和发展了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契机与动力,由此发挥了有别于其他国家民俗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当然,其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共存。*高丙中:《民俗学的中国机遇:根基与前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从二十世纪初的“民族主义”精神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寻求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重构国家和“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这期间贯穿着同样的矛盾: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可以并存吗?现代科技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可以共存吗?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能否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持续?民俗学者在文化自愈进程中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些都是中国民俗学学科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民俗学者被深深涉入非遗运动中,但始终存在很多质疑和反思,例如,对“民俗学与非遗”的两难问题和民俗学者的角色问题(参见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吴秀杰:《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民俗学真的面临两难选择吗?》,《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公共民俗学作为一个概念在民俗学界有不少讨论,但在非遗实践中,并没有被认真思考,因此,民俗学家周星便指出了“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和危险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通过参与非遗运动,“非遗学”的出现便说明了这个新领域的潜在影响(如,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以及相关的课程或课题。同时,高等学校的“非遗”研究中心不断增加,呼应着各级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的“非遗中心”等机构的不断涌现。其中最突出的是相关的“文化产业”专业的建立(参见白云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中华书局,2013年;蔡靖泉:《文化遗产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必须去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看他们如何在吸收包容不同文化元素时维系自己的根。
(三)民众层面
民众的日常生活表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程度。或者说,每当政府和精英真正关注民众,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对传统的传承实践时,这个社会展示的是正确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些表现可以说明,在维系文化之根的基础上的创新才是有生命力和自信的真实表现。
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通过政府和精英执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加上“非遗”的进入日常消费生活,中国百姓对“非遗”的认识可能超出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非遗”不仅是政治词语、文化词语,更是经济词语,甚至是日常消费词语。当然,重要的是,它也是文化协商的话语。其中,媒介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民众在获得文化自觉和自信过程中参与文化自愈的行为表现。
例如有关“外国人”的日常言语表达。曾几何时,中国人对欧美人的称呼有两种文化信息:一种是自卑的,如“洋人”“西人”“贵宾”,以及“外宾”等;一种是自大的,如“鬼佬”“洋鬼子”,以及“番人”等。直到二十一世纪,“外国人”“老外”等称谓,或“美国人”“日本人”等,进入官方和民间的话语。这体现的是趋于平等的文化交流观。
例如当前的“大妈舞”或“广场舞”流行于各地的公共空间。它吸引的不再仅仅是“大妈”,而是处于各种年龄、有着各种背景、来自各种行业的男男女女。它不只是一种民间娱乐形式,同时还体现了民众在获得文化自觉而自信后,通过民俗活动创造生活意义的手段。这是传统地方舞蹈(如秧歌)和西方现代舞蹈(如华尔兹)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吸收融合,进而所创造的新文化表现。这里所体现的自愈,不仅是国家文化层面的,也是群体和个人层面的,特别是个人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的体现,是对自我认同和自我传统的自信。
“麦当劳”等西方“现代生活”符号在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和自信。从“正宗西餐”到“快餐”再到“垃圾食品”,中国人的认识从“崇拜”转到更客观的看法(接受西方的“垃圾食品”说法)。同时,各种西餐或快餐也注定会成为与中国本土不同菜系并列的一种“地方菜”。*至2017年10月,麦当劳在中国的26年里共开设有约2500家店,并计划到2022年开设到4500家,但是已经成为中国本土公司,正式更名为“金拱门”(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8-08/doc-ifyitayr9813546.shtml)。有意义的是,当各种外国餐饮在中国流行的同时,中国地方的、传统的及创新的菜系菜肴也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不是让步于外来的饮食。
再如圣诞节的“中国化”“本土化”或“在地化”。除了商业化的层面之外,中国人将“苹果”与“平安夜”联系在一起,也是中国文化中的谐音象征的一个典型例子。此外,将“平安夜”与“守年夜”联系在一起;将长青的“圣诞树”与金黄的“摇钱树”联系起来,等等。可以肯定,“圣诞老人”“圣诞树”等圣诞节符号在中国将会越来越“中国化”。“观音菩萨”不是到中国后成为“送子”的“女性”了吗?
五、文化自愈机制的实践
如上所述,一个文化在从失去文化自觉到获得文化自信的过渡进程中,其内驱力体现出的是文化自愈机制。对中国文化来说,自愈机制的核心是“本土化”——基于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通过适应和吸收新文化,从而构建与时俱进的新认同。这些认同存在于个人、群体和国家等多个层面。这个机制所表现出的几个方面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具体可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基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并存的价值观;对民俗传统以遗产化和产业化为发展方式;通过本土化达到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现实。
(一)“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并存机制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体系中的一部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并存机制,在生活实践层面,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延续不断的文化特例,并且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机制的核心是那些认同“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的“中国人”(或“华人”“华裔”;泛称Chinese)*Weiming Tu,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Wei-ming Tu (ed.),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34. Also, Yih-yuan Li, “Notions of Time, Space, and Harmony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n Junjie Huang and Erik Zu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E.J.Brill, 1995, pp.383-398.,对其“根”(如上文所引用的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论)的认同与维系。无疑,“中国”和“中国人”都是几千年来多元文化群体的混合结果。“中华民族”(或“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语)准确地概述了中国文化发展历史。所谓“正宗”“纯正”或“本真”等概念无非是构建权力的话语。今天,人类文化历史清楚地表明,维系文化传统的是吸引和包容不同文化及其实践者的“民俗认同”(即共同的生活方式是群体认同及其传统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基于“种族”或“人种”的“民族认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其前提是对此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将是不是“中国人”这个“血统论”(如,所谓的“种族”或“民族”,或政治身份)作为前提。*有关“民俗认同”(folkloric identity)的概念,详见Juwen Zhang,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Making: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Diasporic Folklore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28 (510), 2015, pp.449-475,另见中文译文《美国华裔文化的形成: 散居民民俗和身份认同的视角与反思》,恵嘉译,《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
(二)“非遗”的遗产化和产业化
“非遗”在中国的成功“本土化”实践证明,它离不开两个必要的“变压器”:一个是“遗产化”,另一个是“产业化”。这两个方面,在文化自愈机制中,如阴阳平衡机制一样,成为相辅相成的矛盾体。
其实,“遗产化”机制始终是中国文化发展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对传统或过去的人物或传统事象的遗产化,是获得权威和话语权的一个必要过程。因为中国文化中,“尚古”和“尊老”是根植于“祖先崇拜”的核心信仰(即,灵魂不灭)。那些“传承下来的”就比“新的”有更大的权威和权力,也更容易得到实践者的认可,由此更好地将传统传承下去。同时,这也意味着,遗产化了的传统需要“仪式”(本身就包含着神秘力量)来在现实中发挥其权威作用,从而得到敬重。这也是中国“礼”(或“礼仪”“礼俗”)文化的核心。中国民间生活中的“神”许多都是历史人物的“遗产化”的结果,如,广为流行的“关公”崇拜(即,关羽从历史人物到战神再到财神)。“遗产化”的逻辑和机制直接服务于维系日常生活的“日常化”,也就是保持与传统的连贯性,将现行的传统与外来的文化结合起来,使其本土化。
中国文化的“文化发展”就是“文化生产”,就是“产业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产业发展与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将文化“商业化”也是平民日常消费生活必需的。在现代大规模的商业经济模式下,许多传统的(手工)“产业”模式无法存在,自然要创新出适合当代的“产业”。*例如,虽然传统的手工剪纸仍然存在,但是其“产业”无法满足更大的市场的需要。于是,“非手工”的剪纸便成为“产业”。表面上,批量生产没有“传统”的工艺,似乎不“正宗”(没有本真性),但实际上,正是通过“产业化”才使得剪纸在更多的范围得到传播和交流,从而有经济条件维系这个手工传统的传承。产业化不只是商业化,它强调的是对传承人的培养,对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即对传统艺术(表演)的实践,并通过在公共空间的展演,达到对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的公众教育的目的,以致在经济和文化层面消费传统,最终获得文化自觉和自信。把传统界定为“纯正”或“本真”(“原生态”)、非盈利,或“神圣”的,从而与追求“利润”的或“世俗”的商业化对立,这本身是构建出的抽象的理论命题,脱离了现实。没有经济利益支持,就没有传统的发展;传统总是与现代性携手共进的。*例如,2014年,国家对非遗保护的财政支出是88.43亿元人民币(2013年是77.3亿)。75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得到资助,1735名非遗传承人得到师徒传承项目的资助,并建立了十个国家级的文化生态保护区(http://www.wenwuchina.com/news/view/cat/20/id/227680,2016年4月27日)。此外,2014年设立了非遗保护基金会,协调非遗的保护(http://www.cssn.cn/zx/bwyc/201411/t20141104_1389079.shtml,2016年4月27日)。中国的实践似乎证明,“产业化”为保护那些濒临消失的“遗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文化产业化,包括“非遗”产业化,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一方面,它可以改善有关民众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传统文化的精神生活层面。同时,也在个人、群体以及国家层面提供了构建或重建文化认同的条件。这也意味着其中的一个关键是要协调好传统的手工产业与现代商业产业的关系。
传统的消失与否,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的生命力。或者说,那些基于核心信仰和价值观体系的传统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命力;反之,那些不是根植于这个体系的习俗,则更多地依赖其有效性或实用性。当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时,那些更多地基于有效性的传统自然就会消失。*张举文:《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三)以“本土化”达到文化和谐
如上所论,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的最高表现就是对新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最终达到“本土化”的创新。的确,上面提到的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事例说明,这种创新也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历史上的“三教合一”和佛教的“中国化”丰富和巩固了中国文化的根基。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以及进行中的“圣诞节中国化”和“中国情人节”等日常生活现象,都说明了这是中国文化自愈机制的必然结果。
对本土化问题,有必要从其形式和目的两方面来认识。在形式上,表现之一就是对新文化元素的“中国特色”“命名”或“译名”。在这方面,中国语言文字发挥了独特而重大的作用,即以谐音象征达到意义的包容。另一种方式便是以“改名”或“双名制”(“多名制”)来缓解文化冲突,达到“和而不同”,形成“并置”“共存”事实,如上面所列举的对待西方节日和饮食的反应。能够做到这些,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并遵循内在的文化逻辑。
在内容上,本土化必须基于外来文化元素与本土文化元素的表现形式背后的内在联系之上。例如,在唐朝,大量的外来故事随着佛教的兴盛被融入中国文化,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被融入的故事在其类型和母题上与中国过去已经存在的故事有着极大的相似或相关性。*Juwen Zhang, “Cultural Grounding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oon Man’ Figure in the Tale of the ‘Predestined Wife’ (ATU 930A),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7 (503), 2014, pp.27-49(另见中文译文《“定亲”型故事中“月老”形象传承的文化根基》,桑俊译,《民俗研究》2017第2期); Juwen Zh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elf-Healing Mechanism in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Folklore, 76(2), 2017, pp.197-226.由此,本土化通过为原有母题和意义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有效性而强化了本土的多元信仰和价值观,也丰富了本土的文化表现形式。
总之,在认识文化融合上,必须清楚,不存在“纯正”或“本真”的传统;所有传统都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正是在混杂中才有新文化,即“第三文化”的产生。*Juwen Zhang,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Making: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Diasporic Folklore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8 (510), 2015, pp.449-475,另见中文译文《美国华裔文化的形成: 散居民民俗和身份认同的视角与反思》,恵嘉译,《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由此可见,“本土化”在目的上不是对立,不是有你没我;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正是人类文化发生和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六、结语:中国的“非遗”实践经验与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中的自愈机制
通过审视中国的“非遗”实践和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我们也可以反思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许多曾经存在并辉煌的文化现在只是存在于文献中,或是深深地被融合在其他文化中,成为象征符号。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为某种原因,该文化群体的成员无法延续或不再实践其传统,故其文化载体不存在了;另一个原因是该文化体系中缺少或无法激活其自愈机制——例如,遇到外来文化较强大的冲击时,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改变了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进而彻底失去自己的文化。不论是哪种情况,其关键是对自己文化之根的迷失。这些现象似乎在我们当今的后殖民时代依然继续着。近五百多年的殖民与反殖民历史就突出了这一点。有理由相信,本文所提到的联合国的多个公约,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对这个历史的再认识和修正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中国文化利用了这个历史机遇:在对根的回归中,通过激发起内在的自愈机制,为其当代实践注入新的生命力。
近两千多年,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似乎可以概括出这样两种:一个是基于一神信仰的机制,可称为“中心-边缘”二元对立论;一个是基于多神信仰的机制,可称为“和而不同(共生共存)”论。前者以犹太-基督教文化为代表;后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虽然中国文化是人类持续不断发展几千年的文明之一,并通过其本身展示了其内在的自愈机制和生命力,但是,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里所说的两个体系,有各自的维系机制,但当两者相遇时,其冲突是明显的、严重的。中国文化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这两种模式的“交战”之地,但是,每当中国文化能够回归其根,便展现出有效应对挑战的文化生命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便是一个新的例证。
所以,对中国文化自愈机制的探讨也是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传承机制的一个有益途径。中国的文化自愈机制也表明:在应对“全球化”浪潮时,要坚持维系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和而不同中多元发展,而不应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统一化”。人类文明正是在多元化和多样性互动中,而不是在“统一化”或“标准化”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非遗”运动的全球化趋势迫使我们反思:是否存在适于所有人类文化的一种“普世”价值标准?不同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和自愈机制如何在新时代发挥作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将会如何持续?
其实,民俗学家一直在用同样的逻辑追问一个具体传统的传承与演变机制问题。这也是研究传统或民俗的一个根本问题。现在,我们知道传统的传承掌握在实践者的手中*William Bascom, “Four Functions of Folklo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67 (266), 1954,p.343;Jan Harold Brunv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New York: W.W.Norton, [1968] 1978, p.1; Henry Glassie, The Spirit of Folk Art. New York: Abrams, 1989, p.31; Barre Toelken, The Dynamics of Folklo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32.,但是,还要追问是什么使得实践者选择传承延续或抛弃一个传统。*张举文:《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Juwen Zhang,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Making: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Diasporic Folklore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8 (510), 2015,p.467.本文所探讨的问题试图揭示文化传统传承的一个内在机制:只有根植于一个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传统才能展示文化自觉和自信,才能维系实践者的认同,在面临危机时,才能激发其文化自愈机制,维系其传统之根,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