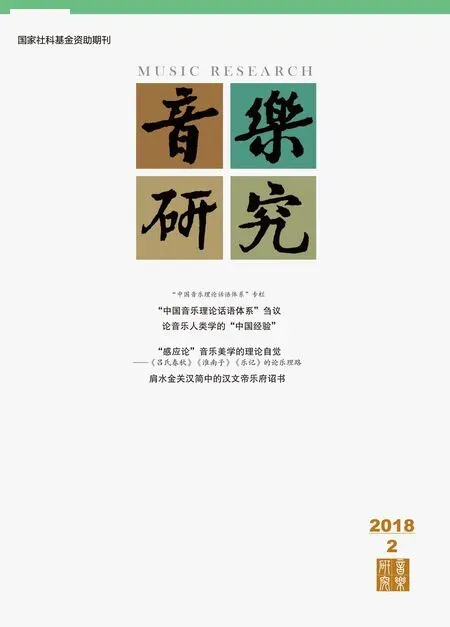“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刍议
文◎杜亚雄
2017年11月3—5日,首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学术讨论会”在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这是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会议,近百名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十分热烈。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受大会组织者的委托做了总结发言。“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当前中国音乐学界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新任务,笔者不揣冒昧,撰写此文,就此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望大家批评指正。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①《论语·子路》。按照孔子的意见,“兴”“礼乐”,先“正名”,“名正言顺”“事成”之后,礼乐方兴。大乎言哉!要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先也要“正名”,不但要搞清楚“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概念,而且要弄明白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这一词组中,“理论”是核心词。“中国音乐”是修饰“理论”的,而“话语体系”则是“理论”及其知识体系借助语言进行表达的方式。因此,要打造“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先要搞清楚何谓“理论”,其次要弄明白什么是“音乐理论”,最后要给“中国音乐理论”定义。在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明确后,方能知道何谓“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才能为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而奋斗。
“理论”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动词,意为“说理”。如《华阳国志》中讲李苾“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②《辞源》,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18页。,又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中武松和武大郎告别时说:“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③施耐庵《水浒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89页。作为名词的“理论”,是日本人为翻译英语中的“theory”一词,采用我国唐代诗人郑谷的诗句“理论知清越,生徒得李频”④刘正埮、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诗中的“清越”是一位擅长写诗的高僧;李频(818—876),唐代诗人,历代评其诗“清新警拔”“清逸精深”。中的词汇而成。这个词和“经济”“社会”“知识”等名词一样,在现代汉语中是源自日语的外来词。
汉语中许多源自日文的外来词,不仅用汉字书写,且有“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使人不易察觉是外来词。像“布尔什维克”“的士”这样的音译外来词,国人不会以为它们和“布匹”“士大夫”有任何关系,而面对“剩余价值”和“异物”这类源自日文的外来词,有人就会不了解前者是德语“Mehrwert”的意译,指“由工人在生产剩余产品的时间内所创造的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的那部分价值”,⑤刘正埮、高名凯等《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而后者是英语“alien substance”的意译,系指“不应进入身体内部的非生物体”,⑥同注⑤,第389页。可能会“顾名思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作为名词的“理论”和古汉语中当动词用的“理论”不同,前者指的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和原理的体系”。⑦同注⑤,第207页。我们当然不能按照古汉语中的词义来理解,更不能“顾名思义”。“理论”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概括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的研究成果。
既然日文的“理论”是英语“theory”一词的意译,而中文的“理论”又是一个源自日语的外来词,指的是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成果。那么,英语中作为音乐术语的“theory”到底是什么意思,需认真加以探究。
“Music theory”(“音乐理论”)在英语中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music theory”包括基本乐理中所有的内容,而狭义的则指根据音乐创作实践概括总结出来的作曲技术理论,⑧“Karp Theodore”, Dictionary of Music, 第 392 页,Evenston :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83.就是我们常说的和声、复调、配器、曲式“四大件”。在英语国家中,“music theorist”是指作曲技术理论方面的专家,而非音乐学方面的专家。
“音乐理论”和“音乐学”既有联系,也有很大区别。“音乐学”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中称为“musicology”,是由“music”和“logy”两个词干构成的一个复合词。“music”说明这个学科研究的核心对象是音乐,而“logy”则是学科名称。据严复先生考证,“logy”和“logos”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两个词在汉语中一般译为“逻辑”或“逻格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或“存在的规律”。严复说:“按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格斯一根之转。罗格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伦理学。故今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⑨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1页。由此可见,用“logy”结响的各个学科都以研究“世界的普遍规律性”或“存在的规律”为目的,“音乐学”既以“logy”结响,它应当是探索音乐的逻辑和普遍规律的一个学科。“音乐学”和“音乐理论”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音乐”,但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都不一样,并不是同一个学科。
关于“音乐学”和“音乐理论”的区别,俞人豪先生曾在其专著《音乐学概论》“引言”中指出:“虽然这两者在一段时期里几乎被作为同义语来理解,但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音乐理论这一概念已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内容和表达学科的性质,因此从上个世纪末起音乐学这门相对系统的学科建立之后,它在国外便逐渐成为对音乐以及相关事物进行研究的总称,而音乐理论则往往指称那种从形式和技术就解读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具有较强创作实践意义的领域。在西方音乐学通常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部门在综合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而音乐理论则更多是作为作曲技法在音乐学院进行探讨和传授。”⑩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虽然“音乐学”和“音乐理论”两者在研究过程中会密切合作,不可能完全割裂开,但二者各有各的领域,研究目的亦不相同,各有专攻,不能混淆,更不能互相取代。
“音乐学”这个词在欧洲最早见于1738年米茨勒于德国成立的学术团体“音乐学协会”(Societaet der musikalischen Wissenschaft)。1863年,德国人克里桑德(F.Chrasander)出版了《音乐学年鉴》,并在前言中说:“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他还指出:“音乐学应与当时呈上升趋势的‘实证科学’相联系,应成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众所周知,1885年阿德勒(G.Adler)发表《音乐科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以后,随着“音乐学”概念深入人心,英语中便产生了与德语“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相对应的词“musicology”,法语中也产生了相应的“musicologie”。⑪同注⑩,第5页。这样,“音乐学”便在欧洲取代了以前所用的“音乐研究”(music research)和“音乐科学”(science of music)等概念,成了独立的、包括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等不同学科在内的学科体系。
“音乐学”形成之时,欧洲“音乐理论”的建构已基本完成。在欧洲,复调拥有很长的历史,中世纪的僧侣在唱颂歌时各自在不同的声部上吟唱不同的旋律。到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乐派(Netherlandish Music School)的作曲家杜费(Guillaume Dufay,1400—1474)等总结并发展了复调理论和写作技术,为后来对位法的完善开辟了道路。在对位法形成之后,法国作曲家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出版《和声基本原理》(1722),根据泛音原理构建了三和弦、七和弦、九和弦和十一和弦,提出了“基础低音”的概念及转位和弦的结构,确认了主音、属音、下属音在和声进行中的支柱关系,从而构建了和声体系,使之成为近代和声学理论的基础。18世纪,曲式学也基本建立起来,德国作曲家H.C.科赫在《作曲指南》一书中阐明了乐句、乐段如何构成,扩充和压缩的乐句、乐段如何不失去平衡,并依据美学原理,提出了适用于创作实践的各种图样和模式。相对于对位法、和声学、曲式学的核心理论形成而言,在“四大件”中,配器法的形成相对滞后,但在“音乐学”最终确立的1885年,配器法业已相当成熟。
因为在欧洲音乐学界产生和确立之时,他们的“音乐理论体系”已建立起来且相当完善了,所以欧洲音乐学界没有、也无需提出建立“音乐理论体系”的任务,大家普遍认为“音乐学”是运用各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各种学术方法研究有关音乐问题的学术领域。
在我们弄明白了何谓“音乐理论”之后,应当为“中国音乐理论”定义。笔者认为“中国音乐理论”就是在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对其实践进行概括、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
鸦片战争前,“中国音乐”就指“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以来,西乐东渐,不少中国人研究和学习欧洲音乐,并借鉴欧洲音乐理论中的各种技术和方法创作出了不少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和我国传统音乐作品有所不同,这样一来,“中国音乐”一词就不仅指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作品和中国人按照本民族固有的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的形式、创作出来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作品,也指中国人借鉴欧洲音乐理论创作和改编的音乐。“中国音乐”就不仅包括传统音乐,也指“新音乐”。“新音乐”主要采用的是欧洲音乐理论和技法,总结和概括这些技法,并不是中国音乐学界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今日,随着对外音乐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各样的音乐理论在我国都有人进行研究,中国音乐界还有不少专门表演外国音乐作品、研究外国音乐理论和外国音乐历史的专家。这些专家中不但有研究欧洲音乐理论的,还有研究阿拉伯音乐理论、印度音乐理论,甚至是朝鲜、日本音乐理论的。他们的研究中和外国音乐理论有关的、具有独特见解的成果,可以是“中国的音乐理论”,但不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中国人研究外国音乐理论的目的是学习和借鉴,并不是要越俎代庖地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总结出一套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供那个国家或地区的音乐家采用,并用以指导他们的创作实践。因此,“中国音乐理论”不是指目前在我国流行的各种各样的音乐理论,也不是指中国人对外国音乐理论进行研究后所取得的独特的学术成果,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中国传统音乐是我们的根,是发展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要想发展中国音乐,必须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话语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学被引进并在我国兴起之时,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尚没有根据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总结和概括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先辈音乐学家有鉴于此,曾提出了建立“民族音乐理论”的想法。据我所知,这一想法是由沈知白先生在1956年提出来的,而在那以前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般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的提法,则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成立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⑫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3期。
沈知白先生为什么要把“民间音乐研究”改为“民族音乐理论”呢?他曾解释说:“‘民族音乐’的概念比‘民间音乐’要宽,它可以包括‘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士大夫音乐’‘文人音乐’等等,而‘民间音乐’则不能。”他还说:“‘研究’是一个动词或动名词,它只能指称一种行为,不适合作为一个专业或一个学术领域,不仅是指‘研究’这件事,它还包括一系列研究出来的成果,甚至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从而表达了最终想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的意向。”⑬沈洽《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评介(1950—2000)》,《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年第1期。因为“民族”在汉语中的一个义项是“中华民族”的简称⑭杜亚雄《“民族音乐理论”不是“民族音乐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中国音乐》2006年第2期。,所以沈知白先生所说的“民族音乐理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音乐理论”。据沈洽回忆,当时沈知白先生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设计的专业课程包括中国的“民间歌曲研究”“民族器乐研究”“戏曲音乐研究”“说唱音乐研究”和西洋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两个“四大件”。沈知白先生希望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的“四大件”,掌握“过去需师傅几十年口传心授才能习得的这种技艺”,而学习欧洲“四大件”的目的则在于“吸收和应用”。⑮同注⑪。
在沈知白先生和高厚永先生的领导下,当年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系为建立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做了许多工作。黎英海先生的《汉族调式及其和声》⑯黎英海《汉族调式及其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高厚永先生的《民族器乐概论》⑰高厚永《民族器乐概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于会泳先生的《腔词关系研究》⑱于会泳《腔词关系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都为以后在这些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开了先河。
上述各位前辈中,除黎英海先生是作曲家外,沈知白、高厚永、于会泳先生都是音乐学家。在那个时代,音乐学家们为什么热衷于建设“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同,在我国开始建设音乐学诸学科之时,中华民族的“音乐理论体系”远远没有建设起来。于是前辈音乐学家们便和作曲家们一道,自觉、主动地担负起建立“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这是中国音乐学界的光荣传统,我国音乐学界应当“不忘初心”,继承并发扬这一光荣传统,而不应当打着种种不同的旗号,去做各种“去音乐化”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建设确定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十年动乱中,这一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后来,虽然也有不少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为这一体系建立做了许多工作,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作曲家金湘先生在2005年指出:“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保存着许多不同于西方的技法和技法因素,由于历史、社会的种种原因,我们对其挖掘整理、学习研究远远不够;这无论是对于当前音乐创作实践或作曲理论建设而言,都是一大损失。”“中国亦已有不少理论家、作曲家在做出大量努力—实践、总结、研究;但应当说,距离达到目标,尚需努力。”⑲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目前,我国已有数百所高等音乐院校,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开设“中国民族基本乐理”课,而包括民族和声、民族复调、民族曲式、民族乐队配器法在内的“四大件”以及民族曲调写作的教学还都处在摸索的阶段。1956年,沈知白先生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的目标,尚未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树立“文化自信”,2015年11月3日,他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⑳《习近平“文化自信”内涵解读》,《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7月13日, 第 12 版。尽快地建立起“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在音乐领域中树立“文化自信”之必须,中国音乐学界应当和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一道,大力开展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我们自己的音乐理论,为早日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