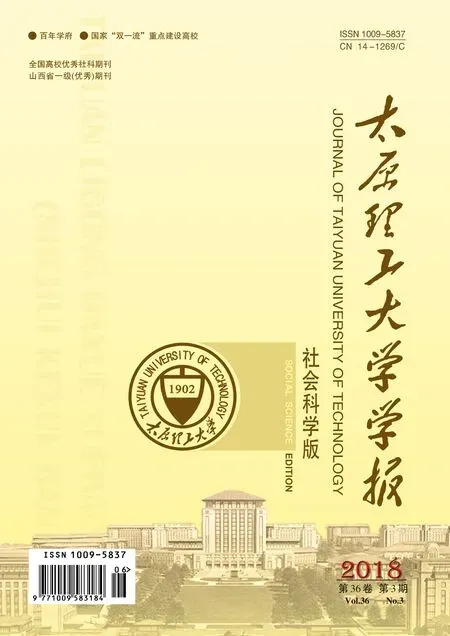历史与记忆
——维柯“诗性智慧”再思考
赵立坤,李化敏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是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哲学与文化的争鸣中提出的一种智慧观,他“将现代科学与宗教文化相结合,创新为一种完整的‘诗性智慧’”[1]。对维柯“诗性智慧”的研究国内外兼而有之且纷繁复杂:维柯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批判者被人们发现、认可和评价是在20世纪,尤以意大利学者克罗齐为典型;以赛亚·柏林将维柯置于反现代的框架中进行解读,进一步拓宽了维柯诗性思想的深刻性;沃格林的《革命与新科学》注重对维柯“诗性智慧”及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剖析,他将维柯视为介于天意与进步之间的阶段;马克·里拉的《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开创了对维柯思想的创新认识,维柯作品中所包含的对天主教神学的捍卫在马克·里拉看来属于反现代思想。国内对维柯思想的研究者首推朱光潜,他的研究属于“翻译和介绍并行”,并随着对维柯作品翻译力度的加大,对其“诗性智慧”的探究也呈现多样化,诸如美学、人类学、历史哲学,以及从诗性思想中所提取的人文主义等。
维柯将最初的人类文明置于“诗性智慧”之上,此一智慧旨在揭示怎样的历史文化观?它镌刻着历史与记忆怎样的文化符号?又赋予历史研究方法怎样的创新?“诗性智慧”对“历史的”看待历史与文化具有怎样的启示?本文立足于维柯“诗性智慧”的知识理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些许思考。
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
法国思想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欧洲思想史上的领军人物,其在几何学领域树立了完美的数理逻辑,在欧洲思想和精神领域保持了绝对的权威。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山鼻祖,他洞见经院哲学错误的实质,指明近代科学的研究方向,建立了关于新的科学的哲学。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强调正确运用能够判断真假是非的才智,即理性。“感官只能得到个别的、片面的知觉,只有理性才能获得普遍的、必然的认识。凡是理性清楚明白的认识,都是真的”[2],即为笛卡尔认识论的内核。在方法论上,笛卡尔提倡力学方法和机械方法,他提出了建立新科学的两步法:第一步要检定材料;第二步为综合材料,将这两步一以贯之即是观察实验—寻求原理—分析现象—得出结论,由此,不难看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是拿一个合理的原则去分析和综合材料,把它们统一起来,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形成系统,从而抓住事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质”[2]。笛卡尔主张在寻求真理时要使用一种确定的方法,尤其是数学的确定性,他认为数学的推理确切明了,数学的基础是牢固的,“几何学家通常用一长串十分简易的推理完成艰难的证明……古今一切寻求科学真理的学者当中只有数学家可以找到一些确切明了的推理”[2]。因此,数学思想的一以贯之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特征。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突出表现为严密的实验、推理、抽象思辨,不可否认,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是“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钥匙”[3]。但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存在某种局限:首先,理性主义将“理性”这样一种意识的形态作为衡量世界形体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准,在如此判定下是无关实践的基础作用的;其次,理性主义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理性的“孤立化”,孤立化的理性是机械论式的,感性和理性成为对立的关系;最后,“理性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为机械论式的科学,“无机的自然界是机械的,植物界是机械的,动物界是机械的,……他们的运动都是位置的移动,……是自动的机器”,这就在另一个层面上“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之本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付有的文化特性”[4]。在此,我们需要思考形成人类历史与文化的洞见究竟是什么?
二、维柯的“诗性智慧”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也以建立“新科学”为己任,但是他的“新科学”与笛卡尔有所不同,笛卡尔式的新科学重心在于建构数学化的科学构筑的自然模式;而维柯的新科学注重探究一种系统性的人类历史。汇聚维柯思想精髓的《新科学》一书共为五卷,第二卷“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包含了几乎一切带有独创性或本源性(original)的东西”[5],维柯从诗性玄学和诗性逻辑两大方面论证了人与神的历史知识特征与范畴。
(一)原则
维柯提出了新科学所遵循的第一大无可争辩的原则,即“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并以此探讨了“诗性智慧”和人类历史的关系,阐明了“神明天意的一种理性的民政神学”。“维柯试图把所有人的活动特征都看作是‘诗性的’,正如他把一个从‘心灵的想象形式占主导地位’这一说法中抽取出的比喻称为‘诗性特征’,他把整个体系称为‘诗性智慧。’”[6]
在对不同民族的研究当中,维柯总结出支配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的真理基础,即三种普遍永恒的制度:“祭礼”“婚礼”“葬礼”*此三项在《新科学》中都被称为原则,特指源头与开始,意思就是这三项都是部落发展所必有的而且充分奏效的条件。。它们“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一定是这种真理基础支配了一切民族,致使他们都要从这三种制度开始去创建人类,所以都要最虔诚的遵守三种制度,因此将这三种永恒的普遍的习俗作为三个头等重要的原则”[5]。最初的先民在对自然救济绝望时求助于宗教,虔诚和宗教使最初的人们自然的成为谨慎、正直和有节制之人;在宗教的引导下,婚礼和祭礼相继产生,婚礼习俗的逐步进化推动了文明的前进;埋葬制度源于古代野蛮民族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古人将埋葬与人类契约一视同仁,埋葬由最初对亡灵的敬意演变为对土地归属的象征。
“三礼”的原则是以“历史由人创造”为前提的,作为不同民族之间共同的道德和情感取向,它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法律、艺术的根本基础,更是一切确凿可凭的历史事实得以融会贯通的纽带。“诗性智慧”自我演绎出人类历史的三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各项制度和艺术在三个时代的更替演进中完善。
维柯视原始人生而就有的感官和想象力为“诗”,“能凭想象创造的叫作‘诗人’,‘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5],人类思想的次序先是想象,而后观察、证明、归纳,想象是历史创造的先天优势与能力,因此原始人是以想象的方式根据自己的观念创造了事物,这区别于自然世界所强调的上帝凭借智力造物,卡西尔认为是维柯第一次系统的提出“想象的逻辑”(logic of imagination)[3],“想象的逻辑”就是诗性智慧的重要特征,诗性智慧就是“诗人或人类制度创造者的智慧”[5]。
(二)方法
“诗性智慧”展示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维柯特别感兴趣的是他所称之为远古和朦胧时期的历史,也就是他感兴趣的是历史知识的扩大;而与此有关,他也就奠定了一些方法的规则。”[7]克罗齐亦认为维柯的“诗性智慧”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体系,他形象地将维柯的方法体系概括为“三大源泉”,分别为语言学、神话及历史学家对“古代世界的记忆”。维柯本人也在论证“诗性智慧”时指出:要运用过去一直都缺乏的新的批判法来讨论各民族创始人的真相。
首先是维柯的语言学证据,他要使“语言学形成一种科学,(并)在其中发现各民族历史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5]。维柯强调语言学证据与哲学证据二者之间的互补:“哲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于语言学家的凭证,就不能使他们的推理具有确凿可凭性,他们的工作一般是失败的。同理,语言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于哲学家们的推理,就不能使他们的凭证得到真理的批准,他们的工作也就有一半失败了。”[5]在维柯诗性思维之下,语言学为历史学带来启发,把语言学的证据放入历史的研究之中本身就是在着力强调研究历史发展的凭证。
其次,神话是维柯诗性历史研究方法的第二大源头,“神话和寓言不是比喻、虚构或是欺诈,它是关于原始人类的科学”[6]。在诗性智慧体系架构中,神代表自然事物、人类事物、社会事务作为“真实的叙述”,神话反映了原始诸民族的制度、发明、社会分裂等历史状况,“一切古代世俗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故事。”[5]神话是历史研究原初的资源,它以“一种原始的、有想象力的头脑所采用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更富于思辨的头脑以法律和道德典范所陈述的东西”[7],“这些神的神谱或世系是在这些原始人心中自然形成的,(它)可以向我们提供一部关于神的诗性历史的时历”[5],诗性的神话思维镶嵌着人类解释自身习俗和人性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第三大源泉是“对古代世界的记忆”[6],“想象不过是扩大的或复合的记忆”[5],诗性的想象是维柯历史研究方法的精髓。维柯重新拣拾科学研究之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并对其重新修复、组合,“凡是最初的人民仿佛就是人类的儿童,还没能力去形成事物的可理解的概念,就自然而然的去创造诗性人物性格,就是想象的类概念(imaginative class concepts)”[5]。维柯所强调的记忆的手法将心灵的研究与人类的想象、情感与意志相结合。
以上三源头反映了维柯“诗性智慧”历史研究方法的总特征,勾勒出历史与记忆的文化符号。“科学和哲学的智慧在试图认识自己之中所用的办法则是在凡俗的、诗性的或创造性的智慧里去寻找自己的根源。……那种凡俗的或创造性的智慧就是一切科学和哲学的根源和前提”[5]。作为“笛卡尔主义”的首次进攻,维柯将17世纪晚期历史批判方法的进程推向了更高的阶段,他倡导知识论以一种更加广阔的基础来批判当时哲学信条的狭隘性与抽象性。一方面,他认为知识分为自然的和历史的;另一方面,他主张人类能够认识自身创造的“人类世界”,这无疑就为史学思想如何“既具有建设性又具有批判性”指出了新的方向。
(三)“寻找真正的荷马”
维柯试图通过寻找荷马的智慧为“诗性智慧”找寻历史的依据。“诗性智慧”作为凡俗智慧,强调感觉和想象的理解性能力,在这种诗性的光芒下,到处是“强旺的感受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克罗齐指出:“对维柯而言,故事不是真实历史的变形,而是本质意义上的历史,故事中被信以为真的变化是真正的真理,与呈现于原始心灵中的真理是一样的,……神话是诗性智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维柯借助《荷马史诗》解读神话的价值,“荷马与其说是维柯发现新科学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原因”[8]。维柯以一个哲学家特有的深度和艺术家特有的厚度重新考察神话故事,重新审视荷马的意义。“对维柯的新科学来说,荷马已成为最完美的证据,正如有关荷马的论争曾是其灵感”[8],只有从诗性思维和历史意识中解读《荷马史诗》,才能真正理解其历史与文化价值。
纵然荷马笔下的英雄们不乏野蛮的习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抱怨说,荷马让英雄情感脆弱,遇事恸哭,又不善于自我控制,常“狂笑”,而且还贪财,这些怎么能用于教导青少年?通通应当删去[9]。然而,这些“缺憾”在维柯眼中却被昭雪——荷马史诗中的凡俗演绎的“既恰当又必然”[5]。这种恰当与必然是“自然、永恒、理想的历史”气质的必然组成,是想象力推动人心灵的不确定性的发展,这种夹杂着原始人“心灵特质”和“超越了偏狭时空”的秩序[10],正是我们所忽略掉的真正的人类历史的精髓——人的历史与文化创造。
从史诗描写的人物性格特征来看,荷马所展示出来的英雄人物是一些“心智薄弱像儿童,想象强烈像妇女,热情奔放像狂暴的年轻人,因此,我们否认荷马有任何(哲学家才有的)玄奥智慧”[5]。以阿喀琉斯为例,拒绝“战胜者埋葬战败者”的提议这是阿喀琉斯的“公道和正义”;“拖着赫克利托的尸体绕墙环行”是他的野蛮;而面对祖国和人类的共同命运,他以私仇为重。“荷马在这里以无比的才能创造出一些诗性人物性格,其中一些最伟大的人物都是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文明的人道德性质毫不相容,但是与当时斤斤计较小节的英雄气质却完全相称。”[5]荷马笔下的性格特征是当时无人道的习俗的写照,而并非哲学家玄奥智慧的产物。“诗性人物性格必然是按当时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这种民族在极端野蛮时期自然就有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必要”[5],显然,人类思维与心智的发展是不同文化与不同阶段的形式表现,因此,荷马的智慧是凡俗的,而非玄奥的。
维柯从荷马史诗入手,发觉荷马所描绘的文化场景——最初的历史必然是诗性的历史。形形色色的诸神还原了人类历史起源时的状况,荷马通过对人与神的感觉、心灵、力量、勇气的描写,汇聚了生命的动力来源,史诗中的人神巧言善变,人在自己的行动中展示性格、抒发情感。简言之,荷马史诗就是在讲述人的求知,以及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进行的探索与求证的过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荷马史诗就是历史,是对过往的人与事的回顾,维柯追寻荷马智慧的意义就在于印证人类历史产生于凡俗智慧,凡俗智慧的记忆才是人类文化真正的滥觞。
三、对“诗性智慧”的再审视
人类历史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是维柯新科学着力探讨的问题,“诗性智慧”试图从自然世界转向历史世界,由上帝创造转向人类自己创造,这种转变为我们深刻地认识历史的“自然性”与“人文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复归性”与“进步性”提供了灵感。
(一)历史的“自然性”与“人文性”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绘了三个世界:“神的世界”“自然的世界”“民族的世界”。他的侧重点在于阐释神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寻找沟通“神的世界”与“民族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在维柯的眼中,“民族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是相对的:首先“各民族”(nations)在他们还完全隔绝时已经被创造出来;其次民族的世界又称为“民政的世界”(the civil world),这是一个“人类的世界”(the world of men),也是“人道”(humanity)的世界。
维柯定义“民族”的依据为“一个集团的人民……在不断变化的发育过程中的……内部压力,或内在逻辑”[5],“民族世界”是具有“自然性”的,它是生育意义上的民族的“本性(nature)”,是民族不可分离特性的必然所在。“维柯把自然的模式转化成历史的进程,借此处理了这个问题(世俗史暗示出自然与神恩的融合)。他把这个模式转化成一种历史单位,但是这个模式不是普遍的人,而是‘民族’。任何这个历史单位在历史中都是按照人类的社群的‘自然’(本质)发展着。……通过这样一种转化,……可以解释历史现象这个多元的领域。”[11]维柯用“诗性智慧”诠释了迥异于笛卡尔自然科学方法的“自然性”,将目光汇聚于人类历史与文化产生的“自然而然”,正是这种“在正常过程中的诞生”维持着历史的赓续。
维柯的新科学赋予历史与文化人文性的关怀。首先,“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我们已把这一点定为第一条无可争辩的大原则”[5]。维柯在肯定历史自然发展的同时也坚信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过去哲学家研究的自然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因此,只有上帝可以创造它;而民政的世界是由人类所创造的,人类就应该认识它,民政社会世界的原则必然要从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去寻找”[5],“人类自己创造历史”是维柯民政世界异于自然世界的显著之处。其次,维柯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起源于共同的习俗,一切民族的起源与发展都保持三种习俗,并经由这三种习俗派生出其他的一切制度。民政世界是由社会中的人与社会组织的演化而构成,这就是包含人类共同意识、共同心智的人类理念的历史。在讨论法律是来自于自然还是来自于人的意见时,维柯谈到人类喜欢社交与否这一问题。他讲道:是习俗而非法律造成部落自然法,因为法律起于人类的习俗,而习俗则来自于各民族的共同本心,“部落自然法和各民族的习俗是一回事,由于都来自于人类的共同意识,所以彼此必一致”[5]。显然,维柯所主张的历史的人文性是基于社会性的人文性,因为他认为各民族共同的本心维持了人类社会,这种共同的人类意识源于人的社会性的潜意识。
诗性智慧下的历史是自然性与人文性交相呼应的历史,自然性是人文性得以彰显的前提;人文性是自然性流露的延续。维柯将人置于历史的生活中去考察,也将历史类比于人的生育成长,如此,赋予人类制度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肯定人的历史主体性,这一见识也流露着对自然科学之学科姿态的批判与反思,“维柯以人的形而上学……对抗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即人的哲学之意,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文化哲学”[12]。
(二)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人类历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每个异教民族都有自己的天帝约夫和赫库勒斯”[5],“在神的一切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人的千姿百态……”[3],不同的神肩负着人不同的道德理想和精神理想,故而“神的区别”也为各民族信仰文化、风俗文化的差异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各民族根据其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次第前进”[5]。各自的本性,习俗,部落自然法和根据自然法所创建的民事政体,以及维持人类社会运行的语言、字母、法律、理性与裁判,尽管大致相似,但是“随古今民族数目有多少,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表达”,表达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所要表达的内容,进一步关系语言、制度等具体因素传播和制定。以自然部落法为例,各部落法都是在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中分别创始的,因此它们是参差不齐的,后来是由于战争、信使往来、联盟和贸易才被通用于全人类。
“基于人由本性散发的普遍需求而制定普遍的规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诗性智慧”所建构的历史是人性和天神意旨相互结合的产物,“……(关于天神意旨的民事方面的理性神学)从立法者们的凡俗智慧开始,这些立法从天神预见这一属性去关照天神,从而创建各民族。”[5]维柯提出“只有凭借天神意旨,人才会被控制在秩序和制度中”,天神被赋予“立法的心理”,天神意旨在整个人类历史及复演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天神意旨作为人类制度的设计者,由它提供给各种制度秩序与规则,从天神的产生到人类历史进行复归,天神意旨都是一种无形的指引。维柯新科学就是要“证实天神意旨在历史中所做的事,必须是一部天神意旨在没有人类认识或是意图往往违反人类计谋的情况下颁布给人类这个伟大城邦的一些制度的历史,因为这个世界尽管是在时间中创造出来的,是特殊的,天神意旨在其中奠定的那些制度却是永恒的、普遍的”[5]。
维柯所阐述的历史的特殊性是始终不脱离普遍性的特殊性:“最初原则产生的各种方式……就说明了它们的本性便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特殊标志”[5],但是,“(这些起源)还是由这些制度所保持的永恒特性来证实”[5]。历史的发展具有普遍模式,“它浸染着每一个细节,并在其他的时期重复出现;因此两个不同的时期可以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7],天神意旨为这种普遍提供了共同的真理基础与准则,使历史的创造活动在个人欲望的推动下转化为社会的“公道”。在诗性体系中,天神意旨就是制约和调节创造活动的必然存在的制约力量,人和天神意旨本身就是历史的事实,是自然的、世俗的和历史的,维柯所说的天意“只不过是神学术语表述的隐蔽在私利行为等历史表面现象后的历史规律”[13],诗性智慧下“理性的民政神学”辩证地处理了历史创建者的真相与其普遍意义之间的关系,辩证地处理了历史的普遍性与人自我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而提供了人类制度的自然性、程序及目的的合理性,揭示了历史的特殊性是基于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历史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李秋零在《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有过相似的论证,“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按照”永恒的理想的历史“历经兴起、发展、成熟、衰败和灭亡,由此导致的复归现象恰恰是在多样性中证实了历史的统一性,在偶然性中证实了历史的必然性,在复杂性中证实了历史的规律性”。。
(三)历史的“复归性”与“进步性”
维柯的“理想永恒的历史”是不断进行演变与复归过程的历史,他认为通过“诗性智慧”这一历史与文化的起源,人类将由野蛮步入文明;同样,伴随高度抽象理性思维的发达,文明亦复演野蛮。在他那里,复归(recourse)的过程有两层含义:本意是依据同样的次序再经历同样的各阶段;而另一层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同一轨迹的、纯自然的发展,而是强调历史的、复审的、申诉的法律意义上的复演。“历史过程既然没有获得公道,仿佛就要向一种更高的法庭申诉复审,而最高的法庭就是凭天神意旨安排的整部历史,这就要有一种分化和过度诡辩的时代,一种思索方面的野蛮时代,才便于恢复到感官方面创造性的野蛮情况,即野蛮时代的复归过程。”[5]
“野蛮的复归”是怎样的一种历史模式?学者见解纷纭。克罗齐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永恒循环,而且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在维柯的作品中,永恒循环几乎别无选择的被认为在诸民族历史中得到了例证,在人类的事务中,它是此消彼长的状态。……在一个新的感性的野蛮状态的漫长岁月中,把居心叵测的才智这种邪恶的机巧消磨掉是必要的”[6]。同时他指出维柯历史的复归不只是简单的循环,“进步意味着每一件事实、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功能,每件实事、每个个体都做了自己的贡献。对史诗而言每一个都是无法替代的,每一个都用更加深厚的声音回应它的先行者”[6],这与柯林武德对维柯所阐释的“复归”的理解异曲同工:“这种周期性的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绝不是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的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一个新的阶段”[7]。维柯列举了野蛮时代和复归的野蛮时期之间诸多的相似,但是这种相似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代表两种完全相同的野蛮时期,他虽然主张“各种原则的自然本性,凡是事务都既起于这些原则,又终于这些原则”[5],但也暗含对复归后超越的肯定,从此种意义上说“历史的复归”是一种进步。
沃格林对维柯的历史理论另有见地,他指出:“维柯是第一个对西方的危机做出重要诊断的人”[11]。在启蒙和理性处于萌芽的时代,维柯的反驳是在精神和知识危机被各种快速发展的因素掩盖本来面目的情况下,对时代提出的一种批判。“在维柯生活的时代,进步理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它的反驳不是针对这个明确的观念,而是针对产生了这个观念的思想,也就是傲慢的自我救赎的思想。尽管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充分的发展,但维柯认为文明的进程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衰落,在这个理论中,他已经对进步理论进行了反驳。”[11]基于18世纪的欧洲文化氛围,抽象理性思维造成了对历史境遇的忽略和人性功利主义泛滥的现代性危机,沃格林认为“复归理论”的反驳“流露出一个明确的体系,……,这些反驳……对我们认识维柯的思想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凸显了维柯的一种意识,即成为新的政治科学的奠基人。……新科学确立起来的……反驳有助于我们定义维柯思想的‘现代性’”[11],沃格林的这一见解更多是立足于认识维柯思想的“现代性”这点上来理解的。
维柯的“诗性智慧”虽然批判了抽象理性思维所导致的危机,但是并没有彻底否定理性的价值。“人的自然的本性是有理智的,因而是谦恭的、和善的、讲理的,把良心、理性和责任感看作法律。……人道的法,是充分发达的人类理智下的判决。……理性的人道(rational humanity)才是人变成人时所特有的那种特征。”[5]同样,维柯对诗性历史的描述也非全然肯定,他指出“最初野蛮的时期,人们极度残酷和野蛮,暴行、抢劫和凶杀之风猖獗,当时除了宗教所规定的神的法律之外没有有效的办法来约束那些已摒弃一切人道法律的人们”[5],可见,虽然诗性时代的人性有其崇高性,但是也充满了非人道性与野蛮性。 “野蛮的复归”将“重演”从历史事实中提取出来重新清洗,达成“反思的野蛮”与“凡俗的野蛮”的和谐,在“复归的历史”中,隐含着“人在文明化道路上可能的反动”与“人以文化创造灵活解决人自身的存在悖论”[12]。
四、结语
维柯的“诗性智慧”不啻为对以笛卡尔“理性主义”所代表的抽象数理逻辑的回应,更是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数学、物理学的人类社会科学。他回归到人类混沌的时代,以诗性的眼光考究人类诗性的历史与文化,在找寻真正的荷马沿途中发现了“打开新科学的万能钥匙”,提出诗的本性才是人类历史与文化源头的真正本质。由人类创造的历史是诗性的历史,古代异教民族通过天意的象征开始他们的诗性智慧,一系列诗性的制度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普遍永恒的原则,历史在普遍的一般性中跳跃着特殊性;人作为社会中的人不断创造历史与文化,彰显历史人文性的内涵;维柯“野蛮的复归”将“重演”从历史事实中提取出来重新清洗,从而达成“反思的野蛮”与“凡俗的野蛮”之间的动态平衡。
维柯的“诗性智慧”提供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包括他对原始信仰、习俗、语言的发掘,对神话的解释,对人类最自然的本性能力“想象”的推崇。他不是从“中途开始”,而是回到历史与记忆,在发掘人类心智世界中去理解历史文化;以诗性智慧揭示历史文化的核心与内在力量,这对理解历史与记忆的文化意义,以及“历史的”看待历史具有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赵立坤.维柯的文化史观[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1):154-158.
[2]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21,16.
[3]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版社,2006:24,212,137.
[4]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71.
[5] [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7,159,188-189,45,9,107,475,9,126,125,47,485,455,453,467,17,624,159,151,122,501,195,167,168,168,49,611,503-535,589.
[6]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维柯的哲学[M].陶秀敖,王立志,译.北京:大象出版社,2009:38,108,109,44,43,5091,195,167,168,168,43,89.
[7]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3,117,113, 114.
[8] 刘小枫,陈少明.经典与解释25:维柯与古今之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29,130.
[9]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86-391.
[10] [美]博纳德特.弓弦与竖琴[M].程志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80.
[11] [美]沃格林.革命与新科学[M].谢华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3,168,169,169.
[12] 黄力之.从维柯到康德:前马克思时期的文化哲学[J].社会科学,2007(11):122-134.
[13] 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