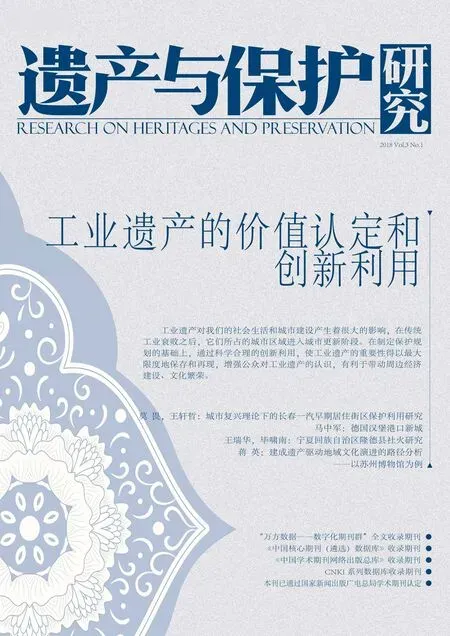莞邑碑刻遗产中的乡约民规
梁燕红
(广东科技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据现有研究,从宋代开始,广东的平民家族开始出现[1],明清时期,由以“家”为核心的文化拓展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日趋成熟,与之相伴的家训族规等也日趋完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清代的东莞作为广州府管辖的14县之一,地方宗族社会也发展得比较成熟,“宗族乡约化”已经普遍存在,甚至族规与乡约一定程度上可互换。对一个家族的约束实际上也可演化为对乡里的约束,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约定可成为乡里邻间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宗族乡约化”进一步演变成“乡约宗族化”。
近年来,东莞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2014年12月编撰出版的《东莞历代碑刻选集》就是其中之一。此书收录东莞历代碑刻200通,为东莞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其中有14方1杨宝霖先生在序言中提及有关乡规民约的有12方。涉及乡规民约。本文就《东莞历代碑刻选集》中的14方相关碑刻做分析,一窥清代东莞的宗族文化和莞邑地方社会状况。
1 《东莞历代碑刻选集》中有关乡规民约的主要内容及存在形态
《东莞历代碑刻选集》中相关的14方碑刻几乎是在祠堂中出现,表现为“祠规”“族规”或“禁条”“禁令”,虽然无乡规民约之名,但有乡规民约之实。涉及内容广泛,主要体现为家族祠堂的选址、作用、管理以及家族子孙的教育与约束等。
14方碑刻是对家族成员行为的明文约束,更多是以禁令的形式出现。一般来说, 以1949年为界,以前的乡规民约称为传统的乡规民约,以后的称为当代乡规民约。根据张明新教授的研究成果,传统乡规民约的存在形态主要有文本形态和组织形态两种[2]。
显然,14方碑刻包含的族规、祠规和禁令都属于文本形态,而且,都是劝诫性条文(或扬善性条文)和惩戒性条文一体并存,惩戒性占主要部分。14方碑刻中,惩戒性条文都以“不得”“禁止”“违者必罚”等规定性词语出现。惩戒的措施根据违反条文的程度有所不同。主要分为4种:①斥责。这是最轻的一种,出现较少。石碣镇水南村陈氏宗祠《族规》第一条规定,若在祖祠内圈养牛猪鸡鸭及堆积柴草等物,影响祖祠洁净,轻者给予斥责;若违反第五条规定,随意将族内房屋出租,处以斥责驱逐。②罚钱(银)。这是最常见的惩罚措施之一,一般情况下,族人违反祠规或者禁令都处以一定的罚款。如:茶山镇南社敬爱堂《祠规》规定,祠内台凳物件私自擅用,罚钱二百文,在祠内安顿私家物件,罚钱三百文,甚至妄行私宰,大干法纪,罚银一两马。石排镇燕窝村《洪圣宫规条碑》中规定,凡违反均罚银,三钱马至一两四钱四分不等。大朗镇巷头社区《已逊陈公祠禁条碑》中除第一条外,其余若有违者均罚银二两。在大朗镇高英村,子孙若违反禁条,将会被罚猪肉一百斤(《善庆堂例规碑记》)。③革胙。这种惩戒方式较之罚钱更进一步,直接剥夺族人祭祀祖先的权利。虎门镇宴岗社区《竹隐梁公祠尝数规章碑》明确规定:“凡有不遵族约要停胙肉,由族尊协同绅耆到祠,要族尊批消其名。”大朗镇巷头社区《已逊陈公祠禁条碑》中第一条“禁止开场聚赌、藏宿匪类,违者革胙。”巷尾社区《南石陈公祠规条碑》明令禁止开场聚赌,藏宿匪类,若违反此禁令,革胙三年,如果再犯,终身革胙,从重处罚。④送官究办。这是最严重的一种处罚办法。在家法族规之外,把严重违反乡规民约之徒或违抗宗族处罚之徒送官究办,交由官府进行处理。如:若违抗茶山镇南社敬爱堂《祠规》的相关规定,不服从祠规管束的,“如抗送究”。
当然,除了惩罚性的条文之外,也有对族人正面的教育,劝导族人保护祖祠,以安妥祖先之灵魂。如:祖祠为纪念祭祀之所,务要整洁(樟木头镇古坑《建筑四房联合祠碑记》);祖祠务要洁肃,以妥先灵(茶山镇南社敬爱堂《祠规》);南石祖众子孙建立祖祠,原为以妥先灵,以序昭穆,以彰敬爱,务洁净堂阶(大朗镇巷尾南石陈公祠《规条碑》)。
2 《东莞历代碑刻选集》中乡规民约与清代莞邑地方社会
14方碑刻主要立于清代(共10方),而又主要见于祠堂和庙宇中,可见清代莞邑地方家族社会已经成熟,家族成员间形成以宗祠(祠堂)为主要情感纽带的共同体,在族长、绅耆的管理下,莞邑乡土社会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文化拓展而成的社会机构,即“家国同构”。 明朝中叶之后,家族制度在广东发展尤其快,其结果是庶人可以和贵族一样用相同的礼仪拜祭祖先。18世纪,庶民按官家模式造族的例子愈多,到了19世纪,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岭南地区家族社会的核心,该区的社群以祠堂为中心,组成大量族乡社区和联族成约的乡际组织[3]。清人张渠在雍正年间在粤为官,著有《粤东闻见录》,记述了清代广东家族宗祠繁荣的景象:粤多聚族而居,宗祠、祭田家家有之,如大族则祠凡数十所;小姓亦有数所,大族祭田数百亩,小姓亦数十亩[4]。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其大小宗祖称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 祠数十所, 小妇单家, 族人不满百者, 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 始祖之庙也。”[5]这是岭南大地上的整体状况。在莞邑社会,到了清代,家族祠堂林立的情形与广东整体情形无异。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记载当时的东莞“巨家多有祠堂、祭田,报本、睦族,工习以地。”1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人们由家及乡,乡村社会的结构也就由一个又一个宗族组成。因此,清代的莞邑地方社会也即宗族社会。冯尔康在其著作《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谈到,清代宗族的发展基本遵循纯血缘和地域与血缘相结合两条路径[6]。清代莞邑地方宗族社会正是如此。
族规和祠规已俨然成为族众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日常的生产生活以及行为习惯也深刻地凝集在族规和禁令之中。因此,从族规、祠规和禁条,可以一窥清代莞邑地方宗族社会之风貌。
14方碑刻文本中非常重视对祖祠的保护,尤其强调祠堂的洁净,禁止在祠堂内摆放什物,其中提及的很多都是农具如耕器经耙,农作物——柴草、桑叶、油菜、五谷等,这与清代地方莞邑社会主要是农耕社会密不可分。王中行《迁学记》有“莞自唐宋以来农力稼穑”之语。【康熙】《东莞县志》载“石冈(今石排)以上习颇刚劲,东南民好稼穑”1[清]郭文炳编,杨宝霖校对:《康熙东莞县志》。,陈伯陶所撰《民国东莞县志》载“邑民务耕作,精种植,濒海则藉鱼盐,无巨商大贾,适四方”2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
绝大多数族规、祠规和禁令内容围绕祠堂的保护展开,对祖先诚敬是传统的孝道文化在莞邑乡村社会的体现。东莞在清代时非常重视拜祭之事,包括墓祭和祠祭。【康熙】《东莞县志》风俗卷记载了9次关于祭祀先祖之事。分别是:至立春日有事于先祠;社日枌榆同里者共祀土神以祈丰年,仍命师巫各入家禳祀;清明有事墓祭;五月五日祀先祠;望前一日俗为孟兰盆以祀其先;霜降扫墓;冬至祀先祠;除夕祀先祖;凡祭墓祭,尊尚燔豕,无者以为非礼。不仅在重大节日要祭祀祖先,而且必须重视祭祀礼节和祭品等级,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和族人之间的亲情。以后,崇祀祖先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如竹园头张氏家训之一即为崇祀祖先:祖宗者,木本水源之谓,入庙思敬,过墓思哀,春秋享祀,百世勿忘3《竹园头张氏族谱》,藏于东莞市博物馆。。
乡规民约在莞邑地方社会的管理中卓有成效,禁令性的条文发挥了现代法律的作用,起到严厉的约束作用,时刻警醒宗族子弟远离恶习,保持乡村宗族社会的醇正之风。有清一代,岭南赌博之风盛行,道光、咸丰年间尤甚。《番禺志》记载,时“广州赌风甚炽”4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官员虽悉知赌博之害处,也屡次发文明令禁止,“然文武衙门赌规甚重,且开赌者非劣弁胥吏,乡间则劣绅婪老包庇,故屡禁屡开,未能绝也”。历任粤都督都曾采取过严厉的禁赌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然穷乡僻壤,私赌仍未尽绝也。吾邑亦然,此最可慨叹者”。由赌博起滋生出了严重的偷盗问题。“赌为盗源,粤之多盗,皆由赌盛”。赌而盗,盗而赌,无限循环,“良民受害,不可胜言”,严重影响了莞邑地方社会风气。从14方碑刻中看出,禁赌与禁藏贼匪是共同的,在惩戒办法中,对赌博和窝藏贼匪的惩罚也是最重的,要不革胙,要不直接送官究办。乡规民约甚至将聚赌和窝藏贼匪写进族谱中,如清溪《邓氏族谱》记载先代“好读书,戒嬉游,喜勤俭,禁赌博,常以是垂训而家道隆。”5《邓氏族谱》1983年,藏于东莞市博物馆。宗族无法管制之时,送官究办。宗族与官方互相配合,共同扼制莞邑地方赌博偷盗之风。
3 结束语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礼俗社会[7]。乡规民约式的礼俗可以实现成本最低的社会管理方式。“家训和家法族规,规范人们日用起居,指导人们处世立身。它立足于教化,规范对象不惟是违规者,控制的手段不只是强制力,付诸惩罚的首要目标指向警戒而不只是显示权力。”[8]家族成员间彼此互相熟悉,容易形成情感的联结体。《东莞历代碑刻选集》收录的有关清代莞邑乡规民约的14方碑刻多是族规、祠规和禁令,是基于当时莞邑社会现实提出的对宗族成员的日用起居、行为方式作出的规范和约束,将惩罚与教化两手并用,“以罚辅教”,带有浓郁的宗族社会色彩和莞邑地方文化特色,同时,碑刻文本的背后也蕴藏着当时莞邑地方社会的风貌。
[1]郑德华.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4):71- 82.
[2]张明新.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5):58-66.
[3]叶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J].历史研究,2000(3):15-30.
[4]张渠撰,程明.粤东闻见录(卷上):宗祠祭田[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49.
[5]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464.
[6]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11.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4.
[8]鞠春彦.教化与惩戒:从清代家训和家法族规看传统乡土社会控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4.